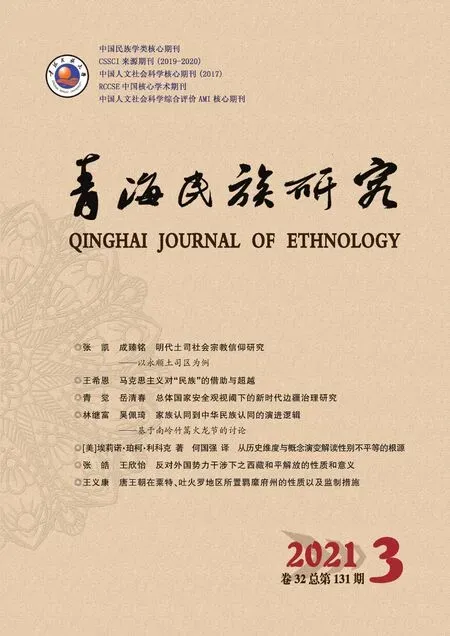明代土司社会宗教信仰研究
——以永顺土司区为例
张 凯 成臻铭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吉首大学,湖南 吉首 416000)
明代的西南地区生活着数量众多、部族众多的族群,就使得该地区在明代成为中央王朝施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地区。明代是土司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不同土司的统治区内管辖着各种族群,这也使得土司区的族群文化多样,宗教信仰多元。以往研究明代土司制度的学者,往往仅关注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政治联系、土司族源的追溯以及土司在土司区内的统治手段等问题,并作出了大量的考证和理论性研究[1][2],却大都忽略了土司史料中关于土司社会宗教信仰的丰富内容。以明代永顺土司的研究为例,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了永顺土司的宗教信仰,但其研究仅说明永顺土司区内所存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以及单独探讨某一宗教信仰在永顺土司区的成因与发展[3],从而割裂了该地区多元宗教信仰的内在联系,缺乏从总体上剖析各类宗教祭祀场所在某一区域内的分布特点的视野,进而无法揭示永顺土司区宗教信仰的总体功能。本研究即以永顺土司境内所分布的祭祀场所为研究对象,阐释这些祭祀场所的修建为永顺土司建立自身与国家稳固的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借此揭示明代土司与国家进行联系的重要手段。
一、“上行下效”:明代土司社会道教信仰的兴起
明代时期,道教在全国的发展有一段漫长但不算艰难的历史。明朝建国之时,朱元璋就认为佛教、道教已与民俗相互渗透,不能完全废除,只有严加管束使得它不至于大肆蔓延才是良策。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待道教是一种“不禁不扬”的中庸态度[4]。但是到了明成祖执政时期,朱棣自认为能够夺取天下是道教神玄武大帝庇佑,故而开始崇尚道教,在皇宫内建造道观,并在武当山兴修道观供奉玄武大帝[5]。而后,明朝历代皇帝均或多或少地推崇道教,至嘉靖皇帝在位时达到了巅峰[6]。明世宗自从继位以来,十分宠信本为道士身份的邵元节和陶仲文,并在他们的劝说下,在皇宫以及全国各地大肆修建道观[7]。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世宗差点在壬寅宫变中被宫女杀死,至此他更加痴迷道教,妄想长生不老[8]。从此以后,明世宗不仅多次花费巨资兴修道观,还对崇尚道教的官员大加封赏,这使得全国的官员之中流行起一片崇道之风[9]。
嘉靖帝的崇道行为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各大土司区。如永顺土司区、容美土司区、播州土司区、河湟土司区等地区都有道教祭祀系统的遗迹[10]。其中,尤以永顺土司区的道教祭祀系统最为完备。根据《永顺宣慰司志》①所载的明代永顺土司区所存在的宗教祭祀场所中,比较典型的道教祭祀场所有玉极殿、崇圣殿以及城隍庙。其实,在永顺土司区,最具代表意义的道教祭祀场所应为祖师殿。按照地方志的记载和如今的考古报告,祖师殿应该是建于宋代,是永顺土司区众多祠庙中最为古老的建筑[11][12]。不过,祖师殿在宋代的功能以及供奉的神位已不得而知,只能确定在土司时期这里也一直是祭祀的主要场所。嘉靖十年(1531年),时任永顺宣慰使彭宗舜对祖师殿的原建筑物进行了翻新,并在这里开始供奉道教的祖师张道陵[13]。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彭翼南继任永顺宣慰使,又以祖师殿为原点,在祖师殿中轴线正后方的第五级台阶上修建了玉极殿供奉玉帝,又在玉极殿右边建造了崇圣殿供奉玄帝[14]。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点,永顺土司区这些与道教相关的祭祀建筑均是在嘉靖年间落成,与嘉靖帝推崇道教的时间背景与社会背景十分吻合。
其实,嘉靖年间汉人社会崇尚道教的风气也引起了一直向化汉文化的永顺土司的关注,并开始在永顺土司社会模仿诸多道教的祭祀活动②。根据《历代稽勋录》记载,永顺宣慰使彭显英、彭世麒以及彭宗舜都有着自己的道号[15]。而在彭宗舜任职期间,不仅重修了祖师殿,还在祖师殿进行了道教祭祀仪式的祈福活动。在现今的永顺老司城考古发掘现场,在祖师殿遗址前悬挂着一口与彭宗舜这次祭祀活动有关的大钟,钟上的铭文记录着这次活动的目的以及主要参与人员:钟面上的文字分为“法轮常转”“帝道遐昌”“道日增辉”“皇图永固”四个部分。在“法轮常转”一条首先感谢了皇恩浩荡,荫封彭氏数代。然后说出了这次祭祀的主要原因在于祈求永顺土司区祖师殿所奉神灵保佑永顺土司区“康宁俗美、岁丰民安”;“帝道遐昌”一条标明这次祭祀的时间是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初五;“道日增辉”一条下则是其余参与这次祭祀的主要人员,身份有信士、把总、管家、头目四类十二人;而“皇图永固”一条下列举了这次祭典的主祭人是彭氏三代土司,即已致仕的彭世麒、彭明辅和在任的彭宗舜;陪同主祭人是各高级土官、土舍三人,低级汉官一人[16]。
从这篇铭文的内容来看,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祈求土司区风调雨顺的祭祀活动,但是铭文透露的另一层信息是,永顺土司此时已经在用汉地道教祭祀体系中的某些仪式在进行祈福:
首先是“法轮常转”“帝道遐昌”“道日增辉”“皇图永固”的条目号。这四句条目号在汉地诸多祭祀场所的碑刻、铭文上均屡见不鲜,常用作祭祀时作为祭祀念词开头的祥瑞之语,可见当时永顺土司对汉地的祭祀仪式模仿的相似度较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句话语本属于佛教祭祀用语[17],唯一的不同只是把“佛日增辉”改为了“道日增辉”。永顺土司这种混淆佛、道用语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汉族社会中佛、道相互渗透合流的影响。在汉族社会中,道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祭祀体系中借用佛教常用祭祀语言的例子十分常见,而这种行为被永顺土司忠实地复制到了永顺土司社会的道教祭祀活动中,并直接反映到了这口钟的铭文上。
其次在于这次祭祀参与的人员基本涵盖了永顺土司社会的所有阶层。这次祭祀的主祭人由致仕的两位永顺宣慰使和在任宣慰使组成,土司区的最高领导悉数出席证明着他们对这次祭典的重视。陪祭人是在任三位土舍与一位汉人经历司,汉人低级官员出席竟能列为陪祭人证明永顺土司对汉官的尊重,也体现永顺土司需要汉官前来参与而体现出这次道教祭祀是由汉人指导,保证了程序的正式性。与主祭人和陪祭人分而列之的是参与人,参与人主要是土目和土民。据铭文所载,这些土目带来了千余名土民参与这次祭祀活动。从规模上看,永顺土司十分重视这次道教模式的祭祀。不过这种道教的正规祭祀活动显然只停留在永顺土司上层社会的模仿之中,未能深入当地土民之中。虽然这次祭祀参与的土民有千人之多,但是其后土目领导或者土民自发在祖师殿进行祭祀的记载并不多见,这一祭祀场所基本上只限永顺土司社会的高层统治者使用[18]。
再次是在参与这次祭祀的人员中,有位身份为“信士”的人。铭文显示他名叫彭世俊,按照字辈应该为致仕土司彭世麒的族兄弟[19]。“信士”专指信奉佛教之人,不过在汉人百姓之中佛道经常混用专有名词,故信士也会表示信奉道教之人。由此可见,当时的永顺土司社会引入道教系统时,一些流行于民间的专有词汇也会一同引入,虽然这些专有词汇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不甚准确,但是在永顺土司的认知里面,只要是汉人社会流行的并与道教信仰相关的信息都会被其忠实地保留下来。
最后是这口铭文钟的构造。这口铭文钟的提梁为蒲牢兽纽,蒲牢双面四爪,抓住钟顶。蒲牢是传说“龙生九子”中的一子,由于喜烟好坐,一般被用于汉族地区的寺院、道观的洪钟之上。提梁之下为莲瓣纹、六道旋纹以及四个十六瓣葵纹,均是汉族地区洪钟之上常见纹饰[20]。可见,永顺土司为此次祭祀而铸的洪钟也高仿了汉族地区的相关器物,其向化汉人礼制之心表露无遗。
由此可知,在嘉靖初年永顺土司区的道教祭祀活动已初具规模,而祖师殿便是这种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但是由于此时的祖师殿是宋代的建筑,而且规模和设施均不能和明朝的礼制相匹配,所以为了应对永顺土司在此处日益繁多的祭祀活动,永顺宣慰使彭宗舜于嘉靖十年(1531年)对祖师殿旧址进行了重新翻修,重修后的祖师殿开始正式供奉道教祖师张道陵。供奉张道陵的原因恐怕是永顺彭氏一直宣扬自己为江西彭氏迁徙而来,所以供奉江西龙虎山的张道陵更能说明自己来源江西的可靠性。并且,从祖师殿旧址建成的年代来看,也与永顺彭氏传说从江西迁来的时间吻合。如此一来,祖师殿即成为了永顺土司今后进行模拟汉人进行道教祭祀的主场所,也成为了自己是汉人后裔的证据。
与祖师殿重修同时间进行的是玉极殿和崇圣殿的兴建。玉极殿供奉的玉皇大帝又称为昊天上帝,是道教里最高的神,而且是明朝法律规定皇帝百官必须定期统一祭祀的神仙[21]。所以彭翼南在修建玉极殿时不但把它修建在了正对祖师殿中轴线的正上方,并且按照典章规定让玉极殿坐北朝南,更便于与天下官员统一祭祀。
崇圣殿供奉的玄武大帝本不是朝廷常祭的主神,但是由于朱棣的个人喜好,全国开始跟风祭祀玄武大帝。到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世宗甚至拨出帑银十一万两翻新太和山的玄帝宫[22]。并且在此期间,永顺土司区附近的永定卫城内也修建了起了供奉玄武大帝的“真武堂”[23],为永顺土司修建这一祭祀场所提供了借鉴。所以到了彭翼南任职期间,便趁着翻新祖师殿,兴修玉极殿的机会一并兴修了崇圣殿供奉玄帝,以迎合嘉靖皇帝的心意。这样,明朝嘉靖年间在永顺土司区的玄武山上便相继落成了祖师殿、玉极殿和崇圣殿三座道教祭祀场所,三位一体的道教祭祀建筑群就此在永顺土司区形成。
除了官方经常祭祀的三大道教场所,民间社会祭祀最为频繁的道教场所当属城隍祠,亦是永顺土司社会引入模仿祭祀的对象。城隍祠供奉的是城隍爷,是守护城池之神。城隍爷并没有特指哪位具体的神祇来担任,而是由有功于各地方的民众精英来充当。城隍祭祀起源于南北朝,滋盛于隋唐,宋朝将其列为了国家祭典的一部分,元代还将全国城隍统封为佑圣王[24]。明朝建国后,延续了前代祭祀城隍的传统,并对各地城隍神按照州县的等级分别赐予王、公、侯、伯四等爵位[25],并在法律上规定了每年祭祀城隍的时间以及祭祀的标准[26][27]。万斯同就认为,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在于“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28]通过明初政府这一系列的规定,使得汉地的民间信仰和国家主导的仪式进行了重新整合,继而形成了一个纷繁但又有序的城隍祭祀系统。基于此,城隍的神性由帝国中央逐步向着全国各地扩散,使得城隍的祭祀成为了一种将国家意识强加于民众的政治运作。但是由于城隍身份的不统一性和地方性,地方民众极易将国家这种貌似隔绝于广大民众的“大传统”与地方信仰层面的“小传统”进行对接,这就使得国家的思想意识借此渗透进了地方民众之中,明朝各地的城隍祭祀行为深受其影响。如此一来,对城隍的祭祀行为便成为了地方恭顺中央的参照标准之一,朱元璋的目的由此得到了实现。
明代的城隍祭祀是国家对汉人社会的一种教化行为,是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地方控制手段,这种行为带有浓烈的强制色彩。但是对于土司社会来说,这种强制性并不存在。不过,永顺土司却自发地在土司区建立起了城隍祭祀系统。因为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区别于自己辖内所管土民的蛮夷身份,更在于与汉人社会无缝对接后,自己的政治权威能无所顾忌地在永顺土司区施行。所以,这造成他们对于国家在汉地推行的神明体系一向采取着主动拥抱的态度,寄希望于通过对国家制度化神明的迎合,来体现出自己与汉人的一体性,这就为国家流行的城隍祭祀体系在永顺土司区扎根提供了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永顺宣慰司志》记载,永顺土司区的城隍祠祭祀的是城隍大王[29]。上文已述,明代的城隍爵位分为四等,“王”是最高的爵位。但是被封为“王”一级爵位的城隍神只存在于明代北京、南京等大型城市所在地区[30][31],并不存在于湖广地区,所以永顺土司所供奉的城隍大王实际上是一种违制行为。不过永顺土司的这种行为并没有受到周边流官的检举,当然也不可能受到国家的任何处罚。可见,中央王朝对待土司社会主动吸纳汉文化的行为采取一种较为开明的姿态。即便在这一过程中,土司做出了某些越轨行为,只要不造成大的影响,中央王朝都不会对这种行为进行追究。对于永顺土司来说,在追求与汉人社会宗教信仰相契合的行为中,除了尽可能地保持与汉人社会祭祀行为的相似性之外,能够使得自己在所模仿的汉人宗教体系中达到尽可能较高的等级也是永顺土司的目的之一。而中央王朝这种行为的“放任”态度,也给了永顺土司游走在制度之外,达到自己对汉人宗教信仰一种尽善尽美的模仿。
由此可见,明代道教祭祀系统在各大土司区的流行与国家的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敏感度极高的各地土司,也在国家大力推广道教的同时,感觉到了这是与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契机,并开始在土司区内大肆建构道家祭祀系统。而对于国家来说,虽然土司社会对内地道教祭祀系统的模仿显得十分青涩,甚至有越制行为,但是作为“异族蛮夷之地”,有这样的向化行为,国家还是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与宽容,以换取“国家在场”的社会效应。
二、“典重明禋”:明代土司社会对农耕神明宗教系统的引入
明朝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本的传统型国家,所以供奉保佑五谷丰登的神明祠庙系统在当时深受统治阶层和基层人民的共同关注。为了突出农耕文化神灵的重要性,明朝政府将与之相关的几大祠庙的祭祀方式写入了明中叶编修的国家行政法典《明会典》之中,名为“正祀”[32]。这就更加带动了明代百姓对这些神灵的追捧,供奉这些神灵的祠庙也成为当时汉地十分流行的祭祀系统,带有强烈的汉文化色彩。这种汉文化色彩浓烈的国家祭祀系统也必然成为了欲与中央王朝有所联系的土司们的模仿对象。如在广西土司地区,就有土司以建设农业祭祀系统为手段,通过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获取地方控制权的事例[33]。而在永顺土司区,也坐落着福民庙、稷神坛以及社令坛三大农耕文化神灵的祭祀场所。在明代,它们也是一心向化汉文化的永顺土司重点建设的祭祀系统。
根据《永顺宣慰司志》的记载,福民庙供奉的是五谷神[34],那么它的职能就和汉人地区的五谷庙类似。而五谷神在明代中央王朝的官方称谓中,本来称为稷神。明代稷神被国家定为大祀,祭祀仪式十分正式,祭祀活动必须皇帝亲躬,并由文武百官陪祭[35]。后来,由于稷神是掌管农业的神祇,地方民众对其供奉祭祀亦十分频繁,五谷神祭祀开始从稷神祭祀中脱离出来,变为民间自发的一种祭祀活动。基于此,中央王朝开始对各地的五谷神祭祀活动统一规范,并深入到基层的村社之中:
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时。若五谷丰登,毎岁一户轮当会首,常川洁净坛。遇春秋二社,预期率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烛随用。祭毕,就行会饮。会中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并不许入会。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坐,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36]
由此可见,明代地方祭祀五谷神不但随处可见,并且有了成套的规约,这些规约使得祭祀五谷神的行为不仅仅在于对神明的恭敬,更在于维护了乡村的和睦,达到了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的目的。国家对五谷神在民间祭祀的规定,在民间得到了很好地执行。究其原因,在于以农耕生计方式为主的汉人社会对粮食丰收的愿望十分强烈,所以五谷神在汉人社会的信仰空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离永顺土司区不远的沅陵县在明代对五谷神的祭祀活动,便是基本按照国家规定所进行:
五谷坛:各乡村每里一百户可立坛一所,以岁仲春、仲秋月上戊日致祭。祀五谷神,五土神,风云雷雨之神。每位:帛一,爵三,铏二,簠一,簋一,笾八,豆八,羊豕各一。祭毕,会饮读誓等仪,从制。[37]
沅陵县的基层村社对五谷神的祭祀活动除了对祭品有些许改变之外,基本与国家典章制度的规定相同。可见,明代五谷神的基层祭祀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沅陵县在明代是辰州府的府治,该地的儒学曾有一段时间为永顺土司应袭舍人的就读场所[38]。那么永顺土司的这些继承人在就读期间就有可能接触到与五谷神相关的祭祀内容,这就给五谷神的祭祀在永顺土司区的开展提供了契机,福民庙也相应在永顺土司区落成。
对于有心模仿汉人祭祀活动的永顺土司来说,五谷神的祭祀活动也起到了祭祀神明以外的功能。《永顺宣慰司志》将永顺土司在福民庙进行祭祀五谷神活动的过程详细地记载了下来,为我们对比永顺土司祭祀过程与汉人祭祀过程的异同提供了依据,也揭露了永顺土司怎样通过五谷神的祭祀活动达到凝聚永顺土司社会人心的目的:
福民庙在白砂溪内,原祖建祠以祀五谷神。每年正月十五日传调合属军民于鱼渡街州上摆列队伍,以伺亲临点阅后,躬诸本庙参谒。令巫人卜筶,一以祈当年之丰熟,一以祈合属之清安。至十月十一仍照前例报答本年丰稔宁谧,岁以为常。[39]
从永顺土司的祭祀过程中可以看出与汉人祭祀五谷神的三大相似点。其一是在祭祀的时间上,汉人的祭祀时间是在春秋两季,这也是农作物播种和收割的两个节点。而永顺土司的祭祀也分为正月十五与十月十一两季,正月向神明祈求丰收,十月报答神明所带来的丰稔宁谧。虽然两者祭祀的具体时间可能不尽相同,但是祭祀的目的和祷告的内容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其二是在祭祀参与的人员上。汉人社会以里社作为单位,祭祀之时如约相聚,进行祭祀。永顺土司社会以土司辖下军民为单位,聚于渔渡街,由土司亲自点阅后集体前往福民庙祭祀;最后是在祭祀过程中均会有人执行祈祷的仪式,并宣读祷文、誓约。
不过,永顺土司社会在进行五谷神祭祀时并不是完全生搬硬套汉人社会那套祭祀方法,也将自身的某些民俗特点融入了祭祀体系之中。首先在祷告的人员以及祷告的内容上,汉人社会派出的是普通的里社成员,所宣读的内容更像是乡里规约,而不是神仙咒文。这体现了汉人社会对五谷神的祭祀目的着重点在于通过对神明的恭敬来维持里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反观永顺土司社会的祷告人员却具有神秘身份,是被广大民众认为能沟通人的世界与神仙世界的巫人完成。其祷告的内容也只是简单地祈求五谷神能够赐福于永顺土司社会,将永顺土司区一年的风调雨顺、社会安宁寄托在神仙的庇佑之上。这体现了永顺土司社会的农业生产水平较汉地还十分落后,农业生产技术还不足以战胜某些自然灾害而达到旱涝保收的效果,只能在精神上寄托于神仙的保佑。
永顺土司社会的五谷神祭祀不同于汉人社会的另一特点是在参与民众的动员形式上。汉人社会祭祀之时是“约”聚祭祀,是一种自愿参与的形式。当然,祭祀活动的参与人即是祭祀誓言的盟约人,虽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故而基本上一里社成员均能到场参与祭祀。而永顺土司社会却是土司传调合属军民于渔渡街等候土司点阅,点阅完毕未有缺额之后一并前往福民庙祭祀。“传调”是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用语,这源于永顺土民的军事性质。这也说明了永顺土司社会的五谷神祭祀的参与是一种带有军事强制性质的活动,土司通过这一活动将宗教信仰仪式和军事阅兵仪式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说,五谷神祭祀活动的进行不仅使永顺土司控制了永顺土民的精神世界,也使得永顺土司在土司社会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可见,永顺土司在模拟汉人社会的祭祀行为时,会有意识地加入土司区的民俗和政治要素,以求使祭祀过程在基本维持汉人社会的特点之上拥有一定的本土化效果,以便达到永顺土司通过祭祀活动掌控永顺土民的目的。
永顺土司这种对汉人祭祀活动的模拟与改变也体现在了稷神坛和社令坛的祭祀行为之上。从上文可以得知,稷神坛和福民庙的祭祀对象是一致的,五谷神就是明朝官方所说的稷神,而社令坛祭祀的是掌管土地的社神。土地种植五谷,五谷丰登方能国泰民安,这使得社神与稷神是历朝历代地方政府祭祀活动的重要对象之一。明朝建国,统治者对社、稷二神的祭祀活动十分重视,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颁布了社稷坛制昭告天下,各州、府、县城内必须设立一定规制的社稷坛,并于春秋二仲月由地方最高长官率辖下官员百姓前去祭祀。如此一来,国家将对社稷二神祭祀制度化,在民间有了不小的推动。
正是在政府推动和民间流行的双重作用下,永顺土司也开始在土司区内修建社令坛和稷神坛对社稷二神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不过祭祀过程却透着强烈的民族风味:
社令坛,在司治东南那乃浦岸,每年遇春秋二社稚牛以祀,原无祠;稷神坛,在锡帽山前,原有坛,每年祈祀其神,常有人见穿红袍戴乌幞头。[40]
根据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知道,永顺土司也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在春秋两季对社稷坛进行祭祀,不过在祭祀的祭品与主祭人上与汉地有明显的区别。明朝在社稷坛制中规定的地方政府进行祭祀所应陈列的祭品中牲口只有羊和猪,并没有规定牛,牛作为祭品只存在于国家级的祭祀活动中,而永顺土司祭祀时是“稚牛以祭”。汉人地方社会不用牛作为祭品的原因在于其农业组织化程度较高,牛是相当重要的生产资料,在明代如若私自宰牛,甚至要受到法律的制裁[41]。而对于生活在山区的永顺土民来说,猪、羊不是易于饲养的牲畜,再加上土司区农业组织化程度较低,牛对于永顺土民来说并不是必备的生产资料,故而在祭祀时使用了牛来代替猪羊作为祭品来进行祭祀。另外在祭祀的人员上,常人所见的“穿红袍乌幞头”之人恐怕身份与福民庙祭祀时的“巫人”类似,也体现了永顺土司社会生产力在明代还较为低下,依然有巫人崇拜的现象,所以由巫人把控着主祭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社令坛的祭祀活动和福民庙的祭祀活动均在春秋两季,很有可能这两项祭祀活动是同时进行的,这也是汉人社会的常例。这使得福民庙的祭祀功能逐渐代替了稷神坛的功能,所以造成了上面史料所述的稷神坛“原有坛”,而后来由于在福民庙进行稷神的祭祀而荒废无坛的结果。
综上所述,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使得土司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制度上更近一步。土司们只有加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才能拥有地方管制的“合法权”。在这一背景下,中央王朝意识形态所主推的信仰体系会成为诸土司主动引入土司社会的对象。尤其是在农耕社会中,农耕文化神灵的祭祀显得尤其重要,也是诸土司重点引入模仿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土司们尝试着将宗教象征体系与自身权力体系融为一体,就此使得自己的权力空间达到最大范围。不过与之相对的是,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祭祀系统在土民中流行,实则加强了国家在土司区的支配力。
三、“渐染风化”:明代土司社会对内地其它宗教系统的模仿
在明代,除了道教祭祀系统和农耕文化系统在内地民间十分流行之外,佛教系统以及诸多地方神系统也有一定的推广空间,国家对这些宗教祭祀系统的态度是,只要不扰乱社会稳定,依然给予十分宽松的发展空间。土司社会是一个多元族群文化并生的地方社会,在这些文化多样性的区域,必定孕育了多种地方信仰体系。这些地方信仰体系,有些是对周边汉地民间信仰的模仿,有些则是自身传统信仰的国家化。如在广西浔州府地区以及湖北的容美土司区均出现了汉地信仰“土司化”以及地方信仰“国家化”的案例[42]。而对于永顺土司社会来说,土司区内有观音阁和伏波庙两座祠庙独立于道教祭祀场所和农耕文化神灵祭祀场所之外。观音阁是典型的佛教祭祀场所;而伏波庙则是一个极具地方色彩的祠庙,并且供奉的神主身上透露出了儒家文化一点或者多点的优良品质,深受永顺周边的汉人社会推崇。
永顺土司区的观音阁为彭翼南所修,供奉的主神为观音大士[43],根据现今的考古报告确为明代建筑[44]。佛教本不是明朝历代皇帝所喜好的宗教,但是在汉人民间地区十分流行。明代的永顺土司区离汉地较近,一些汉地流行的宗教信仰较容易传入土司区,如明代永顺土司区周边的九溪卫麻寮所便兴修了一些寺院[45],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着永顺土司修建了一些佛教祭祀场所,故而在永顺土司社会尤其是统治阶层应该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崇尚佛教。虽然佛教信仰与皇家流行的道教信仰并不契合,但是它也是汉人社会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建立佛教的祭祀场所并且模仿汉人祭祀行为也是贴近汉人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此一来,在永顺土司区修建一座拥有佛教祭祀功能的建筑就成了必然之举。虽然没有直接史料证实当时永顺土司社会的某些人群在观音阁进行过大规模的佛教祭祀活动,不过从现今的考古报告来看,这座高达两层,占地约两千平方米的巨大建筑绝对不可能修建之后在当地弃之不用[46]。可以想象,当时观音阁香客众多、香火鼎盛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观音阁并未和老司城其他类型的祭祀祠庙建筑群修建在一起,而是修建在距离这些祠庙群三里之隔的另一座小山包之上,这座山包也由于观音阁的修建而改名为“石佛大士”[47]。可见明代永顺土司在修建这些祠庙之时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内地的宗教祭祀系统,而是能够分辨不同宗教系统的区别,从而划区建设这些祭祀场所。
伏波庙在永顺土司区的修建亦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伏波庙祭祀的是东汉名将马援,因被东汉光武帝封为伏波将军,故其祠庙被称为伏波庙。其实,东汉时期,马援就是死于南征五溪蛮的途中,才被人以忠烈为名,立祠庙祭祀。也就是说,马援本是征讨永顺土司区先民的将领,应该算是永顺土民的“仇人”,但是永顺土司亦能接受对他的信仰崇拜并修建庙宇对他进行祭祀。这其中展现了明代永顺土司急于洗清自身蛮夷血统,向化中央王朝的渴望。
明初,朱元璋将祭祀活动分为大、中、小三级祭祀。大祀必须皇帝亲力亲为,中祀和小祀才由地方官员带头致祭[48]。而对前代功臣、忠义以及名儒的祭祀属于小祀,理应由各府州县地方政府承祀[49]。不过,由于前代的名人数量实在太过庞大,如全部由地方统一祭祀,经济压力实在太大,所以在正德年间根据各名人的籍贯以及所立功勋的地点,将他们的祭祀划归各自地区分而祭祀,以减轻祭祀的财政压力。而明代马援的祭祀地区正是永顺土司区所在的湖广地区[50]。
按照明朝法律的规定,各司在进行祭祀活动时,其下属的州县文官必定到场一同祭祀,但是武官不再要求之列[51]。永顺土司在明代由湖广都司统领,所以每年湖广布政使带领相关官员进行祭祀活动之时不一定要前往参与。不过,由于永顺土司对汉文化的向往之心,使得他们不止一次自发前往祭祀活动现场进行陪祭。如在彭世麒和彭宗舜的墓志铭中都有他们与一些府州县官员、士大夫交往甚密,并受邀参与州司祭典的记载[52][53]。由此可见,永顺土司在观摩了省级地方官员正式祭典的宏大场面后,心中产生了对这一礼制模仿的想法。而马援战死的地点正是永顺土司区所在之地,这就给了永顺土司一个立庙祭祀的理由。这不仅让马援征剿五溪蛮的历史事实没有成为永顺土司祭祀马援的阻碍,还能使他们利用这段历史祭祀马援,以歌颂马援征蛮的这一行为,更能让自身划清与永顺蛮夷先民的界线,淡化自身在中央王朝心中蛮夷印象,以表达其忠顺于朝廷的心意。
其实,这种借国家意识形态的伏波文化,将自己边缘身份推向正统的模式,也广泛存在于明清时期的广西地区[54]。可见,无论是国家宗教系统的地方化,还是地方信仰系统的土司化,最终不但使得土司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更表达了诸土司向化中央王朝主流文化,加强与中央王朝关系的愿望。因此,土司时期的土司信仰文化并没有强烈的排外性,与之相反,是极具弹力与包容性的。
四、结 语
宗教信仰是某一区域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基础,是该区域领导集团维系其统治的重要社会行为。以明代永顺土司区为例,该土司社会拥有着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宗教信仰体系。除了有本文所述的各种祭祀系统外,还掺杂着八部天王以及吴着祠等当地民间宗教信仰所供奉的祖先神灵。可以说,明代永顺土司社会的宗教信仰是一个以国家公推的儒、释、道信仰为基础,当地民间的鬼、灵、巫信仰为辅助的综合体系。出现这种奇特宗教体系的原因在于,明代诸土司要对国家展现其向化汉文化之心,表现出谦恭的一面,以得到国家的信任与嘉奖,加强与国家的联系,突出自身统治土司区的合法性,以改变自身在中央王朝眼中蛮夷的印象,展现了自身身份建构的动力与张力。而诸土司对当地土民亦要加强精神统治,所以他们又将汉地的宗教信仰由土司上层推广到整个土司社会,从而在土司区修建起一大批汉地常见的祭祀场所,以供土民祭祀。但是,这种对汉地宗教信仰的引入又不是一种照搬行为,他们一方面在祭祀仪式中替换了当地客观物资条件不允许的祭祀贡品;另一方面又结合当地土民农业组织化度低的特点,将主持祭祀的人员由乡约里正换成了有着深厚群众基础以及信仰度的巫人,以提高土民的参与度。土司们就此很好地将本土性生态知识和地方传统民俗融入了新引入的宗教信仰之中,完成了国家宗教地方化的运作。如此一来,在土司社会中,不但有国家“大传统”的扎根余地,又不至于使得当地“小传统”失去发挥的空间,从而提高了诸土司在土民之中的威信,巩固他们在当地的统治基础,更好地维护了地方稳定。
注释:
①《永顺宣慰司志》是一本土司时期流传下来记载明代以及清初时期永顺土司社会状况的史料。根据乾隆十年(1745年)所修的《永顺县志》记载,该司志成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一彭姓土官所修,志中内容尤详记顺治初年前后永顺土司社会之事。虽然该书编写之人已不可考,但是就书中作者对永顺土司社会各方面状况的熟悉程度来看,该作者应是生活于永顺土司社会上层,并深知这里的历史和运作状况。其中,该书第二卷“祠庙”条记载,顺治初年永顺土司区所见的祭祀场所共有十座,除了八部庙和吴着祠之外,其它的祠庙均能在汉地经常见到。就顺治初年当地便有如此大规模的多元祠庙系统来看,这些祭祀场所应于明代兴建,并保留到了清初。也就是说,该书记载的明代永顺土司区类似汉地的宗教祭祀场有八座之多。
②瞿州莲、瞿宏州认为,永顺土司社会崇尚道教的其他因素还有他们的“巫”文化传统和永顺土司短命的社会现实。笔者认为,永顺土司区的巫文化与国家的道教文化属于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接受巫文化不一定会接受道教文化。当然,永顺土司在进行道教祭祀活动时或多或少的会融入一些当地巫文化的文化因子,但这也不能证明永顺土司引入道教文化是因为当地的巫文化在起作用。而关于永顺土司短命现象造成道教在永顺土司区盛行的观点,笔者认为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道教大规模流行始于彭宗舜执政时期,虽然从彭宗舜开始之后三代的永顺土司确实都很短命,但是彭宗舜的父辈以上的寿命都较长,彭宗舜是不可能因为他父辈以前的寿命问题而崇尚道教,也不可能提前知道自己以及子孙寿命的寿命很短而开始崇尚道教。所以说,道教在永顺土司区兴盛的关键原因就是永顺土司投明朝皇帝之所好,在永顺土司区广泛修建了道教祭祀场所。请见:瞿州莲,瞿宏州《道教在明代永顺土司的兴盛及成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