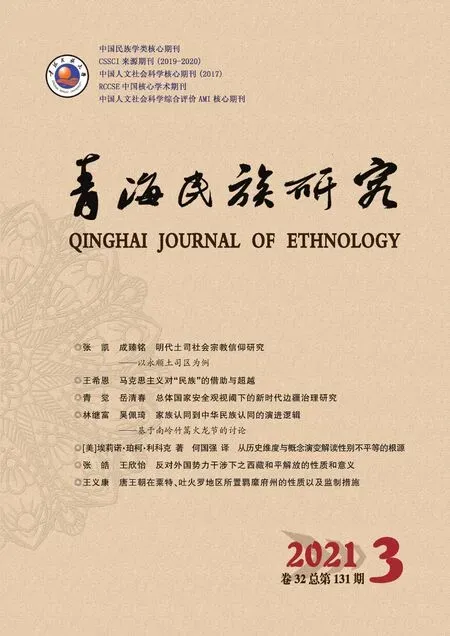张其昀的西北行及其西北开发思想
杨红伟 刘 洁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张其昀(1901—1985年),字晓峰,浙江鄞县人,著名史地学家、教育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者。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深受刘伯明、柳诒征、竺可桢等人影响,尤以柳诒征的影响为甚。[1]由此,张其昀确立了毕生从事中国地理研究的学术道路,强调用西方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实地考察中国地理,特别是要聚焦于区域地理研究。他主张“区域考察者,即指一定区域,作深入的地理研究,愈能直接观察则愈佳,此即所谓‘实验的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或曰客观的方法,或曰积极的方法,亦即所谓科学方法是也”[2]。1934—1935年,张其昀赴西北考察,不仅是其区域地理研究思想的一次重要践行,也使其从地理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先见性的西北开发主张,成为彼时国民政府进行西北开发设计的重要知识依据。①在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潮中,张其昀至为关键,代表着用科学的方法代替传统经验的考察,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西北开发主张由传统向现代转向的趋势,不仅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专门从事张其昀研究者也未曾关注其西北考察及相应成果。②故有以西北考察为主要线索,检视张其昀西北开发思想之必要。
一、张其昀西北考察的缘起与经过
1928年底,北伐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仍然斗争不断,尤其是蒋冯矛盾日益突出。1929年5月15日,西北军将领刘郁芬、孙良诚等人通电表示反蒋,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3]10月10日,冯玉祥令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27人通电反蒋,发动了第二次反蒋战争。为此,蒋介石的理论家戴季陶提出,革命的目的“就是大家要在三民主义之下团结起来、觉悟起来,共同努力于开发中国、建设中国、发扬中华文化、发展中国的事业与中国的富源,完成中国社会国家的建设”,因而中央应“下最大的决心荡平这般西北反革命的叛军”,“荡平西北叛军是救济西北野蛮、创造西北文明、复兴西北文化的第一步”。[4]此实乃国民政府欲假借“建设国家”“开发西北”的口号,达到消除冯玉祥西北军在西北的势力,完成其权力统一的目的。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西北军被瓦解,国民政府的势力得以进入陕甘地区,西北地区的建设事业提上日程。在中原大战结束前夕,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于1930年7月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之后,建设委员会又于1931年5月制定了《开发西北计划大纲》。但直至“九·一八”前,“蒋介石国民党事实上将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剪除异己和围剿南方的工农红军,并未真正把开发、建设西北当作‘要务’,因而其开发、建设西北的种种计划和决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社会影响微乎其微”[5]。“九·一八”后,东北沦陷,国难日益加剧,国人“痛念外患进逼,而国家无后方,无退路”[6],西北开发的呼声甚嚣尘上。为加强国防,恢复国民经济,国民政府逐渐开始从实际落实“开发西北”的口号。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于1932年11月1日创设国防设计委员会。
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发起之初,有着较大的政治考量。据钱昌照称,他提议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首先考虑的是增强国防力量,发展工业化,抵御外侮,“我一向高唱中国工业化,对蒋介石存有幻想,认为蒋介石大权在握,如果他能支持工业建设,事半功倍”;而蒋介石同意设立此组织,则是想“拉拢那些银行家、实业家、名流、学者作为招牌以取信人民”。[7]该组织成立后,蒋介石于11月29日将组织草案向国民政府备案,称:“值兹国难当前,国防机务,万端待理,为集中人才,缜密设计起见,特设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期确定计划,从事设计。”[8]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主要组织为3处8组。3处分别是秘书处、调查处、统计处。8组分别是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及财政、原料与制造、运输与交通、文化、土地及粮食、专门人才调查。据钱回忆:“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委员绝大多数是在蒋介石所批准的由我提出的名单中挑选的。”[9]钱向蒋呈交的名单有四五十人,其中“教育文化方面:胡适、杨振声、傅斯年、张其昀等”[10]。国防设计委员会所设委员中,“都是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实业家,可谓一时之选”,“他们大都未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任职,不仅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过去经常对当政者发表一些批评言论”。[11]
张其昀在中国地理学上的造诣及其相关政论性文章,颇受国民党高层的重视。1923年张其昀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此后四年间,张醉心于编写地理教科书。其编撰的高中《本国地理》,竺可桢审阅后,经教育部审定,于1928年6月发行,之后至少又发行了17版,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地理教科书。[12]此间,张其昀还发表了《方志之价值》(《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4期)、《南宋都城之杭州》(《史地学报》1925年第3卷第7期)、《金陵史势之鸟瞰》(《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13、15期)、《人生地理学之态度与方法》(《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等地理学研究的文章。故于1927年受聘国立中央大学,主讲中国地理。此后,张其昀围绕首都问题、中日关系发表系列文章。如,1927年5月发表《中国国都之问题》一文,主张应迁都南京[13];1928年3月发表《首都之国防上价值》,提出“今后中国的国防,将是以北平、兰州为二基点,以南京为定点,而形成一大三角形之形势”[14]。此外,还有《首都之地理环境》《首都之新气象》《论中日两国经济的关系》《山东问题与民族前途》等一共15篇文章,引起了国民党上层的注意。[15]1930年12月9日,陈立夫、余井塘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递交提案,称张其昀“阐扬党义、擘划建设均能深中肯綮”,故提请特许加入国民党。[16]张其昀以学术成就逐渐积累出的知名度,使其被推荐为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并被批准。
“九·一八”之后,西北战略地位凸显。政府与社会各界为推进西北建设,组织了一些考察团赴西北考察。如,1927年至1933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主要调查地区为内蒙古、新疆,考察涉及地质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气象学等内容。又如1932年8月,陇海铁路管理局聘请国内各方面的专家40余人,组成陕西实业考察团。该团分为南北两组,每组又各分为农林、矿产、水利、工商、交通、经济6部分。[17]然而,此时的西北考察,或囿于某些专门领域,或限于某些专门的地区,未能形成对西北区域的整体认知,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西北开发方案。故著名的西北问题专家马鹤天在开发西北协会第二届年会上称:“年来谈开发西北的人故多,但实际到西北的人太少,情形不明,致多阻阂,不特无益,反生障碍。”[18]因而,在“自‘九·一八’事变以还,东北失陷,强敌压境,曩者认为荒凉不堪之西北,今乃成为中华民族之一大生命线。于是开发之热潮,沸腾海内,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种种事业,经纬万端,靡不各抒言论急待改进”[19]的形势下,政府迫切需要继续组织专业人才对西北,尤其是未详细调查过的甘青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详细的考察。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研究东北、西北、西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问题”[20]。为此,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组织了西北调查团,“分为五队,分任水利测量,地质矿产,垦牧及民族,农作物及移垦与人文地理五项调查事宜”[21]。张其昀负责人文地理调查。张其昀进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后,除仍兼中大地理系教授外,1932年11月还兼任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科学的中国》总编辑,并于1933年与竺可桢、翁文灏等人筹办了中国地理学会。张其昀一贯主张实地调查对地理学的重要意义:“夫地理之学,职在表达地面上实际情形;图书虽极优美,顾其所载天然景象,终难免于隔膜。故实地考察为地理学必经之步骤。”[22]因而,张其昀于1931年6月27日至8月19日进行了东北考察,期以“在东北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收集可以利用的地情资料,如军用的大比例地形图等等,并考察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的势力与动向”,调查万宝山事件。[23]经过考察,张称东北“形势异常险恶,尤其是安沈、南满二路,本是中国领土,但我们沿线考察,竟受到不应有的许多麻烦”[24]。1934年3月24日至5月7日张其昀又进行了浙江考察。两次考察不仅使张其昀进一步将西方地理学的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结合在一起,也为其西北考察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
张其昀偕同任美锷、林文英、李旭旦三名刚从中大毕业不久的学生,自1934年9月10日出发赴西北考察,至1935年8月6日返回,历时近11个月。张其昀曾将西北划分为三部分,即“(一)近西北;(二)远西北;(三)外西北。近西北为甘肃、陕西、青海、宁夏、绥远五省。远西北为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科布多、新疆、西藏。外西北则在新疆以西,包括中亚西亚之一部。……现时一般所谓之西北,殆多指近西北而言”[25]。而其考察的重点,则为近西北:“西北旅行,达一年之久,以兰州为中心,循河西走廊至敦煌,南越秦岭山脉至汉中,北上蒙古高原至绥远北部百灵庙,又曾到青海大湖边上及甘肃西南隅拉卜楞喇嘛寺,尤以乘皮筏看惊心动魄的黄河峡谷,印象深刻难忘。”[26]具体行程为:1934年9月10日上午从南京出发,晚抵徐州。[27]11日沿陇海路西行,经潼关于14日下午抵达西安。[28]在西安考察约20日后,于10月6日到兰州。在兰州停留数日后,又于21日抵夏河,后返回兰州。12月25日到达天水。[29]1935年1月9日由天水赴陕南,经徽县、两当、凰县、留坝、襄城、汉中直抵城固,复由城固折回汉中,经过沔县、略阳、徽县、成县、西和至礼县,后由礼县于2月11日转回天水,13日赴甘谷、陇西等地考察后,26日返回兰州。[30]4月7日赴青,随后转往敦煌、玉门[31],于5月7日返兰。[32]后于6月30日赴宁夏。[33]再由宁夏赴百灵庙一带调查,经北平而返回南京。[34]
二、西北地理环境、富源与开发价值
张其昀西北考察的主要对象是陕甘青等地的“天时、地利、人和及其相互关系”[35],以为推进西北开发计划提供资料。由此形成了张其昀西北考察的特点,偏重人文地理,但又重系统性:“西北开发”应注意其科学性质,如“西北的地形是怎样?气候是怎样?水利是怎样?可垦殖的区域是那几处?输出原料那几项最丰富?地下宝藏那几项最重要?西北人民的生活状况,及种族宗教语言的歧义,又是怎样?”[36]均需调查研究。此种研究以张其昀曾为《方志》杂志组织的“拉卜楞专号”最为典型。其内容涉及拉卜楞寺及其所在区域之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生计、地理、实业等诸多方面,可谓立体之介绍,以期“为言开发西陲、复兴民族者涓埃之助”[37]。由此可见,张其昀西北考察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发掘西北开发潜在价值,形成科学认识,助力国民政府实施西北开发计划。
首先,张其昀真正从地理学的意义上,将陕甘宁青三省划分为不同区域,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各自的特点及其经济地理意义。地理学家无不重视地形地貌的分布与变化,盖其对地表空间单元的影响最大。因而,张其昀首先根据地形将各省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分别介绍其空间特点。如他将青海划分为四区:河湟青海区,“黄河、湟水及大通河两旁谷地,为三千公尺以下之冲积地,土质较腴,为青海省精华之区,古称湟中之地是也”,“青海区,包括青海周围及布喀河流域,地形平坦,无山陵之起伏,弥望草原,为畜牧所宜”;柴达木区,“为环绕于群山中之广大盆地”,“盆地中部湖沼四周,地势低洼,则为沮洳之地”,“盆地北部,戈壁面积,尤为广大”,“盆地周围接近山麓较为高旷之处,则为水草丰美之区”;祁连区,“峰峦重复”,“平行山脉间概成纵谷”;高山区,“柴达木盆地及河湟区之南为高山区”,“重峦叠嶂,绵亘千里”。[38]又将甘肃划分为陇坂区、河西区、蜀山区、草地区,宁夏划分为平原区、高山区、高原区和戈壁区,陕西划分为陕北高原、渭河平原、秦岭山地、汉江平原与大巴山地。
紧接着,张其昀结合土壤、气候等因素分析其经济影响。如,他认为甘肃陇坂区“东连陕省,西迄临夏,南届嶓冢,北达永登,居甘肃之中部”,“地形显著之点,约有三端:一曰破碎高原,二曰台地之发育,三曰平原之狭隘”,“本区平原虽范围甚狭,然因有灌溉之便,农业甚盛,人口最密”;陇坂区黄土弥漫,土壤易受侵蚀,且“土壤既非甚肥,而雨量缺乏,灌溉又不可能,农业全赖天雨,收获常不可靠”。[39]如其陇东一带“山多于田,平原甚少,所有田地均在沟岔山谷之间,东鳞西爪,不成片段,既不便于工作,又苦于山高水缺,各乡水田不及1%,全恃雨水调匀,以资播种”[40]。宁夏平原区包括中卫平原、中宁平原与宁夏平原,“灌溉之利最溥”,“土壤多为粉砂壤土,颜色不一,尤以淡灰棕色为最普通,开渠灌溉,农业甚盛”,“全省七十万人民衣食生活之资,端赖于此;谚云‘天下黄河富宁夏’,良有以也”。[41]张其昀首次从科学的意义上,对陕甘宁青四省区从地形、土壤、气候、水文等方面,进行了区域分类。这不仅为科学认识西北自然环境特点奠定了基础,还为制定西北开发相关政策与措施建立了初步的条件。
其次,张其昀以实地考察为依据,对西北经济发展滞后尤其是对农村经济凋敝、商业经济困顿等原因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二十世纪30年代,陕甘宁青经济凋敝、灾害频仍、兵连祸结,导致农民流离失所,人口锐减。据张其昀观察“近年以来,甘肃兵匪交祸,荒旱连年,人口死亡,逾四百余万,灾情之重,亘古未有”,“甘肃近四年间死于天灾人祸者,约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42]除了分析苛捐杂税[43]、高利贷盘剥[44]、政局动荡[45]等时人常论之因素外,张其昀特别注意从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等方面进行学理的分析。关于自然灾害,他注重从地形、土壤与气候综合作用的结果上进行分析。如甘肃“平原既狭,灌溉水量复缺,大部农田,全属旱田,仰泽于天,每年收成之丰歉,胥视雨水之充沛与适宜与否以为断,甘肃大部雨量稀少,且逐年变化极大达百分之三十以上……春雨为作物下种萌芽所必需,而本省春夏之间,雨泽稀少,降雨愆期,常使夏禾歉收,秋禾难于播种。因此甘肃各处旱灾时起,俗有‘十年九旱’,‘十种九不收’之谚”[46];“陕西全年雨量之半数降于夏季,占全年雨量的百分之五十。春季约占百分之十八,秋季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冬季仅占百分之七。……惟陕西雨量变率甚大,农常苦旱,动辄成灾,有十年一大旱、五年一小旱之称”[47]。
同时,张其昀通过对西北地区生产方式的分析,指出了造成西北经济落后,特别是抗灾能力低的根本原因。农业方面,“西北各地农业经营颇为粗放,青海亦不能例外,大概青海每亩田地之生产量平均不过五元之收入”,甚至玉树札武三族“随意耕种,各不相连,亦不方整,且岁易其处,甚至一易再易,间有用马粪为肥料,永不锄草,藏民于农耕极为漠视不知改良,故收获量甚属有限”。[48]工业方面则工艺幼稚,机器工业少而手工业多,如“甘肃远处西陲,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工业殊不发达,所有工艺大率规模狭小,全用手工,出品因运费浩大,多仅能出售临县,不能远销”[49]。畜牧业方面则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如“青藏人民之圈养牲畜,皆无畜舍之设备,日夜露宿,若遇霔雨,因无厂舍可避,难免冻馁之苦,最易消瘦”,“牲畜较多之游牧族,春时常有牧草不足之感,牲畜老弱者,死亡殊甚,此为仅持游牧而不知种植牧草以补不足之害”,且“牲畜传染病发生,因蒙藏人民缺乏兽医知识,往往蔓延甚远,死亡枕籍,影响于蒙藏人民生计至巨”。[50]至若贸易,则既受制于交通不便,难以畅销,如“宁夏制造各种裁绒花毡,最为精细,惟质厚而重,运费太昂,未能远销,故亦未甚发达”[51];又因落后的贸易制度大受局限,如青海“蒙藏人民之交易,尚在以物易物时代,货币不甚适用”,故“青海贸易,较内地苦难数倍”。[52]
再次,实地考察与客观分析,使张其昀对西北开发的前景抱着科学的乐观态度。如在农业方面,他认为西北虽然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但如能积极改进生产,即可克服艰苦环境,并且可对高地农业发展提供经验。张其昀称:“有人对于西北很抱悲观,以为地势高雨量少,农业前途殊少希望……但如河套宁夏等局部平原,以及甘肃的平凉一带,青海的湟水流域,皆便于灌溉,适于屯垦,所谓足食足兵,是确有把握的。况且中国农业,向偏重于平原,对于高地缺乏经验,现在正可借开发西北之机会救中国农事的缺点……我相信教育如有办法,生产力如能改进,西北的环境不难逐渐克服的。”[53]而西北丰富的资源,则给张其昀以更大的信心。如关于药材,他介绍,青海药材“种类甚多,麝香、鹿茸、犀黄、人参,其最贵重者。大黄、枸杞、红花、甘草等品质亦称优良”[54];宁夏“素称药材重要产地……如枸杞、甘草均为医药上不可缺少之品”[55]。在林木方面,他指出“西北高原之上,复有崇山峻岭,如祁连山及洮河上游之登山,长林丰草,均为著名林区,苟造伐有道,则材木不可胜用,而珍贵山货,品类实繁”[56]。在矿产方面,张其昀认为西北更富开发之价值。如,“能促进交通便利之石油适多产在西北。如陕西之延长,甘肃之嘉峪关、玉门一带均富蕴石油,如能尽量开采,则其效果将转移西北之面目,成为中国之煤油大王……将来西北之经济革命,恐以西北石油之开发为起点也”;如“西北产煤丰富,不仅可供西北之用,晋陕二省之煤田竟占全国总量五分之四,其重要可以想见”[57];再如西北盐资源丰富,青海湖“西二百余里,又有盐池,盐产丰饶,称为青盐,与阿拉善之吉兰泰盐池,均为西北名产”[58],宁夏“盐产之富,甲于西北,所产之盐,纯属池盐”[59]。
2.男:五虎上将关云长,一心麻保汉刘王(一心来保汉刘王),同鸟桃园三结义(同在桃园三结义),押培笨尧困麦城(你别弃我困麦城)。
复次,张其昀认为区域地理的研究强调的是人与空间的系统性互动,因而鉴于西北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其西北考察尤重视对前人关注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调查。如在甘肃,他特别重视对甘南涉藏地区的考察,称“甘肃省会以外,大致可分四区,陇东、陇南与河西诸名,习用已久,惟西南部各县似无专名,兹拟以洮西名之”,“其范围则东有鸟鼠山,西有西倾山,北为积石,南为叠山”,“是区在汉时已入中国版图,但乍得乍失,其地理状况迄今犹未尽晓”。[60]张其昀认为该区国防地位十分重要,“是区本为西羌旧地,汉唐以来,设官移民,屡经开拓,明代以后,回民迁入甚多,致成今日汉回藏三族杂居之形势。而夏河有拉卜塄寺,可称为西北藏族之重心,临夏为西军故里,可称为西北回族之重心,故言开发西北,是区实居重要地位”。[61]因而,他对该区域汉族、回族、藏族做了颇为细致的比较,以期唤起国人正确的认识。张其昀认为临夏回族、循化撒拉族与汉族长久居住在一起,导致其衣食住行、生活习惯大都与汉族类似,所以被称为“汉回”,区别在于撒拉族“操缠语”;汉族与回族的区别,在于信仰不同,“俗呼汉人为大教,回人为小教”;藏族与回族的区别,在于藏族“男女皆穿羊皮长袍,腰束带,解衣而寝,不用盖被,戴羊皮帽,穿牛皮靴,无裤无袜,亦无衬衫”,而回族“如寻常人,惟留长须,自别于汉藏,其以布缠头之俗,尚有存者,妇女亦多缠足”;回族与藏族优点显著,“甘省汉民多有烟瘾,惟有回藏不染此毒。又此二族,每户皆兵,舍生卫教,素称勇悍”。[62]在张其昀看来,拉卜楞寺尤为重要,作为“西陲一个宗教都会”,既是“西北藏族之宗教中心”,“又为汉藏民族接触地带农牧互易之中心”。[63]因而,他不仅组织了《方志》杂志的“拉卜楞专号”,还亲自撰写长文《甘肃夏河志略》以引起国人之重视。[64]
最后,此次考察为张其昀继承并进一步阐发孙中山以兰州为陆都的思想,提供了相应的科学依据。早在“九·一八”发生前,张其昀就提出:中国的国防应以北平、兰州为二基点,以南京为定点,而形成一大三角形之形势;其中,以兰州为西北陆军大本营,可以起到屏障西北边防的作用。[65]此后,他进一步阐发孙中山以兰州为陆都的思想。他认为:“总理以兰州为陆都,并非对于甘肃省有所偏爱,那是根据地理环境而来的。”[66]第一,兰州为距离中国疆域几何中心凉州最近的省会城市,故“与其称甘肃为西北,还不如称甘肃为真正的中部,兰州可称为中国之大陆中心”;第二,“黄河上流的重要支流,如洮水、湟水、大夏河、大通河,皆于兰州附近流入黄河,乃一最富于水利的地方,也是古来最适于军事屯垦的地方,将来引渠灌溉与水力发电,均饶有发展的余地”;第三,兰州为“内流外流之交,农产畜牧交会于此,足以足食,物美价廉”,“有成为中国毛织业中心的希望”;第四,兰州可为交通枢纽,“目前京兰航空线及尚未完成的陇海铁道,皆以此为终点”,“假使把铁道和航空路能延长到新疆边外,与苏俄铁道和航空路相联接,那么在交通上兰州不但为中国的中枢,亦为欧亚大陆的枢纽”。[67]此外,他还以星系理论比拟甘宁青市场系统,称“若以兰州比太阳,甘州之类犹行星,敦煌之类犹卫星,甘宁青三省犹一太阳系,至于西安或包头则属于另一太阳系”[68],凸显兰州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他呼吁:“建国宏业之完成,要当赖我国民皆能深体陆都之新使命,奋发有为,克服环境,以继承我先民建国之精神于茫茫大陆之上也。”[69]
此外,张其昀还认为西北拥有悠久的光荣历史,是复兴民族精神的重要基地。他指出:“振起民族精神,为一切国力之基础,较之天然富源,尤为重要。”[70]西北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为羲皇故里、黄帝遗冢所在,更是拥有着难以胜数的名胜史迹,这些均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是铸造民族之魂的历史丰碑。此正如其后所言:“名胜史迹,处处皆是民族之纪念碑。国民过此,岂有不动可歌可泣之情绪也哉!”[71]他还以在长安古城的亲身感受称“唐之帝国,开历史上未有之盛况,而今吾人在长安道上,所能想象当年之盛况者,果为何物耶?……当余等躞蹀于西京城头眺望南山之际,觉有沉重之心事,若我先民欲以无限之责任,加于中国少年之肩上者也”,呼吁“汉唐之光荣史迹,既为中华民族所创造,今兹国人亦必能恢复而重建之。且其宏远之规模,固可凌驾古代,以适合现代之需要,而成为崭新之陪都”。[72]由此可见,他主张将长安建设为陪都,实乃借恢复汉唐之繁荣,为国人之自勉。
三、西北开发的目标与途径
西北重要的战略地位、良好的资源基础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使张其昀对西北开发的前途抱着无限的期望。他强调:“目前最紧急的问题,即为如何对付日本的经济战,开发西北的呼声,是从这种迫切的需要而喊出来的。我们要把西北地上地下的富源,对内对外的交通,从速发展,和西南东南互相组织,以挽救东北沦亡后的经济危机。以抵抗外国舶来品的吸我脂膏。”[73]并告诫国人“决不可观望形势,畏首畏尾,坐待外人起来越俎代庖才好”[74]。
彼时,不仅西北开发,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均存在道路之争。其中,影响颇大的,乃是工业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特别是在一战后人们站在审视一战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工业文明后果的条件下,一些知识精英提出应“以农立国”,反对工业化。如代表人物董时进于1923年发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称:“中国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宜发挥其所长,不宜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75]但也有人提出应该“以工立国”,如1923年恽代英发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称:“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议。”[76]而杨铨则认为:“今世之立国,农业与工业不可偏废者也”,“工与农实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77]“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1930年代。
张其昀身处这场争论之中,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认为中国应先注意工业化的建设,然后用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他认为“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思想界议论庞杂,徬徨无所宗主,朝野上下均应引以自责。建国大业以发展工业为要着,必先求达经济上之独立,方可进而求国防上之独立”[78]。因而,他对工农之间发展关系的定位则是:“农村复兴应为整个经济计划之一部分,工业与农业都是国家根本实力,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目前尤应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救济农村故属当务之急,但只是治标之策,只有藉发展都市,才能救济农村,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惟一出路”,从而为“利用机械之力来改良农业”提供条件。[79]
张其昀强调,西北开发应以工业化为目标,而工业化首先应以发展交通为前提。他认为,西北之所以在古代有光荣历史,是因为欧亚孔道的繁荣:“昔自长安经金城、玉门关、敦煌以至西域地中海,实为欧亚交通之孔道:其时敦煌之地位,正如今日之上海,货物之交换,文化之传播,皆以次为门户”,而如今“我国对外交通,均在沿海一带,此道遂以蔽塞,徒供考古家之凭吊,西北地位遂亦一落千丈焉”,故西北开发必须建立起经济内循环,“沟通‘东南’‘西北’,交换产品,互相调剂,并进谋世界之贸易。然如交通不便,运输迟缓,则一切无由进行”。[80]为此,他强调应以“铁道为交通之干线。就西北而言,陇海铁道的完成,是第一件重要工作……陇海铁道完成后,西北人口自然会有相当的增加”[81];铁路外,“以西北之辽阔,尚须大行修筑公路,行使汽车,以为交通之支线而补铁路之不足”[82];航空方面,“如空路发达,则西北自可恢复旧日之光荣地位”,“空路较海路为一与九之比,其速率相差如斯之距。将来欧亚交通,将利用航空方法,此亦势所必至也”。[83]
其次,张其昀认为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工业中心的建设十分重要。他强调:“新式工业要素甚多,如原料、动力、人工、资本、机械、技术、运输、市场等,皆须有大规模之组织,固有集中一地之趋势。”[84]以西北开发而言,首先要依据兰州有利的地理位置,将其建设成为陆都,以兰州为中心发展西北的工业化。建设兰州为陆都的目的是期望能够吸引“东南各省人民,投资西北,实施拓殖;应用世界最新之学术与技术,利用大量生产之方法,依地理上之合理分配,以兰州为天然中心;联合多数工程师与企业家,在兰州设厂经营,以此为开发西北富源之总站”,解决西北开发所面临的资金、技术与人才问题,最终促使西北在短期内,“由农业而进至工业化,追随腹地各省平均发展”。[85]
第二,张其昀认为西北的经济开发并非只是简单的实现工业化,西北农业的现代化或农业的发展亦是题中应有之义。以青海为例,“青海河湟一带,人民大都从事农耕,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之人口,以农耕为主要职业”[87]。因而,农业改良实有必要,而其主要方式就是用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工业发展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建设与完善水利灌溉事业,“我国土地利用之根本问题,在于耕地不足,垦荒辟地为目前所最需要者,但自东北沦亡以后,未耕荒地多在西北雨量缺乏之区,必须修明水利工程,以事补救”[88]。灌溉事业的发展有两种方式,其一为利用机械修善、开凿渠道,如宁夏地区“自民国以来,因居民偷惰,渠流不畅,年年淤积,渠底日高。各处川原之地,沦于荒芜者,不可胜计。农民失业,转途他方,言之深堪痛心。若非举行大规模之灌溉,纾不足以目前民生之大困。现渠淤田芜,断非一年人工所能除去,似宜购置挖泥机器,开通新渠,引黄河之水,以收灌溉之益。庶‘河富宁夏’一语,不致转成空谈”[89]。其二为利用电力与水力,如“兰州附近,居民构木为翻车,引水灌田,法良意美,惟水车势力仅及黄河之谷。如能本旧有经验,采最新方法,实行电力灌田,则范围可以扩大。陇东山地几全为旱田。若赖电动抽水机以资灌溉。不但可以增加豆麦产额,或可经营稻作。甘肃山民有利用水力以设水磨。可以碾豆成油,磨麦成面,水流轮转,辘辘震耳。此亦利用水力之先声也”[90]。
第三,张其昀认为可以通过军事屯垦的方式来促进西北经济发展。如“青海在经济上既非旷地而为乐土”,采取军事屯垦对其经济发展甚有帮助。
自柴达木至当拉山一带数千里之地,并非旷土,而几寂无人烟。以目前青海省交通民生状况,若不藉军政力量,欲移民实边,恐不可能。故欲充实青海,即应以赵充国李靖等为师法,以军事为先锋,作屯垦之工作,俟军事屯垦有效,移民事业方可进行。且青海省地势高寒,经营开发,外来移民恐不胜任,仍须赖本地军民之努力。贵省军队近年有玉树之役,能克服高寒环境,是其明证。军事屯垦,系继续古人之精神,而采取最新之方法。青海省今尚未脱手工时代,屯垦工作,当利用新式机械以为之倡,我国农业向系深耕制,屯垦则可实行机器广耕制,且不但寓兵于农,并可寓兵于牧,寓兵于路,改游牧为定牧,筑公路于高原,开矿锯木亦均用机器以代人工,择适当之区域,为屯垦之实验,则充实青海,于是发靱矣。……青海省光明灿烂之前途,吾人愿拭目而俟。[91]
屯垦不止局限于屯田,林垦和牧垦同属重要。关于林垦,“西北各省,拔海甚高,如岷山、六盘、贺兰、祁连等山脉,地多高寒,不宜农垦,但天然森林甚为苍茂,材木之利,可以足住”[92]。关于牧垦,如“陕西北部山地连亘,荒原辽阔,其地理环境与内蒙相似,宜于畜牧”,“陕北沿边各县,牧重于农,盖牧畜利大”,“惟最畏疫症,往往大群牲畜,死亡殆尽,故速宜设立牧畜兽医学校,养成牧畜兽医人才,由学校大规模制造各种防疫药苗,推行防疫注射,此目前所应办之事也”。[93]又如“古称‘洮州之马天下闻’,自茶马之制废,而马政遂不讲。目前军用马匹甚感缺乏,马种退步尤为可虑,况牝马产骡,民间需要亦殷。至牛羊野牲,皮毛乳酪,衣食原料多所利赖,兰州将来为中国毛织业之中心,欲期制品之益精,当从改进牧业入手”[94]。
第四,除经济发展外,张其昀认为西北开发还应特别注意民族问题。他认为:“在目前边疆多事之秋,本属地方性质的民族纠纷,其安危足以牵动大局,甚至反客为主……所以我们不能不先把民族统一民族的工作于短时间内继续完成。”[95]不仅如此,西北各少数民族的诸多优点亦应使之对西北边防做出重大贡献。如“回藏二族皆勇敢善战,藏民生长鞍马,射手尤佳,其生活极简单,糌粑为餐,长裘当被,利于行军,尤擅长驱……当国家有事之秋,汉回藏三族之领袖人才能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盾之以中央军队,济之以现代设备,因势利导,西北保障实利赖之矣”[96]。民族问题的解决首先在于教育的普及, “今日中国之边疆实无所谓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仅有教育问题与生计问题”;“其教育首宜注意卫生,次为生计教育,如教之耕田作工植林采矿等事,以启发天然富源,至于人文训练亦不宜偏重书本”;其次为通婚,“社会力量最重要者为婚姻,异族杂居之地,彼此通婚愈多,则相处亦愈增融洽”,“以教育与通婚为先导,则政治易于施行。如改土归流,新设县治,当不致有何阻力”;最后应平等对待各民族,“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就是不问基本民族或少数民族,都是一律平等相待”。[97]
四、结 语
张其昀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因其出色的学术成就而扬名学界,之后进入了蒋介石的智囊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该组织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研究边疆问题,曾派出西北调查团赴西北考察,张其昀负责人文地理的调查。张其昀的考察从1934年9月10日至1935年8月6日,历时近一年,主要调查地区为陕、甘、宁、青等省。其基于对西北地区的科学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先见性的主张。首先,张其昀将西北开发作为全国性战略大局的考量,尤其是提出西北开发应以国家战略为主的认识,甚有见地。他认为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均为中国最贫省份,今日尤贫。全省正当岁收不及一大市,微论不足养兵,且不足办行政……近年省库如洗,债台高筑,遑论建设”[98],因而“目前开发西北之声,甚嚣尘上,何以解决此类实际问题,拯斯民于疾苦,则视乎中国政治家之手腕矣”[99]。其次,他认为兰州基于其地理优势,有希望成为西北的工业中心。复次,他强调西北开发应注意西北农业、牧业、林业的平衡发展,“西北位于内陆,气候干旱,雨量不足”,应积极建设水利灌溉事业,“以科学方法改良牧业,边疆各族之生计,必可大为增进”,“黄河上流各支流导源之处,天然森林尚多保存,果造伐有道,并利用水利,则木材及副产品不可胜用”。[100]最后,对于西北各少数民族,“须促进边疆教育,保存其优点,补救其缺点。吾民族之传统精神,即为以公正之态度,处理民族问题,一切人民皆或绝对平等之待遇”[101]。总体来看,虽然张其昀关于兰州陆都的设想“过于乐观”[102],但他的西北开发思想依然对于如今的西部大开发有着借鉴意义。
注释:
①关于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的研究,内容涉及:(1)西北开发思潮,如关连吉、赵艳林编《西北开发思想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尚季芳:《试论国民政府时期开发西北的思想主张》,《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杨红伟、武永耿:《简论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形成的表现》,《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2)经济开发主张,如刘瑛:《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开发中的经济思潮评述》,《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杨红伟:《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冯成杰:《民国时期学界移民垦殖西北思想的构建》,《农业考古》2014年第3期;(3)个人的开发主张,如吴映萍:《孙中山开发西北战略思想刍议》,《广东社会科学》2001第4期;胡伟:《翁文灏西北开发思想与实践》,《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薛正昌:《孙中山西部开发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②学术界关于张其昀的专门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地理学思想、人际关系、人文精神、教育思想等方面,如:何沛东:《张其昀主编的〈方志月刊〉及其地理学贡献》,《地理科学》2021年第5期;何方昱:《知识、人脉与时局: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田彤、高伟军:《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孔子研究》2015年第4期;毛文婷、张淑锵:《张其昀与浙大史地研究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