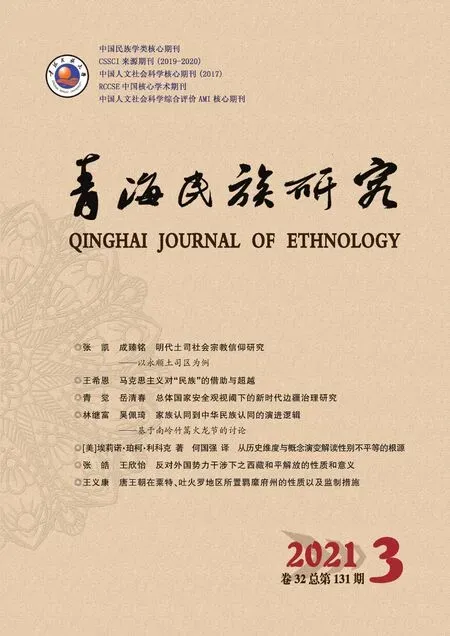“收继”蒙古语源考
牧 仁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10028)
收继婚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与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而其在北亚游牧民族社会延续时间较长,内涵与形式尤显特殊。笔者曾考察大蒙古国及元朝时期(以下简称蒙元时期)蒙古人究竟是以什么词汇表达“收继婚”时,发现汉语中涉及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收继”这一重要概念竟是出自元代蒙古语。
一、蒙元时期指称“收继”的蒙古词语考
元初曾援引比附金朝《泰和律令》创制新法。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立“大元”国号,元世祖忽必烈正式终止了对金朝法律的援引比附,着手制定与元初社会实情相适应的新法。当朝中大臣奏请禁止实行有悖金朝法律规定的收继婚时,元世祖下令:“疾忙交行文书者,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1]①其中“收者”二字原蒙古语当是元代指称“收继”行为的动词。我们根据《蒙古秘史》旁译、明代《华夷译语·人事门》《登坛必究·译语》可知,当时与“收”对应的蒙古语动词是quriya[2]。硬译公牍通常在动词后加 “者”字来翻译蒙古语命令祈使式后缀“tuγai”“tüγei”。 如 此 ,“收 者” 原 蒙 古 语 无 疑 是“quriyatuγai”。由此推知,蒙元时期官方是以词根为“quriya”的诸派生动词指称“收继”一词的不同语态。
孤证不立,另举一例。关于孛儿帖夫人被篾儿乞部夺去的经过,《蒙古秘史》载到 “türün urida uduyit Merkid—ün Toqto'a beki uqas Merkid—ün Dayir usun Qa'atai Darmala ede qurban Merkid qurban a'ut haran üdür—ün erte Toqto'a beki—yin de'ü Yeke iledü—de e Yesügei ba'atur—a Hö'elün eke—yi buli u abtalai ke'en te'ün—iösön ha iran ot u'ui.Temüin—i Burqan Qaldun—i qurbanta qu i'ulqui—tur Börteüin—i tende erüsü iledü—yin de'ü ilger bökö—de asara'uluqsan a u'u.tere asaraqsa'ar a u ilger böködayi i u qarurunügülerün《qara kere'e qalisu k risü idegü aya'atu b 'etele qala'un toqura'un—i idesüke'en e in a u'u.qatar ma'ui ilger bi qatun ü in—tür qalqu bolun qamuq Merkid—te hunta'u.qara u ma'u ilger qara teri'ün—dür—iyen gürtegü bolba.qaq aqan amin—iyan qorpqun qarangqu qab alširqusu.qalqa ken—e boldaqui u bi.quladu ma'u iba'un quluqana küügene idegü aya'atu bö'etele qun toqura'un—i idesüke'en ešin a u'u.qunar ma'u ilger bi qutuqtai sutaiüin—i quriya u iregü bolun qotola Merki[t]—te hunta'u bolba 》ke'et dai in duta'a u'u.”[3]②
兹摘录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相应译文如下:
当初兀都亦惕—蔑儿乞惕的脱黑脱阿·别乞,兀洼思·蔑儿乞惕的歹亦儿·兀孙,合阿台·荅儿马剌等,这三族蔑儿乞惕的三百人,为了以前也速该·把阿秃儿曾将诃额仑母亲,从脱黑脱阿·别乞的弟弟也客·赤列都抢来的缘故,前来寻仇。三次环绕不儿罕山,[追踪]铁木真的时候捉得孛儿贴夫人,交给[也客]·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尔·孛阔看管。就在这样继续看管的时候,赤勒格尔·孛阔逃奔出走,他说:“老乌鸦的命本是吃[残]皮[剩]毂的,竟想吃鸿雁、仙鹤;我这不能成器的赤勒格尔,竟侵犯到[极尊贵的]夫人!全蔑儿乞惕人的罪孽,已经临到我不肖下民赤勒格尔的黔首之上了!想逃我这仅有的一条命,我想钻进这幽暗的山缝啊;可是谁能做我的盾牌[保护我]呢?坏白超的命本是吃些野老鼠的,竟想吃天鹅、仙鹤,我这服装不整的赤勒格尔,竟收押了有洪福的夫人!全蔑儿乞惕人的灾殃,已经临到我污秽不堪赤勒格尔的髑髅之上了!想逃我这羊粪般的[一条]命,我想钻进幽暗峡谷啊!可是谁能作我的围墙[保护我]呢?”说完就逃命去了[4]。
如引文所载,蔑儿乞部为报早日诃额仑被夺之仇,将孛儿帖夫人抢去,因赤列都不在,令其弟弟收续, “iledü—yin de'ü ilger bökö—de asara'uluqsan a u'u.tere asaraqsa'ar a u”即言此。 引文“asara'uluqsan”一词旁译是 “收继了”三字,“asaraqsa'ar a u”的旁译为“收继了以来住着”。关于《蒙古秘史》旁译,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一文认为“《秘史》汉字音写本的译写者们的语言学素养,在14世纪末年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高水平。”这一评价早已为学界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全书旁译仅此二处使用“收继”一词。因为“收继”是首现于汉文文献,专指收继婚的元朝法律名词,未见法外使用。《蒙古秘史》旁译者认为,赤列都已死,所以蔑儿乞部令其弟收继夺来之孛儿帖。否则,上述二处旁译应该使用明代《华夷译语》与《登坛必究》里翻译一致的“抬举”或“收拾”而不该用“收继”。《蒙古秘史》内asara派生动词21例,明代旁译中,10处译为“抬举”,10处译为“收拾”,1处译为“照觑着”。③不选常用的“抬举”“收拾”而选择不见于任何明代蒙汉译语之“收继”来作asara’uluqsan的旁译,显然是特指蔑儿乞部之收继行为。接着《蒙古秘史》假借赤列都弟弟赤勒格尔之口自我贬低地说道 “qunar ma’u ilger bi qutuqtai sutai üin—i quriya u iregü bolun”,这里quriya u iregü bolun的旁译是 “收拾着来着”。这里的quriya u之涵义与上文忽必烈圣旨里的 “收者”(*quriyatuγai)同指收继行为。)从赤勒格尔的这段自白推测,《蒙古秘史》作者亦认为这是蔑儿乞人的收继行为,足证上面两处明代旁译使用“收继”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汉“收继”一词首见于《通制条格》,该书是《大元通制》残存“条格”部分,《大元通制》成书于仁宗延佑三年(1316),但直至1323年才由英宗正式颁行。以quriya u(收拾)表达收续之意的《蒙古秘史》的成书早于《通制条格》。
由上可知,蒙元时期是以quriya(收拾)和asara(抬举)的派生动词指称收继风俗的。quriya一般用于文言,而asara语气相对柔和,有扶持、恩养、伺候等涵义,多用于口语。
除蒙元时期上述两种称谓之外,成书于17—19世纪蒙古文历史文献《黄金史》《蒙古源流》《金鬘》《蒙古风俗鉴》等均以alγa的派生动词指称收继。例如,记载满都海夫人依照收继习俗与巴图蒙克缔结婚姻一事,上述文献各依行文所需分别采用alγa词根之不同派生语态:《黄金史》用algaγul u[5];《蒙古源流》用alγa u[6];《金鬘》用alγam ila u[7];《蒙古风俗鉴》用alγa u[8]。虽说这些alγa同根词均出现于十七世纪以来蒙古文历史文献,然而诸史籍如此一致地熟练运用该词来看,应是古老词汇,绝非元以后新创之词。
至此,我们已确定蒙元时期蒙古语指称收继的三个词根:quriya、alγa、asara。由蒙古文历史文献行文情形观之,quriya、alγa多以文言出现,asara常为口语表述。
“收继”一词乃元代新增法律术语,不见于之前任何汉文文献。根据《元语言词典》,指称收继行为之元代官方用语通常是 “收继”“收续”“收”[9]。而《元典章》相关用语除上述三词外,另有“收要”“继”“接续”“收续”“续亲”等。《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婚姻·收继》部分用“继”“接续”“收续”“续亲”等词指称收继。这些词内涵完全一致,与蒙古语alγa涵义完全对应。元以前汉语,子纳庶母为妻称为“烝”,叔伯死而子纳婶母称为“报”。另有“妻”“娶”“执”“适”“纳”“转房”等指称[10],几乎不见使用“收”“继”以及 “收续”“收要”“收”“继”“接续”“收续”“续亲”等元代常用语。这些词的核心涵义在于“收”“继”二字,而与此完全对应的quriya、alγa两个词恰恰是元代蒙古语中指示收继风俗的核心词汇。
元代“收继”一词创造者目前尚无法确定。元朝时期,蒙古语以音译或意译形式被汉语吸收的例子不在少数。方龄贵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检出114个来自蒙古语的汉词,分别予以考释。其后另写文章补充若干遗漏。《元典章》等元代文献里亦常出现“肚皮”“根脚”等译自蒙古语的词语。那些应时而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悠然褪去,化作尘封记忆,未能像“收继”留用至今,却从一个侧面提示“收继”出自蒙古语之可能性。
二、“收继”之蒙古语原生本义
先从蒙古语词典着手考察关于quriya的解释:
《二十一卷本辞典》: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成书,乾隆八年(1743年)改版重印,1977年11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整理印行。该辞典是最早一部蒙古文辞典。该辞典收录了quriya为词根的词6个,其中2个词与本题相关[11],兹将原蒙古释义汉译如下:
quriyamui,该词是quriya后附加现在时和将来时词缀mui。释义:1.使兄弟亲族靠近自己予以抚恤或帮助;2.指五谷丰收;3.把东西集中起来保管;4.将散在四面八方的东西聚集在一处。
该词是quriya后附加众动态现在与将来时词缀aγamui。释义:悉心照顾亲族及姻亲;使因苦难而四散奔逃的人们聚集一处予以扶养;将衣物整理完备。
现代《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编,1999年增订。该辞典687页收录了词根为quriya的词13个,其quriyaqu一词解释与本文相关[12]:1.收,收起,收集,收回,搜罗,搜集;2.收敛;3收拾;4拢起,收拢;5.没收,收缴;6.收藏,贮藏,积累;7.收复,征服;8.堆放,叠,堆积;9.停止,止;10.耗光,挥霍尽;11.(数)约分。
对比上述两部辞典,我们发现,对“quriya”词义解释有明显不同。《二十一卷本辞典》仍存蒙元时期“收继”历史词义,而现代《蒙汉词典》中,“收继”涵义完全去除。这表明,随着蒙古社会向近代转型,收继习俗逐步淡出,原来表达收继涵义的蒙古词语发生历史语言学演化,“收继”有关古义渐次为时代遗忘。
根据上述蒙古文与汉文史料以及近人相关论著[13],可以概括出元朝以前“quriya”所含“收继”涵义之四指:1.收拢人口;2收拢财产;3收养孤寡,予以保护;4收国安邦。
《二十一卷本辞典》收录了alγa派生词6个,其中与本题直接相关词有2个[14]:
现代《蒙汉词典》收录了词根为alγa的词19个[15],其中附加现代式词缀xu的形动词alγaqu之词义解释较全面,具有代表性:1.连,接,连接;2.衔接,接合,嫁接;3.毗连;4.继承;5.续娶。
与上举《二十一卷本辞典》的2例quriya派生词相反,同辞典alγa派生词解释则与“收继”毫无关联。而现代《蒙汉词典》却保存了alγaxu的古老“收继”(即“5.续娶”)词义。
根据上述17—19世纪蒙古文历史文献对alγa派生词的运用语境以及近人相关研究[16],可以看出alγa派生词主要是指通过“收继”方式,继承和延续逝者之宗族血统、社会身份、地位还有逝者的财产。
至此,我们已为“收继”一词蒙元时期蒙古语原义予以详细解释。为更加深入理解“收继”概念历史文化背景,还须进一步阐释上文被旁译为“收继”之asara派生词。 该词是蒙元时期表达“收继”的口语。将该词与上两词比较,语气明显柔和,情感化,包含扶持、伺候、抚育等意涵,体现对弱者的伦理关怀。蒙古口语所含这层道德关怀无法从“收继”这个中性意译词中体会。翻译时选用“收继”二字,虽较“烝”“报”“妻”“娶”“执”“适”“纳”等中原固有词汇,较少价值色彩,也相对中性、贴切地传达了游牧伦理观念,但并未体现蒙古口语原有的情感色彩。诚然,“收继”作为元朝首创法律术语,去其感性,取其理髓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不同语言文化之间通过翻译沟通,虽极有必要,然终究不可能完美对译。
深入理解“收继”之蒙古语源后不难发现,该词被创造并写入元朝法律,是出自元廷游牧文化与伦理思维,同原来“烝”“报”“妻”“取”“执”“适”“纳”等词义相区别,以示另有所指。元廷明确区分适用人群,主张“各从本俗”,明令禁止汉人收继。
元廷为何禁止汉人收继而仍使蒙古游牧社会保留呢?上文对“quriya”与“alγa”的考释即已解答该问。对游牧社会而言,“收(quriya)继(alγa)”制度绝非仅指“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取其妻妻之”的婚姻接续,其生成即源自北亚地理环境、游牧经济与文化土壤。与不同时期其他地区、民族的收继婚制貌似相近,然而深入挖掘其内涵,便知差异显著。兹举几例,以示大概:
1.“yesügei ba'aturügülerün《dotora minu ma'ui büi.
Dergede ken büi.》ke'eju 《Qongqotadai araqa ebügen—ükö'ün Mönglik oyira büi.》ke'esüuri ire'ülüügülerün:《aqa minu Mönglik kö'ütüügetü büle'e bi.kö'ü—ben Temüin—i güriget—te talbi u irerün a'ura Tatar irgen—e oyisulaq—da'a bi.dotora minu ma'ui büyü.üüget qo oruqsat de'üner—iyen belbisün Bergen—iyen asaraqu—yi i mede k'üminu Temüin—Iötörken ot u ab u ire.aqa minu M nglik.》ke'et nök ibe.”[17]
译文:
也速该·把阿秃儿说:“我[心]里不好受!有谁在眼前?”[有人]说:“晃豁坛氏察剌合老人的儿子蒙力克在跟前。”就叫[他]前来,说:“我的孩儿蒙力克呀![我的]儿子们还小呢!我把我儿子贴木真当做女婿留给[人家],回来的时候,路上被塔塔尔人暗算了!我里面不好过!你要关照你那年幼被遗留下的弟弟们,[和]你那寡居的嫂嫂!我的孩儿蒙力克!快去把我的儿子贴木真带回来!”说罢就去世了[18]。
2.Quyildar se—enügülerün《anda—yin emüne bi qatquldusu.Mono qoyinaöne it kö'üd—i minu asaraqu—yi anda medetügei.》ke'ebe.”[19]
译文:
忽亦勒荅儿·薛禅说:在“安荅”面前,我去厮杀,自今已后请安荅关照我的孤儿们吧。(札奇斯钦书222页)
3.“ügergen usu Tolui kö'ün u'ubai.qorom sa'u u ügülerün《soqtaba bi.soqtaqu—yi minu sergüteleöne it de'üner—iyen belbisün beri—yen Berüde oyin—a gürtele asaraqu—yi qa'an aqa medetügei.ali ber üge—benügülele'e.bi soqtabai.》ke'e'et qar u ot u b ese boluqsan yosun teyimü.[20]
译文:
把咒诅的水,给[皇]子拖雷喝了。他坐了一会儿就说:“我醉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请可汗哥哥好好关照孤弱的侄辈,寡居的[弟]妇吧![我]还说什么呢?我醉了。”说罢出去,就逝世了。(札奇斯钦书431页)
上述《蒙古秘史》三处记载,均是逝者临终之前将孤寡托付与“安荅”或血亲的例子。逝者均用了asaraqu这个口语中表示收继行为的词汇表达其托付遗愿。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为塔塔尔人所害,临终前将孤儿寡母托付察剌合老人之子蒙力克。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固定逻辑推论,也速该巴阿秃儿应将孤寡托付其亲弟荅里台·斡赤斤才对,却将孤寡托付蒙力克。唤蒙力克来,貌似因蒙力克恰巧在附近,事出偶然,实则出自也速该把阿秃儿慎思之选。也速该把阿秃儿去世后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荅里台·斡赤斤等均随泰赤兀部离去,对也速该把阿秃儿孤寡弃之不顾,察剌合老人奋力阻挡离去的人群时被泰兀赤部的脱朵延·吉儿贴以利枪刺中脊骨,重伤死去。证明察剌合与蒙力克父子才是也速该忠心耿耿的心腹。
上引另两段记载中的两位受托者成吉思汗与窝阔台,亦未依循所谓“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与忽亦勒荅儿·薛禅和托雷的孀妇续婚,只是遵守诺言忠实履行了扶养孤寡之义务。
所以“收继”之原蒙古语“quriya”“alγa”“asara”三词,除了“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外,更包含与续婚无关的“安荅”“那可儿”临终受托,履行誓言扶养孤寡行为。“安荅”与“那可儿”扶养孤寡行为,完全是出于托付与受托者间忠诚与信任。可见“收继”蒙古语原义包含以信用为基础的社会规约之意。规约之产生,由游牧社会本身特质决定。作为“行国”的游牧社会是一个动态社会,特殊的结构及其生存方式要求一切物质与制度文化简约高效,衣食住行必便于携带、易于保存、适于移动。然而,战争与自然灾害给部落家庭带来不幸,尤其作为家庭主心骨的男人一旦死去,留下一家孤寡,如何安置?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之存亡直接决定游牧社会之存亡。游牧者的选择便是“quriya”(收)“alγa”(继)“asara”(抬举)方式来保护个体家庭,维持生存。在古代游牧社会全无可能专设社会保障机构来扶助孤寡弱势群体,从而稳定社会基本单位。在此历史背景下,以亲族、“安荅”“那可儿”间高度忠诚与信任为核心的社会忠信体系为基础的“quriya”(收)“alγa”(继)“asara”(抬举)制度是可能的、成本最低、也最牢靠,且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完全符合游牧社会生存法则。遭受苦难或失父亡夫的家庭不受保护,即面临被部落遗弃的命运:如同诃额仑夫人与孩子所遭遇的巨大苦难。苦难的经历虽然成就了像成吉思汗这等坚强人物,但对于普通的孤儿寡母是难以承受的。某种意义上,数千年游牧社会正是依赖该保障体系得以延续。“quriya”(收)“alγa”(继)“asara”(抬举)制度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该游牧伦理逻辑,由己及人,可以延伸到收养敌对部落的孤寡:著名的诃额仑夫人四养子,均是敌对部落之遗孤。这种收养行为当时广泛存在,即使对杀害父祖、深仇大恨的塔塔尔部,也容其身高不及车轮的孩童,收入本部。出于同样的思维惯式,成吉思汗实施“斡那赤敦 阿里合(n id—ün abliqa)”[21]④制度,即抚恤遗孤制度。阵亡者忽亦勒荅儿·薛禅与察罕·豁阿的孤儿依次获得“斡那赤敦·阿里合(n id—ün abliqa)”之赐。收养遗孤在当时是生活常态,个体对集体之忠诚内化为群体文化心理,收继制度对古代游牧社会之稳定及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过去人们分析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之强大原因,多从军事优势,如战略战术、武器、骑兵机动性或者从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等层面予以考察,较少注意其游牧文明伦理规制的骨髓性作用。须知,每位游牧战士都是从个体家庭走出来的,留恋家庭,牵挂子女,人性使然。正是由于“quriya”(收)“alγa”(继)“asara”(抬举)制度的存在,大大减轻游牧战士对身后家眷的顾虑,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因固有成见往往为他者睨视之收继制度,恰恰是游牧民族强大之所在。由此可推想,元初政治制度设计,如果一味援引比附金国法律,丢掉游牧根本制度,就有可能毁坏游牧政权之伦理与社会保障基础,其军事优势随之不存,政权基础发生动摇,衰落直至灭亡。由此不难理解忽必烈大汗为何紧急下发“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旨令,立法保存收继制度。
注释:
①该引文即属“硬译公牍”,是不顾汉语固有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径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
②《蒙古秘史》第111节。该书蒙古文拉丁音写与本文音写稍有区别,引用该书音写内容之处,均循原书音写,未作改动。
③上引《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再复原及其拉丁转写》:第97页(68节)、145页(85节)、518页(171节)、539页(174节)、617页(186节)833页(214节)、385页(145节)、447页(155节)、584页(181节)、633页(189节)、915页(231节)、917页出现三次(232节)、923页出现二次(233节)、925页(234节)、927页(234节)、1183页出现二次(278节)、1153页(272节)
④“斡那赤敦 阿里合(?n??id—ün abliqa)”旁译为“孤独的受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