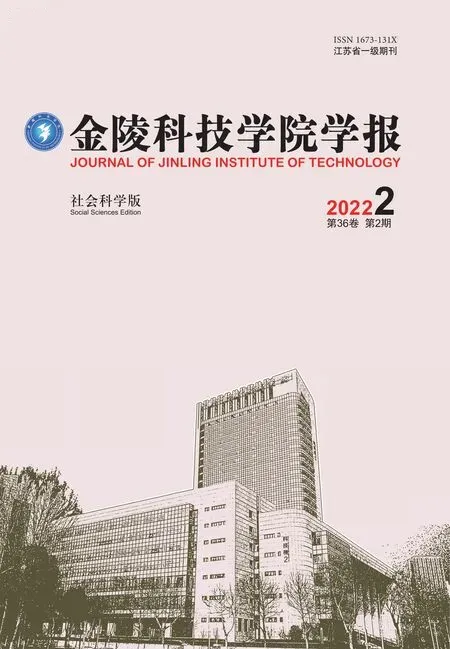“分”视域下荀子与竹简《穷达以时》天命观之比较
陈光连,葛殿聪
(1.金陵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9;2.南京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2)
郭店竹简有道家著作两种四篇,有儒家著作十一种十四篇,其中,《穷达以时》篇是郭店竹简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目前学界对荀子(1)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荀子》([唐]杨倞注,东方朔导读,王鹏整理)。与郭店竹简的思想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荀学与竹简儒家文献之间的关系、荀子的性情哲学与竹简《性自命出》篇之间的异同、荀子的养情思想与竹简文献之间的关联等。颜炳罡先生认为,种种证据说明,《性自命出》之“性”不是思孟学派的道德之性、义理之性,而是气性,或者说更接近于荀学的材性。由此颜炳罡先生认为《性自命出》是荀子性情哲学的源头[1]。刘延福对荀子与竹简儒家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认为郭店竹简思想特别是其天人观、人性论、人道论和诗乐观与荀学更接近。换句话说,荀子对儒简思想的直接继承,远远超过他的前辈孟子[2]。陈光连则从德性教化的视角论证了荀子与竹简思想的学术关联,认为无论是荀子还是竹简,都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个人社会的品性是教化习养而成的,从成德思想可以推断出不能把竹简归属于思孟学派[3]。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郭店儒简是思孟学派的著作,儒简与荀子及荀学的关系不大,这种观点忽略了对荀子与郭店儒简的关系研究[4]。因而,本文从德性论的视角对荀子与郭店儒简《穷达以时》篇(2)郭店竹简《穷达以时》篇存简15枚,289字,因简残,缺17字,凡306字。《穷达以时》可分为三章,首言“知”:察天人之分,知“世”知“行”;次言“遇”:古之贤者均因遇而达;三曰“反”:穷达以时,君子惇于反己。以上是《穷达以时》篇君子成人的思考路径,反映了早期儒家对现实穷达问题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人性的理性追求。这种思考模式与荀子《天论》篇极其相似,荀子或受到了《穷达以时》天命观的影响。的核心概念——分、时、遇、达等进行比较,进而得出“荀子与竹简虽都强调天命对个人际遇的影响,但荀子更强调人在世间的积极有为,正是通过‘天人之分’,才显示出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荀子和《穷达以时》在成人之道上极为相似”之结论。
一、时机与节遇:道德境遇之择路
《穷达以时》云:“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5]26《穷达以时》对天人关系的观点即是如此。庞朴先生说:“天人有分和天人之分的分字读去声,用如名分、职分之分。”[6]庞朴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郑玄《礼记·乐记》“男有分”注释言:“分,犹职也。”其实,《穷达以时》中的“分”犹如荀子“明于天人之分”之“分”,均是“名分”“职分”之意,二者并无殊别。在现实中,天有所命,人有其材;天命有异,材各不同。天之命,人之材,各有其分位也。《穷达以时》认为,天人之间各有其职分,只有明白了这种职分的区别,现实中的人才能明白该如何作为;同时认为,人所处的现实环境——“世”对人之行事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穷达以时》在“天人之分”的前提下强调人在世间的作为,在这一点上荀子与其致思路径是一致的。
《穷达以时》的“天”是一种命运,其所谓“天人之分”主要讨论的是“天人”亦即“天命”与“人事”的关系。而所谓命运并非宿命之命运,而是一种“遇”,是对社会现实中穷达祸福的或然性的一种哲学概括。故而《穷达以时》认为,世间有些事情如“时遇”等,是人所不能掌握的,只能看作是命。而这种命,不过是表现为“天”对人所显示出的力量,是一种异化了的“群”之力,或者说是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人伦关系的一种合力,诚如荀子所谓“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荀子·王制》)。但是,荀子的“天人之分”与《穷达以时》又有所不同。荀子心目中的“天”既无意志也无目的,其所谓的“天职”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近于孟子所谓的“命”。荀子对“命运之天”采取非常明确的态度:“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唐君毅说:“至荀子之言命,则其正名篇曰:‘节遇之谓命’,此乃脱尽一切传统天命之宗教意义、预定意义、形上意义之纯经验事实之命。而命之所指,乃唯是一赤裸裸之现实的人与所遇之境之关系。”[7]在此,唐先生似乎否定了命的形上意义。其实,荀子的“天人之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其一,人能有所作为,而天自然无为;其二,面对自然之天,人必须对现世的治乱负责,更确切地说,人要明于天人之间之分际。从这方面来说,荀子从自然之天出发,把天的人格化面貌与属性完全化解,这或许受到了老子“以道为普遍自然法则”观点的影响。但是荀子在形而上学方面并未受早期道家的影响,而是强调“明于天人之分”,天和人各有分位,天之命因世因时而异,人之材因时因世而不同,使人获得与天命同等的地位。尤其是“制天命而用之”,把人从天的神秘桎梏中解脱出来,凸显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和道德动机。诚如《荀子·宥坐》云:
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3)此为孔子弟子所记述的孔子言论,与《穷达以时》之意相一致。《穷达以时》似有可能为孔子自述。
荀子所言“遇不遇者,时也”与《穷达以时》之“时”均指时机、时世之意。《论语·阳货》云:“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如何理解“遇”与“命”之关系?荀子谓“节遇谓之命”(《荀子·正名》),即将命规定为人作为个体主体的具体道德境遇。孔子曾提及,人若“获罪于天”则“无所祷也”。孟子亦曾引述《诗经·大雅》和《尚书·商书》语句,阐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之精义。荀子认为,对于那些一己所能掌握、决定之事,若能敬慎从事,对于天之职分与人之职分倘若也能审慎分辨,那么,对于一己的穷达毁誉也就能够安适因应,处之有道了。
在此,荀子区分了“义辱”和“势辱”两个概念的内涵:“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籍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是荣辱之两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荀子·正论》)荀子认为,人生中最大的光荣是人自身焕发出来的荣耀。至于那些外在的荣誉,或由天命决定,或需世人赐予,并非凭借努力修为便必然可以获致的。因此,得之固然可喜;倘若不曾获致,也无损于经由人自身对德性价值的体悟所获致的荣耀。反之,若舍弃德性的价值,那么无论外来的富贵荣华如何显耀,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也不会因此增益。因此,孟子有“仁则荣,不仁则辱”的评述。荀子对此也有精微的论述:“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能奉行仁德便可突破贫穷的影响,不因贫穷而改变自己的心志,若对仁德的价值能深刻体悟并竭力践履,则对自身的声名、际遇便能泰然处之。
朱熹集注:“见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8]如此,遇者达也,不遇者穷也。遇与不遇是君子达与穷的关键。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偶然因素掺杂其中。成败进退,荣辱穷达,孔子也曾不遇其时,荀子亦受“势辱”之困,诚如《穷达以时》列举的舜、吕望、管仲、百里奚、孙叔敖等人,也都曾处于贫穷、困厄之境。但因其都像《孟子·公孙丑上》记载的那样,善于吸收别人的优点,践行善事,因而都经历了从不遇到遇、从“天人有分”到“天人相合”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与主体的道德修养素质、为善力度相关,也与遇与不遇直接相连。只有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方能达至天人相合。
二、穷困与显达:“惇于反己”之进路
《穷达以时》认为,“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惇于反己”[5]32,要求人们应“惇于反己”,不必专注人世间的穷达祸福,只关注自己的德行即可,并提出“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的思想(4)《穷达以时》在“察天人之分”的理论指导下,在古之贤者“兼善天下”的事实中,认识到了“遇”与“达”的关系,在“穷”与“达”的思考中,作出了“遇不遇,天也”的结论。这里的“天”,不是神格的,不是道德的,而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与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一样,《穷达以时》亦把人的视域投向了人间的祸福、贵贱、穷达。在这里,《穷达以时》所谓的“天”不是命运之天,而是把天与时、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遇不遇,天也”这一结论的基础之上,以“穷达以时”来概括“因时、因世,有遇有达,或不遇而穷”的社会现实。因此,荀子思想重在积德,诚如《穷达以时》提出的“德行一也”,要求“惇于反己”,也就是反求于己。《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只有“惇于反己”,才能达到儒家人性追求的终极目标:追求人性的超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尊严和社会价值。。《说文》:“穷,极也。从穴躳声。”引申为困厄、贫困。《论语·卫灵公》载:“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穷”是困厄,“君子固穷”是指“不为穷困而败节”(《孔子家语· 在厄》),而小人则无所不为。在这里,孔子没有进一步解释“君子固穷”应怎样,只是与小人进行了比较。《孟子·尽心上》发挥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固穷”的价值标准是不失义,价值导向是“独善其身”;“显达”的价值尺度是“不离道”,价值导向是“兼善天下”。
孔孟讲穷达,是强调其道德价值的张力,以道德规范来控制主体“穷”与“达”境遇下的行为趋向,使其收敛而修道立德。为什么“穷”或“达”?为什么由“穷困”到“显达”,或由“显达”到“穷困”?《穷达以时》认为,这既取决于“时”,更取决于“行”。“穷达以时”,君子可能不得志,也可能因遇而显达,“穷达”或“德福”对君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子的德行。《论语·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朱熹集注引尹氏曰:“德必修而后成,学讲而后明,见善能徙,改过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君子因世、因时,有遇而达,或不遇而穷,都要以一以贯之的进德修养,既不能二三其德,也不能三二其行。“德行一也”是早期儒家对人性的理论追求。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荀子也继承了孔孟儒家以及《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的“君子惇于反己”的修德进路,并进而向外和向内展开为修礼与积德。荀子云:
是故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闵,明达用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和平,志意广大,行义塞于天地之间,仁知之极也。夫是之谓圣人。审之礼也。(《荀子·君道》)
君子立志如穷,虽天子三公问正,以是非对。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荀子·大略》)
贫穷与富贵、劳倦与显达,在于心志践道,以行遵礼。当君子珍视德性价值的心志足够坚定,而践行此一价值的意志也坚定不移,那么,一切外在的贫穷贵贱、祸福得失便无法左右、影响人之作为。所以圣人“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荀子·修身》)。“志意修则骄富贵”,“君子贫穷而志广”。荀子以为,志意修洁、德行敦厚、知虑纯明是人所能拥有的“义荣”。而就知虑而言,用以衡量得失、选择利害,不仅可以应对万变,而且还可以解决疑惑。可谓“知虑取舍,稽之以成”。人之所以成为君子,最重要的是通过应用内在的知虑功能、发挥义辨和能群的特征优势而权称天下。于是志意以之而修炼,德行以之而敦厚,知虑以之而清明,才能养成君子独具的德操,以化导天下。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圣人之材,人皆有天生学得仁义法正之质。如此,君子若能积习礼义,化性而伪起,笃志而不懈,其精神便可达到仁义的境界。
故《荀子·大略》云:“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君子能以义因应,随时变通,知其当曲而曲,故其扬人之美,举人之过,言己之光美,非谄谀,非毁疵,非夸诞;其与时屈伸,柔从如蒲苇;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慑怯,非骄暴也。又仁、义、礼乃人类行己处世之规范,为君子所须持守者,其三者间之关系如何?荀子所言:君子处仁以义,如是则仁而能断,是为仁;行义以礼,如是则断而不悖于礼,故为义;制礼反本成末,以仁义为本,终成为礼节,是为礼。如是三者相通为一,是为道也。因而君子即使贫穷也坚守道义,追求仁德;君子之学,也志在穷而不困,虽忧虑而志意不衰,不是为了追求显达、富贵的人生,而是透彻人生祸福之不惑。
三、在己与慕天:君子人格之淬炼
在“制天命”的过程中,荀子以志作为君子人格淬炼的重要原则,将理想人格的实现与志的修为紧密联系起来,融入了道的原则和义的价值,赋予了道德人生的价值取向,而非梁涛先生所言的“荀子在否定意志天的同时,又不得不对人的命运作出解释、说明,故提出‘节遇之谓命’,用盲目命运观取代传统的道德命定论”[9]。其实,诚如上文所论,在穷与达、德与福的关系上,荀子并没有寄希望于“以俟其时”,更没有把富贵、幸福寄予天命或来世,而是汲汲于“贫而不怠道”的对仁义的坚守、对礼义的追求中,这也正是《穷达以时》“惇于反己”思想的反映。荀子云: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
俞樾认为,“节犹适也,是节然也,犹曰是其适然者也”[10]。“荀子固然可以有‘节遇之谓命’的思想,也可以赋予天以时运的内容,但问题是,作为荀子思想核心的‘天人之分’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来的?” 对此梁涛先生认为,荀子之所以“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因为“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而并非因为时运可遇而不可求,由此认为荀子的“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与《穷达以时》的“惇于反己”是两回事[11]。其实,在此需要明确荀子此段话是在何种意义上展开的?或者说,它的理论归旨到底是什么?虽然笔者也认同梁涛先生的“这段文字仍然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下展开的,是前面‘天人之分’内容的延续”这一观点,但同时也认为,此段文字更确切地说是荀子“知天”与“不求知天”思想在社会人伦中的反映。诚如东方朔先生所指出的:“依荀子,‘敬其在己’即是要人致力于自己当为的事业并严肃认真地完成;‘慕其在天’即是那种心存侥幸、妄想借助天的力量以实现自己愿望的人。物之生在天,而成之在人,废人而思天,非愚即妄。”[12]东方朔先生所言深刻地指出了“在己”与“慕天”之分别所在,即天成与成人。而这里仍需进一步分析君子在己者何?依荀子言,在己者三: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
关于志意修,上文已作论证。而就德行厚、知虑明二者来说,早在《诗经》《论语》等先秦典籍中就有关于君子敦厚之德的讨论。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荀子继承了以上思想,认为温柔敦厚是君子人格的主要特征。“志意致修,德行致厚,知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荀子·荣辱》)荀子虽主张人性是趋恶的,若顺从本然的性情去发展,势必酿成暴乱,走向犯法乱纪。但他对此却不持悲观的论调,而是认为有了礼义法正即可化性起伪,出于治而合于道。而且他认为,君子的修养必须先从志意磨炼做起,骄傲富贵,轻视王公,以发挥个人心智,明辨是非,进而养成坚韧不拔的心志。故曰:“志意修则骄富贵矣,道义重则轻王公矣,内省则外物轻矣。”(《荀子·修身》)由此可见,虽然荀子的“天”为自然之天,《穷达以时》的“天”为命运之天,但基于“天人之分”,《穷达以时》“君子惇于反自”和荀子“敬其在己”的思想均强调淬炼君子人格,故理论内涵和致思路径是极为相似的。对“时”与“命”,荀子和《穷达以时》都在承认人世之命不可抗拒的同时,把视阈投向人之德性的践行及君子人格之养成上:
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困;学非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穷达以时》)
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荀子·宥坐》)
“动非为达也”之“达”即“非为通也”之“通”意,指身份显达、地位崇高而尊贵显赫。君子虽然生不逢时或怀才不遇,但人之为学并非追求富贵显达。荀子强调“德操能定能应”,志意坚定,心忧不衰,故所言“动非为达也”,其意在于,人之有所作为、行动、学习,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显达,不是为了名扬天下,更不是为了欺世盗名,而是为了达至“德行一也”,并经过学习使主体的认识由德行向德性转化,从而使人之德性具有向善的价值取向。《穷达以时》云:“穷达以时,德行一也。”并进而向往“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的潜龙之德。主体在自身德性迁化的过程中,通过“时”或“遇”伦理境遇的不断充实而使君子的人格获得提升。《周易·乾·文言》云:“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倘若道德主体从自身的德性出发,通过培养坚定的意志为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力量之源,则即使不得志也不感到窘迫,不为人所知也不感到遗憾,心忧患而意志坚定,应万物之变而成就伟业。
《穷达以时》和荀子均强调命运对人之际遇的影响。《穷达以时》云:“遇不遇,天也。”人之遇与不遇,有其不确定性,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遇不遇,天也”即是对这种历史必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理论概括。但二者并没有否定人的活动及其作用。诚如荀子重视化性起伪,主张通过渐、化、修、习、积、教等方式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在《穷达以时》和荀子看来,穷达取决于命运,祸福在于修为,明白这种“天人之分”,人则不应汲汲于个人的穷达祸福和现实时遇,而应“惇于反己”,关心属于自己的德性修为。故荀子提出对天的态度是不急、不辩、不察,人之在世,积善成德、成就圣心、完善德性才是职分所在。
四、结语
“分”是荀子德性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划清了“所为”与“所不为”的界限,强调了人之“所为”,反映出其对道德主体的清醒认识,即与“天有其时,地有其材”相并立的“人有其治”。通过对荀子“天人之分”与郭店竹简《穷达以时》中关于穷达、时遇、祸福等范畴的考察可以发现,荀子所谓“节遇之谓命”其实质即是“制天命而用之”,表现在人为追求仁德的汲汲践履之中,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德福、命运观。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将命和个人的道德修养相联系;又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孟子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孔子和孟子所言的“天”和“命”是人所不能改变的客观的决定力量。荀子的“制命”与孔孟不同,其以“分”祛除天的神秘,把吉凶祸福寄希望于现世的德行,重塑人们德福一致的信仰。荀子在此吸取了《周易》“德福一致”的思想。《文言》解释《周易·乾·九二》:“龙,德而正中者也。”《周易》以“中德”为基本准则,建立了对吉凶祸福的判定标准,充分显示了主体对人文道德意识的重视。诚如黑格尔所言:“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和谐,是被设想成必然存在的,或者说,这种和谐是被设定的。”[13]在现世之中,道德与幸福是矛盾的,但在人的绝对意识之中,道德与幸福在精神中达到了统一。 “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荀子·仲尼》)而《穷达以时》的德福观表现为察天人之分,知世而行,因时而达,惇于反己,与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无论是荀子还是《穷达以时》都以“分”为中心,注重在处理福与祸、富与贫、贵与贱的关系之中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