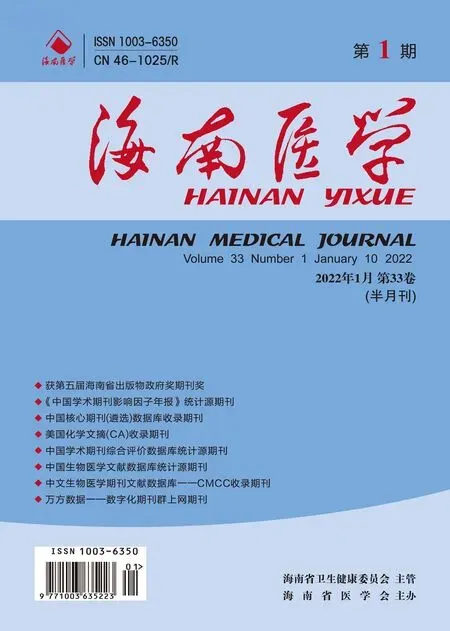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与肿瘤坏死因子-α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赵鹏,金海,朱加兴 综述 庹必光 审校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贵州 遵义 563003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其病理特征为肝细胞内过量的脂质聚积;它的诊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通过影像学或组织学检查证实存在肝脏脂肪变性;二是排除其他明确病因引起的肝脏脂肪聚积,包括过量饮酒、药物(如他莫昔芬)、病毒、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遗传病(如威尔逊病)等。该病有两种主要的病理类型,即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NAFL)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其中NASH可进一步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以及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HCC是该病发展的最终也是最严重的结果,合并NAFLD的HCC患者常年龄偏大,且死亡率更高[1]。NAFLD的发生常伴有多种合并症,如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内NAFLD患者中合并肥胖者占51.34%,在NASH患者中合并肥胖者上升到了81.83%,在某些区域范围内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90%[2]。近年来,肥胖所导致全身性慢性炎症反应越来越被重视,肥胖导致脂肪组织功能失调,促使体内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上调,如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1家族等;在细胞介素-1家族中,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的作用十分重要,其参与了肝病发展的多个阶段。临床调查发现,在NAFL和NASH患者中,这些因子的表达水平与病变的严重程度相关[3-5];NAFLD的发生和进展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除了造成肝脏功能损伤外,NAFLD对其他多个系统(如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等)也有明显的影响[6],且目前仍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案。了解这些炎性细胞因子在NAFLD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将有助于寻找NAFLD预防及治疗的新方法。本文就IL-1β、IL-6和TNF-α在NAFLD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给予综述。
1 健康肝脏到NAFL阶段
在从健康肝脏发展到NAFL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是肝脂肪变性,此时肝脏仅出现脂质聚积,而无细胞损伤[1]。脂质在肝脏的聚积是由于肝脏中脂肪酸的获取与消耗之间存在不平衡,即获取增多和(或)消耗减少;这种失衡可以通过几种途径发生,包括肝脏脂肪从头合成(de novo lipogenesis,DNL)的增加;从脂肪组织分解进入血浆中的脂肪酸的增加;膳食脂肪摄入的增加;脂肪酸氧化以及酮体生成的减少、低密度脂蛋白颗粒(LDL)向肝外转运甘油三酯的减少[7]。
1.1 促进肝脏的DNL过程 DNL是一种复杂且受到严格调控的代谢途径。在正常情况下,机体通过DNL途径将多余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酸,之后进一步将脂肪酸酯化为甘油三酯进行存储,这些甘油三酯在需要时可以通过β-氧化途径为机体提供能量。在人体中,DNL途径主要活跃于肝脏和脂肪组织[8]。NEGRIN等[9]发现即使仅使用生理浓度水平的重组IL-1β处理体外培养的原代肝细胞,经处理的肝细胞中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FASN)、乙酰辅酶A羧化酶-2(acetyl-CoA carboxylase-2,ACC2)等与脂质合成密切相关的酶基因表达水平也呈上调趋势;肝细胞中甘油三酯的累计量增加,并且其增加量随着IL-1β浓度的升高而升高,当重组IL-1β浓度达到10 ng/mL时,经处理的肝细胞中甘油三酯总量与未处理的细胞相比增加了50%;而在使用阿那白滞素(Anakinra,重组型人IL-1受体拮抗剂)处理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模型后,实验组小鼠的肝脏脂肪变性明显减轻,其肝脏重量占体质量的百分比与生理盐水处理的对照组小鼠相比减少了约20%[9];这提示IL-1β能通过上调肝细胞新生脂肪生成进而促进肝脏中的脂质蓄积,在肝脏的脂肪变性中起重要作用。与IL-1β相似,TODORIC等[10]发现,使用TNF刺激体外培养的人肝细胞时,果糖和葡萄糖驱动的肝细胞脂滴积累明显增强。TNF也能促进肝细胞中乙酰辅酶a羧化酶α(acetyl-CoA carboxylase alpha,ACACA)、脂肪酸合酶和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转录因子1(sterol-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1,SREBF1)等与脂肪合成相关酶的mRNA表达水平上调[10]。
1.2 促进脂肪组织的脂质分解 除肝内的DNL外,肝脏中的脂质蓄积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血浆中的脂肪酸随着血液流动经肝门静脉进入肝脏。血浆非酯化脂肪酸(non-estesterified fatty acid,NEFA)池贡献了大部分流向肝脏的脂肪酸,尤其是在禁食状态下;非酯化脂肪酸池中包含来自饮食的脂肪酸以及脂肪组织中的脂肪分解产生的脂肪酸,并且脂解过程所动员的甘油三酯对于维持NEFA池的功能稳定起主要作用[11-12],当脂肪细胞的脂质分解增加时,血浆中脂肪酸水平随之上升;并且同位素人体代谢追踪研究发现,来自脂肪组织的脂肪酸占NAFLD患者肝脏中甘油三酯来源的很大一部分,提示脂肪细胞脂解失衡是膳食诱导NAFLD的重要机制[11];脂肪组织中的脂质分解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严格调节的过程,这些调节信号包括儿茶酚胺、胰岛素、生长激素、利钠肽和一些脂肪细胞因子等,这些信号作用于下游的脂肪酶,进而对脂质分解发挥调节作用[12]。在脂肪组织中,脂滴的大小反映脂质的生成与分解之间的相对速率关系,MIYOSHI等[13]发现,在过表达脂肪细胞中的甘油三酯脂肪酶(adipose triglyceride lipase,ATGL)后,脂肪组织的脂滴较对照组明显减小,即ATGL表达增加促进了脂肪组织的脂质分解;后来YANG等[14]发现,在使用TNF-α处理脂脂肪细胞后,G0期G1期转换基因2(G0S2)的mRNA表达水平显著降低,而G0S2蛋白能够抑制ATGL,减少脂肪组织的脂质分解;VAN等[15]的一项实验发现,在向健康成年男性注射重组人白介素-6后的2 h开始,其动脉血中的脂肪酸浓度开始上升,尤其是低剂量注射时,其浓度可超过对照组60%以上。以上证据表明IL-1β、IL-6和TNF-α通过上调肝脏中的新生脂肪生成以及促进脂肪组织的脂质分解升高血浆脂肪酸水平进而加重肝脏脂质蓄积,在肝脏肥胖性脂肪变性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阶段
美国肝病协会发布的指南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定义是: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脂肪变性,伴有肝细胞肿胀等肝细胞损伤,并伴有或不伴有纤维化[1]。除了单纯的肝脂肪变性外,肝细胞肿胀和小叶炎症是NASH的特征性病理改变。特别是肝细胞气球样变是诊断NASH的关键特征,也是目前使用的NAFLD组织学分级和分期系统的一部分[16]。病理研究证实,肝细胞气球样变与脂肪滴的积聚有关。脂滴在肝细胞胞浆中的积聚可进一步导致内质网的扩张和细胞骨架的损伤,从而促进肝细胞球囊化的过程[17],这种由于脂质积聚对肝细胞产生的损伤作用被称为脂毒性。肝细胞肿胀是脂肪毒性的重要表现。脂毒性使肝细胞处于脂质应激状态,并释放出含有多种物质的细胞外囊泡。这些囊泡中所含的CXCL10、神经酰胺、线粒体DNA和肿瘤坏死因子样凋亡诱导配体(TRAIL)等,这些因子可促进巨噬细胞的活化,并促进巨噬细胞向肝脏的转移和浸润[18]。MIURA等[19]发现,长期高脂肪饮食会使常驻肝脏的巨噬细胞(即库普弗细胞)向促炎的CD11c+表型(也称作M1表型)分化数量增加,并增加促炎细胞因子的生成,如IL-1β、IL-6、TNF-α等,加重肝脏脂肪变性和局部炎性反应。HADINIA等[20]的研究发现,与单纯非酒精性脂肪肝和健康人相比,NASH患者体内的IL-1β和IL-6水平显着升高。当使用NOD样受体蛋白3抑制剂降低NASH模型小鼠体内的IL-1β以及IL-6表达水平后,肝脏中浸润的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量降低,肝细胞的损伤也得到了显著改善[21];也就是说,IL-1β等炎性因子促进肝脏脂肪变性,如继续进展则会进一步引起肝细胞损伤,如肝细胞肿胀,从而进一步促进肝脏炎症的出现。肝脏炎症与肝脏脂肪变性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3 肝纤维化以及肝硬化阶段
在前面已经提到,肝纤维化对NASH的诊断是可有可无的,但纤维化是NASH进展的一种表现。当纤维化发展为晚期纤维化时,可导致肝硬化,最终发展为肝细胞癌[22]。肝纤维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肝星状细胞(HSCs)的活化。此后狄氏间隙中的Ⅳ型胶原被Ⅰ和Ⅲ型胶原所取代,并开始出现细胞外基质(ECM)过度沉积。当病情进一步发展,肝纤维化隔形成及相关的血管改变会逐渐导致肝实质整体结构的改变,开始出现门脉高压及相关的病理生理事件,进而转变为肝硬化阶段[23]。体内多种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因子参与肝纤维化的过程。库普弗细胞是位于肝窦腔的常驻巨噬细胞,约占肝窦细胞的30%。它们在肝脏炎症中起着关键作用[24]。前面已经提及,长期高脂肪饮食会使库普弗细胞向M1型转化的比例增加,促炎细胞因子如IL-1β、IL-6、TNF-α增加,加重肝脏脂肪变性和局部炎性反应。IL-1β可促进肝星状细胞增殖,显著增加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1,TIMP1)分泌,TIMP1能抑制细胞外基质降解,从而促进肝纤维化。在TIMP1高表达的小鼠模型中,肝脏出现严重纤维化[19,25]。静息状态的肝星状细胞经IL-6处理后表型转变为肌成纤维细胞样细胞,肝肌成纤维细胞能促进细胞外基质的合成[23,26]。
4 肝细胞癌阶段
与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癌相比,非酒精性脂肪肝引起的肝癌患者多为年龄较大的女性[27]。此外,有研究发现,即使在没有肝纤维化或肝硬化的情况下,NAFLD患者也可出现肝细胞癌[28-29],并且无肝硬化的HCC患者更容易发生更大的肿瘤,肿瘤复发率也更高[30]。FU等[31]研究发现,高脂饮食显著降低了二乙基亚硝胺(DEN)诱导的肝癌小鼠的存活率,并导致严重的肝功能障碍。高脂喂养小鼠肝内脂肪滴和肝癌细胞数量多于对照组,肝癌沟及周围无胶原蛋白,巨噬细胞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更高[31],这提示由NAFLD发展来的肝细胞癌患者病情加重风险更高。IL-6、TNF-α、IL-1β对肿瘤均有促进作用,它们可以促进癌前细胞的增殖和存活,并在缺氧情况下促进血管生成[32]。IL-6通过激活肝细胞STAT3通路促进肝癌细胞在体内外的生长[33]。一项关于IL-6与肥胖和癌症死亡率的大规模前瞻性研究表明,高体质量指数(BMI)与肝癌相关死亡率显著相关。与BMI正常患者相比,BMI为35 kg/m2的女性肝癌死亡相对风险高1.68倍,男性肝癌死亡相对风险高4.52倍[33]。与IL-6类似,TNF-α也与细胞转化、增殖、侵袭、血管生成和转移有关[34-36]。IL-1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介导肝癌细胞的恶性行为,例如,IL-1β介导同源盒C10(人类肝细胞癌组织中上调最多的同源基因之一)过表达,上调3-磷酸肌苷依赖蛋白激酶1(PDPK1)和血管扩张剂刺激磷酸蛋白(VASP),促进肝癌转移[37]。在肥胖的NAFLD患者中,巨噬细胞向脂肪组织聚集,并向促炎的M1表型分化[38],M1表型巨噬细胞可通过IL-1β信号通路导诱导表达的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PD-L)1,从而调节肝细胞癌免疫逃避和促进肝细胞癌的发展[39]。通过基因敲除抑制IL-1β通路的激活,可以防止肝细胞癌的增殖、侵袭、迁移、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等行为[40]。
5 结语
总的来说,IL-1β、IL-6和TNF-α在NAFLD的初期加重脂质在肝脏的聚积,脂质过度聚积通过脂毒性造成肝细胞损伤,并加重了肝脏中炎性细胞的激活与浸润,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引发肝脏炎症;之后通过促进肝脏星状细胞的活化使疾病进一步发展为肝纤维化及肝硬化;在肝硬化加重为肝癌之后,它们会促进癌细胞的增值、侵袭及转移等恶性行为;目前NAFLD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因此,通过寻找新的靶点来推进该病的预防和治疗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通过抗炎方法治疗NAFLD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已有研究证实,在使用药物等方式使IL-1(α/β)驱动的自身炎症被抑制时,模型动物体内的炎性因子、血脂水平及肝功能指标水平下降;肝脂肪变性和肝细胞膨胀等也得到了改善[41-42];虽然要实现临床应用,还需要更多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支持。但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将对NAFLD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