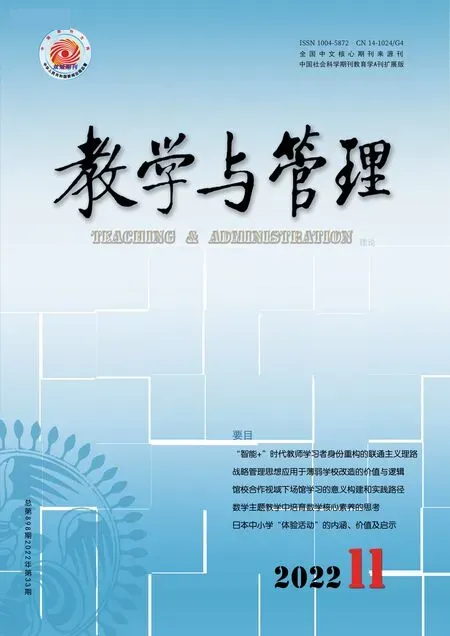“隔离”与“留置”在中小学的异化与回归*
郭未来 吴文胜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杭州,311121)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规定:教师有权以“限时罚站”惩戒学生的轻微过错,也能以“停课停学”来处理学生的严重过错[1]。诸如此类的规定,为教师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惩戒方式和惩戒体系。但是,要落实这些规定,实现惩戒的教育目的,需要教师的实践智慧。因此,明晰“隔离”与“留置”的意蕴、异化及其回归,对教师有效实施教育惩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隔离”与“留置”的意蕴
在中小学,“隔离”与“留置”是教育惩戒的重要手段[2]。“隔离”,即“将学生从扰乱的背景中暂时分离出来”,“中断其扰乱行为”[3]。“留置”,即“放学后把学生扣留在学校里一段时间”[4]。“隔离”和“留置”是指教师对犯错学生活动的强制性限制。在理论上,“隔离”与“留置”主要有两种特性:空间属性和教育价值。
1.“隔离”与“留置”的空间属性
“隔离”与“留置”为犯错学生创设了独立的静置空间。其一是静置空间与学生过错相联系:犯错学生面临与其他学生的冲突情景时,往往难以意识到自身的过错。教师通过“隔离”或“留置”,将学生爆发的情绪状态进行暂时静置。教师向犯错学生明确“隔离”或“留置”是对其过错的惩戒。在静置空间里,犯错学生暂时独处或进行自我独白,认清过错所在。其二是静置空间与教育目的相结合:“隔离”或“留置”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成长。在静置空间中,教师对犯错学生进行教育性引导,鼓励学生尝试着修复人际关系。犯错学生的人际修复从师生关系开始,并以此为指引,与被冒犯者达成和解,逐渐走出作为惩戒的静置空间。其三是静置空间与生活世界相融合:客观上,“隔离”与“留置”会造成犯错学生自由的被剥夺感。在静置空间中,这种被剥夺感产生了“异于常人”的莫名疏远。犯错的学生暂时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自由活动。同时,静置空间也为教师的介入和学生生活世界的展开创造条件:学生在“隔离”与“留置”中冷静下来,然后在教师帮助下,以理性方式去认识自己的过错,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控制情绪的能力。
“隔离”与“留置”为犯错学生创设了特殊的公共空间。其一是公共空间揭示待改的过错:“隔离”与“留置”以强制力介入学生过错,把学生的过错暴露在公共空间。惟有在公共空间之中,“过错”才能称之为过错。如学生不小心磕到自己,这只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而过错却指涉人际之间的冲突关系,只能在公共空间中被揭示。其二是公共空间明示对受害者的补偿:在公共空间中,“隔离”与“留置”是对学生过错的回应,同时也可视为对被冒犯者的补偿。不管是基于关怀的原则,还是基于等价的原则,公共空间中被冒犯者的补偿诉求应该得到尊重和理解。学生因过错而受惩,这是犯错学生的应偿,也是被冒犯者的应得。其三是公共空间启示必然的正义:在公共空间中,通过“隔离”与“留置”对学生的过错进行惩处,启示着必然的正义。“隔离”与“留置”是呈现在公共空间的正义实例。教师、犯错学生以及被冒犯的学生都亲历惩戒正义,体验惩戒正义的感召:犯错必然受惩。
2.“隔离”与“留置”的教育价值
“隔离”与“留置”对犯错学生的教育价值有:其一是学会尊重。教师实施“隔离”与“留置”是以尊重学生主体性为前提的,同时也禁止教师冷漠对待学生。尊重呈现为以教师人格榜样对学生的关注和帮助,是教师对犯错学生负责的表现。“隔离”与“留置”是对犯错学生过错的回应,流露着教师的善意,是帮助学生改正过错的必要过程。在这过程中体现的是教师的尊重,并最终导致学生对他人的尊重[5]。其二是正视过错。“隔离”与“留置”是教师创设的挫折境遇,并在此境遇中引导学生的情感偏向。“隔离”与“留置”的过程同时也是犯错学生对自身过错以及相应惩处嫌恶的过程,其表现为:“隔离”与“留置”中潜藏着犯错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冲突,以及犯错学生对教师干预的反抗。教师在冲突与反抗中引导学生对挫折的承受,并帮助学生正确看待自身过错以及相应惩处。其三是独立反省。“隔离”与“留置”没有割裂教师与犯错学生之间的伦理关系和情感关系,而是进一步为犯错学生的独立反省创造条件。犯错学生在独立空间中更能发现自己的过错,以及明确过错所带来的后果(人际关系的有限剥夺)。犯错学生弃绝自身过错,然后才能复返和谐的师生关系、重获班级归属感,进而更新自我秩序观念。
“隔离”与“留置”对其他学生的教育价值有:首先,“隔离”与“留置”能维护班集体的完整。经过教师的干预,班集体有权拒绝或接纳犯错学生[6]。“隔离”与“留置”致力于弥合班集体的裂隙。“隔离”与“留置”犯错学生是“犯错应当受惩”的共识显现,该共识是班集体共存关系的显现,是维持班级秩序、修复师生关系的必要之举。其次,“隔离”与“留置”能完善班级的人际关系。在班级中,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是共存状态。同学关系对犯错学生实现着三重教育价值:尊重、挫折与独立。以犯错学生为中心,其身处在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的交叉点上,此位置决定了这两种关系只能发挥正向的价值引领作用。教师在对犯错学生进行“隔离”与“留置”的同时,也向其他学生传递着维护秩序的自觉意识。最后,“隔离”与“留置”具有一定的超越价值。“隔离”与“留置”绝非隔绝社会关系的行为,这种保持距离的超越价值就在于犯错学生对社会关系的出离与复返。因此,“隔离”与“留置”可以带给其他学生深刻的认识与反思。无论有意或无意,学生在充当规则的反叛者时,也为其他学生重新思考秩序的合理性提供了难得契机。
二、“隔离”与“留置”的异化
“隔离”所面临的是较为激烈的矛盾情景,教师极易因情景诱发冲动,从而使之偏离教育的准线。当“隔离”本身不具有教育性时,犯错学生也就得不到有效教育。“留置”则要求教师规划实施的范围、程度等关键要素,以免给犯错学生带来身心伤害。在实践中,“隔离”与“留置”主要有两类异化表现,即非教育化与反教育化。
1.非教育化
非教育化的“隔离”与“留置”对犯错学生发展呈现为无意义。无意义在于其意义对于犯错学生不可通达、转移矛盾以及扩大范围。首先,无意义表现为:“隔离”与“留置”与教育目的无涉。教师对犯错学生实施“隔离”与“留置”时,将注意力放在“隔离”与“留置”本身,而没有或无法向犯错学生传递惩戒的意图。如教师将处于斗殴状态中的同学拉开,但没有跟进对“拉开”行为的解释;或者教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评判学生的是非对错,而忽视该解释对犯错学生的可接受性。在这个层面上,教师与犯错学生并没有形成对话关系,沟通和理解就会存在障碍。其次,无意义表现为:“隔离”与“留置”对矛盾的调控失败。教师以强制力去化解学生之间的矛盾,然后在原有矛盾的基础上可能增加师生之间的新矛盾。新矛盾是一种中介,其效力依赖于教师在犯错学生心目中的威信。新增的师生矛盾会影响学生之间原有矛盾的激烈程度。但是,教师如果权威不足,则会导致“隔离”与“留置”出现反作用:弱化教师权威。甚至可能导致犯错学生对“隔离”与“留置”公开表现出不服从,进而激化教师与犯错学生之间的矛盾。这样,“隔离”与“留置”同样无涉教育性,甚至会走向教育的反面。最后,无意义表现为:学生代理实施“隔离”与“留置”。教师将惩戒的权力交予某学生代为实施,最终引发“隔离”与“留置”的非教育化。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隔离”与“留置”的权力只能仅属于教师,而千万不能交给学生去代理。代理实施可能会引发两种极端:其一,让代理实施的学生养成“官僚”作风,助长其权力欲。其二,代理实施的学生承受惩戒实施的风险,可能受到被惩戒学生报复。教师采用学生代理的方式,会在无意识中扩大“隔离”与“留置”的影响范围,引入一些与惩戒教育性无关的因素。
2.反教育化
反教育化与教育规律相违背,也忽视了学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度实施、强加暴力和刻意冷漠。首先,反教育化表现为:过度实施“隔离”与“留置”。教师缺乏对“隔离”与“留置”适用条件的深入分析:一方面,“隔离”对学生过错在此刻的升级趋向极为敏感,其介入对冲突的升级呈现为两可状态。“隔离”对学生争执的过度干涉,则会妨碍学生人际关系的发展。小摩擦和小误会并非全都需要教师进行干预,学生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自主能力。另一方面,“留置”对犯错学生的自由活动采取一定限制,而“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如某教师因学生翻墙外出饮酒,将学生带到水房用水管抽打[7],可以说,此类“留置”已经超出一定限度,会有危害学生身心、触犯法律的危险。其次,反教育化表现为:暴力实施“隔离”与“留置”。教师以强制力去实施“隔离”与“留置”,而忽视班集体给予的权威,也无视犯错学生的身心特点,则会使强制力转化为暴力。如在“隔离”犯错学生过程中,进行强行拖拽、拉扯,则极易引发体罚,造成学生身体损伤。在“留置”过程中,忽视或限制学生生理需求,威胁学生,则会导致心罚,诱发学生的心理疾病。“隔离”与“留置”如果忽视对学生主体生命的应有尊重,最终会导致“暴力干涉”问题。最后,反教育化表现为:刻意实施“隔离”与“留置”。“刻意”是出于教师的非理性,将犯错学生当作自己不当情绪的发泄对象,而不是教育对象。可以说,“刻意孤立”是“隔离”与“留置”的一种异在形态。《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给予了“刻意孤立”的判定依据:目的上,教师主观故意针对特定学生;行为上,教师冷漠应对或制造条件冷漠应对学生正常需求;结果上,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8]。“刻意孤立”已经完全背离了教育目的,缺乏对学生生命的基本尊重,背离学生的成长规律。
三、“隔离”与“留置”的回归
1.尊重主体,生成共识
没有学生不会犯错,关键是教师如何看待学生的过错,以及如何引起学生对自身过错的反思。任何学生都具有独立人格,过错只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或多个片段。教师要尊重学生改过的自主性,并在“隔离”与“留置”中适当地给犯错学生找台阶。教师给犯错学生台阶,并非是一种示弱或者无能,而是为了寻求师生之间的价值共识,向犯错学生释放教育性的善意。犯错学生在“隔离”与“留置”中受到限制,感到不自由或不自在是师生冲突爆发的潜在隐患。犯错学生产生限制感就已经达到了“隔离”和“留置”的客观效果,需要教师及时跟进对限制感进行解释与引导。犯错学生不是被动服从的客体,而是会反思批判的主体。一方面,教师引导犯错学生对自身过错进行回顾,重新感受冲动爆发所带来的失控性灾难。另一方面,教师帮助犯错学生站在被冒犯者的角度,设身处地体会被冒犯者的痛苦与虚弱。
冲突固然是一种可见的过错,但过错的根源在于犯错学生的动机。“隔离”与“留置”须深挖犯错学生的动机,并在动机层面进行纠偏,将其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教师可以通过听取被冒犯者的言辞,或者其他旁观者的陈述,以推断犯错者的动机。教师尊重犯错学生,就是要尊重他的所有言行,并将之视为促进其成长的重要契机。教师要给予犯错学生为自己动机进行辩白的机会,辩白的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另外,教师必须耐心地分析犯错学生的犯错动机,细心地观察他的言语表情、肢体表达以及语音语速,这些都是其动机真实性的有力佐证。这样教师就能得到两种可能的情况:动机合理,行为不合理;动机不合理,行为不合理。动机合理的情况,可以为犯错学生指明一些其他合理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动机不合理的情况,就需要教师久久为功,伺机教育。
2.承担责任,积极筹划
“隔离”与“留置”是对学生冲突的直面回应,也是教师以责任担当回应学生过错的直接表现。教师要将责任贯穿于“隔离”与“留置”过程的始终,并以此维护自身的权威形象。“隔离”与“留置”作为一种惩戒形式,没有权威则无以令犯错学生“口服”,没有责任则无以令犯错学生“心服”。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必须注重自身的权威形象,与学生保持一定距离。与学生靠得过近,会让“隔离”与“留置”变成儿戏。而与学生离得过远,会让“隔离”与“留置”缺乏温度。教师责任不仅具有一定的外显性,还具有一定的内隐性[9]。责任和权威并非一日之功,体现在教师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点滴之中,与学生交流的每时每刻。深入了解班级里面的每一个学生,能让责任在“隔离”与“留置”中发挥关键作用。了解的内容不仅包括家庭背景和日常习惯,还包括教师有意或无意地为学生所“制造”的一次次感动。感动或许是有预设的,但同时也是真实的,它可以是纯粹的“老师为我好”,也可以是含混的“老师对我很负责”。
“隔离”与“留置”本身的教育性有限,因此教师要放宽视野,拓宽相关渠道帮助犯错学生。学生积弊式的过错往往有非常深厚的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学生的价值理念发生扭曲。当犯错学生出现“屡教不改”或者“直言顶撞”时,就更加考验教师的教育惩戒能力。一方面,教师要加强与该学生家庭方面的沟通,尝试着形成亲师之间的教育合力。另一方面,教师要深入考察犯错学生的伙伴关系和同学关系,及时清除造成学生过错的核心因素。当然,教师之间也应针对某些过错的理解和处理进行交流合作,教师的范围包括且不限于课任教师。对于极特殊的犯错学生,为增进对该学生的理解,甚至要进行跨学段的教师交流。教师要对学生的过错事例进行匿名的收集和整理,并建立相关的案例库。总之,教师必须深入分析犯错学生的过错,才能为学生的成长进行深远谋划。
3.慎用惩戒,注重关怀
教育惩戒是一门艺术,“隔离”与“留置”则更是艺术中的艺术,其对教师教育惩戒能力的要求可谓近乎苛刻。教师不仅要对公序良俗、法律规定以及过错事实有深入了解,还必须在冲突情境中保持清醒和理智,避免被卷入。“隔离”与“留置”始终围绕犯错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务必更加审慎。实施“隔离”或“留置”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其一,明确犯错学生的过错所在,避免该学生被其他学生社会性孤立。该举措作为学生过错的应得,不能衍生到过错之外。教师应该留意被惩戒学生是否存在被其他学生孤立的情况,一旦发现应及时加以引导和纠正。其二,明确该举措是对过错的否定,但仅指向过错的事实本身。犯错的学生行为有错,但并不涉及其人格问题。教师在该举措的实施过程中,必须禁止侮辱性的言论和粗暴的行为。其三,该举措兼具惩戒与教育属性,要注意实施的时机。在辩证实施过程中,要引导犯错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惩戒是对犯错学生行为进行否定的过程,教育就是对其行为进行积极引导的过程。
结合法律文本要求,“隔离”与“留置”作为惩戒方式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教师不能忽视对犯错学生的关怀,因此,教师必须深入学习《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及相关法律法规,使实施的惩戒兼具合法性与教育性。学生犯错的根源在于遮蔽了自身的情感偏向,需要教师的价值榜样作用予以引导[10]。教师关怀犯错学生,才能得到犯错学生的理解,师生之间的交流才会畅通。教师关怀犯错学生,就是要让教师在犯错学生面前真心实意地流露自己对该学生的关爱。惟有教师给予犯错学生真情,才能产生真挚的师生情谊。真情的流露建立在对犯错学生的了解之上,它不能含有任何目的性,是一种纯粹的心灵对话,“为他着想”就是这一对话的内在表达。教师不仅看到了犯错学生的此刻过错,更预见了犯错学生的未来。在“隔离”与“留置”中,教师为犯错学生而忧虑,就像为自己忧虑一样,而这忧虑同样会传达到犯错学生心里。总之,“隔离”,不离的是对犯错学生的保护;“留置”,留下的是对犯错学生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