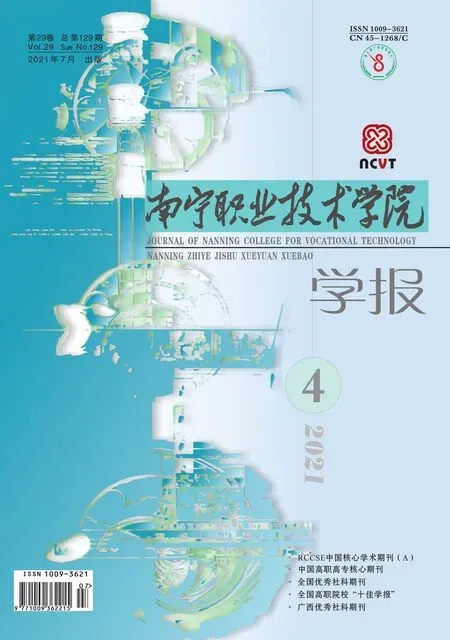壮族花婆形象变异探究
——以广西马山县局仲村内芒屯为例
韦於坊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花婆,又称圣母婆、花王神等,是壮族地区民俗文化中专司生育的女神。壮族地区的先民认为人是生长在花婆后花园中的一朵朵花,花朵代表了人魂,花的荣枯与开败反映人的健康与生死。有关花婆的神话传说至今仍在民间流传,还有不少与花婆相关的民俗承袭发展,如花婆节、求花、还花愿等。民众对花婆的信仰使得花婆神话传说得以流传与演变,并与地方习俗和风物相结合,在各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传说和地方民俗。
一、花婆的由来:由始祖神到生育神
壮族地区的花婆信仰由来已久,《岭表纪蛮》载:“獞俗祀‘圣母’,亦曰‘花婆’。阴历二月二日,为‘花婆’诞期,搭彩楼,建斋醮。延师巫唪诵,男女聚者千数百人,歌饮叫号,二三日乃散,谓之‘作星’。又獞人乏嗣,或子女多病,则延师巫‘架红桥’‘剪彩花’,乞灵于‘花婆’,斯时亲朋皆贺。为其岳父母者,并牵牛担米增之。”[1]记录的是古时百姓庆祝花婆诞生与祈求花婆禳灾除恶的习俗。《南越笔记》记载:“越人祈子必于花王父母。有祝辞云:‘白花男,红花女。’故婚夕亲戚皆往送花,盖取《诗》华如桃李之义。”[2]记录的是古时百姓向花婆求子的习俗。许多学者由此探寻这一民俗背后花婆文化的由来、形成原因,及其发展与演变,其中以姆六甲和花婆的关系之争最为热烈。有学者认为花婆即壮族的创世女神姆六甲(又作米洛甲、姆洛甲等),此观点的论证大多基于古籍记载或口传神话中姆六甲生于花中,且其职能与现在流传在民间的花婆职能相似。
《壮族文学史》(第一册)收录了一则姆六甲神话:
相传姆六甲是一位造天地、造人类和万物的女神。她吹一口气,升到上面便成了天空,天空破漏了,抓把棉花去补就成为白云,天空造成了,她发现天小地大,盖不住,便用针线把地边缘缝缀起来,最后把线一扯,地缩小了,天能盖得住了。然而地又不平了,大地边沿都起了皱纹,高突起来的就是山,低洼下去的就成了江河湖海。她没有丈夫,只要赤身露体地爬到高山上,让风一吹,就可以怀孕,但孩子从腋下生下来,她见地上太寂寞,便又造了各种生物。她的生殖器很大,像个大岩洞,当风雨一来,各种动物就躲进里面去……[3]
由学者蓝鸿恩收集整理的姆六甲故事同样记录的是姆六甲从花中生,但造人情节有些许不同,为捏泥造人。蓝鸿恩认为:“壮族古代神话中的姆六甲,就是花王神的原型。姆六甲是从花朵中生出来的,所以人们都是姆六甲屋后花园里的花转到世上来的。”[4]学者过伟记录整理的壮族民间艺术家黄勇刹讲述的《送红花白花》故事中提到“米洛甲管花山,栽培许多花。壮人称她为‘花婆’、‘花王圣母’”[5]。
从学者们在民间收集到的姆六甲神话传说来看,其中虽有情节差异,但“姆六甲从花中生”“姆六甲造人”的主题不变,可见当时在人们心中姆六甲是一位创世女神,壮族先民的始祖神。随着母系氏族的衰落和父系氏族的逐渐形成,男性始祖神布洛陀形象出现,使得曾作为始祖神的姆六甲地位逐渐下降,有学者分析姆六甲发展演变的轨迹为“原始祖神(生天、育地、养万物)→始祖母神(生育人类和其他动物)→始祖女神(与始祖男神配偶人类)→花王圣母(专司生育)”[6]。
也有学者认为姆六甲不是花婆神的原型。学者黄桂秋认为姆六甲是壮族神话中的创世女神,而花婆只是壮族巫教中信奉的生育神祇,“关于姆洛甲掌管花山,赐花送子给人间的神话包含有明显的宗教巫术观念,纯属壮族师公杜撰”[7]。覃守达认为“壮族乜洛甲崇拜和花婆崇拜在起源与原型及其意象结构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不能随便认为‘花婆崇拜是从乜洛甲崇拜演化而来的’或者‘花婆崇拜的原型是乜洛甲崇拜’”[8]。由于文献资料匮乏,目前关于姆六甲与花婆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神话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不断附会地方风物与传说,因而存在各种异文,这也使得关于花婆的神话传说更为丰富。
二、花婆的变异:由一神到十二神
掌管民间婚育的女神花婆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象与称号流传,某些地区还对花婆的职能做更加细化的分工。对比目前学界对各地花婆的研究,马山县局仲村内芒屯流传的花婆神话中花婆形象有横向与纵向的扩展。
(一)“三肖”花婆
花婆形象的变异常见为从一个女神分化为三个女神。如仫佬族地区的花婆传说中认为花婆为“三肖姐妹”,即云肖、碧肖、琼肖三姐妹;广西柳城县古砦乡的人们将“三肖姐妹”视为祖先,在每年的三月三举行“花婆节”纪念她们[9]。或是将花婆分为三个名号,如杨树喆研究的壮族民间师公教中,花婆圣母被分为“上楼”“中楼”“下楼”三个名号,“这样花婆也随之由一个神演变为三个神,一个掌管长寿,一个掌管生养,一个专司收魂”[10]。局仲村内芒屯的花婆传说在内容上融合前者,“三肖”女神的形象演变为当地花婆的管理者,“三肖”名金肖、银肖和碧肖,金肖分管上楼、银肖分管中楼、碧肖分管下楼。“三肖”女神又由金灵圣母总管。由此观之,内芒屯壮族神话传说中的花婆形象在当地形成了更为系统的分工,突出了当地神话系统中的垂直关系。杨树喆认为花婆分工的产生是当地壮族民间师公教受到外来道教观念的影响,为解决名与实矛盾而想出的办法[10]。
(二)“十二娅”花婆
除了垂直关系上的神职变化外,内芒屯壮族神话的花婆职能还在横向上扩展,将花婆形象分为十二个神,称为“十二娅”①“娅”为壮语音译,表示年老的妇女。。这十二位花婆有自己的名字,互为姐妹,在职能上有更为细致的分工,分管上楼、中楼和下楼,共同掌管地处傲山的花园。
1.上楼
传说上楼居住着一娅、二娅、三娅和四娅。一娅达香②“达”为壮语音译,为用于人名前的称谓词。专管人丁与六畜,还负责管理家庭与财富,此外,家中的门神与灶皇也属她管理。二娅名为达花,负责培育代表幼儿的花朵;夫妇求子后在房间内安置的床头婆即为达花,每年农历六月六③六月六为当地壮族儿童的节日,相对应九月九为老人的节日。要祭拜她。三娅名为达茶,是坏神,平常喜欢撩弄小孩、故意作恶,导致小孩夜啼或生病。四娅叫达酒,负责管理坟山、祖先的坟墓以及家中的纪念堂。
2.中楼
中楼住着四位神,分别为五娅、六娅、七娅和八娅。五娅名叫达绸,专管仪式中供桌上的供品和宴席上的菜品。六娅名达丝,负责管理花芽,即未出生儿童的魂魄,此外,她还负责管理雨伞、药材、针线和衣物等。七娅名达权,是个坏神,相传她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被她扰乱的小孩就会染上无家教、挑食偷吃、偷盗等坏习惯。八娅名达行,负责管理人们建桥填塘。
3.下楼
下楼的四位神为九娅、十娅、十一娅和十二娅。九娅名达布,专管捕捉动物,平日还能为人们消灾除害。十娅名达绸,管理种棉花与纺织,同时负责捡花与夺花,捡花即当有人求子时,达绸就将花从花园里送到求子夫妇手中;夺花即有人做了极恶的事后,达绸就会将属于那个人的花夺回,他就会遭遇重大灾厄或死亡。十一娅达园和十二娅达霞共同负责管理放牛和挑担劳作等事。
相较于其他地区,内芒屯神话传说中的花婆形象有其独特之处,其在人数与职能方面有了横向与纵向的扩展,分工更为细致,神职体系更为完整。十二娅虽有自己的职责,但内芒屯壮族民众在举行求花、护花等仪式时,大多共同祭祀十二位神,极少分开单独祭祀。
三、花婆形象变异中的文化价值观
民间信仰是提供一个可以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的“集体象征”[11]。内芒屯壮族民间的花婆文化,体现了当地壮族人在生命意识、自我认知和性别观念等方面的文化价值观。
(一)生命意识的强化
内芒屯壮族先民相信灵魂不灭,同时珍视今世的生活,对生命持以敬重态度。民众以花为人魂,花的枯荣开败对应着人的生老病死,当人们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时,大多希望通过神职人员查看花园里花的状况,进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得“花”重新焕发生机。这是当地壮族先民朴素的植物崇拜观念,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从花婆信仰仪式使用的道具中可窥见。
花婆信仰仪式中的“花”是至关重要的道具。“花”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彩色剪纸,用红、黄、绿色的剪纸剪成六个双手做上举动作的小孩,在他们托举的中心用纸片剪成细纸条,形似一朵花,六个小孩围成圈,形成灯笼状,像是在共同托举着一朵花;下半部分是一个塑料碗,装满生米,然后把剪纸放置在碗上,“花”便做好了。据道公所述,这一仪式道具象征着小孩的灵魂,碗里的米要给上面的“花”以滋养。以“纳亲架桥”为例,仪式中“花”先后被放置在仙桌上、认亲的桥头边、蓝某耿夫妇的房间里,有着不可代替的象征意义。“花”最先被摆放在“请娅上楼”仪式中仙桌前方的位置,意味着在请十二娅来家中享用祭品时要让她们认识并爱护这个小孩;在认亲过程中,三朵“花”依次从认亲长辈的手中交到蓝某耿夫妇手中,意味着他们愿意护佑该儿童成长;认亲仪式结束后,“花”被放置到靛蓝色布中,由众亲戚用肩膀托着靛蓝色布与花一同走回家,同时还有一名亲戚在一旁将剪碎的彩纸不断朝布与花中挥洒,意味给“花”以滋养。人们对仪式道具的虔诚呵护赋予“花”以生命的象征意义,在人们眼中,对“花”的爱护能在现实中转化成对孩童的爱护。人们的生命意识通过这一过程得到不断强化,进而对儿童的生命观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内芒屯壮族的花婆传统大多是以桥为依托的过渡礼仪。在当地祭拜花婆的各类仪式中,“求花架桥”的求子仪式,是无子嗣的夫妻希望通过求花架桥求得儿女;以除厄退灾、治病转运等为目的的架桥仪式,是时运不济的人希望通过架桥仪式改善自己的运气;“纳亲架桥”仪式是父母希望通过认亲架桥,使自己的小孩能得到更多人的护佑,从而健康成长;小孩成年后举行的“还花愿”仪式,是健康长大的孩子通过还愿表达对花婆的感谢,同时昭示自己进入人生新阶段,如进入婚姻生活等。这些仪式的共同点皆在于表达人们渴望从原先的人生状态中抽离出来,进入新的境遇或状态,体现出内芒屯壮族先民对人生阶段转换仪式的重视和对生命的珍视。
(二)自我认知的变化
与求花架桥、渡厄架桥不同,内芒屯的“纳亲架桥”仪式中对花婆的祭拜更侧重于依靠“人”来解决问题,神的职能和人的职能发生了改变,体现出当地人在自我认知上的变化。求花架桥仪式旨在祈求掌管人魂的花婆通过桥将“花”送到夫妇身边,使其拥有子嗣,得偿所愿;渡厄架桥是期望通过架桥求得神仙保佑,以此退灾改命,二者皆将自身愿望付诸于神,祈求神灵保佑,在愿望实现之后通过还愿仪式对神予以回馈。在“纳亲架桥”仪式中祭拜的花婆十二娅既是祭祀与祈求的对象,同时还多了一重见证者的身份。
“请娅上楼”中,人们将十二娅请到仪式现场,除求得神佑外,更重要的是请神见证认亲仪式,认亲仪式为整个“纳亲架桥”仪式的核心。人们在自然崇拜与生殖崇拜中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意识到人类在改造自然和创造文化上的价值。于是人神职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神由原先的愿望承担者转化为仪式见证者,孩子健康长大的愿望更多地被放置在认亲对象身上,期望认亲后外姓人家也能护佑孩子,使其少灾少难。此外,在孩子长大成年后,不论是否举行还愿仪式,认亲双方长此以往保持拟亲属关系,持续两三代人后才可能终结。相较于向神还愿,认亲更具有人情味,人不再单一地祈求神助,而是通过扩大社会关系来实现自己的愿望。由此观之,内芒屯民众由单独的求神信神向求神与求人相结合转变,神不再全能化,而是转向对人的职能的见证,在此过程中强化了人们对个体能力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本思想。
(三)性别观念的转变
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花婆为壮族女始祖神“姆六甲”演变而成,她由原先的女始祖神转变为专司生育和护卫儿童的神,“姆六甲地位变化之大,普遍认为这是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男女地位变迁反映神话的必然变迁”[12]。父系氏族的兴起使得女性神的地位与信仰逐渐衰微,且旧时壮族农村也存在着重男轻女思想,女性社会地位较低。而在如今内芒屯壮族民众的花婆信仰中,我们能窥视到当地女性神以及女性,因生育与抚养孩子的能力而得到当地人的尊重,男女性别平等思想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
从本次调查的“纳亲架桥”仪式来看,在最初确定认亲对象的过程中,或将第一个路过架桥处的人认为亲戚,或通过生辰八字推算认亲姓氏,两种情况皆不论男女,只要对方同意则举行认亲仪式,并非强求认男性为亲戚。其次,在安置床头婆的神位时,道公要求认亲双方的女性长辈站在花束下举起双手由下至上作捧起花束的动作,这一环节只能由女性完成,肯定了母亲在抚养儿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出当地民众对男女平等观念的发展与深化。
此外,在过去的普遍认知中,男性身强力壮,更适合体力劳作,因而在架设桥梁、捕捉动物、放牛劳作时祭祀的神大多为男神。在内芒屯,花婆变异为十二娅之后产生更为细致的分工,其中一娅管理门神与灶皇、四娅管理坟山与祖坟、八娅管填塘建桥、九娅管捕捉动物等。女性神职不再局限于婚育,其职能的扩大化反映出当地民众在性别观念上对女性予以应有的尊敬,为社会平等和谐发展作出贡献。
花婆这一女神形象在神话传说与信仰仪式的传承与沿袭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体现了文化的地域性和独特魅力,它承载着内芒屯壮人的传统信仰与精神观念,蕴含着人们的民族记忆与民族精神,并反映出珍爱生命、重视个体、性别平等的观念。但以宗教仪式为载体的花婆信仰依然存在着落后成分,我们在对蕴含其中的丰富文化内涵进行学术分析的同时,要警惕其糟粕,引导当地民众理性思考与判断,力求发挥花婆文化在社会导向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