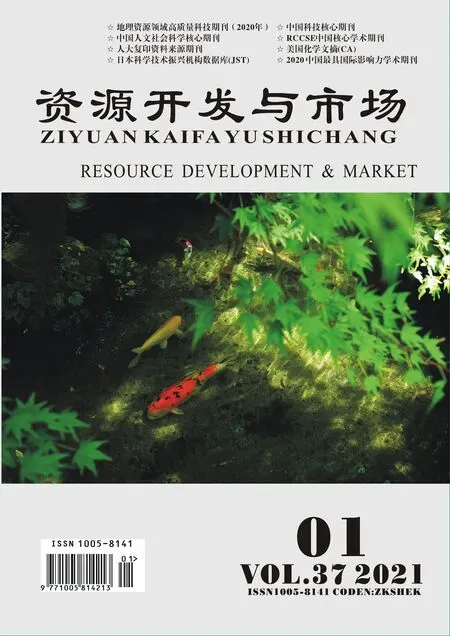西成高铁沿线区域A级景区空间点格局研究
马遵平,谢泽氡,2,林雅琳
(1.绵阳师范学院 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四川 绵阳 621000;2.西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旅游是人们离开日常居住地到异地进行的非谋生性活动[1]。与日常活动不同,旅游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资金和精力,因此在影响旅游决策的诸多因素中,景区吸引力与交通可达性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2,3]。景区是促使人们离开日常居住地,到异地空间进行游憩活动最主要的拉动因素,旅游者通常会选择拥有高级别景区的城市作为目的地,而交通运输系统则是促使异地游憩活动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旅游者进行决策时也会重点关注交通的可达性,在经济成本、旅行时间和舒适度之间进行权衡[4]。现代旅游发展的历程表明,交通技术的变革使得旅游者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转移到更远的地方,缩短了对目的地的空间感知,降低了出游阻力,这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5-8]。
高速铁路简称“高铁”,是指基础设施设计速度标准高、可供火车在轨道上安全高速行驶的铁路。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2019年末我国高铁运营总里程突破3.5万km,占全球高铁里程的2/3以上,成为居民跨区域出游的首选交通方式[9]。与原有的交通方式相比,高铁显著地改变了旅游流的规模、速率和方向,产生了一系列的地理空间效应----时空压缩效应、替代效应、扩散效应、同城效应、过滤效应、马太效应[10,11],在促进目的地城市的空间联结和一体化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2-14]。同时,高铁开通也加剧了目的地的空间竞争,强化了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5,16]。高铁对区域旅游空间关系的再配置,极大地影响了沿线旅游系统各要素的规划与布局,尤其体现在景区方面[17]。
近年来,有关中国高铁与区域旅游空间关系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大多数研究局限于高铁对目的地旅游流的影响[4,10,11,17-19],而由此导致的空间响应——沿线景区的空间格局则鲜见。鉴于景区在整个旅游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和在出游决策中的重要性,对其进行空间点格局分析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高铁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影响,为区域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优化、旅游投资的可行性分析提供支持。
1 文献回顾
高铁的开通提高了目的地的可达性,进而影响了区域旅游流的规模和流向,整体上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但局部并不均衡,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关于中国高铁的研究表明,2009—2013年高铁使国内城市的可达性平均提高了12.11%,但这种改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已经开通高铁的城市,对于西部地区和尚未开通高铁的城市来说则不显著[20]。反映在旅游流上,即表现为高铁开通后客流集中于主要节点城市,然后再向周边扩散,区域空间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趋势[21]。Masson S与Petiot R发现,高铁增强了巴塞罗那的旅游集聚,并形成了马太效应,使一些原先处于劣势的城市,如法国南部城市佩皮尼昂的旅游竞争力进一步削弱[15];杜果与杨永丰在分析高铁网络对重庆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高铁加剧了区域旅游竞争,导致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被边缘化[22]。高铁对那些在区位、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接待设施和交通网络等各方面均具优势的中心城市意义更大,引发的时空压缩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它们作为区域旅游集散中心和扩散源的地位[23]。随着高铁向内陆城市的延伸,这些旅游经济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高铁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旅游城市群的等级结构,重新定义了其中的核心城市[8]。
高铁的开通重新配置了区域旅游市场,最直接的表现是对过夜游市场的影响。Albalate D等分析了西班牙的旅游面板数据,指出高铁只是分流了原有航空运输的游客,总体上没有明显增加过夜游客的数量[24,25];Ure†a J M、Menerault P、Garmendia M选取了欧洲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国内游客和家庭过夜人数作为内生变量,发现高铁带来的驱动效应大于航空运输,这可能是因为高铁刺激了会议和商务需求[26]。受此启发,Albalate D和Fageda X将西班牙的外国游客数量和外国过夜游客人数作为内生变量,发现航空运输带来的驱动效应要比高铁大得多[24]。实际上,早有学者注意到,高铁在开通的初期会对游客数量的增长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会导致过夜游客数量减少和游客类型发生变化[27,28],这主要体现在商务游客增多,低端的有限服务酒店被挤出市场,而那些服务质量好、设施齐全的大型商务酒店成为住宿市场主流[25]。Beckerich C、Benoit-Bazin S与Delaplace M在分析巴黎周边1.5h半径内的高铁效应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9],高铁带来的旅游收益主要流向沿线的中心城市,而对于那些非中心城市,旅游人次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因为过夜游客的比重减少,人均旅游支出实际是下降的[30-32]。总之,高铁压缩了游客在节点城市间旅行的时间,同时也缩短了他们在节点城市的逗留时间[33],旅行空间行为表现出“暂住地—吸引物”模式,这使得那些在“一日游”范围内的景区更受青睐,节点城市的“一日游”市场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中小城市。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高铁与旅游空间关系方面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区域目的地城市尺度,以旅游需求(旅游流)研究为主。景区是旅游产品的核心,旅游系统中的其他要素(餐饮、住宿、购物等)皆是依托景区进行布局[34],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旅游产业空间聚集效应[35]。因此,分析高铁沿线区域的景区空间格局,可以揭示区域旅游产品供给的空间分布规律,为区域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优化、旅游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提供支持。基于此,本文以西安—成都高铁(简称“西成高铁”)为研究对象,获取高铁沿线8个市级行政区的全部A级景区和高铁站点的地理坐标,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空间描述统计等方法对沿线景区的分布热区、不同类型景区的空间点格局和“一日游”圈景区分布进行了分析。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西成高铁按建设工期实际分为两段:绵阳—成都—乐山段和绵阳—西安段。前者是四川省内首条城际客运专线高铁,全长314km,2014年6月通车;后者全长658km,2017年3月建成并接入成都—乐山段。西成高铁是西部较早开通的跨省高铁,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纵贯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穿越秦岭山脉,是我国旅游资源禀赋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截至2019年,西成高铁沿线的8个市级行政区(西安、汉中、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共有301个A级景区,依据景区的主导吸引物类别划分为自然遗迹类、人文遗址类、现代重建或人造类3种类型[36],3种类型及相应等级的景区数量分布见表1。景区及高铁站点坐标数据来源于XGeocoding 地址经纬度批量解析转换工具(http://www.gpsspg.com/maps.htm)。将坐标数据导入ArcGIS10.2软件中,经投影坐标转换后绘制出研究区域的景区和高铁站点图(图1)。

表1 西成高铁沿线区域景区数量分布

图1 西成高铁沿线区域A级景区空间分布
2.2 研究方法
核密度估计:核密度估计能够根据输入的数据点来估计整个空间的数据点的分布状况,可反映一个聚集核对周边的影响强度。核密度估计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空间事件发生的概率越高。计算公式为:
(1)
式中,f(x)为核密度估计值;n为景区个数;h为带宽;k(*)为核函数,(X-Xi)为估计点X到事件Xi之间的距离。
Ripley′s K函数:本研究采用Ripley′s K函数进行空间点格局分析,基本思想是从点群中随机抽取的点落在以定点为圆心,r为半径的圆内的期望点数与空间范围内点密度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2)
式中,A为研究区总面积;n为空间点(景区)数量;uij为两个点i和j之间的距离;Wij是以点i为圆心,uij为半径的圆;I值为聚集指标。当uij≤r时,Ir(uij)=1;当uij>r时,Ir(uij)=0。采用Monte Carlo随机模拟199次,将模拟值的最高值Khi和最低值Klo构建置信区间(上下包迹线区间内),计算相应的实际观察值Kobs和理论值Ktheo。实际值落在上下置信区间内为随机分布;实际值落在置信区间以上为聚集分布;实际值落在置信区间以下为均匀分布。
“一日游”圈:“行游比”是指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旅行时间与在目的地观光游览的时间之比,一般只有当双程行游比≤1.5倍,更有利于旅游者进行出游决策[37]。有研究表明,单程2h以内的旅行时间能够保证较高的“一日游”体验质量[38]。因此,确定以7h左右为“一日游”范围内的最大时间距离。综合考虑旅游者下高铁后换乘前往景区交通工具的时间、途中停顿与延迟的时间和不同等级公路行驶速度等现实因素,最终取实际距离100km为“一日游”的最大距离范围,通过地图量算,在研究区内100km的实际距离相对应的直线距离约为60km。据此,本文以8个市级中心城市站点为圆心,利用ArcGIS10.2软件绘制半径为60km的“一日游”圈。
3 结果及分析
3.1 景区的热区分布
热区分布表明(图2),西成高铁沿线区域的A级景区形成了以西安、成都为中心的双热区。以往研究表明,城市规模是高铁影响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那些拥有更多商业机会和旅游设施的城市,高铁对游客数量的刺激更显著[39]。因此,高铁会进一步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旅游市场地位,强化景区尤其投资经营门槛较高的景区趋近中心城市布局的态势。

图2 西成高铁沿线区域A级景区热区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成都,西安热区的景区密集分布于市辖区内,而成都的热区则形成了以成都市为中心,向南、北辐射的两个次热区,这反映了两个中心城市旅游业极化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研究表明,西安之于陕西省的旅游市场具有“独霸性”,形成了单极核的大西安旅游圈,呈现出单核辐射发展模式[40,41]。西安热区的景区密集分布于西安高铁站“一日游”圈范围内,南向的汉中则并未呈现明显热点,说明西成高铁的开通并未改变陕西单极化的旅游发展模式,甚至有所加强。地处四川盆地西缘的成绵乐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四川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42]。研究表明,成都—乐山段的高铁开通后,成都旅游核心节点的中心作用和对边缘节点的控制力被削弱,而其他城市则有所增强,相互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有了明显的提升[43],在空间点格局上,表现为景区密集分布于各城市“一日游”交集圈内,热区也呈现出辐射融合的趋势。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促进了该区域地理单元内的邻近城市形成共同的旅游市场,同时缩小了城市旅游发展之间的差距。
3.2 不同类型景区的聚集格局
西成高铁沿线区域不同类型的景区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聚集分布状态,这符合Prideaux关于交通系统的变革会导致区域旅游企业的空间竞争力发生变化,从而驱动旅游企业产生空间聚集的研究结论[6]。关于我国长江经济带景区空间格局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可达性的改善加速了区域景区的空间聚集[44]。景区在交通可达性高的空间聚集,可有效降低游客的行游比,形成规模吸引效应,扩大市场容量。因此,景区聚集分布的趋势与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这也是形成区域旅游产业聚集效应的基础。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景区的空间分布受到区域的自然、历史、人口、经济等因素的制约[45],导致聚集程度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可通过地理空间尺度(距离)导致的景区空间点格局变化来识别。
研究区内的自然遗迹类景区在65km范围内呈聚集分布,之外则呈随机分布状态(图3)。在研究区内的122个自然遗迹类景区中,有38个依山沿河分布,另有64个是以特定自然地理条件形成的生物或非生物景观作为主要吸引物。自然遗迹类景区的地理位置相对固定,在较大地理空间尺度上呈现随机分布的特点,但在较小的地理空间尺度,其布局发展则仍然受到区域交通可达性、客源市场范围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图3 自然遗迹类景区聚集格局(1单位尺度=60km)
研究区内的人文遗址类景区在75km范围内呈聚集分布,之外则成随机分布状态(图4)。人文遗址类大多存在于人类定居历史较早且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域[46]。研究区内的人文遗址类景区共有88个,其中成都和西安之和(46个)超过总数的一半,其他人文遗址类景区也主要分布在城市及其周边,因此人文遗址类景区聚集分布的地理空间尺度大于自然遗迹类景区。

图4 人文遗址类景区聚集格局(1单位尺度=60km)
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在研究区内一直呈高度聚集分布(图5)。与其他类型的景区相比,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的形成受区域自然、历史条件的制约小,更有赖后期的投资建设,高铁开通加剧了该进程。高铁对中国经济地理的影响研究证明,高铁显著地增加了节点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那些人口基数较大的城市[20]。成都和西安是两个户籍人口均超千万的大型城市,共有89个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其他6个市辖区只有73个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这表明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尤其是投资规模大的综合性景区更趋向在拥有大规模城市人口和经济体量的地区布局,以获得足够的旅游流,保证其持续经营。

图5 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聚集格局(1单位尺度=60km)
3.3 景区的“一日游”圈分布
“一日游”旅游线路的产品组合简单、易于操作、投入成本相对较少[47],高铁开通减少了过夜游客,强化了“一日游”市场。围绕着8个市级中心城市,西成高铁沿线形成了8个半径60km的“一日游”圈和4个“一日游”交集圈(图6)。

图6 西成高铁沿线区域A级景区“一日游”圈分布
分布在“一日游”圈内的A级景区多达266个(占总数88.4%),其中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150个(占总数49.8%),说明研究区内以景区为核心的一日游产品的供给已具备一定的规模。4个“一日游”交集圈分布在绵阳—成都—乐山一线的城市群区域,交集圈内的A级景区共有85个(占总数的28.2%)分布较为密集,其中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达到62个(占交集圈景区数的72.9%),反映出西成高铁的绵阳—成都—乐山段已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旅游空间竞争。
4 结论与讨论
高铁建设极大地强化了我国以城市旅游为基础的经济关系[48,49]。近年来关于中国高铁与旅游空间关系的研究受到重视,但大多数的研究仍局限于高铁对目的地城市旅游需求(旅游流)的影响,而由此导致的空间响应——景区的空间点格局则鲜有研究。从供求关系看,景区作为区域旅游产品的核心,其空间分布必定会受到目的地城市旅游流的影响。与此同时,目的地城市旅游流的形成也有赖于景区产品的供给,并随着高铁的开通愈加明显。日本九州新干线的研究表明,高铁促使游客聚集在拥有丰富旅游资源(自然风光和历史遗产景区)的城市,加剧了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不平衡[30]。因此,景区的空间格局是区域旅游经济关系在空间上的映射。对高铁沿线景区的空间点格局的研究,可进一步明晰高铁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影响,有助于区域旅游吸引物和设施的整体优化布局。
西成高铁作为我国西部地区较早开通的跨省高铁,对带动沿线区域的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成高铁沿线的8个市级行政区共有301个A级景区,形成了以成都、西安为中心的双热区分布和由成都向乐山、绵阳辐射的2个次热区分布;沿线区域的人文遗址类景区和自然遗迹类景区分别在65km和75km范围内呈聚集分布,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则表现出高聚集分布;有88.4%的A级景区分布在8个中心城市的“一日游”圈范围内,28.2%的A级景区分布在绵阳—成都—乐山的一日游交集圈内,且大多为现代人造或重建类景区。
相对于高铁开通后带来的区域旅游流的迅速变化,景区的投资与开发对此变化的响应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因此,现阶段高铁沿线景区的空间点格局,可以视为高铁开通一段时期以来对沿线景区布局影响的空间呈现,这也是本研究的立论基础。未来通过监测不同时期的景区地理坐标及相关数据的变化,可进一步揭示高铁沿线景区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和高铁对这种演变过程的地理空间效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