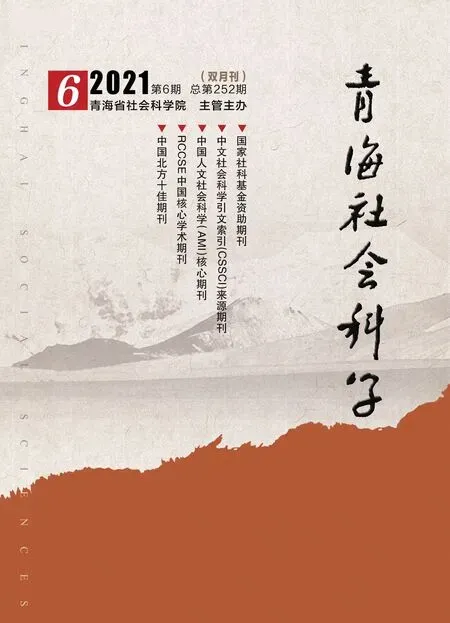小说《帕洛马尔》引发的对自我、语言、离言问题的思考
◇陈 曲
当代著名的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小说《帕洛马尔》是其小说艺术的总结,同时成就了他思索性小说的高峰。无疑《帕洛马尔》是卡尔维诺对世界思索的结晶。卡尔维诺认为认识世界与自我是人类追寻的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包含了人们赖以活着的全部基础与意义。认识世界的基石是自我,然而在卡尔维诺深究自我的过程中,发现其吊诡的存在,它是以语言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中。而语言如影随形在我们自我建构的每一步,并继续在认知真理的路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卡尔维诺试图在《帕洛马尔》中,以小说家的方式记录自己对自我、语言的思考及对真理的追寻。本论文细捋其思索的轨迹,梳理自我、语言以及最终进入沉默与离言的逻辑路线,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牵扯出来的种种问题及引发的思考。
一、问题的引出
卡尔维诺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帕洛马尔》试图通过小说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对真理、意义求索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中,卡尔维诺借用了三种方法:观察、语言及沉思。而实际上观察及沉思最终都得汇入语言。语言是其他两种方法展开的方式。那么我们首先从卡尔维诺对语言的探讨开始入手: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的“三.一.二.蛇与人头骨”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帕洛马尔先生在墨西哥参观托尔特克人的古都图拉的遗址。陪同他的是一位墨西哥朋友,而这位友人在每一块古代石刻面前都停留一下,讲述这块石刻的神话故事,指明它的寓言和道义上的反思。正当这时,来了一群学生,跟随他们的老师总是在给学生描述完一样石刻时加一句“不知道它有什么含义”。当他们来到一个叫作蛇壁的雕刻面前,老师说:“这是蛇壁。每条蛇口里都含着一个人颅骨。不知道这些蛇与颅骨有什么含义。”那位墨西哥朋友沉不住气了,说道:“怎么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含义!它们表示生死相连,蛇表示生,颅骨表示死;生之所以为生,是因为它包含着死;死之所以为死,是因为没有死就无所谓生。”[1]291帕洛马尔在钦佩墨西哥朋友博学的同时,也尊重那位老师的态度,他想:“一块石头,一个人像,一个符号,一个词汇,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它们,那么它们就是一块石头,一个人像,一个符号或一个词汇。我们可以尽力按照他们本来的面貌说明它们,描述它们,除此之外不应该有其他作为;如果它们的本来面貌后面还隐藏着另一个面貌,那我们不一定要知道它。拒绝理解这些石头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也许是尊重石头的隐私的最好表示;企图猜出它们的隐私就是狂妄自大,是对那个真实但现在已失传的含义的背叛。”[1]291通过语言来追寻意义,也许正是对意义的背叛,因为“任何一种解释又需要另一种解释,环环相扣”,那么意义就在这一环套一环的无限解释中延宕。借助语言去寻找意义,反而我们可能会迷失在语言的重复中。找到的不过是意义的碎片。卡尔维诺又在“二.三.二.白猩猩”一节中,描述了一个名叫“白雪”的白猩猩。白雪将一个汽车轮胎紧紧抱在胸前。卡尔维诺这样写道,“在漫长而黑暗的生物进化之夜中,人类文明的第一束曙光就是这样出现的。白猩猩要模仿人类这样做,手上只有一个汽车轮胎。这个人类生产的制成品,对白猩猩来说就是毫不相干的,它不具备任何象征性,也没有任何意义”[1]283,这是个抽象物,即使白猩猩对它加以认真思考,也不可能从中悟出许多东西。但是,“有什么能比这样一个环状的空心物更能盛装各式各样的意义呢?也许白猩猩在思想上如把自己等同于这个轮胎,便可能走到沉默不语的尽头,发现语言的源泉,并在它的各种想法与那些决定它的生活方式却未曾用语言表达然而是显而易见的各种事件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1]283在本节结尾处,帕洛马尔心里想:“我们大家手中都旋转着一个旧的空心轮胎,并想借此找到语词本身并未表达的最终含义。”[1]284
那么这里我们会发现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有关自我的问题。卡尔维诺之所在借助语言去寻找意义的路上受阻,是因为有自我的存在。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将语言视为工具,而自我便是使用这个工具的主人。所以这个工具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主人的特性。卡尔维诺认为,语言处处弥散着自我的气息。也恰恰是因为这个自我的存在,使得语言没法通向真理之途。自我便是通向真理之途的最大障碍。而在自我掌控下的语言,更是无法走向意义的腹地。那么我们首先得了解自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它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二是关于语言本身的问题。卡尔维诺觉得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是碎片式样的,丧失意义的。他希求对意义的持存。那么是否存在更好的语言,与我们此刻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或者说一种与世界、思合一的语言?如果有,它是否能带我们进入真理?而卡尔维诺提出的“沉默”,是否便是追寻真理的最好方式?
二、自我——一种语言的存在
我们首先从“自我”这个概念入手。粗略地捋一下西方哲学关于“自我”的探讨线索。自我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它是肉身还是精神?抑或者是精神与肉体的综合?在传统的意义里,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自我是一种精神存在。但自我如何认同自己,作为一个人如何确定自身?奥古斯丁较早地涉及了有关“自我同一”问题。他认为人能够自我理解,心灵一旦产生,这种运动便开始了,他称之为“自知”的活动。自我是“时”“是”“思”的统一体。自我首先是自我,它必然在时间中延展,既面向过去又面向未来,不然,自我同一就没法理解。之后的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中确立了自我的第一性,然而这个自我对时间的缺失,无法完整,所以笛卡尔寻找了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虽然我看到在我的本性中的这种缺陷,即我不能不断地把我的精神连到一个同一的思想上,可我仍然由于一种专心一致的并且时常是反复的沉思,能够把它强烈地印在记忆中,使我每次在需要它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它,并且由于这种办法能够得到不致犯错误的习惯。”[2]28但是问题紧接着而来,笛卡尔将自我记忆建立在理性世界之上,如果世界是混乱的,记忆便无法起作用,那么自我的同一性和连贯性也将无法实现。然而理性主义者忽略了这点,认为自我即具有同一性,它就是这个坚实并可以依靠的精神存在,将之推到本体的位置。这样自我与客体的对立越来越明显。并将对世界的认知建立在这种自我同一的基础之上。
然而裂痕还是出现了,当人们高举人性,在对人力量的充分肯定中,休谟开始重新思索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自我。笛卡尔的自我给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而在休谟看来人是不可能感知到事物背后的实体的,有关自我这个实体也一样。休谟说自我是“处在永远流动和运动之中的直觉的集合体或一束知觉”[2]45,自我是复杂的,甚至是断裂的,不可能存在同一。如果自我没有了同一性,那么以自我为基础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没办法保证其正确性了。自我变成了流动的,不是稳定不变抽象的实体。而康德对先验自我的改造并没有真正实现对它的批判,他没有放弃实体自我。尽管他尽力不把自我与实体划上等号。在胡塞尔那里,依然相信真理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我。他认为任何一种知识都必然是在逻辑上设定的意识结构。并再次强调哲学是哲学家的个人事务。胡塞尔按照皮浪主义试图将事物悬置起来,“一切在有机体上被给予的物质物都可能是非存在的,但没有任何有机体上被给予的体验能是非存在的。”[3]这样,胡塞尔将世上一切的事物都还原成了意识存在,除了绝对意识。绝对意识变成了绝对存在。他将先验自我预设成了创造世界的本源。
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在上面这一条有关“自我”论述的链条当中存在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如果“自我”持存,那么自我持存的表征是什么,我们如何觉察到这个自我。二是“自我”是否能脱离时间而持存。
有关自我是否能够自我指认,其实追寻到最后,似乎还是绕不开语言。我们借助语言给自我一个落脚点。自我成了一个充满语言的场域。或者说它就是语言本身。思考一旦开始,其实都是符号化的过程。或者说思考与符号化是一体的,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思考的展开就是语言的展开。当我们去思维自我的本体时,恰恰是通过语言进入到语言之中。那么第二个问题有关自我的持存便可迎刃而解。自我本身本来就是语言的一种建构。何谈实体?如果自我的持存一定要放在时间的维度才成立的话,我们会发现时间也不过是我们语言思维的一种建构。那么我们似乎便可以将自我全部还原到语言的层面。
与此同时,理性与自我这对概念,二者似乎先天就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理性帮助自我找到了同一性以及主体性,而自我的同一性与主体性使理性成为可能。在两者紧密结合后,开始对世界进行同一性的法则。自我借助理性把自然的外在存在变为内在意识,通过理性的逻辑认知,对世界重新摆布、计划,从而试图获得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和自我的确定性。然而实际上理性依然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想象和建构,是自我的一种分别与计度。理性是自我给自己设计的外衣,好掩盖自己弥散的事实。如果结合上面所分析的,自我本身即是语言,我们很难体认出一个游离于语言之外的抽象的自我。那么理性其实也可以被看成是语言的一种建构。理性的先验性我们无法体认,就像我们无法体认自我一样。理性不过是来自语言的假设。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离开自我,达到对世界的认知呢?也许这个问题太过吊诡。我们只能按照胡塞尔规划的路线,先将客观实体世界存而不论。然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然没有办法逃离自我,同样,自我的的确确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维度。也许这个维度有很多局限,然而我们不可能将之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
我们回过头看卡尔维诺的思索,其实一直纠缠卡尔维诺的问题就是有关自我的问题。他认为自我妨碍了与世界的亲近。它成了壁障,一旦沾染了自我的习气,就会破坏世界的和谐,从而无法找到意义的源头。在这个逻辑的推导下卡尔维诺认为人类目前使用的语言是完全沾染了自我习气的语言,它以理性为特征,对世界万物进行同一化的讨伐。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站在语言的角度去看,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摆在那里,也不存在等待我们剔除的自我的习气。同时语言也并非被理性污染,理性不过是语言的一种建构而已。所以一切又都回到了语言的层面。那么困扰我们的是,我们人类目前所运用的语言是否就是完美的语言?如果语言是通向真理的桥梁,并一度有人认为语言就是真理本身,那么我们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是否已经无事可做呢?
三、两种语言
(一)世间的语言
在《圣经》的开头称上帝与其逻各斯运行于水上,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世界就有了光。逻各斯可以理解成语言。上帝造世界用的就是语言。或者说这个世界是在语言中展开的。没有语言,世界即不存在。世界是在语言的明晰中逐渐展开的。上帝与语言是不可分的,语言同这个世界密切相连。此刻的语言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与神秘的气息。直到人类建造巴别塔,威胁上帝权威时,上帝让人类的语言变乱,彼此互不相通。人类忘记了原有的那个统一的,与世界合一的语言。语言随之变成了众声嘈杂。在《圣经》的这个故事里我们发现语言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原初的,充满巨大力量,与世界合一的语言;另一种是分别的、杂乱的、无法通向最终真理的嘈杂的语言。
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中提到的一环套一环的语言,“任何一种解释又需要另一种解释,环环相扣”,这样的语言便是上文提到的第二种语言。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第二种语言呢?这种语言正是大众使用的世间语言。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大众认为语言即发声器官与听觉器官的活动。我们将语言看成人的表达,是人的活动,是一种形象的概念性的再现。“人们把表达看作人类各种活动中的一种,并把它建构到人借以造就自身的那些功能的整个经济结构中去。”[4]5这第二种语言披着理性、逻辑的外衣,对一切进行重新摆置,计算。卡尔维诺认为通过这种语言无法到达真理的腹地。意义只能在嘈杂的喧哗中丧失。正如德里达提出的概念:“延异”“撒播”。语言以这样的运动或生成方式来自语言符号体系内部,不指向语言链条之外的任何先验概念。就像德里达说撒播“既不追溯某种原始的在场,也不神往将来的在场”,撒播在延异的链条中产生了多样性的语义。它是迷乱的,没有确切的指向性的,在语言的海洋中沉浮。语言在此不指向语言体统之外的任何东西。能指与所指是断裂的。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里用白猩猩手里的旧轮胎比喻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已经不复是与世界、思合一的语言。它变成理性的象征物,自我中心最后的避难所,关注于某种实在之物。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允许有任何裂隙存在。世界的存在在这种理性的彰显中被遗忘了。语言不复关注存在与意义。而卡尔维诺无法阻止这样的语言继续繁衍。在它控制的解释下,世界被粗暴地放置于人的计算与摆置之中,而解释一旦开始,就沾染了自我局限,意义悄然遁形。然而卡尔维诺明白人们最尴尬的处境是,我们只能依赖这样的语言认识世界,如果语言世界只是符号的狂欢,那么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曾经表述过三个命题:(1)无物存在。(2)即使有某物存在,我们也没法认识。(3)即使某物被认识,也无法用语言说出来。[5]我们的自我从上文论述看本就是语言的汇成,按照高尔吉亚的这几个命题,可以推论我们认为的外物无非是我们语言的一种建构。所以从这意义上说无物存在。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无非是用语言对其的描述、建构、摆置,所以也没法实现对物的真正认识。变乱的语言、世间的语言、充满延异与撒播的语言都是卡尔维诺认为一环套着一环需要不停解释的语言。以为是走在追寻意义的锁链上,原来不过是走在语言的迷雾森林中。我们似乎跳不出这语言编织的网,连自我也成了语言的一连串言说。
(二)神圣的语言
那么是否存在像《圣经》中提到的第一种语言,上帝运用的语言,与世界合一,充满神秘与力量的语言?我们会发现在人类早期的文明中都充满了对这种神秘语言的记载。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中国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名,可以理解成名称、称谓,也就是语言。有了称谓,有了语言,大地豁然展现,语言是万物的母亲,万物因语言而生。因为语言独有的理性与明晰,让原本不存在的或者是浑然一体,不能被人所认知的世界刹那间展开。老子说的无名,是相对于有名来说的。一种是语言,一种是非语言。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没有名,又何来无名,二者虽然是两种相,却隶属于一个逻辑链中。天地的开始,万物的初始是酝酿在无名之中的,而这个无名其实亦是一种语言。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语言的语言,人们又如何去理解天地之始。所以它依旧包含在语言之中。而这种语言正是上帝运行于水上,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语言。它带有原初性。未经人类工具理性的玷染,不是琐碎、无意义的,片断式的,而带有与原初世界的合一,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是人类武断式的强行切割,而是充满了诗意与神秘的原始气息。
但是这种将语言神圣化,为其找到神性本源,就是我们想要追溯的最终的语言形态吗?在这样的语言中,人类的求索可以终止,意义得以圆满的展现吗?或者说这样的语言难道不也是一个赫然存在的“大我”的一种表达吗?如果说现在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沾染了盛气凌人的气息,在逻辑推演中计算世界,那么第一种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充满神秘与力量的语言,难道不是跟第二种语言充满了相似的构成吗?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与这种把语言标画为纯粹人类功能之一的做法相对,另外有人强调,语言之词语有其神性的本源......但人们不光是要把本源问题从理性逻辑的说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且也想消除对语言的纯粹逻辑描述的界限。与那种把概念当作词语意义惟一特性的观点相反,人们把语言的形象特征和符号特征推到突出的地位上。”[4]5这种神圣化的语言不过是看似与我们日常语言相反,然而内部运行机制却全然相同的语言。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尽管以截然不同的姿态出现,然其本质却是一致的。这种语言也是以工具的姿态出现,它没有独立的意义。而以这样姿态出现的语言,通过它的指引,我们很难说就一定能见到澄明的真理。因为这样的语言虽然与第二种语言不同(第二种语言是众声喧哗,意义在解释的锁链中悄然丧失),但它的意义全部来自一个主体性的权威(这个权威或者是上帝,或者是众多民族原始时代设计的各种创世神)。意义之所以发生,语言之所以具有有效性,其全部解释都来自这里。问题似乎走到了一个困境。
四、沉默与离言
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在面对学者朋友口若悬河地去解释古代石雕的各种意义的时候,帕洛马尔先生心想,“拒绝理解这些石头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也许是尊重石头的隐私的最好表示。”[1]291当帕洛马尔先生在动物园看到一只白猩猩抱着一个旧轮胎时,他想“也许白猩猩在思想上如把自己等同于这个轮胎,便可能走到沉默不语的尽头,发现语言的源泉,并在它的各种想法与那些决定它的生活方式却未曾用语言表达然而是显而易见的各种事件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1]283可见卡尔维诺在面对纷乱而无意义的语言时,试图通过沉默来实现对意义的尊重与持存。卡尔维诺不愿如德里达一样,否定意义的存在。他将意义保存在沉默里。试图用非语言的沉默让意义持存。我们的日常用语仅仅只有一种维度,那便是在逻辑精神下对物的世界的指称意义。而这种语言切断了人与世界的通道,世界的本真意义在这里被掩盖。语言堕落成为理性的工具,人成了语言的主人。而在这样的语言的主导下,人们具有“观点”却没有了“思”。它将我们与世界分开,掠去了我们的“思”之渴望,对意义的守护。语言失去了通向不可言说的道路,这个道路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指与所指占满,而没有任何超验意义存在的空间。而唯有沉默是语言的另一种形式,或者说是语言本真形式。它独立于世界与主观自我,隐遁在世界之中。让语言不再是一种工具,让我们走向语言的源头。这是抛弃了我们引以为傲的理性绝对中心的语言,它来自最初的世界而非人的想象。
卡尔维诺认为沉默也许才是保有意义的开始。唯有在沉默中,人与物之间,词与物之间不再是一方凌霸另一方,一方屈从在另一方的权威之下。不再是人们用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以受过逻辑训练的心灵对词与物的粗暴摆置。然而沉默无语并非死寂,就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无声中保持的不过是声响的不动。而不动既不是作为对发声的消除而仅仅限于发声。不动本身也并不就是真正的宁静。不动始终仿佛只是宁静的背面而已。不动本身还是以宁静为基础的。但宁静之本质乃在于它静默。严格看来,作为寂静之静默,宁静总是比一切运动更动荡,比任何活动更活跃。”[4]22在这样一个充满丰盈的沉默中,卡尔维诺试图克服语言与自我对事物的压迫。在沉默里,不是对语言、自我的全面否定与驱逐,而是以一种更为宽广的姿态,召唤着词、物、主体,并得以安放。我们在静默中,找到了语言的源头。这是前语言状态,一切都安然自若。
但是当问题推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这种静默、沉默、宁静,是否就是我们追寻真理的腹地。沉默,是否能理解成老子所说的无名。无名,天地之始。无名与有名是在同一个逻辑链条当中的。无名其实亦是语言的另一种姿态。天地玄黄,混沌一片,是否就是无名对应的世界,就如同我们以有名,而生万物的世界。那么他们的深层机制还是一样的,最终都还原成了语言。无名是语言的另一种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做结论,世界不过是语言的诉说,所有真理与意义,都逃不过语言的给定。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离言的事物,意义或精神?
我们都知道《道德经》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似乎是悬挂在人们头顶的一个寓言,默默诉说着什么。它在挑战语言的边界。以语言的方式暗示一个超出语言之外的“道”。当我们发现世界与语言异常紧密的关系后,一个超出语言的世界却在召唤着我们。那是离言的,借助语言永远无法达到的。语言无论以任何姿态出现,都不仅不再是通道,反而成了认识的障碍。卡尔维诺说:“我们大家手中都旋转着一个旧的空心轮胎,并想借此找到语词本身并未表达的最终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沉默是不可言说的开始,而不可言说是通向意义的道路。正如中国禅宗中对文字、概念、逻辑的破除,无非也是对离言境界的追求。超出语言,方才是进入真理的开始。而这也可能是卡尔维诺对语言的最终想象,对意义的最深求索,同时也是一个新的问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