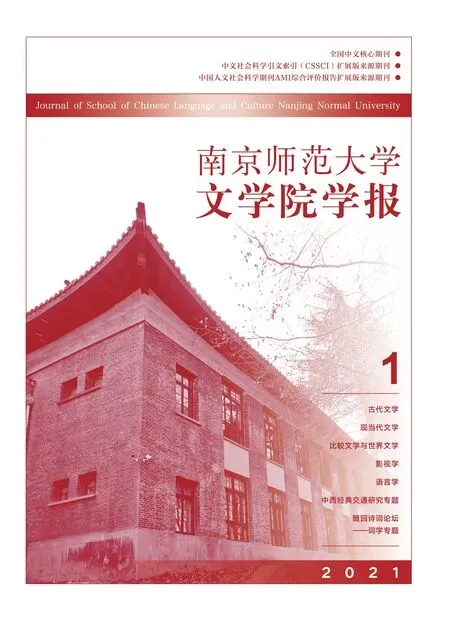代际间的幽灵
—— 论《单手掌声》中二战创伤叙事
施云波 朱 江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常州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2014年布克奖得主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1961—)是当今澳洲文坛知名的左翼作家。他长于描写底层的疾苦,社会边缘人员的挣扎,书写澳大利亚历史的创伤。他20世纪末创作的小说《单手掌声》(TheSoundofOneHandClapping,1997)取材于澳大利亚二战后斯洛文尼亚难民移民的创伤故事。弗拉纳根的父亲曾在二战中沦为日军战俘,妻子玛嘉达就出生在战后移居澳大利亚的斯洛文尼亚难民家庭,可以说《单手掌声》是一本带着作家体温的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作家通过书写平复家族创伤的疗伤之作。
《单手掌声》的故事概况如下:澳洲斯洛文尼亚二代移民索尼娅成长在塔斯马尼亚简陋的工棚里,在她三岁时,难民母亲在一个风雪夜突然消失,而索尼娅对那晚的情形完全失忆。自此,消失的母亲成为了家族的幽灵,她是父女意识表层不能谈论的禁忌,但在无意识中以一种“缺席的在场”占据父女全部的生活。父亲酗酒家暴,索尼娅则是麻木自残。为了逃离家族创伤,索尼娅16岁离开家乡前往悉尼,但从创伤的物理空间逃离的结果是心灵永陷创伤的时空。最后为了避免与母亲相同的命运,终止创伤的传递,索尼娅一步步回到家乡,回到斯洛文尼亚民族在二战中的过去,创伤幽灵的面目渐渐清晰……
相较于直接描写战争惨烈的弗拉纳根布克奖获奖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TheNarrowRoadtotheDeepNorth,2013),《单手掌声》更侧重从间接的角度切入,分析战争创伤作为一种事后影响在家族中的代际传递。这种传递以一种幽灵般的神秘方式进行:一方面人物意识的表层对超越理解和接受能力的创伤产生了记忆的缺失,另一方面过去的创伤成为了家族甚至民族的“记忆之场”,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在几代人中无意识的传递。只有直面创伤的魅影,努力寻求救赎,才有可能切断创伤的时空传递。弗拉纳根对普通难民家庭创伤书写的背后是二战给人类心灵造成的苦难,这种苦难在战争结束后远未停止。
一、意识表层创伤记忆的缺失
心理学研究集大成者弗洛伊德在他那篇重要的论文《暗恐》(“TheUncanny”,1919)中,以霍夫曼(E.T.A. Hoffman)的《沙魔》(TheSandman)为分析对象,阐述文学作品中的暗恐(非家幻觉)(1)参见:童明.暗恐/非家幻觉[J].外国文学,2011(4).其实是过去某个被主体意识压抑的恐怖性经验的强制复现。20世纪中期,匈牙利心理分析家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与托罗克(Maria Torok)在吸收弗洛伊德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代际间幽灵论”,指出家族中隐秘的创伤往往以无意识的形态发生代际传递,如同幽灵般纠缠在受创主体的下一代身上,使他们产生人格的分裂。两位心理学家合作的专著《外壳和核心: 心理分析的更新》(TheShellandtheKernel:RenewalsofPsychoanalysis,1994)对代际创伤的“幽灵”(phantom)是这样论述的:
这是一个事实,幽灵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仅仅是生者的发明。是的,一个发明,即使是在个体和集体的幻觉伪装下,这个发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由于一些爱的客体生命的隐藏而产生的鸿沟的具象化。因此幽灵是一个元心理学(2)元心理学又译“后设心理学”,是以心理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深层理论,又称“心理学的心理学”,是关于心理学基础和界限的学科。的事实,长期纠缠我们的不是死者,而是他者的秘密给我们留下的鸿沟。[1](P171)
由此可见,幽灵表面上是死者的鬼魂,实际上是受创主体心灵的投射,受创主体在创伤事件上失忆造成了认识的鸿沟,使他们深受煎熬。他们的生活被割裂成两重空间,第一重是当下熟悉而真实的世界;另一重是创伤幽灵时时造访的隐秘的空间,为了保护自我免于崩溃,受创主体将创伤完全隔离在不为意识所知的角落,形成“秘穴”,无法承受的痛苦被隔离、埋葬,自我的意识无力感知创伤。《单手掌声》中代际间的幽灵造成两大结果,一是受创主体无法在意识层面感知神秘创伤的本源,每一代人都只能选择将创伤压抑、掩埋或封缄,表现为失忆或回避创伤经验来放逐记忆;二是幽灵的强制回返必然会使创伤在人物的无意识中代际传递。
二战斯洛文尼亚难民母亲玛利亚、父亲博扬、女儿索尼娅都以各自的方式放逐不能移除的创伤记忆。《单手掌声》的开头,玛利亚行走在塔州的丛林小路上,此时玛利亚既是受害者,也是丈夫和女儿的加害者,在此后的岁月中,玛利亚将作为“缺席的在场”,存在于父女的创伤记忆中,直接导致了父女生活的崩溃。母亲玛利亚之所以以放弃生命为代价来放逐自己的记忆,正是因为记忆的惨烈使她无力承受。玛利亚是家庭、民族创伤的承受者,她成长于二战这个动荡的年代,又不幸身为纳粹统治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处在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宗教的双重歧视下,玛利亚的父亲从事斯洛文尼亚民族地下抵抗运动,不慎被同族的天主教牧师告密,全家受到纳粹军方的残酷报复。玛利亚的父亲被当众枪毙,整个家族的女性被依次轮奸,最小的女儿玛利亚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直到自己最终被纳粹轮奸……
《创伤与康复》(TraumaandRecovery,1992)的作者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详述了性侵给女性带来的精神创伤,认为这种创伤的症候与退伍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同样对主体具有摧毁性。[2](P21-22)因为性侵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直接摧毁了受创主体对自我的认知,被性侵的身体是“肮脏的”,是为主体精神所不容的,主体因此被分裂成碎片,肉体与精神处于永恒的矛盾中。而且,玛利亚的惨剧也是整个族群讳莫如深的耻辱。二战后,玛利亚毅然决然地与博扬离开欧洲移民澳大利亚,意图隔绝所有痛苦的往事,建立新的生活。但在塔州这块“没有巨人,没有魔法,没有快乐结局”[3](P16),带着流放时代恐怖暴行的土地上,恶劣的自然条件,瓦楞铁皮的破败工棚,水坝上繁重的苦力,斯洛文尼亚难民移民在澳步履维艰的生活,这些都在唤起玛利亚拼命忘记的创伤记忆。被玛利亚封存在“秘穴”中的幽灵,一旦受到相似的条件刺激,异质记忆便被唤起,而此时的玛利亚远离故国亲人的支持,直接暴露在“白澳政策”(3)“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的立国之策。表面上是对以华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更深层次是以盎格鲁-撒克逊英裔文化为尊,欢迎英裔移民,实际上并不欢迎来自东南欧的白人难民移民。的歧视下。最终玛利亚用一种极端惨烈的形式——自戕(4)玛利亚的自杀站在全知的视角来看是“自戕”,从人物的受限视角来看是“消失”“出走”,正是这种神秘的消失给索尼娅造成了童年的创伤,直到故事的结局,人物才知道当年的真相。而创伤幽灵的面目一旦清晰,受创主体走出创伤便有了可能。来强迫自己摆脱过去的记忆。
博扬是用酗酒和暴力来使自己摆脱创伤的记忆的。面对妻子的自杀,繁重的体力劳动,看不见希望的人生,博扬充满了愤懑和不甘,痛苦和悔恨,或许还夹杂着思念。博扬酒后殴打女儿时吼道:
我敢打赌你和那些该死的男生一起出去了,我知道,我知道,你这该死的荡妇,你这小贱人,你就像你那妓女的娘带着……
这时,他的上唇抬起,颤抖着,他的头在颤抖,他的身体在晃,他的愤怒瞬间倒塌了,仿佛一个长久以来被抑制的记忆突然升起,但他奋力反击,用尽身体所剩的每一丝力量把它打回去,一路后退,他突然间摇摇晃晃,就像一头中弹的野猪在横冲直撞,在激烈愤怒的否认中他只吼出一个单词“狗屎”。[3](P12)
博扬“用尽身体所剩的每一丝力量”把“长久以来被抑制”创伤记忆打回无意识,用暴力来拒绝忆起过去的创伤,这个深陷创伤的男人甚至编造了妻子私奔来抑制自我的创伤记忆,避免触及内心的创痛。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指出当受害者面临难以承受的痛苦时,会选择暂时忘却太多或太过强烈的刺激,忘却是受害者逃避伤害的策略,但对创伤记忆的放逐最终会导致记忆危机,使主体愈加深陷创伤。
索尼娅关于母亲的创伤更是“无言的恐惧”(speechless terror)。对三岁的小女孩索尼娅而言,亲眼目睹母亲的消失对她造成的震撼正如一场超越所有震级的地震,她的意识彻底隔绝了这一段回忆,只能通过一些象征的手段或碎片化的细节来间接感知。婴孩的肉体和心灵都强烈依赖母亲,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所有的焦虑都与婴儿期最初与母亲的分离有关,康奈尔大学教授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在《书写历史,书写创伤》(WritingHistory,WritingTrauma,2001)中分析结构性创伤——“缺失”(absence)时首先列举了“与母亲(亲人)的分离”,并认为这是生命本身的创伤。婴儿从呱呱坠地开始,便离开了给予温暖和安全感的母体,开始了向死而生的人生。离开母亲是痛苦的,如果这种离开并不纯粹是生命本身的过程,而是突发的恐怖事件导致母亲突然消失,这时候结构性创伤就会叠加历史性创伤,主体突然失去安全感的保护,意识上会更加拒绝接受。
创伤研究先驱雅内曾提到了一个心理学创伤研究的著名案例。一名叫艾瑞丽的女性,父亲整日酗酒,艾瑞丽需要边工作边照顾病危的母亲。母亲病逝那晚,艾瑞丽独自守护一夜,第二天,当悲伤的人们赶来悲悼死者之时,女儿却拒绝认为母亲已经死亡,她对昨晚的经历失忆了。艾瑞丽的主体意识是:母亲死亡的话,自我必然会感觉悲伤,但是现在她没有丝毫的悲伤,所以母亲未病逝。艾瑞丽并未撒谎,为了使主体免于崩溃,她的意识屏蔽了这段记忆。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和焦虑》(Inhibitions,SymptomsandAnxiety,1926)多次引用雅内这一案例,来说明记忆在创伤事件中的受阻。
索尼娅跟艾瑞丽一样,都对母亲的突然消失产生了失忆,因为此时小女孩索尼娅无法与超越她理解能力的经验和解,只能将失母之痛压进无意识的深处。事后,索尼娅出现了思维的断裂,她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回忆起母亲出走那晚的场景,只能记起风雪敲打着窗户的声音。《单手掌声》中索尼娅一家都通过放逐记忆来摆脱创伤的幽灵,其思维的断层和意识的空白使他们无法彼此建立联结,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生存的现实世界陷入混乱,人际关系疏离而隔膜,主体的整体性开始崩溃,母亲玛利亚的自杀、父亲博扬的酗酒、女儿索尼娅的麻木和痛感缺失都是主体失忆的后果。
二、无意识中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
卡鲁斯(Cathy Caruth)在《创伤:记忆的探索》(Trauma:ExplorationsinMemory,1995)中对创伤记忆代际传递的见解如下:创伤记忆是超越历史的症候,有着十分强烈的痛感,严重改变了受创主体的心理状态,其反复发作使受创主体反复经历创伤,如果主体没有能力削减创伤的力度与创伤和解,很有可能会将这种破坏力向下传递,比如由一代向二代,由亲历者向见证者传递。怀特海德(Anne Whitehead)在《创伤小说》(TraumaFiction, 2004)中这样论述:“关于跨代创伤的理论表明,情感能跨越代际。一个个体所经历的创伤事件会被传递,这样其影响会在另一个个体身上或更多的后代中重演。”[4](P14)
亚伯拉罕和托罗克则认为:
由于充分的原因,幽灵是没有被意识到的无意识所形成的。在一种还没有被认定的方式中,幽灵从父母的无意识传到了孩子的无意识。[1](P173)
当可耻的、无法言喻的体验被禁止进入受创主体的意识时,创伤就会潜伏在无意识中代代相传。创伤不需要言说就会自发传递到下一代,其沉默的魅影萦绕着整个家族。代际间的幽灵理论解释了小说中人物间的创伤传递,《单手掌声》中索尼娅的受创并不是真的由于母亲的幽灵,而是由于创伤代际间的传递。亨氏·安特(Heinz Antor)的《理查德·弗拉纳根<单手掌声>中移居的创伤与自我定位的伦理》(“TheTraumaofImmigrationandtheEthicsofSelf-PositioninginRichardFlanagan’sTheSoundofOneHandClapping”)对小说中创伤传递的评论十分具有代表性:
母亲玛利亚·布洛无法应对自己过去欧洲的伤痛以及塔斯马尼亚新环境的变化所造成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困难,这使她受到了二次创伤,以至于她在19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上吊自杀。这反过来再次伤害了玛利亚的丈夫博扬以及小女儿三岁的索尼娅。她亲眼目睹母亲离开家里的小房子,出发去塔斯马尼亚积雪覆盖的冬季森林中上吊,这种丧失(5)Loss译为“丧失”,指突发事件造成的历史性创伤;Absence译为“缺失”指生命中本身就存在的结构性创伤。使她深受创伤。[5](P206)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凄凉的景色与饱受战乱的欧洲并无二致,唤起了玛利亚过去恐怖和毁灭的痛苦回忆,引起了她创伤的泛化,即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威胁泛化”(generalization of threat)。玛利亚无法消解创伤的破坏强力,最后拎着从故国带来的唯一的回忆的载体——手提箱,走进了塔州的丛林,她的自戕就像第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使创伤在家庭中快速无声地传递。多年以后,这只手提箱和她最后留下的斯洛文尼亚语摇篮曲片段“Aja, aja”承载着她的创伤,是过去与现在记忆的焊接点,成为博扬和索尼娅乃至整个澳洲斯洛文尼亚难民移民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emoire)(6)“记忆之场”这个概念是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法国史学界颇具影响的历史著作《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1984)中提出的,诺拉认为法兰西国家民族记忆遗产中的一些象征符号,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再到将来,成为了民族记忆的节点。,预示着代际间幽灵的复归。
在索尼娅的成长历程中,熟悉而又陌生的手提箱是一个将过去的记忆静置的神秘存在,它被放在与父女日常生活隔离的角落,如同创伤记忆沉睡在黑暗的无意识中,亦如弗洛伊德笔下的暗恐。创伤记忆本身是破碎的,无法形成文字,手提箱作为一种片段化的、图像化的方式,成为记忆传承的媒介。当小索尼娅凝视着手提箱中父母的定情信物——雪绒花和照片时,通过手提箱传递的斯洛文尼亚移民的创伤记忆被编码、被传递、被扩散,手提箱成为玛利亚家族创伤符号化的表征。索尼娅的梦中曾反复出现盖满鲜花的棺材,她梦见自己也躺在里面,竟感到一种有着归属感的幸福。棺材是死亡的象征,躺在棺材中这一个片段化的梦魇,说明索尼娅的无意识中已经有了死亡的冲动,家族死亡的阴影在不断传递。
除了手提箱这一有形的记忆之场之外,母亲玛利亚的斯洛文尼亚语摇篮曲也是创伤代际传递的载体。在母亲神秘消失后,这首歌不时出现在索尼娅的脑海,先是单词片段“Aja, aja”,再是句子,小说结尾处是整首歌,它就像《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的鬼魂在风雪夜敲打着窗户,喊着“让我进来,让我进来”。上一代的创伤记忆不甘心就此隐匿在历史的缝隙中,它要求被重现、被传递、被理解。这使索尼娅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童年的创伤记忆是痛苦的,主体需要隔绝它才能存活,因此索尼娅记不起整首歌,但是摇篮曲又饱含母亲对女儿的爱,这种爱也在这创伤的歌中传递着。索尼娅常常无意识地重复一个动作,“当她听到她们谈论她母亲的时候,她慢慢地把左手背转过来,露出张开的手掌。然后她用右手的食指绕着手掌画圈……然后索尼娅用右手握住她张开的左手的四个手指,非常缓慢地把它们合在手掌上。”[3](P82-83)这个动作是当年喝下午茶时母亲对小索尼娅做的,在索尼娅听到对母亲的诋毁而十分痛苦时,便会不自觉重复这个动作,最后结尾时,她也像母亲那样对自己的女儿做了这个动作。在这个动作中,手掌被打开又被合上,象征着记忆在一次次的重演,一次次的掩盖,但是不管看见与否,痕迹就在掌心里,同时被盖在掌心的还有母亲手上的温度。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诚然痛苦,但却好过完全的失忆。没有手提箱、儿歌和掌心的温暖,母爱就彻底消失了,这将使主体走向彻头彻尾的虚无。因此受创主体无意识中创伤的幽灵时时到访未尝不是向索尼娅提供一种与过去取得联系,认知原初创伤的机会。
父亲博扬也承载着创伤,并把它向下一代传递。在他还是孩子时,母亲就像开了天眼般告诉他,这片土地将血流成河。二战中纳粹侵略者召集博扬学校的全体学生,当着孩子的面用机关枪扫射十多个村民,作为对游击队员杀害一名士兵的报复,孩子们不允许闭眼,博扬看到的只有一片猩红。在他阿姨农场的谷仓外,被打死的游击队员的尸体血液凝结成黑色的硬壳。在备受欺凌的斯洛文尼亚,少年博扬曾看见纳粹士兵将人的头当球踢,爱人玛利亚的父亲被枪杀,全家女性被侮辱,战争中人像苍蝇一样死去。战争结束后,澳政府承诺会有更好的和平繁荣的生活,受此吸引,博扬携带妻子迅速移民澳大利亚,却发现自己是在塔州的大坝上,抡起大锤做着繁重的重体力劳动,并被英裔白人歧视。创伤传递下的博扬,跟其他的南欧移民一样,用酗酒和暴力来解决这一切,并在无意识中将自身的创伤传递到女儿身上,他大声地咒骂着女儿,将妻子诋毁为“荡妇”,最终民族的、集体的、家庭的创伤经由父母的主体间空间(intersubjective space)辐射穿透(7)“辐射穿透”是约兰达·甘佩尔(Yolanda Gampel)提出的,用于指创伤的代际传递,父母间的创伤尤其容易沉积在孩子身上。到小索尼娅身上。在索尼娅的成长过程中,来自邻居、养父母、父母亲、同学肉体或精神的伤害,如同一张密密的网,将索尼娅困在其中。她陷于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无法忘记,亦不忍忘记,但又无法完整地记起。创伤记忆的传递让人绝望,主体会世世代代陷于这种创伤的传递吗?后代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奋力一搏切断创伤的传递,即使不能让所有的伤痛戛然而止,也能实现某种创伤的平复?
三、回溯创伤,寻找救赎
斯洛文尼亚难民移民受困于家庭和民族创伤的代际传递,但是正如《哈姆雷特》中死去的父亲的幽灵频繁出现是为了启示哈姆雷特,索尼娅家族中创伤的幽灵跨越代际的传递,其目的正是为了获得意识的理解,走出创伤的控制。拉卡普拉的创伤心理康复研究认为,受创主体完全摆脱创伤回到最初圆满的愿望是不现实的,所以他不主张用“超越创伤”这样的术语,但他认为创伤的复现正是为创伤的平复创造条件,受创主体积极面对,用叙事记忆来代替创伤记忆,将无意识中无法言说的创伤呈现到意识的层面,可以使受创主体与创伤的过去和解,继续生活。[6](P144-145)
《单手掌声》中索尼娅回溯原初创伤的努力源自于其怀孕。为了逃离家族令人窒息的创伤,索尼娅在被父亲暴打后逃往悉尼,切断与过去创伤空间的一切联系,但颇为吊诡的是,她的逃离使她反而长久陷于创伤的时空。索尼娅在大城市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母亲的出走、父亲的拳头、养父吃人的眼神、同学的鄙视、噩梦的创伤片段不断闪回。索尼娅与身体所处的日常世界愈来愈解离。也许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怀孕后,正是与腹中的胎儿血脉相连,使自己有勇气回到家乡,踏上了重建与过去联结的救赎之旅。
索尼娅努力记住她腹部形成的第一个东西……有什么东西像抽筋一样攫住了她,把她的五脏六腑聚拢在一起,然后抛了出去,就在一周前,在悉尼那个决定命运的早晨。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起初,她只把它理解为一种渴望,好奇、大、陌生就像头顶的天空一样。一种想要再一次看到独特的塔斯马尼亚的光和它所触及的东西的欲望。[3](P17)
此时,她已经历经两次早期堕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个已经成型的胎儿很可能是她面对创伤的最后一搏。
回溯创伤,寻找救赎,一方面需要对创伤的幽灵进行祛魅,认知当年的创伤;另一方面,由于创伤导致了情感的解离,救赎创伤需要恢复麻木的情感,在爱中理解创伤,重建与世界的联系。小说的开头,回到家乡的索尼娅驾车一路向西,拐上满是砂砾的小路,创伤的过去就像被水坝阻拦的洪水,平静的外表下神秘激烈的暗流涌动着、等待着。索尼娅靠在大坝上,张开双臂,抚摸着大坝,如同孩子般搜寻着对生活的安全感。她渴望了解父母在二战中的遭遇,在战后塔斯马尼亚生存的艰难,以及母亲走进丛林的原因。但是当年死过好几个难民劳工,父亲也在此流血流汗的大坝上,只留下一句凸出的铭文:“向1955年通过建造这座大坝,帮助利用大自然造福人类的所有国家的人们致敬。”[3](P27)表述非常官方,绝口不提这群勉强在二战中生存下来的难民在此再次经历的苦难。斯洛文尼亚难民移民们二战中和战后所有的苦难已经被历史主流话语轻轻带过了。索尼娅徒手从土中挖出了母亲当年白瓷器的碎片,拼命想要拼贴完整。她见到了让她又爱又恨的父亲,常年的体力劳作让他十分苍老。父亲双唇颤抖,很难对女儿说出完整的句子,一则是英语语言能力不够,二则创伤记忆是破碎的、非线性的,如同海面下的冰山,在黑暗的无意识中释放着持久的影响力,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父亲苦笑着说,自己是一个“老杂种酒鬼”,没有什么话可以对女儿说。他只是拿出了母亲的手提箱与女儿一起默默地翻看当年的照片和雪绒花。因此索尼娅回溯创伤,从认知的角度,所得十分有限。此时,二战已经结束了40多年,母亲也在30多年前走进了丛林,所留下的只是一些往日的碎片。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或某个民族的创伤是何其渺小,经过岁月的层层过滤,所留下的信息屈指可数。在研究后期,弗洛伊德放弃了寻找病人童年的原初创伤,认为这是不可及的,并且认为受创伤的主体不可能一次性地康复,其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尽管创伤的细节依然不可知,索尼娅回归的情感意义是巨大的。创伤是一种情绪的过载,远远超过了大脑皮层的负载能力。过量的刺激使大脑无法对新的事物进行认知、分类、总结,更无从安放在原来的记忆结构中,因此大脑无法记住创伤记忆的细节,只留下体验创伤时或痛苦或愤懑或绝望的情感维度。索尼娅的心结就在于三岁时被母亲用出走的方式抛弃,被父亲长期疏于照顾,她辗转于多个寄养家庭,体验到的是漂泊感和被抛弃感。这种感情过于痛苦,索尼娅的心灵无法承受,所以她用麻木和解离来隔绝内心所有的感受。因此创伤的救赎更大程度上是要恢复麻木的情感,在交流和爱中理解彼此,恢复与世界的联结。索尼娅回归后与父亲见面,尽管父女间没有多少言语,尽管母亲当年的创伤故事只有几张照片传递有限的信息,但是亲人间的爱已然在流动,铁板一块的创伤世界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过去不再是封闭和沉默的,而是在一点点被诉说,情感上的联结对主体走向康复意义重大。
另外,母亲当年的朋友赫尔维在索尼娅的创伤平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索尼娅暂回塔州之时,赫尔维如同母亲般竭力挽留索尼娅与她同住,将半夜自残的索尼娅送到医院。她十分坚定地数次告诉索尼娅,索尼娅的母亲是一个好女人,非常有幽默感,并且非常非常爱孩子。这样,索尼娅不再用母亲留下的白瓷器的碎片自残,当她对母亲不再怨恨之后,对自我的憎恨就得以缓解。母爱的丧失给女儿所造成的创伤,最终在赫尔维身上得到了弥补。她鼓励索尼娅联系父亲,为索尼娅寻找便宜的旧公寓,帮助她生下孩子。赫尔维是千千万万个二战难民移民的一员,为了躲避战争的创伤,他们背井离乡,前往澳大利亚与世隔绝之地寻找世外桃源,却发现依然在塔斯马尼亚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受尽歧视,从事最低等的劳作。在这群被澳主流社会所抛弃的边缘人群中,个体间彼此的理解和爱是残酷生活的安慰剂,尽管无法彻底走出创伤,但确实使受创主体获得暂时的喘息。
《单手掌声》的结局是,新的生命为两代人的和解提供了新的希望。父亲多年在工地上从事体力劳动,语言功能已经退化了。但看见了怀孕的女儿,也试着表达内心的情感。
博扬又一次挣扎着想要说话。“我……啊,不。不……”他卡住了,在大脑中重新组织语言,尽量像正确的英语。“我很想给你写,嗯,信,但是,嗯,我的英语,工作、喝酒可以,没法写在纸上。”
博扬轻声说道,如同在自言自语,他的声音如此之轻,以至于索尼娅要身体前倾才能听到他用破碎的声音低语,这几乎算是他一生的道歉的话,“永远没有足够的话对你说。”[3](P39-40)
尽管不善言辞,但是很明显,父亲博扬对女儿的归来是十分欣喜的。他的祖国在二战中抛弃了他,战后澳大利亚也没有接纳他,连他的妻子也用死亡的方式抛下了他。女儿的回归温暖了他孤寂的心灵。而即将出生的孩子又使他和女儿之间有了联结的纽带,给了他用行动表达情感的机会。父亲又恢复了年轻时做木工的习惯,亲手为孩子打造了摇篮,把女儿破旧的公寓整修一新,甚至将索尼娅童年时摔破的茶壶重新修补好。孩子出生的那天,博扬直奔花店,虽然只买到了雪绒花的澳洲版——白色的康乃馨送给索尼娅,但博扬发自内心地笑着。故乡的雪绒花已经永远不可再得,但康乃馨的花语亦是温馨的爱,就像移民们在这块新的大陆上尽管已不可能回到创伤前的原状,但爱却给了他们走下去的希望。
父亲的爱也在唤醒着女儿的爱,而唯有爱才能终止创伤的代际传递。“博扬并不笨拙地抱着婴儿,以一种放松的方式,抱在他的右臂上,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食指的指节抚摸着她的下巴。”[3](P416)“博扬离开后,一个小小的奇迹发生了。在这新的一生中第一次,而不是最后一次,索尼娅哭了,她的眼泪像夏雨一样落在她孩子的头上。”[3](P418)小索尼娅自三岁起便没有任何眼泪,即使在被父亲暴打时也从不哭。爱的回归使她流下了幸福的泪水,碎片化的创伤记忆逐渐向叙事记忆转化,生命中又有了信念、爱和美,最终索尼娅把自己的孩子叫玛利亚,这象征着母亲的重生、爱的重生。代际间的幽灵已经转化为新的生命。
四、结语
弗拉纳根对玄妙的东方文化十分感兴趣,“单手掌声”取自日本临济宗白隐慧鹤禅师所创之公案(kōan),佛家偈语不能通过理性的语言来把握,而只能通过直觉来感受。米尔科·朱拉克(Mirko Jurak)认为尽管《单手掌声》看起来比较消极,但对这个标题的解读是开放性的,索尼娅最后的结局展示了她具有更高自我意识和超越异化的状态[7](P27-28), 就像二战创伤的幽灵在斯洛文尼亚难民移民几代人之间无声地传递并最终得到一定的康复那样。
在意识的表层人物隔绝了无法承受的创伤,但在无意识中,创伤就如同单手击掌,风过树梢那样在无声地传递。斯洛文尼亚二战难民移民在澳大利亚社会苦苦挣扎,在白澳政策下,他们的存在即是原罪,因此无法在澳大利亚寻找立足点,只能成为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下等白人”。他们如单手击掌那样发不出任何声音,这种存在的虚空感和无力感是难民移民们共同的感受。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面前,外来移民们唯有退缩到个人的生活中,抱团取暖,依靠自我的力量回溯创伤,寻找救赎,重建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联结,尽管整体的救赎依然是不可知的。弗拉纳根用一个普通难民家庭的故事,在悲观的乐观主义中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创伤。
——玛利亚·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