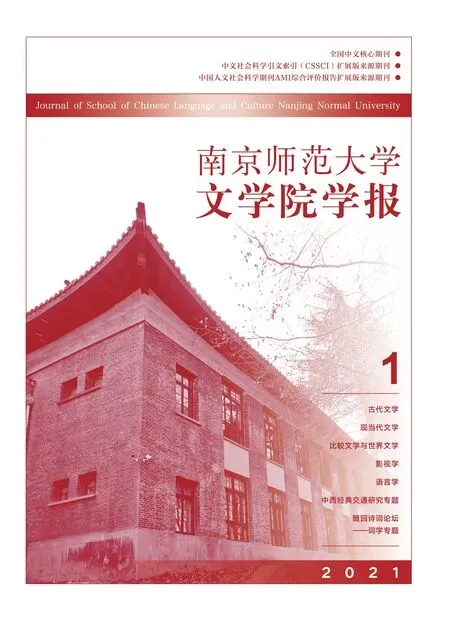杨绛:知识人与小市民诉求相撞击迸发的幽默语言
陈留生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6)
一、引言
杨绛是独特的喜剧作家。“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1](P115)杨绛由于创作了《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剧作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学界和观众之中产生强烈反响,其风头一度盖过其大名鼎鼎的学者丈夫钱钟书,以至于他们夫妇外出时人们都介绍钱钟书是杨绛的丈夫。
杨绛喜剧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重要原因是其喜剧语言,对此,很多研究者做过多方位的展示与分析。但对于杨绛何以会铸成如此有魅力的喜剧语言,从哪里出发才能给杨绛喜剧语言在喜剧史上准确定位,学界还没有出现有说服力的探究成果。对于杨绛戏剧语言发生动因语焉不详,对其语言风貌也就把握不到位,对其文学史地位也就定位不准。笔者以为,杨绛喜剧是由知识人与小市民的生命诉求相撞击而迸发的喜剧语言而铸就的,这种独特的喜剧语言正是杨绛喜剧语言的魅力之源。也许,由此出发,可以探寻到杨绛喜剧语言的真貌。
创作主体的生命诉求是决定剧作语言造诣高低的关键因素。诉求,是指追求、要求。本论文指涉的生命诉求就是指生命的陈诉、追求、表达。生命诉求是生命属性、生命形态、生命感悟、生命体验、生命意志、生命价值等的综合作用,最后以生命诉求的形式呈现出来;它直接指向人的根本属性,关乎人的全方位需求。话剧语言关乎的就是生理需求、生存需求、教育需求、娱乐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多个方面。喜剧,是一种独特的戏剧文学样式,它的创作主体往往存有内在的优越性,以俯视的眼光来关照笔下的芸芸众生,以游戏的态度来驾驭笔下的人物和语言。喜剧创作者往往比其他体裁创作者更为理性、睿智,往往会与所表现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让自己对笔下的林林总总都掌控于手中,了然于胸中。杨绛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高度喜剧涵养的剧作家,她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就是这些因素的极致发挥及其奇妙遇合的杰作。
在20世纪40年代,已过而立之年的女性学者杨绛似乎是忽然之间横空出世,强势进入戏剧的。她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引起剧坛震动,戏迷迷恋,一时成为文坛佳话。杨绛闯入话剧界,当然有李健吾等友人的劝导的原因;但这只是一种灵感的触发,在骨子里,这些作品是她生命诉求的自然倾泻。杨绛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知识分子的熏陶、教育;后来又与知识分子组成家庭,丈夫、女儿、她自己都是知识分子;一家3口又都终身从事知识分子工作。这些生命历程,铸就了她知识分子的生命观念、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判断标尺,她是知识分子理想愿景的承载人、执行者、守护神,重义轻利、重情轻利是她处世为人、臧否人物的基本标尺。她又长期生活在城市,无锡、上海、苏州、北京是她30多年常呆的处所,在娘家及婆家大家庭,有许多市民亲戚;在周边,她接触了大量市民。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与耳濡目染的桩桩件件中,她对于市民阶层的方方面面都熟稔于心,对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事风格了如指掌。杨绛最看不惯的就是市民阶层在对待情感问题上的作派:重利轻情、见利忘情,尤其是在情感取舍上,往往置利益的考量于首要地位,而枉顾杨绛十分器重、把它看成比生命还重要的情感。当李健吾等友人催促她创作时,小市民见利忘情的一幕幕情景就像一幅幅浮雕一样,展现在眼前。当她拿起笔来,就会展现市民阶层在情感选择与处理上的种种人物与事件。在情感问题上,知识人的正能量与小市民的负能量碰撞、交锋,以知识人的正能量臧否小市民的负能量,让他们的生命天平发生错位,进而产生了《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高超的喜剧语言。
概而言之,杨绛因其独特的生命诉求的抒发使得《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显示出其独特的喜剧语言范式:以幽默喜剧语言为基调,多种喜剧语言元素融汇在一起的,高超的、雅俗共赏的喜剧语言艺术。
二、知识人家庭孕育知识人生命诉求
(一)书香家庭孕育知识人生命图式
语言和人的生命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语言是生命的表征,而生命只是纯粹的观念。”[2](P5)“有鉴于现实生命,看似客观的想法却充满了情感。个人的言语体系不断地尝试表达主观思想,结果,这种习惯用法便成了专门用于表达的手段。”[2](P9)伍尔夫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3](P1)语言和生命具有双生互动关系,语言成就了创作者,创作者也让作品语言熠熠生辉。话剧语言是创作者内在生命诉求的载体,只有创作者的生命诉求才能为话剧语言灌注活力。文学艺术创作中一个带有规律性的事实是:当创作者将主体的生命诉求在作品中全然抽离时,他同时也抽空了文学,掏空了语言,作品的语言也就缺少了生命的精魂,只剩下话语的空壳、言语的碎片,只会是僵死的文字堆积。因此,在艺术创作中,由遗传、教育、习得等途径所铸成的才华非常重要。除了遗传之外,童年经验往往是生命深处永久的精神家园。童年在生命的长河中虽只是短暂的一段时光,但却像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而规约着水质、水量一样,永远沉淀在生命的河床之中。艺术家要么直接描写童年记忆,要么间接动用童年库存,至少是童年记忆作为先在结构。童年时段是语言的学习、掌握的黄金时段:“在最初几年内孩子们对大量的语言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这些语言信息将成为生命中的永久信息,而“永久记忆中的情景记忆就像一个存储经历的大仓库,并且明显会随着经历而成长。”[4](P55)久而久之,这些记忆就会形成一种生命的图式:“图式是语义记忆里的一个结构,它对一群的一般和期望的排列方式作出规定。”[4](P173)图式由一个人的生命诉求所决定,一个剧作家话剧语言的基本模式,剧作家在剧作中的语言造诣,在很大程度上由“图式”所决定。
杨绛的生命“图式”正是由其原生家庭奠定的:杨绛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读书人,她从小就在书堆里长大;后来嫁的也是读书人,她自己一辈子和丈夫一样,终身以书为伴,读书、教书、写书,完全是书化人生;他们唯一的女儿也是读书、教书、写书。原生家庭幸福,在和谐的家庭中成长、生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人性与世态》(Les而Caractrèes)。[5](P61-62)
杨绛和丈夫钱钟书的幸福生活更是一直被人当做文坛佳话而津津乐道。这种与书为伴的生命状态及一直生活在和睦幸福家庭的生命际遇,使得她性情平和,对人对事极少疾言厉色;她有恬淡的人生,高雅的趣味;她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属于俗念稀少的知识人; 她自小父母家教极严,又自律严格。她宽厚仁慈,又具有女性所特有的温柔、贤淑。这些都使得她灵魂高贵、心灵淡雅。她自白: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6](P2)
虽然杨绛一直生活在书斋里,但她对于社会人生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一方面,她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她父母都是无锡人,杨家也是个大家庭,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会与她家发生千丝万缕的交接,她自己也在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南方城市居住过,对于南方市民的特性,具有全面的了解与感悟;另一方面,书海世界之中,百般世态,一样不缺,五颜六色的生命精彩纷呈。
杨绛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她整合能力、举一反三能力极强,自己的耳闻目睹、书海的点点滴滴、父母的谈论评说,使得杨绛从幼年开始就播下了关注世态人生的种子,也为她日后在剧作中展示市民社会林林总总人生世相奠定了基础。
自小时候起,杨绛就是阅读十分广泛的人,小说、散文、诗歌都广为涉猎。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戏剧相关内容: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时,她就研读了大量描写外国世态人情的剧作,进入清华大学之后,她又选修了著名戏剧家王文显讲的莎士比亚作品的研读和法国文学专题研究课程,自己也阅读了大量戏剧名著。跟随钱钟书赴欧洲学习的时候,更是系统研读西方戏剧作品。这些都为她日后从事喜剧创作奠定了喜剧形式方面的基础。
(二)知识人生命图式铸就幽默性生命诉求
由于在书香家庭不断得到熏陶,杨绛在家里家外好评如潮,几十年来成为文坛佳话。现摘录几段: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7](P310)
杨绛还天性幽默、谑趣盎然,可谓天生的喜剧家:
我说杨绛先生是天生的喜剧作家,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话。因为她好与她笔下的人物开玩笑,而且善于开玩笑,处处不失温柔敦厚之致,这也许是作者有幽默的天性吧,由此亦可见她胸襟的冲淡与阔大。然而隐藏在这幽默与嘲讽的后面,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严肃与悲哀。[8](P661)
杨绛恬淡的生命状态使得她的喜剧创作具有理性的观照、睿智的笔调,与喜剧精神相融通。“所谓喜剧精神,就是理性的旁观态度加调侃的玩笑精神。”[9](P1)“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6](P239)格森也曾指出:“通常伴随着笑的乃是一种不动感情的心理状态”,如果你把自己从社会生活中解脱出来,“作为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来参与生活,那时许多场面都将变成喜剧。”[10](P64)那么,杨绛是怎样写作的?对此,李健吾描述道:
这种写作的迅快,有时候倒表示孕育的成熟,才情的畅达,和工具的老练。这不是潦草。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正相反,她富有缄默的智慧,她是一位勤劳的贤淑的夫人,白皙皙的,不高,不瘦,不修饰,和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她和她的小女孩子一样靦觍。唯其具有性静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画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描得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8](P664)
但杨绛的恬淡并不表明她就没有自己的追求、坚持,没有属于她的喜爱、憎厌,恰恰相反,她的追求很鲜明,坚持很执着,而且还憎爱分明。简言之,她所追求、坚持、喜爱的就是作为一个成长、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学贯中西的女性知识分子的理想层面的精粹。
杨绛的生命经历铸就了她独特的知识女性的生命特性,同时,她无论是在老家无锡,还是后来到北京、上海学习、生活,都要和不同类型的市民打交道。在这些日常生活及交往中,使她非常了解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从她的叙述及创作倾向来看,在她这样一个心地纯洁的知识女性眼里,市民往往以物质利益来评判、取舍情感的言行是最不能容忍的。她的创作就是知识女性生命诉求的抒写,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就是知识人与小市民的生命诉求相撞击而迸发的喜剧语言而铸就的。当然,知识人的生命诉求是占据优势地位和主导地位的。
三、知识人与小市民生命诉求的撞击
在《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这两个作品里,首先是张扬爱——“爱”,是杨绛生命诉求的核心。这里的“爱”是大爱,包括同情心、利他心、包容心,但中心是男女爱情。“爱”,是杨绛喜剧的核心标杆,是衡量一切人事的标准。其次是嬉戏“钱”——和金钱有关的一切物质利益。“爱”是杨绛及其张扬的知识人的根据地,“钱”则是小市民的守护神。在这里,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和市民话语体系是对立的,可以说,知识人与小市民的生命诉求相撞击,也即“爱”与“钱”相较量,这两个作品的喜剧性源自于情爱标准的错位、情爱方式的错位、人生目标的错位,表和里的错位:原本是属于爱情范畴的东西却被金钱所占用了,作品的喜剧语言由此而产生。《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在演出之后,都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作为知识人的话语体系,在《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中的切入视角是不尽相同的。在《称心如意》中,作者设计和自己性情有些相似的李君玉深入到市民世界里,犹如受难的耶稣一样,历经屈辱与磨难,既参照出小市民的情感方面的错位,产生出喜剧性话语,又坚守了自己的立场和初衷,出污泥而不染,最后还喜剧性地达成了自己的目标。而在《弄真成假》里,作者不是作品中的一分子,而只是一个置身事外的、居高临下的观察者、讽喻人,也是作品里林林总总人与事的设计者。在《称心如意》中,爱支撑着李君玉,她才忍辱负重;在《弄真成假》中,爱支撑着杨绛,以此来褒贬人事。在杨绛笔下,和知识人相对立的小市民往往是两面人——当面一套,实际是另一套,他们服膺的是利益,人生的轴心是金钱。
(一)李玉君与《称心如意》的喜剧语言生成
在《称心如意》中,李君玉貌似林黛玉进了大观园,其实是杨绛式知识分子落入上海小市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貌似是小羊羔落入群狼窝,其实倒是小羊羔战胜了群狼。孤儿李君玉来投靠舅舅、阿姨,她却遭到舅舅、舅妈、姨妈们的排挤,被踢来踢去没有人愿意收留她,使得她受尽屈辱。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收留李君玉,都是出于一己之私利。可是当李君玉歪打正着地得到朗斋舅舅的爱怜,不仅认李君玉作孙女,还有可能继承一大笔财产的时候,他们又称是为她好,要把她弄回去,其实想调虎离山,以便争夺财产;当得知弄不回去之后,又设计陷害李君玉,但不仅没有成功,还落下让人耻笑的把柄。
李君玉可谓一直都在忍辱负重,她说:
我还是耐着心让他磨,等他火气过了,觉得我这个秘书还可以,就认真用我了。
有职业总比没有职业好啊。
能这么顺顺利利地忙,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不是享福的。
对于“称心如意”,绝大多数解读者都理解为李君玉被朗斋认作孙女,还得到一笔可观的财产而“称心如意”了,其实这种理解既不符合杨绛的原意,更是对李君玉的一种曲解。先看下列一段对话:
李君玉:我们?我跟谁?是刚才出去的我那位又漂亮又阔气的表哥吗?哎,你也看中他!何况我这么个孤苦伶仃的穷女孩儿!
陈彬如:君玉,我以为……
李君玉:你真有眼光!所以我要东躲西躲不敢见你,你跑来就叫人轰走你。
陈彬如:别生气,君玉,是我给他们轰糊涂了。不过我也知道你不会轰我,所以我不死心,总是找到你,看看你。
李君玉:看看我!我是什么好看的东西吗?你跑来只看我一眼就走了!你没有给我留下地名!你都没想到吧?我没法儿和你通消息,天天心神不定的盼着你来,也不知道你回去了没有,憋着一肚子气,又没个人可说的,可是你只想看看我!
陈彬如:怎么了,他们对你怎么了?
李君玉:我给他们这里推到那里,谁家都嫌我。懊悔当初没听你的话,不到上海来!我本来想回北平去了,又不知道你走了没有。
由此可见,李君玉之所以忍辱负重不回北京,是在等待她的爱,也就是说,是爱在支撑着她坚持了下来。她的“称心如意”,绝对不是物质上得到一大笔财产,这种解读视角和小市民的想法如出一辙,根本没有悟透作品的意思。其实,她的“称心如意”,是指可以和心爱的人终成眷属了。至于可能得到的一大笔财产,只是生命的小添头。
总之,对于市民社会,李君玉是身在其中,又超然事外,似乎像牵线木偶一样,被动地随人摆布,可实际上,却初心不改,始终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李君玉虽然在表面上总是处于劣势地位,但她“得道多助”,她仰仗杨绛坚守的知识人的正义立场而最终胜出。同时让林林总总的人物登台表演,淋漓尽致地把他们的喜剧性展现出来。这些人物在李君玉这面照妖镜的照射下,尽显他们的丑态。
(二)隐身杨绛与《弄真成假》喜剧语言的发生
在《弄真成假》中,却不见李君玉这样带有杨绛身形的角色,杨绛似乎是站在一边,静静地观察着、体味着林林总总的人物如何沉溺于物质世界里难以自拔。如前所述,这些人物的喜剧性同样以错位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在《弄真成假》中,杨绛独特的喜剧语言是通过四类各具特色又紧密相连的喜剧形象来承载的,他们以张祥甫、冯光祖、周老太、周大璋和张燕华为代表。这些人物形象各有各的话语体系,各有各的面貌,也各有各的诉求和理想。四类形象就是四个喜剧点,通过他们“错位”的话语,组接成了一个面——中国的现代世态生活的风貌。
张祥甫之所以不同意女儿和周大璋恋爱,就是因为他感觉到他会亏本:
我挑女婿呀,只做稳稳当当的现货买卖,不做空头。
眼睛里看准了一宗货,稳是赚钱的,那么,眼都不能霎一霎,闪电手腕,立刻得拍下来。何况现在这市面上等着嫁男人的女孩子要多少,真有女婿资格的能有几个!都是拿了三块五块的本钱,做三十万五十万的空头交易呢!
婚恋与做生意原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但张祥甫却用做生意的理路来衡量婚恋的是否可行,充满了铜臭味。他这些话是板着脸声色俱厉说出来的,但,他越是严肃,读者或观众就越是忍俊不禁,情场不是生意场,无端地把两者混同在一起,其语言的喜剧性就出来了。
如果说张祥甫话语的喜剧性质是来源于把生意场移植到婚恋场的话,那么冯光祖就是把学术场混同于情场,他对心爱的人张燕华这样求爱:
那我把意思整理得清楚些,分五点:第一点哪,就是说,根本这个问题,值得不值得讨论。从前的小姐,提到男女婚姻问题就觉得不好意思,有关自身的重大事情,都糊里糊涂的让人包办了。
并且需要仔细研究的——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现在要研究的,是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人究竟应当不应当结婚?——有人说,家庭是自私的根源,社会上许多罪恶——营私舞弊之类都是从结婚开始的。那么,结婚究竟是好事、坏事呢?
第三点是说,为什么我还不结婚呢?这里有几个理由,我慢慢儿告诉你听。第四点是说,现在可以结婚了吗?
这下面包括两项:一项是从你的观点说,一项是从我的观点说——第五点就是把这两项合拢,就是说……
这简直让人窒息,还没等他条分缕析完毕,心上人张燕华就气跑了。他的一系列求爱表白,是严重的错位。感情,往往是一片混沌,既难条分缕析,更不讲一、二、三、四,他的喜剧性的话语,使得一个可笑又可爱的书呆子形象跃然纸上了。
周老太误以为是张家把宝贝儿子藏起来了,于是贸然跑去张家与张家人交涉。她进了张家就是刘姥姥进到大观园——一个弄堂里的没有见识的市民老太太,闯进装扮成书香门第的富丽堂皇的商人家里,本身就含有喜剧性;又是在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在明显不占理的情形之下,她的一系列话语、动作,都严重地错位了:
你们好便宜呀, 养了一个毛丫头, 就想把我的儿子都拐走了, 我们周家十八代祖宗行好积德修来的子孙, 倒送给你们张家现成受用去!
她原本是来理直气壮的要人,后来却因为儿子与张燕华阴差阳错地私奔而被张家反咬一口。错位、突转,彰显出周老太话语的喜剧性。
周大璋和张燕华是这个作品的主要人物,剧名“弄真成假”就是因他俩的纠葛而起,作品语言的喜剧性就很大程度上因他俩对爱情的追求而产生的:本来,男欢女爱是难有喜剧性的,但他们都不守本分,不安本位。原本都是普通人家,周大璋甚至是出身于贫寒之家,但他们却“错位”地把自己装扮成上等人,吹嘘成有钱人,他们装扮、吹嘘的话语就显示出极强的喜剧性。周大璋自吹自吹的“名片”是:
世代书香人家的子弟,阔人家少爷,留学生,博士——
可事实上他家境惨淡,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厚着脸皮和寡母一起寄住在已嫁妹妹家的阁楼上,受尽了妹妹婆婆的冷眼和挤兑。他自己也只是保险公司的小职员,还因为经理嫌他“做事不认真,迟到、早退,——转追女人”等被辞退。从自卑心理学视角来看,周大璋是陷入了“自卑——超越”的泥淖中不能自拔了——他往往误以为自己已经是贵人一等了。在外人那儿他的胡吹就有功利目的,他也通过自我吹嘘和善于伪装,差一点就把一位富家女追到手了;同时,还把号称有大笔陪嫁的贫家女张燕华“弄真成假”地弄到手了。
总之,杨绛以隐身的方式,直接用自己知识人长期形成的知识人爱情观来参照出张祥甫、冯光祖、周老太、周大璋和张燕华在对待儿女或者自身的爱情上面的种种“错位”,从而铸就各式各样的喜剧语言。
综上所述,在杨绛的生命世界中,有一个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就是“情”——情,不能沾染俗世的灰尘;不能用利益去衡量,更不能用利益去获取与交换。而市民社会往往就犯了杨绛的忌讳,他们是只重视利益,而不珍惜感情。在《称心如意》中,芸芸俗众不重视亲情,只注重利益,他们把“外来户” 李君玉当成洪水猛兽,毫不顾惜他们之间的骨肉亲情。而在《弄真成假》里面则不把爱情当回事儿,他们眼里只有利益。《弄真成假》的结局是对题目的最好诠释:周大璋和张燕华“真”的爱钱,“假”的爱情,但结果是“真”的没成,“假”的却成了,所以才叫“弄真成假”。这是剧作最大的错位,是该剧最具喜剧性的地方。但也正是这出乎意料的结局,才使他们回归了生命的本真,抵达了婚恋的本性——婚恋不是做买卖,而是要以爱情为基础,他们与杨绛的婚恋理念投合到了一块。由于他们和杨绛在“三观”上存在着明显差距,杨绛是用自己知识人的生命诉求来烛照出这两个人的喜剧性的。这些俗众因情感与利益产生了“错位”,他们就有种种盘算、种种表演,发于声就产生了“错位”性喜剧语言。
四、杨绛喜剧语言的独特性
由于杨绛独特的人生经历铸造了非同一般的生命诉求,使得《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中出现了知识人与小市民的生命诉求相撞击而迸发的喜剧语言。杨绛的喜剧语言既是中国现代喜剧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其独特性。在此,可以从中国现代喜剧语言发展的历时态与共时态两个维度来辨析杨绛喜剧语言的造诣及其在现代喜剧语言中的地位。
(一)从历时态维度看,杨绛喜剧语言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语言集大成者。
喜剧也是伴随着话剧的脚步在中国产生的,喜剧是生命所需要的,“作为人们至关重要的交流这一基本需求和愿望的工具的语言也成了人们娱乐休闲的资源。”[4](P4)中国现代喜剧创作也可谓群星闪耀。20世纪20-30年代属于中国现代喜剧的早期时代,早期话剧语言的实践者有欧阳予倩、熊佛西、陈大悲、余上沅、洪深、丁西林等,趣味语言、讽刺语言以及幽默语言等喜剧语言形态都已经出现,是中国现代话剧语言形成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喜剧往往借助于游戏和狂欢,来宣泄文化给人们所带来的压抑,让人生回归生命本源的自由和奔放。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喜剧精神冲击力、心灵震撼力不足,而娱乐性又贫弱,在观众心目中的影响力不大。中国现代早期喜剧创作者对于真正的喜剧精神存在着天然的排斥性,陈大悲、熊佛西们追求的是“高级趣味”,竭力贬损所谓的“低级趣味”,即基于感官刺激而产生的趣味和愉悦。这种趣味观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低级趣味”是“高级趣味”的基础,“高级趣味”中也蕴含着“低级趣味”,二者水乳交融,难以截然掰开,撇开了基于感官刺激的而产生的趣味和愉悦的“低级趣味”,也就抽掉了高级趣味的根基,更是忽略掉了生命的根基。这就必然导致中国现代早期喜剧语言不奔放、不热烈,中国现代早期喜剧语言的喜感不足,乐性不畅,极少酣畅淋漓的喜剧语言。在20世纪20-30年代,真正立足于喜剧语言本性创作的是丁西林。丁西林喜剧就是以喜剧语言取胜的,丁西林、杨绛被李健吾称为第一道、第二道纪程碑,但细究起来的话,杨绛喜剧语言和丁西林喜剧语言还是存有同中之异的。
1.喜剧语言的生命热度有所不同
丁西林是工科教授,他在创作时显得过于理性,主要是受到外国喜剧的启发,没有经过他自己生命的燃烧,他的喜剧语言的生命热度不够,给人感觉是在为喜剧而喜剧。往往机智就是其作品喜剧语言的一切:机智既是喜剧语言的起点,也是喜剧语言的终点;既是喜剧语言的手段,也正是其最终的目的。而在杨绛的《弄真成假》等作品里面,机智只是喜剧语言的起点、手段,而其终点与目标则是展现中国的世俗社会的世态人情,特别是表现在这俗世中芸芸众生的愿景、祈求、挣扎,给人提供的是一幅幅生命雕像。可以说,杨绛的语言是灼热的生命燃烧的结晶。杨绛喜剧的机智是通过选取能够展现创作主旨与塑造人物形象的精妙的语言而间接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杨绛的喜剧语言在丁西林们的基点上往前跨了一大步,这一大步主要体现在生命热度的增强。文学是人学,生命燃烧的热度往往决定一个作品乃至一个作家创作水平的高下。
2.喜剧语言的形象依托略有差异
丁西林主要是为了追求嬉趣功效,其喜剧语言主要是立足于机智俏皮,至于是谁说的,符不符合人物的生命特性,有没有生命的个性差异,他考虑的不多。而杨绛则不同,她的人物的喜剧语言是高度个性化的,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情景之中说什么话。例如周母对张祥甫夫人的一段话:“啊呀!亲家太太,这话就不能四四方方地讲了,讲规矩呢,新亲没有喝过会亲酒,也好意思找上门来么?可是讲理呢,我们到底是男家,男比女大,阳比阴贵,倒叫你们女家压没了我们男家,就是皇帝也没有这个规矩的。”活脱脱地把一个深受男尊女卑思想毒害的市井老妇人的形象凸显出来了,在《弄真成假》所有出场人物中,只有这位周老太太的嘴里才会吐出这样个性化的喜剧语言。
3.喜剧语言的生命实感强弱分明
丁西林以五四精神为底蕴,张扬个性解放、婚恋自由,在此基础上展开故事情节,但就具体内容而言,则显得空泛,具体的能指性不足。丁西林社会生活的现实依托不够,喜剧语言的生命实感较弱。而杨绛则立足于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坚实大地,将中国市民日常生活话语进行喜剧性展现。她对中国的市井世态了如指掌,她不像闭门读书的书生,而是市井社会的观察者、洞察人,所以,她的喜剧是偏于写实的,她并没有直接去展示那种带有理想意味的东西,她是用自己的理性、理想去烛照这些市井世态里的芸芸众生,高屋建瓴地把他们生命中不符合知识人理想的东西以错位的方式展现出来,让人感知这些人生命中的喜剧性,进而感悟出生命不可以这样进行下去。一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杨绛的喜剧创作受到了外国“世态喜剧”的影响,但也不能夸大这种影响,杨绛只是受到外国“世态喜剧”的启迪和触发,在骨子里,还是“中国风”:她笔下的人和事都是国产的,而非外国舶来品。
4.喜剧语言的整体风貌各有偏侧
丁西林的喜剧语言主要是喜剧性的,而杨绛的《弄真成假》等喜剧作品的语言则要复杂得多,杨绛的许多喜剧语言实际上都带有悲喜剧的色彩,特别体现在表达周大璋内心的感受时。每当他自我吹嘘与自我膨胀后,紧接着出现的通常是与他自我膨胀恰恰相反的自身的现实状况。当他刚刚在周家大吹大擂并完全俘获了婉如母女的心以后,他又不得不回到让他十分不堪的家里面(还是寄居在妹妹的家);当他刚在妈妈面前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使得母亲都飘飘欲仙的时候,叔叔就来借钱,让他不得不说出自己真实的现状,而且还引来了更大的麻烦——母亲要到张家去要儿子,让他的谎言全部都告破,计划也全部落空。人物的命运也是悲喜剧性的,周大璋、张燕华虽然如愿结合,但又都不合他们的初衷,本来周大璋想娶有钱人家的女儿的意愿落空了,而张燕华要嫁有钱人的希望也成了泡影,这里面悲剧的意味相当明显。但是由于周大璋的下列一席话使两人的结婚成了一场大喜剧:
嗳,燕华,好看不开,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你要称心,只有一个法子。事实如此,好哇!我不承认这个事实!我说它不是!我改造它!称着心要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说这是吹,这是骗,随你说。这是处事的艺术,这是内心战胜外界的唯一方法!精神克制物质的唯一方法!这世界不就变成了咱们的世界了吗?不都称了咱们的心么!
这是一段典型的精神胜利法,也许他平时的大吹大擂,也多半是源于这种心理。但是,正是这段精神胜利法产生了奇妙的效果:燕华叹息着醒悟道:“从此以后,我也随分按命了”。
由于喜剧语言的整体风貌各有偏侧,他们喜剧语言的社会影响也有明显的差异:丁西林展示了知识人的小游戏式的幽默,其间透露出的是知识人的高雅,丁西林的读者群也多半是和他一样的知识人,是高雅趣味欣赏高雅趣味;一般民众对于这一类喜剧就不会那么热衷了。而杨绛的喜剧语言则是驳杂的,因而是多色调的。如前所述,杨绛是用她知识人高雅的理想来烛照市井平民的婚恋大事,通过错位的途径,映照出这些芸芸众生“俗”的一面,它的《称心如意》与《弄真成假》等喜剧创作无不如此,尽管各个作品各有自己的角度,但总体思路都是差不多的。在这种创作动机之下,杨绛的喜剧语言的主调只可能是否定性的。当然,在与她站在同一高度的知识人,或者就是她代言人的语言则是肯定性的,譬如《称心如意》里的李君玉,这是她的喜剧中少有的肯定人物,李君玉只是一个参照物形象,她是杨绛理念的化身,她参照出作品中林林总总人物的喜剧性。
(二)从共时态维度看,杨绛喜剧语言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喜剧语言的佼佼者。
文学艺术活动是人的生命能量的释放形式,而喜剧往往是生命负能量的释放途径,是较少物质需求含量的高级生命享受。喜剧语言就是通过讽刺、归谬、戏谑等途径,让剧中人物自导自演,以游戏的方式来清除生命负能量。也就是说,喜剧语言是人的生命能量的洗涤剂,是生命正能量的守护神。20世纪40年代,正是中国现代喜剧及其语言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是:陈白尘“忠实于自己的灵魂”[11](P90)的讽刺语言,李健吾回望“青春”而激发的诗性喜剧语言。陈白尘的《升官图》以“一喜到底”的讽刺语言在中国现代讽刺语言中独占鳌头。李健吾在《青春》中,青春所特有的依情而为、率性而动的特性发挥了决定作用,给了主人公冲决文化规约的力量,其命运也发生喜剧性逆转,剧作的诗性语言因此而产生。而杨绛则在《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中,用“爱”这一知识人的根据地来参照“钱”这个小市民的守护神。这两个作品的喜剧性源自于小市民情感标准的错位,原本是情感范畴的东西却被金钱所挤占,作品的喜剧语言由此而生。
1.杨绛与陈白尘:幽默喜剧语言与讽刺喜剧语言的高峰并峙
如果说陈白尘喜剧的立足点是民间和精英的混和物,而杨绛则是纯粹的雅致的读书人。颇有意味的是:这样一个读书人却将笔触伸向了市民世界,用知识人的理想、理性,来烛照鄙俗世故的市井世界,因而产生出喜剧性。但是,杨绛也没对这市井世界作太过的讽刺,总体格调仍是幽默的。这说明,杨绛是善意的,对于民间的种种鄙俗世故是持一种宽容、包容的姿态,她只是带着怜悯的态度站在知识人理想的山巅上来俯视这帮俗世里的芸芸众生,杨绛的喜剧语言是她用知识人的生命诉求来对市井俗世远距离观照的结晶。
陈白尘的《升官图》演出后,产生了强烈反响;杨绛的《弄真成假》是1943年写成的,在上演之后,也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沦陷区的各大报刊常常有宣传和评论的文章登载,有的朋友还给她寄来评论的剪报,鼓励她要继续创作这样的喜剧作品,剧团的演员甚至也以演出她的喜剧为荣,还联名写信给她表示他们的谢意。据说,那时有人在介绍钱钟书的时候,常常会冠之以“这是杨绛的先生”。甚至还有一则趣闻:一天夜晚,钱钟书和夫人杨绛一起去看杨绛的话剧演出,钱钟书看到在剧中的观众与同仁对杨绛的热烈场面,从戏院出来的路上,钱钟书的心中就有些波动,他对妻子说,他已经决定要写一篇长篇小说。他所说的小说就是后来风靡文坛的《围城》,杨绛的成名“迫使”心高气傲的钱钟书都坐不住了。
但是陈、杨两个人的剧作反响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用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来衡量的话,陈白尘40年代的喜剧语言侧重于“酒神精神”的挥洒,他是站在绝对优势的制高点上来俯视、唾弃这些负面人物,读者与观众能够在一种狂欢状态中尽情享受艺术语言的盛宴。在喜剧的狂欢中,负能量就此得到消解,生命也由此得以涅槃。而杨绛的喜剧语言则偏重于“日神精神”展现:“如果说, 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 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 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 那么, 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 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 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12](P192)杨绛的出发点是让人们苦中作乐,在这种情景之下,杨绛不可能狂欢。
概而言之,陈白尘是中国现代讽刺喜剧语言高峰的缔造者,而杨绛则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语言高峰的创造者,他们从不同的路径为中国现代喜剧语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杨绛与李健吾:否定性喜剧语言与肯定性喜剧语言的极致
在20世纪40年代,李健吾以《青春》一剧奠定了他在此时段的喜剧史地位,这是一部肯定性喜剧语言的杰作;杨绛同期则是以《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而蜚声剧坛,而其总体格调则是否定性喜剧语言。在此,就以《弄真成假》中的周大璋和《青春》里的田喜儿为代表,剖析一下两者的异同。
《弄真成假》中的周大璋和《青春》里的田喜儿都在追求在俗世眼里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弄真成假》中的周大璋,是寡妇家的穷小子,他梦想富家女做老婆;而《青春》里的田喜儿,也是寡妇家的穷小子,他在追求村长家闺女香草。在讲究门当户对的传统社会,这是两个极难达成的人生目标。
首先,两人追求爱情的手段不同。《青春》里的田喜儿是靠真挚的情感来打动心上人,以执着的反抗来与门当户对观念做殊死的抗争;而《弄真成假》中的周大璋则是吹牛、说谎。周大璋从一出场,就具有信口雌黄的“口技”,是颠倒黑白的伪君子。他为了追求真正的富家女张婉茹,抛弃号称是富家女、实际上是一贫如洗的旧情人张燕华,却借口是为了成全张燕华和冯光祖,“一个男子甘心退让, 在他是多么丢脸的事!可是为了心爱的人, 为了她的幸福, 就宁愿做懦夫, 做弱者。”但在追求失败时又对张燕华深情地说:
我的爱, 是一斤一两约着卖的吗?你明知我爱的只有你!我所以退步, 不过是为了你的幸福!可是我忍不住还是要到这儿来, 不能看见你, 也能偶然听到你, 时刻感觉到你———这是多么矛盾、多么可怜的心思呀。我还有自尊心, 怕人家笑, 我得借一个名目, 算是来找婉如。婉如!没头脑的一个小动物罢了!……燕华, 除非是为了你的好, 我甘心退让———我周大璋从没有对我的环境低过头!?
真是巧舌如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其次,两人爱情追求的结局迥异。《青春》里的田喜儿仰仗他们母子的拼死抗争,实现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和心上人香草终成眷属;而周大璋则“弄真成假”,最初的愿景完全落空,只能和一贫如洗的张燕华缔结连理。需要深入玩味的是,杨绛并没有用自己的理想去整合这铜臭味十足的俗世,她是理性的,她深知这俗世远远不完美,她只是轻轻地揶揄这些过于俗气的芸芸众生,重重的幽默了他们一下,然后,让他们各归本位。《称心如意》中那些希图得到原本不是他们的财物的愿望都没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里的周大璋和张燕华虽在表面上是“弄真成假”,可实际上他们也是回归了自己的本位——两个人“门当户对”地结为伉俪,他们原本都带着人格面具在表演,此时则摘掉了这些面具,回归了生命的本源,从这个角度说来,他们是“弄假成真”的。在杨绛笔下,这些俗世人的发财梦、荣华梦最终都归于破灭。细究起来,他们都没有什么损失,好像是做了一个美梦,梦醒了,他们还在原处。周大璋和张燕华也由人格的分裂达成了人格的统一(至少是暂时的统一)。
总之,《青春》是李健吾浪漫精神的挥洒,而《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则是杨绛求实心性的硕果。李健吾的《青春》倾泻的是肯定性喜剧语言,其间饱含着诗情画意;而杨绛的《弄真成假》展现的是否定性喜剧语言,其间满含幽默、苦涩,也不乏独特的诗意。杨绛立足于市民社会的大地,又充溢着诗意:圣洁的感情不容金钱来玷污,她在对情感圣洁性的呵护上流溢出浓浓的诗情画意。
五、结语
苏珊·朗格认定:“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没有艺术爱者对生命情感的创造,就没有艺术。……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作生命情感的象征形式。”[13](P51)在长期的生命历程中,杨绛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情感形式,她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就是其“生命情感的象征形式”。确立这一视角,对于杨绛喜剧语言的研究具有以下意义:
(一)可以进一步理清杨绛喜剧语言的发生动因
杨绛对于包括知识分子、城市市民在内的人生世相参悟透彻,对于自己所处的知识分子阵营和《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所表现的市民阶层的方方面面都一清二楚。因此,她在用知识人的标尺去衡量小市民的喜怒哀乐时,卡位十分准确,掐中了市民阶层在情感处理与抉择时的七寸,既照见市民阶层的可笑之处,又道出市民阶层的悲凉之点,让人感到市民阶层在情感问题上既可笑,也可怜,她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的喜剧语言都映射出“含泪的笑”。
如果抛开了杨绛独特的生命诉求,不由知识人的生命诉求与小市民的生命诉求相撞击这个视角来关照,不从杨绛对于市民阶层在情感处理问题上的鲜明立场与复杂情感出发,很难探寻到《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等杨绛喜剧语言的发生动因。
(二)可以进一步弄清杨绛喜剧语言的本然面貌
杨绛的剧作围绕市民阶层在处理情感与金钱关系方面的错位而展开故事情节,因为这种“错位”而产生出独特的喜剧语言。杨绛与她笔下的市民阶层的分歧涉及到精神定位、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等根本性问题,一个人的品味和境界,往往决定其生命的高度、宽度、深度。杨绛钟情于情感,不容许金钱玷污,她维护的是高层次的生命需求;而她笔下的市民追求主要是的是物质利益,真挚情感往往都让位于物质考量。
1.杨绛的喜剧语言具有天然的喜乐性,这是由于在市民社会的芸芸俗众在情感与金钱问题上的“错位”而生发出来的。在《称心如意》里,除了李君玉之外的芸芸俗众的言语都因这种错位而产生一连串笑点,而《弄真成假》里的4类人物的话语全都错位,通篇作品都是喜乐性语言的组接。这在幽默性喜剧中是极少见的,也是极难达成的,这除了杨绛具有高超的喜剧语言天赋以外,就是由于作品人物的整体“错位”才产生的。
2.杨绛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的喜剧语言是多种喜剧语言元素融汇在一起的,其总体基调是幽默,整个作品的语言有趣而可笑,又包含杨绛深厚的情感——对于情感世界的倾力维护,对于为了金钱而漠视情感行径的鄙视;而且还蕴含了杨绛的睿智——对于庞大的俗世的驾驭,对于浩如烟海的市民的掌控,这就犹如一个弱女子在驯服一群脱缰的野马。这些戏剧语言又有轻轻的嘲弄、讥讽、揶揄——嘲讽芸芸俗众太不珍惜宝贵的情感,他们都是金钱的奴隶,物质的附庸,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当然,这嘲弄是裹上了一层女性温柔的面纱,使其不激烈、不尖刻,还有淡淡的哀怨、深深的怜悯——感慨他们生命质量的低下,他们没有灵魂的依托、心灵的飞升,只是物质的空壳,使得喜剧语言具有“含泪的笑”意味。更有满满的诗意——《称心如意》中杨绛派驻的李玉君,就是这种诗意的化身;而在《弄真成假》之中,诗意既隐身其间,又无处不在。这诗意正是引领整个作品走向的精神航标,更是贯穿整个作品的红线,使得整个作品的基调与风貌坚守了高品位的阵地。
(三)可以进一步厘清杨绛喜剧语言的历史地位
1.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把杨绛的喜剧语言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喜剧语言的大坐标之中,才能参照出它的贡献和地位来。与丁西林等早期幽默喜剧语言相比,杨绛的喜剧语言具有更加广泛的生活内蕴,具有忧愤深广的精神境界,具有更为宽阔受众基础,杨绛喜剧语言实现了雅俗共赏,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都可能成为她的粉丝。因此,虽然都是幽默喜剧语言的高手,与丁西林相比,杨绛的喜剧语言艺术造诣更高,更受各方喜爱。
2.与同时代喜剧语言佼佼者陈白尘、李健吾相比,他们三人各有各的造诣,各有各的特点,他们在各自的喜剧语言领域都达到了中国现代喜剧语言的高峰。但是,杨绛又是最特别的一个:她的喜剧语言既兼具各家之长,又熔炼自成一家。她具有女性的细腻,但又不是那么感性。她有知识分子的纯粹,又不是不谙世事,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她的生命是内热外冷的奇妙组接,她既不像陈白尘那样,传达对讽刺对象的极度鄙视;也不像李健吾那样过于仰仗诗意的挥发,硬是把不可能化为圆满的现实。因此,她既没有陈白尘式的极度夸张的讽刺语言,也没有出现李健吾那样张扬的诗意语言,而是多元喜剧语言因素交融的杨绛式喜剧语言。
“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14](P99),杨绛所针对的是中国市民的“俗”,其参照系则是传统文人的“雅”,也即孔子所言的“君子”与“小人”的对峙与撞击。在《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之中,杨绛高层面的、独特的生命诉求的倾泻,铸就了她高水平喜剧语言;独一无二的杨绛创造了当世无双的喜剧语言——以幽默喜剧语言为基调、多种喜剧语言元素融汇在一起的,高超的、雅俗共赏的喜剧语言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