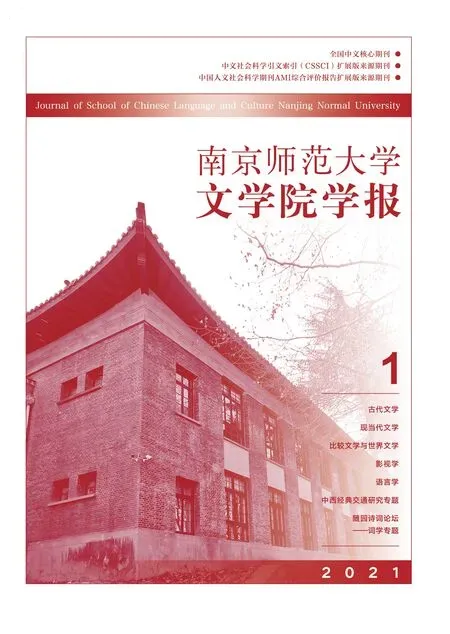以群短篇小说创作钩沉
施学云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以群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先后出版《文艺创作概论》(天马书店,1933年)、《创作漫话》(天马书店,1936年)、《文学的基础知识》(生活书店,1946年)、《文艺思想问题笔记》(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在文艺思想战线上》(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我们的文艺方向和创作方法》(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谈有关文学特性的几个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谈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今昔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等著作。(1)叶子铭先生编辑《以群文艺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选录了以群各时期有代表性的论文81篇,认为以群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是在文艺评论方面。尤其是由其主持编写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多次出版,被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广泛使用,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人们关注以群,大多关注其熠熠生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实绩,却忽略了以群作为一个左翼作家的文学事实。以群有不少文学作品发表,虽不似其他知名作家那样创获丰富,成绩斐然,但也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话剧等诸文体,先后出版《生长在战斗中》(中国文化服务社,1940年)、《旅程记》(集美书店,1942年),以及《新人的故事》(重庆当今出版社,1943年;新群出版社,1947年)等文集。(2)叶子铭等学者将《新人的故事》视之为报告文学,以群之子叶舟编纂的《以群年谱和著作年表》则将其视之为短篇小说。笔者探察集子所收作品原始出处,《新人的故事》共收录七篇作品,初刊时《一个人的成长》《再生》《复活》被列入所载刊物“小说”栏目,《一个小兵的来历》《杨疯子》《挣扎》(即《踏进斗争中》)、《突进》(即《红枪会的英雄》)被列入所载刊物“报告”“速写”栏目。由于报告文学与纪实性短篇小说在文体区隔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当时期刊的这种划分并不一定准确可靠,但是为了尊重历史原貌,我们不妨还是将其称之为小说、报告文学合集。因此本文辑述短篇小说时,亦仅考虑该文集中的《一个人的成长》《再生》《复活》三则文本。遗憾的是,其他更多作品散见于当时的各类报刊杂志,未有整理。查阅资料发现,目前研究界亦尚未关注以群的文学创作,短篇小说更是知之甚少,无人提及。2021年是以群诞辰110周年,为还原以群作为一个左翼作家的文学实践本相,笔者对以群的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初步钩沉,冀图引起研究的注意。考虑到以群作品与时代叙事之间的密切同构关系,本文拟以“全面抗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分期依据,将以群的短篇小说创作分为全面抗战前、抗战中、抗战胜利后三个阶段。
一
从“左联”成立到全面抗战发生前夕,以群主要从事左翼文学活动,先后奉命组建“左联”东京支部、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和左翼作家联盟安徽分盟,曾担任“左联”组织部长、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编委等。这一时期,以群创作出《小黑子和“小猪”》《在监牢里》《巴夷》《薪俸》等短篇小说。辑录来源如下:
(1)《小黑子和“小猪”》刊于《北斗》1932年7月20日第2卷第3/4期合刊。时文皆署名“华蒂”。同期载有白苇的墙头小说《夫妇》《墙头三部曲》、慧中的小说《米》、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续)》等作品,以及起应《关于文学大众化》、何大白(郑伯奇)《文学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学》、寒生(阳翰笙)《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田汉《戏剧大众化与大众化戏剧》等文论,并附陈望道、魏金枝、杜衡、陶晶孙、顾凤城、潘梓年、华蒂(以群)、张天翼、叶沉、西谛、沈起予等参与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讨论的小论文。(3)以群以较长篇幅回答了征文给定的四个问题:“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中国现在的文学能否大众化”“文学大众化是否伤害文学本身的艺术”“文化大众化应该怎样才能够实现”。以群认为,“文学之最主要的任务,就在于推进社会的发展。要使文学能够负担起这样的任务,就必须把文学的基础建筑在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的身上。以工农劳苦大众的意识为意识,以工农劳苦大众的立场为立场的文学,才是大众自身的文学,才能在大众中发展作用。”参见华蒂《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北斗,1932(3/4)。华蒂(以群)另在该期发表《国际文坛新讯》,介绍了世界各地纪念歌德百年的活动,以及法国革命作家艺术家同盟、日本作家同盟第五次大会有关情况。
(2)《在监牢里》刊于《小说家》1936 年10月15日第1卷第1期。该文列入“关于孩子的故事”专栏,其他三篇分别是王次云《她的弟弟》、张雪玲《铁柱的兔爷》和契萌《报名》。(4)《小说家》1936 年10月15日创刊于上海,主编欧阳山,编辑委员会成员包括欧阳山、张天翼、周而复、蒋牧良、陈白尘、聂绀弩等。由两次小说家座谈会发言记录可以看出,该刊旨在克服宗派主义矛盾,但作家言辞之间仍免不了颇多火气,宗派意识并未完全根除。该刊创刊号上与以群同栏目发表的张雪玲小说《铁柱的兔爷》,引起争议,有读者认为是套作。同期还载有谷斯范《不宁静的城》、蒋牧良《古记》、绀弩《酒船》、辛劳《饥饿的伙伴》、草明《单纯的遗嘱》、张天翼《酒后》、东平《教授和富人》、周而复《罢饭》、欧阳山《苦斗》等小说九篇,以及胡风译作《小说的本质》、1936年9月2日小说家座谈会第一次记录等。另,1936年10月30日小说家座谈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载于《小说家》1936 年第1卷第2期(“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出席座谈人员合计十九人。参会人员名单上列有“以群”,但并未见其个人发言记录。
(3)《巴夷》刊于《中流》(1936年10月20日 第1卷第4期)。同期载有鲁迅的《捷克文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何其芳《呜咽的扬子江》、鲁彦《旅人的心》、许钦文《抄拢子》、华沙《季工大金》、萧乾《苦奈树》、巴金《我的路》(作家自白),以及若干通讯、书评。《巴夷》被列入封面目录予以推介。
(4)《薪俸》刊于《国闻周报》(1936年11月30日第13卷第47期)。同期载有萧乾的文论《论奥尼尔》、素芝的短篇小说《老文蒂伯伯》、张天翼的长篇小说连载《在城市里(二十二)》,以及若干时事评论、社会问题论文。《薪俸》被列入封面目录予以推介。
《小黑子和“小猪”》《薪俸》《在监牢里》皆可视为左翼儿童叙事小说,给我们塑造出了小黑子、小瘌痢、小北佬、跷拐儿、小孩儿等儿童群像,侧重展现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和反抗的可能性。《小黑子和“小猪”》里的小黑子一家靠租种田地为生,遭到地主的严苛盘剥,本就难以维持生计,又遇到洪灾,父亲抢险丧命,哥哥被抓壮丁失踪,小黑子只能和母亲一起去逃难流亡。在城里乞讨时,遭遇“小猪”(地主家的孩子)的歧视和侮辱,小黑子愤恨中掌掴了“小猪”,抢走了她手中的猪油豆沙白米粽子。小黑子和“小猪”迥然不同的身体形象和生存境遇,反映出旧中国底层社会存在的紧张尖锐的阶级矛盾。《薪俸》里的小瘌痢、小北佬、跷拐儿都是当铺的雇工,工资微薄,受尽压榨,当铺经理还要减薪。只因为小瘌痢私下和同事们闲聊时,说了句从报纸上学来的话,“其实怪只怪我们当初自己不会团结,像上海那些做工的团结起来罢工,要求加工资,总会达到目的”,被经理威胁开除。小瘌痢虽然畏惧恐慌,最终还是鼓足勇气,主动离开了当铺。小北佬在惩罚了举报人洋鬼子之后也遭开除,身有残疾的跷拐儿则只能无奈留守。“罢工”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潜隐的文化符号,隐喻着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影响力已经通过传媒扩展到基层社会。小瘌痢们也许并不完全了解罢工的革命性内涵,但是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为他们反抗苦难、反抗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提供了更多可能。《在监牢里》里的小孩儿天性活泼聪慧,虽然饱受苦难,孤苦伶仃,但是毫不悲观绝望,仿佛是这令人窒息的监牢里一朵生机勃勃的春花,狱友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生机和活力。小孩儿获释后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东北义勇军,四处奔走于抗日的最前线。监牢内外,拘禁与自由,苦难与希望,无论身处何境,小孩儿都能蓬勃生长,因为他找到了人生成长的路径,寻得了坚持战斗、反抗苦难的人生要义,这是作家以群对旧中国新人形象的理想建构。细读这几则儿童叙事文本,作家的叙事笔调始终冷静节制,但内在隐含着对于底层小人物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昭示出底层社会产生反抗的必然性。
另一短篇小说《巴夷》读来颇费思量,讲述了一个名叫巴夷的印度看守出于同情心,偷偷照顾入狱者的故事,让人看到了残冷黑暗空间里一丝美好的人性。这倒与当时有关印度巡捕、印度看守形象的负面书写有些差异。该文本创作的心理动机或与以群的两次监狱生活有关。1930年以群因在《浙江潮》上刊发进步文章,抨击国民党统治,被捕入狱。1934年8月在与“上海反帝大同盟”干事刘丹会面时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先后转到南京、苏州关押。幸其堂兄叶元龙曾相继任安徽省和贵州省教育厅厅长、财政厅厅长,经请托得以保释出狱。
二
全面抗战时期,以群始终活跃在抗战文化中心,通过文艺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等多种形式建构自己的抗战叙事。1939年6月,以群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战地访问团,与宋之的、罗烽、杨骚、袁勃、杨朔等作家一起到战地访问。10月下旬,访问团兵分两路,宋之的等人返回重庆,以群、袁勃、杨朔继续北进,先后渡漳河,越过武长公路封锁线,到达晋东南敌后根据地,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当地作了三个月的访问。(5)以群曾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太行山之秋》(连载于《全民抗战》,1940年第120-123期),详细记录了这次战地访问经历。路上所见所闻成为以群“新人”叙事的主要素材来源。这一时期,以群通过战地采访采集写作素材,拿起手中之笔书写抗战中的凡人俗事,表现普通民众民族意识和抗战意识的觉醒,先后创作出《一个人的成长》《复活》《再生》《邂逅》等短篇小说,旨在鼓动全民抗战情绪,凝聚全民抗战意志。辑录来源如下:
(1)《一个人的成长》刊于《文学月报》1940 年4月15日第1卷第4期。同期载有碧野的小说《灯笼哨》、南斯拉夫施奴德尔的小说《故国的城》、沙汀的报告文学《老乡们》、欧阳山的速写《南泉默写:最大的赞美》,以及“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里的五篇诗评、译作等作品。该刊《编辑后记》里提到,“以群的《一个人的成长》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发展的性格”。
(2)《再生》刊于《青年文艺》1943 年5月15日第1卷第5期。同期载有丰村的小说《回炉货》、易巩的小说《某青年》、胡风的文论《<白马的骑者>题记》、骆宾基的文论《读诗小记》、卢荻的诗《祝福》、苏金伞的诗《向日葵》,以及若干散文、译作等作品。《再生》被列入封面目录予以推介。(6)《青年文艺》1942年10月10日创刊于桂林,主编葛琴。
(3)《复活》刊于《天下文章》1943 年6月1日第3期夏季特大号。同期载有茅盾的小说《偷渡》、蒂克的小说《秦淑的悲哀》、罗荪的随笔《情感症》、何其芳的诗《歌六首》、袁勃的诗《雁的故事》等。(7)《天下文章》1943年3月15日创刊于重庆,主编吴熙祖、周彦、徐昌霖。
(4)《邂逅》刊于《文艺先锋》1944 年4月20日第4卷第4期。同期载有老舍的长篇小说连载《火葬》、王蓝的短篇小说《父亲》,以及若干散文、诗词、文论等。该文另易名为《五年》,刊于《文章》1946年1月15日第1卷第1期,同期载有徐迟的短篇小说《一塌糊涂》,魏金枝的短篇小说《独乐乐》,李健吾的剧本《王德明》,以及若干诗歌、文论等。
《一个人的成长》《再生》《复活》讲述的是抗战文化背景下底层民众转变成长的故事,塑造出了高世昌、赵长生、女宣抚员等新人形象。《一个人的成长》中的乡村少年高世昌自幼散漫好斗,为反抗日本侵略主动加入八路军。他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革新自我,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面,纵使负伤住院,与原部队失散,还是历经艰辛一路追寻,最终回归队伍,真正成长为英勇忠诚的战场英雄。《再生》中的赵长生因战争家破人亡,后又被日本人威逼利诱当上了特务,假装投军企图借机向根据地水井里投毒。在根据地部队的温暖关怀下,他良心发现,幡然醒悟,把自己锻造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复活》中的女人终日痛苦于家庭及工作的不幸,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后被八路军特务队拯救。虽然她极不情愿在日本人那里继续做宣抚员,忍受欺凌,也极力申请回到根据地工作,但是为了抗战事业,她克制住内心的压抑,服从组织安排,毅然担负起卧底这份艰巨的新工作。这种新人成长叙事虽颇具戏剧性,但叙事原型都来自于作家战地采访获取的真实素材,并不是小说家臆造的神奇故事,而是挣扎在抗战洪流中的晋东南地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作家藉此表达的是,“他们的身体被敌人残酷地摧残、毒害、凌辱着,然而,他们却还艰苦地保持着心灵的生机。当机会到来,由于别人的启发或是自己的惊觉,他们立刻会在新的空气中,新的阳光下,如脱胎换骨一般地再生或复活起来,以数倍于前的生命力献予洗雪公仇私怨的斗争。”[1](P2)
随着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整个中国社会心态、作家情绪都发生了改变,抗战文学逐渐呈现出新特质,由初期单纯明朗、慷慨激昂的激情动员叙事转向细腻真切、感伤沉郁的个体与民族生存叙事。诚如以群在厘析全面抗战五年间的小说成果和动向时,认为:“自武汉失陷以后,作家们为抗战所激起的那种狂热渐渐地平伏,而渐趋于冷静,对于时代、对于现实看得更深进了一层,因而自然地对单纯的片面事实的歌颂或记录,感到了不能自满,于是就将注意点转向于观察一群事实并概括一群事实的方向去。”[2]这一时期的以群,也不再局限于反映根据地战斗生活和乡村新人的成长,而是转向对国统区现实生活和知识分子心灵的细致观照。小说《邂逅》(《五年》)讲述的就是抗战相持阶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分化和精神嬗变的故事。主人公石铭与黎靖原是一对恋人,抗战初期都曾是热血青年,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当石铭到北方抗战前线参加流动宣传队后,两人失去了联系,直到五年后在渝邂逅。这时的黎靖已为人妇,终日陷于家庭的琐屑之中,殚精竭虑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贫乏与困窘,不再热心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昔日那个萦绕不去充满活力的美丽身影早已逝去。石铭劝说无果,倍感失望,孤独地回到前线继续坚持战斗。文本通过前线和大后方不同人群生存状态的差异比较,展现出漫长的战争对于人性的伤害与磨损,传达出以群对大后方沉闷迟滞、蝇营狗苟现状的不满与批评,对坚持抗战到底的英雄意志的彰显与褒扬。文本基调压抑低沉,隐含着深重的悲哀和痛苦,又孕育着孤独反抗的忧郁和坚韧,塑造出了一个内心柔弱敏感、情感细腻丰富而又果敢坚强、勇于牺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人形象。
三
抗战胜利后,内战全面爆发,以群先后辗转至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文学活动,在香港期间参编《小说》月刊(8)《小说》月刊1948年7月1日创刊于香港,编辑委员会成员包括茅盾、巴人、葛琴、孟超、蒋牧良、周而复、以群、适夷等。,协助潘汉年做好知名作家、民主人士返回内地的工作。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新的历史图景已经徐徐展开。面对新时代的召唤,以群敏锐观察到当时社会各阶层中不少人士对未来出路的迷茫与焦虑,创作出《路》《试炼》等短篇小说,展现时代大裂变前夕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呼吁人们“留下来”,共同参与新的人民历史的建构。辑录来源如下:
(1)《路》刊于《小说》1948 年9月1日第1卷第3期。同期载有郭沫若的回忆录《神泉》、茅盾的短篇小说《一个理想碰了壁》、绀弩的短篇小说《在新加坡上岸》、郁茹的中篇小说《龙头山下》、史特朗的报告文学《农民老李》、周而复的长篇小说连载《白求恩大夫》,以及巴人、适夷、无咎、秦似的文论作品等。
(2)《试炼》刊于《小说》1949 年1月1日第2卷第1期。同期载有艾芜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茅盾《春天》、葛琴《贵宾》、适夷《方县长》、周而复《在省政府里》、蒋牧良《挖了下去》、艾明之《搜查》等七篇短篇小说,张天翼的寓言《混世魔王》,以及孟超等人的五篇小说批评。
《路》《试炼》这两篇小说侧重展现不同阶层人们对于新时代新出路的不同态度,鼓舞人们抛弃惶惑犹豫,坚定地参与到新时代的历史建构中来。《路》里的企业家蒋国鼎表面上是个民主人士,并无鲜明的政治立场,但其实是个极端自私的商人,虚伪贪婪,唯利是图,从不关心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在上海民众发动反美扶日爱国运动之际,他激烈反对女儿爱琼参加爱国运动,嘲笑年轻人的爱国热情,还情欲膨胀,痴狂追求自己的女秘书李丽君,整日耽于夜总会而不能自拔。他不相信共产党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拒绝友人程万里的劝说,穷尽心思想把企业迁离内地,最终带着情人李丽君一同乘船奔赴香港。站在新的历史关口,蒋国鼎、李丽君们在彷徨失落中选择了逃离,更多的爱琼和程万里们则在坚定信念中选择了留下来。《试炼》里的主人公陈群奉组织命令秘密创办培英学校,坚持了八年,因内战爆发,学校失去办学经费即将关门。他四处筹款而不可得,更加深了长期积累起来的对这份职业的厌倦,一心想向组织申请调离。在得知自己的上线为了保护自己和其他同志不被暴露英勇牺牲后,灵魂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洗礼,决心留下来,与师生一起向周边百姓借粮,维持学校运转。没想到平时他们很少和百姓打交道,关键时刻却得到了百姓的无私支持。作家藉此隐喻的是,在新时代的大潮面前,人们都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与锤炼,而历史的建构最终还是要依靠人民,最可靠的出路还是与人民为伍,与时代同行。
四
以群短篇小说创作体量不大,但特点鲜明,彰显出强烈的左翼文学色彩,这和以群长期的“左联”活动经历及其自觉的左翼文学追求密切相关,与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精神影响密切相关(9)以群对鲁迅、茅盾先生尤为尊重,“左联”乃至新中国时期曾多次撰文深情回忆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呼吁深化加强对鲁迅作品及其精神的研究。抗战时期应组织安排,以群与茅盾先生过从甚密,悉心照料,被人们称为茅盾先生的“大管家”。鲁迅、茅盾先生的文学思想及其精神对以群影响至深。。1932年,年仅二十一岁的以群奉命到安庆组织创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安徽分盟,后返回上海担任“左联”组织部长。在安庆期间,以群邀请周文共同主办《安徽学生》(10)《安徽学生》主编落名“叶燦”,载有《编后的话》及文论两则。经查相关资料,发现“叶燦”应z为以群。以群,原名叶志泰,入中学后改名叶元燦,常用笔名华蒂、以群等,“叶燦”该名比较罕见,当为“叶元燦”之简化。考定依据有二:一是据作家周文回忆,当时他经以群协调转到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处工作,共同编辑《安徽学生》。提及该段经历时,周称以群为“叶元烁”“华蒂”。参见周七康整理《周文自传》,新文学史料,2002(2)。二是据时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盟宣传部长刘丹回忆,以群奉命到安庆组织建立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安徽分盟,主编《安徽学生》。参见刘丹《关于安庆左翼文艺活动的情况》,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安庆文史资料第24辑.1992,p29。,依托《安徽学生》阵地撰写文论,宣传左翼思想,传播左翼文化,这一时期的以群已然显示出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卓越才能与巨大热情。青年以群就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作家对于现实社会的把捉。作家的任务就在于以锐利的眼光,观察出现实社会的矛盾及其必然的发展。……绝对不能迷混在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梦中;相反的,必须站在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广大的群众的立场上来写作。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抓住社会进展的枢纽,才能抓住群众的心;也只有这样的文艺才能发生其对社会的反作用——激发群众的情绪,推进社会的发展。”[3]抗战时期,以群呼吁作家打破与“大众”之间无形的墙垣,克服“旁观者”或“访问者”的角色限制,深入生活,参与战斗,因为“无论‘访问’得怎样周详,‘参观’得怎样普遍,却决不能了解到中国民众生活的深处”,“不能溶合在中国民众之中”,“不能了解中国民众自身的‘感觉’,因而也不能发生对于中国民众的深切的‘同感’”,“而这‘感觉’和‘同感’,却正是文艺的生命”[4](P57-58)。这种鲜明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以及对文学社会功能及作用的高度推崇,一步步深化并根植于以群的文学理论世界,成为以群文学理论思想的深厚底色和坚硬基石,也深刻影响到了以群的短篇小说创作。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以群的短篇小说创作也是对其文学理论思想的生动实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群的每一则短篇小说皆突出其社会效用,莫不与社会现实密切关联,莫不深切把握着时代脉动,莫不隐含着敏锐的批判与建构意图。
细读以群的短篇小说,我们很难找寻到作家个体情感的恣肆奔放和故事情节的复杂交织,给予读者深刻印象的还是一个个“人”的塑造,尤其是“新人”形象的塑造。塑造人,始终是以群小说创作的核心观念。以群曾批评小说家过度关注故事的“趣味”与“出神入化”“惊心动魄”,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并且认为“描写人物的性格,决不能借杂凑的支离的‘议论’,也不能用罗列的琐碎的状貌或动作,而必须抓住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由人物在这环境中‘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地想’‘怎样地做’,来表现人物的特征的性格”[5](P238)。1940年12月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小说晚会,讨论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问题。以群也热烈参与讨论,明确提出:“小说的主体是人物。失去了人物,那小说将等于一张白纸;而没有生动的人物,则那小说也是如一幅没有光暗的图画……应从行动中表现人物,从发展中表现人物,从矛盾中表现人物。小说家应该更勇敢地从复杂的现实中,从广大的地区内,去发掘新人的萌芽,确定新人的存在。”[6]基于这种自觉的小说叙事观,以群的作品着意于在宏阔的时代环境、复杂的现实变动和丰富的痛苦中表现人物,建构人物,尤其给我们集中塑造了一批新人形象——他们曾经是蒙昧的孩子、怯懦的农民、纤弱的女工,抑或单纯的学生,在苦难中成长,在战争中洗礼,在人民群众的怀抱中滋养,在民族国家的土壤中建构起人的主体性,逐步发展为时代的新人,自由诚朴,生机盎然,参与建构并时刻见证着一个民族的崛起、一个国家的新生。综观以群的短篇小说创作,我们感受到的始终是一个左翼作家执着的现实主义追求和炽热的民族国家情怀,虽未那么绚烂夺目,亦在沉静坚守中辛勤耕耘着自己的文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