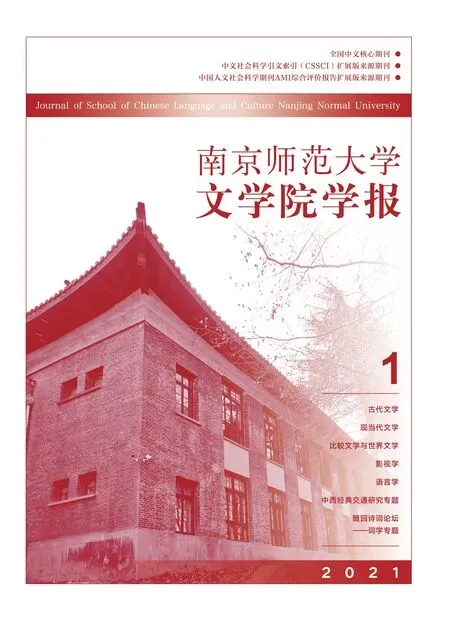退行巨婴·暗黑童话·隐性置换
——《隐秘的角落》精神分析理论解读
周 粟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088)
阿根廷心理现实主义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 Sabato)在小说《隧道》中,塑造了内心丰富却又过分敏感的主人公胡安。胡安对一位素昧平生的姑娘产生了极端的认同感,因为只有她留意到自己画作中不起眼的“隐秘”小窗;而这位惺惺相惜的女人,最终却死在了他的刀下。整部小说传达出这样的主题:“人心之晦暗,犹如一条长长的孤独的隧道”[1]。
正如研究者在评论《隧道》时所说,“那个隐秘的小窗户将两颗孤独的心灵相接通”[1]——2020年成为“爆款”的心理悬疑剧《隐秘的角落》中,主人公朱朝阳与张东升之间那份“隐秘”的镜像关系恰巧与此形成互文。可以说,对于“人心”的触摸与窥探,已成为众多文艺作品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笔者认为,以“精神分析”作为理论武器,最适合碰触《隐秘的角落》里隐藏的角色内心,进而有利于使作品“脱离时空和因果的掣肘,而流住进‘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的铸模’”[2](代序P3)。这是因为,精神分析学说关注的核心正是人的潜意识。“‘潜意识’……处于更隐秘、更深层、更原始的层面,……它包括人的原始冲动、各种本能(主要是性本能)与本能相关的各种欲望。”[3](P132)精神分析理论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电影文本(1)下文将借用“电影学”相关理论,分析《隐秘的角落》这部接近电影质感的网络剧。的阅读技术,它在根本上是一组欲望分析的基本模型”[4]。
本文将由“精神分析”这一锋利尖锐的理论之刀切入,挖掘《隐秘的角落》文本表象下潜藏的潜意识隐喻表征;同时结合《隐秘的角落》于泛文本层面特殊的“反转结构”,尝试“洞穿”屏幕之外受众的内心欲望,并最终窥探其潜意识文本内里更为深刻的美学指涉。
一、“我还有机会吗?”——对心理防御机制下“退行”巨婴的描摹
(一)退行心理防御机制下的双生巨婴
精神分析理论指出,由于“人格要面对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本我巨大能量和超我强大制约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生成“心理防御机制”,从而“减轻压力痛苦,帮助个体回避矛盾,自我安慰,自我开脱”。[5]这其中,“退行”作为一种“消极心理防御机制”,会使人在遭遇巨大压力时,呈现出与真实年龄不相符的幼稚行为反应——通过放弃真正成熟的应对方式,回到假想中的孩童状态,从而平复巨大的焦虑,重塑内心的安全感。
《隐秘的角落》中,许多细节钩沉都指向这种隐秘于人物内心的潜意识防御机制。剧中的朱朝阳和张东升具有一个共同点——退行性的“巨婴”心态。当孩子输掉了在乎的游戏,常常会问“我还有机会吗?”如果得到否定的答案,那就宁愿关机重启,全部推倒重来。这源于孩童时期“本我”的本能发泄——不属于我的东西,宁可摧毁,也不想让他人得到。剧中,当张东升问出“我还有机会吗?”并得到否定的回应时,其潜意识中的“退行”机制开始运作,他在“本我”的强烈驱动下内心退化为“巨婴”,随即选择山顶推下岳父母、换药害死爱妻的极端手段,强制重启,推倒重来;同理,在说出“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事,就是给你们开了门”之前,“退行”机制早已在朱朝阳的潜意识中生根萌发,如同玩游戏的孩子看到“GAME OVER”后选择关机重置一样,朱朝阳其实早已暗下决心,“重启人生”。无论是成年张东升在决定害死妻子前夸张的“假哭”表演,还是少年朱朝阳得知父亲对自己偷偷录音后的“可怜”演绎,都呈现出典型的“巨婴”心态——一种向大人卖惨博取同情,进而获得欲望满足的退行性潜意识外现。
剧中针对这种典型的“巨婴”心理,展开了较为传神的细节刻画:当张东升自以为扫清岳父母的阻碍重获妻子的依恋时,竟情不自禁做出高高跃起假装投篮命中、大口啃食咀嚼苹果等孩童才会做出的幼稚举动;当电梯里发现对方没有父母看护时,张东升立即对曾经向自己滋水的小孩,实施睚眦必报的凶狠“复仇”,而非像成熟成年人一样“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当被问到最大的愿望时,张东升脱口而出“我希望一切可以重来”。——在张东升内心存留的那块“隐秘的角落”(即潜意识)中,他始终秉持“告别过去,重新开始”的强大信念,但他坚持的所谓凤凰涅槃的背后,正是覆水难收的罪恶肇始。
进一步看,朱朝阳更是在张东升版“巨婴”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朱朝阳的心思更加缜密(用头发丝作机关防备严良和普普两个同龄人),对人心的理解更加透彻(紧抓张东升这个强大对手的唯一弱点——憎恶背叛,顺利“借刀杀人”)。他总能如“小大人”般窥探到大人自责、内疚、懊悔、愤怒等细微的心理变化,把握心理痛点后“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一种放大孩童在成长过程中察言观色能力、进而寻求物质或情感回报的本能彰显。潜意识中,朱朝阳在“退行”的基础上新增了另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压抑”,他以强大的的隐忍压制自己的本能欲望,相较张东升更能接受“延迟满足”;他通过塑造出楚楚可怜的“超我”道德形象,激发大人们的怜悯与关注,但这种内在的成熟又能在旁人眼里形成“羚羊挂角”、毫无察觉的假象。当逐渐意识到单纯的忍让和直接的反抗并不能重获父爱时,朱朝阳便不再执着于“情绪”上的对立,而是在“心绪”层面谋划面向长远的计策:他充分借助不幸家庭中锻炼出的人生经验和天生具备的缜密思维,通过“扮猪吃虎”,最终“杀人诛心”。
例如,当父亲为给痛失爱女的再婚妻子有所交代,选择偷偷对自己录音时,朱朝阳强压住内在“本我”强烈的愤怒和极端的嫉妒情绪,转而带着充满愧疚的语气对父亲说:“我真想和晶晶妹妹交换一下,就算我死了也没关系,这样,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卑微的话语却如软刀子一般,生生插入并剥开父亲内心最不愿被碰触的“隐秘的角落”——他敏锐地抓住父亲本就无比内疚、生怕再次伤害唯一的孩子的敏感心理,瞬间赢得了父亲加倍的关注与怜爱。又如,当父亲的再婚妻子央求朱朝阳不要告发她弟弟王立时,朝阳直接用父亲曾经的教诲“弱弱”地回应道:“爸,你不是让我从小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吗?”真诚的话语却立刻使父亲骑虎难下,如同将良心置于火上炙烤般煎熬。再如,朱朝阳会利用张东升内心“隐秘角落”(潜意识)中对“背叛”行为的极度痛恨,刻意设计存储卡事件造成严良“背叛”张东升的假象,激发一向冷静的张东升失去理智,在“借刀杀人”的同时,竟把老练的张东升玩弄于股掌之中。
(二)“巨婴”身后的渴望与“本我”反噬的毁灭
相比张东升外露的“巨婴”心态,朱朝阳充分隐忍压抑的心理防御壁垒,使其显得过于成熟;但本质上,朱朝阳和张东升一样,仍然是典型的退行性“巨婴”。朱朝阳“少年老成”的表象背后,是渴求重获父爱的淳朴愿望;而张东升变态心理的本质,也仅仅是为了活得更有安全感。例如当普普天真地问出“你读书就是为了杀人吗?”时,张东升会坦承地回答:“你们有没有特别害怕失去的东西?有时候为了这些东西,我们会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又如他对妻子会毫无自尊地说出:“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你不离开我,我什么都可以接受。”由是观之,朱朝阳和张东升看似违背常人伦理的恶行背后,隐藏着隐秘而单纯的初衷——对缺失的爱与安全感的渴求。
从精神分析“三我”理论看,“本我”秉承的就是毫无约束的快乐原则,而“超我”必然要对人有责任、良心与道德上的合理规范。“幼稚的人谈喜欢,成熟的人谈责任。”原本善良单纯的初心愿望,却孕育出畸形黑化的“恶之花”,进而催生出不择手段的卑劣恶行,朱朝阳和张东升在被强大“本我”反噬的过程中,放弃了亡羊补牢、迷途知返的成熟做法,任凭不受约束的欲望将其推向“摧毁重建”的罪恶快感并越陷越深,最终毁灭在由“本我”搅动的罪恶泥淖中不能自拔。
被众人轻视的人生虽然可悲可叹,但在任性地产生“推倒重来”的心念且付诸行动的当下,“张东升们”已彻底放弃了人之为人必须承受的责任,也就相对失去了体验正常人生的选择权利;当他们刻意忽视多样人生的客观存在和人性本身的含混复杂时,本质上他们已失去了“重来的机会”,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再“重启人生”。
二、关于“小白船”的“暗黑童话”——“镜像理论”与“耻感文化”催生的白日梦
(一)以“镜像理论”看潜意识的梦境编织
作为一部充满话题性的高评分网剧,《隐秘的角落》诞生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如张东升凝视镜子中秃头的自己,铲掉曾经挂过结婚照的墙皮,等等。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无论是张东升戴假发的怪异举动,还是朱朝阳下意识搓手、用涂改液修改日记乃至更换全新的日记本的行为,都呈现出典型的“掩饰”心理。张东升和朱朝阳试图抹去与铲除的,其实正是他们头脑中痛苦不堪的自卑记忆,他们的潜意识深处充满了“忘掉过往、重启人生”的强烈需求。例如朱朝阳和父亲因为录音笔事件谈话后,吃剩的糖水碗里出现了一只显眼的苍蝇,这隐喻着父子俩的亲密关系已经不再纯粹,“黑化”后的朱朝阳决定重塑曾经失去的人生;而张东升摘下假发、凝视镜中丑陋自我的过程,则象征着他在外人看不到的隐秘角落终于能卸下心房,回退到拉康镜像理论提到的“想象界”阶段,再次经历一遍由“理念我”到“镜像我”的“镜像同化”过程,进而尝试修复他既极度自卑又充满无限自恋本能的潜意识。
“在拉康的脚本中,在镜像阶段,父亲被假定为缺席的,那是由母亲统御的阶段。”[6](P531)当张东升凝视镜中自我的时候,其实镜中潜意识里呈现的正是年幼时期的本我,而这个年幼的自己恰好与朱朝阳形成了镜像关系,即代表着“镜像我”的朱朝阳也在同样凝视着象征“社会我”的张东升。对于父爱缺位的朱朝阳来说,张东升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父亲的角色,教导自己如何面对成长过程的手足无措;而对于人生充满压抑与遗憾的张东升来说,具有同样缜密思维和被众人轻视经历的朱朝阳更是与自己惺惺相惜,他在潜意识中多么希望朱朝阳能够“重新来过”,盼望“朝阳”真正再次“东升”。
于是,正常的“掩饰”行为在两人共同经历的痛苦渲染下逐渐异化,镜面内外的二人需要找到一个更加适合的出口,以满足潜意识中不断膨胀的本我欲望需求——这个出口就是编织容纳全新人生的“童话故事”,也即包裹着潜意识的“白日梦”。从人格心理学角度看,“压抑”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选择性遗忘”,所以张东升用铲掉墙皮的方式铲除曾经被妻子背叛的过往记忆,朱朝阳也选择性地编造了一本新的日记记录自己全新的人生童话;同时“压抑虽然使自我暂时免于威胁,但这些难以被个体接受的意念并不会消失,它们在潜意识里蠢蠢欲动,伺机突破”[7](P94),所以张东升才会在临死前对朱朝阳嘱托:“你可以相信童话。”张东升希望以自己尽管扭曲但满足了本我欲望的人生经历给朱朝阳“洗脑”:虽然无法像《红与黑》中的于连那样完成逆袭,改变“世界与自己为敌”的笛卡尔式悲剧,但他们却能够活在虚妄美好的“隐秘角落”中;因为只有在自己构建的白日梦境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这类人,才能如唐·吉诃德般获得所谓的强大力量,于想象世界中主宰自己的人生。
(二)“耻感文化”裹挟下的欺骗与逃避
正如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所说:“与怪兽作战者,可得注意,不要由此也变成怪兽。若往一个深渊里张望许久,则深渊亦朝着你的内部张望。”[8](P119)张东升“存在主义”式的主体性焦虑浸染了朱朝阳的内心,最终朱朝阳被其教导的笛卡尔式“童话”彻底“同化”,他决定一生都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虚妄童话里“快乐”地沉沦下去。实际上,活在“童话”的梦境里是一种极端的“逃避”行为,但正如日本一部知名电视剧剧名所写的那样——“逃避虽可耻但有用”。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深受东方思想中“耻感文化”影响的人,易于在“成长过程中相信一种安全感,即依靠他人对循规蹈矩的微妙的认同感”[9](P199)。用梦境来逃避现实的张东升、朱朝阳们始终坚信,只要不打破这种“安全感”,他们就能沉醉在童话般美好的幻象里自欺欺人。这是因为,“耻感文化”里,“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受到众人奚落,或是因为受到嫌弃,或是因为他自己想象会受到讥笑”,但必要条件是“它要求有旁观者在场”——如此,“只要不良行为未‘公之于众’,他就不必懊丧”。[9](P197)张东升和朱朝阳二者的内心极度敏感,他们既容易“举轻若重”(“高自尊人格者”,极其在意他人评价,缺少“钝感力”),又往往“举重若轻”(“耻感文化”下,只要恶行不为他人所知,就可对“负罪感”视而不见)。他们宁愿选择逃避,也要极力追随潜意识的欲望召唤,臣服于由强大“本我”裹挟着的、能够“随心所欲”的本能快感。
朱朝阳之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妹妹少年宫坠落当天的实情,是因为他选择了“相信童话”,直至最后,他已分不清童话和现实孰真孰伪,深信自己在日记本中编织的另一个版本就是真实人生。但正如普普在给他的信中所说:“少年宫那件事,我从来没和严良提起过。我会永远帮你保守这个秘密。不过我还是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有勇气地说出来,因为只有那样,才算是真的重新开始,对吗?”朱朝阳在和张东升一样选择“相信童话”的那一刻,已经彻底放弃了真正“重启人生”的机会,他注定一生都要在谎言中欺骗下去。这里,《隐秘的角落》与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形成了强烈的“互文”关系——时过境迁,除了当事人以外,人们并不会在意和追究事实的真相,只会赞叹童话、梦境中的当事人的传奇经历;而“造梦者”也选择后半生都去相信所谓传奇美好的童话梦境,把真相压抑进潜意识的冰山深处;但是,这些编织童话的讲述者、这些创造梦境的造梦人,在践行本我“快乐至上”原则的同时,却再也无法摆脱终其一生“始终在逃避”的沉重心念。
(三)“三我”模型下的人性角逐
从精神分析人格理论角度看,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三我”模型中,被欲望反噬后的朱朝阳恰恰代表了其潜意识中的“本我”,而普普象征着朱朝阳纠结但仍心存善念的“自我”部分,严良则体现了朱朝阳潜意识中理想化的道德“超我”。纵观《隐秘的角落》全片,普普(“自我”)自始至终没有向严良(“超我”)提起少年宫的真相——她既没有告发朱朝阳(“本我”),也没有纵容他(而是采用写信的方式,期望朱朝阳能够“良心发现”,说出真相);而严良(“超我”)始终想向警方坦白真相,他渴望维持社会正义和公正,不能容忍杀人犯罪的张东升逍遥法外,甚至大公无私地希望朱朝阳(“本我”)向警察说出真相,坚持“至善原则”。所以当“超我”(严良)质问“本我”(朱朝阳)“你为什么要撒谎,告诉警察吧!”时,朱朝阳才会代表“本我”祭出完全追随本能欲望的回答:“我想要重新开始,像我爸希望的那样。”这正符合精神分析学说中“三我”的理论观点,即“本我”(朱朝阳)和“超我”(严良)始终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只有通过“自我”(普普)的中间调和,使其此消彼长。
同时,由《隐秘的角落》后半部分那段亦真亦梦的“童话故事”看来,朱朝阳的内心并非没有经历过强烈的波动和斗争。在他的潜意识中,“超我”部分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在开学典礼上,代表“超我”的严良才会带着光芒走进礼堂,与朱朝阳对视;所以从船上坠亡后又在朱朝阳的“童话”中被“复活”的严良,才会笑着对老陈说出坦荡的一句“我没有做坏人”;也因此在看不出真实还是梦境的最后,严良会向老陈表达出“长大想当警察”的愿望。朱朝阳在潜意识中仍然重视象征“公平正义、道德责任”的“超我”的强烈感召,而“童话”中老陈的回应也同样意味深长:“行啊,当不当警察不重要,把腰杆挺直了!”由此可见,朱朝阳在潜意识中深知自己的处境——他一直是在“童话”中逃避真实的人生,他终其一生都将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和良心谴责,他永远无法如象征“超我”的严良那样真正“挺直腰杆”,成为一个坦荡的大写的人。
(四)“白日梦境”与“暗黑童话”
荣格曾说过:“梦是通向内心深处和心灵中最隐秘深幽处的一扇小暗门。”一旦自我防御机制的力量减弱,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真实欲望就可能重新浮出水面,所以精神分析非常重视“从梦的显相中找出梦的隐义”[3](P133),挖掘出隐秘的“皮袍下的小”。同时荣格指出,“心灵中永远存在对立的张力(特别是意识和潜意识的两极)”,而“梦就是心灵力图恢复平衡而自发产生的一种象征。潜意识通过梦刺激意识重新定向,从而与潜意识相协调”,由此荣格得出一个结论——“梦具有补偿的作用,梦的功能在于补偿意识和自我”。[7](P116-P117)在影视创作历史上,从《野草莓》到《八部半》,从《穆赫兰道》到《盗梦空间》,有大量以梦境为意向进行心理描摹与人性雕琢的优秀作品。丹泽尔·华盛顿在《时空线索》演出了即使是梦境也充满宿命轮回往复的悲剧性,马修·麦康纳在《惊涛迷局》中为“儿子”创造出了与早已离世的自己相遇的童话世界,而斯派克·李在《第25小时》中更是展现出这样的哲学思辨:梦境越是美好幸福,反衬之下的现实则越显出冷冰冰的残酷;也正是因为赤裸裸的苦涩现实,才迫使做梦的人逃到编织的梦境童话中寻求暂时的心灵补偿。
在《隐秘的角落》中,张东升、朱朝阳缓解所背负压力的泄洪出口同样是创造“白日梦”。当梦幻童话中“小白船”飘入绝美银河的同时,“暗黑童话”里张东升遇害妻子的尸体已无助地漂泊在大海上。这里,创作者于不经意间向观众抛出了尖锐的问题:“梦境就一定是美的吗?童话不残酷吗?”实际上,《隐秘的角落》在开场动画的隐喻中,已充分展现了狼吃小鸡的残酷现实;那些正义战胜邪恶的童话般结局,正是成年人为了教育孩子而赋予的“第二重文本”。因此,“小白船”的梦象实质上是朱朝阳创造的“暗黑童话”,只是经过朱朝阳对意识和自我的补偿作用后,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了。人格心理学认为,“合理化”(又称为文饰作用)是“用一种自我能接受、超我能宽恕的理由来代替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或理由,以证明自我价值感的防御机制”[7](P97)。朱朝阳在自己编织白日梦境时,选择性地让隐藏的梦思(梦的隐义)“采取了伪装的、合法化的方式、隐蔽的方式在梦中体现出来”[3](P134),并通过梦的“二度修饰”使得童话般的梦境更加栩栩如生,这样,深藏在朱朝阳内心的强烈负罪感通过梦的“移置”作用被想象性地替换掉了,而“梦的隐义则更加隐蔽”[3](P134)。最终,象征美好纯洁的“小白船”,载着朱朝阳编织的“暗黑童话”,内化为其潜意识中得以逃避现实甚至“诗意地栖居”其间的“隐秘角落”。
三、影像阅读的快感溯源——“影子主角”的极致反转与审美欲望的“隐性置换”
(一)悬疑经典中“影子主角”的极致反转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10](P22),这其中,“突转”即“意外的转变”[10](P22),指的是“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10](P33)。从这个定义看,“突转”可以被理解为悬疑剧中广泛使用的“反转”手法。笔者认为,“反转”技巧存在着提升受众审美快感的内在逻辑——通过前期制造“悬念”及“反转”后的释疑过程,让受众产生“恍然大悟”的完形补偿心理,并在大脑极度兴奋的运作下,通过迅速整合原本零碎的细节线索构成“心理闭环”,“进而在提升故事戏剧化程度的表层意义下,满足潜藏在观众内心的深层欲望”[11],最终完成创作者与观众间以作品为纽带的思绪“共谋”。
传统的国产悬疑剧往往以“人物之反”或“情节之转”这两种“反转”结构谋篇布局。“人物之反”指“人物身份或命运转变前后的二元对立”,而“情节之转”则是“情节向相反情境转化的过程”。[12]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悬念引发的突转不仅指剧情的跌宕起伏,而且还立足于人物刻画,力求通过情节的合理突转而表现人物或剧烈或细腻的丰富变化”[13](P46),可以说,《隐秘的角落》就是内地悬疑剧中精妙运用“人物之反”的典型作品。虽然全剧前半部分会以数次的“情节小反转”撩拨观众的完形欲望,但全剧结尾处朱朝阳回忆妹妹坠落的惊人一幕,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人物极致反转”。正是这次极为隐晦但又令真相昭然若揭的大胆“反转”,使得观众产生“恍然大悟”的惊呼,即“受众由前文本所积累起的所有情感和认同,由于其‘不可靠性’而化为乌有”[14],并推翻了观众在此前持续抱持着的“朱朝阳是乖孩子”的人物合理性期待。由此,观众在目睹这一“极致反转”并看到“全剧终”的黑幕后,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这种快感源于《隐秘的角落》创作者将这种“绝不悬置的细节勾连做到极致”,从而帮助观众的头脑在观剧后“获得‘智商提升’的象征性快感”[11]。
正如《隐秘的角落》编剧所说,“那些以弱制强的情节是阅读快感的来源”[15],为保证剧中朱朝阳隐秘的“惊天秘密”直到全剧结尾处才被“反转”揭示,以达到“出乎意料”的心理震撼,创作者必须让观众在此之前保持住对朱朝阳“将信将疑”的心理预设。特别是在“张东升之心路人皆知”的故事前史的铺垫下,剧情做到持续“保守秘密”的难度极高。由此,《隐秘的角落》采用了一种欧美成熟悬疑片常用的角色设置方法——笔者称之为“影子主角”。《肖申克的救赎》中,影片的“第一主角”虽然是蒂姆·罗宾斯扮演的安迪,但他与观众之间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疏离感,使得观众虽无法看透“第一主角”的内心世界,但会被其自身散发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与此同时,观众反而对由摩根·弗里曼饰演的“第二主角”老瑞德倍感熟悉,印象深刻。朱朝阳就是和安迪一样的“影子主角”——为了使其最后一刻的“极限反转”充满惊喜,创作者必须要设计一个角色(老瑞德/张东升)挡在“影子主角”(安迪/朱朝阳)身前,同时聚光灯下的“第二主角”既要具有强烈的角色塑造力(减轻观众对“影子主角”的过分关注),又要把握观众情绪和注意力的平衡分寸,使其对若即若离的“影子主角”(安迪/朱朝阳)兴趣不减。这就好比一个“畏影恶迹”的人想要逃离自己影子的追随,若只是在阳光下疯狂奔跑,影子同样会跟跑得更快,只有做到“处阴休影,处静息迹”——躲到“隐秘的角落”之中,影子才会瞬间消失。所以,当预判到观众将会看出朱朝阳和张东升的镜像关系时,《隐秘的角落》绞尽脑汁设计出了张东升的那些“名场面”,以分散掉观众过多投射于朱朝阳身上的注意力;而朱朝阳也要尽量如影子般隐藏起自己的锋芒,潜伏在“隐秘的角落”中,等待最终反转那一刻的“华丽转身”。
和《隐秘的角落》一样,以《非常嫌疑犯》《一级恐惧》《七宗罪》为代表的欧美经典悬疑片,其核心看点就体现在这些看似弱小的影子主角“扮猪吃老虎”的过程中。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电影叙事善于抓住观众心理上的认同,这在电影学中被称为观众对角色的‘同情’(sympathy),在剧作法中称为观众对角色以及角色动机与行为的‘共情’(empathy)”[16]。当观众对“影子主角”因认同感和保护欲产生强烈的“同情”心理时,《隐秘的角落》再通过极致的“反转”,就更能彰显小人物对自身缺陷束缚的巨大突破,进而让现实中同为“普通人”的观众与其产生屏幕内外的“共情”。而在反转点到来之前,对于“影子主角”朱朝阳来说,其扮演者最合适的表演境界,就是要“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不能有任何抢戏的‘表演痕迹’”[11],进而让那些最有观剧经验和阅人无数的“专家型”观众,也只有在最后的“反转”到来时,才感受到出乎意料的补偿性快感。
(二)屏幕内外审美快感的“隐性置换”
让-路易·博德里曾指出,观众观看影像的过程就如同婴儿正在注视着镜子,这时观众处于由“象征界”向“想象界”的“退化”期,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与影像本身会产生充分认同;拉康也认为,“影院中的‘凝视’是观众在倒退进‘想象界’以后的‘观看’”,观众的代入过程则是在将自己的欲望投向屏幕,“因此可以说观影的快感就是通过银幕之‘镜’而获得的‘自恋’”[3](P145)。同电影的“造梦”机制相似,以精神分析角度看,《隐秘的角落》作为一部充满电影质感的网剧,同样在激发屏幕外的观众对剧中角色产生强烈的“欲望投射”;观众或许会惊讶地发现,当他们深度投入剧情并关注剧中角色的潜意识时,这些角色背后的本我欲望也已悄无声息地“侵入”甚至“洞穿”了观众内心的“隐秘角落”(潜意识)。
有学者指出,“本文总是由意识本文(表层结构)和无意识潜本文(深层结构)组成……文化习惯于让显露层面从意识本文中呈露,而让隐蔽层面在无意识潜本文中暗藏。”[17](P116)对于一般的“爆米花”观众来说,他们只会将注意力停留在表象文本即“故事再现”的影像阅读体验上,但是“研究者或研究型观众或会同时深入到隐喻层面文本的阅读”[5],这说明,“表象文本即故事本身在作用于观众意识层面的同时亦作用于观众的无意识层面”,而其中“无意识层面的互动虽然相对隐蔽,但恰恰至关重要”。[5]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进入促进了对这一层面的揭示”,即“创作者(导演)的无意识与受众(观影者)的无意识的相遇”。[5]
“阵图入眼浑如梦,回首江山又梦间。”试想一下,假设观众把整部《隐秘的角落》本身看作一场由导演引领观众进入的“大梦境”,那么剧中(梦中)的三次“坠落”细节就形成了合理的解释。无论是“第一次坠落”(爬山时岳父母被张东升推下山顶),“第二次坠落”(朱朝阳的妹妹朱晶晶在少年宫不慎摔下五楼),还是“第三次坠落”(严良在船边向朱朝阳进行嘱托后坠入大海),“坠落”这一动作意向本身都像“梦”中潜意识的求救信号,在暗示着一种寻求猛然“惊醒”的急促状态。但无论是张东升的岳父母,朱朝阳的亲妹妹(朱晶晶),还是朱朝阳的好兄弟(严良),这三组坠落的人都只是“造梦者”张东升和朱朝阳的“梦中人”,因此如果将《隐秘的角落》看作一场“大梦”,那么这“三坠”也并未“惊醒梦中人”,梦中的三组配角的坠落“故事”,在两位核心“造梦者”(张东升和朱朝阳)看来,也只是所做梦境中的三场“事故”而已。与此相反,当剧情后半段张东升也想跳楼寻死时,作为梦境制造者的他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向死而生”。张东升不敢“彻底醒来”,因为他仍要选择苟且“寄生”在由朱朝阳编织的暗黑童话中,任由梦境随波逐流,逃避真正大梦醒来的那一刻。
面对这些于潜意识中激烈博弈的“梦中事”,屏幕外的观众何尝不是在随着故事走向“咬牙切齿”?他们或哀其不幸,或怒其不争,而如此强烈“代入感”的形成,正是源于观众已随角色的潜意识进入故事编织的梦境之中,也即屏幕外观众的本我欲望不经意间已与屏幕内的角色完成了“审美置换”[17](P67-P70)。因此,观众才会想要替代剧中(梦中)角色完成对潜意识中“隐秘”欲望的完形补偿。与《隐秘的角落》相比,在导演王小帅的悬疑电影《闯入者》结尾处,角色坠下窗台后,故事旋即戛然而止,给观众留下了“醍醐灌顶”般的“留白”。《闯入者》选择的这种处理手法,让观众对影像(梦)中角色的“情感投射”突然“中断”,随即产生“间离”效果,迫使观众跳出原有被影像(梦境)引入的“思维舒适区”,引起观者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辨;而《隐秘的角落》却在剧中(梦中)三次“下坠”后仍选择让观众继续“沉睡”,这样的设计使得梦境中的故事持续流转,从而满足了观众潜意识欲望中被影像“持续催眠”的审美期待。“基于拉康理论的精神分析电影理论认为,电影观众作为‘凝视’的主体,是由电影‘建构’起来的,屏幕上放映的一切则是主体欲望的客体。”[18](P490-P491)《隐秘的角落》一反内地悬疑类影视剧因受制于表达惯性、作者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常常出现的戛然而止、含混不清的“隐喻性”表达困局,充分利用悬疑剧情擅长“释疑”的叙事特点,使观众从悬疑剧这类“‘高级思维游戏’中体会到特殊的审美意趣”[11],令其思绪得以流畅地游走于“想象的能指”之间。
举例来看,《隐秘的角落》开篇就“开门见山”地以“女婿山顶推下岳父母”的“名场面”,震撼了早已习惯开篇“拉家常”般慢热剧情的内地观众。这“一推”不仅从影像角度强烈调动起观众的感官刺激,更于伦理层面迅速“推动”了角色与观众间陌生感与疏离代沟的打破——张东升代替观众想象性地释放出蕴含于“本我”的内在情绪,从潜意识层面唤醒了看似不道德但又十分“过瘾”的本能快感。这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口腔期”“肛门期”等的五期理论虽颇受现代心理学指摘,但其核心观点值得借鉴,即“所有排泄都是一种快感”。《隐秘的角落》中,大量出现的因紧张而流汗、因恐惧而流鼻血、因愤怒而狂喊、因崩溃而痛哭等场景,本质上都暗含着一种彻底“排泄”的快感。当看到“凤凰男”张东升屡次想“凤凰涅槃”却被岳父母和妻子全家嫌弃、打压、背叛甚至无视时,当感受到朱朝阳妹妹不仅“鸠占鹊巢”还要面对哥哥放肆说出“他(爸爸)跟我说了,他就是讨厌你”的恶毒语气时,观众在“隐秘角落”(潜意识)中与痛苦压抑相连的记忆很可能被激活唤醒,“本我”中的不甘、愤怒甚至与朱朝阳同样产生的嫉妒心理,不经意间会随着内在情绪喷薄而出。正如博德里所说,观众可“伴随着银幕中的人物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失去什么,这种幻觉性的、想象性的满足正是观影快感的原因”[3](P145)。从观众的潜意识来看,无论是剧中严良帮助朱朝阳发泄,大喊“你大爷的!”,还是游戏菜鸟朱朝阳将父亲再婚妻子视为游戏中的假想敌后,立刻“一击KO”,都是一种压抑情绪凌厉奔涌的透彻宣泄,是角色在替代观众完成潜意识中欲望“排泄”的想象性满足,由此,《隐秘的角落》通过这种较为高级的处理手法,实现了观众内在欲望与角色潜意识之间不经意的“隐性置换”,最终推动受众获得影像引发的审美快感的彻底释放。
四、结语
古人云:“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对于人心中欲望的把握,是人之为人的永恒难题。正如《隐秘的角落》中张东升对严良所说的那样:“我不会杀你,我会让你们活下去,活得像我一样”,潜意识中不受约束的“本我”欲望往往会不断膨胀到无以复加,进而贪婪到尝试吞噬人性的“为所欲为”的境地。但是,当不受约束的欲望之舟在人心中翻江倒海时,潜意识中的“超我”仍会发挥更加强大的抑制作用,因此当严良最后嘱托朱朝阳时,化身“超我”的他才会语重心长地说道:“别做第二个张东升。”
有读者在评论悬疑经典小说《白夜行》时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隐秘的角落》通过对潜意识与人心的极端细腻的把握,把人性中的崇高精神和卑劣弱点都撕碎了呈现到观众眼前,达到了以往悬疑剧很少企及的人文思辨高度,整体提升了中国国产悬疑剧的创作水准。令人欣喜的是,在《隐秘的角落》大火之后,《沉默的真相》也以成熟的悬疑剧制作技巧和精良的工匠创作精神更进一步,赢得了超高的口碑反响。正如黑格尔所说:“心灵能观照自己,能具有意识……构成心灵的最内在本质的东西正是思考。”[19](P16)期待国产悬疑剧的创作者持续以对“心灵”的深入思考,推动更多揭示人性内涵、提升精神文明的经典作品面世,并在未来使中国内地悬疑剧成为足以冲出亚洲、走向国际的重要影视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