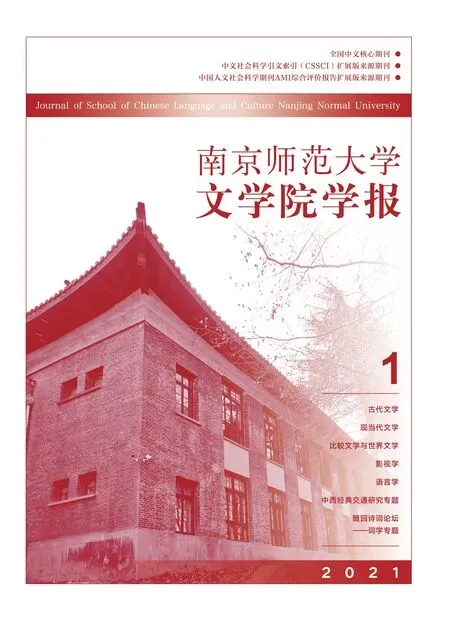讽喻还是娱乐
——宋玉《风赋》性质论
归 青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宋玉的代表作《风赋》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这篇作品想象丰富,构思精巧,语言精美,受到历代读者的赏爱。对于这篇作品的主旨,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讽喻说。人们认为作者通过雄雌二风的对比描写来揭示贫富、贵贱的对立和社会的不公,希图唤起国君的反省,从而改善政治。在《风赋》研究史上,讽喻说可以说是占着压倒性优势的意见。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声音,有少数学者认为,《风赋》的主旨不在讽谏,而在奉承君王,可以名之曰献谀说。与讽喻说比较起来,献谀说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又不无道理,客观上启发了人们对《风赋》评价的思路。在《风赋》性质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说明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也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风赋》是为讽喻而作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察:一是《风赋》有没有讽喻的效果;二是作者有没有讽喻的主观动机。就一般的情况而论,作者的主观动机和作品的客观效果是一致的,作者通过写作的构思和表达,最终形成某种效果而达到写作目的。审美效果是作者有意追求的结果,因此人们可以通过作品的效果去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有效地确定文本的性质。但是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由于作者的主观倾向表达得不够直接清晰,这时接受者的主观因素(时代、教养、阅历等前见)就会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发生较大的影响,从而对作者的原意和作品性质的理解产生较大的分歧。因此尽量祛除成见,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来求得作者的原意就是值得尝试的方法。
《风赋》存在着讽喻的效果,这是肯定的。这从古今大多数评论都认为本篇是讽喻之作这一现象中就已经得到了证明。即使献谀说者也未必会完全否认其讽喻的效果。但是,现在我们想要问的是,《风赋》的讽喻效果究竟是出于作者的有意追求呢?还是缘于读者的联想?
我们先来概述一下本文的梗概。楚王和宋玉共登兰台之宫,忽然一阵清风吹来,楚王披襟当之,大呼痛快之余,忽发奇想,就问宋玉,这样爽快的清风难道是我和庶人共享的吗?宋玉答道:这是大王之雄风,庶人怎么能和大王共享呢?楚王惊奇之余,就让宋玉解释其中的道理。宋玉说,风分雄雌,是由风所加的对象决定的,这就引出了宋玉对雄雌二风的描写,文章也在对二风的尽情铺写中结束了。
讽喻说的主要根据就在雄雌二风的对比描写,特别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庶人之风的描写上。大王之雄风是何等的舒畅,庶人之雌风又是何等的阴暗、肮脏,两相对比,这不就是贫富、贵贱的对立和社会不公的隐喻吗?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当作者把这两种现象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使读者朝讽喻的方向去理解,然而这未必是作者的原意。
先来看雄风一段。照讽喻说的看法,“时襄王骄奢,故宋玉作此赋以讽之。”[1](P246)雄雌二风的描写“反映了王公贵族生活的豪奢和黎民百姓生活的悲惨。”[2](P275)意思是说,雄风一段的描写意在揭露楚王的骄奢豪侈。可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按照宋玉“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1](P246)的理论,本段开始一直到“故其清凉雄风”之前,由于还没吹到王宫内苑,这时的风还不能说就是雄风。真正的雄风是这样的:
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衡,概新夷,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憯凄惏栗,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1](P247)
这一段描写既谈不上奢华,也算不上放荡,呈现的完全是美的意象。人们读了这一段,得到的都是美的享受,唤起的只能是赞叹向往之情,很难想象会由此产生愧疚、不安或者反感、拒斥的反应。一般读者尚且如此,对于楚王这样的人来说,倒要求他从中引起反省,这不是很奇怪吗?事实上,君权天授,人分等级,尊者豪奢,贱者贫困,对于楚王这样的人来说真是再正常不过了,享受“清凉雄风”的快感一点也不过分,怎么能指望他会因此而反省呢?也许有人会说,楚王虽然不见得会引起反思,但宋玉却是带着这样的目的谲谏的,但是这样的说法,恐怕也说不通。我们只要看看宋玉在《招魂》中对魂魄引诱方法的描写就可以明白了。主人为了吸引魂魄回归,不惜对声色享受大事铺陈,这说明无论是宋玉,还是一般人对于楚王享受豪奢生活都是视为当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楚王享受雄风的快乐,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仅楚王不可能从中领悟讽喻的意思,就是宋玉也不可能有借雄风来劝谏楚王的想法。
那么庶人之风这一段集中描写了穷人生活的困境,这总包含了讽喻的用意了吧。
夫庶人之风,塕然起於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於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目蔑,啗齰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1](P247)
写了陋巷中雌风的状貌,展示了庶人生活贫困、环境肮脏的一面,似乎是在展现人民群众的贫困生活,和雄风一段比,这一段包含的“批判”意义相对比较明显。但是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讽喻吗?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注意到,作者对庶人之风描写的前提(风有雄雌的说法)本来就是荒诞的,这也等于预先告诉了楚王(包括读者),所有这一切叙述都不是对真实现象所作的客观描述。他说得越认真,荒诞感就越强烈,读者也就越不会当真,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唤起楚王的反思呢?还有他对雌风的描写,也是竭尽夸大之能事,对雌风所到之处的丑陋、肮脏、病态作了穷形尽相地刻画。特别是写到雌风被于人身引起的种种怪相,真可以说是集丑陋古怪之大成,夸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同样会使读者产生失真感,使楚王和读者因此成了冷静的旁观者,从而也就消解了因身临其境而产生的同情心,这是不利于发挥讽喻效用的。我们的疑问是,倘若作者真是意在讽喻的话,他为何要采用这种与写作目的背道而驰的叙事策略呢?
再从两段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段一正一反,构成了对比、反衬的关系,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这两段间有没有主次之分?倘若有的话,哪一段是为主的?哪一段是为次的呢?按照讽喻说的思路,大约认为庶人之风才是重点,因为这一段描写穷人的悲惨处境,比雄风一段更具有批判性,更有助于引起人的思考,在满足了楚王享受雄风的快感后,让他感受一下庶人之风,也许会引起他的思考。但是这样的理解是不合文章内在的逻辑关系的。从全文看,这两段都是为了回答楚王“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的问题。雄风一段直接回答了楚王的问题,赢得了楚王的欢心,自是全文的重心所在。至于庶人之风一段,则是为了进一步满足楚王的兴趣而引申出来的,如果楚王不问,这一段也就不存在了。从两段的关系看,雄风是为主的,决定性的;雌风是为次的,被延伸出来的。假如没有雄风,雌风就不可能存在。反过来,假如没有雌风,文章虽然会因此逊色,却依然可以独立存在,“批判性”强的部分受制于不具讽喻含义的部分,这是讽喻说在解释上的一个难点。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需要回答,那就是这两段的对比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对比。按照讽喻说的解释,那是从社会不公、阶级对立角度出发的对比,但问题是,作者对雄风的描写完全是正面的,美好的,是不会引起反感的。把美丽的意象赋予要否定的楚王,却让受苦受难的庶人来作反衬,这样的关系是构不成对比的,也很难达到理想的讽喻效果。这说明,用讽喻说来解释本文的性质是难以说通的,作者恐怕没有讽喻的意思。
二、《风赋》的目的在取悦君王
既然讽喻说存在着上述矛盾,不能圆满地解释文本,那么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来对本篇的性质试作阐释,看看能否把问题说通,从而还原作者真实的写作意图,准确地把握《风赋》的性质。
能不能认为《风赋》是宋玉创作的一篇戏说(也就是说笑话)之作,或者说,是一篇以取悦君王为目的的喜剧性美文呢?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文章告诉我们,楚王(包括读者)期待于宋玉(文中的人物)的,就是要把一个荒唐的命题说圆通,而宋玉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完成这一在常人眼里难以完成的任务。挑战和应对,提出歪理和说通歪理,就是本文得以推进的动力所在,也是吸引读者读下去的张力所在。
文章一开头说,楚王站在高台之上享受到了痛快的清风,情不自禁地叹道:“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1](P246)第一句是由衷的赞叹,第二句应该理解为是楚王用问句的方式给宋玉布置了一个肯定性的命题,实际是要求宋玉把这个荒谬的命题给说圆通。对此宋玉不可能有第二种回答,不存在选择的可能性。果然,宋玉的回答把楚王的问题转换成了一个肯定性的命题,“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1](P246)提炼一下,那就是说,风是分雄雌的,这就成了全文需要加以论证的中心论点。紧接着楚王又说:“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1](P246)表面上好像是对宋玉之说的反驳,是以常识质疑怪说,指出宋玉之说的荒谬,实际上是给宋玉的回答增加难度。风既然是自然现象,怎么会有雄雌之分呢?读者的悬念一下子被提了起来,大家倒要看看宋玉将如何解释,文章的张力充分显现出来。然而没想到的是,宋玉三言两语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先讲了两个生活中的现象,“枳句来巢,空穴来风”[1](P246),说是因为树枝弯曲,才引得鸟儿来做巢;山洞中空才会产生大风,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1](P246)意思是说,风所以分出雄雌,不是由风决定的,而是由风所依托的对象决定的。这样的说法出人意料之外,却又有着一定的思辨深度,不能不承认有着一定的道理,难题被轻而易举地破解了,楚王取乐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然而楚王并不想就此罢休,他的好奇心被宋玉的回答激发了起来,既然风分雄雌,那么所谓的雄风到底是怎样一种风呢?可不可以说来听听呢?难度进一步增加,读者的心又紧张了起来。要知道,风无形无色,看不见,摸不着,很难描写,现在要求讲讲雄风的样子,更是难上加难。想不到宋玉意到笔随,洋洋洒洒,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清凉雄风在王宫内苑里逍遥徘徊,掠过花草树木,一溜烟直入密室洞房的情景,不仅生动细致,而且极富情趣,这使楚王对宋玉的才华大为叹赏,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连连叹道:“善哉论事!”楚王意犹未尽,既然说了大王之雄风,何妨顺便说说庶人之风,仍然是出难题。在对庶人之雌风的描写中,宋玉用漫画式的夸张笔法,集中展示了雌风的丑陋、阴暗和病态,以此来反衬大王之雄风,再次满足了楚王的虚荣心和优越感,这时庶人的痛苦和丑陋因为作者变形和夸大的处理,就转化为楚王(包括读者)欣赏的对象,让人因他们的滑稽古怪而发出捧腹大笑。
雄雌二风的关系首先是对比的,是贵贱、雄雌、美丑之间的对比。和讽喻说理解的对比不同,对比中贵者和雄者的一方,不是被否定的负面力量,而是加以赞美的正面力量。雌雄二风无论反差怎样强烈,都是相反相成,意在说明(也可以说是论证)“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1](P246)的道理。这一句话,才是作者用力之所在,目的是把风分雄雌这个匪夷所思的怪论说通,而不是为了揭露社会的不公,促使君王反省。还需指出的是,这两段又是有主次之分的。雄风为主,雌风为次。写雌风是为了反衬、突出雄风,目的还是为了满足楚王的虚荣心和取乐要求,也借此显示作者思辨和语言的才华。
从取悦君王的目的来看,文章三段的布局可以说是严密完整,合理有机的。每一段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娱乐戏说的效用,形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世界。这样的理解,我觉得要比讽喻说合理,可能也更接近作者的原意。
三、《风赋》的喜剧特征
如果说《风赋》的写作是以取悦君王为目的的话,那么笑的效果就是作者想要致力营造的,这篇作品就应该是一篇喜剧性的美文。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本文的喜剧性究竟体现在哪里,笑又是怎样产生的。
其一是荒诞之喜。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当事物呈现出一种违反常理的现象时,人们常会因为这种现象的荒诞而产生可笑的感觉。在本文中,当楚王发出清凉之风是不是与庶人共享的问题时,宋玉明确地告诉楚王说,“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1](P246)一本正经地宣称风有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并且很严肃认真地描绘了雄雌二风的状态、形貌,洋洋洒洒,一泻千里。这就在常识和怪说、内容的荒诞和言说方式的严肃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读者心中造成了明显的错位感和荒唐感,由此发出了愉快的哈哈大笑。
其二是意外之喜。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着一个人所共知的难题,却被人以一种超越常人的思路和方法解决时,也会使旁观者因为出人意外而发出惊喜之笑。问题的难度越高,解决的速度越快,喜感也就越强烈。这个意外之喜在本篇里主要表现在两处:
首先是对风分雄雌的解释。风是自然现象,从来没有听说过风还有雄雌之分。楚王提出了这个题目,并且设置了难度,在此前提下,要把怪论说圆通,难度可想而知。孰料宋玉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1](P246)不仅应对敏捷,而且言之成理。楚王包括读者听后,瞬间的反应应该是愕然,紧接着一想便觉得不无道理,随即就会因为领悟和赞佩发出惊喜之笑。
其次是对雄雌二风所作的穷形尽相的描绘。对风分雄雌的解说固然有难度,要对雄雌二风作精细的刻画更殊属不易。但这个难题也被宋玉轻松地解决了。凡是读过《风赋》的读者莫不为宋玉出色的描绘能力所折服。他不仅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有画面感,有动态感,在风的形象中渗透着人的感情,而且神思泉涌,佳言妙句联翩而至,使人对宋玉的才华赞叹备至,因而发出惊喜之笑。
其三是滑稽之喜。喜剧是对于丑陋和滑稽动作的模仿,这在本文中集中体现在对庶人之风的描写里。这一段所描绘的都是让人产生厌恶感的现象,本来病痛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同情心的,但由于作者使用了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拉大了对象和读者(包括楚王)间的距离,不仅消弭了因感同身受带来的痛感(也就是同情心),而且还因为反衬出读者(包括楚王)的优越感而成了观赏玩味的对象。尤其是其中对遇风得病者的描写:“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目蔑,啗齰嗽获,死生不卒。”[1](P247)真可谓穷形尽相,恶形恶状,由于夸张失实,没有人会把这当真,因此只能作为优越感的反衬,成为被人取笑的对象。
《风赋》的喜剧特征还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概括、分类,但上述几种无疑是比较明显的。我们通过对《风赋》蕴含着的喜剧因素的分析,基本上可以认定本篇乃是一篇具有浓厚喜剧特色的美文,是一篇以取悦君王为目的的戏说文章。
四、余论
在对《风赋》的性质作了以上的论述后,我们还想顺便提一下,类似这样的戏说文章在宋玉的集子里其实并不少见,这里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对楚王问》中写了楚王和宋玉间的一段对话。楚王问宋玉,为什么大家对你有那么多负面的议论啊?宋玉说,这很正常啊。唱通俗歌曲的人成千上万,能唱《阳阿》《薤露》的只有数百人,等到唱《阳春》《白雪》时,会唱的只有几十个人,会唱最高雅的歌曲全国只有寥寥数人而已。就像鸟中有凤,鱼中有鲲一样,越是卓然不群的人就越是不被众人理解,越是容易招致攻击。所以被多数人非议,非但不能证明我有问题,相反恰好说明了我是不世出的人才。[1](P839)像这样的回答,不能认为作者的目的在为自己辩诬,因为从功利的目的看,这是不能有效达到辩诬目的的,但倘从取乐的角度来看,则对文章的构思和效用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这篇文章的看点全在有趣,是一个笑的文本。刘勰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3](P254)刘勰把这篇文章解释为抒愤之作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就是宋玉故意正言若反,以嬉笑之辞来抒发忧愤,其意仍不在辩诬,喜剧性仍然是本文的特色。宋玉集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好几篇,例如《登徒子好色赋》《讽赋》《大言赋》《小言赋》等,限于篇幅,只能在此提一下。这说明,说怪话,讲笑话,以言语取乐是宋玉作品的一大特色,可以说,宋玉是中国游戏文学之祖,《风赋》的特点放在宋玉作品的系统里看,是很常见的,体现了他一贯的特点。但放到整个中国文学的潮流当中来看的话,则是一个异数,因而容易被人误读,现在是到了恢复他原貌的时候了。
最后概括一下本文的基本观点:《风赋》是一篇以取悦君王为目的的喜剧小品,获得笑的效果才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目标;《风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讽喻的效果,但这个效果不是作者有意求取的,而是读者联想的结果,这在以儒家政教文学观占主导的时代里是很自然的现象;相对于讽喻说,献谀说更接近《风赋》写作的实际,而本文所持的娱乐说对解释《风赋》的性质可能更为精准;在文体上,《风赋》兼有描写文(赋)和议论文的特点。既可把《风赋》理解为在议论文框架内的描写文,也可以理解为用赋体写的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