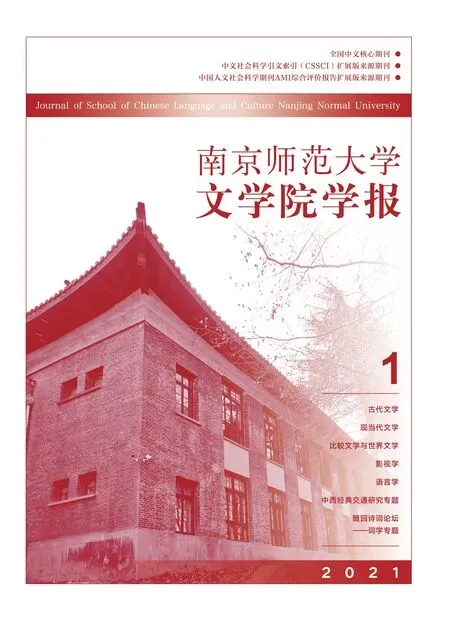李白坐狱浔阳献诗崔涣的法律适用考论
冒志祥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中国古代有很多狱中上书的名篇,如秦李斯的《狱中上书》、汉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狱中上书自明》、南朝梁江淹的《狱中上建平王书》、明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等。这些上书,或陈请王侯冀得宽恕、自剖衷心表明心迹,或与家人袒露心路历程、表明自己的愧疚之心……上书多用表、书、疏、启等,且无一例外均为“诏狱”。除文书形式,也有用诗词歌赋表明心迹的,如南朝梁王伟的《狱中赠人诗》:“赵壹能为赋,邹阳解献书。何惜西江水,不救辙中鱼。”以诗的形式强调自己有赵壹之才、邹阳之谋,希望有人爱才惜才、救自己出牢笼。
但狱中给谁上书、用什么形式上书、上书能否送达被上书人手中、能否产生实际效果,面临着很多法律问题,也考验着上书人的智慧。李白的浔阳献诗,就充分展现了独特的智慧。
李白57岁时因“附逆”李璘被系浔阳狱。在狱中,他主要给三类人写过诗:一是给曾经的好友,如《送张秀才谒高中丞》[1](P1063);二是给家人,如《在浔阳非所寄内》[2](P572);三是给当权者,如《万愤词投魏郎中》[1](P1542)等。其中,李白给时任宰相崔涣献诗最多,共5首,即《狱中上崔相涣》[1](P670)《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1](P672-673)《上崔相百忧章》[1](P1538)。李白为什么要反复给崔涣献诗?狱中献诗符合唐朝法律吗?这些献诗对李白附逆案件的审理又产生了多大作用?厘清这些问题,对全面理解李白诗歌、完整了解李白其人大有裨益。
浔阳,与“寻阳”通,唐朝浔阳属于江南西道的江州。李白给崔涣所献5首诗,内容有很大的重复性。《狱中上崔相涣》,开头写当时的现实:安史之乱,战士流血,百姓绝户;接着则颂赞崔涣和皇帝,“羽翼三元圣,发辉两太阳。”“贤相燮元气,再欣海县康。”而且将“贤相”置于“二圣”之前;最后流露献诗的真实目的:“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自己就像覆盆之下的鸟儿,等待着天恩浩荡,希望崔涣能出手救出浔阳狱中的诗人。《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其一以白起坑杀四十万俘虏的历史,假想“能回造化笔,或冀一人生”,强调自己对国家还能献出一份微薄力量。其二以平原君门客毛遂和孔子学生曾子自比,以“白璧双明月,方知一玉真”自明心迹,强调自己绝没有“附逆”贰心。其三以楚国宋玉《神女赋》“襄王有梦,神女无心”的典故,表明自己希望做襄王梦里的倾国倾城美人,再次申明自己为国效力的愿望。《上崔相百忧章》则叙述“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万愤结缉,忧从中催”的处境,借李广命舛、邹阳蒙冤,表明自己的冤屈,希望崔涣“台星再朗,天网重恢。屈法申恩,弃瑕取材”。冤狱能尽快清雪,“冶长非罪,尼父无猜。覆盆傥举,应照寒灰”。从5首诗的同质主题看,诗歌结构基本都是叙事、抒情、求请。可见,李白的5首献诗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狱中上书,是借诗歌述心明志,以诗伸冤,是一种特殊的“陈首”。诗人在《上崔相百忧章》中希望“屈法申恩,弃瑕取材”,那么,围绕一个“法”字,诗人希望崔涣如何“屈法申恩”,进而“弃瑕取材”呢。本文结合崔涣的宣慰大使身份和《唐律疏议》的条文,尝试对此作出解读。
一、李白为何会反复献诗崔涣?
李白献诗,适逢崔涣宣慰江南。此前,李白与崔涣并无交集,且崔涣宣慰江南的时间也在李白下狱之前,非因李白案而来。《新唐书·本纪》第五载,“(天宝十五载)七月庚午,(玄宗)次巴西郡。以太守崔涣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见素为左相。”[3](P153)按照唐制,此时崔涣实为宰相。同卷“(天宝十五载八月)庚子,上皇天帝诰遣韦见素、房琯、崔涣奉皇帝册于灵武。”[3](P153)故李白诗中多称“崔相涣”。前书同卷再载:“(至德二载)八月丁丑,焚长春宫。甲申,崔涣罢”[3](P158)。据此,崔涣为相的时间在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年,757年)七月至至德二载八月。关于崔涣,新旧唐书皆有传。《新唐书·崔涣传》说:“玄宗西狩,迎谒于道。帝见占奏,以为明治体,恨得之晚,房琯亦荐之,即日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3](P4318)而《旧唐书·崔涣传》记载比《新唐书》要详细一些:“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幸蜀,涣迎谒于路,抗词忠恳,皆究理体,玄宗嘉之,以为得涣晚。宰臣房琯又荐之,即日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扈从成都府。”[4](P3280)新旧唐书对崔涣的记述有共同的特点:“明治体”“抗词忠恳,皆究理体”,即为人正直,能言善辩,颇知法理。
李白狱中献诗,皆源于崔涣此时的特殊身份:江南宣慰使。宣慰使在唐时属于临时设置的职位,唐设宣慰使主要集中于唐太宗时期、唐肃宗时期和藩镇割据时期。《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对宣慰使都没有介绍,但从史料的一些零星记载中,可以梳理出宣慰使的主要职能和人员设置。陆贽《论淮西管内水损处请同诸道遣宣慰使状》论及宣慰使的职责是“今者遣使宣命,本缘恤患吊灾,诸道灾患既同,朝廷吊恤或异,是使慕声教者绝望,怀反侧者得词,弃人而固其寇雠,恐非所以为计也。”[5](P4823)可见宣慰使是“宣(皇帝)命”“恤患吊灾”、宣化声教。《新唐书·列传·孔穆崔柳杨马》记载:孔巢父曾为魏博宣慰使,“辩而才,及见田悦,与言君臣大义,利害逆顺,开晓其众”。后来“李怀光据河中,帝复令巢父宣慰”[3](P5007),而为李怀光所害。据此可知,宣慰使被赋予纠察违失官吏、开晓政义的权力。宣慰使的职责还包括代替皇帝到各州县宣扬政令、安抚百姓、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调查处置人事纠纷、宣慰少数民族事务等。关于宣慰使宣慰地方的随员设置,《旧唐书·裴度传》记载:“(以度)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诏出,度以韩弘为淮西行营都统,不欲更为招讨,请只称宣慰处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司勋员外郎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冯宿、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等为两使判官书记,皆从之。”[4](P4417)可知宣慰使宣慰一地,配属宣慰副使、行军司马、判官、书记等,据此,宣慰大使是可以独立审覆案件的。且宣慰大使的任选一般颇知法理、抗词忠恳、身居要职、深得帝宠。李白与孔巢父等六人并称“竹溪六逸”,对宣慰使的职责自然比较清楚。
《新唐书·本纪六》载,至德元年“十一月戊午,崔涣为江南宣慰使。”李白在代拟的自传体表文《为宋中丞自荐表》中也说“宣慰大使崔涣”为自己推复清雪[1](P1777),《旧唐书·崔涣传》载:至德元年“八月,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圆同赍册赴行在。时未复京师,举选路绝,诏涣充江淮宣谕选补使,以收遗逸。”[4](P3280)宣慰大使抑或江淮宣谕选补使,两者当为同一名称的不同说法,而江南宣慰大使,主要是代替皇帝宣慰江南道。唐时的江南道包括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李白系狱的浔阳,即在江南西道。如果如刘昫所说的江淮宣谕选补使,则负责江南道和淮南道的广大地区,当然也包括浔阳。
如前所考,崔涣为相在757年7月至758年8月。而至德二载“(二月)戊戌,庶人璘伏诛。”也就是说,李白下浔阳狱的时间一定是在至德二载二月至八月的这段时间。李白的献诗也应该写于至德二载的这段时间。但崔涣此次非因李璘案专门而来,其宣慰江南的时间较早,只不过崔涣宣慰江南,给了李白附逆案审覆清雪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白浔阳下狱到底于流放前还是流放后,抑或于首次流放后,因史料模糊,有一些争论。比如,《新唐书·李白传》云:“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3](P5763)明确是“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也有学者认为,李白的流放夜郎是在乾元元年,那必然是在至德二载浔阳系狱之后。还有学者认为,李白有两次流放夜郎的遭遇,系狱浔阳当在两次流放之间[6](P27-29)。可以肯定的是,李白本次浔阳下狱一定是与附逆李璘案有关,也一定发生于至德二载(758年)。有理由相信,《新唐书》关于李白的记载极有可能是错误的。
后来,崔涣因“惑于听受,为下吏所鬻,滥进者非一,以不称职闻”(《新唐书》本传)而罢相,其对李白浔阳系狱案件的查处也并没结束,宋若思是李白浔阳附逆案件审理的继任者。据《太平寰宇记》卷105记载:唐至德二年(757年),宋若思“为御史中丞领江南西道采访使兼宣城郡太守。”关于“中丞”的职责,《旧唐书》有:“大夫、中丞之职,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中丞为之贰。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讯之。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而已。若有制使覆囚徒,则与刑部尚书参择之。凡国有大礼,则乘辂车以为之导。”[4](P1862)也就是说,御史中丞的本职就是“掌持邦国刑宪典章”,对“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讯之”,而且可以“使覆囚徒”。结合李白的《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1](P674),崔涣罢相之后,宋若思可能以“御史中丞领江南西道采访使兼宣城郡太守”的身份接替崔涣继续审覆李白案件,履行中丞职责,以“覆囚徒”,并在崔涣审理的基础上,为李白从浔阳狱脱囚,还安排在幕府任参谋。崔涣与宋若思是李白浔阳附逆案件的先后两位具体推覆主官,故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说:“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复清雪,寻经奏闻。”这里的“前后”,学术界很多人认为推复清雪的是两起案件[7](P50-54)。笔者认为,此处说的是经过前后两位官员才推复清雪了李白的附逆案。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明确“经宣慰大使崔涣”,强调了崔涣作为宣慰大使“推复清雪”的作用。另外,李白的这句话也明确点出浔阳系狱与“永王东巡胁行”有关。
二、 李白献诗伸冤的法律可适性
前文已论,宣慰大使和御史中丞是可以对“称冤而无告”案件进行查处、或“有制使覆囚徒”的。李白知悉崔涣此时正在江南宣慰,他认为,推复清雪其冤案有了机会。李白献诗,既是伸冤,也是利用法律在为自己创造审覆清雪的条件。
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用了“陈首”一词,这是《唐律》中的法律术语。唐代对《唐律》和《疏议》是等同看待的。白居易的《论姚文秀打杀妻状》中有“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这里的“相争为斗,相击为殴”实际上是《唐律》第302条疏议的内容。白居易是明确将其以“准律”之“律”对待的。结合《唐律疏议》,可以考察李白“陈首”的法律可适性。
(一) 李白的“陈首”属于坐狱疑犯的权利
因李白系狱与“永王东巡”有关,作为附逆案件,如果被定罪,属于《唐律》列出的十恶重罪,非死则流。从附逆的韦子春等人被杖杀就能知悉此案之重。李白必知此次系狱的高度危险性。《唐律》对系狱疑犯的“陈首”权利,规定有“八议”,对疑似重罪还有所谓的“三请”。“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列出的实际是法外施恩的种种情形。“三请”即“奏议”“奏定”“奏裁”。《唐律疏议》卷二说:“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议者,原情议罪,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8](P32)“八议”“三请”一可保疑犯有申辩的权利,二可保特殊疑犯能得到宥免,三是明确此类案件要经皇帝最终裁决,体现皇恩浩荡。
尽管李白一直认为其被定“附逆”是冤枉的,但其《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和《赠韦秘书子春二首》《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伎》等又是铁证凿凿,要想“推复清雪”,一是要有当权者的受理,高适、魏郎中(姓名不详)、崔涣皆符合此条;二是受理之人能惺惺相惜,欣赏其才华,容纳其个性;三是对李白附逆之事的来龙去脉比较熟悉;四是具有相当权力,对“推复清雪”能发挥实质作用。关键是,受理此案要符合唐律规定。这个人选,崔涣最符合。根据《唐律疏议》,除有审覆权的崔涣之外,其他人等都无法替李白伸冤。所以,李白才多次给崔涣献诗。
那么,李白为什么只是献诗而不上表文呢?上表文只能呈送皇帝,对狱中的李白来说,他不是现任官员,被拘押浔阳是被人告发,所以他没有资格给皇帝上表。那能否用“启”类文书给崔涣上书呢?这也不是首选:因为这对崔涣不够礼貌尊敬,对崔涣能否受理也拿捏不准,不能很好展示自身才华和表达衷心。后来李白代拟推荐自己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是其当时已脱囚,二是以宋若思的名义上书自荐。
李白狱中献诗,一来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名声伸冤,并借此展示自己的才华;二来可以试探崔涣的态度,引起崔涣的注意,获得崔涣的欣赏。毕竟,以诗歌形式呈崔涣,也很符合崔涣的身份和唐代时尚。毕竟崔涣本次的宣慰,还承担着为皇帝选才的任务。李白对身负打通选举之路、“收遗逸”的崔涣献诗,自有深意。
李白浔阳坐狱,“冤而无告”,对此类附逆大案,申诉的步伐稍微放松,结果可知。《唐律》第490条规定:“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就是对“不服”的案件、人犯以为的“冤案”,仍然可以“更为审详”。《唐律疏议》的相关解释是:
“狱结竟”,谓徒以上刑名,长官同断案已判讫,徒、流及死罪,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之罪名,仍取囚服辩。其家人、亲属,唯止告示罪名,不須问其服否。囚若不服,听其自理,依不服之状,更为审详。[8](P568)
本条文的意思是,对已经判结的案件,只需告诉家属所判罪名,不需问其“服否”。对不服判决的,继续由囚犯辩护。如果囚犯不服,“听其自理”,“依不服之状,更为审详”,这对确保冤狱推复清雪、保障疑犯充分的申诉权有很重要的意义。
所以,无论对未判疑犯还是已判囚犯,“陈首”都是其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既可以在审判前和审判中,也可以在审判之后的继续上诉和申诉程序中行使。李白因为系狱浔阳,“冤而无告”,既然“陈首”是其权利,他当然会极限利用。因此,献诗崔涣,与其将其看做文学行为,不如将其看做利用法律维护权益的行为。
(二) 程序性“陈首”一般不能越诉
李白多次给崔涣献诗,也是希望能尽快摆脱牢笼之灾。“陈首”讲求程序。按照唐律,越诉一般不会得到受理。《唐律》第359条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十条杖九十”,即越诉人及受理越诉的人,都要受到惩处。本条下“疏”解释为:
凡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上,令有明文。谓应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其越诉及官司受者,各笞四十。若有司不受,即诉者亦无罪。“若应合为受”,谓非越诉,依令听理者,即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谓不受四条杖六十,十条罪止杖九十。若越过州诉,受词官人判付县勘当者,不坐。请状上诉,不給状,科“违令”,笞五十。[8](P447-448)
从疏议条文可见,对“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上,逐层审理。但本条文有例外,“若应合为受,谓非越诉”,对此类情形,如果有司不受理,则要受到惩处。“应合为受”的具体情形是什么,从“疏议”解释可知,如“依令听理”“请状上诉”,当然也包括上级按照特殊规定调卷审覆。比如,宣慰大使的审案或干预审案。
《唐律》第485条“诸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规定“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是要受到惩处的。《唐律疏议》的解释是:
依狱官令:“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配征赎。其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断徒及官人罪,并后有雪减,并申省,省司覆审无失,速即下知;如有不当者,随事駮正。若大理寺及诸州断流以上,若除、免、官当者,皆连写案状申省,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即封案送。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若不依此令,是“应言上而不言上”;其有事申上,合待报下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谓故不申上、故不待报者,于所断之罪减三等;若失不申上、失不待报者,于职制律“公事失”上各又减三等。即死罪不待报,輒自决者,依下文流二千里。[8](P561-562)
从李白浔阳附逆案件看,李白案件的审理应该是遵循了“断罪应言上”,而且也符合一定程度的“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即遇到皇帝行幸外地,不在京师,各州可以审理结束后再行申奏,不需要提前“奏裁”。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说:“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复清雪,寻经奏闻。”当时唐肃宗还未“还都二京”,乃在灵武。李白《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就有:“伏蒙圣恩,追赴行在”,因为皇帝“行幸”京外,审覆官可以“案覆理尽申奏”,不必等圣裁后再定罪,所以李白才如此说。这是李白浔阳附逆案审覆的特殊之处。
在《上崔相百忧章》中有句“见机苦迟,二公所咍。”这里的“二公”,即指府县的副职。如果按照正常的审理程序,李白附逆案件的审理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很可能面临“冤而无告”、审覆无门的状况。若如此,狱中的李白不知要吃多少苦头。《唐律》第469条云:“诸囚应禁而不禁,应枷、锁、杻而不枷、锁、杻及脱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迴易所著者,各减一等。即囚自脱去及迴易所著者,罪亦如之。若不应禁而禁及不应枷、锁、杻而枷、锁、杻者,杖六十。”李白作为系狱囚犯,且为附逆重罪,是要“锁禁”的。
《唐律疏议》此条下为:
狱官令:“禁囚:死罪枷、杻,妇人及流以下去杻,其杖罪散禁。”又条:“应议、请、减者,犯流以上,若除、免、官当,並锁禁。”即是犯笞者不合禁,杖罪以上始合禁推。其有犯杖罪不禁,应枷、锁、杻而不枷、锁、杻及脱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不禁及不枷、锁若脱去者,笞四十;流罪不禁及不枷、锁若脱去者,笞五十;死罪不禁及不枷、锁、杻若脱去者,杖六十:是名“递加一等”。“迴易所著者,各减一等”,谓应枷而锁,应锁而枷,是名“迴易所著”,徒罪者,笞三十;流罪,笞四十;死罪,笞五十。[8](P545-546)
对坐狱疑犯,流以上都要“禁、枷、锁、杻”且“不得脱去”,李白如何受得了?!李白《在浔阳非所寄内》中,即直接将囚禁之所称为“非所”。无疑,寻找一个特殊的伸冤程序,除了尽快解除非人的“锁禁”,还能加快伸冤审覆过程,离开“非所”,洗脱罪名。
(三) “陈首”有特殊情况
前文叙及,“陈首”是权利,“陈首”一般不能“越诉”,但也有例外。《唐律》第484条强调“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但本条也列出了例外情况,包括“邀车驾及挝登闻鼓”,即所谓的拦驾告状和击鼓鸣冤。但对坐于狱中、带着刑具的李白,显然都不现实。
李白所犯“附逆”之罪,应由各州府先审,经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三司会审,上报朝廷,交由刑部、门下省复核,再奏请“圣裁”,程序繁复。但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二帝分身灵武和剑南,《唐律》规定了“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的权力。而宣慰大使有权力简化审覆程序,“案覆理尽申奏”。这也是李白多次向崔涣献诗伸冤的重要原因。
当然,此类处分只针对个案。《唐律》第486条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强调“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但既然存在“制敕断罪,临时处分”,就为李白伸冤打开了一条方便之门。
针对第486条,《唐律疏议》的解释强调:
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制敕,量情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有輒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谓故引有出入,各得下条故出入之罪;其失引者,亦准下条失出入罪论。[8](P562)
尽管反复强调由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但既有此规定,就有可能对个案“临时处分”。身为宰相的崔涣以“江南宣慰使”的身份宣慰江南、处分事宜,如果崔涣受理李白“冤而无告”的附逆案件,就会形成特殊的效果:一是可以绕开州县断狱,使李白附逆案件被推复清雪;二是崔涣看问题的角度毕竟会异于地方州县,认知高度非地方可比。只要崔涣同情李白,附逆案件就会出现转机;三是崔涣可以先“案覆理尽”再“申奏”,一旦崔涣认为李白浔阳坐狱可清雪,李白就可以脱囚,而脱囚后再“申奏”,被皇帝推翻的概率会大为降低;四是宣慰使是代表皇帝的,通过宣慰使“推复清雪”,会增加当事人的政治筹码,利于后期求官。因此,李白在至德二年代拟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恳请皇帝“拜一京官”才有了可能。
对附逆之罪,最终的处分权在皇帝。李白借崔涣和宋若思两人,只是暂时脱囚,凭智慧与人脉巧离开了监狱,但脱囚非脱罪,李白自己也只是说“脱余之囚”,《自荐表》中,李白也借宋若思之口强调“臣所管李白”。而能“脱囚”,仅是因为皇帝“行幸”在外。要想“脱罪”,关键在皇帝。故李白脱囚之后才会急于借宋若思身份上《自荐表》,希望皇帝“拜一京官”。李白最终也未能如愿,还是免不了被流放的命运。
(四) 李白的献诗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请托
有人认为,献诗崔涣,是李白的阿谀之作。此说有失偏颇。唐律是禁止无关人等为疑犯求情的,除非是职责所在,且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某种关联。《唐律》第135条规定:“诸有所请求者,笞五十;谓从主司求曲法之事。即为人请者,与自请同。主司许者,与同罪。主司不许及请求者,皆不坐。已施行,各杖一百。所枉罪重者,主司以出入人罪论;他人及亲属为请求者,减主司罪三等;自请求者,加本罪一等。”本条规定了各种请求“曲法”的情形和处罚措施。“疏议”则强调:
凡是公事,各依正理。輒有请求,规为曲法者,笞五十。即为人请求,虽非己事,与自请同,亦笞五十。“主司许者”,谓然其所请,亦笞五十,故云“与同罪”。若主司不许及请求之人,皆不坐。“已施行”,谓曲法之事已行,主司及请求之者各杖一百,本罪仍坐。[8](P217-218)
《唐律》还规定:“但是官人,不限阶品高下……为人嘱请曲法者,无问行与不行,许与不许,但嘱即合杖一百。”(135条)[8](P219)而且“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准枉法论。与财者,坐赃论减三等。”(136条)[8](P219)各种对请托说情的处罚规定,尽管不可能消除封建时代枉法的产生,但从法理的角度,李白断不会去冒违法的风险,“授人以柄”,崔涣也绝不会枉法去审理这桩附逆案了。
所以,李白献诗崔涣,是利用了合法途径,采取了合法措施。对李白的献诗,不能简单地看做向崔涣求情,而应看做是合理合法合情的求诉。李白的献诗,是在法理许可范围之内的一种特殊的申诉,是对法律的巧用。
李白、高适、杜甫曾经同游梁园,留下了一段诗坛的千古佳话。李白坐狱浔阳后,曾给高适写过《送张秀才谒张中丞》,其中“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流露请托之意。李白托人婉求高适,却没有看到高适的任何回应,据此,有人认为高适薄情寡义。如果换个角度,则不会如此看。比较李白浔阳狱中所有诗歌的标题,唯此诗有“送张秀才”几字,说明李白此时的尴尬处境和权衡考量。高适此时在广陵,为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作为平定李璘江淮之乱的重要领导者,高适的任职区域对浔阳并无管辖权,且“宰相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3](P3329),只要高适一回应李白,即违反《唐律》,不仅不能营救李白,还会被政敌利用,让自己陷入险境,甚至给李白带来更多麻烦。相对于邀请李白参与李璘幕府的韦子春等被杖杀,李白的流放显然还是得到了有话语权者的暗中相助。这其中,或许就有高适。尽管李白被流放的结局仍令人们愤懑,但对附逆案件的审理中,如果众人禁口,那李白的结局可能会更惨。
三、 李白献诗伸冤的可期结果
从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所述事实和所用术语看,李白对《唐律》是比较熟悉的。李白的狱中献诗,借助法律和理情,达成了初步的预期效果。
(一)利用狱中献诗展示了自己的贤能
法律有救赎机制。《唐律》开篇列有多种救赎的方法。《唐律》第7条中的“八议”,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救赎。与李白同时期一个叫王去荣的,因为会使用石炮,尽管众大臣上书认为其罪无可赦,但却被唐肃宗免死。对于李白来说,更可利用“八议”中的“议贤”“议能”来救自己,而且这两“议”也是展露才华的良机。
李白狱中所献5诗,在赞美崔涣的同时,也很好地利用诗歌伸冤并显示了自己的才华。至德二载李白代拟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中,刚刚脱囚的李白,就把自己的“贤能”作为求取京官的重要手段。他强调自己“三适称美”“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是“希世之英”。向崔焕献诗,借助崔涣的特殊身份做一次个人宣传,这或许是李白此次系狱浔阳的意外收获,如果不是因为崔涣被“罢相”,李白或许会有给崔涣的更多献诗或表文。后来,李白为宋若思代拟的《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祭九江文》和借助宋若思所上的《为宋中丞自荐表》,就是明证。对李白而言,不仅要从附逆案中洗脱出来,而且还要完成华丽的蜕变,让自己的“贤”“能”上达天听,能“拜一京官”,那就实现了人生的理想,或许能安放李白毕生追求的灵魂。
(二)以诗伸冤得到崔涣乃至更多人的帮助
李白此次坐狱浔阳,乃谋逆重罪。《唐律》对此类重罪,不仅要求“三请”,也赋予在押人犯很多权利。《唐律》第353条规定:“诸犯罪欲自陈首者,皆经所在官司申牒,军府之官不得辄受。其谋叛以上及盜者,听受,即送随近官司。若受经一日不送及越览余事者,各减本罪三等。其谋叛以上,有須掩捕者,仍依前条承告之法。”《唐律疏议》的解释为:
犯罪未发,皆许自新。其有犯罪欲自陈首者,皆经所在官司申牒。但非军府,此外曹局,并是“所在官司”。“军府之官”,谓诸卫以下、折冲府以上,并是领兵曹司,不许輒受首事。其谋、叛以上事是“重害”,及盜賊、之辈,并即须追掩,故听于军府陈首。军府受得,即送随近官司。其受首谋反、逆、叛者,若有支党,必须追掩,不得过半日。及首盜者,受经一日,不送随近州县及越览余事者,减本罪三等。假有告人脱户,合徒三年,军府受而为推者,合徒一年半之类。其谋反、逆、叛,为有支党,事须掩捕,“仍依前条承告之法”,谓若满半日不掩,还同知而不告之罪:谓谋反、大逆,不告合死;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8](P441-442)
本条文规定了羁押疑犯欲“自陈”,何人可以收其陈状。如果李白得到崔涣复审附逆案件的机会,陈状就到达崔涣手里,案件也就有了“推复清雪”的机会。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说,“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这里的“陈首”,乃陈述案情、供认案件经过。《唐律》第353条有“诸犯罪欲自陈首者”,从法律的角度看,“陈”包括自陈和他陈,自陈是疑犯的重要权利,《唐律》对此设有专条保护。“首”当为“自首”,有别于告发。李白因附逆李璘而被人告发,李白认为,“附逆”不实,自己是被“胁行”。“陈首”既是唐律赋予的权利,也是李白争取的权利。李白的献诗,就是一种特殊的“自陈”。
作为江南宣慰使的崔涣,对李白的浔阳案件进行了再审,李白终于等来了宋若思帮助其“脱囚”的机会。但唐肃宗的“奏裁”,使得57岁的李白重染风霜。因此次的牢狱之灾,身心俱疲的李白,从此便归隐当涂,几年以后,多病的李白就离开了人世。
(三)献诗之举加速了浔阳附逆案件的处理和李白“脱罪”的进程
史料的缺失,我们已经无法还原李白附逆案件清雪审覆的全过程,但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中“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复清雪,寻经奏闻”的自我表白,证明了此次案件审理的大致过程和结果。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复杂的。崔涣的罢职,差点让李白的努力前功尽弃。但宋若思的跟进,无疑再次给了李白脱囚的机会。
郁贤皓先生认为,李白能从“附逆”中解脱,与李白积累的重要人脉有一定关系[9](P65-67)。宋若思是宋之悌的儿子、宋之问的侄子。早年,李白与宋之悌就有交往,李白写过《江夏别宋之悌》,畅叙两人友情。但李白的脱罪,更主要的还是依赖于宣慰大使崔涣。
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学术界可能没有注意到,李白在《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中,以一个很长的标题作为诗名。一是可见李白对“脱余之囚”的兴奋,二是体现了李白对宋中丞的感谢。那么,宋若思为什么能直接“脱余之囚”并将李白辟为参谋呢?实际上,崔涣的主要推复清雪工作已经完成,合理的猜测是,崔涣已经将李白的案件“奏闻”或者“审覆”,宋若思只是继续了崔涣的工作,顺势完成“脱余之囚”,并给了李白职责范围的回报。李白的附逆案件,如果没有“奏闻”肯定是不行的。当然,“奏闻”不是“奏请”。
李白利用法律、人脉和他的才气,终于使自己逃脱了一次可怕的牢狱之灾。
回头审视李白的《在浔阳非所寄内》《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万愤词投魏郎中》和《狱中上崔相涣》《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上崔相百忧章》,李白浔阳坐狱的初步审覆,是将法理与才情、友情、人情、亲情的一次相对完美的组合,尽管审覆推雪过程充斥着悲伤,但也蕴含着人伦与智慧。可以说,在充满法理情的话语场域中,李白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要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