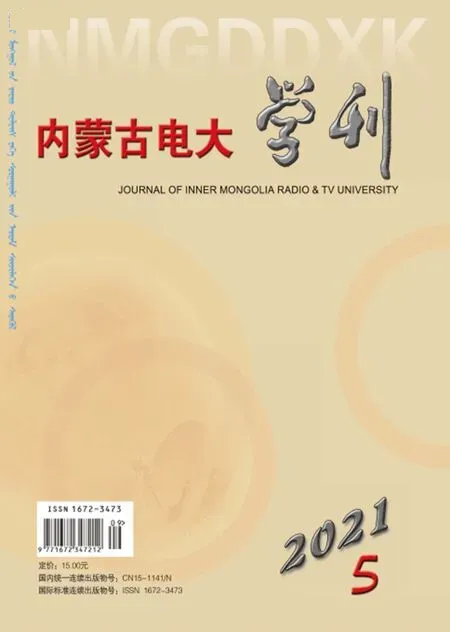论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中的非正义性
马金辰,张 楠
(1.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010060;2.内蒙古开放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1)
作为西方第一个系统地论述正义的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正义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作用。“正义”是柏拉图建立理想政体的支柱,也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石。为了在政治上寻求一个正义的国家秩序,柏拉图在理论上建立了“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在牺牲个人权益的基础上强调国家整体至上的集体主义。为了实现“理想国”,柏拉图提出了让德性至上的哲学家担任王的理论。哲学王统治思想是遵循柏拉图心目中善和正义的理念建立的,然而对国家整体利益以及集体主义的过度重视,以及对个人独立的忽略不计,使柏拉图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走向了一种在政治上表现为另一种不正义的极端,即其哲学王思想统治思想的非争议性。
一、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的非正义性
“正义观念产生于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一般秩序与规范人们行为的普遍法则的确定与认同。”[1]P15关于什么是正义,在《理想国》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上半部分,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名批判了“给朋友善、给敌人恶”“强者的利益”“民主、自由”等三种正义观,并在这种驳斥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正义理念的基本观点。柏拉图的正义观可以分为大写的“正义”和小写的“正义”两类,大写的“正义”是城邦的正义,小写的“正义”是个人的正义。城邦与个人之间,大“正义”与小“正义”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小“正义”构成了大“正义”,大“正义”维护了小“正义”,众多正义的个人构成了正义的城邦,正义的城邦又维护了个人的正义。可以说城邦的大“正义”与个人的小“正义”二者互为前提,缺一不可。出于对当时雅典内忧外患的思考,柏拉图提出了上述正义的观点用来改变这一局面。柏拉图认为,正义是雅典各城邦迫切需要的品质。从对正义的推崇出发,一个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被柏拉图构建出来。在这个理想城邦中,“服从理性领导不是内屈从于外,而是外欲望服从内(理性),正义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在的德性;在国家层面,就是所有人服从智慧者的领导。”[2]P125一言以蔽之,正义就是个人从理性出发对欲望的自我约束,进而让国家的所有人都服从哲学王的统治。
以智慧的哲学王为统治核心的理想国是柏拉图心目中的天堂,在现实中不具有实现的可能。随着对现实政治关注的不断加强,柏拉图开始不断探索在现实中实现理想国的可能。基于对现实的关注与考虑,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提出了实现理想国的途径——依法统治的君主政体。在《法律篇》中,法律的德性与权威取代了哲学王的德性与权威。从表面上看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从《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的统治变成了《法律篇》中“法律”的统治,看似是“弃德化而逐法治”,而实质上,建立在德性之上的极权主义才是永恒的,但是无论是哲学王还是法律,柏拉图始终追求的是一个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整体主义至上的国家,法律不过是代替了哲学王的地位成为实现国家极权主义的必要手段,其哲学家治国的核心内涵没有改变。[1]P329-330可以说,“柏拉图的法治国家是他理想的王政国家要在现实中实现的一个手段。”[1]P33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所处的时代在政治上缺乏秩序同时个人主义又大行其道,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关怀,他建立的国家秩序虽以正义为名,但其实质是建立在“哲学王”德性完善基础上的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的国家秩序是以其理想国家在德性上的自足与整体主义为基础的。在这种极权主义的国家秩序下,个人是没有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的,其实质是在法律外衣下的哲学王的极权专制。从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柏拉图忽视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过分强调国家至上。这样的正义在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雅典或许是必要的,但其牺牲了个体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有违现代正义的价值追求。
二、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中哲学王产生的非正义性
建立在正义、智慧、勇敢、节制基础上的理想国,需要赋予知识完善、德性自足的哲学家绝对的权威来实现。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国家的统治者哲学王必然是一个正义的人。但根据柏拉图“正义就是一个人只能从事一份符合其天性的工作”[2]P125的观点,哲学家不应该做国家的统治者,其“正义”应该是发挥其所长,致力于哲学的理论思辨。哲学王一人身兼哲学家和统治者两个职位,“这也好像意味着正义的城邦在不正义的对待哲学家。”[3]P128-129是否预示着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思想是允许通过不正义的手段来实现所谓正义的目的?如果为实现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那么柏拉图的正义观以及哲学王统治思想在理论上就是不充分的。
柏拉图用著名的“洞穴比喻”论述了这一悖论。从哲学角度可以将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理解成关于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无知走向有知,从被遗弃状态走向被拯救状态的故事。从政治学角度,黑暗洞穴状态就是一个普通的城邦,而城邦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是一种被感官所控制的生活状态,大家都是被感官所束缚的“囚徒”,少数哲人突破了感官的束缚领悟到真正的哲学和真理。已经参悟到正义的“哲学家”就其本意来说是不愿意再回到洞穴的,但是为了城邦整体的幸福,他们不得不违背本性回到洞穴中宣扬真理。而再次回归的哲人却因宣扬“真理”被同伴们杀害。在这个比喻中,哲学家重返洞穴始终是违背其本性的。柏拉图也曾认为“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1]P277可以说,“不热心权力”是哲学家成为哲学王的必要条件。而让不热心权力的哲学家成为哲学王的唯一途径就是强制。“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建立者的职责,就是要迫使最好的灵魂达到我们前面说的最高的知识,看见善,并上升到那个高度;而当他们已到达这个高度并且看够了时,我们不让他们像现在容许他们做的那样,逗留在上面不愿再下到囚徒中去,和他们同劳苦共荣誉,不论大小”。[1]P277
柏拉图提到应当强制哲人参与城邦生活,但却没有回答这些掌握正义的哲人成为哲学王后是使城邦生活变得更加完美,还是会破坏了原有的城邦生活?而城邦里的“囚徒”又该如何看待哲人,是把他们奉为哲学王还是异类?建立一个理想国,哲学王是必然需要公众的支持,否则就会重蹈“洞穴比喻”的悲剧结局。而如何让公众接受哲学王的统治和教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1]P277但是,柏拉图的说教更多是编一个神话欺骗其他人来维持哲学王的统治。从哲学王长生的途径以及理想国建立的基础来看,都是需要通过强制和欺骗等非正义手段实现柏拉图所谓的建设正义城邦的目的。
三、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统治下生活模式的非正义性
按照柏拉图的构想,理想国追求的是整体的幸福和正义,为了实现这个正义目标,全体公民要形成一个彼此协调、和谐团结的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在这个城邦公民集体中,全体公民要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与大家分享。在这种国家至上的理念下,哲学王统治下的生活模式有以下三点是非正义性的:
一是哲学王专制统治的非正义性。柏拉图没有对哲学王统治下理想国的政体结构做进一步的详细介绍。但从《理想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统治,实质上就是专制独裁统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讨论了五种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荣誉政体和僭主暴君制。柏拉图认为具备一定条件的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哲学王就是这样一种在理想的状态下设立的君主政体。在这一体制下,柏拉图赋予哲学王的权力是许多专制君主才有的。例如,有且只有一位哲学王,为了维护其神秘性,其应该在王宫深居简出,对普通人避而不见,并由专门的人作为其与外界沟通的代表,负责宣布政令和上报民情。除此之外,哲学王可以不受道德约束,可以欺骗、撒谎。无论个人的小“正义”还是国家的大“正义”,正直与诚实本应该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人类这一群体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道德基础。但为了实现国家的大“正义”,柏拉图认为哲学王可以欺骗人民。与此同时,哲学王也可以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哲学王可以定期清理,如放逐或处死道德低下的下层人以维护城邦的正义。而城邦之间甚至可以通过战争进行掠夺,“如果我们想要足够大的耕地和牧场,我们势必要从邻居那儿抢一块来……下一步,我们就要走向战争”。[1]P362这样,从对城邦的管理模式来看,哲学王和僭主一样都是实行的专制独裁统治,他们同样需要借助军队等暴力组织的力量来完成统治,区别就在于:从外在表现来看,哲学家王是正义的,僭主是不正义的;从出发点来看,哲学家王是看到了善的理念,拥有真理的;从个人角度看,哲学家王的欲望导向了一个没有“竞争性”的对象——知识,而僭主的欲望则导向了那些更为“低级”的、有竞争性的事物:爱欲,金钱,权利。就如同哲学王产生的非正义悖论一样,哲学王管理下的理想国也在论证着柏拉图“只要目的是正义就允许过程和手段的非正义性”的正义悖论。
二是个体私生活消失的非正义性。由于柏拉图赋予了哲学王的权力过分极权,导致哲学王的独裁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侵入了公民的私生活,即大“正义”削弱了小“正义”。柏拉图认为私有观念是城邦混乱的原因,实现城邦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就要保证培育公民优良的道德品质。因此,在理想国的统治集团中禁止护卫者阶层私有。按照他的要求,公民需要同吃同住,每年按需定量领取粮食等必需品,禁止任何人拥有私产。与财产“公有”制相配套,柏拉图甚至主张在统治集团中取消家庭,将妇女与子女“共有”。通过消灭小家庭,使全城邦形成一种亲缘纽带关系,由此达到全体公民的共情共感,杜绝“化一为多”的恶,实现“化多为一”的善和城邦的团结一致。柏拉图取消家庭的论述,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等同于社会的伦理道德生活,并从道德的框架出发,把社会伦理道德原则等同为政治原则予以论证。诚然,他论述的提出受限于时代的发展,但仍然违背了古今中外甚至是同时代的家庭伦常,通过用群婚取代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方式毫无疑问是用社会倒退的办法去实现所谓的正义。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虽然允许劳动阶层可以在统治者的严格监督下建立家庭和拥有私产,但是并不意味着消除了等级观念,相反集中反映了柏拉图的等级观念。柏拉图抛开血缘和经济地位按照道德水准把民众分为三个等级:生活在下层的劳动者是最低等级,因为他们受欲望的支配,所以道德水平最差;卫士是中间等级,勇敢的美德是这一阶层与生俱来的;管理者是最高等级,其天生具有智慧的美德。柏拉图认为每个人天生都应该具有每一项美德,但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美德的多少是不同的,越是往下层,人的美德越少。因此,柏拉图从这一道德的认知角度出发,认为下层人天生应该接受高等级人的统治。同时要用严刑峻法管理道德低下者,定期清理,或放逐,或处死。而允许劳动阶层拥有私产,其目的也是为了根除斗争和贫富对抗的经济根源。
三是个体自由消失的非正义性。柏拉图认为,正义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来保证优良的城邦生活,他一直坚持并且强调国家重于个体,公民必须绝对地献身于国家,通过消融个人的利益来建立维护城邦统一的秩序。例如,应该处理掉天生不健全的孩子,“至于一般或其他人生下来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们将秘密地加以处理,有关情况谁都不清楚”[1]P194;依据国家利益有选择性地治疗疾病,“对于体质不如一般标准的病人,不值得去医治他,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好处”[1]P117;“不同阶层婚姻选择的不均等,结婚的机会对于优秀人物应该多多益善”[1]P207,柏拉图希望通过压抑个体的欲望来实现理想国的统一完整。
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思想对个体自由最极端的非正义统治体现在对个体意识和思想的束缚。柏拉图所认为的城邦政治的正义要求个体有怎样的本性,过怎样的生活,处于怎样的等级中,个体就要遵照要求执行。从巩固阶级统治的角度尚可理解柏拉图所提出的个体正义要求,但是取消家庭既是人伦的倒退也是哲学的倒退。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倡导解放个人思想、倡导独立思考,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柏拉图认为摧毁个体自我意识存在的基础是取消家庭的存在,但他忽略了个体自我意识的消亡会使得苏格拉底和他所倡导的正确自我意识变得不复存在。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教育是实现正义的唯二途径之一,但是任何先进的教育、伟大的智慧都无法消除“共妻共子”的家庭制给个人自我意识带来的消极影响。诚然,在后期柏拉图用法律取代了哲学王统治,没有从理论上阐述人们必须服从于国家,只要在法律准许下公民就享有自由。然而,柏拉图所谓的法律是道德化、哲学化的法律,无处不在、无微不至。哲学王法治之下的公民与理想国中的公民一样没有个体的自由。在柏拉图哲学王统治的蓝图中,为了实现大“正义”,就要使个体安守本分,因此严格控制人的思想便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具体来说,柏拉图主张:严格控制教育内容;为了拒绝其他思想,主张闭关锁国,排斥商业,反对进出口;主张立法者诉诸宗教。可以看出,隐藏在柏拉图法治背后是对哲学王统治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仍是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国家至上主义与极权主义,生活于此的公民仍无法享有自由,绝对地服从于统治。
综上所述,柏拉图为了实现国家中每一阶层人尽其才、各司其职、不相僭越的“正义”,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统治思想。在这种思想中,哲学家作为“善”的代表和化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智慧而享有集权,对所属的公民实行绝对的统治。柏拉图在理论上构建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超出现实,以正义为核心,但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历史、阶级的局限性,这种国家制度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建立在这种空想之上的政治正义也同样缺乏现实的根基。从哲学王产生“洞穴比喻”以及哲学王统治下的城邦生活模式都可以看出,柏拉图所建立的国家正义是以消融个人的独立存在为前提的。哲学王身兼数职的论述违背了“各司其职”的正义要求,而对个体权利、自由甚至人性的忽略不计也违背了现代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实践中,作为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的正义观和哲学王统治思想更多价值应是引导后世更多学者关注正义在道德和政治制度领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