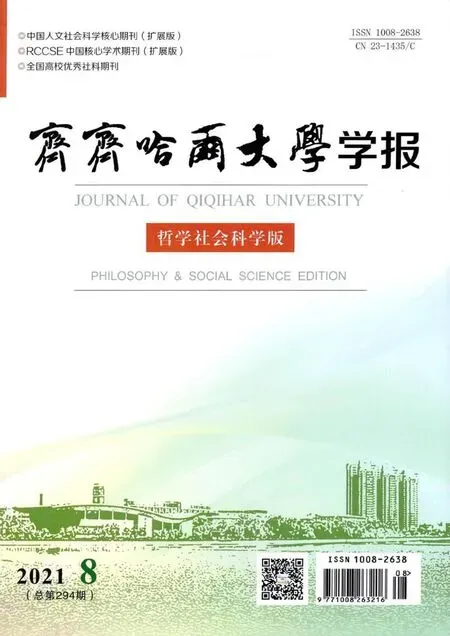论《诗经》四言体的语言文化意蕴
郝桂敏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诗经》四言体诗歌形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与周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革对文学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诗歌语言形式在周代的进一步演进、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传承等都有密切联系。
一、周代的社会变革为《诗经》四言体形成提供了语言学及诗体学基础
(一)周代的社会变革促使大量新词汇的产生
政治经济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周代社会的重大变革,一定会引起语言的变化,两周语言的变化由周初便拉开了序幕。
词汇是语言变化的先锋,所以语言变化首先会表现在词汇的变化上。商末周初之际,社会由青铜器进入铁器时代,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政治上,周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实行封建宗法制度。周代社会的巨大变化,正如朱广祁先生所云:“在这一时期,农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中心,而狩猎已不占重要地位,逐渐成为贵族们消遣行乐的一种形式了。从《诗经》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各种农具,有了播种、耕耘、除草、防治虫害、收获等一系列成熟的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繁多,耕作质量提高,产量有了一定的保证,农田的开垦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着。此外,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财富比起殷商时代来,已经大大丰富起来。经济的发展繁荣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远比殷商时代内容丰富,水平提高,达到了成熟的地步。这些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使社会交际比过去繁复得多,对语言发展特别是词汇的丰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语言必须有适合这些要求的演变”。[1]
周代的社会大变革需要出现新的词汇来表情达意。周代社会的巨大变化,让人们开阔了眼界,也引起了人们思维的发展和变化,使得人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不断提高,单音节词的物质结构(交际手段)不再能有效地承担新的交际任务了。社会生活发生变化,语言一定要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是一条基本的语言发展规则。“汉语发展的历史表明:词汇,这一对于社会发展最敏感、几乎处于不断变动中的语言组织的基本单位,往往成为语言发展中的关键因素。”[2]59两周时代是汉语词汇由单音词为主向复音词为主过渡的重要时期,此时出现了大量的复音词。周代复音词主要是在商代大量单音词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时产生新的词汇有三个途径:一个是在单音词上加新的音节,而靠单字增加音素变成新词很艰难。二是增加大量的同音词,而大量增加同音词不便于交际。三就是在单音词(即单个字)的基础上增字变成新词,最后一种办法在当时最易行。正如程湘清所说:“于是,单音节的形式开始被突破了,从而转向利用语法特点——词序和虚词——把单音节有规律地搭配起来而构成双音词和双音词组(也包括一小部分三音节词和四字成语)。”[2]58-59具体办法是利用重言、联绵字,以及单音词前后加虚字或衬字的办法,造出双音词。同时还造出一些三音词,三音词可以和其他单字组成两个双音词,从而组成四言句式。据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刘馨阳2018年的硕士论文《<诗经>复音词研究》,复音词在《诗经》中共有1182个。[3]复音词的大量出现为《诗经》四言诗体的兴成提供了语言学基础。
周代出现最多的词汇是双音节词,如黎民、人民、农夫、大王、先祖、同僚、孝子、孙子、妇人、君子、圣人、先民、庶民等等。也出现了很多双音节动词,如洒扫、颠沛、保佑、改造、从事、戏谈、沸腾等等。它们反映事物更加丰富,表情达意更加准确,适应了两周时期的社会重大变革的需要。周代也出现了很多形容词,大部分是叠字、双声、叠韵词汇,如关关、夭夭、萋萋、参差、蒹葭。这些词汇由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所以很多词汇一直流传至今,成为现在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诗经》内容的庄典性适合用四言形式来表达
周代复音词的大量出现,为诗歌发展提供了两个路径:一是双音词加上商代传下来的大量单音词,组成以三言为主体的诗歌,二是双音词加上双音词(或者双音词加上单音词加衬字等)、或者三音词加上单音词组成以四言为主体的诗歌。
但是,《诗经》诗体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以四言为主体,为什么《诗经》以四言为主体而不是以三言为主体呢?这和《诗经》内容的庄典性对四言形式的选择有一定关系。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产物,周礼的庄典性决定了《诗经》内容的庄典性。《诗经》祭祀神明的诗歌以《周颂》为代表,歌颂祖先的诗歌以《大雅》为代表,《大雅》和《周颂》主要用于国家大事,因此《诗经》属于庄典体。不同的诗歌内容需要不同的诗歌形式来表达,庄典体的《诗经》必然不会选择以三言为主体的诗歌形式来表达。因为以三言为主体的诗歌,往往“具有生动、惊挺、简劲、顿宕的表达效果。但正是它们这种‘动宕’的属性不适于表达正式、庄重或严肃的内容。这一点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却是三言语体风格的典型特征。”[2]198同时,三言体诗歌还具有很强的诙谐性和口语性,《诗经》的内容显然不适合用三言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而四言的诗歌节律模式是一种平衡、标准和富于庄典性的结构,适合表达严肃的内容,它是四音节韵律,而“四音节韵律在汉语文学中是最普遍、最有影响力的诗歌形式。”[2]199《诗经》尤其是《大雅》《周颂》的典雅严肃的内容,适合用四言的诗歌形式来表达,这也是《诗经》选用四言为主的诗体来表情达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复音节词汇的大量出现促进《诗经》四言新诗体的产生
汉语语言大发展与诗歌发展之间相应关系告诉我们:以双音节词语为主的复音词的大量出现,必然要相应地产生新诗体。《诗经》以四言为主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新诗体,《诗经》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韵素为基本结构单位的诗歌模式,导致了韵律系统的新变化。
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诗出现以前,诗歌以二言形式为主。从二言到四言(而非三言)的转变,固然可视作社会变革、民族文化心理等诸多外界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然而,以从古代韵律结构演变的视角观之,汉民族诗歌发展进程中由以二言为主的诗歌形式直接发展为四言的诗歌形式却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概言之,韵律结构的演变,导致了整个语言体系(自然也包括文学)的改变,反映到文学上来,表面上观之便是“二言体”向“四言体”的诗体演化,实质上是古代汉语从“韵素音步”到“音节音步”的转化。[4]137-138
上古的二言诗体结构的重复,是以韵素为基本结构单位的。上古诗歌韵律节奏模式是“2+2”,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弹词》)“断竹”现在看是两个音节,而在上古时期确是四个韵素,每个词有两个韵素。双音节为主复音词语的大量出现,奠定了汉语一个汉字一个读音的语音体系,语音体系的变化,导致了汉语诗歌韵律系统的改变,这必然随之产生新的诗歌体式。
复音词的出现之所以导致《诗经》四言诗体的出现,其原因不仅仅是词语字数增加的结果,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韵律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冯胜利认为:“‘双音词的发展’是表面的现象,而韵律结构的演变才事关语言的系统,才能导致整个语言体系(包括文学)的改变。就是说,从‘二言体’到‘四言体’的诗体演化,不过是远古汉语从‘韵素音步’到‘音节音步’的转化在文学诗体上的一种反映而已。”[4]137-138以往韵素系统为主的诗歌,一个单字常常包含两个韵素,二言诗歌就包含了四个韵素。两个韵素是一个音步,二言诗歌每句诗就包含了两个音步。在双音词为主的诗歌里面,不能出现二言诗歌的原因,是由于一个音节不能单独成为一个节奏单位(即一个音步,音步至少有两个音素),双音节有两个音素,才能构成最小的节奏单位,因此以双音节词语为主的诗歌,必然要以四言为最佳形式。因为双音节词语构成诗歌的最佳原则也是最小原则,那就是“2+2”模式,即两个双音的四言模式。这里的“2+2”,和之前的以单音节韵素为主的二言诗歌的“2+2”诗歌韵律不同:二言诗歌的“2”是两个韵素,即二言一句的诗歌形式,而四言诗句的“2”是两个音节,四言诗歌的“2+2”就是四言一句的诗歌形式了。
总之,周代复音节词语的大量出现,使得诗歌一改先前以韵素为主的韵律系统,出现了以音节为主的韵律系统,韵律系统的这一改变促进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诗歌形式的出现,这是诗歌在当时条件下在节律形式方面的最佳选择,正如冯胜利所说:“上古韵律系统的改变不仅导致了汉语的变化,同时也导致了它的文学形式的转型。……没有韵律的作用绝对不会有它所以如此的发展,尽管它的发展不都是由韵律决定的。”[4]142-143
二、《周易》卦爻辞所引古诗为《诗经》四言体诗的兴起开了先河
在诗歌由二言向四言转换的漫长过程中,连绵词、双音节的短语大量涌现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类词语和短语被吸收到《诗经》的创作中来,成为四言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诗经》四言诗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和固定的创作范式,而《诗经》之前,《易经》中所引用的古诗,不但具有大量的二言体诗歌,同样具有二言、三言、四言相互混用的诗歌,这类作品当视为二言诗歌向四言诗歌过渡阶段的创作,为《诗经》四言体的兴起开了先河。
《易经》卦爻辞大量引用古代诗歌,这些古诗当是文王时期存在的,计68首。纯二言诗5首,纯四言诗3首,纯三言诗未见。以四言为主(四言诗句占诗歌半数及以上)的诗歌有《乾》等22首,占诗歌的32%;以二言为主体的诗歌15首,占诗歌总数的22%。以三言为主体的诗歌14首,占诗歌总数的21%,其他混合形式的诗歌17首,占诗歌总数的25%。《易经》卦爻辞所引古代诗歌,在语言形式上以二言、三言、四言为主的诗歌居多,这类诗歌共占《易经》所引古诗的75%。未见纯粹的五言诗歌和六言诗歌(五言诗句和六言诗句与二言、三言、四言混合运用的诗歌里,五言和六言的诗句也只是以一、两句的形式出现)。可见,《易经》卦爻辞所引古代诗歌,在诗体上以二言、三言、四言为主流。
(一)《易经》卦爻辞所引古诗表现出由二言向四言过渡的迹象
1.以二言为主体的诗歌15首(诗中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二言诗句)
(1)纯粹的二言诗
纯粹的二言诗歌5首,多篇幅短小,语言古奥,当为中国上古诗歌的遗留。这类诗歌有《蒙》所引古歌《女萝之歌》(4句),《谦》所引《鹣鸟之歌》(4句),《豫》所引《大象之歌》(4句),《临》所引《统治之歌》(8句)。
《谦》所引古歌《谦鸟之歌》:[5]83“谦谦,鸣谦。劳谦,撝谦。”这是一首比翼鸟飞翔之歌。 “谦谦”读为兼兼,指鹣鸟,“鸣谦”,是鹣鸟的鸣叫声,“劳谦”,指鹣鸟相互慰勉,“撝谦”指鹣鸟举翅相互招引。这首二言诗歌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全诗句末押韵。诗歌用比喻手法,托物言志,通过写比翼鸟的和鸣、劝慰和招引,寄托了诗人对幸福爱情的向往。全诗一章四句,篇幅短小,言简意赅,意蕴深刻,有上古诗歌的韵味。
《豫》所引古歌《大象之歌》:[5]86“鸣豫,盱豫。由豫,冥豫。”“豫”是大象的意思,这是一首大象之歌。大象在上古是人们的交通工具,诗歌描写了大象的几种形态:“鸣”“盱”“由”“冥”,分别是鸣叫、举目张望、悠闲和闭目安神的意思。全诗一章四句八个字,每句尾字相同,四句话只是第一个有所改换,却把大象的可爱神态描写得活灵活现,诗人对大象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大象曾是上古时期的交通工具,而《诗经》中未见大象这种交通工具,可以推见《大象之歌》的产生时间可能很早,该诗展现了上古时期二言诗歌的基本面貌。
(2)非纯二言、以二言为主体的诗歌10首
这类诗歌篇幅往往较长,多与三言、四言混合运用成诗,体现了二言诗歌向三言、四言发展演变的迹象。如《坤》所引古歌《大地之歌》[4]16:“履霜,坚冰。直方,含章。括囊,黄裳。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诗人于降霜的秋季启程,从南方踩着秋霜来到北方,此时北方的大地已经覆盖上了坚冰。“直方”,广阔方正,大地上的冰雪带给世界一片光明,分外妖娆。“括囊”是给口袋打结,“下裳”是黄色的下衣,黄色的下裳并非普通百姓的服饰,说明诗人当是贵族阶层。诗人挎着扎紧的行囊,身穿黄色的下裳,看见眼前龙蛇在郊野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流血满地。该诗当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诗歌,龙蛇的争斗可能是写实,也可能是对当时社会斗争的影射。全诗二言诗句六句,四言诗两句,是二言、四言混合运用、以二言为主体的诗歌,展示着二言诗向四言诗过渡的痕迹。
又如《否》所引的《献茅之歌》:[5]70“包承,包羞。休否,倾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是一首收获茅草的歌。体裁似风,手法似赋。《说文》:“承,奉也。”“包承”是说把茅草包起来献给主人。《说文》:“羞,进献也。”与“包承”同义。“休”是休息,“倾”是躺下休息,“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说怕丢了茅草,把它系在桑树根下。诗歌二言诗句四句,四言诗句两句。从诗歌内容看,也当是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诗歌用虚词“其”“余”,说明其创作年代与《诗经》相距不会太远。《坤》和《否》从诗体上看都体现出了由二言向四言过渡的迹象。
再如《复》所引的《归途之歌》:[5]120“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不远复,休复,频复。 中行独复,敦复,迷复。”这是一首归途之歌,主人公可能是商人,但由于思乡心切,出门不远就回来了。“复”是返回的意思,《尔雅·释言》:“复,返也。”“来”与“复”同义,《诗经·小雅·采薇》:郑玄《笺》云:“来犹返也。”“七日来复”是说诗人回家的路途不远,“不远复”,是说诗人离家不久就又回家了。“休”是喜悦的意思,“敦”是急促的意思,“频”愁眉不展的样子。“独复”,独自回家,“迷复”,迷失了道路。诗歌中主人公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是恋家的人,提到回家他很高兴,也很急促,但又由于一个人回家,迷失了方向,所以又颇有忧愁之色。全诗三章,第一章全为四言句式。全诗四言诗句三句,两言诗句四句,三言诗句一句,诗歌体现了以二言为主、且与三言、四言混用的现象。
总之,《易经》所引古诗纯粹的二言诗歌篇幅短小,表现了上古时期诗歌的基本面貌,而以二言为主体的诗歌,多为二言与三言、四言混合诗句,尤以二言、四言混合诗句居多,体现了二言向四言过渡的迹象。
2.以四言为主体的诗歌22首(诗歌中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四言诗句)
这类诗歌包括纯粹的四言诗和其他以四言为主体的诗歌。
(1)纯粹的四言诗3首
纯粹四言诗有《乾》所引的《群龙之歌》(3句),《蹇》所引《艰难之歌》(6句),《归妹》所引《嫁妹之歌》(8句)。这些诗歌虽然出现了整齐的四言形式,但是比起《诗经》的四言诗体,其四言形式显然是简短的。
如《乾》所引古歌《群龙之歌》:[5]09“见龙在田, 或跃在渊,飞龙在天。”这是一首群龙出没的诗歌,“见”读为本音,借作“乾”。“乾”本身有出现的意思,就像春天的草木那样冤曲而出。“乾”也有“健”的意思。龙是传说中上古时代常见的动物。诗歌大意是说有的龙在田间出现,有的龙在水潭中跳跃,有的龙在天空飞翔。在中国上古时期有畜龙的传统,犹如今天养猪。诗歌对龙的赞美,表达了诗人对龙的喜爱之情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全诗由三句四言诗句组成,每句句末押韵,铿锵有力。从诗歌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看,该诗离《诗经》都应该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再看《归妹》所引古诗《嫁妹之歌》:“归妹以娣,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5]256传说该诗是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嫁女于文王的诗歌。娣和须都是妾的意思,诗歌是说帝乙嫁女于文王,妹妹随同姐姐陪嫁。虽然延期出嫁,但婚期已经确定了。至于为什么延迟婚期,诗中说姐姐的衣服不如妹妹的好看,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诗歌展现了商代的婚俗图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诗歌一章八句,全诗以整齐的四言形式出现,展现了四言体诗歌的最初形态。
(2)非纯四言、以四言为主体的诗歌
这类诗歌共19首,如《同人》所引古诗《抗战之歌》:[5]75“同人与野,同人与门,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乘其墉,弗克攻。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同人与郊。”这是一首战争题材的诗歌。“同”是汇聚的意思,先写“同人与野”,是聚集族人于郊外,之后再由小宗聚集到城门,最后由大宗聚集到宗庙。他们埋伏到草莽中,山岭中,三年没有松懈。部队没有因为“弗克攻”的暂时失利而懈怠,而是等到了“大师克相遇”,最终坚持到了战争的胜利。诗歌除了三句三言、两句五言诗句之外,其余七句都是四言诗句,是以四言为主体的篇幅较长的诗歌。全诗三章,每章三句,有《诗经》重章的雏形,但和《诗经》的重章又不同,各个章节之间没有重复的诗句。全诗用赋的手法平铺直叙,读来缺乏《诗经》用叠句而产生的一唱三叹的音乐之美。
总之,纯粹的四言诗大约在商代就出现了,数量不多,篇幅短小,多为一章;以四言为主体的诗歌数量较多,篇幅较长,多分三章,类似《诗经》的重章格局,只是缺少《诗经》各章之间诗句的重叠,可视为《诗经》四言诗体的先河。
3.以三言为主体的诗歌14首(三言诗句占诗歌一半或一半以上的诗歌)
纯粹的三言诗在《易经》卦爻辞中未见。以三言为主体的诗歌14首,如《讼》所引《诉讼之歌》:[5]39“不克讼,归耳逋。其邑人,三百户。不克讼,复即命。 鞶带或锡之,终朝三褫之。”这是首诉讼诗,其主题是要求人要为官清正廉洁,表现出宣扬礼制的正统观念,当是周代初年的诗歌。诗歌的主人公是个贵族,其封地有三百户,主人公没有胜诉,便转回封地逃亡,“逋”是逃亡之义。逃亡不久又听从王命自首。“鞶带或锡之”指过去所拥有的封号。“锡”,同“赐”,“鞶带”是代表等级的皮革绶带,“褫”音尺,剥夺的意思,诗歌中说主人公的封号被剥夺了。诗歌除了两句五言诗句外,其余六句都是三言诗句。诗歌分为两章,每章四句,有似《诗经》中多数诗歌的每章四句的结构。每章开头诗句重复,从诗歌形式上有周初诗歌的格局,说明周初虽然有以三言为主体的诗歌,但纯粹的三言诗并未见传世,也说明我国古代二言诗歌之后,诗歌并未向三言的形式发展,三言在周代之前也不是诗歌的主流形式。
4.其他混合形式的诗歌17首
这类诗歌中最多的是二言、三言、四言混用的形式。三言与四言混用的,如《大有》所引《丰收之歌》[5]79:“无交害,大车以载。匪其彭,自天祐之。”这是一首丰收之歌,表现了主人公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交”是全部的意思,“害”是收割的意思。诗歌说不用等收割完毕,庄稼就用大车运走了,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彭”通“尪”,男巫的意思,诗歌说农业丰收不是因为巫师的缘故,是有上天的保护,由此可见该诗可能是商代诗歌。诗歌三言、四言句式各占一半,篇幅短小,类似《诗经·周颂·丰年》。
以上从《易经》卦爻辞所引古诗的情况看,上古诗歌以二言体为主,二言之后诗歌形式向三言为主体和四言为主体的形式发展,诗歌二言、三言、四言混用形式的诗歌增多。以三言为主体的诗歌,并未形成诗歌的主流形式,而以四言为主体的诗歌却渐成主流。尤其到了商代和周初,出现了纯粹的四言诗和大量的以四言为主体的诗歌,诗歌形式逐渐向四言体过渡。
(二)《易经》卦爻辞所引古诗以四言句式居多
从句式上看:《易经》卦爻辞所引古歌计560句,四言句式217句,占诗句总数的38.8%。二言句式153句,占27.7%。三言句式155句,占诗句总数的27.3%。五言句式27句,占诗歌总数4.8%。六言句式8句,占诗歌总数1.4%。虽然《易经》卦爻辞所引古歌中纯粹的四言诗还很少,但四言的句式占诗歌总句式的38.8%,以四言为主体的诗歌占诗歌总数的32%,四言句式在诗歌中分布最广,这进一步说明,上古二言诗体至少在商末已经开始向三言、四言诗体发展,这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三言诗句明显少于四言诗句,且纯粹的三言诗未见,说明继二言诗之后诗,我国的诗歌明显向四言诗体过渡,为《诗经》四言体的兴起开了先河。
三、中华民族以和谐对称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是《诗经》四言体形成的重要因素
“对称”这一规则表现在自然界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晶体(雪花等)和我们人体本身,都是对称图形的具体表现。在人类发展史上,生存在不同地域的世界各民族,都曾经不约而同地制作了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对称形制的泥陶制品,也是对称的美学原理作用的结果。
中华民族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周代进一步发展了农业文明。从《诗经》中新出现的复音词,我们可以看出周代农业发展的盛况。据刘馨阳的统计,[3]《诗经》中复音词1182个,其中与农业生产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相关的词最多。以叠音词为例,《诗经》中叠音词352个,其中与动物相关的词56个,与花草庄稼形貌相关的词35个,对劳动声音模拟的词14个,与自然界相关的词47个。这些新出现的叠音词,充分说明了周代农业生产生活的新变化。周代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对称和谐节奏的进一步发展。
周人重视农业生产,因此在劳动生产中,必然要遵循大自然的节奏,所以在周人的精神世界中,表现为与天地万物的亲近和对大自然生命节奏的自觉认同。周人首先适应了春秋这两个大的生命节奏:每年仲春之月,农夫们到田地里去耕种,到仲秋之月,便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由于春秋两个季节对于周人的生活特别重要,周人对这两个季节便特别敏感并抱有深厚的亲切情感。他们常常以春、秋来代表一年的四个季节,如《鲁颂·閟宫》“春秋匪解”,郑玄《笺》云:“春秋,犹言四时也。”[6]后来,春秋时期人们还把各国历史名为“春秋”,也说明春秋这两个季节对于周人生命节奏的重要意义。[7]日月的出没更迭也影响着周人的生命节奏,因为传统的农业人生,人们必须自觉遵守包括日月在内的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人逐渐习惯于把早、晚作为一天生活中两大节奏的起始点,形成了全民族一天之内生活、习惯、行为、情感、心理等方面不可违背的两大节奏。春秋、日夜两大对称节奏对《诗经》对称节奏的形成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四言诗将两个对称音组连接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节奏感。因而,由两个对称音组相连而成的四言诗,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诗体。”[8]28赵敏俐先生认为,四言诗歌形式是中国早期诗歌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诗歌形式:
中国早期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体现了先民对于汉语诗歌音乐形式的掌握和对艺术之美的自觉追求。其在艺术上的最高成就是《诗经》。这305篇作品中,绝大多数都以四言为主,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向着四言诗的典型形态靠拢。大多数的四言句都由两个对称音组组成,……大多数的诗歌都遵循着句式之间的对称原理,大多数的诗篇都遵循着首句押韵与偶句押韵的规则,强化着每一联之间的对称效果。[8]29
赵先生的话说明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体式形成是受到了对称原理的影响。
总之,《诗经》以四言为主的诗歌形式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多方面的原因。商末周初的重大社会历史变革,既为《诗经》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也为《诗经》语言形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周代初年的社会变革,汉语词汇系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大量的以双音节为主的复音词,在文学上导致了诗体发生转型,宣告以韵素为节律单位的二言诗歌退出历史舞台,为《诗经》以音节为韵律单位的四言为主的诗体形成提供了语言前提。《诗经》尤其是《雅》《颂》在内容上的庄重和严肃,对《诗经》的语言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诗经》的四言形式应运而生。《易经》中卦爻辞所引古代诗歌,表现出由三言向四言过度的迹象,为《诗经》四言形式的兴起奠定了诗体基础。《诗经》以四言为主体的诗歌形式,也适应了周民族对称的审美心理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