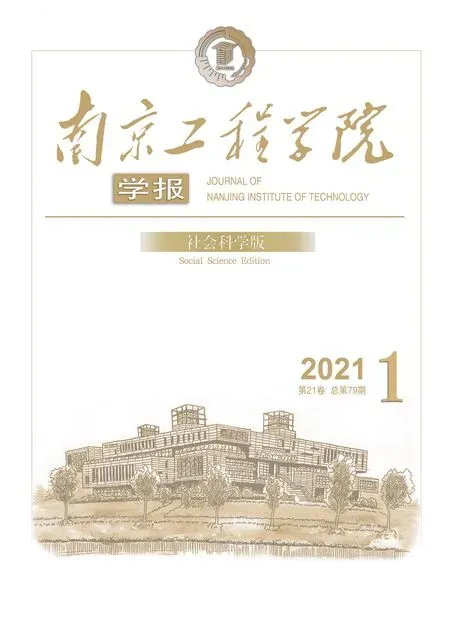新时代对外传播视域下毛泽东诗词英译策略研究
刘荣强,张玲玲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对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明确要求。由此,在新时代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及对外传播工作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赋予国内译者及其他对外传播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应高度重视,并扎实落实,不容忽视和偏颇。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先后20多次引用毛泽东诗词,一方面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另一方面用生动形象的方式阐述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思想[1]。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引用毛泽东诗词,对于新时代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和对外传播赋予了新的内涵。本文立足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的基本趋势,从译本定位、英语诗歌基本结构要素把握、词语翻译等方面入手,对毛泽东诗词英译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策略。
一、译本定位
概括说来,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具有如下三大基本趋势:第一,随着我国对外传播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对外传播工作者应充分树立自信,消除以往的边缘化心态;第二,通过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使国外受众听得懂,乐意听;第三,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倡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2]。这三大趋势为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包括译者在内的对外传播工作者要深入领会,以避免具体落实时的盲目和随意。毛泽东诗词英译及对外传播应根据这三大趋势处理好所涉及因素之间的关系和有关问题,包括译本的定位、译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及目标读者之间的关系、翻译策略的选择等,尤其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诗词英译及对外传播,除原诗词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之外,其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文化也应得到重视,在译本中得到有效诠释,这是我国对外传播工作者充分树立自信的态度展示和实际行动表现。近些年来,党中央倡导坚定“四个自信”。单就文化自信而言,毛泽东诗词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浓缩和集中体现。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底蕴,尤其喜爱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作品,毛泽东诗词创作是在继承中国古典诗词基础上的创新和升华。同时,毛泽东诗词还融入了他本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例如源自《庄子·逍遥游》的“鲲鹏”之典在毛泽东诗词中就用过四次之多。此外,毛泽东诗词创作与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密切关联。这些因素在毛泽东诗词英译和对外传播工作中都不容忽视。施莱尔马赫把翻译概括为两种:一种是让目标读者靠近原作者,另一种是让原作者靠近目标读者。将毛泽东诗词翻译成英语,就以上两大翻译策略而言,无论选择哪种,或者以哪种为主、哪种为辅,由于毛泽东的身份以及他所倡导的文艺思想与其诗词作品的密切关联,国内译者及其他对外传播工作者都不应因国家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而只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而忽视其中深刻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内涵,否则其英译就会有失偏颇,与新时代对外传播的要求不相符合。从策略上讲,可充分发挥副文本的作用,包括序言、后记、附录、脚注、尾注、照片、图片等,对有关内容进行总体介绍和具体说明。在国内英译本中,顾正坤译本[3-4]和李正栓译本[5-6]都特别注重副文本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具有代表性。
其次,毛泽东诗词英译及对外传播应注重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这对于国内译者及其他对外传播工作者来说责无旁贷。如果只是亦步亦趋地照搬国外译者和出版机构常用的话语体系,是否符合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要求则存在较大的疑问。国外目标读者之所以选择我国译者的译本而不是选择阅读英语国家译者的译本,目的之一就在于寻求具有差别化的阅读体验,以便能够更好地走近毛泽东本人和他的作品,即使我国用于对外传播的英译本在语言和文化上与他们的接受习惯存在一定的差别,也会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他们有心理准备,对此国内译者不应太过担心。国内译者的译本,当然要争取做到使国外目标读者读得懂,喜欢读,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对国外目标读者一味地去迁就、去迎合,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国内译者及其他对外传播工作者应密切联系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趋势和要求,认真研读现有的国内外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借鉴不同译本中的成功经验,避免其中的问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视野,把近年来我国在其他汉语图书英译以及其他领域对外传播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融入到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及对外传播之中,以便更加有效地提升对外传播效果,推动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
再次,国内译者及其他对外传播工作者应根据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趋势和要求,把毛泽东诗词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念创新性地展示和分享给国外目标读者。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时代命题,是毛泽东诗词英译及对外传播的重大突破口之一。由此,国内译者及其他对外传播工作者要有大局意识并具备与新时代要求相符的对外传播能力,不能与新时代脱节,不能偏离当前我国对外传播的大趋势,更不能自娱自乐或自我欣赏。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和平外交核心价值基础上的伟大创新,是对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文化创造性的发展,是对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治理体系和新秩序的伟大贡献[7]。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不仅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而且在外交上关心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正义事业,立场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已经融入到了他的诗词创作之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沁园春·长沙》《念奴娇·昆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五律·挽戴安澜将军》等。由此,当前对外译介和传播毛泽东诗词,毛泽东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思想在译本中应得到充分体现,否则的话,一方面,毛泽东诗词的对外传播会有失偏颇;另一方面,也将与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的要求不相吻合。如上所述,有关内容可通过副文本方式加以介绍和说明,使伟人毛泽东所具有的包括关心中国人民和人类共同命运在内的深刻思想得到更加有效的彰显,并在英译和对外传播中赋予新时代的内涵。
二、诗歌结构要素把握
译者应根据新时代我国对外译介和传播毛泽东诗词的具体目的,平衡好原诗词结构要素与国外目标读者预期、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不能凭空想象和主观臆断,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英译本在诗节和诗行总数上应与原诗词完全保持一致。毛泽东诗词的国外英译本在诗节和诗行的处理方面大多与原诗词存在较大的差别,不注重形式对等。国内英译本在诗节上均与原诗词保持一致,但在诗行总数上仍有个别译本与原诗词有一定的出入,例如许渊冲译本为475行,超出原诗词18行;顾正坤译本为463行,超出原诗词6行[8]。毫无疑问,英译本在诗节和诗行总数上与原诗词保持一致是完全有必要而且是可行的。如果不一致,则缺乏合理依据。在诗节和诗行总数方面进行形式上的改变,谈不上是译者创造力的彰显。单就某一具体诗词作品的英语翻译而言,为了克服具体的翻译障碍和解决有关翻译问题,英语译文对原诗词作品中个别诗行进行删减,将原诗词作品中的某一行在译文中用两行或多行来表达,或者对原诗词作品中多个诗行在译文中进行前后顺序的调整,只要译文能够做到与原诗词作品功能对等并且做到诗行总数保持一致,则是可行的操作方案。
其次,英译本不宜机械照搬英语诗歌的韵律、节奏和音步。国内部分译者尤其喜欢采用AABB和ABAB这两种韵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韵式并不是诗歌形式上的必然构成要素,不是在所有英语诗歌中都会得到应用。国外目标读者在阅读包括毛泽东诗词在内的中国诗歌英语译文时,在很大程度上所要寻求的是一种有别于他们平时阅读原创英语诗歌的体验,他们能够接受译文与他们本国原创英语诗歌在结构形式上所存在的差别。即使他们真的喜欢阅读韵式上完全归化了的译文或译本,以上两种韵式频繁的使用也未必是他们所普遍认可或接受的。毛泽东诗词英译,需要对国外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只有建立在具体调查基础之上的翻译才能具有针对性,才会有说服力。否则,如果译者仅凭自己的好恶而选择以上两种韵式,无论译文的结构形式看上去多么的优美,对外传播效果也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韵式上,译者宜争取最大限度地对原诗词作品之中押韵的诗行进行相应的尾韵处理,当然不能为了押尾韵而凭空增添、删减甚至改变原诗词作品中的内容,也不可为了押尾韵而改变译文中同一诗行各英语词语之间的自然顺序,以免造成因韵害意或因韵废意的问题。同样,诗行内押韵的处理也不宜只是为了追求音、形、意方面的美而偏离具体翻译和对外传播目的。毛泽东诗词作品英译在节奏和音步的处理上也不可太机械,而应以能够有效传达原诗词的意义、思想和情感为基础,不能使之成为翻译的限制、障碍或点缀。由此,对于国内译者来说,非常有必要拓宽对当前英语国家英语诗歌创作及接受情况的认识,以避免因主观臆断而影响译本的对外传播效果。追溯到100年前埃兹拉·庞德的《华夏集》翻译实践,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韵律和节奏上已经死板僵化了的美国诗歌进行了有效革新,对美国诗歌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9]。一个世纪之前那些僵化了的韵律和节奏在英语诗歌中的使用就受到了庞德的批评,这足以值得我们去思考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向国外翻译和传播毛泽东诗词,对英语诗歌中有关韵律和节奏的使用就更不能去机械地模仿或简单地照搬,否则更将会事与愿违。
三、词语翻译
在词语翻译上,要根据具体翻译目的,以国外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为基础,不能过分放大原诗词作品本身在词语使用方面的语言特点、艺术特征以及有关词语所沉淀的中国文化内涵。诚然,建立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是新时代的要求,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确实要树立文化自信,要立足于中国文化,但是将毛泽东诗词中的有关元素英译,译者不可无视对外传播的具体目的,否则难以使国外目标读者读得懂、读得进去,建立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则无从谈起。
第一,专有名词的翻译。对于毛泽东诗词中的词牌名,国外英译本倾向于删掉不译,而国内英译本则较为多样化。国内的1958年、1959年、1976年译本以及1978年的吴翔林译本均采用了威妥玛拼音法[10]275;赵甄陶译本在译文的标题处将词牌名删掉不译,在译文后的注释中采用意译法做了简要说明,例如将《浪淘沙·北戴河》标题翻译为“THE SEASIDE RESORT BEIDAIHE”[11]50,在译文后注释为“The original is written to the tune ofWavesWashtheSand”[11]51。黄龙译本在标题处对词牌名采用拼音加英语词语补充说明的方式,例如将上述标题翻译“Beidaihe—to the melody ofLangTaoSha”[12]75。许渊冲译本[13-14]和顾正坤译本[3-4]均采用意译法,例如将上述标题分别翻译为“Tune:RipplesSiftingSandThe Seaside—Beidaihe”[14]93和“BEIDAIHE to the tune ofWavesSiftSand”[3]131,对词牌名“浪淘沙”均做了意译处理。李正栓译本在标题处对词牌名采用了拼音法[5-6]。几十年来,随着汉语拼音在我国的普及以及在专有名词英译实践中的应用,对于包括词牌名在内的汉语专有名词,如果没有相匹配的通用威妥玛拼音法译名,翻译成英语时已没有采用这种音译法的必要,否则会与时代脱节,也与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相违背。将词牌名进行意译没有太大价值,无论是在标题中直接使用,还是像赵甄陶译本中那样用于注释,并不可取。词,在我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尤其是经过近现代以来的发展,词的内容已与词牌名的意义失去了内在的关联。词牌名采用意译法,则会使国外目标读者尝试去理解有关英语词语所表达的意义,但他们却又不明白所理解的词牌名意义与作品本身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反而会给阅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使他们阅读整个译文的体验受到影响。在标题处将原词牌名删掉不译,单就国外目标读者对译文的阅读体验而言,可避免阅读上的障碍和困惑,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对于希望走近毛泽东本人及其诗词作品的国外目标读者来说,仍然有些欠缺,可通过增加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仍以《浪淘沙·北戴河》为例,如果将标题翻译为“Beidaihe”,即删掉词牌名,在译文后增加注释“The full title is ‘Langtaosha Beidaih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original peom is written with the melody of ‘Langtaosha’ in the Chinese Ci poetry”,这对于国外目标读者来说,但最起码可知道词牌名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在标题处直接采用拼音法来处理,虽然也不一定是最佳方案,对于国外目标读者来说读起来有点像“乱码”,但最起码可避免意译法给他们带来的困惑或误读,通过脚注、尾注或其他副文本方式加以说明,可使有关阅读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少甚至消除。有关说明不宜太过细致,毕竟绝大多数国外目标读者阅读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目的是为了走近毛泽东本人和他的诗词作品,而不是要专门学习词这种中国诗歌别体。此外,黄龙译本中对词牌名的处理方式也非常值得借鉴。
毛泽东诗词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人名和地名,例如秦皇(秦始皇)、汉武(汉武帝)、华佗、魏武(魏武帝曹操)、唐宗(唐太宗)、宋祖(宋太祖)、成吉思汗、黄公略、张辉瓒、昆仑(昆仑山)、井冈山、武夷山、匡庐(庐山)、龟蛇(龟山和蛇山)、六盘山、湘江、金沙江、赣江、汀江、湘(湖南)、鄂(湖北)、黄洋界、龙岩、宁化、清流、归化、会昌、吉安、橘子洲、钓鱼台、大渡桥……对于这些专有名词,宜优先采用已有的通用英语译名。如果没有通用英语译名,宜根据近些年来国内专有名词英译基本规范来进行操作。译者应对原诗词作品中的专有名词仔细考证,避免望文生义或张冠李戴。对于在不同诗词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某一专有名词,如果需要按照专有名词来翻译,一定要确保一致,避免在不同诗词作品的译文中各自有不同的名称。考虑到英译时具体诗行不宜过长,有关专有名词在译文中可根据原诗词作品的整体语境和风格进行相应处理,以免译文诗行太长在形式上与原诗行发生背离并且使国外目标读者的阅读体验受到影响。如果有关人名和地名在原诗词作品中具有文献价值,则不宜省略。对于影响国外目标读者阅读、在作品中具有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的专有名词,可通过脚注或尾注方式对有关背景知识简要说明,但不宜采用文内夹注,以免使英译本整体的阅读体验受到影响。对于套用西方文化元素的处理方式,国内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例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不可沽名学霸王”,“霸王”意指“西楚霸王项羽”。许渊冲将该行翻译为“Do not fish like the Herculean King for renown”,套用了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Hercules”。对此,李崇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用“the Herculean King”来翻译“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达到了神似的效果[10]85。然而,只要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和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翻译方法并不可取,有关学术观点也有待商榷。就英语诗歌在我国的传播和接受而言,肇始于清末的英语诗歌汉译,起初可谓也是上述归化策略大行其道,但随后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试想,今天我国有多少读者在阅读翻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时会喜欢阅读被附加了浓厚中国文化元素的译文?这种操作方式在当前的英诗汉译中不可取。同样,在当前的汉诗英译中也不可取,毕竟国外目标读者寻求差异化的阅读体验和通过译文或译本走近原诗人和原作品是这类翻译实践活动的逻辑开端。
第二,数字及所搭配词语的翻译。毛泽东诗词中使用了大量的数字,其中有的为虚指,有的为实指。虚指数字的使用是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毛泽东诗词的风格。实指数字的使用与具体事件和事实密切相关。由此,译者非常有必要理清毛泽东诗词中的有关数字究竟是虚指还是实指。对于虚指的数字,更多体现的是原诗词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彰显了原诗词本身的气势和风格,是一种情绪的渲染,英译时不宜直接照搬,不宜做简单的对等处理,否则会令国外目标读者感到费解,甚至会造成误读。即使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在阅读毛泽东诗词时,更多的是体验这些虚指数字以及所在诗行所带来的情感上的共鸣。由此,虚指数字英译时,宏观上应密切结合具体翻译目的和所在诗行的整体表达,微观上要关注数字所搭配的名词,先确定有关名词的翻译,然后再考虑数字的处理,注意整首译文意义和风格的把握并确保语言表达的地道。对于实指数字,如果数字后有搭配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除进行归化处理外,例如将长度单位“里”替换为“英里”并对有关数字进行数值换算,最好通过脚注或尾注方式对所涉及事件或事实加以说明,使作品本身的文献价值得到彰显。例如《七律·到韶山》中的“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将其中的“三十二年”翻译成英语虽然没有任何困难,但除了要做到数字对等外,最好注释说明作品不仅表达了毛泽东久别故乡的情况,也抒发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命运、革命事业和国家建设的情怀,以便国外目标读者对这一作品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甚至引起他们的共鸣。
第三,普通词语的翻译。这类词语翻译成英语要与它们在原诗词作品中真正表达的意义和风格做到对等,最好使用当代英语中的普通词语,避免使用旧词、偏词,要注意同义词、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以及词语之间的搭配,确保译文词语使用的质量,提升译文的表达力和感染力。《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世上无难事”,李正栓将其翻译为“In this world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5]177。其中的“难”翻译为“fear”,非常得当。如果根据词典中的基本释义“difficult”,将该诗行翻译为“In this world there is nothing difficult”,则逻辑上讲不通,世界上怎么会没有“困难”的事情?这样翻译,显然违背常识,会令国外目标读者感到费解。“难”字在原作品中并不是“困难”,而是“畏惧;担心”的意思。脱离语境而只停留在字面意义或词典中的基本释义来进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是大忌。《西江月·井冈山》上阙第三行“敌军围困万千重”和下阙第四行“报道敌军宵遁”都使用了“敌军”一词。在许渊冲译文中,该词都被翻译为“foe”[14]16-17,第一个“foe”位于所在诗行结尾处,与第一行结尾处的单词“below”押韵,使译文第一个诗节形成ABAB韵式;在赵甄陶译文中,第一个“敌军”根据译文语境做了省略处理,第二个“敌军”被翻译为“foe”[11]9;在黄龙译文中,分别被翻译为“enemy”和“foe”[12]19。这几位译者倾向使用“foe”一词,除了许渊冲还有出于韵式的考虑之外,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英语单词比“enemy”或“enemy troop(s)”显得更加“雅致”。然而,严格说来,“foe”一词的使用有待商榷,虽然该词与“enemy”是同义词,但该词在当代英语中较少使用,给读者以过时、陈旧之感。再以《忆秦娥·娄山关》中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为例,许渊冲将其翻译为“The wild west wind blows strong; /The morning moon shivers at the wild geese’s song”[14]60。尽管“wild”和“strong”都可与“wind”搭配,但就所在诗行而言,无论是内容的表达,还是风格的诠释,将“wild”和“strong”同时与“wind”搭配使用则不妥,较为累赘,尽管“wild west wind”采用了头韵,也难以实现较好的阅读体验。另外,“wild”一词重复使用了两次,也会使译文的阅读体验受到影响。由此,从宏观视角入手,立足于具体翻译目的,平衡好源文语境和译文语境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普通词语的翻译进行精雕细刻地把握格外重要。此外,无论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翻译,词语的选择和使用,技术层面的处理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则要看是否能够引起读者心灵上的碰撞与共鸣。
第四,用典的翻译。毛泽东善于在诗词创作中用典,非常具有表达力和感染力,增强了诗词作品的艺术性。如果从理解原诗词作品的角度来考虑,译者应该对用典的具体出处追本溯源,以便能够更好地走近毛泽东,与原作者对话,更加深入地理解有关用典在原作品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从英语表达的角度来考虑,则不宜过分放大原诗词作品的用典特征,以免给国外目标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阅读负担和障碍。译者应根据具体翻译目的,从宏观视角入手来考虑怎样进行语际转换更为得当。对于专有名词类的用典,如果具体翻译目的要求译文既与原文做到功能对等,又争取做到形式对等,如上所述,则可采用近些年来国内专有名词的翻译规范并通过注释方式来处理;如果具体翻译目的只要求做到功能对等,翻译成英语时将有关用典在原诗词中真正表达的意义用普通英语词语表达出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一枕黄粱”是对成语“黄粱美梦”的简化。对于译者来说,一定要把对原作品的理解和进行双语转换分开。理解阶段,需要对有关用典寻根探源。但将其翻译成英语时,只需把该词语在原作品中真正表达的意义用普通英语词语表达出来即可,不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没必要对“一枕黄粱”加注释说明其出处。否则的话,就不是在翻译毛泽东诗词,而是在通过毛泽东诗词的英语翻译帮助国外目标读者学习汉语成语了,这样显然就偏离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和对外传播的真正目的。另外,无论原诗词作品中用典与否,英译时不宜套用西方文化中的有关典故。例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诗人兴会更无前”,黄龙将其翻译为“And poets’ Pegasus is inspired to fly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12]70。 原本是一个普通词语的“兴会”,译者套用了“Pegasus”这一西方文化中象征诗歌灵魂的典故来翻译,虽然译文能够展示出译者所具有的西方文化功底,对于某些目标读者来说,也许会感到译文很“美”或者很“雅”,但这种操作方式很难使国外目标读者走近毛泽东和他的作品,甚至会对他们造成误导,有时也会使国外目标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在新时代,如果仍沿用这样的操作方式,也不利于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
四、结语
当前英译和对外传播毛泽东诗词,国内译者及其他对外传播工作者应立足新时代加强有关理论学习,明确并契合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的新趋势、新特征和新要求,进一步开阔视野,提高对外传播能力,不可盲从或机械照搬,不能想当然或自娱自乐。要从宏观视角入手,按照规范的程序,解决好新时代毛泽东诗词对外传播中为何译、为谁译、译什么、怎么译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克服微观层面的翻译障碍,使译本符合新时代对外传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