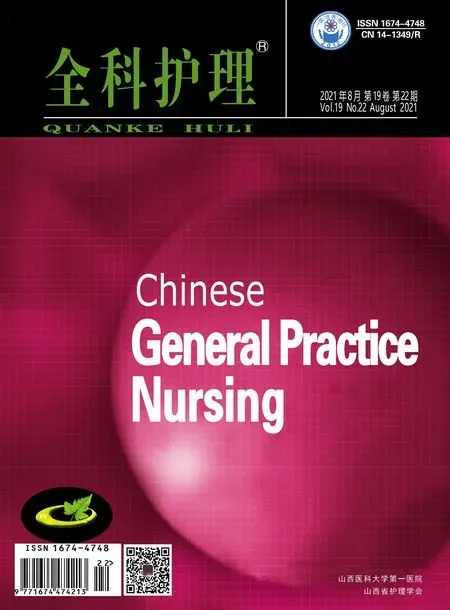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度的相关研究进展
温 华,陈长英,唐 涵,陈怡杨,郜心怡,董诗奇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疾病谱变化,以癌症、心血管等为代表的慢性病的患病率、病死率仍处于上升阶段,疾病负担大[1]。而近年来,随着优逝理念的出现,病人及其家庭逐渐开始重视死亡质量。死亡和死亡的质量被定义为对生命最后几天和死亡时刻的评估,关于如何准备、面对和经历那些已知的晚期疾病[2]。从照顾者角度看,“善终”属性包括维护社会关系、积极保健、照顾者信心和能力、病人准备和死亡意识、死亡和死后支持等[3]。死亡准备度是指终末期病人即将面临死亡时,其家庭照顾者的心理情感以及行为、认知情况[4]。研究显示在照顾晚期病人时因照顾负担重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焦虑、抑郁、躯体症状和较少的社会支持,对病人死亡准备不足的家庭照顾者则表现出更多的症状[5]。提高死亡准备度可以有效满足家庭照顾者及病人的生理、心理需要,提高临终照护质量,提高双方生活质量。死亡准备与丧亲结局(包括复杂性悲伤、抑郁和焦虑)之间的相关性和预测性关系的证据也强调了丧亲准备的重要性[6-7]。但是多数家庭照顾者仍报告对死亡毫无准备[8],并且高强度的照顾压力导致出现更多的抑郁、焦虑和复杂性悲伤症状[9]。对死亡有认知和行为准备的照顾者,在情感上也往往准备不足[10],因此指导专业人员对家庭照顾者的死亡准备进行评估和支持是必须的。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对死亡持避讳、恐惧的态度,导致死亡准备、死亡教育等发展较滞后。但随着文化的发展,国内的死亡观念也逐步发生转变,舒适且有尊严地走完一生成为护理研究的重要课题。现综述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度概念及发展、研究工具、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现状,以期为今后国内死亡教育及临终照护的发展提供借鉴。
1 概念及发展
死亡准备度的概念源于照顾者准备度的概念及研究,照顾者准备度最初是指照顾者在准备实施照护工作时,为满足被照顾病人的生理、心理需求所做的准备,包括生活护理、心理护理、处理压力情绪等[11]。之后照顾者准备度更多用于临终病人照顾者的研究,死亡准备度的概念应运产生。2006年,Hebert等[9]的研究把死亡和丧亲相关的照顾者准备度定义为照顾者对病人即将死亡所感知到的准备状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层面:①认知维度指照顾者为准备死亡所需要的医疗、实践、社会心理或宗教/精神信息;②情感维度指心理上或情感上为死亡做准备;③行为维度指任务,如遗产规划、葬礼安排、重新安排工作日程等。之后,其团队构建了一个包括医疗、心理、精神和实际问题的EOL理论框架[4]专门用于描述照顾者死亡准备的领域和特征。关于死亡准备度的定义多与照顾者的角色密切相关,很多研究与 Hebert的定义相似,将其描述为照顾者对临终亲属的照顾准备状态的感知[12-13];一些研究将其定义为照顾者对病人死亡的准备情况[14-15];另外有研究将其看作是一个人对死亡预警和准备的感知[16-17]。Schulz等[18]将死亡准备描述为一种预先心理和实际调整,照顾者在确认病人即将死亡时参与其中。最新的概念分析研究中,死亡准备被正式定义为“认知、情感和行为质量(或状态/准备)来减少不确定性,保持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当前/未来损失相关的痴呆和死亡”[19]。由此可知,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度的概念已逐渐清晰,通过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认知、情感、行为的准备,减少不确定感。
2 研究工具
目前许多研究工具的设计目的并不是用来评估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的情况,但有研究认为在理论上评估照顾者需求在生命末期(end-of-life care, EOL)被满足程度的工具也可以表明准备的水平。
2.1 照顾准备量表(Preparedness for Caregiving Scale,PCS) PCS于1990年由Archbold等[11]基于角色理论,探讨相互关系和准备度对照顾者角色紧张的预测作用,对78名老年人及其家庭照顾者进行方法学研究后得出,用于测量家庭照顾者照顾病人或家庭成员时对角色任务和压力应对的感知准备情况。该量表包括8个条目,主要包括生理需求、情感需求、服务计划、照顾压力、舒适照顾、应对和管理紧急情况、获取医疗信息资源和帮助及整体照顾准备度,应用Likert 5级评分法对每个条目进行评分,从“一点准备也没有”到“已做好充分准备”分别计0~4分,总分0~32分,分值越高表明照顾者的照顾准备状况越充分。Cronbach′s α系数为0.86~0.92。量表开发后被广泛应用于姑息照护、癌症、脑卒中、痴呆等病人照顾者的研究中,被用于评估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程度[20]。国内学者刘延锦等[21]将其翻译为中文版,并应用于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中文版照顾准备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5,表明中文版照顾准备量表有较好的信度,适合用于评价我国家庭照顾者的照顾准备度。该量表条目包含心理社会和护理实际等多维度问题,具有较好的普适性,但不具有特异性,缺乏照顾者面对绝症病人即将死亡的心理及行为的具体准备条目,可能与量表开发时未基于该类病人的原因。因并不是为针对性评估对死亡的准备而设计,因此也限制了该工具在这方面的适当及针对性。
2.2 死亡应对自我效能感量表(Death Coping Self-Efficacy Scale) 本量表改编自Robbins[22]提出的与临终关怀相关的死亡应对自我效能感量表,量表包含了由3个维度组成的29个问题。有12个问题是针对临终关怀和解决提供精神和精神护理的末期病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信心;9个问题是关于护理人员应对悲伤的能力,旨在检查护理人员在面对他人死亡时如何减轻自己的悲伤;其余8个问题与对死亡的心理准备有关,旨在评估对自己死亡准备的信心水平。问题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临终关怀量表、死亡应对量表、死亡准备量表总分分别为12~60分、9~45分、8~40分,总分为29~145分。其中较高的评分表明照顾者在为最终死亡做准备时采取了有效的适应策略,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95[23]。中文版量表的内容效度测试结果显示,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标在0.40~1.00,平均为0.87,中文版官方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24]。该量表条目维度较多地关注在心理层面,可以较完整地评估护理人员在面对死亡时的心理状态,但缺乏实际准备的评估,若在研究时评估范围包含除心理以外其他方面,需配合其他量表使用。
2.3 单一条目问题 有研究在病人死亡后4~5年使用单个问题,如“How prepared were you for your(relative′s) death?”等来针对病人死亡前家庭照顾者的死亡准备度进行调查,并应用Likert 7级评分进行计分[25]。Tsai等[26]应用此单一条目与围死亡情景感知量表中的3个问题一起对照顾者进行调查。或者使用单一条目[27]“If your loved one were to die soon,how prepared would you be for his/her death?”,采用3级评分法“一点也不”“有点”和“非常”进行评分,搭配复杂性悲伤量表(the Complicated Grief Scale)进行家庭照顾者的死亡应对评价。Mori等[28]用单个条目“Have you acted in preparation for death?”评估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行动,回应类别是从不、有一点行动、有行动、有很多行动,后3种反应被认为是在为死亡做准备,并举例澄清行为的性质,如增加了时间与病人、修复与病人的关系、帮助病人满足愿望等。在尚未出现专有的评估工具时使用单一条目组合其他量表成为趋势,但这种方法需配合研究内容,且配合使用的量表可能并不能完全包含绝症病人照顾者死亡准备的相关方面,具有一定的限制性。
目前针对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的评估工具研究刚起步[29],可能受惧怕死亡的社会文化影响和需准备的条目范围较大,导致相关评估工具的开发也较有难度。但基于社会发展、人类思想进步,准备应对死亡必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需根据我国社会文化的基础,研制更可靠、多维度、实用的评价工具。
3 影响因素
由于缺乏针对死亡准备的研究工具,其相关影响因素尚不清晰。因在照顾过程中对病人的死亡准备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可推测出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目前有研究分析出部分相关影响因素。
3.1 与病人关系 目前被发现的人口学因素尚不清晰,但有研究显示在与病人关系中,配偶关系的家庭照顾者比其他关系的家庭照顾者对死亡准备更不足[4]。可能的原因是,相比其他关系,配偶更加依赖对方,这种依附安全感会影响配偶的死亡准备[30],使得自身难以支持面对家庭成员的死亡。这也提示专业医务人员在家庭照顾者的管理中,应更加关注配偶关系照顾者,给予针对性的指导支持。
3.2 照顾经验 研究显示,照顾者的照顾持续时间、先前是否有过相似照顾经验、先前是否接触过预立医疗计划(ACP)或有关于死亡的相关计划都会对照顾者准备具有影响[4]。相关经验使家庭照顾者对类似医疗情况更加理解,会对预期情况有所准备。但也有研究显示相反结果,照顾者准备程度并不取决于照顾的持续时间或强度[31],反而会造成专业人员对照顾者误解从而忽视。因此,如何准确认识照顾者的照顾经验,识别准备不足的家庭照顾者并给予支持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3.3 信息缺乏 缺乏信息会导致不确定性,抑制家庭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影响EOL的决策、控制和规划,从而限制照顾者对死亡的准备[19,32]。由此显示,相关各方(医护患)和家庭照顾者之间的清晰一致、可靠的沟通是十分重要的[4,33],照顾者管理的不确定性与沟通不当导致获取信息不足有关。即将死亡病人一般具有复杂的照护需求,家庭照顾者需及时根据病人需求改变自己对病人情况的准备,并且需掌握更多关于病人的预后信息以为病人即将死亡做准备。因此,相关信息必须得到补充支持,信息支持不足会导致准备不足。
3.4 社会支持 研究显示,社会支持能有效影响家庭照顾者的死亡准备,当家庭照顾者在为终末期病人提供照护时,同伴的支持对照顾者的护理行为有积极影响[34]。因为充分的社会支持可以成为照顾者管理其准备工作和应对病人死亡总体策略的重要安慰来源。未来在家庭护理团队的管理中,应加强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持,给予充分工作和情感上的帮助。
3.5 负性情绪 有研究对幸存照顾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照顾者对病人死亡前的经历感到悲伤,强调并未对病人死亡做到完善准备,情感上的支持不足,导致出现罪恶感和力不从心的感觉[33]。另外,照顾者的抑郁情绪也是重要影响因素[27],抑郁情绪导致照顾者的积极照顾行为减少,在照护过程中受负性情绪的影响,导致照顾者与专业护理团队、与病人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得不到心理支持,更易造成对病人情况的难以掌握。这提示在临终照护中重视对照顾者的情感支持,应加强有效沟通,缓解不良情绪。
目前缺乏有效的针对性研究工具,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过程的复杂性及照顾者的个体差异性等导致死亡准备的研究因素有待进一步探索,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其他有效方式提高对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影响因素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开展有益的干预支持。
4 相关研究现状
由于当前安命疗护、姑息照护服务的推广,病人的临终护理质量得到提高[35-36],通过预立医疗计划等形式,使得病人对死亡的观念及准备得到改善[37]。照顾者又称非专业护理人员,作为与病人作为相互作用的密切相关者,在绝症病人的照顾中,必须同样面临病人即将死亡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对于照顾者的死亡准备易被忽视,为此通过文献回顾对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4.1 探索死亡准备经验及内容 由于晚期痴呆病人的特殊性,导致其家庭照顾者的死亡准备研究成为热点,Supiano等[38]通过对106名家庭照顾者在面对痴呆家庭成员死亡时的心理准备和悲伤体验之间的关系的评估,结果从具有充分准备和准备不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建设积极记忆、将死亡视为痛苦的结束、解决关系、理解痴呆、意义的理解会帮助照顾者对病人的死亡做好准备,而角色丧失、得不到支持和难以创造新生活的照顾者报告死亡准备不足,难以理解疾病和死亡的意义。除痴呆外,其他绝症病人照顾者同样是研究重点,Walsh等[33]对已故成年癌症病人的幸存照顾者探讨照护病人生命最后一天的体验,发现照顾者会因失去照顾者的角色而感到痛苦和内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更全面地了解病人和照顾者之间交流的影响、死亡准备、死亡后照顾者角色的转变以及对照顾者经验的探访。Breen等[39]对16名接受姑息治疗的家庭照顾者进行面对面访谈探讨对死亡的准备,结果报告照顾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和对未来的担忧和计划之间犹豫不决时面临较大压力,难以预料的疾病发展过程,要求面对护理需求需做出复杂准备。Wiener等[40]对即将丧子的父母照顾者进行相关准备的研究,结果显示大约40%的父母对孩子所面临的医疗问题和如何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都感到没有做好准备,该研究确定了父母需准备具体的医疗和情感问题,并且指出对有关子女状况的沟通不满和缺乏指导可能会造成父母的痛苦程度越高,准备越不足。随着临终关怀在国内的逐渐开展,终末期病人照顾者的照顾体验成为研究热点[41-42],此类相关研究显示,通常家庭照顾者对死亡准备经验不足,并总结进行死亡准备的相关方面,需专业人员给予支持,尤其是面对病人死亡给照顾者带来的情感创伤较大,未来在绝症病人的护理中,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者角色支持、心理支持必不可少。
4.2 给予死亡准备干预支持 目前在对终末期病人照顾者的准备研究中,已渐渐重视对家庭照顾者的死亡准备,如Hudson等[43]团队为接受姑息治疗病人的家庭照顾者设计了一个心理教育干预项目,将106名癌症家庭照顾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在标准姑息照护的基础上,接受护士提供的新干预,内容包括照顾者角色准备、自我照顾的重要性及策略、病人死亡阶段准备、放松练习等内容,结果显示在短期内照顾者准备得到显著提高。Moore等[44]探索英国记忆服务中心在帮助痴呆症病人的家庭照顾者为生命结束做准备方面的实践和作用,该服务中心会提供痴呆症的进展、痴呆症的终末期性质、精神状态和死亡的意义、精神能力、临终偏好和法律安排等信息,结果发现这些信息符合照顾者角色,但该机构较少地为照顾者提供死亡话题的谈论,未来需提供更多的生命结束和预立医疗计划等信息服务,完善机构的相关工作。Alvariza等[20]为姑息治疗重症病人的家庭照顾者设计了一项基于网络的干预计划,为增加照护和死亡准备,内容包括医疗问题、症状和症状缓解、家庭沟通、如何度过死亡前的时间、做一个照顾者、为死亡时刻做计划、对未来的考虑。干预信息通过视频与书面的形式呈现,并设有在线的同行支持讨论论坛,通过访谈及调查研究结果证明在促进照顾准备和死亡准备方面是有效的。但目前受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针对照顾者死亡准备的干预支持较难开展,更多的是利用姑息照护、临终关怀等护理模式对照顾者照护行为及情绪进行干预支持,但针对照顾者的死亡准备干预支持较少,尚未出现成熟研究。虽然相关研究在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研究开始重视照顾者死亡教育,国内余彩玲等[45]对晚期癌症病人家属实施死亡教育联合人文护理,探讨其对病人家属心理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此方案可缓解病人家属的负性情绪及心理应激状态,提高家属的生活质量。死亡教育在国内的开展目前大多集中针对在校医护学生[46-47]、临床护理工作者[48-49]或病人群体[50],目的在于改善对待死亡的态度。改善相关工作人员的死亡态度及死亡意识,在之后工作中对照顾者给予支持帮助,但目前针对照顾者死亡教育发展仍不足,如何立足本土研制适合我国照顾者文化的死亡教育模式,利用快速发展的网络科技等发展综合有效的干预项目,改善家庭照顾者的死亡准备是未来研究的挑战。
在目前的研究中照顾者在认知上、行为上的准备比较容易得到满足,但是情感上的准备是具有挑战性的,在临床工作中不应盲目确信家庭照顾者为病人死亡做好了准备,尤其由于家庭照顾者的照顾时长和强度易造成已对预期死亡状况掌握的假象。照顾者报告希望自己对死亡过程有更好的准备[51],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重视对绝症及终末期病人家庭照顾者的死亡准备支持。
5 展望
死亡准备作为临终护理的必备内容,被认为是“好死”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目前姑息治疗服务正逐渐被推广,但它往往强调病人对死亡的准备,却较少关注家庭照顾者“对死亡的准备或死后的生活”。作为与病人密切相关的部分,家庭照顾者的预期死亡和准备死亡的观点研究往往被忽视。通过本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家庭照顾者的死亡准备往往不足,同样需要给予支持,并且研究大都缺乏前瞻性,较少在病人死亡前进行家庭照顾者死亡准备的评估及干预,多为照顾者在病人死后进行情景回忆,影响研究的真实可靠性。许多政策及研究都显示可通过优势的干预措施,加强家庭照顾者对病人的死亡准备,可以有效改善病人的临终护理质量、死亡质量及照顾者的身心状态。而推动准备的要素包括前瞻性的确定准备相关的行为、心理等方面的因素,评估准备的效果。但是目前在死亡准备定义、测量工具方面仍存在局限性(如缺乏清晰度),尤其受我国文化的影响,开发研究适合我国社会文化基础的测量死亡准备的量表及干预措施是重中之重。明确死亡准备的概念及影响因素,对于未来预立医疗、终末期护理等干预计划具有良好的支持作用。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针对我国的社会背景,进行相关研究以支持我国终末护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