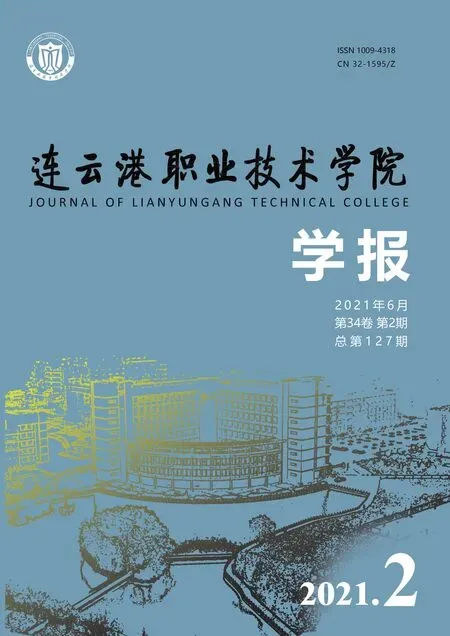西北女性生命形态的冷峻反思、苦涩歌咏与艰难探索
——张冀雪小说论
杨若蕙
(甘肃政法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广袤苍凉的大西北,一直以其辽阔的地域空间、恶劣的生存条件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而被外界所误解和遗忘。西北的农村,更是长期被认为是贫穷、落后和愚昧的象征。西北的文学,虽然也曾一度引起学界和读者大众关注,但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西北文学中由数代作家倾心建构的“西部精神”,也只是与男性结缘,是男性的力量、野性与剽悍的代名词。而西北的女性,却始终在西部文学中处于被遮蔽或隐性存在状态,即便出现,也似乎只是可有可无的附属与点缀。可喜的是,当代也出现了致力于表现西北女性生存状态的作家,张冀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张冀雪并非土生土长的西北人,她由河北来到宁夏,继而在陕西、甘肃、新疆辗转半生,创作经历20余年。写作伊始,张冀雪便立志“关注西部”,并“指向了大西北那些偏僻的干旱贫困的被现代文明遗忘的山村角落,一头扎进了几乎是与世隔绝的文化封闭圈内,以她独特的敏感与洞察,把其中人物的生存状态艺术地呈现在读者面前”[1]92。张冀雪尤其关注西北女性,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生命形态的冷峻反思、苦涩歌咏与艰难探索,不仅抒写了她们由失语到言说继而走向自我探索的艰难过程,更体现出西北文学在女性形象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的坚韧努力与初步成果,因而有着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一、无处逃遁的喑哑受困者的冷峻反思
(一)生存的艰辛
西北以其独有的地域特点,造就了西北人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更决定了西北女性的生命形态。西北的自然景观曾经是塑造西北文学特有风格与精神的重要因素,“与其他地区相比,产生于这些地区或描写这些地区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有悲壮、苍凉、雄奇、浩瀚等共同的特点。”[2]5但对于张冀雪及其所塑造的西北女性,特别是西北乡村女性来说,则使她们成了无处逃遁的喑哑的受困者,只能在严峻酷烈的自然条件下默默忍受。大西北的乡村,伴随着女性的生存常态就是令人心悸的空旷、使生命枯竭的干旱和无情肆虐的风沙。枯焦的生命注定与柔情温婉无缘,乡村女性只有像西北汉子一样坚韧强悍,才有可能抵抗极端生存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生存压力的酷烈更使西北乡村女性无暇乃至无力去言说和叫喊,只能默默承受,无奈地向命运低头。《活水》中没有名字的“女人”,随着汉子,带着娃崽,赶着装有全部家当的驴车,离开了干的冒烟、“活得孽障”的庄子,只为寻找一口活水。“女人”既是无名的,也是无言的,她只能“痴痴地坐在车尾,痴痴地盯牢了越来越远去了的那些山疙瘩”[3]109,能否走出困境,女人并不知道,她只能在未知的命运中挣扎乃至低头。既然前路茫然,受困的乡村女性也就只能被迫返回,无奈地困守。《回家的路》中,“女人”尽管瘦得像一头母山羊,弯曲的腿拖拉着像一截枯树枝,依然不得不忍着病痛,除了给一家老小十口人做饭,还要放着六十只羊。“女人”终于决心要去看病了,和男人背着案板、铁锅、粮食和油桶出发,可空旷的天底下,“公路像条青灰色的带子由老远的地方扭了来,穿过沙野地就一直伸向天边。”[4]98对于陌生公路、车辆和未来的恐惧,使“女人”明白,“庄户人的孽障日子得有个长性。”[4]99贸然前行,失去了熟悉的路,就可能回不了家,也就没有了生活。只有重新回家,守着这份“孽障”,才是唯一的“路”。
(二)被围困的灵魂
西北乡村的女性不仅被贫瘠的土地困住了手脚,使得她们只能围绕着一盘石磨原地打转,还有与外界的信息隔绝,使她们变得木讷寡言、沉静忍耐甚至麻木不争。她们执拗地以自己固有的认知方式要求自己,也以此评价别人。她们顽固地拒绝所有陌生的、新鲜的、不同于己的人或事,竭尽全力用自己的善良和坚韧维护现存的一切。《豆子的乡土》犹如一篇寓言。外来的艺术家想到哑石村一探究竟,盘桓了“三七二十一天”才找到进村的路,又住了“二七一十四天”,却最终一无所获。哑石村的男女老少无一例外地抄着手,笑呵呵的模样,并不多说什么,问起什么来,都只是回答“谁知道哩”。哑石村的“奶奶”年岁大到无人能说清楚,她的地位更是不可撼动。她一再告诫爱读书的痴望远方的豆子:“鬼狐把魂迷了去,就回不了家了。”[4]122她断言唯一跟着戏班子走出大山的凤儿是“野女子”,就此泯灭了唯一想要走出去看看的豆子的意志。“奶奶”就是西北乡村女性生活传统的象征,她的长命百岁和崇高威望,虽使固守乡土的女性灵魂不会迷失,却也造成了她们生命形态和心灵世界的愚弱板滞与裹足不前。
(三)低下的生命轮回
西北乡村女性的喑哑与受困还来自父权文化的围剿。尽管有了法律的权利保障,但男权中心文化和男尊女卑的道德习俗依然根深蒂固。在张冀雪笔下几乎与世隔绝的西北乡村,“女人们”生活在男人的天空之下,不仅每天要起早晚睡,做饭、缝衣、挑水、烧炕、拉土、垫圈……永远有做不完的农活、干不完的家务,还要承受脾性暴烈的西部汉子家常便饭一般的怪罪和责打。“女人们”不仅要承受物质生活中的苦,还要忍受宿命一般难以改变的生命悲剧,即便是现代文明的力量近在咫尺,面对复杂顽固的传统习俗,也束手无策,爱莫能助,只能是一声叹息。作品《我在甘草铺的时候》中,十七八岁爱读书的俊秀姑娘王改改,几经抗争,却最终屈服于父亲安排的换头亲,嫁给了“把头一个媳妇经常打得浑身没块好肉”的沾满恶习的三十岁光棍。母亲虽然心疼改改,却也只能抹着眼泪同意,并且以亲身经历劝慰女儿:“我年轻的时候也哭过、闹过,挨的那个打呀,就别提了!可是……还是依呀!”[4]109“我”是改改的老师,想尽了办法,依然无能为力。当“我”求助于校长时,校长也只是敷衍:“这种事多的是啊……”甚至在十多年后,当“我”向一个妇女干部打听改改时,她还用平静的语气和淡漠的神情叹气道:“唉,现在,这样的事还有的是……”一代又一代的西北乡村女性,在相同的生存环境和道德习俗中被禁锢着,被压制着,一遍又一遍地上演着相同的命运悲剧,难以逃遁,也无处可逃。
西北乡村女性卑微、沉默的生命轮回在苍黄的大地上,喑哑就是她们不变的生存状态。她们有语言,会哭泣,却无法言说;她们有力量,能吃苦,却走不出困境。张冀雪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温暖细腻的情感,用心去贴近这些低矮屋檐下受难的灵魂,彰显出一种宽厚的悲悯情怀,也体现出对改变西北乡村女性命运的急切期待。但对于造成西北乡村女性喑哑受困者命运形态的内外原因,她更是进行了冷峻反思,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
二、满身伤痕的出逃与重生者的苦涩歌咏
(一)不屈的歌者
张冀雪在西北乡村有着较为长久的生活经历,对西北乡村女性有着浓厚的爱意和感情。她知道她们的命运困境,更熟悉她们身处困境时的真实想法和内心情感。她知道,这些与她心灵相通、血肉相连的姐妹们,当外在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她们一定会拼尽全力试图逃出陈旧的生命窠臼,哪怕为此而伤痕累累,也在所不惜。所以,她不仅要反思,更要歌颂,歌颂这种西北大地养育的生命韧性,尽管其中充满了苦涩与惨烈。
长篇小说《将军戈壁》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西北大地乡村女性感天动地的生存史。这里有在长征中失散的红军女战士唐光秀,在将军戈壁备受屈辱的艰辛生存中仍坚持寻找组织的坚定信念;有援建大西北的大学生施燕芬,将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了戈壁雪野深处;更有那历经命运折磨最终血性反抗的贺三巧。在当地人中,贺三巧出众而又惹眼,不仅模样俊秀,还性格开朗爱笑。就是这样一个会扭秧歌爱唱歌、积极参加扫盲班和热情投入区镇工作的女子,不仅招来爱忌妒小心眼的丈夫毒打,也招来了周围人鄙夷嘲讽眼光的践踏和亵渎。在工作接触中,她仰慕爱恋儒雅的区书记于青田,却只能在远处默默地投去一眼深情。酗酒丈夫的再一次毒打并伴随着的一声声“烂婊子”的人格侮辱,成为压垮她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贺三巧举起利斧,砍死了丈夫。作为杀人犯,贺三巧被判死刑。刑车上,她昂首直立,迎向冷硬劈人的西北寒风。行刑前,她又唱起了最喜欢的“花儿”,用这最具大西北风格和最能代表大西北乡村女性真挚心声的乡野山歌为自己送行,也是在为自己卑微而又刚烈的生命浴火重生祝福。新时代的到来和新政权的建立为西北乡村女性逃离传统枷锁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但她们要想真正获得独立与重生却面临重重艰辛,需要踏着布满荆棘的道路勇毅前行,才能无愧于这新时代和新政权所提供的伟大历史机遇。贺三巧的行为是过激的,也是偏颇的,甚至是变异的,但这正是处在成长、变化和转型中的乡村女性最为可能的人生选择。这一选择尽管带来了惨烈的后果,却也预示着属于贺三巧们的春天已经来临。
(二)觉醒者的抗争
“自古以来,妇女的解放,从来就是人类文明的标尺。千百年来,人类社会进行了一次次的努力。西方世界,已经颇见成效地大致实现了男女平等,实现了民主与自由在两性间的公正施与。而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广大乡村,这几乎还是纸上谈兵。”[5]随着时代进步,西北乡村世界已然苏醒,乡村女性的自我意识、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如何对待两性关系,也就成了体现女性觉醒的重要标尺。小说《黑荞麦》细腻描写了这个过程的艰难曲折。主人公黑荞麦是典型的西北乡村女子,皮肤黝黑,手脚粗大,能吃苦,肯干活。因为在暴风雪之夜帮着随孩孩家找回了迷散的羊群,被随孩孩的娘相中,定下了亲事。随孩孩是县上工作的穿制服的公家人,他被迫同意了这门婚事。可是,他长期住在县城,偶尔回家,也只是漠然蔑视地对待妻子。黑荞麦恪守妻子本分,照顾生病的婆婆,养育两个尚年幼的小叔子,担负起养家的重担。又一个风雪之夜,善良的黑荞麦救下了陷入困境的来自内蒙古的老李,惺惺相惜的两人互生好感,黑荞麦第一次有了发自内心的笑容,第一次心中生出了怨恨:“随孩孩呀随孩孩,俺黑,俺丑,可俺也是个人呀!”[4]268她头一次觉得自己也是个女人。但黑荞麦还是无奈地拒绝了老李的示好,老李只好远走他乡。但当随孩孩因为在县城犯了男女作风问题而回家,想要和黑荞麦和好时,黑荞麦拒绝了,她抬头挺胸地走了,去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幸福,再也没有回村里来过。黑荞麦是带着心灵的创伤离开的,她以决绝的态度和坚定的脚步,开启了西北乡村女性寻求自我的芳香之旅。
(三)希望的重生
乡土文学是时代转型和文化冲突的产物。“只有当社会向工业时代迈进,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时,乡土文学才能在两种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凸显其本质的意义。”[6]1中国社会在日益完成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广大乡村发生着巨大改变,乡村女性也将面临新的困境。“作为商业化大潮的首当其冲者——女人,她们不仅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体与推进者,而且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商品社会不仅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而且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必然再次以女人作为其必要的代价与牺牲。”[7]375当农村男性大量涌入城市,传统的男耕女织模式,就演变成了男工女耕,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留守也就成了乡村女性的生存常态。在这样的生存常态下,乡村女性只有历经挫折的自我独立,才能找到重生的机会与可能。小说《新麦地》中,麦香是典型的留守妇女。丈夫祁三娃到省城打工,一去半年,杳无音讯。各种猜疑折磨着麦香,她决定去省城寻夫。庄子离城太远,要先走乡间小路到公路,再坐汽车到县城,最后坐火车到省城。麦香从未独自出过远门。第一次寻夫,胆小惶恐的麦香只到县城就被吞噬了,钱包被偷,城市以极不友好的冷酷将她赶回了乡村。第二次寻夫,麦香冷静、坚定和成熟了许多,但当她来到省城,得到的却是丈夫早已被抢劫遇害的噩耗。寻找丈夫的精神支柱被彻底击碎,她回到庄子,“头一件事就是一头扑到那块已经平整过的坡上的土地。育种、施肥……麦香默默地,靠着自己柔弱的肩膀,种下了一茬新麦。”[8]102麦香和新麦,构成塬上一道极其坚忍的风景。麦香虽然失去了丈夫,但未自怨自艾;她虽然满身伤痕,却获得了精神重生。不靠男人只靠自己坚强生存,这是千百年来女性最伟大的胜利。认识到自己的价值,珍惜自己的自尊和独立,才是乡村女性唯一的精神支柱和人生出路。为此,西北乡村女性付出了无数血泪代价,路虽曲折,但充满希望。
三、漂泊返乡的现代知识者的精神探索
(一)诱惑与坚守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乡土就是永远的精神家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梦绕魂牵。张冀雪的大半生都属于西北乡土,当她在都市中遭遇困惑乃至困境,返回西北乡土便是她寻求精神探索的唯一可能。甚至只有在西北乡村女性身上,她才能找到精神的寄托与生命的方向。张冀雪的这一类小说近乎作家的灵魂自叙传,她的此类小说中都会有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担负着历经漂泊后重返西北乡土的精神探索者的重任。这个“我”往往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西北的大漠戈壁,迎接着荒野疾风,寻访过边防哨卡,甚至亲历地下六百多米的矿坑油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受这里的粗粝与柔情,同时也获得了丰富的精神滋养,找到了人生的指向和生活的支点,从而使生命的底色更为坚实和丰厚。
《关于汤的神话》是犹如梦魇一般的呓语,断续讲述着“我”两次离开“汤”,但最终未能成行的心灵历程。“汤”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地方,西北风一夜之间就刮光了树上还不太枯黄的叶子,人们的生活一日如同百年,缓慢寂静,没有任何色彩。外面的世界既有遥远的大海,也有朋友的等待和守候。但城市的召唤就像塞壬的歌声之于奥德修斯,既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也是致命的无形陷阱。“我”知道,只要能走过第一个车站,朋友一定在那里等“我”。但每一次刚刚踏上旅程,“我”都会感到无比的莫名的困倦。“汤”用她的匮乏,孕育了“我”精神的全部,已成为“我”的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旦离开,“我”就会失去生命的光泽,呈现出萎靡的面容与神情。“我”的再次试图离开,是因为那远方的泉水,喝下它可以使人忘记忧愁、没有烦恼、永不衰老。但这一次,“我”连第一个车站也没有到达,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了并不想抛弃的东西,一种奇特的魔力使“我”宁愿留在“汤”,成为一只琥珀中的昆虫。作者用塞壬的歌声做引子,意在指明诱惑与坚守的矛盾。城市的诱惑美妙而又动人,抵抗这诱惑需要拼尽全力;坚守在乡土需要忍耐苦难荒凉,却能够感受到温暖和安宁。在这致命诱惑与苦难坚守中,“我”选择了后者,也就意味着获得了精神的支撑。
(二)出离与返乡
张冀雪并不掩饰西北乡土的荒凉和人们对她的偏见,但在经历了都市的冷漠、欺骗、逼仄后,却让“我”更坚定了重返的决心,因为只有这里才是诗意的栖居,才具有自我救赎的力量。《秋水草地》中,“我”十七岁时曾在“金色之湖”插队,得到过慈祥的母亲河西大妈的守护。时隔多年,当“我”经历了失败,而又失败的那么惨重,那么凄绝的时刻,作为单亲母亲的“我”,带着幼小的女儿,奔赴路面干裂、土尘依旧的梦魂萦绕的西北故土,回归那滋润着“我”的心的“秋水草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迅猛发展,城市高度繁荣,相伴而生的是社会环境中的丛林法则、人情淡漠、利益当先思想等等,这些无时无刻不折磨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当“我”惶惑蹒跚地努力走进都市时,才发现都市并不是属于“我”的世界。在经历了一次一次的失望,一重又一重的打击后,“我”用尽最后的力气,经过两天两夜的路程,赶回了敞开胸怀默默迎接着“我”的数千里戈壁。虽然河西大妈已化为坟茔,“我”却重获生命的力量,真正拥有了沉静和无畏。依然美丽的秋水草地使“我”获得了自我拯救的力量,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也是对诗意化乡土的追寻,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返乡之旅。
(三)探索与反思
张冀雪带有灵魂自叙传色彩的精神探索也不只是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的呓语式作品中,也呈现在颇具先锋色彩的实验性文体中。在外人眼中,西北往往被赋予了神秘、奇特、魔幻等文化色彩,从而与先锋小说的艺术气质不谋而合。张贤亮曾盛赞“南有残雪,北有冀雪”[9]1,便是对张冀雪小说创作中先锋艺术倾向的肯定。张冀雪的带有先锋色彩的精神探索既与焦虑、孤独、恐惧、死亡等先锋文学的精神指向一致,又有着源自西北乡土的个人独特性。她往往通过一位永远游走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现代女性“我”的心灵历程,在不断反思和重新审视西北乡土的同时,思考生存的意义与生命价值的实现。《石头城堡》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天边外·在路上”[10]130的叙述模式,表达作家关于生存的焦虑、生命的轮回、时间的循环、信念与意志等的思考。因为干旱和瘟疫,麦麦与村人被迫踏上了迁徙之旅。他们要去一个叫“石头城堡”的地方,但这个地方距离有多远,究竟在哪儿,谁都不知道。这些在沙野地里生下来的人们,沉默得像一具具走动着的木乃伊。途中不断有陌生人加入,不停有人倒毙,也有陌生人的劝阻。他们经历过找到一个枯竭、颓败的古城堡的失望,也有过看到海市蜃楼的短暂惊喜,还留下了伊萨老爹悲壮的死而不僵的身躯,但他们也还只是在宿命般地默默前行。麦麦作为整部作品的灵魂人物,仿佛就是为了沙漠中的寂寞、宁静和茫然而存在。那有着一双美丽的湖水一样灰蓝眼睛的骁勇的沙漠斗士,就是支撑麦麦活下去和走下去的信念;那只搭在麦麦肩上的粗硬的手,则象征着心灵消耗殆尽的人们只有靠着相互扶持才能抵达那迢迢无望的终极。在这条无尽跋涉的路上,人们个个脸色灰黑消瘦,眼睛烧得通红,肩头和双手伤痕累累,凝住的血混杂着金色的土。对此,麦麦不禁痛苦质问:“为什么与生俱来要伴着这无穷无尽、永不休止的苦痛呢?”[4]342最终,麦麦在途中生下孩子后倒下,完成了生命的轮回,这支行进的队伍也因此而始终保持着一股浓浓的生命的气息。石头城堡虽远在天边外,麦麦最终没能抵达,但她生命的意义,永远都在路上。《石头城堡》“传导了始终无以抵达内心化的精神寓所而始终不能摒弃心灵净土的渴求这样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执着的求索意识。”[11]这种体验和求索,正是西北乡土赋予张冀雪先锋气质,使她在重返乡土中坚持着一种精神探索的立场和姿态。
四、结 语
张冀雪以女性生命形态和命运探索为中心的小说创作,以灵动多样的艺术形式,融合了地域特征和时代变迁,“通过爱情、婚姻、家庭表现个性的觉醒和张扬,写出西北农村社会历史的进步与道德审美评价这一二律背反中的动荡与困惑。”[1]92同时,通过重返西北乡土的“我”,折射出现代知识女性面临生存困惑与意义危机的执着探索,体现了作家在孤绝中坚持追求精神勘探的个性气质。张冀雪的创作虽不免有情节较单薄、人物形象较单一等局限,但并不妨碍“在西部领域的女性写作方面,她作为开拓者的存在,始终都是色彩鲜明的一面旗帜,号召着源源不断的一代代作家投身麾下,为之辛勤耕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