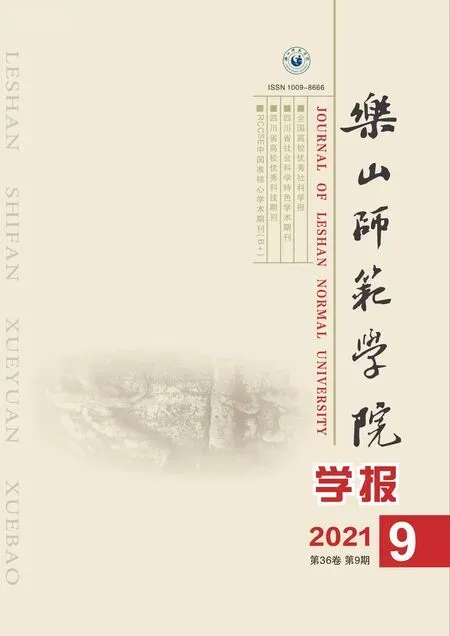苏轼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苏祖川
(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重庆 400020)
苏轼的法治思想长期被掩盖在其文学成就的巨大光芒之中,但宋代士大夫多具备较高法律素养[1],而苏轼更是具有高度的法学理论修养,且具备长期从事立法、行政和司法工作的实践经验。纵观苏轼一生,其少年自科举入仕途后,在开封等地掌管过基层司法刑狱,又从事过史官等清议工作;既任过杭州太守等地方主要行政官员,也任过中央政府六部的高级官员。苏轼参与过王安石变法等最高层的政治活动,又对中低级的行政、司法活动有所亲历体察。苏轼熟悉宋代法律,其法治思想见诸他的著述、诗文、奏状及实践活动中。考察苏轼的法治思想,对开拓苏轼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发掘苏轼在古代中国法治思想史上的贡献,都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的法治思想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考察其整个思想系统,苏轼的法治思想有着贯穿一致的基本精神。苏轼的法治思想仍归属于儒家法律思想的体系,但承继孟子学说较多,和有宋一代王安石等偏重法家理念的思想家具有显著区别。苏轼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民本、重礼和轻刑三个方面。
一、民本思想是苏轼法治思想的基石
苏轼在讨论法治问题时,继承孟子的进步思想,将民本思想作为构建法治思想体系的基石。孟子在儒家学派中,明确的提出并阐发了民本思想,其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民贵君轻”的命题中。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328,将“民”放在首要位置,置于“君”之前。根据这一命题,孟子进一步推演出有关君臣、君民关系的诸多子命题,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2]186又如:“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2]42在儒家学派中,孟子的观点是相对激进的。这一系列体现民本思想的命题,充分肯定了民众反抗专制君主暴政的正当性,将民众利益置于专制君主一人利益之前。
苏轼接受并发挥孟子的观点,贯彻民本思想,以此为出发点阐发了一系列法治观点。
首先,苏轼从民本思想出发来解释君民关系。封建社会中,君民关系是构建任何法律治理结构的基本制度前提。苏轼认为,在封建社会进行有效法律统治,必须从民本思想着眼,率先考虑君民关系问题。君民关系中,民心又决定了君主的存亡。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有一段关于君民关系的著名论述:“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人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3]730从上引论述可以看到,苏轼的君臣观与孟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苏轼明确的提出,失去人心的君王就不是君王,而是独夫。这里的独夫就是孟子讲的“一夫”。失去人心的君王,就成为民众的“仇雠”,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臣视君如寇雠”。
其次,苏轼认为,脱离了民本,就谈不上法的长期有效治理。苏轼多次以商鞅、韩非等为例,从反面论证这个问题。如苏轼论商鞅,“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3]730据此,苏轼又提出:“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3]103苏轼将秦代统治和商鞅、韩非作为反面例子。认为既然法的统治必须建立在人心基础之上,没有民本作为法律的支撑,法律就不能作为一种长期有效的治理手段,相反,会给整个社会和君主带来不良的后果。商鞅等缺乏民本思想的法治手段是难以持久的。
其三,民本决定犯罪产生原因。苏轼认为,犯罪产生和法律的无法施行,在于民本出现问题。政府必须考虑民众是否被政府的错误政策逼到了犯罪的境地。在论述盗贼盛行问题时,苏轼明确指出税负沉重导致了盗贼的产生,也即“旧时孤贫无业,惟务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稀少。是时告捕之赏,未尝破省钱,惟是犯人催纳,役人量出。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3]754苏轼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要解决盗贼这样的犯罪问题,要达到法的有效施行,必须让利于民,解决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即“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3]135。
其四,苏轼比较注重考虑立法和执法活动对民众产生的实际影响。苏轼在评价法律问题时,不仅从理想化角度考虑,也多注重从实际后果考虑问题。这个思想特别集中于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的表现。王安石作为古代的改革家,其出于富国强兵目的施行变法。苏轼作为变法的强烈反对者,并不反对变法目的,而是反对变法措施在实际运行中会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的后果。这是苏轼法治思想的一大可贵之处。如针对青苗法,王安石变法措施规定农户自愿借贷,不得对不愿意借贷者强制抑配,但苏轼认为此项措施在实际施行中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政策走样,造成强制抑配。苏轼尖锐地指出:“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3]735并断言:“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3]735后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诸多苏轼所预言的弊端。又如苏轼批评农田水利法,认为农田水利法兴水利,会对部分田地物权带来混乱,造成纠纷,且增加不必要的诉讼。“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3]732也是从法律实施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出发来考虑问题。
二、“礼本法末”——苏轼的重礼倾向
礼与法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古代中国法治思想史的一个大问题。针对礼是否是一种法律渊源,学术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是否将礼作为一种法律渊源,都涉及到理论上如何看待礼法关系、礼有何具体作用以及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如何处理礼法关系等一系列子问题。苏轼在礼法关系上,明显持儒家重礼的观点。
首先,苏轼坚持礼本法末论。在讨论礼法关系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时,苏轼明确提出:“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3]50苏轼用“法者,末也。礼者,本也”,概括了其对礼法关系的基本看法。苏轼又进一步认为,如礼法关系处理不当,则会出现毁灭性的后果,苏轼提出了“昔者汉兴,因秦以为治,刑法峻急,礼义消亡,天下荡然”[3]232,也是以秦朝忽视礼造成破坏性后果为例,从反面加以论证礼比法更为重要。
其次,苏轼从儒家人性论角度对礼本法末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在理解礼本法末的依据时,苏轼从儒家人性论的角度来进行阐发。苏轼还是承继孟子的主张,认为人有不忍之心,故产生礼,就是所谓“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3]102苏轼指出:“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3]34这是强调依靠律法本身不解决根本问题,只要以礼才能弥补法的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
其三,苏轼处理实务中的礼法问题时,明显表现出以礼断案的特色。苏轼的实务主张可以与苏轼著述中有关礼本法末的正面阐述互为印证。这方面有好几件比较典型的材料可以用来说明苏轼以礼断案的特点。
第一个案件是张诚一案。朝廷官员张诚一因“邪险害政,有亏孝行”,被除去观察使遥郡防御团练使刺史的职务,但仍旧担任了其他官职。苏轼的处理意见提出,张诚一多年来未安葬其亲生母亲,且张诚一在其母去世时并非离家赴远方任职,并非不具备安葬母亲的客观条件,张“冒宠忘亲,清议所弃,犹获提举宫观,已骇物听”。同时,苏轼在奏状中还提到,张诚一还被举报有打开亲生父亲的棺木以掠取财物的行为。此事也是人伦大防,“使诚有之,虽肆诸市朝,犹不为过”。苏轼认为对此事也应当一并查明,“使诚无之,亦当为诚一辨明”。故苏轼认为,张案涉及礼法人伦,张的行为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应当将张诚一交付司法处理。[3]776
另一个案件是李定案。李定作为政府官员,一直不讲明其母亲的姓氏来历,因此在母亲去世时也没有举行丧礼,李定本人也没有按丧礼在为母亲举孝时辞去官职,始终在任上,“强颜匿志,冒荣自欺”。苏轼对李定给予了强烈的负面评价,认为李定“身负大恶”,是“无母不孝之人”。指出:“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教,为害不浅。”苏轼还提到,虽然李定曾经在其父亲年老,要求辞官赡养父亲,也就是具有“乞伺养”的行为。但其父亲当时已经年满八十九岁,人所共知,李定系被迫为之。不能因这一“乞伺养”行为减少李定不孝的罪责。苏轼据此提出了重罪的处理意见。苏轼认为,按照律法,父母死亡而隐瞒不行丧礼,应当处流刑两千里。而李定所犯的罪行,不仅仅是隐瞒不举行丧礼,而是连其生母是谁都予以隐瞒,因此达到不去官的目的。按举轻明重的律法原则,李定的罪行应当被处以比流刑两千里更重的刑罚。[3]777
从苏轼对这两起案件的处理意见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苏轼对违反儒家道德伦理的亲族案件,贯彻了其正面阐发的重礼的观点。苏轼在处理意见中一是对法律条文本身引用少,始终强调的是“孝行”“风教”等礼的概念。二是对违反礼的行为,苏轼都是要求从重处理的。这就比较明显体现了苏轼重礼的法治思想。
其四,苏轼针对一些具体的立法问题,从重礼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解读。这方面也保留了一些比较有力的材料。如苏轼强烈反对大臣擅自议论配享问题,认为法条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这是涉及到封建礼仪的大事,法条中规定此条,对礼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即“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庙,重朝廷,防微杜渐,盖有深意”[3]831。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苏轼对居丧问题专门所撰写的《奏状乞改居丧婚娶条状》。宋代曾颁布法令,允许祖父母、父母老疾的情况下,男子可以在父母丧期婚娶,以更好地赡养父母。苏轼从礼的角度强烈反对这一法条。苏轼认为:“人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释丧而婚会,邻于禽犊,此礼之重者也。是直使民耳,岂不过甚矣哉。”[3]1009-1010苏轼提出,成年男子完全不存在不再娶就无力赡养父母的问题,所谓在丧期再娶可以更好地赡养父母,无非是为了在丧期举行嫁娶的托词,本质上是以色废礼,有伤人伦之正。婚丧问题的立法必须在尊重礼的原则下进行。否定礼的重要性,随意立法,就会伤害到法的正当性。故苏轼认为该法条应当废止。
三、苏轼法治思想的轻刑观
轻重刑问题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各思想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苏轼从民本思想出发构建法治思想,其法治思想的推演自然倾向于轻刑。一般说来,法家推重重刑思想,儒家重视轻刑思想。苏轼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其法治思想也认同轻刑观,这也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同点。苏轼又属儒家学派在民本问题上比较激进的孟子一派,其倾向轻刑也符合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且苏轼本身具有多年的基层行政和司法经验,对民间疾苦,尤其是司法实务中的具体弊端,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这也是形成苏轼轻刑观的重要因素。
轻刑思想不仅仅是刑法本身严厉与否问题,一般还包括法网疏密、慎刑恤囚等几个方面。苏轼在这些问题上都有比较明确的阐发和论述。翻检苏轼的文章著述,其针对轻刑问题的论述比较多,有多篇专门针对轻刑问题的文章著述。我们认为,轻刑问题能够作为苏轼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在苏轼的整个理论体系和法律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苏轼在应试科举的《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提出了罚当从轻赏当从重等一系列的轻刑思想,认为:“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3]34如果说应试考试答卷尚不足以全面概括其思想体系,后来的种种文本都充分体现了苏轼的轻刑思想。
苏轼的轻刑观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立法应宽简,法网不应当过密过重。苏轼比较前朝得失后认为法网疏密与治理效果有直接关系。即:“《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断罪所用,至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而奸益不胜,民无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3]136
其二,慎重刑法,是维护统治的有效手段。苏轼认为:“凡为天下国家,当爱惜名器,慎重刑罚。若爱惜名器,则斗升之禄,足以鼓舞豪杰。慎重刑罚,则笞杖之法,足以震詟顽狡。若不爱惜慎重,则虽日拜卿相,而人不劝,动行诛戮,而人不惧。此安危之机,人主之操术也。自祖宗以来,用刑至慎,习以成风,故虽展年磨勘、差替、冲替之类,皆足以惩警在位。”[3]820
其三,司法实务中不宜过多使用重刑。苏轼在理论上对轻刑主张比较明确。认为不能随意施加重刑。提出:“自有刑罚以来,皆称罪立法,譬之权衡,轻重相报,未有百姓造铢两之罪,而人主报以钧石之刑也。”[3]972且苏轼明确反对肉刑,在有人提出恢复肉刑时,苏轼指出:“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3]731
苏轼在实务中对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处理则比较复杂。苏轼在担任地方官员时承担具体司法判案的职能。从现有材料看,苏轼在具体判案过程中对于聚众反对官府的民众,在一些场合处罚是相当严厉的,乃至于法外判案,加重处罚。如在《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中,苏轼要求对聚众反官府的带头者法外刺配,提道“谨按颜益、颜章以匹夫之微,令行于众,举手一呼,数百人从之,欲以众多之势,胁制官吏,必欲今后常纳恶绢,不容臣等大革前弊,情理巨蠹,实难含忍。”[3]842又如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也要求法外重处。提出:“欲乞朝廷指挥,盗贼情理重者,及私盐结聚群党,皆许申钤辖司,权于法外行遣,候丰熟日依旧。所贵弹压奸愚,有所畏肃。”[3]851但苏轼在诗文中,对司法被刑讯的民众又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苏轼有诗说:“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4]25反映了苏轼这方面的心情。
苏轼轻刑观在实务中的矛盾反映了其法治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士大夫阶级的轻刑观,在实务中必然遇到与现实执政需要的矛盾,难以真正的贯彻。当然,这也是整个儒家法治思想的矛盾,不为苏轼本人所独有。
其四,刑罚执行中,给予人犯相对温和的待遇。苏轼在其诗中,对囚犯表现出一定程度同情。而其在执政中,也重视对囚犯的人道待遇。苏轼集中有描写说,“熙宁中,轼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上,诗曰:“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4]23苏轼著名的《乞医疗病囚状》也是比较典型的代表。苏轼针对囚犯在狱中病疾死亡问题,专门上表。借前朝皇帝的诏书,在文中较充分地阐发了病囚医治轻刑的具体理由。对病囚问题产生原因比较明确的说明,提出了相对周全的解决方案。[3]764-766
苏轼也多次阐述了应当采取轻刑的原因。
第一,轻刑符合儒家道德和法治体系。重刑违背了儒家法律道德,“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无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责者。苟以时言上,检视无他,故虽累百人不坐。其饮食失时,药不当病而死者,何可胜数?若本罪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异?积其冤痛,足以感伤阴阳之和。”[3]764
其二,重刑本身不足以威慑民政减少犯罪。苏轼提出:“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皆未见其益也。”[3]754苏轼总结说:“乃知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其间凶残之党,乐祸不悛,则须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举皆阙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3]754
苏轼甚至举军法为例说明问题,认为以军法之严厉都无法解决军人逃亡问题,重刑更不能解决民政问题。“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3]734这也与其民本思想呼应相和的。
四、结语
综上,苏轼的法治思想承继孟子这一儒家激进学派,在法治思想中贯彻了民本、重礼、轻刑三个方面的基本精神。苏轼应当说是儒家孟子这一学派在法治思想上的典型代表。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