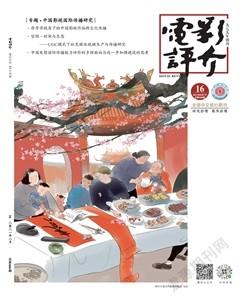荒原与小城
宋珊珊
一、诗电影:突破传统叙事的诗意实验
在世界电影史上,许多国家都不乏被称为“诗电影”的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诗电影”这一概念在学界历来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且不同的影视工作者对“诗电影”的理解有很大不同。在帕索里尼看来,电影的语言特性本身便应该是“诗的”,这里所谓“诗的”,主要指的是电影的“非理性”色彩,这是从电影的梦幻性本质出发而做出的评论。[1]在前苏联导演爱森斯坦那里,电影中的“诗意”则主要是借由节奏、隐喻和象征来实现的,更像是一种剪辑手段,用以突出强烈的斗争思想,表现强烈的革命情怀。而到了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作品中,“诗意”则体现为一种诗性智慧,与隐喻蒙太奇学派不同,他排斥“象征、隐喻之类”可能让电影“失去自我”的东西,强调对自然世界的“直观观察”,以此激发观众心中源自生命本源的想象力。[2]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境下,人们对“诗电影”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思考。然而,纵使这些思考千差万别,还是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它们都关联着人们对诗歌本体的认识。从诗歌本体出发,可以发现,“诗”的语言特性可以是“非理性的”,“诗”中的意象又可以是“隐喻的、象征的”,而“诗”的创作本意则可以是由“人类生命本源”中生发出来的。这样看来,上面这些大师关于“诗电影”的阐释虽有不同,却并不矛盾。
为了将“诗电影”的功能阐释得更为清晰,不少学者在介绍这种电影风格的时候,或直接或间接地采用比较或排除的思路。比如,帕索里尼就曾强调,只有“诗的”电影语言才可以将电影的表现力从“传统叙事程式”中解放出来[3]。在爱森斯坦看来,“诗的方法”使“电影暂时摆脱了纯粹的戏剧和剧作的结构”[4]。同样,塔可夫斯基将“诗意”描述为一种有别于“传统戏剧逻辑”、不同于情节上“呈线性发展”的叙述方式[5]。虽然这些导演对“诗电影”的具体风格观点不一,但从他们的评述中,读者还是可以看到,所谓“诗的”,基本上是与“叙事的”相对,是与传统的叙事原则以及叙事方法相抗衡的。电影若可以被称为“诗的”电影,也就说明它具有“非叙事”的风格特征。就像是在诗歌中,诗人不是没有描写,有时甚至有很多描写,但是这些描写并非是按照叙事语法组合起来的,而是作为意象,按照抒情语法进行排布的。从诗歌的功能来说,大部分诗歌的任务并不是要让读者完整地了解某一事件,而是去品味和思考。所以,诗歌里有反复的咏叹,有借此说彼的隐喻,有一个个意象,按照一定的韵律进行罗列与排布。所以,读者在读诗歌的时候,需要思考,需要去品味意象背后的内容和情感,需要自己去填补诗歌里没有言明的细节和情绪。
简言之,在“诗电影”中,叙事不是目的,激发审美、启发观众思考才是重点。在“诗电影”中往往体现着这样一系列特征:有着强烈的艺术探索与实验气息,有突破传统叙事的风格特征,有遵循着诗意节奏的场面调度,有包含象征性的镜头剪接和细节处理等。在《影子》和《小城之春》中,导演分别打造了荒原和孤城的意象,这两种意象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仿佛诗韵般反复吟咏,展示着导演的艺术探索,也对抗着作品的叙事性和戏剧性。
二、真空地带:诗电影中的时空实验
(一)被遗忘的荒原
《影子》这部作品改编自乌克兰作家米哈伊洛·科丘宾斯基(Mikhaylo Kotsyubinsky,1864-1913)的同名小说。作品描述了生活在乌克兰客尔巴阡山脉的胡楚尔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由于父辈种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男女主人公不能美满结合,后来男主人公伊万前往他乡做苦力,女主人公玛莲赫卡则意外落水身亡。面对玛莲赫卡的死,伊万十分悲痛,且久久不能平复,直到遇见剧中的第二位女主人公巴拉格娜,伊万才再次燃起结婚的冲动。然而,伊万难以忘记玛莲赫卡,他也不能给予巴拉格娜和谐的夫妻生活。巴拉格娜最终背板了伊万,而伊万最后也被巴拉格娜的情夫所砍杀。
作为一部经典的诗电影,这部作品的艺术实验气息十分鲜明。而要说明作品所蕴含的实验精神,又不得不先谈谈它作为一部诗电影的历史沿革。从历史沿革上说,乌克兰地区的诗电影与前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艺术创作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的蒙太奇电影学派兴起之时,其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甫仁科便被誉为“乌克兰大地诗人”,他在银幕上饱含深情地描绘了乌克兰的土地、人民以及社会革命景象。杜甫仁科与同时代的爱森斯坦以及普多夫金一起,作为前苏联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蒙太奇镜头的缔造者,深刻且持续地影响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前苏联地区的影视创作。而《影子》的导演帕拉杰诺夫正是于前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学习期间,直接受教于杜甫仁科和普多夫金。然而,即便如此,观众依然不难发现,《影子》与前辈大师的诗电影作品有多么不同。不论是杜甫仁科还是普多夫金的作品,其中都充满了昂扬的社会革命精神。这些作品着力于刻画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面,书写人民革命,具有革命史诗般的气质。而帕拉杰诺夫的《影子》既没有直接描写革命,也没有针砭时弊。与此相反,导演选取了一个发生在遥远山区部落的爱情故事加以处理,并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以及社会革命相距甚远的故事空间。这一实验所带来的影响醒目且深远。1965年,同时期的苏联著名导演塔尔可夫斯基就曾评价道,这部作品连同此后帕拉杰诺夫的《石榴的颜色》,“先是影响了乌克兰,然后波及苏联全国,最后影响了全世界”[6]。导演帕拉杰诺夫也是由这部作品开始,享誉世界。
在《影子》这部作品中,帕拉杰诺夫对时空的处理十分耐人寻味。通过这部作品的全名——“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观众可以感受到,导演力图描绘一个被忘怀了的、祖先的世界。导演并没有仔细地去界定这些祖先具体属于哪个历史年代,作品也没有意图指出他们居住的具体区域,只是在电影开篇的背景字幕中简要交代了,“这是乌克兰人的祖先胡楚尔人曾经栖息的客尔巴阡山地的某个角落”,并解释道,“客爾巴阡山脉居民,仿佛生活在卡吕普索岛与世隔绝,就连上帝也遗忘其存在”。
在电影中,这个故事空间具体被描绘成一片荒原,荒原上有村庄院落、有山川河流,春季有开满鲜花的山坡,冬季更有铺满白雪的旷野。大自然的寒来暑往自成一体,在这里居住的人们的生活,也如大自然一般,自成一体。《影子》的故事情节自伊万哥哥和爸爸的葬礼开始,于伊万本人的葬礼结束。这种设计更能让人联想到,正是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胡楚尔族人一代代出生、一代代成长、一步步走上人生高地,继而慢慢老去,最终被埋葬在这里,走完一生。在剧中,除了有限的几位主人公,其余的人皆无名无姓。通过这些处理,电影中的故事空间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剧中的这些所谓的祖先的影子,看起来不像被刻在历史丰碑上的祖先,而更像是一组模糊的、遥远的概念,一组远离现实的概念,或者亦可以说是一组对抗现实的概念。
(二)孤独的小城
《小城之春》这部作品描绘了中国南方一个无名小城里的一个欲言又止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周玉纹虽然已嫁为人妇,然而,其对丈夫戴礼言却没有多少感情。而随着昔日的情人,同时也是自己丈夫的至交好友章志忱的到来,她的心中再次泛起波澜。但最终,故事以昔日情人的主动离开,以及小城生活的平复收场。
与帕拉杰诺夫的《影子》相似,《小城之春》的创作风格在当时中国的艺术环境中也属于一种时代强音的变奏,有着鲜明的实验气息。导演对于时空的设定也历来为众多电影研究者称道。从人物的对话、着装,以及故事中的生活设施可以判断,小城故事发生的时间大致与作品创作的年代相符,但小城的具体位置却无从得知。从始至终,这小城中入镜的,只有五人——主、妇、客、妹、奴。除了角色构成的高度浓缩之外,影片中的物象也是高度浓缩的,复调式地反复描摹着破败的城墙和小院,而具体的社会环境面貌则被导演隔离在镜头之外。《小城之春》中,破败的城墙看似不堪一击,却像围城一样,围出了一方孤独的天地,城里的人,走不出去,城外的人,留不下来。这些高度浓缩的处理,也让费穆笔下的小城,如帕拉杰诺夫的荒原一般,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概念性空间。
《小城之春》这部影片的实验性在今天广为称道,但在当时却是毁誉难量。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前苏联的电影理论,尤其是蒙太奇理论可以说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电影理论”[7]。这些电影理论被介译到中国的同时,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强音,弊病丛生的社会现实得到刻画,一大批有着革命觉悟的无产阶级人物被塑造出来。而费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展开了他的影视创作和探索。根据留存下来的评论资料,可以了解到,费穆早期的作品也精于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他曾专门在电影技术上下功夫,并避免凸显影片的戏剧性特征。不过,在此之后,费穆也曾拍过一批京剧艺术片,以及一些包含戏剧性冲突的作品,如《狼山喋血记》等。按照陈墨的说法,这种看似倒退的艺术实验,实际上体现着费穆对“影”“戏”关系的重新思考[8]。或者说,这体现着费穆对电影的写实功能和中国戏剧的写意功能的重新衡量。经过这些衡量思考,费穆最终创作出《小城之春》,然而,即使《小城之春》是费穆的又一次实验探索,这部作品也已经与作为时代主流的现实主义风格相去较远了。
程季华在其1963年写就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中曾这样批评过费穆的《小城之春》,他指出,这部作品“反映了费穆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两重性及其软弱的性格,反映了他在解放战争的伟大时代中心情的苦闷、矛盾、灰暗和消沉”[9]。但从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小城之春》这部在今天看来举足轻重的作品,在当时并不是作为既有的艺术主流的一部分出现的,而是作为相对另类的,游离于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之外的一种艺术尝试而出现的。
三、世外之地:民族文化安放的所在
在《影子》和《小城之春》中,帕拉杰诺夫和费穆两位导演不约而同地于社会现实的边缘地带建构了世外之地,或者说概念性空间。这种艺术空間的设定安放了什么样的艺术理想呢,这便是文章将要继续探究的内容。
(一)在被遗忘的荒原上书写民族记忆
翻开乌克兰历史不难发现,乌克兰西部的客尔巴阡山脉,长久以来被不少学者视为斯拉夫民族的起源之地[10]。这是一个容易唤起人们思考民族起源的空间。帕拉杰诺夫也较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片荒原上的风俗人情。这些风俗人情连接着影片的故事线索和一系列的故事情节。这其中充斥着丰富的丧葬、婚嫁和节庆活动,也包含着决斗、偷情和巫术施展等细节。每一个片段都有着很大的戏剧性展示空间,可以给影片增添很大的戏剧张力。可是,观者若是抱着探寻戏剧张力、体验戏剧冲突的目的观影,难免会大失所望。以电影开篇的两场葬礼以及穿插其中的决斗情节为例,让我们来看一看导演的叙述重点究竟在哪里。
在第一场葬礼,也就是伊万哥哥的葬礼中,最先映入观者眼帘的,并不是亲人悲伤的情绪,而是一组民俗活动。从影片开始,导演便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在教堂之外,随着伊万从雪地一路走向教堂,观众可以透过摇摇晃晃的摄影机镜头看到,这里就像集市一般,妇女们试带着围巾,手工艺人展示着各种手工艺品,甚至还有癫狂的愚人正在被人责打。帕拉杰诺夫将镜头的焦点从他们身上一个个地摇过去,把他们的行为动作一个个排列在长镜头里,就好像是把这里的民俗风貌一幅幅地浓缩在铺开的长卷画纸上,让人分不清这是葬礼,还是狂欢。即便观众想要将自己的情绪带入影片,恐怕也很难分清,应该以哪种情绪带入剧情,悲伤和欣喜都显得不合时宜。
等到伊万进入教堂,导演又用长镜头记录下了教堂内的陈设布置以及颂祷仪式。继而,伊万的父亲与仇家的争执迅速演变成决斗与杀戮,导演并没有给这场决斗预留充分的情节埋伏,两家的打斗也没有花哨的动作手法做陪衬,杀戮就这样毫无征兆地直接降临了。随着伊万父亲被仇家砍杀,整个屏幕的画面瞬间降成二维,只剩下白色的背景和红色的血似血马一样在屏幕上奔腾。这一系列的设计,没有伏笔,没有延宕,毫无征兆的杀戮和极快的收场,以及屏幕画面的降维,都在对抗着影片的戏剧性,在阻止观众的情感带入。
在第二场葬礼中,导演将长镜头与特写镜头结合,呈现了出殡仪式的细节。与第一场葬礼相似的是,这里虽然增加了一组特写镜头,但是这些特写镜头并不是为了交代人物情绪而设置的。在这些镜头里,导演将摄影焦点对准了出殡过程中的一些功能性的角色,如执幡的人,手捧献礼的人,点燃冥灯的人等,他们的脸上并没有多少情绪,更像是一组代表着丧葬仪式的符号。导演虽然也给了伊万一个特写,但是伊万的形象在这里也就如同一个交代事件的符号。他面无表情地,甚至有些好奇地看着大人们把木楔钉入父亲的棺椁。唯一流露出悲伤情绪的是伊万的母亲,但摄影机选择了从侧面记录她的悲伤,将观众置于一个旁观路人的位置,旁观着她的悲伤。继而又是一个长镜头记录下了茫茫雪原上缓缓前行的送葬队列。可以看出,第二场葬礼中,悲伤氛围的渲染似乎也不是导演着力的重点。
仔细观察这两场葬礼可以发现,关于情绪的描写和烘托十分有限。大量的时长被分配给了几组长镜头。在这几组长镜头中,观众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个古老民族的一系列民族特征,可以观察到葬礼中独特的民俗活动。此外,还有一系列的特写镜头定格在葬仪活动的细节上。在这些长镜头和特写镜头面前,一组组民族符号被凸显出来,而本片的故事性似乎成了陪衬。用帕拉杰诺夫自己的话来说,从拍摄《影子》开始,他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即“一个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其视为纯粹的政治问题。关于这些主题,在《影子》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通过影片,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导演在他所创造的概念性的空间里没有安放太多的悬念,没有突出精彩的故事情节。取而代之,他在影片中展示了大量的民族元素,描写了隆重的民俗活动,刻画了这片土地上古老的信仰,以及这片土地上源自大自然的、也来自于人的,原始且旺盛的生命力。他通过对民族记忆最朴素的关注,安置了他对于乌克兰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和深切关懷。作为一个出身于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帕拉杰诺夫很难被定义为一个典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身上怀有的深厚的民族情结,应该被视为一种更为普世的民族情结,或者说是民族责任。
(二)在世外孤城里重燃传统文化气息
与《影子》稍显不同,《小城之春》这部作品对民族文化的观照,不在于凸显民俗元素,也不在于陈列传统文化符号,这里的民族文化气息更体现为一种对传统审美意境的运用。在费穆的《小城之春》中,他将中国文化艺术中的写意之美,灵活地融入他的电影中,他对电影的写实功能加以改造,增添了多重写意意趣。写意风格不仅仅融入了他对景物的拍摄中,更渗透到他对人物的打磨和塑造中。
石秋仙在《论中国诗电影的发展脉络》一文中,直接指出,“费穆的《小城之春》直接借用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化景物为情思,使整部影片充满着意境之美”“达到了诗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11]。香港著名影评人刘成汉在其论著《电影赋比兴》中,将电影元素与中国诗词元素加以类比,并将中国诗学中“赋、比、兴”的概念应用于具体的电影分析中。在他看来,费穆的《小城之春》正是“赋比兴的典范”,很好地诠释了中国诗词的美学风格和美学技巧[12]。陈墨也曾在他的《费穆电影论》中指出,“代表着费穆电影的民族性、传统性”的,正是“他对比兴的用功、对写意的兴趣”[13]。
这些概括可以说是非常贴切了,《小城之春》这部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景物比兴,特别是对荒芜的城墙、破败的院落的描绘,高度浓缩了战火洗礼后中国城市的普遍景象,凝聚着家园遭遇不幸的隐喻。对于这些景象一遍又一遍地描绘反复诉说着导演对家国命运的忧思。此外,除了大处的孤城和院落,小处的物象也充满着比兴的意味。比如药这一物象在剧中就反复地出现,牵引着礼言和玉纹的关系。白日里,玉纹为礼言买药,晚上玉纹又服侍礼言吃药,除此之外,二人之间便少有其他方面的交流。药在二人中间,既连结着二人的夫妻关系,也暗示着二人的夫妻关系是病态的,需要医治的。再比如,灯烛的物象在剧中也是反复地出现,穿插在玉纹和志忱的交流过程中。灯烛本就是晚间的物象,再加上剧中的灯烛总是明灭不定,这便暗示了二人之间见不得光的情愫。在剧中每每玉纹来私会志忱,也总有开灯关灯以及断电燃蜡的细节,隐喻着二人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
在这些诗意的比兴手法之外,导演还用中国传统艺术中留白的方法处理了影片中的许多细节。导演将许多可以实写的内容,留了白,没有实写,而是有意拓展了作品的写意空间。比如,导演将小城以外的空间留了白,将戴家之外的人际社会留了白。但这些留白的设计,并不是为了给剧情设置悬念。如,导演虽然提到了玉纹和志忱往日的情人关系,却也无意再去深挖他们感情的来龙去脉,可见,导演的着力点不在于给出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在已经无比凝练的剧情中又留下了一些不准备解开的情节,这为影片平添了几分难言的灰度氛围。此外,作品中的对话设计,也有留白写意的特征。人物间的对话十分精炼,特别是情绪到了深沉之处,语言愈发简练,言简意深。
同帕拉杰诺夫的《影子》相似,在费穆营造的这座世外孤城里,没有离奇的故事情节,戏剧冲突也并不强烈。《小城之春》这部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中有主仆,有夫妻,有姑嫂等。但很明显,影片并不着意突出他们的阶级身份,不刻意设置人物间的阶级冲突。在剧中,主仆之间互相敬爱,夫妻间相敬如宾,情人间也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姑嫂间更是表现出难得的互相体谅。导演几乎没有为常见的纲常伦理冲突留下戏剧性空间。与此相反,导演将故事情节娓娓道来,在可能埋设悬念的地方设置了旁白,来交代人物关系和故事背景。导演不求在叙事中体现戏剧张力,而是着意打造舒缓的叙事节奏。在这样的叙事节奏中,导演将小城打造成一个写意的空间,并在其中安放了一组组写意的意象,凸显了中国传统文艺的审美意趣,展示了导演对于民族文化满满的致敬。
结语
乌克兰导演帕拉杰诺夫和中国导演费穆,在作品中分别创造了荒原和小城这样的世外空间。在这两方概念性的理想空间里,两位导演倾注了各自的民族情感,即使隔着时间和空间,他们所书写的民族情怀依然是相通的。从诗电影风格的角度来比较《影子》和《小城之春》这两部作品,这仅仅是将两位导演的作品拉近比较的一个尝试。对两位导演更深入的比较研究有赖于对他们更多的作品进行分析,以及从更多的视角对这些作品进行解读。
参考文献:
[1][3][意]皮·保·帕索里尼.诗的电影[ J ].姜洪涛,译.世界电影,1984(01):11,21.
[2][5][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M].张晓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66,15-16.
[4][苏]多宾.电影艺术诗学[M].罗慧生,伍刚,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10-11.
[6][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一九七○~一九八六)[M].周成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6.
[7]贾斌武.现代电影观念的启蒙——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对蒙太奇理论的介译与探索[ J ].文艺研究,2018
(03):107.
[8][13]陈墨.费穆电影论[ J ].当代电影,1997(05):29,30.
[9]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271.
[10][美]保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M].颜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9.
[11]石秋仙.论中国诗电影的发展脉络[ J ].中文自学指导,2007(05):62.
[12]刘成汉.电影赋比兴[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