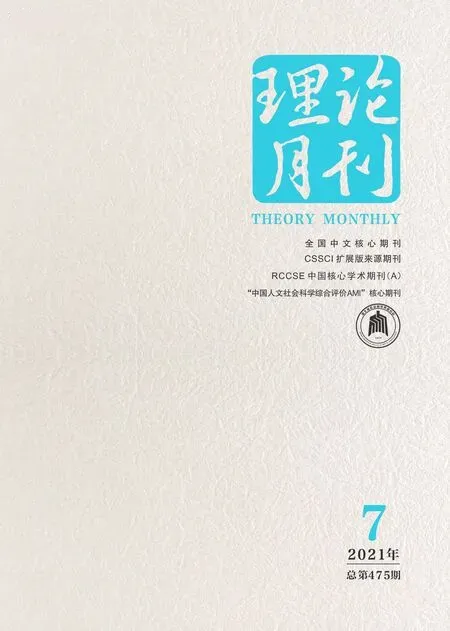针对“劳动的二重性”理论的逻辑检视与创新发展
□张原锟,张树青
(1.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一、针对“劳动的二重性”理论的逻辑检视必要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开创性地通过抽象分析,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划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此说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实际是价值)的来源,这即是著名的“劳动的二重性”理论。“劳动的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也被其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p55)。在该理论提出之后,国外学者对以该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基于不同的理解,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并出现了三次比较集中的争论: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庞巴维克和希法亭为代表的学者对价格理论与价值理论之间在逻辑上是否存在矛盾展开了争论;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以斯威齐、温特尼茨、米克、塞顿为代表的学者对劳动价值理论能否解释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决定的争论;第三次争论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以萨缪尔森、森岛通夫、曼德尔为代表的学者对劳动价值理论本身是否成立的争论[2](p103-106)。在上述国外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学者已经开始从逻辑方面分析检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传入中国后,国内学者也对其展开了积极讨论,同样出现了不同观点和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我们发现部分学者已经开始从逻辑方面对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核心的“劳动的二重性”理论进行分析检视。例如,钱津认为,抽象劳动是和劳动同义的类概念,而具体劳动概念的层次比抽象劳动概念要低,将两者并列会产生“白马非马”的逻辑问题[3](p20)。赵学增认为,“劳动的二重性”理论将一个完整的劳动变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两种分别独立的互无联系的劳动,这可能在逻辑关系上存在问题[4](p15-16)。晏智杰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财富或商品的两种不同用途和不同存在形式,两者的创造源泉没有分化的可能,价值源泉与财富源泉应是一致的[5](p24-26)。抽象劳动本身就是对具体劳动的抽象,不存在脱离具体劳动的抽象劳动[6](p13)。任洲鸿认为,“劳动的二重性”理论使用生理耗费来定义抽象劳动,这将导致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工作变得困难[7](p26)。王新水认为,因抽象而得到的作为共相的具体劳动与所谓的抽象劳动,是无法真正区别开来的[8](p29)。
如果我们想要正确认识国内外学者各种争论的本质,重视和科学回应那些在逻辑方面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的各种不同观点,那么就有必要对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核心的“劳动的二重性”理论进行逻辑检视,看其是否做到了完全的逻辑自洽。这项工作对我们科学验证和正确认识乃至创新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针对“劳动的二重性”理论的逻辑检视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具有双重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同样具有双重属性[1](p55),即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是指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它将形成价值。具体有用劳动是指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它生产使用价值[1](p60)。以上就是“劳动的二重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由于马克思在对“劳动的二重性”理论进行阐述时,使用了思辨性极强且抽象的方法,这使得想要真正理解该理论变得很困难。因此,如果我们想一窥“劳动的二重性”理论产生过程的本来面目,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回到该理论的阐述过程本身,看其是否经得起严格的逻辑检视,是否真正做到了完全的逻辑自洽。基于这样的逻辑思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抽象人类劳动”概念阐述过程的逻辑检视
1.“抽象人类劳动”概念的阐述过程。马克思说:“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1](p51)
2.针对“抽象人类劳动”概念阐述过程的逻辑检视。首先,马克思是从撇开商品体的使用价值开始,对“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进行抽象,得出了“抽象人类劳动”概念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抽象是指从许多事物中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的过程,是形成概念的必要手段[9](p151)。但是,把概念仅仅看成是抽象的,认为它所表现的只是一些事物的共同点,而不涉及事物的特殊性、个性,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个别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10](p30)。因为,概念反映了个物之间的关联,是无限的多样性的总体。例如,在对黑、白、大、小等不同个体的马进行抽象时所得出的马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将颜色、体型这些特殊性都包含在内了[11](p13)。所以,对同类个物进行抽象得出概念时,个物与具有类的属性的概念之间是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关系。在哲学上个别与一般是一对具有种属间辩证关系的概念范畴。列宁关于个别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曾有专门论述:“对立面(个别与一般)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无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12](p558)
其次,依据上述个别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在对诸如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进行抽象时,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去找出它们的共性与本质,那么这些劳动的共性与本质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马克思早已经在无意中给出了答案。马克思说:“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法、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1](p55)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所定义的有用劳动过程中所说的有用性或叫有用效果就是上述这些劳动的共性与本质,而有用劳动就是对这些劳动抽象后得出的作为一般而存在的劳动概念。而诸如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各个具体有用劳动)则是个别。这样的个别与一般作为对立面是同一的:作为个别的具体有用劳动一定是与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相联系而存在的。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只能在作为个别而存在的具体有用劳动中存在,只能通过这一个个具体有用劳动而存在。任何具体有用劳动(无论如何)都是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任何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都是具体有用劳动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定义有用劳动过程中所说的有用性或叫有用效果是有双重含义的,其一也是最重要的含义是指劳动的特殊有用性,即是指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其二是指劳动的有效性,即是指有效劳动(也称有用劳动),这是与无效劳动(也称无用劳动)相对称的劳动。
因此,作为个别而存在的具体有用劳动与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只不过是相对而存在的具有哲学上个别与一般之间辩证关系的概念范畴。具体有用劳动强调的是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之间的差异性与个性,但这种强调并不抹杀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之间的共同性与本质,它是在承认各个具体有用劳动具有共同性与本质的基础上,强调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之间的差异性与个性。与此相对应,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强调的是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之间的共同性与本质,但这种强调并不抹杀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之间的差异性与个性,它是在承认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之间的差异性与个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之间的共同性与本质。具体有用劳动是具有“个体”属性的劳动,而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则是具有“类”的属性的劳动。这就是具体有用劳动与有用劳动或叫具体有用劳动与劳动(在这里有用劳动可以简称“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再次,如果不按照个别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对事物进行抽象,那么经过抽象后得出的所谓的抽象人类劳动,就会因为它是在完全撇开了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之间的差异性与个性的基础上所得出来的,所以它就和被抽象的对象(各个具体有用劳动简称“具体劳动”)毫无关系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抽象人类劳动根本就不是对各个具体有用劳动的科学抽象。因为这种所谓的抽象人类劳动和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之间,已经不具有哲学上一般与个别之间的辩证关系了。可以说,劳动的有用性既是各个具体有用劳动的共同性,更是各个具体有用劳动的本质属性,因此具体有用劳动的有用性是不能被撇开或被抽去的。如果把各个具体有用劳动的有用性撇开或抽去了,实际上就等于把劳动的本质属性撇开或抽去了,进一步说也就是把被抽象的对象——各个具体有用劳动撇开或抽去了。这时被抽象的对象——各个具体有用劳动(简称“各个具体劳动”)就不存在了,而与之相对应的只能在各个具体有用劳动中存在,只能通过各个具体有用劳动而存在的有用劳动(简称“劳动”)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人类劳动”概念阐述过程的逻辑检视
1.“人类劳动”概念的阐述过程。马克思认为:“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1](p57-58)
2.针对人类劳动概念阐述过程的逻辑检视。
首先,马克思是从撇开那些被抽象的劳动——人类劳动力的生产耗费的特定性质开始,对缝和织这样不同质的生产活动进行抽象后,得出所谓的人类劳动的。
其次,如果我们运用哲学上个别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马克思对“缝和织”这种不同质的生产活动所做的抽象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那么生产活动就会因为这种撇开而不存在了,当然人类劳动也会因为这种撇开而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单独剩下所谓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实际上,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不是经过这样抽象后得到的,而是对缝和织这样不同质的生产活动进行抽象后得到的。因为人类劳动力并不是特指的,它既可以指缝衣这种人类劳动力,也可以指织布这种人类劳动力,更可以指其他种类的人类劳动力,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人类有特定用途的劳动力,所以人类劳动力的消耗才能是人类劳动。此时的人类劳动(有用劳动)也只是一个具有类的属性的概念范畴,它既可以指缝衣这种人类劳动,也可以指织布这种人类劳动,更可以指其他种类的人类劳动。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劳动仅是对诸如“缝衣”“织布”等具体有用劳动进行抽象后得出的劳动概念。相对于“缝衣”“织布”等具体有用劳动来说,人类劳动就是指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
再次,马克思把人类劳动本身看成是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不是将人类劳动本身看成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这说明他把自己所谓的一般人类劳动力和人类劳动力看成是一样的东西。但上述我们已经指出人类劳动力并不是特指的,而马克思所谓的一般人类劳动力则是一种特指的人类劳动力,即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这种所谓的简单劳动力,因为它仅是众多具体的人类劳动力中的一个极端特例,所以将它称为所谓的一般人类劳动力是不恰当的。当然,将这种所谓的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称为人类劳动本身,显然也是不恰当的。
(三)“一般人类劳动”概念阐述过程的逻辑检视
1.“一般人类劳动”概念的阐述过程。马克思认为:“要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可以叫作一般人类劳动。”[13](p18-19)
2.针对“一般人类劳动”概念阐述过程的逻辑检视。首先,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不能仅靠哲学上的逻辑抽象去解决问题,更要靠科学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不同的劳动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是具有不同有用性的劳动,而劳动的有用性是劳动的本质属性,对各个具体有用劳动进行抽象只能得到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根本得不出质上相同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更不能得出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这样的结果。
其次,把不同的劳动化为质上相同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只需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劳动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化为简单的劳动。这里之所以说不需要,是因为不同的具体有用劳动之间是可以相互换算的。不需要借助所谓的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而且这种所谓的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既不是作为个别而存在的具体有用劳动,也不是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因为它的含义是指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所以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是不可能具有简单劳动力的,因为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p190)所以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劳动力应是指具体有用劳动力。其二,具体有用劳动力不管它如何简单,它都不是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所能具有的。其三,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在社会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能在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只能是相对简单的某种具体有用劳动。
再次,上述已经明确了有用劳动就是对各个具体有用劳动抽象后得到的作为一般而存在的劳动概念,所以作为一般而存在的劳动并不是马克思所谓的一般人类劳动力耗费所形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一般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劳动不是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而是相同的、无差别的具体有用劳动。因为作为一般而存在的有用劳动不能离开具体有用劳动而独立存在,它只能在具体有用劳动中存在,只能通过具体有用劳动而存在。所以用来衡量各个具体有用劳动的标准尺度的劳动,只能是“相同的、无差别的”具体有用劳动。这在理论上的表述就是:为了确定互相交换的商品背后所对应的不同种类的具体有用劳动的数量,必须首先将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的个性不同的劳动,分别换算成作为标准尺度的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具体有用劳动,然后再计算这种作为标准尺度的具体有用劳动所持续的时间长短,以此来确定不同的使用价值中,究竟包含多少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但标准尺度的具体有用劳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逐渐从各种商品中脱颖而出的,固定用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生产,实际上标准具体有用劳动就是货币商品生产时所耗费的具体有用劳动。
三、针对“劳动的二重性”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针对“劳动的二重性”理论阐述过程的逻辑检视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劳动的二重性”理论的阐述过程在三个方面未能做到完全的逻辑自恰。
首先,该理论的阐述过程违反了个别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在对各个具体有用劳动进行抽象时,未能意识到劳动的有用性是劳动的根本属性,错将劳动的有用性不适当地撇开了,这导致正确的抽象结果——有用劳动没有被得出,而错误的抽象结果——抽象劳动被当成了正确的抽象结果。“劳动的二重性”理论也因这个原因无法做到逻辑自洽。
其次,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不是通过将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即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后得到的,因为这样做之后,生产活动就会因为这种撇开而不存在了,当然人类劳动也会因这种撇开而不存在了,不可能还剩下所谓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所以,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应该是对“缝和织”这种不同质的生产活动,即对种类不同的具体人类劳动进行抽象概括后得到的。
再次,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与“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不是一回事,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作为一般而存在的人类劳动(有用劳动),而是相同的、无差别的具体有用劳动。因为有用劳动是不能离开具体有用劳动而单独存在的,它只能在具体有用劳动中存在,只能通过具体有用劳动而存在。所以用来衡量各个具体有用劳动的标准尺度的劳动只能是相同的、无差别的某种具体有用劳动,这在理论上的表述就是:我们必须首先将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的个性不同的劳动,分别换算成作为标准尺度的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具体有用劳动,然后再计算这种作为标准尺度的具体有用劳动所持续时间的长短,以此来确定个性不同的劳动所生产的不同的使用价值中,究竟包含多少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但标准尺度的具体有用劳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各种商品中脱颖而出的,固定用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生产,实际上标准具体有用劳动就是货币商品生产时所耗费的具体有用劳动。
(二)逻辑检视结论的进一步分析
为什么说标准具体有用劳动就是货币商品生产时所耗费的具体有用劳动呢?要想科学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既需要像马克思那样能够识破“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1](p49)这一假象,弄清商品的交换价值仅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这一真相。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将所谓的“抽象人类劳动”认定为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点。因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表明,如果人类没有普遍产生公平交换的意识,就不会出现所谓的交换价值的概念,更不会产生探求如何准确计量交换物价值的问题。无论是偶然的物物交换也好,还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也好,都是需要将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种类不同的具体有用劳动进行统一衡量。其中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是先将生产不同商品的各个具体有用劳动分别换算为生产货币商品的具体有用劳动,然后再看它们数量上的大小,以此计算出彼此相交换时的数量比例关系。但这一切不是由专门机构来完成,而是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自动实现的。这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这句话最核心的含义。而偶然的物物交换是将生产交换物的不同的具体有用劳动彼此进行相互衡量,这种相互衡量产生的结果是否公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这样的偶然物物交换也天然具有相对属性。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却打破了偶然的物物交换所天然具有的偶然性和相对性,使得商品价值具有了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必然性和绝对性。因为决定某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生产该种商品的具体有用劳动,商品价值还和与其进行交换的生产货币商品的具体有用劳动有关,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的。这种以货币为媒介的普遍的商品交换,使得生产各种商品的私人劳动,通过市场上商品的交换,变成了被社会承认的劳动——社会劳动。上述商品价值的决定以及它成为商品交换价值的依据的过程,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极具辩证意义的复杂过程,需要另文加以详细说明,本文暂不讨论。
(三)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真正二重性
通过上述分析,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真正二重性如下:
首先,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可以划分为某种具体有用劳动与标准具体有用劳动双重属性,简称具体劳动与标准劳动的二重性。因为衡量不同种类的单位商品中各自包含多少同质的具体有用劳动量,这既是一个科学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对不同的具体有用劳动如何按被选为标准的某种具体有用劳动进行公平度量的问题。这就类似于我们面对具有不同比重的物体,如果要想计量它们各自的重量,那么必须首先建立起有关物体重量方面的度量衡制度,然后才能具体地去称量各个不同物体的重量。我们去计量不同种类的单位商品中各自包含多少同质的具体有用劳动量,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先建立一套有关具体有用劳动方面的度量衡制度,然后才能具体去计量不同种类的单位商品中各自包含多少同质的具体有用劳动量。而且这样的问题即使在理论上一时无法说清其内在机制和原理,但是社会发展实践却早已给出了一些恰当适用的解决办法。这符合人类从最初的偶然的物物交换发展到后来的以货币为媒介的频繁的商品交换的历史。
其次,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可以划分为个别的具体有用劳动和社会必要的具体有用劳动,简称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p5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本意是指抽象劳动所持续的时间,但如果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文字表述其实用来指称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平均的个别的具体有用劳动所持续的时间可能更合适。这种新的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对应的劳动就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平均的个别的具体有用劳动(简称“社会必要劳动”),相应的与这种社会必要劳动相对应的是个别的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具体有用劳动(简称“个别劳动”)。因此,在新含义下,商品中包含的劳动还具有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二重性。
再次,与上述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所具有的新含义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二重性同样的道理,由被很多人称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4](p007)也可以得出新的含义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新含义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对应的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相应的个别劳动一起,构成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所具有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第二种含义的个别劳动的二重性。
综上,利用哲学上个别与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对“劳动的二重性”理论的阐述过程进行严格的逻辑检视,发现该理论的阐述过程未能做到完全的逻辑自洽。基于此,分析了标准具体有用劳动为什么是货币商品生产时所耗费的具体有用劳动这一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所真正具有的三个方面的二重属性:一是具体劳动与标准劳动的二重性;二是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二重性;三是第二种含义的个别劳动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