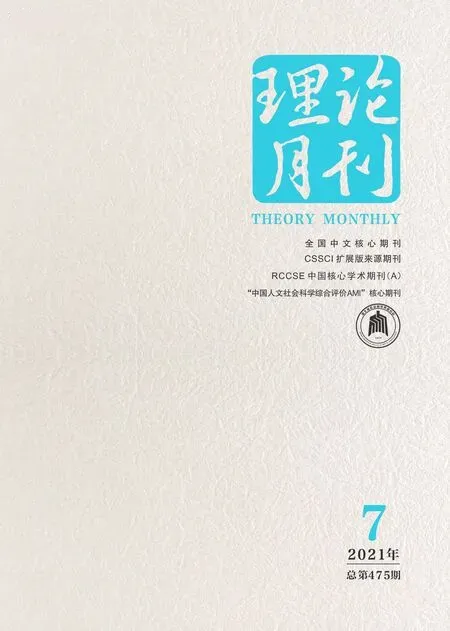悖谬与自由:论偶发艺术的“不确定性”
□曹晓寰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偶发艺术的创始人阿伦·卡普罗在《纽约艺术中的“偶发艺术”》(“Happenings”in the New York Art Scene,1961)一文中表述:“偶发艺术,就是事情的发生。”[1](p61)“是描述那些最具冒险性、开拓性及挑战性的东西。”[1](p61)他在《无题文章和其他作品》(Untitled Essay and Other Works,1967)中透露:“我一直梦想一种新艺术,一种真正的新艺术。”[2](p4)“我们是冒险家。我们不必‘希望’任何东西。”[2](p7)可见,卡普罗认为的偶发艺术是一种新艺术,这种艺术在于冒险地探索一条完全自由创作的道路。
自由创作意味着挣脱传统创作规范的约束。对此,偶发艺术进行了一系列叛逆求新的实践,消除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家与非艺术家的界限,导致艺术在定义、形式、内涵上的“不确定性”。在一定意义上,艺术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学科的“不确定性”具有同构性。学界通常将偶发艺术作为研究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一个论题,对偶发艺术在哲学层面的内涵并未足够重视。因此,对偶发艺术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本身进行思考成为值得学界关注的问题。
一、偶发艺术及其思想来源
偶发艺术(Happening Art)指具有即兴表演性质的活动。该活动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产生并盛行。“偶发”一词原是美国拉特格大学《人类学家》杂志的一个栏目标题。1959年,阿伦·卡普罗(Allan Kaprow)在论文《杰克逊·波洛克的遗产》(The Legacy of Jackson Pollock)中使用该词描述艺术创作的一种状态。此后,“偶发”便用以指代具有偶发性、开放性、不确定性特征的艺术现象。同年,卡普罗在纽约鲁本画廊(Reuben Gallery)策划了一场偶发活动“6部分中的18个偶发事件”,引发了一股偶发风潮。进行偶发创作的还有吉姆·戴恩(Jim Dine)、克莱斯·奥尔登堡(Claes Olden⁃burg)、罗伯特·惠特曼(Robert Whitman)、乔治·西格尔(George Segal)等人。
偶发艺术产生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时期。一方面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个顶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潜藏的重重危机面临爆发。此时西方社会原有的后现代力量获得了发展条件,并对传统的现代或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和挑战。这一时期被相当多的学者看作现代与后现代的分界,如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论述后工业社会来临的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论述后现代性状况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自此,后现代主义从审美领域向哲学领域扩散,最后进入人文、社会等领域。
偶发艺术在产生之日便浸染了历史和文化上的复杂性,其艺术探索是在各种矛盾形态的碰撞、交锋中进行的。简单来说,对偶发艺术产生启示和催化作用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杰克逊·波洛克(Paul Jackson Pollock)的行动绘画,在一定程度上行动绘画被认为处于“改变绘画定义的边缘”;二是约翰·凯奇(John Milton Cage)的偶然音乐,偶然音乐的理念涉及东方的佛教禅宗思想。
杰克逊·波洛克是抽象表现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他采用滴画法(drip painting)创作了一系列姿态性作品,这些具有即兴、随意、无中心、无空间特征的作品就是为人熟知的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该术语在1952年由艺术批评家哈罗德·罗森博格(Harold Rosenberg)提出。罗森博格认为行动绘画是从政治、美学、道德价值中解脱出来的一种行动实践。
波洛克在《我的画》(My Painting)一文中有过表述:“我的画不是来自画架。在绘画前,我几乎不去绷画布。我宁愿把未绷紧的画布钉在坚硬的墙壁或地板上。在地板上我感到更加自在。我觉得这样更接近我的画,我更能成为画的一部分,因为我可以绕着它走,从四个侧面入手,然后真正走入画中。”[3](p33-34)“当我在绘画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熟悉’后,才明白自己在做的事。”[3](p34)这种行动绘画的方式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如《整整五浔》(Full Fathom Five,1947)、《作品1号》(Number 1A,1948)、《作品31号》(Number 31,1950)。1950年波洛克在接受威廉·莱特(William Wright)采访时,针对其提问:“是否可以说无意识是艺术家的创作源泉?”他答道:“无意识不仅是现代艺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并且无意识的驱动力在看画的时候也很重要。”[1](p6)“在我看来,可能性是无穷的。”[1](p10)正是对无意识、可能性的重视,促使波洛克赋予了行动绘画一定的自由度。
1959年卡普罗在《艺术新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杰克逊·波洛克的遗产》。文中他对波洛克的绘画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在的分析,认为波洛克的绘画突破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创作传统,这种突破可以看作艺术发展的一个转折。就此,卡普罗指出:“有二种选择。一种是继续这个方式。在既不偏离也不深化的基础上变化波洛克的美学原则,也许能创作许多好的‘接近绘画’的作品。另一种是完全摆脱绘画,我指的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单一的、平面的、矩形或椭圆形的绘画。”[1](p57)卡普罗的论点不仅反映了他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艺术变革的预言,同时反映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某种交错,以及后现代艺术的反艺术思想如何从现代性中孕育而来。随后,卡普罗举办了一些突出行动且摆脱绘画的活动,这些活动初步具有了偶发性质。
约翰·凯奇是美国先锋派作曲家、哲学家。1952年他在黑山学院组织了一场演出,旨在探讨有目的的无目的性(purposeful purposelessness)。演出由一些不相关的“事件”组成:舞蹈家默斯·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跳舞、钢琴家大卫·图多尔(David Tudor)弹琴、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en)朗读、画家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白色绘画作品展览。凯奇则做了一场演讲并以“一根琴弦、一次日落皆为演出”为结尾。这场由门类不同、样式不一的“事件”组成的演出呈现出偶然性、随意性、不确定性性质,与偶发艺术的风貌十分契合,因此,常被学界看作偶发艺术的真正开端。
约翰·凯奇从劳森伯格的《白色绘画》(White Painting,1951)中看到了变幻的光影,体会到禅宗“空”的思想,受此启发创作了钢琴曲《四分三十三秒》(4′33″,1952),由大卫·图多尔在伍德斯托克的音乐会上进行了演奏,钢琴曲总长度4分33秒,演奏的规则是无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该作品被认为是机遇音乐(Chance Music)的典型作品。此后凯奇创作的作品《钢琴曲4—19》(Music for Pia⁃no 4—19,1954)与《钢琴与管弦乐队音乐会》(Con⁃cert for Piano and Orchestra,1958)是对机遇音乐的进一步发挥。机遇表示契机、时机,具有不可预料、不断变化的特点。“空”来源于缘起论、三法印、万法皆空思想。凯奇对禅宗的理解虽遭到美国学者阿伦·瓦兹(Alan W.Watts)的指责,认为其利用禅宗思想来“反抗文化和社会习俗”[4](p199)。然而,凯奇对禅宗的调和性艺术转化对偶发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
1957—1958年,卡普罗进入凯奇开办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习音乐创作。凯奇提示卡普罗使用录音带预先制作声音,以某种随机顺序进行播放。卡普罗接受了该建议,对创作过程中的随机性加以了关注,并尝试将创作拓展到一切可能的范围。例如,将声音、灯光、气味作为创作元素,将空旷的田野、沙滩、树林作为创作场地,逐渐发展出一种“对绘画的多种层次的空间再现”的艺术形式,即偶发艺术。同凯奇一样,卡普罗善于从禅宗中获取灵感。他通过禅宗的冥想练习创作“基于呼吸的绘画”,这种具有沉思意味的绘画具有不可捉摸、无法确定的特征。
此外,偶发艺术还从更早的达达主义中汲取养分。达达主义具有反叛性、非理性特点,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是代表人物之一。杜尚创作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No.2,1912)以连续重叠的形象表现了运动中不同瞬间的美,对运动中的不稳定性和瞬间的模糊性进行了渲染。此后,杜尚创作了《泉》(Foun⁃tain,1917)、《带胡须的蒙娜丽莎》(L.H.O.O.Q,1919)等作品,其另类的创作方式推进了西方艺术形态和美学观念的发展。卡普罗表述过杜尚带给自己的影响,尤其“艺术是任意性的”[5](p222)方面,他认为“我对艺术专一而又持久的兴趣是有哲学基础的”[5](p222)。结合上述路径,不难看出卡普罗认为的哲学基础同“不确定性”是息息相关的。
二、偶发艺术的“不确定性”
由波洛克的行动绘画发展到动作拼贴,由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剧场化表演发展到“行动的舞台”,卡普罗开创的偶发艺术使创作成为一种即兴表演活动,从而“超越了‘仅体现在绘画中’的尝试,绘画的‘动作’已被戏剧和生活取代”[6](p106)。自此,作为即兴表演、生活化、媒介融合的偶发艺术背离了西方的艺术传统。“不确定性”是偶发艺术进行新艺术探索的主要策略,也是偶发艺术进行反形式、非理性、游戏性、无目的性等反艺术实践的总体反映。
“不确定性”在偶发艺术的首次活动中便得到充分体现。1959年,卡普罗在鲁本画廊进行了一场活动“6部分中的18个偶发事件”(18 Happen⁃ings in 6 Parts)。“6部分”指的是将画廊分为3个房间,每个房间分为2个部分,共为6部分。“18个事件”指的是每个部分安排3场活动,共构成18个“事件”。“偶发事件”的具体表现为:在“事件”开始前,人们获得相关的计划和指示,这些计划和指示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像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事情,如坐下、行走、说话、画画、挤橘子汁。活动过程充满随意性、自由性。正因如此,“偶发事件”显示出生活的真实状态,体现出卡普罗所推崇的普通的事、普通的意义。
卡普罗曾使用“质朴”“直接”“孩子气”等词语形容波洛克的绘画,认为作品的“坦白”带给自己启发。卡普罗也从凯奇的课堂上获得关于生活随机性、开放性的启发。这些启发使卡普罗将直接、随机的事物视为主要艺术元素。例如,一种被压碎的草莓味道、一道被抓伤的痕迹、一声叹息、一场没完没了的演讲、一道掠过的闪电、一张古琴的轻颤、跳跃的投影。
吉姆·戴恩将绘画、表演等媒介进行了融合。1960年他在贾德森画廊(Judson Gallery)开展了一场“偶发事件”《微笑的工作者》(The Smiling Work⁃man)。“事件”中戴恩身穿红色工作服,用橙色和蓝色“颜料”写下“我喜欢我所做的”几个字,过程中他不仅将“颜料”(番茄汁)喝下去,还将“颜料”浇在脑袋上,任其随意流淌。其滑稽的行为凸显出创作的偶然性和游戏性。这种方式贯穿于他此后的创作中,如《龇牙咧嘴的巨大鬼脸》(The Enor⁃mous Grimace of Teeth,1960—1961)、《儿童的蓝色墙》(Child’s Blue Wall,1962)、两幅《名字画》(Name Paintings,1968—1969)。吉姆·戴恩将创作视为生活的延伸,而生活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的。因此,他不得不将生活中变化、混沌、不确定以及无厘头的思想和行为搬进艺术中,他在介绍自己的“偶发事件”时坦言:“我并不确定它意味着什么。”[1](p68)
《如何制造偶发事件》(How to Make a Happen⁃ing,1965)是卡普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演讲。在第一部分他列出了偶发艺术的11条规则,将偶发艺术定义为一种开放式表演,目标是对既定传统的瓦解。例如,第1条是“忘记所有标准的艺术形式”[7](p1)。他强调,关键是要创造一些新东西。第2条是“可以通过将偶发事件与生活相混淆来避开艺术”[7](p1)。他解释道,创作需要模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在第二部分他列举了几个实例,如《肥皂》(Soap)、《呼叫》(Calling)、《下雨》(Rain⁃ing),将之作为粗略的创作指南。次年,在《近期的偶发事件》(Some Recent Happenings,1966)中卡普罗总结了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件”:《鸟类》(Birds)由南伊利诺伊卡本代尔大学委托,1964年2月16日在校园边的树林进行;《家庭》(Household)由康奈尔大学委托,1964年5月3日在一个垃圾场进行;《肥皂》(Soap)由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委托,1965年2月3日至4日在萨拉索塔进行。这些“事件”无须排练也不必重复上演,它既可以作为一幕出现,也可以作为连续剧形式出现。卡普罗认为:“偶发事件是把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许多场面进行的集合”[8](p5),“它是艺术,但似乎更接近生活”[8](p5)。这种接近生活的艺术在其另一篇文章《不能成为艺术的艺术》(Art Which Can’t Be Art,1986)中进行了更为肯定的表达。的确,卡普罗将日常生活中的刷牙、肘部运动称为“做艺术”。
奥尔登堡的代表作《在商店的日子》(Store Days,1961)就属于接近生活的艺术。该“事件”发生在纽约东二街107号的一个商店里,店内是甜饼、汉堡、衬衣等项目的陈列。“事件”展示目录上登载着他的一篇文章《我追求一种艺术》(I Am for an Art)。“我追求一种从生活本身获取形式的艺术,它曲折、延伸、积聚、下雨、下雪,它同生活本身一样沉重、粗糙、迟钝、甜蜜、愚蠢。”[1](p98)“我追求雨水淋湿面包的艺术。老鼠在地板上跳舞的艺术。我追求苍蝇在灯光下光滑梨子上走路的艺术。我追求潮湿洋葱和坚硬绿芽的艺术。我追求在蟑螂爬行时咔哒咔哒敲坚果的艺术。”[1](p101)此后,奥尔登堡进行了诸多生活化的创作,如《印第安人》(In⁃jun,1962)、《自体》(Autobodys,1963)、《电影院》(Movie house,1965)。透过奥尔登堡的创作及表述,可以看出艺术家对创作开放性、不确定性的追求。
纵观偶发艺术种种不合时流的实践,无不反映出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不确定性”是偶发艺术进行反艺术创作的有力武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艺术的真正含义。“不确定性”建立在破坏传统艺术规范以及“毁弃他人已建构之物”的基础上。一般来说,传统艺术的建构从审美性出发,以审美性指导创作。偶发艺术对审美性却加以弱化,认为审美性并非是唯一的,而是多元观念中的一种。1988年卡普罗在接受小约翰·霍尔德(John Held Jr.)采访时表示“我的兴趣不是否定绘画,而是增加画家当时的选择余地”“打开另一个大门”。
概括地说,偶发艺术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主张反形式,拒绝将形式加以形式化。针对形式在传统艺术中的必要性,偶发艺术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将其扬弃,使形式不再具有必要意义。第二,推崇创作中的非理性。体现在艺术家把一些杂乱无章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思想注入创作中,借此表达非理性与理性具有同等的地位。诚然,非理性作为主宰人类行为和决策的隐形力量,是不应回避的。第三,重视艺术的生活性和游戏性、生活的艺术性和开放性以及观众的参与性。游戏作为一种自由愉快的活动,会以自身规则冲撞到统一规范,观众的参与行为则会削弱艺术的权威性及艺术家的合法性,从而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离。第四,倡导创作的无目的、无意义。无目的在偶发艺术看来恰恰是合目的性的,但艺术惯于遭受规范、准则的干预,逐渐被剥夺了自由表达的乐趣和话语权。对此,偶发艺术提倡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以维护创作的自由。
可见,偶发艺术极力想从确定的、限制性的思想桎梏中挣脱出来,以方便自身在不确定性、开放性、自由性中前行。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在1969年出版的《美学理论》中指出,艺术的自明性或自身的可理解性已消失殆尽。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美学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前后不一的观点,使他的美学思想呈现出某种含糊性。他在1977年出版的《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强调了寓意、讽喻、模棱两可在社会和艺术中的重要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存美学试图将生活的无规则纳入美学范畴。因此,如何看待对待“不确定性”不仅限于艺术层面,还延展至其他层面。
三、“不确定性”的哲学内涵
主张“不确定性”的偶发艺术以藐视安稳的勇敢向传统艺术发起了攻击,成为推动西方后现代艺术进程的中坚力量。“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反叛性策略,是对关于艺术的悖谬性与悖谬的普遍性、创作的游戏性与自由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思考的出发点。从哲学层面看,作为偶发艺术内在结构和方法论基础的“不确定性”并非是孤立的,它与悖谬、自由、多元等形态是交织并存的。
(一)“不确定性”作为反叛性策略
“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也就是不可界定、无法确定。19世纪现代派代表人物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在《1845年沙龙》中提出创作的三大原则:过渡性、逃脱性、偶然性。这些原则影响了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进入20世纪,阿多诺反思了现代派原则,在谈论现代艺术的审美性时表述了一个观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从而使其美学兼具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性。本雅明虽受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却不主张用本体论原则探讨艺术问题,他对艺术问题的观点往往前后不一。和阿多诺一样,他的美学在保留现代美学特点的同时夹杂了后现代美学特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反文化”“非主流”运动风靡一时,这些运动向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作为反叛性文化策略的“不确定性”,势必对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逻辑主义进行攻讦。大致来说,“不确定性”源自现代性,经过一系列反叛性的批判活动,显示出对现代性的超越。
后现代主义学者伊哈布·哈桑(Ihab Habib Has⁃san)将“不确定性”提炼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倾向之一。康德就美的“不确定性”使用过两个隐喻:一是炉膛中摇曳不定的火苗的不确定性,二是小溪流水淌过后不规则的痕迹。康德的观点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的高度评价,利奥塔认为康德将美与自由同等重视。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强调“延异”的自我生成性质,“延异”有差异和延宕双重含义。它作为一种散布和播散,代表了一个无限区分、无限推延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中心/边陲、正常/异常、平衡/失调的秩序遭到破坏,从而成为不确定、无中心、模糊化的运动。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提出“根茎”概念来暗喻世界,“根茎”具有非中心、无规则、不确定的形态。“根茎”是一种游牧思想方式即开放的、充满差异的、非地域化的、多元的。美国哲学家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发扬了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批评,他认为,当代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对“不确定性”做出解释。
此外,“不确定性”存在于以严密著称的数学、物理、科学领域。如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库尔特·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科学知识不会永久地拥有可信度,任何追求确定性、完整性、稳定性结论的知识都面临难圆其说的风险。
(二)艺术的悖谬性与悖谬的普遍性
悖谬,就是悖论、荒谬。悖论,是集两组相悖命题于一身的奇妙力量,它伴随人类思想特别是语言的形成而出现。早在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时代,芝诺就提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命题,反映出语言系统隐含的“确定性”和“含糊性”同在的特征。18世纪,康德在其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二律背反命题:有限与无限,可分与不可分,自由与不自由,神的存在与不存在。这几组命题展现出悖论的难以克服性。19世纪以来,不乏展现悖论命题的学者、艺术家。荷兰版画家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用艺术形式表达了悖论思想,其作品《高与低》《画手》引导人们通过一步步富有逻辑的推理推导出毫无逻辑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20世纪中后期,偶发艺术代表卡普罗在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意识到不被视为艺术的艺术实践与其说是悖论,不如说是矛盾。
伴随悖论而来的还有荒谬。荒谬,即不分真假、混淆是非。意大利戏剧家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在其著作《幽默主义》中强调了逻辑合理性的虚假性及世界的不可知性。法国荒诞派剧作家欧仁·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认为世界始终是荒谬的。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讲,荒谬具有普遍性。当人类从试图探究世界和人生的合理性开始,便发现世界和人生的荒谬性不可避免。这是因为世界是辽阔无边的,且处于永恒的运动中。人类世界不过是无限宇宙的一个局部,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而,荒谬与真实未必对立,它们之间还充满各种错置和例外。换句话说,很多时候荒谬等于真实,真实等于荒谬。
利奥塔提出了概念悖谬推理(paralogy),也就是以异质标准对歧见进行探求。他认为连续的、不可区分的功能已失去其优越性,知识正将自己的进化推理为不连续的、不可修正的、差异的、悖论的。悖谬作为人类思想危机的根源之一,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它是在人类思想活动中嵌入难以解决的问题,使思想在反复的矛盾穿梭中形成一种“不确定性”状态。偶发艺术将创作当成某种矛盾、混沌的行动,正是以荒谬的普遍性为基石的。如此一来,蕴含着思想内容的艺术创作触及具有悖谬性的主体结构后,又通过反映主体结构的悖谬性进一步构成创作上的悖谬性。
(三)创作的游戏性与自由的可能性
艺术创作是人的思想寻求自由的表现之一,而思想的自由是不确定和含糊的。早在1952年的黑山学院“事件”中,艺术便开始探讨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尝试以游戏否定目的,以无目的否定意义。这样做显然不是为了实现传统艺术关于形式美、结构美、现象美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突破那些限制。这是偶发艺术显得反常、粗糙和突然的原因。例如,忽视形式甚至反形式,忽视主题和风格甚至刻意模糊主题和风格,忽视理性和逻辑甚至主张非理性和反逻辑。偶发艺术的冒险活动无疑是为了在无目的的游戏中寻求自由的可能性。
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在《什么是文学?》中论述了创作自由的无止境性质。他认为一个有创作使命感的作者是一个无止境寻求创作自由的人。萨特关于自由的观点对新小说派、荒诞派戏剧及后现代艺术产生了启迪。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中论述了游戏的自由性质。他认为:“游戏本身对游戏者来说,其实就是一种风险。我们只能与严肃的可能性进行游戏。这显然意味着,我们是在严肃的可能性能够超出和胜过某一可能性时才参与到严肃的可能性中去。游戏对游戏者所展现的魅力就存在于这种冒险之中,由此我们享受一种做出决定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同时又是要担风险的,而且是不可收回地被限制的。”[9](p494)。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巴伦(Frank Barron)在其著作《独创性与个人自由》中将独创性与含混、复杂、自由进行了关联。
自由,有时也被看作无政府主义。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反对方法》中通过否认理性和经验表明科学的无政府性,并指出一个不抑制进步的原则“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他还将无政府主义与艺术中的达达主义加以类比,从而成为一个科学的达达主义者。对偶发艺术产生直接影响的作曲家凯奇在1961年为《沉默》一书写序言时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从艺术层面看,无政府主义指代的是对反主流、自由精神的疯狂拥护,一定意义上被看作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美国批评家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称之为反作用的后现代主义,它同样预示着“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10](p145)。“怎么都行”囊括了多种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偶发艺术开展的无固定形式、无固定原则、无确定目的,以及无完整体系的批判活动,实际上追求的就是自由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不确定性”本身。
简言之,“不确定性”是偶发艺术的主要策略,也是后现代艺术进行反艺术、反美学实践的主要动力。利奥塔认为后现代艺术“不受预先定下的规则的主宰”“拒绝正确的形式”,善于表达“不可表现之物”[11](p118),因而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源于此,他认为艺术家常常处于哲学家的位置。德里达提倡的“解构”使创作成为一种不具固定结构、不含确定意义且无始无终的自由活动,为文化的自由发展开辟了无限前景。与偶发艺术有所交叠的还有同期的波普艺术和激浪派。吉姆·戴恩的《车祸》(The Car Crash,1960)、奥尔登堡的《在商店的日子》(Store Days,1961)既可看作波普偶发艺术,亦可看作激浪派的即兴活动。当然,与偶发艺术有所交叠的还有随后的身体艺术、大地艺术,这些运动是对偶发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四、结语
“不确定性”用美国学者哈桑的话总结就是:“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叛逆、变态、变形。”[12](p186)严格地说,偶发艺术的“不确定性”不应被“确定”,而应采用断裂、碎片、开放、无中心等方式探析,才能最大可能地显现其“事件”性质。偶发艺术的作品亦不能固定化、永久性地看待,它是自身不断更新和再生的一个过程,“是持续不断地、反省性地与世界发生碰撞,其中,作品远不是这一过程的终点,而是其意义的后续研究的发起者和焦点”[10](p245)。
诚然,世界万物都是在“褶皱”式的运动中渗透和交错的,其中充满着数不清的不可确定的“事件”。这些“事件”没有黑格尔认为的那种“必然性”。这是由于“不确定性”存在于一切“必然性”之中,任何一种“必然性”都有可能遭遇“不确定性”的侵入和干扰。就此而言,“不确定性”弥漫于知识现象的种种层面。因此,以“不确定性”面对文化现象的复杂多变,才能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并开辟多元的解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