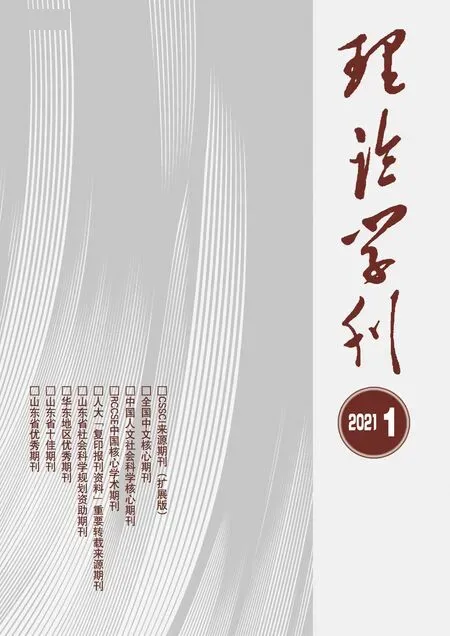论马克思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超越
刘晨晔,杜 立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1;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素以其开创的先验哲学体系著称,而这样一个宏观且晦涩深奥的哲学体系离不开康德发动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康德主张重新对理性进行自我认识,他通过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颠倒知识与对象的关系,回答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发动了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为重建形而上学开辟了道路。。基于这场“哥白尼革命”,康德的哲学体系成为一种先验哲学体系,其伦理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则表现为一种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的先天的道德律,康德将其视为道德形而上学的最高价值标准。显然,康德要试图建立的是一门抛弃了一切经验性的纯粹理性的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但是,康德的道德范畴是基于先验哲学体系下的道德,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一切感性经验谈论道德的高尚,却并未说明如何在现实中进行道德实践,这个问题不仅反映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分裂,更反映了康德先验哲学体系内部出现的二律背反。由于在道德的目标和实现之间出现一系列鸿沟,康德的先验性道德被置于遥远的天国无法于现世实现。由此,马克思基于其唯物史观视野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加以批判。马克思从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出发,以唯物史观为视角,将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下的道德转换为物质基础上的道德,从而为人类的道德诉求提供了现实指导。
一、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
在论述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内容之前,需要先对道德形而上学的由来进行简要阐述。
首先,何为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伴随西方哲学家们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究竟何为世界的本质或本源?所以,形而上学其实就是一种对事物“是其所是”的追问。作为一种询问事物本源本体的理论体系,形而上学首先在自然领域内发展起来,成为“自然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Natur)。自然形而上学旨在探索机械的自然界所蕴含的自然规律。在康德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自然形而上学。在自然形而上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道德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但到了康德这里,为了改变道德哲学的地位,康德发动了一场哲学领域内惊天动地的“哥白尼革命”,建构起一套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并将其提升至主导地位。
与自然形而上学在自然界寻找本源相对,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其实就是在为道德寻找一种本源。也就是说,道德形而上学其实是在为道德寻找一种正当性依据,以及利用这种正当性依据去解释人为何要履行职责以及依据什么去履行职责。早在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康德就提出道德形而上学概念,并给出如下界定:“不以任何人类学(即不以任何经验性的条件)为根据的纯粹道德学。”(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5页。在此之后,1785年康德又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的前言中提到过“双重形而上学”,而1797年《道德形而上学》一书的出版才真正标志着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康德对道德形而上学作出论述,在书中他将道德形而上学分为法权论和德性论。在康德那里,法权论是来自于外部法律立法的强制,而德性论是来自自身内在世界伦理立法的强制。可见,康德其实是将德性义务作为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相比之下不难看出,在本质意义上,“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是处于并列地位的,正如“自然形而上学”是纯粹物理学而非经验性的部分一样,“道德形而上学”也是纯粹伦理学而非经验性的部分。但二者的内涵存在不同,“前者包含出自单纯概念(因为不包括数学)的、有关万物之理论认识的一切纯粹理性原则;后者则包含先天地规定所为所不为并使之成为必然的那些原则”(3)陈文珍、舒远招:《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建构到马克思的道德意识形态批判》,《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理解为“自然形而上学”在道德领域中的、具有至高意义的纯粹形式化的表现。由此,康德总是强调一种“头上的星空”(自然规律)和“内心的道德法则”(道德规律)。应该说,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目的就是要树立起道德的最高准则,从而建构起一整套伦理学的概念,如命令、义务、意志和善等,并将其视为道德领域的最高标准。
(一)合乎动机的道德法则
在康德那里,道德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出于结果的道德和出于动机的道德,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详细论述了这两种道德,并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三大认识能力作为这两种道德行为的依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阐述了人的三种认识能力,即感性、知性和理性,在道德现象的研究中,康德将感性和知性置于同一层面,而将理性作为另一层面分析进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首先提到感性直观,感性直观是人的认识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人们认识到的是进入到时空中的事物,即事物的表象,人在这个阶段接受到的是在物自体的刺激下通过感官接受事物的表象,这是以经验为基础而获得的判断。但感官经验总是变化的,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也意味着由感官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而知性则为自然立法,知性的功能在于对感性直观提供的材料(表象)进行整理,即将感性获得的杂乱无章的材料进行整合。但是,知性作为一种范畴虽然可以整理统合杂乱的感官表象,但其认识对象最终也只能运用于感官经验现象而非超验的物自体。这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感性和知性作出的简要说明。与表象相对,物自体是事物表象的来源,是无法进入到时空中的事物,感性与知性不具备认知物自体的能力,唯一能认识物自体的只有纯粹理性。由此,康德提出,感性与知性和经验有关,而理性则超越经验,知性虽然将感性经验获得的直观材料进行加工,而这种知识并不完整,其获得的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知识。但人具有追根溯源的本性,即具有一种追求必然性和确定性的本性,这种本性决定了人总要追求一种知识的完满性,这种追求完满性的本质决定了理性的必然出现。理性作为最高的认识能力把通过知性获得的知识再次概括统一,获得绝对的、无条件的、完整的知识。
由康德对感性、知性和理性三大认识能力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逻辑线索:一方面是由自然规律(感性和知性)产生的合乎结果的他律的道德,即感性直观—经验对象—自然规律—假言命令—他律;另一方面是由道德规律(理性)产生的合乎动机的自律的道德,即理性—物自体—道德规律—定言命令—自律。在康德看来,感性经验对应物理学的客观规律,即自然规律的命题,这种命题对应的是一种假言命令,假言命令是一种有条件的命令式,以“如果……就……”的形式呈现,这种命令式完全是以结果为中心的命令式,基于假言命令出发的行动或实践行为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即为了达成某种愿望而不得不去行使的手段,简言之,假言命令的本质就是为了实现其他事情才做某种事情(如果A则B)。比如,“如果我撒谎,我就要受到惩罚”,所以也就意味着为了“避免受到惩罚”这一目的才去行使“不能撒谎”这一手段。康德经常以“童叟无欺”为例对此进行说明,“例如,街头小店,铺面上挂着童叟无欺的金字招牌,而且也确把同样货物,以同样价格售与一切顾主,不论是白发老者还是黄口小儿。这确实合乎‘要诚实’的责任诫律的。然而,小店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诚实的责任吗?当然不是。是出于尊老爱幼之情吗?恐怕也不是。他的真正动机只能是维持店铺信誉,以便更多地增殖财富的完全个人利己的动机”(4)[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所以,这种层面的道德行为是出于他律的“逼迫”下的道德行为,是符合假言命令的道德,这种来自假言命令的符合经验世界规律的道德有着极强的他律性,它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或外界因素影响,而非康德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法则。所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理性是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表现为以责任为动机的道德规律。这样,由于理性自己为自己确立法则,这种法则适用于实践理性的实践领域,这体现为以“应该”为系词和连结方式的命令式,即定言命令。定言命令宣示了主观准则要普遍符合客观规律,是无条件的命令式(A就是B),其目的和手段是统一的,比如要“为了诚实而诚实”,而不是为了利益或者为了避免惩罚才诚实,这就要以理性形式自身而非经验确定。与责任联系便表现为道德规律,这种道德规律是以责任为动机,而非仅仅追求合乎责任的结果,这种责任源于先天的纯粹的理性观念。从康德对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的分析来看,出于假言命令的道德是他律的道德、是经验世界层面的道德,而非康德意义上的纯粹道德;相反,出于定言命令是自律的道德、是纯粹理性层面的道德,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真正的道德法则。
(二)合乎自由的善良意志
通常意义上,意志往往被人们用来表示通过某种坚定的信心与努力去达到人们向往的目的,这样一种过程与状态是意志实现的状态。但是在哲学意义上,意志代表着一种行为的选择,行为选择的背后来自于一种原动力,这种原动力不是外在世界的物质性需求,而仅仅是主体心中唯一的形而上的依据。基于这种哲学意义上意志的内涵,康德将其推向自由意志。那么,意志又如何在康德的推动下成为一种自由意志呢?康德的解决方法是将意志与纯粹理性和自由联系在一起。康德认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不是根据经验质料(欲望),而是要依据形式决定其意志,这就意味着理性所遵守的且唯一遵守的是自己为自己确定的法则,即一个只以理性自身作为自己的法则,这样的意志便是善良意志,即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所遵从的理性法则是意志所固有的,这种自律性的自由意志与上述服从道德规律的意志完全相同。康德提出:“这个道德律是建立在他的意志的自由律之上的,而他的意志乃是一个自由意志,它根据自己的普遍法则,必然能够同时与它所应当服从的东西相一致。”(5)[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63页。也就是说,善良意志之所以具有绝对的价值,并不因为它可以达到一个预定的目标,因为定言命令的特质不允许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去做某种事情,由此,这种善良意志的发生仅仅是因为意识到纯粹理性暗示给自己的使命或义务。因此,基于这种纯粹性与绝对性,康德眼中的善良意志是真正具有绝对价值的意志。所以我们可以概括出善良意志的三个特点:第一,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纯粹的善,是最终获得自由的善。因为它仅仅听从内在理性的指令,这种指令只能在纯粹理性中完成,不受其他任何因素影响,所以康德认为除了来自纯粹理性的善良意志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无条件的善。第二,善良意志是自在的善。这种自在的善来源于上述的定言命令的本质,即善良意志不是为了达成某种既定的目标和所意愿的事情而善,而仅仅是由于其内在的意愿而善,即来自主体内在世界的纯粹理性的绝对律令,由此,自由意志是一种自在的善。第三,善良意志是最高的善。康德将善的意志作为先验的东西预设在人的意志之中,意志的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则所根据的唯一原理,这种自由意志成为人类对道德行为评价的最高标准。
(三)合乎崇高的至善
康德也对至善概念作出详细说明,并且在研究至善概念时也赋予其层层递进的关系。实际上,康德的至善概念应当有四种内涵:一是“至上的善(the supreme good)”,即德性,它规定并引导着幸福;二是“完满的善(the perfect good)”,即它必须与幸福相一致;三是“共同的善(the common good)”,即“伦理共同体”,它既是一个“德性王国”,又是一个“无形的教会”;四是“最高本源的善(the highest original good)”,即上帝,上帝是道德化的上帝。这里重点介绍前两种内涵的善。
第一种善为德性自身,即“最高的善”。康德认为,这种德性是“原生的善”,这种最高的善的德性是“人根据普遍的法则去履行义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出于法则对自然欲望进行自我限制,德性的本质就是这样一种自我限制的道德能力”(6)Immanuel Kant,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56.。从这个意义上,康德的伦理学也被称为义务论伦理学,康德的至善论内在于他的伦理学中。就本质而言,这种伦理学注重义务及其背后的道德律令,其实际意图就是要寻找最高的道德,赋予德性以“最高的善”的地位,这既论证了动机论意义上的善,也论证了人的最高价值——自由、自主、自制。在一定程度上,“在康德看来,纯粹实践理性并不要求人们放弃对幸福的权利,因为德性需要幸福意义上的人的‘实存’,而且如果幸福得不到满足,幸福的欲望可能会‘践踏’德性,甚至败坏德性,……但是,无论是德性还是幸福都不是完满的善,而这种至善又要求德性和幸福的统一来作为欲求能力全部而完满的对象,于是,康德不得不讨论二者的统一关系问题”(7)冯显德:《康德至善论与康德伦理学》,《学术论坛》2005年第4期。。这就涉及到康德所说的第二种善。第二种善是“完满的善”,它必须要求德性与幸福相统一,在康德这里,至善是实践理性的最终对象,是道德与幸福的完全统一,是至高无上的无条件的善。但是,这种至善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涉及“德福一致”。提到至善必然涉及到善恶,善恶是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而善恶又和道德律密切相关,道德律决定善恶,善是对道德律的遵从,恶则是对道德律的悖反。善恶之所以与道德律(定言命令)有关,主要通过福祸对比说明。福祸与善恶相对,但福祸与感性经验相关,因为人首先作为自然存在,受自然法则的制约,满足本能欲望是获得幸福的首要方面;而善恶与人的意志有关,它体现人的意志自由。人们探求幸福的欲望是德行准则的推动原则,这种幸福所遵循的是自然法则,发生在自然界,但德行准则又是幸福发生的原因,这种德行准则遵循的是道德法则且只和物自体有关,所以这成为康德实践理性的一对二律背反。为了实现至善的理想境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康德提出三个公设,即: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无法做到永垂不朽,所以只能通过信仰上帝来超越此生的有限性来达到至善。由此,康德这种所谓完满的至善只存在于其设定的三大悬设的理想中,或者说这种德福一致只能在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下实现。因此,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下的道德形而上学其实是一种披上了神秘外衣的思辨哲学。
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鸿沟
从上述关于康德对道德的定义可知,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他的道德概念是纯粹内省且纯形式化的,因而他的自由观仅仅在形式上才普遍有效,或者说仅仅在他自身设定的先验哲学体系下方可生效。康德提出的无条件的道德形而上学其实是在把经验世界与道德世界相分离的基础上仅仅通过纯粹理性建构出来的普遍有效的形式。因此,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难免出现由物自体和现象的割裂引发出的一系列鸿沟,如感性和理性、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至善和现实的德性之间的鸿沟,这几大鸿沟成为道德从彼岸走向此岸的最大障碍。
(一)感性与理性的鸿沟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人的三种认识能力,即感性、知性和理性。他认为,感性直观是人的认识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人们认识到的是进入到时空中的事物,即具有因果联系的表象,这是以经验为基础而获得的判断。由于人在感官世界中认识那些具有自然因果性的经验对象并受其制约,这就意味着人具有有限性,如“人要活着必须要吃饭”,这种追求现世的幸福发生在经验中,是人满足欲望、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作为伟大精神的立法者,首先是作为肉体存在需要满足自身生存的现实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康德至善的绝对性和无限性相悖,无法为至善提供根据。另一方面,人具有穷根究底的本性,总要追求一种完满性,这种追求完满性的本质决定了理性的必然出现,感官经验所获得的知识不具备普遍有效性,那么理性作为最高的认识能力把通过知性获得的知识再次概括统一,从而超越经验获得绝对的无条件的完整的知识,从而产生了形而上学。由此,人又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人虽然存在于有限的知性世界无法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但仍对至善不断追求。所以理性的这种先验特征又注定了人具有摆脱经验的能力,遵从道德律,如“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从而使得人同时也具有无限性的一面。“吃饭是为了活着”,这是遵守自然法则的表现,而“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这又合乎康德的目的论。在康德那里难免出现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分裂,也可以理解为理论理性(自然界)与实践理性(物自体)之间的分裂。在康德看来,人同时具备这种感性和理性但又无法统一,因为人一旦沾染现世的幸福(如吃饭这种本能欲望活动)就不能称之为绝对的至善或道德法则。于是,康德在理解人的活动时就陷入了有限的感性和无限的理性之间的分裂,使得二者变成绝对对立的关系,导致先验哲学下的人出于生存一只脚不得不踩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另一只脚又踏入了纯粹的理性世界,并且只能借助中介,即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三大悬设来实现。这样,道德就只能通过先天命令式的口气来对人类发号施令,成为披着宗教外衣的道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德在晚年撰写了《判断力批判》一书,尝试通过审美来连接现象与物自体,重在从情感角度弥合这个鸿沟。但是就道德法则而言,这种道德律令依然具有极强的神学色彩。
(二)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的鸿沟
与感性和理性的鸿沟相对应,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是康德物自体和现象分裂导致的第二个鸿沟。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对前面的三大认识能力进行回顾,即感性、知性与理性。感性作为认识的第一阶段,所获得的是感官产生的杂多的经验材料形成事物的表象;知性作为连接经验产生的表象的法则出现,即范畴,对感性材料所获得的知识进行加工,但这种范畴的统一性仍不是最高的统一性,它还是和经验有关,属于经验统觉(经验自我);它还要以判断的统一性为条件,即基于理性的先验统觉(先验自我),这种先验统觉将经验统觉所获得的杂多表象统一在一个意识里,意识的同一性以自我的同一性为前提,所以在这里康德借助先验统觉明确区分了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那种包含着先验的统一的自我意识就是先验自我,经验性的统觉就是经验自我。在这里康德的鸿沟就暴露得愈加明显:感性和知性的统一是经验性的综合统一,这种统一性在于统一那些直接作用于感官的经验材料;理性的统一是先验的综合统一,这种统一在于统一那些不直接作用于经验对象的而是赋予知性以统一性的综合统一性。这与上述感性和理性的鸿沟相吻合,康德赋予先验自我和理性至上地位主张先验自我不可知,因为它统一的是物自体层面的先验理念,这就导致一种先验幻相,由此可以得出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各具不同的特征:经验自我所认识的是可知的现实对象,先验自我所认识的是不可知的物自体。虽然先验自我是认识得以生成的逻辑条件,其具体认识实现的首要条件应该是经验自我。康德只是在抽象的学理层面为道德普遍化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如果按照康德对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的说法,这种至高的道德只是存在于学理层面的崇高幻想,既然由先验自我认识的物自体无法被认知,那么这种来自于神秘物自体的精神只能称之为一种概念意义上的道德,同上帝一起存在于天国,这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三)至善与现世的德性之间的鸿沟
康德的德性论是一种先验的德性论,康德伦理学的终极目标不仅是确立道德法则,而是建构一个以德性为核心的包括诸至善在内的价值体系(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但是,这种至高的德性要摆脱欲望的锁链,使德性作为一种先天的、无条件的法则独立存在。基于此,人类永远无法为“至善何以可能”这样一个命题找到答案。康德提出的德性王国是一个理想国,在康德那里,人以德性为最高价值并服从理性所先天给予的道德法则,无条件的至善要通过康德设定的三大悬设实现,而三大悬设在现世根本不存在,这也意味着这种悬设下的“德福一致”的至善就无法实现。但是,人作为现实的存在又需要实现道德,虽然康德一边提出要照顾感性关切,把幸福与道德规范共同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一边又认为德性与幸福之间的同一性是找不到的,因为德性在现实中不能被任何经验所支撑,沾染感性经验的幸福破坏了道德法则。遵循康德的思路,我们可以对幸福概念作出简要解释:一方面,幸福是人要维持和繁衍生命的本然物性。幸福首先是满足现实的人物质感性活动的幸福,如人活着必须要吃饭,这是人得以存在的必然前提。另一方面,幸福也是人寻求生命意义的应然神圣性。这一层面上,幸福也指来自内心的精神感受,如助人为乐的“乐”就是在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获得的幸福感,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幸福感使得人身心愉悦,获得灵魂的自由。所以,人的肉体性和精神性结合才是完整的内在人性结构。基于对幸福的定义,康德的至善无法实现的原因就在于康德的伦理学分裂了人性整体,使得道德在精神性和物质性之间出现分裂。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康德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彼岸的理想,康德对于道德的贡献在于可以提供哲学依据并以这种抽象的道德原则来要求每个人要自律,但是这种神秘的先验哲学无法承担起在现实中实现道德律的重任。康德的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只能作为一种彼岸的理想成为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如何在现世实现这种至高的德性并使这种道德由天国走向人间便成为康德先验哲学所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要弥补这种分裂必须找到一条从彼岸通往此岸的道路。
三、马克思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超越
康德自由观实际上是脱离了现实世界的纯粹抽象的理想化学说,他将自由推向遥远的彼岸世界并在其中寻找一种精神慰藉,从而忽视了处于现实之中的有着广泛感性的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所以,康德只是从学理上解释了道德的普遍化,但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这种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是康德先验哲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所以要使道德从彼岸走向此岸的唯一途径就是超越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走进唯物史观的道德体系。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超越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唯物史观理论下道德与康德纯粹理性前提下的道德不同,它不是一种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一种基于物质活动条件基础上的道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39页。
(一)主体的重新出场——唯物史观中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的科学也是属人的科学,因此,要说明马克思对康德先验哲学的超越,必须先说明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是如何有别于康德先验的道德主体出场的。在康德看来,人是上帝的子民,受上帝的束缚,上帝是最高立法者,人只有借助上帝的力量来实现联合;而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所以他更加关注人现实的生存处境。马克思找到了康德那里最根本的缺陷,即康德没有意识到任何思想理论都应该是以物质利益以及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基于这种认识误区,康德将这种意志变成脱离了物质生活的纯粹思想上的道德假设。马克思批判了康德以自由意志为标志的道德形而上学,抛弃了康德具有极强虚幻色彩的脱离了现实物质利益的高尚精神。在马克思看来,康德是在抛弃了人的感性需求之后心安理得地谈论善良意志,并且在善良意志的规定下将人的感性欲望和个人需求统统抛到了彼岸世界。但是道德既不是来源于上帝,也不是抛弃了物质活动后的人类纯粹理性的产物,而是来源于个人感性物质需求的实现以及人与人之间物质联系的需要。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个前提。从从事物质活动的人出发,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完全不同于康德的先验自我,他肯定人现实的感性欲望,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作为物质存在的主体,首先满足其自身的基本需求是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道德的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物质利益的作用。这样,马克思使以现实经验为基础最真实具体的人逃离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圈子,同时也彻底反驳了康德将人视为上帝奴仆的主张,粉碎了康德笔下被宗教色彩渲染的人的幻象,改变了人的思维与存在割裂的状态,实现了人的复归。
另外,人类的自由解放不仅是一种理想诉求,更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运动。马克思批判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92页。从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出发,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39页。在这里,马克思找到了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并重新确立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并且从从事感性活动的人出发来阐明唯物史观视野中的道德,从而为道德确立了真正的主体。也就是说,道德在康德那里源于纯粹理性,理性才是道德的终极根据,康德是沿着一条先验哲学的道路,从对一切现实的批判中论述了人内在世界的自由;而马克思则看到个人本质的不断变化以及与社会环境的联系,并强调人的历史性,所以马克思代表着自由研究的经验之路。由此不难看出,康德先验哲学下自由的主体是理性的人,马克思唯物史观中自由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人在康德那里只是纯粹理性的存在者,康德忽略了人同时也是现实的和历史的人,人的本质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由此,马克思对康德的超越之处首先在于肯定了此岸世界中现实经验的人,而不是那种存在于幻想的天国中的抽象的人。同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反驳康德的至善,而是列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和资本家道德沦丧的现实状况,进而指出了康德道德法则的不可实现性。马克思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存在于此岸世界的人改造现实活动的自由王国,在那里人人都将实现“德福一致”。
(二)客体的重新阐释——物自体转为现实客体
纯粹理性认识物自体,且将其作为规范人的道德行为的依据,理性作为最高的认识能力超越经验获得绝对的完整的知识。但问题在于,康德的物自体,如自由意志、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这种物自体是抽象且不被经验世界认知的,因为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人们的感官经验所认识到的事物只能是进入到时空中的事物(表象),物自体无法进入时空中,也就无法变成被人的感性直观所认知到的表象,这种自在之物是超越人的感官之外的存在。康德其实认识到了人在认识和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受动性问题,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能动与受动是相互统一的。由此,康德割裂了现实的感性意义、实践的对象性活动以及现实的人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能动性,从而将认识主体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将认识的客体放置于纯粹理性层面加以理解,从而只能是抽象而无法认识到事物本质。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康德的这一误区,在马克思看来,康德的物自体之所以无法被认知,是因为康德的道德主体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物质实践活动,康德意识到道德律是实践理性的动机,但他忽略了真正的意志应该是以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既然人是从事物质活动的人,那么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可以能动地从事物的现象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不应该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此,马克思在对物质的探索中就批判了康德物自体独立于人之外不可认知的片面性,他抛弃了康德孤立地讨论物自体和人的片面性,既没有脱离物自体去思考人的认识,也没有脱离人的认识去思考物自体,而是以一种唯物的方法将两者进行结合。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人作为感性的客观存在物表明了人的这种物质性,人又通过实践实现了人对外在世界的改造,所以马克思正是运用这种唯物的方法将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超越了康德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论,将抽象的物自体拉回我们真实存在的现实社会之中。在感性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基础上,主体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并对其进行改造。更为重要的是,主体对物自体本身认识的正确与否更是可以通过放置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之中而被检验出来。那么物自体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被认识,康德的物自体在马克思这里便转化为现实的客体。马克思正是通过打通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批判了物自体的概念,提出主体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可以认识物自体并根据事物的本质对其进行改造,从而将抽象的物自体从天国拉回真实存在的现实社会之中。
(三)主客体的统一——在实践中传承
康德所谓的实践与马克思所谓的实践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这句话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体现出在马克思的唯物论中实践的至关重要性。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康德所设定的实践理性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他要通过道德形而上学来确认个体的理性实践的特殊性以及完整性,将实践理性仅仅视作一种最高的价值标准,或者说,康德的实践理论仅限于伦理领域的实践,是仅仅存在于大脑中的意识的实践。与康德的实践理性相反,马克思的实践是基于物质活动意义上的实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是要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向人们证明整个社会理性实践的特殊性与完整性。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其实是一个囊括了多重含义的总体性概念。与康德虚幻的伦理学中的实践不同,马克思的实践更多的是指向现实的经济领域以及社会领域等实际的物质性活动,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处于实践的基础地位。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强调真正的实践是能动的主体在现实社会中创造的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的活动,是主客观相统一前提下人的感性活动。由此,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134页。在马克思看来,康德式的理性思考或者关于纯粹理性层面的自由与平等只是一种只存在于天国的价值指向,可将其作为革命的价值目标,但无法成为现实革命的指导。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颠倒了以往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通过确立人的主体能动性抬高人的主体地位,并且仅把实践理性看作一种用来解释的衡量标准,忽略了任何认识应该都是在实践中得以形成的。由于没有看到现实的人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能动性,康德将认识客体放于理论理性层面加以理解而无法认识到事物本质。所以,康德的最大问题在于割裂了现象界与本体界,将自由置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但马克思则完全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134页。。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代替康德先验的道德主体、以现实的客体代替康德不可认识的物自体,并通过实践活动将二者进行统一。马克思坚信只有实践才能将现实的人与客观世界关联起来,一切认识都来源于人的现实活动并在现实活动中达到对事物的认知。康德仅仅关心道德形而上学的至高无上的理想王国本身,而马克思关心的则是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道德的理想王国,并且利用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揭示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缺陷。此外,实践还包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真正诉诸到革命行动当中才是真正的实践,唯有实践才能引领人们真正走向自由解放,以现实的生产实践为基础,来寻找自由的道路,必然使自由实现于此岸世界。因此,正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视野中的自由真正实现了从理念到实践、从思辨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
总之,马克思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超越性在于:马克思运用辩证批判的方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肯定了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这种双重属性的道德。马克思既肯定了道德的精神性,将道德看作是不同于动物的人类独有的社会意识,同时又反对将这种精神性的道德视为超越物质活动的纯形式的精神。与此同时,基于唯物论视角,马克思肯定了物质对于道德的决定性,提出物质是第一位的、道德的精神性是从属的,物质性是精神性道德的基础。由此,马克思将康德形而上学的伦理道德从虚幻的彼岸世界拉回了现实的此岸世界。如果说康德在虚幻的彼岸世界为人们设定了幸福的终极理想,马克思就是要打破这种虚幻性和欺骗性,唤醒人们对现实生活不平等的控诉。他将人的内在需求和道德理想相统一,科学地阐明了如何真正实现“德福一致”的关系。马克思就是要弘扬以人的物质活动为基础的、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人类幸福生活为终极目标的道德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