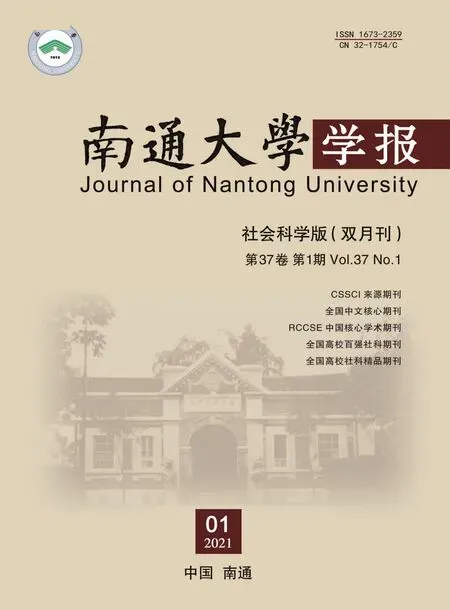语序在汉诗诸体中的功能演变及诗学启示
赵黎明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引论
所谓语序,顾名思义是指句中语词排列的顺序。在汉语语法学界,不同语法学家所用名称不尽一致,有称为“词语次序”的,如吕叔湘、朱德熙等;有称为“词序”的,如黎锦熙、赵元任等;也有称为“语序”的,如张世禄等。在《辞海》里,“语序”与“词序”为同义词。由于汉语是孤立语,缺乏印欧语系的形态变化,语序于是成为句意表达的重要语法手段,“凡文中实字,孰先孰后,原有一定之理,以识其互相维系之情”[1]22,不但古代汉语如此,现代汉语基本也是这样。既然语词排列成为句意表达的有效手段,句子就有正常与非正常之分。黎锦熙说,“汉语乃是各词孤立的分析语,全靠词的排列来表达意思”,而句子则有“正式句”与“变式句”之分[2]7,所谓“变式句”其实就是词的排列有所变动的非正常句子。如何变动呢?当然是应有位置的变动,也就是先后顺序的错动,王力把这种词语变动叫做“倒装”,即“目的语、描写语、叙述词等,有时候不居于它们常在的位置,我们把这种变态叫做倒装法”[3]317。在他看来,这种倒装有时是有条件的习惯性倒置,但有时则是无条件的随意性倒装,后一种现象在诗歌用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实际上,在古诗人那里,这种倒装并不是一种无谓的语言游戏,而是一种非常自觉的诗学手段。在各类古诗特别是近体诗中,古人常常有意使用这种倒错之法,以营造特定的艺术效果。他们将这种做法誉为“诗家妙法”,把经过如此处理的语言叫做“诗家语”,这样的掌故在历代诗话中比比皆是:
东坡《煎茶》诗云:“活水还将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贮月归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状水之清美极矣。分江二字,此尤难下。“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即少陵“红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也[4]140。
古人津津乐道的这类“倒语”,本质上就是一种语序错位,即出于艺术目的而对语词正常次序的有意挪动,具体而言是使“句中的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不在通常的位置上”[5]202,这些“无条件的”倒装现象,在古诗文中出现的规律是诗歌多于散文、近体多于古体。
关于倒装在古诗中的具体表现,语法学界与诗歌学界其实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揭示,它的语法类型无非是这样几种:主语后置,如“东门酤酒饮我曹,心轻万事如鸿毛”(李颀《送陈章甫》),“饮我曹”即“我曹饮”;宾语前置,如“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王禹偁《对雪》),“勤勤谢知己”即“谢知己(之)勤勤”;主宾换位,如“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王维《叹白发》),“须臾白发变垂髫”即“须臾垂髫变白发”;定语前置,如“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生长明妃尚有村”即“尚有生长明妃(之)村”;定中换位,如“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枫林晚”即“晚枫林”;状语前置,如“盘喜黄粱熟,杯余白酒浑”(苏舜钦《晚意》),“盘喜黄粱熟”即“喜盘(中)黄粱熟”;状语后置,如“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王建《水夫谣》),“臆穿足裂忍痛何”即“臆穿足裂何忍痛”,等等[6]7-26。显然,语序错置在古体诗中存在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古人将其视为独特艺术方法也是客观存在的。
为此,本文无意于为语序分析增加若干诗例,也不拟专门与古人的“诗家妙法”唱反调,而是拉长时段观察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语序是不是汉诗古今通用的艺术手段?在汉语诗歌的千年演变中,语序的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代诗歌排除了语序错综,是否意味着与“诗语”“诗性”失之交臂?既然不再依恃语序,现代汉诗如何实现新的“诗性”、创造新的“诗语”?这些追问都涉及一个核心疑问,即新诗的散文句法是否具有诗歌文体合法性的问题。
一、诗句“错综”的历史演变
作为语法结构的一部分,语序在古今诗歌中的变化,也和其他语法形式一样,经历了散—韵—散的“U”字形轨迹。如果把古体、近体、词、曲视为古代诗体的不同成长阶段,那么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除了中古之后“律化”的扭曲之外,诗体前后两端都是与散文无异的自然语序。揭示这一事实,并不需多少细致的语法分析,只需看看几个阶段的诗例就可了然:
先看古体诗。不论是《诗经》还是《楚辞》,不论是两汉乐府还是各类歌行,语序都是自自然然的,看不出任何矫揉之处: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周南·汉广》)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楚辞·离骚》)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门合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乐府·上山采蘼芜》)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观沧海》)
据此,王力先生判断,“古体诗的语法,几乎完全是古代散文的语法。我们说‘几乎’,因为有若干虚字的用法似乎是古诗所特有的……凡写古风,必须依照古代散文的语法;若连用散文中所无,而近体诗所有的形式,就可以认为语法上的律化。”[7]219这里,王力所说的“形式”虽专指虚字用法,其实语序情形也应包含在内。据他的观察,这个变化上限可溯及梁齐,而成熟则在中晚唐之后,“到中晚唐以后,七古就渐渐趋于律化了。除了语法上的律化之外,还有修辞上的律化。从语法和修辞两方面看,律化的情形更为明显”[7]226。这说明在整个唐代律化现象已经波及古体诗,并对诗歌句法也产生影响了。
至于近体诗,律化程度就更为深广了。需要指出,所谓诗体“律化”,实际上是一种整体律化,不光指平仄、对仗等格律要素,还包括虚词、语序等语法因素,因此,“倒装”成为诗人“炼句”——实现诗意的一种常用手段。实际上,语序颠倒,并不仅见于诗,散文中也常出现,如否定或疑问句中宾语提前或谓语后置(“时不我待”“微斯人,吾谁与归”等),就是典型的倒装形式,因此在古诗人眼里,这种语言的习惯性倒装,不能算是诗歌意义上的倒装。作为诗学方法的倒装,应该是“出其不意”的倒装,亦即超出常规语言惯习的“陌生化”诗艺手段。语言学家王力把这种诗人随意为之的倒装,称为“无条件倒置”,也就是超出散文语法规范的诗语颠倒。他结合唐诗创作,总结出诗语颠倒的五种情形:其一是主谓倒置,如“夜足沾沙雨,春来逆水风”(正常语序为:夜则沾沙之雨足,春则逆水之风多);其二是目的语倒置,如“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正常语序为:三湘接楚塞,九派通荆门);其三是主语和目的语都倒置,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正常语序为:风折之笋垂绿,雨肥之梅绽红);其四是主语倒置,目的语一部分倒置,如“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正常语序为:鹦鹉啄馀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其五是介词性的动词倒置,如“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正常语序为:片云共天远,永夜同月孤)[8]277-278。
不过要是细究起来,有些语言现象还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看起来是“倒置”,其实是其他结构,蒋绍愚先生就揭示了“假倒装”的几种情况:第一种是述宾结构被误以为倒置,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其中“飞白鹭”“啭黄鹂”,就是“述语+宾语”,而不是主谓倒置;第二种是通常认为是述宾倒置,其实是“主语+谓语”,如“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就是一个包孕句,即主谓结构中又套一个主谓结构;第三种是人们以为是“宾+述+主”的倒装形式,如“薰琴调大舜,宝瑟和神农”,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被动句,顺正的表述应该是“薰琴调(被)大舜,宝瑟和(被)神农”,或“大舜调薰琴,神农和宝瑟”。[5]206-209在他看来,唐诗真正的倒置,只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主谓倒置,如“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王维《出塞作》)应是“天骄猎”;二是述宾倒置,如“竹沾青玉润,荷滴白珠圆”(白居易《秋霖即事》)应是“沾竹”“滴荷”;三是定语倒置,如“远劳从事贤,来吊逐臣色”(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应是“贤从事”;四是状语倒置,如“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韩愈《永贞行》)应是“未曾见”,等等[5]213-216。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相对于其他古诗体,倒装现象在近体诗中表现比较突出,但在近体诗自身演化过程中语序变动程度并不平衡,早期打有古体诗印记,后期则受散文影响,因此倒装等变态语法在近体诗的演变也呈现出“U”字结构。特别在后期,语序变化基本恢复到散文状态,演化节点跟近体诗的“唐宋之变”大体吻合。“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9]1195,所谓“以文为诗”,实际上是指由韩愈开其端绪、苏黄发扬光大、江西诗派延续余脉的“宋调”传统;其与“唐音”不同之所在,不单表现在感性、知性的差别,也体现在字法、句法、章法、手法的不同。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六月二十日渡海》)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黄庭坚《登快阁》)
诗里不仅有胡适所谓的“自然的说话口气”[10]133,还有平顺的语序表达,所有这些都是所谓“文”的内容部分。
作为诗的变异形式,词是很复杂的文体,一方面保留音乐文学的某种痕迹,时常被诸管弦;一方面又脱胎于近体诗,有着严格的格律,“词的来源,可以从两方面来说:若是从‘被诸管弦’一方面说,词是渊源于乐府的;若是从格律一方面说,词是渊源于近体诗的”[8]537。而在某些方面则更接地气,是更自然的文体,谓其为古诗时代的口语诗也不为过: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争忍有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林逋《长相思》)
近日门前溪水涨,郎船几度偷相访。船小难开红斗帐。无计向,合欢影里空惆怅。
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重愿郎为花底浪。无隔障,随风逐雨长来往。(欧阳修《渔家傲》)
这些作品不仅全是活泼口语,而且语序自然,全然没有近体诗中矫揉倒错现象,所以钱锺书说“词之视诗,语法程度更降”[11]250,所谓“更降”当然是指向散文或口语的靠拢。当然,为了表达需要,词也偶有倒装现象,其情形与近体诗差不多:有主语后置的,如“春回常恨寻无路,试向我,小园徐步”(晁补之《金凤钩》),“试向我,小园徐步”系“我试向小园徐步”;有宾语前置的,如“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李煜《虞美人》),“尊前在”系“在尊前”;也有主宾倒置的,如“龙如骏马,车如流水,软红成雾”(向子《水龙吟》),“龙如骏马”系“骏马如龙”;另外,也有述宾结构整体提前的,如苏轼《江城子》“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亲射虎,看孙郎”系“看孙郎亲射虎”,等等。
最后落到曲。曲是词的进一步变化,变化的表征就在于“有无衬字”[12]9,也就是说相对于词而言,曲加上了更为散文化的衬字即虚词,语脉更为连贯,语序更为顺通,庶几接近于日常口语了:
会真诗,相思债。花笺象管,钿盒金钗。雁啼明月中,人在青山外。独上危楼愁无奈,起西风一片离怀。白衣未来,东篱好在,黄菊先开。(张可久《中吕·普天乐·秋怀》)
风飘飘,雨潇潇,便做陈抟睡不着。懊恼伤怀抱,扑簌簌泪点抛。秋蝉儿噪罢寒蛩儿叫,淅零零细雨打芭蕉。(关汉卿《双调·大德歌·秋》)
因此,抛开唱与韵的因素,曲实际上跟白话诗十分接近了。正是因为词曲摆脱了近体诗格律和语法束缚,所以胡适认为它们同属中国诗体的“第三次解放”[13]163-164,跟其倡导的白话自由诗只有一步之遥。
二、“唐人句法”的成因、功能及限度
从上述简单梳理不难看出,诗句“错综”主要体现于近体诗中,而在近体诗里又集中出现在唐人诗句中,可见语序倒装并不是古诗普遍现象,而是唐诗语言的特有现象。这种认识并非笔者发明,古人早有类似说法。明人李东阳说,“‘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岂不佳?终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诗家语。”[14]63在以唐诗为艺术圭臬的明人眼里,诗例中所谓“唐人句法”、“诗家语”等,指的主要就是语序的倒置(“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实为“露下落芙蓉,月中杨柳疏”)。这种语法手段,主要由唐人开启,因此集中体现在唐诗之中,“句法有倒装横插,明暗呼应,藏头歇后诸法。法所从生,本为声律所拘,十字之意,不能直达,因委曲以就之,所以律诗句法多于古诗,实由唐人开此法门。”[15]1571唐人发明的这种手法,因为可以造成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而常被后人摹仿,也常为诗家所称道:
倒一字语乃健。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扶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16]9026。
诗用倒字、倒句法,乃觉劲健。如杜诗“风帘自上钩”“风窗展书卷”“风鸳藏近渚”,“风”字皆倒用。至“风江飒飒乱帆秋”,尤为警策[14]272。
实际上,这种“劲健”的“诗家语”,固然可以造成某种艺术惊奇,但其背后往往有不得已的语文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对韵律对仗的迁就。王力先生认为近体诗的倒置,八成都是由于韵脚、平仄的原因而造成的。在前面所列的五种倒装情况中,第一种至第三种是因为“韵脚关系;如果不倒装,必须改变韵脚”,第五种则是因为平仄的关系,不倒置则犯了失对的毛病[8]279。蒋绍愚先生也认同这种说法。他以李商隐《今月二日》和杜甫《遣意》为例,认为两诗中分别使用“薰琴调大舜,宝瑟和神农”“云掩初玄月,香传小树花”,而不说“大舜调薰琴,神农和宝瑟”“云掩初玄月,小树花传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平仄、对仗的需要。要是采用上面那种常见的句式,‘大舜调薰琴’就是三平调,而且出句的句脚用平声(琴),对句的句脚用仄声(瑟),都不符合平仄的要求。‘小树花传香’也是三平调,而且和‘云掩初玄月’也不成对仗,所以必须说成‘香传小树花’”[5]212。因此,抛开古人“诗家语”等模糊的溢美之词,近体诗采用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多半还是为了迁就平仄对仗等诗律要求。
某些艺术需要也是倒装的重要因素。不过,与其说是倒装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它的结果,由于打破了语句的原有秩序,阻断了语意的正常流动,因此延缓了读者获得意义的时间,同时产生一种“陌生”之感,这是不少人认识到的倒装的艺术效果:“在诗的句法中,中国诗语的倒装最适宜于对所谓‘反常化’或‘陌生化’的解释。由于声律的限制和表意的考虑产生语序的倒装,就与日常话语表达的顺序相反,因不顺产生‘陌生’的感觉;而且倒装倒置的语句屈曲延缓了读者感知字句的时间……”[17]280为了造成“生”的感觉,产生奇异的效果,有些诗人故意颠倒词序,比如老杜的“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倒置不倒置于韵脚和对仗都无妨碍,但是一经倒置就显得“特别新颖,不落平凡”。“‘鹦鹉粒’和‘凤凰枝’,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所啄馀者已经不是普通的香稻,而是鹦鹉之粒,所栖老者已经不是普通的碧梧”,因此都是“妙手偶得”的“警句”[8]279。还有学者根据现代心理学知识,认为倒装这种变异的语法手段,不仅造成陌生效果,增强阅读难度,而且产生更强的心理刺激。“这类极为常见的词语离析并倒装,消解其静止的意象形态,使其在新的语言关系中获得运动的活力。同时这种离析和倒装由于背离人们读诗已形成的语法习惯而使阅读变得困难,用西方格式塔心理学的说法,这种对习惯的背离可以造成更大的‘完型压强’,产生更强的心理刺激力。”[18]475
倒装带来的艺术效果,当然远远不止这些,突出意象、排除知性因素,其实也是唐诗乐于采用“错综句法”的原因之一。唐人重感性、抑知性,重意象、反议论,在诗中把某些意象提到显著的位置,如把“知湖外碧草,见海东红云”中的“碧”和“红”,分别提到句首变成“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杜甫《晴》),就使整个诗句变得更为具象,也更具直觉意味。另外,语序错位,客观上可造成诗的复义或朦胧,也是可以想见的事实。因为“这种被重新排列组合得错综颠倒的诗句整个儿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使原来依次呈现的直线过程变成了平行呈列的叠加印象,而怎样叠加,怎样组合,则完全可凭读者审美经验”[19]67。
此外,倒置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或造成了另外一重艺术效果,就是话题驱动、焦点突出。把需要突出的话题或焦点提到醒目的位置予以强调,被认为是汉语“主题句”的一个显著特色,近体诗中很多倒装多是话题驱动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倒装。基于这种语言认知,有学者认为老杜被热炒千百年的“鹦鹉啄馀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其语言倒错既不是平仄规则的限制,也不是别的因素所致,而是出于“主题句”需要,“因为这首诗是关于秋天的,用‘香稻’和‘碧梧’作主题能给人很丰富的、有连贯性的联想,而用‘鹦鹉’和‘凤凰’则无”[20]93。话题驱动的例子还有几种:第一种情况“句首的名词和名词语很难说是主语,却可以说是话题,全句也就是一个‘话题+述题’结构”,例子有“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小寒食舟》)、“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第二种情况“句首的名词很难说是状语、定语还是主谓谓语句中的主语”,如“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山寺》)等;第三种情况是“明显的主谓谓语句中的大主语同时也是话题”,如“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陪诸贵公》),等等[21]299。
“唐人句法”的肇因及其艺术效果,当然不止上述几条。从古诗语言的特殊需求来讲,区区五十六言(或二十八言)之内,要照顾音律,又要避免“过熟”,难免要对语句进行特殊处理,这是可以想见的。另外,在讲究“诗文之辨”的古人那里,欲造成想象的跳跃,不打断散文语脉,也无更好办法可想,因此,倒置自然成了作诗之法,“错综句”也因“诗家语”而备受青睐。然而,凡事太过都会走向反面,当诗家将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作为写诗不二法门广泛推崇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走上了与诗的“本质”越来越远的道路。它不仅阻隔了情感的正常表达和交流,而且将“诗性”寄附在扭曲的文字形式上,这不但背离了诗性的本质所在,也妨碍古人奉为诗歌圭臬的“自然”之旨。因此,包括提倡“炼字”的诗家,对“用工太过”的做法,也多有微词,比如对人们津津乐道的“红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魏庆之就批评其“可谓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处,不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为天然自在”[16]9021。实际上,如果跳开近体诗,将观察的视域拉长,从汉语诗歌的整体发展着眼,倒装之法并不足以成为诗性实现的必然手段,因为事实非常明显:在近体诗之前,一般没有语序变异,古体诗的诗意传达并不受到根本影响;在近体诗之后,词曲采用自然语序,并不妨碍其传情达意功能的实现;特别是白话自由诗,没有颠三倒四的语句错综,照样能完美表达幽微的感情、复杂的意绪。
三、“错综句”在新诗中的命运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作为古诗立足之本之一的“诗家语”“唐人句法”,在古诗中的演变趋势是重要性逐步降低:于宋诗中已有改变,于词曲中变化更大,于白话新诗中基本失去效能。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在新诗中完全绝迹,也不是说使用倒装就会妨碍诗意表达。个别诗人出于特定修辞需要,在某些地方变动一下语序,有时候也还是存在并有一定艺术效果的,比如“忽然一个右转,最咸最咸/劈面扑来/那海”(余光中《车过仿寮》),为了突出“右转”动作和“扑面而来”的风,将主语“那海”置于句尾,颇能显出风景的层次性,造成艺术的陌生感。然而,从整体上讲,这只是少数诗人的特殊偏好,并不构成现代诗艺的主流,更谈不上“诗家语”(本体论)意义上的艺术成规了。
这一重要改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诗歌语言自身进化的产物。严羽只知批评宋人“以文字为诗”等有碍抒情诗正统,不知道这文字变化中包含的是诗歌的历史进化趋势,更不知道这“文字”之中,不单有文语、文句,还有散文语法。宋人把说话的方式、散文的语法带入诗中,带来的诗歌语言的“唐宋之变”,不站在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是无法看清楚其变化趋势的。相对于典型的唐诗,只消看几首宋诗,便可知晓这种变化: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篓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轼《惠崇春江晓景》)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气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应灯火是渔船。(秦观《金山晚眺》)
这些诗例除了亲切可人、如出口语之外,语法都是平平顺顺的自然语序。宋诗这种“以文为诗”的做派,被五四新诗加以肯定和继承,“作诗如作文”作为一个诗学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语序颠倒于是作为不“自然”文学之典型症候而被推向了历史的反面。胡适的“自然”诗学所含内容十分广泛,有自然的性情、自然的节奏、自然的言语(口语、俗语),等等,这里面显然也少不了“自然的语序”。在他眼里,中国诗体的演变趋势就是一个语言逐步走向自然的历史,“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轩词:‘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此绝非五言七言之诗所能及也。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一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语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语之自然也。”[22]在此,他专门挑出近体的“不通”说事,所谓“不通”在他那里就是语序的颠三倒四。这时,历代诗人津津乐道的杜诗句法,被新文学作家作为反面教材加以警示。钱玄同在与胡适有关诗歌句法的讨论中,特别指出了旧诗文的“文法不通”之弊:“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实‘危心坠涕’也。杜诗‘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香稻’与‘鹦鹉’,‘碧梧’与‘凤凰’,皆主宾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23]胡适随之加以借题发挥,指出文法不通的律诗都“做不出好诗”,“这都是七言所说不完的话,偏要把他挤成七个字,还要顾平仄对仗,故都成了不能达意又不合文法的坏句。……他如‘羯胡事主终无赖’‘志决身歼军务劳’,都不是七个字说得出的话,勉强并成七言,故文法上便不通了。——这都可证文言不易达意,律诗更做不出好诗。”[24]于是,颠覆古诗语句错综之法成为五四新诗文体革命的重要义项之一。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草创时期的新诗在语法层面再也不把语句错综视为诗歌手法,大量的作品不仅平白如话,而且语序自然,全然没有了古诗语中的矫揉之句。下面这种例子在新诗中占据着绝大的比例: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
(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的诗中,天上飘微云,地上吹微风,微风吹头发,月光恋海洋,都是毫不扭曲的词序。再看周作人的《小河》,也是把近体诗中靠“扭断语法的脖子”制造诗意的作风扫除精尽,全是一派散文的、口语的自然语法:
一条小河,稳稳地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果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
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
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
……
(周作人《小河》)
自此我们看到,至少从事实上来讲,作为诗学手段的错综语序,在诗歌的历史舞台上基本失去效能。现代诗人中没有哪个诗人还愿意对这种“雕虫小技”倾注心思,也没有哪首诗歌杰作是靠这种文字功夫取得成功的。这类例子太多了,如穆旦《诗八首》:“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等等,每一句话都成分齐全,每一句话也都排列有序,但丝毫不妨碍想象的跳荡腾跃,也丝毫不影响诗歌的复义效果。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语序(“诗家语”之一)的本质是什么?它是诗的本体还是一种辅助手段?
这不能不牵涉到诗的本质。什么是诗?什么诗性?这个问题看起来十分简单,细究起来其实复杂无比。过去,一般把专于抒情且有韵律的文字通称为诗,现在看来这种传统定义充其量只描述了诗的显像特征,并没有道出它的深刻本质。诗是什么?诗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道”,是诸神的秘密暗示,是永远无法道出的语言,而被诗人捕捉到、形诸文字的不过是它的部分显像,所以,当我们谈论“诗”时一定要把这被显现出来的部分与无法显现出来的部分分开,前者类似于言语、现象,后者才是语言、本质。如此看来,作为文字形式的诗体,不论是旧体还是新体,不论是中体还是外体,其本质都是功能性的,即是通达诗的桥梁,而不是诗性本身。分清了这一层,始可以谈诗体。在传统文体家眼里,一提到“诗”就把它与音韵节奏等同,诗有固定的格律被视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在中国语文中格律则进一步窄化为对仗押韵等文字语音要素。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和做法是误把显像当本体,真正是“舍本”而“逐末”,因为通往诗性的道路千万条,有格律的文字不过是其中一条。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新诗从破除“诗的文字”开始,探索通往诗意本体的各种可能途径,切实击中了传统诗体的某些要害。
搞清楚了这一点,再来分析所谓“诗家语”的本质。从杜甫等诗人创作实例以及后代诗家的点评来看,不管是“诗家健法”还是“诗家语”,语序倒错本质上不过是迫于平仄对仗等格律要求而做出的特殊文字安排,简言之,不过是依附于格律的文字小技;至于其朦胧多义等艺术效果,其实是这种手法的一个意外收获。当然,对于这种艺术效果,还是应该部分肯定的,因为不论古今还是中外,语义的多义性、诗意的朦胧性,乃是诗歌的文体特性所在,“含混性(ambiguity)是一切自向性话语所内在固有的不可排除的特性,简而言之,它是诗歌自然的和本质的特点。我们欣然同意燕卜荪的一个说法:‘含混的妙用根植于诗歌的本质’。”[25]199在近体诗的有限尺幅之内和有限的手法之中,语序倒装不失为一种一时有效的艺术手法,然而将其视为古今通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诗歌手段,就有些言过其实了。实际上,同写近体的宋人已经意识到这种方法的局限了,宋人“以文为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对此的“纠偏”举动。由词到曲直至新诗的语言演变事实,也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宗唐者所推崇的“诗家语”,其实应该是“唐人语”,是诗歌发展一个特定阶段的形式,对于汉语诗歌来说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我们一步步地否定了古诗的文体禁律:诗不必有固定的格律,因为节奏也有不同的形式;诗不必有固定的格式,因为散文的制式也是很好的诗;诗不必在语言上颠三倒四,因为正常的语序也可以传达幽微的诗意……那么,如何才能传达这幽微的诗意呢?这里面要分两层来说:第一,不管是新体还是旧体,都是捕捉“神的暗示”(荷尔德林)的文字形式,二者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第二,作为暗示形式的言语,不确定(多义、朦胧)的暗示语言,可以选择多种方式,这些方式有断裂的、颠倒的,也有连续的、顺序的。实际上,就现代汉诗而言,很多作品每一句话都成分齐全、顺序分明,然意绪则朦胧闪烁,意义游移不定,篇幅所限,举一短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断章》)繁复意义的制造并不仰仗字句的有意倒错,而是靠诗歌内部空间的特殊处理。
古人使用错综字句,有一个艺术目的,就是制造“生”的艺术效果。这种避免艺术过“熟”而刻意使用的“生”的方法,与形式主义所称道的“奇异化”颇为相似,“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26]10。对于古人的这种“陌生化”追求,我们当然应该肃然起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制造陌生化并非仅有矫揉文字一途,其他方式照样可以实现,词曲直至新诗的大量实践足以证明这一点。
四、结语
总起来看,基于汉字和近体诗的特殊情形,语序作为艺术手段在汉诗的发展史上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对此我们不能一概加以漠视和否定,然而对这种作用也不应过于夸大,更不宜将其作为艺术通则甚至诗歌本体来看待。通过对语序问题的历史考察,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些启示:正如“只管抓着韵律的问题不放手”[27]22并未触及新诗体建设的核心一样,老是纠缠于文字形式的细枝末节,老是斤斤于语序之类的传统成规,其实并未抓住中国诗体发展的要害,也没有触及新诗问题的核心。中国诗体发展的要核是什么?是“诗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的适应与否问题。在新诗发生之初,胡适对中国诗体症候的判断是形式与内容不适应,因此开出了“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把以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的药方[28]193。胡适强调了创作的“自由”,强调了文的形式,但却止步于“文”。废名在胡适基础上更进一步,在“自由”之上加上“诗性”,在“文”之中再加上“诗”:“我乃大有所触发,我发见了一个界线,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27]12废名说这番话的时间是20 世纪30 年代,半个多世纪的新诗发展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不过现在看起来,他们二者合起来才够完美。对于中国新诗建设来讲,如果不是出于诗性内容的内在需要,包括语序在内的一切艺术手段,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