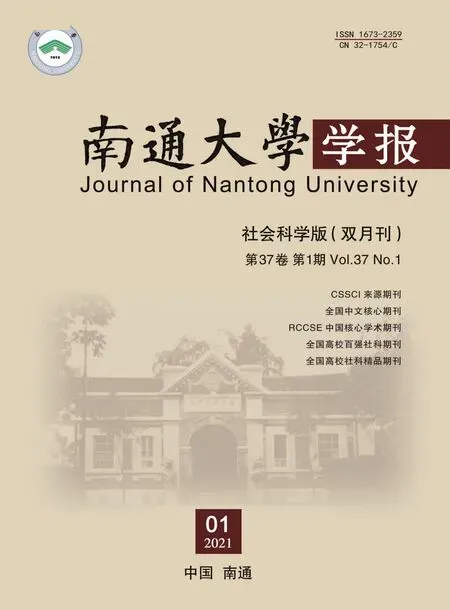论侵权法中恶意的界定及运用
董春华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缘起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恶意是一个高频词。在北大法意数据库“法律法规”分项之下,以“恶意”为法规标题搜索,有36 项;以“恶意”在标题和正文中搜索,有14 010 项。恶意串通、恶意造成他人损失、恶意抢注商标等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恶意”,但这些法律法规中的恶意究竟何指,却不得而知。
我国侵权法学者对恶意的性质研究较多。一些观点指出,恶意是动机,即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恶意指行为人在从事民事行为时,明知其行为缺乏法律根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1]8“恶意是指故意心态中之恶劣者,含有明显的加害性追求。”[2]54另有观点指出,恶意是直接故意。“恶意是行为人对禁止性法律规定和他人受保护权益的公然漠视,是行使正当权利时显然以追求他人之损害为目标或主要目的的一种直接故意。”[3]443“恶意并非一类独立的过错类型,其性质上属于故意中的直接故意。”[4]265-266还有观点指出,恶意是动机,也是无正当理由从事违法行为。恶意“指无正当理由故意从事某种违法行为,具有不正当的动机”[5]234。“恶意为最高程度的故意”似乎作为通说已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这些观点均未深入探讨恶意在侵权法中的地位及其运用。
司法实践中涉及恶意的诉讼较多,以知识产权领域为甚。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单列为民事诉讼案由。尽管《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中文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以及《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正面列举和反面排除的方式详细规定了何为恶意,而法院仍只能在个案中界定“恶意”,无法形成统一的规则。知识产权领域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侵权人判定高额赔偿的案例并不多的原因之一是侵权人主观“恶意”的确定难。
法律法规高频使用“恶意”却未使之含义愈加清晰,学者对恶意的界定有简单化之嫌,也未深入探讨恶意在侵权法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司法实践对“恶意的证明标准”无所适从。本文尝试依据侵权法相关理论和学说回答以下问题:恶意所指到底为何?法律法规所指恶意有何特殊?恶意与故意何种关系,故意可否取而代之?恶意在一般侵权中是何种地位,哪些特殊侵权的责任构成需要恶意?这些侵权脱颖而出成为“异类”的依据是什么?一项形式合法的行为如何基于恶意构成侵权?
二、恶意的概念及其与故意的界定
(一)恶意的概念及其含义的类型化
古今中外,最早实质意义上考察恶意在侵权法中之地位的是英国和美国。我国有学者认为,“英美法系民法中多以‘bad faith’来表示恶意”[6]45。在英美侵权法文献中,“malice”“bad faith”及“willful”都可被译成恶意(的)。Malice 在侵权法中指代恶意,指基于不当目的而为,主观上非常自私、恶劣。Bad faith 在诸多场合与good faith 相对,涉及欺诈、误导、欺骗他人,或忽视、拒绝履行某项法定义务或合同义务,是邪恶的动机,适用最多的是保险法领域。Willful 常见于知识产权侵权中的“willful infringement”,译为恶意侵害,虽也是积极实施一项行为,更偏向故意。因此,malice 恶性程度最高,bad faith 次之,willful 倾向于故意。恶意有多种含义,可总结为四种:“怨恨或仇视;故意实施非法行为;无正当理由故意导致损害;任何不当或不好的动机。”[7]366
第一,恶意指怨恨或仇视。这是恶意最原始之意,也是口语上的意义,非法律术语。英国法发展早期,法院认定恶意即为仇视和报复:“当一个人被报复或其他坏情绪和愿望所驱使,选择致他人损害,即存在恶意。”[8]484但在后来的诸多案例中,法院明确表示不应狭隘地解释恶意。因此,英国法院很早就抛弃了对恶意的口语意义上相对狭隘的理解。
第二,恶意指故意实施非法行为。该种含义意味着恶意与故意无异,这与我国一些学者对恶意与故意的界定一致。故意既是侵权法主观构成要件“过错”的类型之一,也是英美法中故意侵权类型的责任构成要件。故意实施非法行为包括故意和非法行为两大关键要素。实施非法行为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若有损害并满足因果关系要件,故意的主观状态会导致侵权责任的发生,这与恶意的基本含义不能等同。这样的界定更符合一般故意侵权,而非恶意侵权。
第三,恶意指无正当理由故意导致他人损害。该种界定与美国侵权法中的“表面侵权”规则和法律之恶意的含义类似。表面侵权是指采用合法的手段,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形下故意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①Aikens v.Wisconsin,195 U.S.194,204(1904).,该种行为多见于商业及贸易领域。鲍恩勋爵在里程碑式的案例Mogul Steamship Co.Ltd.v.McGregor,Gow & Others 中重申:“恶意意味着故意从事一项错误行为并给他人造成损害。”②Mogul Steamship Co.Ltd.v.McGregor,Gow & Co.,(1889)23 Q.B.D.598,612.
第四,恶意指不当动机。在早期,意味着不当动机的恶意与侵权法无关。“恶意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人的怨恨或邪恶,即便不是报复性的恶意,也可构成恶意。法学家扩大了普通人对恶意的理解。”③Pratt v.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1919]1 K.B.,275.后来,英国法院认定恶意即指不诚实或不当动机,“在侵权法中,坏的动机被称为恶意”[9]539。更多基于行为动机上的分析,即实施这一行为的目的是期待损害他人的利益。通常,动机不能成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只影响过错判断和赔偿范畴。
经常有学者将恶意与善意相对,民法中的“善意”指第三人在受让原权利人权利有瑕疵的物时,不了解“相关信息”,即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10]150,是道德上中性的表达,并未有鼓励和肯定的意味。因此,恶意不必总是与善意相对立,“恶意”的道德评价倾向性更高。
总之,恶意确实很难有统一的含义以及法律意义上的概念,但不当动机以及无正当理由故意实施行为导致他人损害,是其必不可少之意义,恶意即无正当理由故意导致他人损害的不当动机。
(二)对恶意与故意的界定相关观点的评判
1.恶意能否与故意通用。从词意来看,“恶意”指居心不良,“故意”指存心的、有意识的。两者皆表明当事人主观上明知某事不能为而为之,但“恶意”多了动机不良的意味,在道德上更值谴责。动机在心理学上一般被认为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是行为背后的原因和内在驱动力,动机导向了故意,是确定故意的要素之一。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当事人很难直接证明作为动机的恶意,法官也无从察觉人们在从事一项行为时是恶意还是善意。故意则是直接导致法律后果的主观状态,是引起某种确定的直接结果的意图。“在故意,行为人‘明知’‘预见’或‘确信’损害结果或危险性会或基本上会发生;且对结果‘欲求’‘默许’或‘接受’。”[11]87恶意是主观状态,是希望某行为发生或不发生。故意也是主观状态,在实施或不实施一项行为时,一个人希望他的行为产生某种后果,它包含的期待是伴随行为的结果。“医生做一个有风险的手术,很可能会导致病人死亡,但他并非故意杀人。仅仅期待一项结果是简单的故意。若结果不应该产生,行为人知道事实却使之发生,该故意就具有可谴责性。可谴责性的故意是简单的故意加上知晓。”[12]16因此,故意行为是计划性行为和选择性行为,既有认识因素,也有意志因素,它与作为动机的恶意存在本质区别。
在法律意义上,恶意与故意的范畴也不同。“故意从事一项非法行为并不必然是恶意行为。”[13]84“一个人可以故意实施一项行为,却没有恶意。但他不可能恶意做某事却没有故意。恶意从事一项行为包含故意实施,恶意包含故意和意愿。”①State v.Bobbins,21 N.J.338(1956).
2.故意能否涵盖恶意。“恶意”在主观的严重程度上高于“故意”,如此也与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功能更为相符。[14]德国侵权法理论将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日本民法典》第709 条规定:若某人因故意或过失使他人权利或法律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则有责任做出相应赔偿。这里的故意意味着“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侵害他人的权利,将会被评价为违法,仍然实施该行为”。《欧洲民法典侵权法草案》第3:101 条规定,故意是意在造成此种损害,明知损害必然发生或可能发生而放任损害的发生。可见,故意指向行为的后果,恶性程度低于恶意,但恶意不是故意,也不能由此得出“恶意是最高程度的故意”这一结论。
故意的恶性程度低于恶意,是否意味着故意包含恶意?霍姆斯在构建现代侵权法体系时提出,“故意侵权包含了欺诈、恶意和故意。在民法中,根据伤害可预见性之程度,欺诈的、恶意的、故意的和过失的构成哲学上的连续系列”[15]131。他把欺诈和恶意置于故意侵权类型中,主要是因为他主张,侵权责任与人的主观状态无关,而与政策考量有关。但恶意侵权给他出了难题,他后来承认,认定恶意需要考虑道德可谴责性,且将该类案件限定在不当动机的情形,行为人对道德情形的感知对确定通谋很重要。虽然在美国现代侵权体系中,恶意侵权并未成为独立的侵权类型,霍姆斯也试图排除恶意,但“一些重要的侵权在他的时代要求证明实际恶意或者不当动机”[16]8,这使故意根本无法涵盖恶意。“恶意是一些故意不法行为的责任前提,却不同于故意,因为它需要考虑动机。”[17]903故意无法涵盖恶意的根本原因是,恶意可使某些形式“合法”的行为构成侵权,故意通常不能产生该法律效果。
总之,恶意与故意性质不同,不能通用,但在赋予一种动机法律意义之时,我们又不得不借用故意来描述恶意的含义。从证据学角度看,很难探究行为人的真实意志,行为人完全可以声称自己在行为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同样,故意作为一个法律拟制的概念,在探究行为人是否存在故意时,其动机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恶意既不能等同于故意,也无法被故意涵盖,当恶意作为恶意侵权的构成要件时,应严格限制恶意所适用的范畴,扩大恶意的解释等同于扩大恶意侵权的适用范畴。
三、比较法上侵权法对恶意的规制
英美法系各国普通法中的侵权法有恶意侵权之规定,大陆法系侵权法虽未明确规定恶意侵权,但以不同方式对其加以发展。我国侵权法未规定恶意侵权导致他人损害之情形,故研究比较法上主要国家侵权法对恶意的规制,对我国侵权法发展和完善恶意侵权有较大意义。
(一)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侵权法对恶意的规制
罗马法中最早与恶意有关的术语称作“malitia”,由罗马法学家提出,主要与民事案件有关,意味着“罪恶”,在一些情形下,“malitia”被直接用作“dolus”,意味着直接、邪恶的故意,“dolus”也作恶意和欺诈解释。[18]643另外,对财产占有的判定上,罗马法将恶意占有与善意占有联系在一起,恶意占有和善意占有的法律效果存在区别。在罗马法中,作为不当动机,恶意从未影响侵权责任构成、赔偿范畴和过错的判断。
《法国民法典》第1382 条和《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被认定为侵权法的一般条款,规定了故意或者过失致他人损害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未涉及恶意。与恶意最接近的当属《德国民法典》第826 条与《奥地利民法典》第1295 条第2款:“一个人以违反公序良俗的方式故意侵害他人,应当为此承担责任。”此条文将以故意为要件的侵权限定于此情形,无法推断故意与恶意有必然联系,其他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大都与此类似。大陆法系各国未在侵权法中直接规定恶意,一方面是因为恶意不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这是一般规则;另一方面,大陆法系侵权法理论认为,对于人的主观状态的划分源于刑法,“填补损害功能是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功能”[19]23,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损害结果并无意义。各个国家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对恶意的讨论,主要与善意和诚实信用原则联系在一起。
大陆法系各国主要通过对侵权法一般条款进行推理的方式,以判例的路径发展恶意侵权,恶意诉讼是被认可的恶意侵权类型之一。解释一般条款可给恶意诉讼侵权提供赔偿依据,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中国等国《民事诉讼法》均对恶意诉讼导致损害的救济进行了规定。虽然各国侵权法并未明确恶意诉讼致害之救济,但恶意诉讼致害在禁止权利滥用和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制范畴。
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侵权法来看,恶意并未占有重要地位。在极少数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国家,惩罚性赔偿的主观构成要件多是故意而非恶意。但在恶意抢注域名、商标和专利侵权的情形,各国大都通过特别法进行规制,明确规定恶意侵权的具体内容。
(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侵权法对恶意的规制
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不同,恶意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十分精彩,英国侵权法和美国侵权法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英国法相对保守,美国法更加灵活、开放。
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中,17 世纪时,恶意是谋杀的构成要件;18 世纪时,它开始有规律地在民事和刑事判例法中出现;19 世纪时,它首次出现在刑事成文法中。①The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 (24 & 25 Vict c 100).相较恶意,一些侵权中更早地涉及故意,但对于故意的证明,只能依据结果及相关事实进行推断。19 世纪,英国侵权判例法开始热烈地讨论恶意,但鉴于恶意属于动机以及证明动机的难度,法院通常拒绝作为动机的恶意在侵权法中发挥重要作用。19 世纪末期,动机在侵权法中开始变得重要,但此时的法院仍认为动机与损害并不相关,典型案件是Allen v.Flood 案。法院判决,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任何法律权利,原告不存在被雇主雇佣的权利,被告未实施违法行为,也未使用非法手段。不管被告的动机如何邪恶,他的行为都是不可诉的。显然,当时的英国法律无法接受动机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沃森勋爵说:“英格兰法不会将动机作为民事不法行为的构成要件。”②[1898]A.C.92.此时的英国法律倾向于以客观的故意为基础,利用故意比使用动机能更好地控制责任。20世纪,恶意在侵权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恶意作为侵权责任要件的案件类型逐渐增加。作为典型的侵权责任案件,恶意诉讼经历了从刑事恶意诉讼至民事恶意诉讼的发展,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对于恶意诉讼的前一诉讼是否可延伸至民事诉讼,英国法院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英国最高法院在新近的Willers v.Joyce③[2016]UKSC 43,52; [2018]A.C.779.案中判决,恶意诉讼的前一诉讼可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
相较英国,美国法院对“不当动机在侵权责任构成中之作用”的态度趋向多元化,不同法院对不当动机的态度不同。“不管行为人在道德上如何受谴责,有些法院认定不当动机没有任何法律意义,行为人不负法律责任;有些法院认定行为人基于不当动机负责任。”[20]412尽管美国随后的侵权法对恶意的态度并不统一,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基本形成了几项以恶意作为构成要件的恶意侵权,如恶意诉讼、恶意利用程序等。“恶意诉讼产生于内战后,是普通法给错误使用刑事程序以侵权救济。”[21]443-446与英国不同,美国一些州认可民事恶意诉讼。1932 年,亚利桑那州首次认可民事恶意诉讼。①Ackerman v.Kaufman,41 Ariz.110,112-114,15 P.2d 966,967(1932).1980 年,宾西法尼亚州制定了《德拉格内蒂法》,基本条款题为“民事程序的不当使用”②42 Pa.C.S.A.§ 8351(a).。
霍姆斯的侵权法体系影响了美国侵权法,他改变了“个人道德可谴责性与侵权法无关”的观念,架构了恶意、故意和过失构成侵权法完整的义务体系,他将义务分为三种:“违反欺诈或恶意的义务,恶意干涉合同关系属此类,恶意未被故意侵权涵盖,具有独立地位;违反绝对义务,即故意侵权;违反过失的义务。”[22]464
(三)恶意在各国侵权法中的地位发展之趋势
大陆法系侵权法规制恶意侵权较晚,但从恶意诉讼的发展来看,呈现更开放的趋势。英美法系侵权法对恶意的讨论持续几百年,却不情愿承认民事恶意诉讼。故意与过失是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这虽不可动摇,恶意仍有一席之地。我国侵权法兼具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特征,未明确规定恶意的作用和地位,通过解释一般条款在案例中的适用发展恶意侵权。我国恶意侵权的发展还处于较初级阶段,但这样具有活力的体系安排,对于未来出现的新情况,需要考虑是否基于恶意给受害人以赔偿时,无论在法律解释还是理论突破上,在一般条款的基础上认可恶意侵权,不仅可能而且可行。未来侵权法的发展是去道德化,还是加强道德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这是各国侵权法面临的重要课题。以恶意为侵权责任要件的恶意侵权的出现和发展,是侵权法发展不可回避的难题。
四、作为判定过错和损害赔偿范畴考量因素的恶意
对于恶意在侵权法中的地位,各国普遍接受的基本规则是:恶意只是侵权责任的一个加重要素。英国Allen v.Flood 案是经典案例,是法院和学者反对“恶意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引用最多的案例。
(一)恶意不是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罗马法区分了私犯和准私犯,但未对侵权行为(私犯)或准侵权行为(准私犯)进行抽象和概括以提炼出包含一切侵权行为或准侵权行为基本要件的一般条款。[23]44《法国民法典》第1382 条、《日本民法典》第709 条以及中国《民法典》第1165 条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代表,均未明示恶意。《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的列举式模式也未涉及恶意。“就基于过错责任原则所认定的侵权责任而言,其构成要件有几种学说。法国民法主张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三要件说。德国民法主张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四要件说。”[24]23德国民法及德国法系国家民法一般以行为的不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意大利民法强调损害的不法性,不法性作为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的四要件说受到挑战,一些合法行为如得到政府许可的排污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加害人也会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构成的三要件说抑或四要件说,都不体现恶意,恶意不会影响侵权责任构成,这是通说。
英国和美国较早开始探讨恶意在侵权责任中的地位并确认:“我们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一个表面合法的行为,不会因为不当动机,变成不合法和可诉的。”③[1898]A.C.1,124.在现代侵权责任体系确立之后,故意侵权类型通常无须证明恶意,恶意更不会是过失侵权和严格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英美法系侵权法中,义务理论在过失侵权中占了上风,但权利理论同样存在,且涉及恶意的问题:恶意决定了原告权利未受到侵害却遭受损害时能否获赔。19 世纪初,原告只有经济损失时,必须有特定权利受到伤害才能够获赔。Hannam v.Mockett①2 B.& C.934,4 D.& R.518(1824).案中,野乌鸦习惯在原告的土地上筑巢,原告出售小乌鸦获取利润。被告存心恶意地在附近放枪,把乌鸦吓跑,原告失去利润。原告对野乌鸦及获取的利润无特殊权利,被告剥夺原告利润并未侵害原告的特定权利,不构成侵权。后来,“当导致金钱损失,却未侵害任何特定权利,证明恶意或欺诈,可使行为人负责任”[12]18。也就是说,行为未侵害特定权利的情况下,若行为有恶意或欺诈,行为人仍然可能承担责任。
因此,一般侵权中,恶意不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不法行为不会因为动机好就成为合法,一个合法的行为不会因为不当动机就变成非法。“虽然某些侵权责任要求以不当动机作为构成要件,但总的来说,动机对于侵权责任不会产生影响,因为‘如果行为人被认为是非法的,好的动机并不会免除被告的责任;如果行为是合法的,不好的动机不会使其承担侵权责任’。”[5]234
(二)恶意是判定过错和赔偿范围的考量因素
恶意不能作为侵权责任的独立责任标准,它只是判定侵权责任的一项加重因素。恶意作为侵权责任的加重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判断过错的参考因素和损害赔偿的加重因素。
过错的判定多数情况下集中于过失,过失的判断又聚焦于义务。“在成文法国家,很多情况下,法律法规对行为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有明文之规定。如果行为人不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行为,违反法定义务,常常因此被认为存在过失。”[4]276英美法系的“理性人”以及罗马法中的“善良家父”都是法律拟制的证明过失的技术手段。故意的证明标准相对宽松,行为人故意导致损害,无论其是否可预见损害,都要负责任。在过错判定中,若受害人能够证明行为人基于恶意而行为,行为人被认定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恶意会影响侵权损害赔偿的范畴,典型例子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和某些特殊侵权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我国最高院2001 年《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10 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第1 款规定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该规定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区分恶意、故意、重大过失及一般过失。侵权人根据过错程度不同,承担不同的赔偿责任。在某些特殊侵权的侵权责任已经确定的情形下,恶意对损害赔偿范畴有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恶意是认定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惩罚性赔偿是以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有符合补偿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25]114大陆法系侵权法对惩罚性赔偿持保守态度,坚持侵权法的损害赔偿规则是填补式赔偿。在知识产权领域,一些国家将恶意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要件,即行为人以恶意而行为,在一般损害赔偿之外,可判决惩罚性赔偿,如我国《商标法》第63条第2 款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恶意不能成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与以往法律不符和实用主义的考虑。”[26]346各国侵权法都明确恶意不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可行性是反对恶意成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另一依据。“人的主观状态是人的消化领悟能力。”②Edgington v.Fitzmaurice,29 Ch.459,483(1885).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是很难的,尽管这在刑事案件中很常见,但民事案件以填补损害为目标。“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动机给司法系统太多的压力,探求行为人的动机会让法院陷入各种困境。”[27]659
五、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恶意
恶意不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这是一般规则,一般规则通常都允许例外。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各国,现阶段侵权法都存在以恶意作为构成要件的恶意侵权。侵权立法并未体现这些具体的恶意侵权,但这些恶意侵权却影响着司法实践。笔者综合各国情况,选择讨论较有普遍性的恶意侵权,并探讨这些恶意侵权为何以恶意作为构成要件?是何种共同特征让它们独立于其他侵权类型?
(一)以恶意作为构成要件的恶意侵权类型
1.恶意诉讼。大陆法系多数国家通过法律解释以判例的方式解决恶意诉讼事项。《德国民法典》第826 条第2 款和《奥地利民法典》第1295 条第2 款、《希腊民法典》第919 条、《日本民法典》第709 条等是恶意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些国家《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并通过司法实践对立法进行诠释。英美法系对民事恶意诉讼态度保守,直至2016 年,英国最高法院才明确判决,恶意诉讼可延伸至民事程序。美国较早承认民事恶意诉讼,但各州法院意见不一,其他多数普通法国家至今未承认民事恶意诉讼。
何种恶意能够使“形式合法”的起诉行为构成侵权?美国1965 年《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653 节指出了恶意诉讼之本质:“诉讼必须以正当目的的动机启动。如果提起诉讼的首要动机是不合法的目的,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通过诉讼来陷害相对人,该目的在行为人决定提起诉讼时发挥了实质作用,则首要动机就是非法的,构成恶意诉讼。”据此,前一诉讼的首要目的是陷害相对人或者谋取非法利益,构成“恶意”,首要目的是为正义哪怕败诉也不构成恶意。
2.恶意通谋或恶意串通。恶意通谋系英美法系术语,恶意串通则在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中加以规定。恶意通谋分为合法手段的恶意通谋和非法手段的恶意通谋。美国有法院将民事通谋界定为“两个或更多主体共同行为以达成非法目标或者通过非法或者犯罪手段达成合法目标”[28]308-309。但该定义存在逻辑问题,非法手段或非法目标可能导致该行为具有非法性,非法性说明已经在法律层面上给行为以定性。“对于故意导致伤害,伤害原告的压倒性目的在不合法手段的通谋中并非必须。”[29]本文所涉恶意通谋仅指合法手段的恶意通谋。恶意串通属大陆法系民法术语,我国《民法典》规定其为无效法律行为,更关注行为效力。“‘恶意’与‘串通’组合起来内在要求对行为的伦理评价,明显表达了对第三人的侵害性。”[30]339
无论恶意通谋致害还是恶意串通致害,恶意都是侵权责任构成之要件。“‘恶意’具有不同的判断方法或构造难度:‘观念主义’要求行为人认识到相对人实施了足以危害他人的行为;‘意思主义’于观念之外,还要求行为人有损害他人的共同故意;‘获利主义’则进一步要求行为人有获得不当利益的意图。”[31]12从证据的角度,原告很难证明恶意通谋和恶意串通中的恶意,若由此判决原告败诉,会助成被告实现侵害他人利益之目标,因此,法院可依据证据进行法律推定,或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考察当事人通谋或串通的根本目的是否造成他人损害,或有报复、其他邪恶动机。
3.滥用职权。在英美法系,公职人员恶意滥用职权导致个人损害,个人可起诉该公职人员请求侵权赔偿。在我国,《刑法》第397 条规范滥用职权。在侵权领域,我国并不支持滥用职权的损害赔偿,对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导致公民人身、财产损害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涵盖了英美法系侵权法中个人主张的滥用职权的侵权损害赔偿。本文旨在探讨恶意对特殊侵权类型的影响,故各国对滥用职权致害以不同方式加以救济,并不影响以滥用职权侵权损害赔偿为例论证恶意侵权具体类型的共同特征。
滥用职权的公职人员导致当事人损害,责任构成要件为:滥用职权应是滥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职务权限,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一般的职务权限无关,则不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人或是以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或是以不法方法实施职务行为。在出于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时,即使从行为的方法上看未超越职权,也属滥用职权。与恶意相关的滥用职权是,当公职人员以不当目的或不当动机以合法方法履行职务行为导致损害,恶意可使其看似“合法”的职权行为具有可诉性。公职人员在实施职务行为时,并不要求其指控的人必须有罪。
4.恶意抢注商标侵权。商标侵权具有特殊性,我国《商标法》及其下位法规定了“商标恶意侵权”,包括恶意抢注域名、恶意抢注商标等。不论域名案是作为商标侵权案件还是不正当竞争案,“与其他一般侵权案件不同,它是以恶意而非以故意或过失,即过错作为认定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6]45。《商标法》第32 条和最高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 条对此有规定。在恶意抢注人未被主张恶意抢注之前,“抢注行为”形式上是合法的。立法以“不正当手段”作为抢注行为的责任构成要件,不正当手段即明知或应知他人使用商标而予以抢注,实际上是降低了责任构成要件,此处要件应为“恶意”,即将商标据为己有并给使用人造成损害,是“恶意”而非“不正当手段”让形式合法的注册行为构成侵权。不少国家《商标法》也规定恶意抢注商标,造成在先商标使用人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证明“恶意”时,明知他人正在使用商标这一证据并不充分,行为人抢注商标的目的是将商标据为己有,给在先使用人造成损害,此为恶意之要件。
(二)恶意侵权具体类型之共性
上述四种主要恶意侵权类型是否有共性?是何种标准或者规则使它们区别于其他侵权?
1.不当动机是恶意侵权的构成要件。与其他侵权不同,恶意侵权的共同特征是恶意为责任构成要件,若行为人无恶意,即便造成损害,也不承担侵权责任。恶意有多种含义,若适用统一的恶意之含义,会避免不同恶意侵权带来的困惑。是何种“恶意”将恶意侵权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这些案件中的“恶意”应是不当动机,是不当动机将该类侵权联系在一起,并使形式合法的行为构成侵权。何为不当动机?不同恶意侵权含义不同,但行为的根本目的是伤害原告即为不当动机。如在Tuttle v.Buck 案中,被告是有钱的银行家,在原告所在小镇开了一个理发店,根本目的是破坏原告理发店的经营。1 年后,原告理发店关门,被告随后也关闭了理发店。法院认为,“当一个人处于商业的竞争位置,不是为了自己经营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将竞争对手驱离商业之目的,且怀有一旦自己的恶意目的实现便退出的意图,他便犯下了荒唐的错误,并构成一个可诉的侵权行为”①119 N.W.946,948(1909).。行为人的根本目的是伤害原告,这一不当动机使被告看似合法的竞争行为变成了不合法行为。
2.权利滥用。对权利进行限制是现代法律发展的结果,对所有权的限制最有代表性,土地的所有权人最初拥有其土地“上至天空下至地心”的所有权益。如Bradford Corporation v.Pickles②[1895]AC 587.案中,被告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井的唯一目的是截断原告水源,而非给自己带来任何利益,法院判决该行为合法,即便有恶意动机,被告也有权这样做。后来,各国陆续通过立法确定了“禁止所有权滥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意味着行为人必须在合理限度内行使自己的权利。“行为人须有权利、权利之行使边界不明、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或者权利之行使造成权利人所获利益与他人所受损失严重失衡。”[32]129下面分析恶意侵权中行为人如何滥用权利(权力)。
恶意诉讼中的行为人如何滥用权利?传统二元诉权说对程序意义诉权和实体意义诉权的划分,将诉权表述为一种兼有公法和私法两种性质的权利。“诉权作为一项程序性权利,是当事人对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具有公法性权利的性质。”[33]155诉权是当事人对民事权益进行司法保护的请求权,是保护私权的权利,符合公法的通性。恶意诉讼中的被告滥用的是国家的强制权和个人提起诉讼的权利。人们获得公正判决是法治的一部分,但它不能沦落为施以不当目的的工具。合法形式的通谋也是滥用权利的典型例子。个人之间进行联合的自由是人类自由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结社在本质上是人的结群行为,是不同个体间彼此进行联合的一种人类活动方式”[35]5。自由结社对个体自由有重要意义,结成贸易同盟也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人们有法律权利去联合,但是该权利只能基于有权利和有正当性的故意而实施,不当动机即会破坏行使该权利的合法性。”[8]497滥用职权侵权只适用于恶意行为的公职官员,他们滥用了公共权力。任何公职官员都会被赋予特定的权力以履行特定的法定职能,当他的行为与赋予他的职能不一致时,就需要负责任;当他以恶意违反这一职能且对个人造成损害时,他要负侵权责任。滥用职权侵权只适用于作为公职人员的被告。恶意抢注商标是滥用正当竞争权和注册商标的权利。正当竞争权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法享有的参与公平竞争的权利。注册商标的权利也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最高院在王碎永诉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③(2014)民提字第24 号。案中认定:“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
随着侵权法的不断发展,会有更多的侵权类型被认定为恶意侵权,但权利(权力)滥用能够作为统领恶意侵权的重要特征,在于行使合法权利的根本目的是给他人造成伤害。《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民法典都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将恶意侵权与权利滥用联系起来,意味着正当行使权利造成他人损害不承担责任,行使权利以损害他人为根本目的要承担责任。
六、结论
恶意有多种含义。不同于口语中的恶意,法律意义上对恶意的恰当界定是无正当理由故意导致他人损害的不当动机。恶意与故意有密切联系,它是证明故意的佐证,也不同于故意,故意无法涵盖恶意,更不能取代恶意。大陆法系通过解释一般条款发展判例的方式推动恶意侵权的发展,英美法系延续恶意侵权发展的普通法传统,形成了发达的恶意侵权体系,这都给我国恶意侵权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范本和借鉴,各国由此形成了大致相仿的恶意侵权体系,如恶意诉讼、恶意通谋、滥用职权以及恶意抢注商标等。不当动机之恶意和权利滥用使形式合法的行为成为实质不合法的行为,它们是恶意侵权的两大根本性特征。法律的形式和实质受到行为目的的影响,被告行为的根本性目的是造成对方损害,即便该行为形式上合法,也是可诉的,“造成对方伤害”的根本目的即为恶意。
恶意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发挥作用,是道德可谴责性影响侵权责任的典型体现。依据伦理学,这是道德在法律中的界限问题。恶意是人们对行为人的道德评价,不是法律要体现道德,而是法律应该在何种范围以及何种程度上体现道德。侵权法是最活跃的法律部门,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侵权类型不断出现并被认可,恶意在侵权法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它在侵权责任中的次要地位不会改变。恶意作为恶意侵权构成要件所适用的领域应是狭窄的,以防止该种类型侵权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