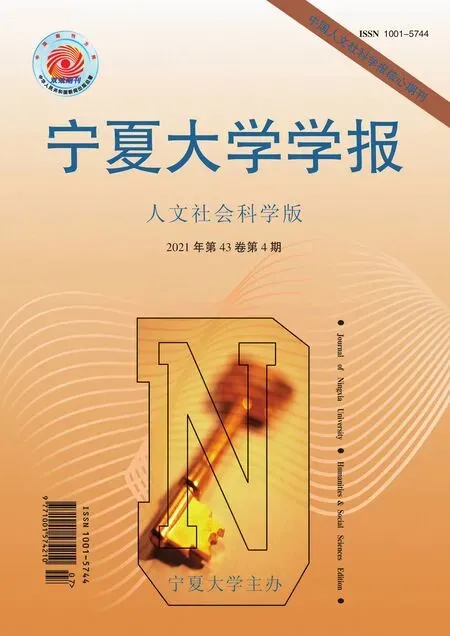域外之眼:近代西人记述下的广西女性日常生活
庞少哲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近代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后,西人纷纷来华。他们对中国社会多有关注,尤其是对接触到的人物及社会情状,是其日常谈及的重点,甚至写入书信、报告和回国后的传记、回忆录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了解和认识。这些西方人,包括在华外交官、医护人员、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不同群体。在他们的接触对象中,较为关注和好奇于中国女性的身份、地位及其社会关系。这既是因近代中国女性的生活情状与欧美女性在穿着打扮、行为习惯、社会地位等方面大相径庭;也是部分西方人为了传教的需要,传教士(特别是女传教士)借以与中国女性的接触,希望将其传入中国家庭。同时,也为更好地了解中国,为制定相应的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目前学界对近代西方关于中国女性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就,相关研究成果推陈出新、不断涌现。不过遗憾的是,在近代西方人关于广西女性记载颇多、资料丰富的情况下,学界有关近代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研究尚付阙如。因此,本文试图从来华西方人记载中了解近代广西女性日常生活百态,包括西人记述下的广西女性婚姻日常状态、居家日常生活、日常聚会,以及常见的鬻女与弃婴等社会现象,以期更好地解读近代时期的广西乃至中国社会。
一 婚姻日常状态——男权专制
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嫁关系的成立与否,并不取决于男女双方,而是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出嫁前一切由父亲做主,甚至母亲也无权干涉女儿的终身大事,出嫁后的日常生活一切听从夫家,“以夫为纲”。可见,从婚嫁伊始,女性的选择权便掌握在男性手中,包括婚姻能否维持长久亦由男子决定(如夫可休妻、寡妇不可再嫁等),女性在婚姻生活地位上宛若男性的附属物。
有西方人记载,广西有一男子付修卢(Fou Siao-lou)因感生活寂寞,遂向族长征求娶其女的意见,族长竟以对方除掉自己的敌人为嫁女的交换条件,几周后付修卢返回族长家中邀赏,族长便将女儿许配给他[1]。可见,女儿的终身大事由父亲做主,被当成有条件的“奖品”赏给“有功者”,女性自己无法选择。即使是西方在华教会内部,一些女性教徒和慕道者亦害怕自己没有能力为女儿作出恰当的婚姻安排,“在中国,女性是不自由的。女性要遵循夫家的信仰并且必须执行他命令的迷信行为”[2]。
广西女性在辛苦劳作的同时,有时还会遭到丈夫的欺辱和殴打。在美国医生富玛丽(Mary H.Fulton)的接诊者中,就有被丈夫殴打抛弃的女子[3]。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一晚,有西方人听到“街道传来女子的阵阵哀嚎哭声,死了吗?不,她只是被丈夫殴打了!”[4]甚至还有在吸食鸦片的驱使下,丈夫打妻卖孩,导致家庭破散[5]。当一些对福音有所期待的女性想邀请女教士前来家中宣教时,“也常受丈夫阻挠,因为只要丈夫愿意,就可随意左右妻子。这里(中国)几乎连法律都没有,更何况反虐待”[6]。“妻子无权反对丈夫,若是丈夫伤害了妻子,常以妻子‘不孝’之由逃脱法律惩罚”[7]。这是中国传统的“夫为妻纲”。而同为女性的婆婆,对儿媳妇也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每个儿媳妇都成了婆婆绝对的奴隶”[8],“婆婆们有着近乎可怕的威严……从新娘踏进婆家的那一刻起,她就要受到婆婆的管制”[9]。并且,“妇女成为寡妇后不可再嫁,只有当媳妇熬成婆时才能在家族中有所地位”[10]。女性,尤其是妻子,在中国男权专制的家中几乎毫无地位可言,无怪乎当美国人法默(Ada Beeson Farmer)死后,其丈夫采用中式葬礼的习俗将其葬在桂平西山的坟场时,沿途“许多人都停下观望,他们并不明白为何要给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如此风光的葬礼”[11]。
除了一夫一妻制外,在中国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还留有多妾的婚姻形式,因此,男子纳妾是常有之事。妾虽身处富贵人家,但多数情况下,纳妾不过是为了添一劳力,“日里拿来当牛用,夜晚拿来暖被窝”[12],既不必支付工钱,也可兼做家务、传宗接代,更可打骂,甚至有“纳妾是养牛”[13]的说法。因此,妾虽外表看似衣食无忧,实际隐忍无尽。据清朝律法,“妾”之地位较“妻”更为低下,且无法替换,谓之不可失序,“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14]。妾似乎只是一个能够传宗接代的婢女罢了。
既无律法保护,妾室境遇就不难想象了。有关妾室的生活状况,来华西方人也有记载。如英国人柏德贞(Charlotte Bacon)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大太太婚后无子,便劝丈夫纳妾。纳的妾是大太太的丫头,嫁给主人后产下一子。大太太心生嫉恨,便借机将新生儿害死,却可免遭罪责”[15]。法默在日记中亦有提及:“1905年6月8日,昨晚,有个商人的二太太跳河自杀了,可怜的人啊,据说是因大太太打了她”[16]。其实妾室遭妻室毒打现象并不罕见,甚至还有可能被妻室毒死[17]。妾室境遇十分悲惨,一般人家是不愿做妾的,“父母贫,则卖为妾;父母富,则嫁为妻。为妻为妾,亦视父母贫富何如耳,非有种也”[18]。卖为妾后身家一切皆由夫家做主,甚至随时可将妾转赠或价卖。
无论是妻室或是妾室,在家中都受夫权管制,就连男仆在男主人的授意下都可将女主人不放眼里。例如,法默在1905年5月4日外出,“去潘家,门卫说夫人不在,但孔太太先前已进屋去,便带夫人出来迎我,门卫很生气并推了孔太太”[19]。妻室的面子尚且不受尊重,何况妾室。从西方人的记载来看,他们对官宦妾室充满一定的同情与怜悯之心,除了批驳与呼吁废止纳妾制外,更是希望从讲道入手以“拯救”其于“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不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平民女性对婚姻几乎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中国婚嫁全凭父母主持,又每多出童年定聘,而男女两人素不谋面”[20]。婚前由父亲做主,婚后听命于丈夫,这反映出当时的男权专制。民国成立后,随着新思想、新观念的大力宣传,愈来愈多受压抑已久的女性反抗不平等的婚姻关系,试图打破这种传统的男权专制。据调查,在1923年广西746起离婚案件中,女性作为原告的有608起,占总数80%,其中因受虐待和意见不合而离婚者占64.97%,还有一些女性因婚姻不能自主等各种原因,自杀者也不少[21]。例如,住在法默隔壁的一个妇人,“十分善良,可丈夫却异常恶毒,她无法反抗,之后服毒自杀”[22]。为此,法默认为,“东方社会的家庭结构就是如此,除非女性能掌握自己的人生,否则终将背负沉重的压力无望死去”[23]。其他未选择离婚或自杀的女性,或由于孩子因素,或碍于他人眼光,或无法接受新思想的冲击等,仍旧选择低声下气地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婚姻状态。
二 居家日常生活——家务繁重
与其他地方不同,广西由于特殊的地理、地情,加之非汉族的少数民族较多,外出劳作之女性见惯不怪。因此,广西“女勤男惰”的传统由来已久,“妇女悉从事生产,与他处游手好闲者不可同日而语。广西女子一如男子,能种地饲畜,肩挑背负,虽在孕妇,肩承重担,亦能行所无事”[24]。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妇女“是伟大的劳动战士……整个农村经济的生产权都操在她们手里,她们比男人要做更多、更繁重的工作,而且做些男人所不能做的苦工”[25]。她们几乎包揽家中大小家务,除了缝衣做饭、相夫教子外,还要下地农忙、畜牧等,甚至是农田割稻,女多于男“,男子坐在茶馆里抽着烟喝着茶高谈阔论的时候,正是他的妻子在田野间‘汗滴禾下土’”[26]。养家糊口由妇女承担,而男子多逸。来桂西方人亦发现:“通常情况下,妇女都会坐在家中照顾小孩、纳鞋、做针线活等,所有事情都需要她们去做”[27]。甚至本该由男人干的重活也都压在妇女身上:“我们常看到排着长队的妇女一起上山,肩上背着沉重的树枝和木头,从山上下来,有时还被隐藏的老虎吃掉”[28]。
广西平民女性的日常生活,时不时在西方人的笔墨中有所反映,更多的是对于家务女性的不解与无奈。由于包揽繁重的家务,她们“根本没有时间溜达闲逛”[29]。西方人在市镇街上就常常只见男性不见女性,“穿越数英里的人群,我们几乎很少见到女性”[30],甚至新年期间“在街上碰到女子时会被视为不好运”[31]。并且广西城镇女性大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西方人对此亦深感不解,“这简直就像笼中的小鸟一般,我实在不能理解至少有一半的中国女性能够天天待在家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32]。以至西方人认为“女传道员非常有必要去她们家坐在她们旁边,陪她们做鞋、缝衣等,并时不时帮助她们,再趁机将上帝福音传播给她们”[33]。然而,“很少有女性会读书写字,所以她们愚昧、无知和迷信”[34],这给女传教士的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对一个讲官话的妇女讲授最简单的教义需要近一个小时”[35]。在西方人看来,广西女性的日常生活相比西方女性更显可怜和令人同情。
在这些西方人的记述中,近代广西女性的居家日常生活可简而概括为“忙”。农村妇女既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家庭,里外全包。城镇妇女虽相对好些,却似乎也总有忙不完的家务。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女性的“忙”,都是以家庭为中心,她们本身并无受教育的权利,而是从小围绕家庭展开劳作,并在潜意识里认为这是一种“妇道”,女性只有为家庭忙碌才能体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家务繁重”是来华西方人对广西女性的印象之一,也从侧面折射出近代中国女性不平等与悲哀的一面。
三 日常聚会——繁琐礼节
中国自古即为礼仪之邦,传统女性大多居于闺中,家境富贵的女性更是不轻易与外人接触,更何况是“非我族类”之外国人。近代广西官宦之家承袭汉族传统,亦是严格区分男女界限。“上层社会的妇女几乎在家庭以外是难以见到的,唯一能够接触到她们的途径就是去她们家中”[36]。为此,西方人要想与这些女性接触,就只能设法前往家中拜会。《辛丑条约》之后,由于中外条约的规定以及清廷对西方列强的畏惧等诸多因素,地方官对来华西方人较为优待,官太太对西方女性亦较前友好。在此情况下,双方发生日常聚会也就不足为奇。
初入富贵人家之“豪宅”,西方人对其建筑的描述较为详细:“十分漂亮并很有特色。尖屋顶下弧形曲线的屋檐向外延伸,并装饰有雕花的尖角。她们的花园是自然与艺术的结合体,园中除种有花草树木外,还架设小桥、石柱假山,寓意‘小桥流水人家’”[37]。与富有特色之建筑相对应的是,上层人家的衣着亦十分华丽。例如,1905年平乐知县夫人邀请法默到家中参加“春宴”,这是妇人之间的宴会,为西方人近距离接触广西上层女性打开方便之门。法默在回忆录中将这一接触过程详细记录下来,并附带自身看法。初次见面时,官太太这一上层女性穿着打扮显得十分华丽,法默很欣赏,甚至羡慕不已。“那些惊艳华丽的服饰,简直无法形容,它绣在丝绸上,连金饰也那么华美”[38]。这在澳大利亚人金指真(Rhoda Watkins)的著作中亦有描述:“富有阶层的妇女打扮很有特色,身穿刺绣丝绸的裤子和长袍,平直的黑发发髻上插着宝石碧玉簪”[39]。当法默走到夫人跟前时,“夫人向我鞠躬,我也照着回了个礼。然后安排座位,我想坐低一点的位子,夫人却坚持要我坐上座”[40]。“晚宴五点半开始,由于我是特殊客人,便十分荣幸地被第一个请进去。按照中国礼俗,我需要礼貌地婉拒,当然,我确实做了,只是并没有中国人那样客套得厉害”[41]。从法默的这段话也可以看出,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的传统礼节是有一定熟悉程度的,这在邀请他们的官宦人士看来,传教士是有礼貌且得到认可的。与知县夫人相处的这趟“春宴”过程中,中国人显现出来的好客、谦虚、客套,以及繁文缛节,在西方人法默眼里或许带有一丝丝的不解与无语,认为这些是“毫无意义”的多此一举。在即将进餐时,“是关于‘上座’的‘推脱战’,我并未像她们如此相互谦让,因为我是个外国人,这些礼节看上去也毫无意义。当轮到来宾中的第二位尊贵女士时,她也继续推辞,人们便坚持把她按在了座位上”[42]。“坐定后,夫人举起筷子喊我的名字,优雅地欠了下身,将筷子放下,然后是酒杯、勺子、小碗等,都要拿起依次行礼,最后再深鞠一躬。每次我都要还礼。接着,她对每一位客人都行了相同的礼”[43]。尤其是在餐毕后,看着“每位客人都吸水烟,对于我来说,这显得十分低劣粗俗”[44]。在法默看来,这与她们的身份地位十分不符,虽衣着华美服饰,举止却十分虚伪、低劣粗俗。
同为西方人的柏德贞(Charlotte Bacon)前往官太太家中做客时,也遇到繁琐缛节,但她却认为“中国人十分热情好客,对待外国人更是礼仪周全,仁至义尽”[45]。两者反应截然不同,其中或多或少都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她们从自身立场出发,对中国礼仪作了不同解读。
而普通人家与法默之间的聚会,法默在日记中亦有记载。作为一名女传教士,对平民女性的讲道方式,往往是邀请她们到自家听取福音,辅以音乐、美食作为吸引,偶尔也前往对方家中宣讲。例如,法默在日记中写道:“1904年6月21日,今天下午,许多妇女前来参加聚会,门庭若市……她们十分积极,我尽力向她们宣讲福音”[46]。“1904年7月13日,继续开妇女布道会,房间里挤满了人”[47]等。双方频繁的往来,使西方人能近距离观察平民女性的行为举止及其显现出的共同特点。
然而,双方交往看似进展顺利、聚会成功,总能吸引妇女前来听讲,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记载中看,她们前来法默家中的动机并非单纯听取福音,还带有对西方事物的好奇。例如,“1904年6月22日,今天的雨非常大,……中午十二点半左右,客房挤满了人。到了下午一点,我正准备宣讲福音,可由于屋内过于潮湿,导致我无法演奏管风琴,许多人就离开了”[48]。其中,些许女性似乎是带有一定的“凑热闹”心态前来观摩,只为听听音乐,并非真心为听取福音而来。更有甚者,是为品尝西方新奇的食物,当“食物端上后,她们便立即将食物包进手帕带回家”[49]。有时她们即使前来,也很少遵循会场秩序,常使得现场一片混乱:“一次开会时,有只大老鼠跑进屋内,在场的人马上起身,拿起竹竿追赶,直到抓住老鼠、打死、扔出门外”[50]。显而易见,这是对当时女性嘈杂和无秩序的苦恼和无奈。
四 罪恶的勾当——鬻女与弃婴
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现象严重,引发的鬻(卖)女现象古已有之,两广地区亦未例外排除。平民百姓多是在穷困潦倒时,不得不将女儿卖掉,以换取更多的生活保障。到近代社会,鬻女早已见惯不怪,而父母们一般不会卖掉男孩,反而在遇到灾荒时将其带到西方人所建之教堂以求救济活命[51]。被卖的女童或成为婢女供人使唤做工,或成为人妾,或是从事卖淫活动等。这些在来华西方人的记述中不难寻到。
被卖为婢的女童,其“身体完全隶属于主人,供给主人无限量地奴役和榨取。主人不顾她的身心发育和劳动力强弱,往往叫她们做超出能力的事情”[52]。甚至有“蓄婢是养猪”[53]的说法。这些作为婢女的丫头们“在为客人端茶倒水的同时,还要给家里的女主人烧烟斗,清理居室,并且保证家里随时有火用”[54],她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主人家手里,完全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任何自由,就连结婚嫁人的终身大事也由主人包办”[55]。此外,婢女被打是常事,法默在回忆录中记载:“住在我们隔壁一位很有钱的中国人,买来一个婢女,却时常殴打她”[56]。富玛丽接诊病人时也接到被虐打致伤甚至致残的婢女,“耳朵被割到耳垂处,耷拉着”,还有“一个女孩的喉咙险被割断,另一个女孩是舌头几乎被切断”[57],这都是受到主人“惩罚”的结果,手段十分残忍。
而被卖作人妾的女童,常常家庭条件较为困苦,被父母卖出后,还有被转卖的情况。如若碰上灾年,女童更是被父母变卖以筹糊口钱粮,这些女童几乎都被迫从事卖淫活动。在1902年的桂平饥荒中,“困苦的人们濒临绝境,父母们只好以四五角钱一个的价格卖掉小孩,大点的女孩就像称猪一样,每磅一角三分,然后被送去海岸城市做不道德的勾当。在那些饥荒的日子里,每周都有上百女孩乘船经梧州送往沿海”[58]。1905年平南饥荒后,更是有“无数儿童,尤其女童,被卖为奴或运到沿海从事不法勾当”[59]。有西方人将卖女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
掌秤的男人喊道:“55斤。”
“不。”一位老妇回应,“56,看,秤还没平呢。”
“好吧,56斤,快点,后边还有很多呢!”
“你给多少?”老妇问。
“6角一磅。”
“什么?才6角?你看,她很胖,而且11岁了。”
“不行,6角。”男人坚持着价格。
“看,她有好衣服和手镯,给7角吧。”
“这些对我都没用,我只要她”[60]。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双方以6.5角成交。“据估计,闹饥荒时期,从梧州口岸每天可卖出一两百名女童到广东”[61]。
此外,在广西还有将女儿出嫁以换取钱财的事例,这也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卖”。据记载,“有一次和一位农妇谈话,她说‘乡下的姑娘,到了十五六岁差不多都卖了去’。经她解释,才晓得她所说的‘卖了去’就是出嫁的意思,事实上也的的确确等于‘出卖’。一般赤贫的人家,由婆家出一笔礼金,没有妆奁陪嫁,就将一个人嫁了过去,而这笔礼金作为父母的收入”[62]。法默曾目睹:“女儿往往被嫁给岁数很大的男人,甚至烟鬼父亲试图用女儿换取鸦片的钱”[63]。还有富玛丽在桂平的助手阿葵(Mui A-Kwai),“八岁时因父亲赌博败光家产,其妻儿为了生活,将女儿全部变卖,一男人花二十八元将阿葵买下,两年后以五十元转手他人,十八岁时又被以八十元卖予他人为妻”[64]。鬻女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而官府却只禁止卖出牲畜,对贩卖人口并不关心[65]。从这一层面上看,女童地位甚至还比不上牲畜,地位之低可窥一斑。
贩卖的女童经过一段时间的抚养,在到达一定年龄能够从事劳动后进行出售。对于底层百姓来说,自身贫困、能力有限,如若碰上灾年更是无法抚养妻儿,女婴被随手抛弃路边或丢入水中任其溺亡便成常有之事。例如,1905年有西方传教士在桂平专门成立盲童收容所,这些盲童都是清一色女孩。“一天在拜访一户人家时,发现一小女仆被打致盲,最后被赶出家门在外乞讨……第二个女孩是个盲童,六岁时其主人用一元钱雇人将她带走、丢入河中……第三个女孩是个弃婴,当时在门外躺着像只牲畜一般,全身肮脏、被虫子覆盖,还患有疾病”[66]。所幸这些都被救下,但也有未来得及被救的,“我曾到一妇人家中为其接生……次日一早我前去探望时,妇人冷漠地告诉我孩子扔河里了,我大吃一惊,再三询问下对方说家中无米抚养。这是她以此方式处理的第五个女婴”[67]。实际上,这家妇人饲养了一头猪、七头水牛,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家中不算赤贫,却宁愿狠心溺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抚养。之所以选择溺死女婴,是因为“有些人相信杀死一个女婴后,下一个出生的将会是男婴”[68],妇人往往对此抱有幻想且执迷于此。不单单是外来西人目睹了广西的弃婴与溺婴,就连当时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对广西的印象亦是“俗尚溺毙小孩,而以女孩为尤甚……每夫妇养育小孩最多不过二人,多则溺毙之”[69]。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广西重男轻女风气的盛行。
综上,无论是鬻女现象的普遍还是司空见惯的弃婴溺婴,对女童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在当时人的眼里宛如牲口一般可随意处置,甚至还不如牲畜。来桂西方人虽尽可能对这些受伤女童进行救治,但由于这是中国社会早已普遍存在的陋习,单靠个体西方人的力量却也无法改变鬻女与弃婴的常态。这些被救治的女童,由于受伤严重或其他因素,存活率有限而出现一定死亡,使来华西人遭时人误解或造谣,甚至引发中西冲突。即便这些女童因未被卖出而活了下来,但她们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往往成为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五 结语
作为近代广西女性种种情状的目击者和亲历者,来华西人的相关著述是不能忽视的。这些记述弥补了有关近代广西社会的知识,加深了对近代广西的了解,勾勒出一幅幅近代广西女性日常生活的画卷,能够较大程度地真实反映近代广西女性的生存生活处境。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记载多少带有一些个人的主观看法,其认识也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代时期,来桂西人不论是对官员妻妾还是市井平民女性,甚至未成年女童,都给予一定的关注,基本上是亲眼所见或现场实录,通常以附有时间的日记体形式进行书写,可信度较高,其中内容大量涉及广西女性的日常生活。这些日记往往被带回西方国家,包括来自遥远中国女性的奇异故事,对西方虔诚的读者来说十分有趣,不仅可以激发西人对中国的好奇、兴趣和认知欲望,还无形中构建了近代西人的广西乃至中国女性观。
近代广西女性和当时中国其他地区的女性一样,在西方人的记载中社会地位较低。具体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婚前听命于父母(尤其父亲)、婚后以夫为纲、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等。这些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状况,与西方国家差异甚大。正是由于愈来愈多受过较高教育的西方人来华,以自身文化为参照,对异域中国进行记载,从而能够比较真实的记录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进行中西不同社会的对比,进而对近代中国女性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予以批判与抨击。她们对女性权益的呼吁、争取,促使中国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社会问题,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例如,从1895年至1949年间,来华西人、教会在广西城乡创办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共261所[70],其中有专门的女学堂,以及男女学生同时招生的综合性学堂。这些西方人从女学入手,试图改变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女子教育使女性知识水平得以提高,逐渐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在五四运动及抗日战争时期她们积极投身女性解放与爱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人对中国女性的记述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由于他们多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记述过程中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理解偏差。因此,在研究中对于这些资料的使用要辩证看待。从已有西人的记载来看,他们从自身视角观察到的多是广西女性的负面形象。如上层女性聚会时的虚伪、低俗、愚昧,普通家庭女性的无知、无序、可怜、无自由,以及女童的被卖或遗弃等,广西女性被描绘成深陷水深火热,以待西人拯救的外在形象。为此,有的西方传教士甚至决定要“尽快学习中国语言,向她们传授真正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将上帝的福音传给那些心灵处于黑暗的人们”[71]。或许,正如英国作家劳克所言:“既然传教士到中国是为了使中国人信奉基督教,那么,他们必须要把中国人描绘成坠入偶像崇拜、迷信和罪恶之中的人”[72]。这样才能突出自身既是福音的传道者和捍卫者,又是中国人的拯救者和教化者。
尽管从现存资料来看,来华西人对中国女性的记载带有一定的立场与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以域外者的视角对广西女性的描写,仍能呈现出一幅幅近代广西不同阶层女性日常生活的百态图景。日常家居生活中的繁重劳务、婚姻地位上的男权专制,被抛无依和惨遭贩卖的女童,无一不指向中国近代社会的习俗弊病,促使中国人自省自醒,推动社会改革的进行。就这一层面而言,不能否定其积极意义。特别是民国以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推动社会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注,兴起女性解放运动的潮流。到五四运动时期,受传统社会压迫的女性要求解放的呼声愈发高涨,原本受汉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束缚的广西妇女逐渐走出庭院深闺、奔走呐喊。而乡村少数民族的妇女自古与汉族地区女性足不出户有所区别,她们皆要外出劳作,“女勤男惰”中的“女勤”现象并非妇女解放的结果,而是由广西的地理、地情决定的,这恰恰是广西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