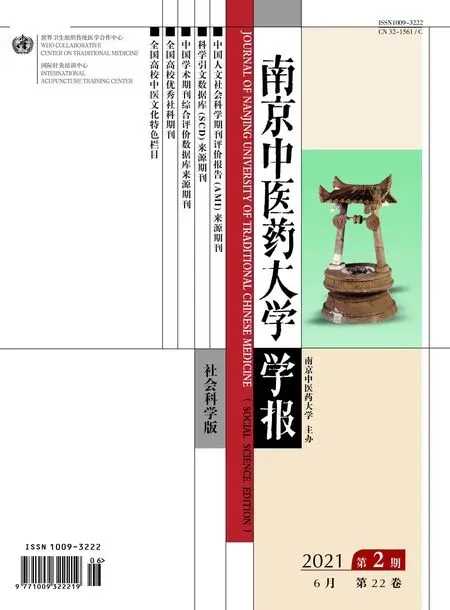张公让与《中西药典》
刘芳,罗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006)
1 张公让其人
张公让(1904-1981),原名其升,广东梅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张氏自幼聪颖,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专修文艺,次年转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医学,两年后又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193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医学士学位。后回乡随父研习中医,开设诊所。抗战期间在故乡梅县任松口镇平民医院院长,其间还到松江中学教授医药卫生知识。1945年迁诊所至梅县城。1947年迁广州市行医,举办中西医师进修班,培养新人。[1]
张公让既接受了正规的西医学教育,又“深得五代祖传中医之秘”,可谓兼通中西医学。张氏一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从医数十年,边行医边著书立说,著有《中西药典》《中西医典》《肺病自医记 吐血治验记》《医案医话 治医杂记》《医学衷中参西录(选评)》和《公让选方》等书,并常在各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如《答问》(张公让问,陆渊雷答)《肺病治验》《医药杂谈》等。张氏积极传授中医药宝贵经验,大力提倡中医中药科学化,其著述超过500万字,为医界留下了丰硕的遗产。1949年7月,其迁往香港行医,在香港创办“中国新医药研究院”,1975年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客座教授。张公让心系祖国大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晚年曾数次为振兴广东中医药建言践行。1981年10月张公让病逝于香港,终年78岁。
2 成书之因
百多年来,科学昌明,“西药踏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一日千里,进步无疆。中药呢?仍然滞留在原始之状态中,数千年来,进步很慢,许多良药神方,又秘藏在民间,不公开为世用。”今日本草数千年来验之多人,传之久远,有确定疗效,故“虽然西药成就辉煌,然而中药也仍然有它的价值。”(《中西药典·自序》)张公让认为中西药物各有千秋,若能舍短取长,一炉共冶,则治效必更佳,故著《中西药典》。中西兼论,明其药效,较其长短,以期减少中西医的误会与偏见,有益于人类健康。《中西药典》为张公让的代表著作之一,初版于1943年,名为《药物篇》;1948年大为更改,增订再版,名为《中西药典》。
3 主要内容
《中西药典》书分二部,一部为总论,另一部为各论。总论部分有“疾病之定义”“药物在各脏器之选择性”“药物各种作用”等内容,大体相当于西医的病理学与药理学总论。如“疾病之定义”简言人体为何会生病,相当于西医病理学总论;“药物各种作用”“药物在各脏器之选择性” 相当于西医药理学之药效学;“药物使用部位”“药物在体内之变化”“药物之分布及蓄积”“药物的排泄”相当于西医药理学之药动学;“影响药理作用诸点”“药物之相助及相抗作用”“药物之配合及形式”“特异质过敏性习惯性”相当于药理学影响药物药效的因素。
各论部分,共分26章,计载药物500余味[2]。其中前24章是按药物的功效把中西药划分为24个类别,每一类别先是关于该类别药物的名词解释,次言该类药的功效特点与药理作用,再言宜忌、中西药之比较,最后详列各种具有该功效的重要中西药物。对于每一具体药物,西药多详言其药理药效,中药或用西药之理释之,或不言药理仅言功能主治;中药之功效,常一药多能,故对其介绍常超出其类别功能,如附子列入强心剂类,然依张仲景之用附子,书中将其主治数列为“治恶风恶寒漏汗”[3]97“治疼痛解痉挛”[3]98“治脉沉微肢厥”[3]98“治下痢清谷”[3]99。对于常用中药,药物介绍之后亦列常用方剂,例如柴胡列属解热剂,在介绍其功效、药理之后,又介绍小柴胡汤、大柴胡汤、四逆散之组成、功效及主治等。第25章“十余年来欧美发现之新药”,此章介绍当时所用较新西药,主要有磺胺剂、青霉素、链霉素、维他命。第26章“补遗”,“药品不易列入上述各章者,皆列于补遗篇。盖一药常有数种作用,入甲固不可,入乙亦不能也”[3]170。
4 学术特点
4.1 中西并举
(1)药物按中西功效分类。书中各论部分的前24章按功效分类,其分类方法为中西并举。有偏于中者,如发汗剂、止汗剂、健胃剂、强壮剂、催乳剂、通经剂、解毒剂;有偏于西者,如呼吸系统治疗剂、尿防腐剂、强心剂、血管收缩剂及血管扩张剂、麻醉镇静剂、子宫收缩剂;有中西互通者,如解热剂、泻下剂、止泻剂、催吐剂、镇吐剂、利胆剂、利尿剂、止血剂、兴奋剂、催淫剂、驱虫剂。
(2)每类药物之下,列有中药西药。各论26章,除第12章尿防腐剂、第25章仅列西药外,其余24章均中西药并举。例如强心剂,既列有西药毛地黄、斯托洛番汀、咖啡因属、肾上腺素、葡萄糖,亦列有中药附子、马钱子、万年青、黄芪。
4.2 中西药疗效比较
张氏在《增订再版自序及例言》中言:“我这本书是中西药兼论而加以比较的。西药好在什么地方?中药好在什么地方?我都有详细的说明,而加以比较。”“一般而论,急性病当然以西药为胜,磺胺剂、盘尼西林、链霉素,哪一项中药比得上它;但慢性病则中药为佳,中药之强壮剂、兴奋剂,如参芪归地之类,西药尚无其匹。”在各论诸章中,有许多章都列有中西比较,例如第十章呼吸系统治疗剂中言:“总观呼吸道之治疗,镇咳剂以西药之苛第因为胜,中药无此神品。呼吸镇静剂,西药之吗啡甚佳。惟其因心脏衰弱或呼吸中枢衰疲者,则中药之固肾强壮剂及黄芪等为胜。此西药不及中药者也。稀释性袪痰剂中药无有胜铔剂者。惟慢性气管枝炎,则又以中药之细辛、半夏、干姜、白术、茯苓等为胜。若急性炎症则西药之盘尼西林、磺胺剂有奇功,中药不能望其肩背也。”[3]78又如第16章强壮剂中言:“强壮剂西药不及中药,凡禀赋虚弱者及传染病之恢复期,中药之人参、黄芪、当归、熟地、白术、茯苓、附子、肉桂殊有神功,西药之砒铁剂虽佳,但效力极慢,不能如中药之能于数日内恢复其大部分之健康也。”[3]115
4.3 中西药理汇通
《中西药典》以西释中,汇通中西,理多揣测,然不离临床心得。《初版自序》中言,“不佞愚鲁,惟幸能虚心好学,但治医之日浅,而用力又不专,更无实验室、动物试验之设备以为研究之助,仅凭几本参考书及临床所得,以论中药西药,得无管窥蠡测、纸上谈兵之诮?”例如石膏一药,将其列入解热剂,分析其解热药理言:“然其解热所用,似非钙所能,必在稀释血液中之水分也(石膏症为大热汗出狂渴,大热则蒸发水分多,汗出则水分损失更多,此时血液必浓缩,狂渴及引水自救也,石膏能治此症,其为稀释血液无疑)。”“石膏一物欧美尚不知利用,且忽视之。故其在体内之变化,尚无研究报告者,实一憾事也。然在吾国数千年来用为重要之解热剂,其效验无可疑也。”[3]20又如黄芪列入强心剂,张氏阐释其药理药效则言:“总观黄芪有强心、利尿、改善皮肤血液循环、兴奋横纹肌、平滑肌及脑脊髓中枢诸作用,余虽未作动物试验,然依临床观察,当如是也。”[3]106
4.4 临床心得丰富
《中西药典》一书,其特点与价值之一在于著者丰富的临床用药心得,其中不仅有成功的、效卓的,亦有失败的、与前人记载不相符的体会。如石膏治高热头痛有神效,“回忆十余年前,家母远行受暑,高热狂渴,昏不知人,头痛如破,余与家父商治,皆主竹叶石膏汤。每剂石膏一两,日进两剂,次日即愈。”[3]20再如浮小麦治疗失眠,“余经验栀子、枣仁之力甚微,有时甘麦大枣汤反有效,其理甚不可解。”[3]136“先父七十余岁时,常失眠,余奉以此汤,得安睡。如无浮小麦则麸皮亦可代之。”[3]140
4.5 博引时医效验
张公让医术精湛,且虚心好问,如《治血吐验记·时贤治验》中记云:“陈逊斋先生云,彼昔在汕,时得一单秘本,有一条以干姜一味止血,今市医用四逆汤止咯血,亦以干姜为主药。干姜止血之理,余昔不明,曾与陆渊雷先生邮书讨论,彼亦不甚了解,惟云有治案耳。”[4]张公让不参加党派,广交朋友,国民政府南迁时还曾任总统府特约医师、国史馆医事顾问、中央党部医事顾问等职,故对时医、名医之治验知之甚多,在《中西药典》中常博引时医治验以明药效,如谭次仲之“竹沥可治脑出血”[3]76“杜仲与牛七治脚软卓效”[3]121;卢觉愚谓“山楂煅成性研末,每服五分,治吐血下血甚效”[3]46“白术亦有制淫作用”[3]142;张锡纯“治痢下血多用三七”[3]111,谓山茱萸“治虚脱谓功胜参芪”[3]122;“广州奇医谭孟勤有一剂用细辛八两者”[3]74;余云岫言止嗽散“治伤风咳嗽甚佳”[3]76;“梅县名医刘竹林先生云其父秘传云黄芪得蚯蚓则不燥热”[3]23等。
5 结语
《中西药典》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其中所列许多西药,由于耐药性或副作用大已不用或少用,如书中所列链霉素、磺胺剂,今代之以头孢菌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于中药药理的科学分析,由于当时重视不够,研究者稀,同时亦受到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张公让所能获得的相关参考资料并不多,而有些参考资料的结论甚至与中医的功效相反,使其无法以西释中、汇通中西,例如远志一药,西医认为是刺激性祛痰剂,其药“于心之制阻力甚大,无论心有何病,皆不宜用”,“中医却大相反,凡心悸、怔忡、不寐(神经性心脏病)皆用之,以为安神宁心强壮之品,无用之却痰者。此中医之误耶?抑西医之化验未确耶?犹待将来之研究也。”[3]71
《中西药典》从药学的角度比较中西之长短、汇通中西之理、结合中西之用,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尝试。虽然该书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今天读来仍不乏启迪与借鉴之处,对当代仍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