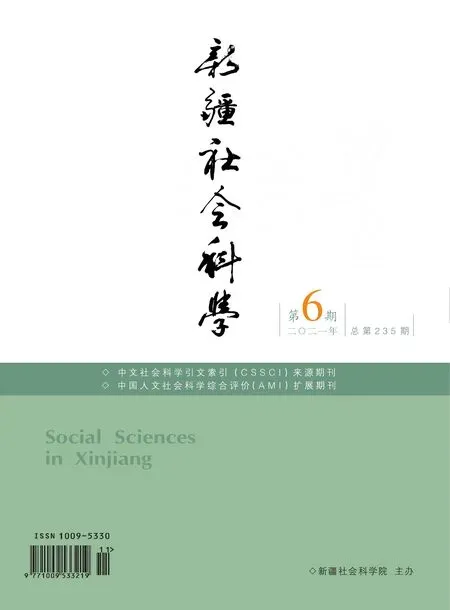“环-链-层”融合与合作社的组织生态演化*
——组织融合驱动产业融合的实践机制研究
张益丰 吕成成 陆泉志 高 强
内容提要:拓展农产品供应链、价值链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益举措,农民合作社的嵌入对于推动农业融合发展与价值链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探讨合作社在推动农村产业链融合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多维功能。研究证实:驱动合作社形成创新融合的动力源于组织对其生态位宽度的追求。融合初期,合作社面向社员构建“吸附型”融合环境,发展供应链重要节点的“环融合”;融合中期,合作社围绕农产品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构建产业“链融合”,且合作社发展纵向联合优于横向联合。融合后期,农合联形成多维供应链集束发展的产业联盟“层融合”。因此,推动产业由“环融合”向“层融合”升级跃迁的关键是禀赋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内部社会化服务完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涉农一二三产业之间融合发展的趋势明显,“三产融合”已成为推动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1)郭军、张效榕、孔祥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基于河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案例》,《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3期。着力构建三产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不仅被视作确保如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途径,更被视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2)张晓山:《下一步农村改革最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农村经营管理》2018年第9期。在农业产业融合过程中,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联合社)以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农合联)在农村产业融合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3)黄祖辉:《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业产业组织的变革与前瞻》,《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1期。但在具体发展实践层面,合作社、联合社及农合联在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内在关联如何?由合作社→联合社→农合联的跃迁如何有效形成?驱动跃迁的内在动力机制是什么?这三个循序渐进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已成为阻碍农业经营主体谋求融合发展,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掣肘。本文借助组织生态学的分析框架,探寻合作社向农合联进化过程中“环-链-层”融合发展背后组织生态位宽度拓展的演化过程,以及实现跃迁进化的必要条件,从而实现对上述问题的有效解答。
一、文献综述
当前农业三产融合研究重点围绕融合过程、(4)潘璐:《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一种路径》,《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融合效应评价、(5)郭军、张效榕、孔祥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基于河南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案例》,《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3期。融合条件分析(6)钟真、黄斌、李琦:《农村产业融合的“内”与“外”——乡村旅游能带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吗?》,《农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4期。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一)融合过程研究
1.融合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定位。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将成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7)杨涛:《农村产业融合的实践特征与提升路径》,《中州学刊》2019年第5期。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帮助小农进入市场,提高他们的议价能力,缓解信息不对称。(8)Tolno,E.,Kobayashi,H.,Ichizen,M.,Esham,M.and Balde,B.S.,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Farmer Organizations in Enhancing Smallholder Potato Farmers' Income in Middle Guinea,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2015,7(3),p.123.立足农业资源开发,围绕农民和农民合作社发展将是农业产业融合突破的重点。(9)宗锦耀:《以农产品加工业为引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工作通讯》2015年第13期。
2.农业产业融合的发展目标。肖卫东、杜志雄将农业三产融合定义为农业产业化的高级形态,通过打破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边界,实现“1+1+1>3”的产业融合效果,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10)肖卫东、杜志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产业融合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农民福祉,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11)王志刚、于滨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概念内涵、组织边界与增效机制:安徽案例举证》,《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2期。
3.农业产业融合的实现途径。有研究认为产业融合沿着供应链向前后延伸、拓展农业新功能和推广应用先进技术三种途径演化,(12)熊爱华、张涵:《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条件分析及政策建议》,《理论学刊》2019年第1期。而三种途径实际上均强调突破要素配置的制约,通过跨界集约化配置资源来促进农村产业协同,突出农业与二、三产业的结合,强化现代农产品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乡村旅游民宿等产业建设。(13)钟真、黄斌、李琦:(农村产业融合的“内”与“外”——乡村旅游能带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吗?》。
学界对于农业产业融合在主体定位、发展目标、实现路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上述研究集中在政策规制设计,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融合发展主体间互动与融合过程并未有效涉及。尤其是作为农户与现代农业实现有效衔接重要载体的农民合作社组织融合路径、融合形态的研究存在缺位。
(二)涉农产业融合测度与评价体系
有研究者利用DEA方法、层次分析法与灰色关联度分析农业产业融合的效率。(14)李玲玲、杨坤、杨建利:《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效率评价》,《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年第10期。除了对农业产业融合自身效率的检视以外,研究者更关注影响农业产业融合的关键因素分析。学者将融合分解为农业外向型融合与内源型融合,并且外向型融合通过要素禀赋的中介效应正向影响内源型融合。(15)钟真、黄斌、李琦:(农村产业融合的“内”与“外”——乡村旅游能带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吗?》。刘斐等的研究更侧重于农业产业融合过程中农民响应机制的分析。(16)刘斐、蔡洁、李晓静、夏显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个体响应及影响因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上述研究的立足点均聚焦在农业产业宏观维度的技术测度,未考虑多元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融合分析,因此通过微观视角分析农户与经营主体、经营主体相互融合,显然更适合探究农业产业融合内部演化的实现绩效。
(三)涉农产业融合条件分析
有研究者重点围绕农业产业融合外部条件、内部条件以及内外部因素交互展开论述。外部条件分析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融合过程中外部服务支持体系建设与金融保障措施将成为影响当前农业产业融合的主要因素。(17)朱信凯、徐星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苏毅清等则强调农业产业融合的实现基础是围绕农村资源禀赋,将外来要素向农村进行有效集结。(18)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8期。政府通过项目资助,实现地区产业与组织的重构将有助于融合的实现。(19)张益丰、王晨:《政府服务、资助对象选择与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新疆农垦经济》2019年第2期.有学者关注合作社的内生发展,认为发挥小农户的主观能动性是关键。(20)王乐君、寇广增:《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6期。有研究提出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以服务驱动小农利益与现代农业相结合是农业产业融合的核心要义。(21)罗必良:《小农经营、功能转换与策略选择——兼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1期。也有学者主张内外部相关要素整合,形成差序性融合与结构性融合。(22)陈学云、程长明:《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产融合路径:逻辑必然与实证判定》,《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1期。
尽管上述研究从完善利益联结机制、(23)姜长云:《日本的“六次产业化”与我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经济与管理》2015年第3期。高素质农民培育、(24)张益丰、孙运兴:《新型职业农民创业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以山东省莱州市文峰路街道金丰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发展为例》,《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技术嵌入、(25)何大安、许一帆:《数字经济运行与供给侧结构重塑》,《经济学家》2020年第4期。金融服务(26)温涛、陈一明:《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现实障碍与突破路径》,《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7期。等层面对农业产业融合进行了分析,但研究围绕农业经营主体组织间融合与产业融合的衔接研究相对欠缺,尤其是缺乏以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我进化与实现融合进化的研究。
众所周知,农民合作社作为一种由农民自发组织形成的合作组织,近年来发展迅猛,服务农民功能不断增强,已然成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在众多合作社理论研究中,关于组织融合的研究前期主要围绕“订单农业”为代表的契约农业展开,(27)叶祥松、徐忠爱:《显性契约还是隐性契约——公司和农户缔约属性的影响因子分析》,《学术研究》2015年第5期。后期围绕合作社创新发展绩效进行论述。(28)Ma,W.and Abdulai,A.,Docs Cooperative Membership Improve Household Welfare?Evidence from Apple Farmers in China,Food Policy,2016,58,pp.94-102.有研究认为,以合作社为核心来承载并提供多元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合作社发展成功的重要保障。(29)赵晓峰、赵祥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能力建设与小农经济的发展前景》,《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4期。但相应的研究存在一个结构性思维断点,即以合作社为载体提供社会化服务如何实现合作社功能扩展或者组织间融合,演化路径是什么?
研究从交易成本降低、规模效益提升、生态位演化视角分析了联合社成立的必然性。(30)崔宝玉、王孝璱、孙迪:《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的设立与演化机制——基于组织生态学的讨论》,《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0期;孔祥智、岳振飞、张琛:《合作社联合的本质——一个交易成本解释框架及其应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苑鹏:《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发展的探析——以北京市密云县奶牛合作联社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8年第8期。其中孔祥智、黄斌将联合社运行机制定义为技术引领型、专业协作型、产业链“内循环”型以及行业协会型四种机制,形成差异的原因来自于环节的依附度、多元度、兼容度、辐射度方面的异质性。(31)孔祥智、黄斌:《农民合作社联合社运行机制研究》,《东岳论丛》2021年第4期。崔宝玉等进一步提出联合社与合作社的互动既要考虑生态圈内的协调,又要考虑与外部生态系统的耦合,一旦在建构生态位竞争机制过程中出现错位,两者的关系将会畸变。(32)崔宝玉、王孝璱、孙迪:《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的设立与演化机制——基于组织生态学的讨论》。尽管上述研究就小农户联合、合作社联合已进行了论证,但组织间融合的基本规律、实现融合的条件分析却未有涉及,因此强化融合过程分析就显得极有必要。
韩江波提出“环-链-层”产业融合架构并针对宏观产业融合生产环节,产业链、价值链、组织链及供应链多链管理,(33)韩江波:《“环-链-层”:农业产业链运作模式及其价值集成治理创新——基于农业产业融合的视角》,《经济学家》2018年第10期。我们将借鉴其“环-链-层”架构设计思路,运用组织生态学理论来分析组织融合的基本演化规律。研究提出下列基本假设并进行论证:
1.合作社产生于农业产业融合的初期,小农户加入合作社实现“吸附式”融合。合作社通过为小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促进小农户与合作社在农产品供应链的生产环节实现“吸附式”融合,构成产业“环融合”。
2.联合社产生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中期,合作社之间通过联合实现“互利共生型”融合。围绕农产品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有助于扩展其生态位宽度,构建产业“链融合”;并且合作社纵向联合优于横向联合。
3.产业融合的后期,成熟的联合社将不同的供应链整合形成空间融合,构成产业联盟性质的“层融合”。联盟生态位宽度是多维“束”,合作社→联合社→产业联盟演化规律实现了生态位宽度拓展由平面向立体的嬗变,资源的配置能力与社会化服务提供的完备性决定了产业融合的成效。
二、“环-链-层”视角下农业产业有机融合的实现路径
(一)生产端“环联结”与专一型种群演化
生态位是一个种群或者一个物种在一个群落中的角色,如果某一种群对其他种群的成长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则两个种群或者种群之间存在交互作用。(34)Elton,C.S.,Animal Ec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某一种群对其他种群的成长产生正向(负向)影响,种群之间的关系会形成共生(竞争)关系。(35)Gause,G.F.,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Williams and Wilkins,Baltimore,Maryland,1934.传统组织生态学认为两个具有相同基础生态位的种群之间无法均衡共存。根据 Lotka(36)Lotka,A.J.,Elements of Physical Biology,Williams & Wilkins Company,1925.与Volterra(37)Volterra,V.,Fluctuations in the Abundance of a Species Considered Mathematically,Nature,1927,119(2983),pp.12-13.的分析框架:设种群的设立率为λN,种群死亡率为μN,而种群的成长率为ρN,N为种群数量。其中:
单个独立种群成长率为

(1)
ρN=λN-μN
(2)
λN=a0-a1N
(3)
μN=b0+b1N
(4)
将(3)与(4)式代入(1)得:

(5)

(6)
其中,r=a0-b0为内禀增长率(Intrinsic Growth Rate)。当两个种群间其中一个种群扩展,将会影响另一个种群的生存空间,两个同质种群的成长率分别为:
(7)
(8)
当原始种群环境出现新的竞争者,K1-a12N2 产业发展初期鼓励合作社对小农户、家庭农场进行吸纳,围绕供应链的某一环节展开合作,通过组织间“吸附”融合,将农户吸纳进合作社,实现以合作社为核心的产业“环融合”,促进合作社在供应链重要环节(如生产端)生态位宽度增加,形成具有组织凝聚力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实现集体行动中减少农户“搭便车”行为的发生,降低小农户种群的“死亡率”。(40)Echols,A.and Tsai,W.,Niche and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twork Embeddedness,Stru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3),pp.219-238.假设1成立。 图1 “环融合”发展示意图(41)图中双箭头线段表示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就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形成互动关联,农户在以合作社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中获得生产与服务信息;虚线表示农户之间存在相互关联与信息交流;当前以合作社为核心形成的“环融合”占据农产品供应链生产端的优势位态。 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在环境资源与自身能力之间进行均衡调整,(42)Ajzen,I.,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es,1991,50(2),pp.179-211.由于资源禀赋受限,合作社无法将所有精力用于全产业链的拓展,必定会在战略上进行取舍,专注于农产品供应链的某个环节进行开发就成为当前多数农民合作社经营过程中的理性选择。合作社实现全产业链发展必须具备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外部资源的持续输入。通过政策支持,各级政府(部门)为合作社发展提供外部物质与无形资产等资源的扶持,为合作社进行全产业链拓展提供充分条件。二是自身能力与资源相匹配,合作社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社会资本来引领合作社发展成为合作社实施全产业链发展的必要条件。(43)Caplan,R.D.,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y and Organizations:Commensurate Dimensions,Time Perspectives,and Mechanisms,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1987,31(3),pp.248-267. 单就普通合作社而言,独立谋求全产业链发展难度较大,合作社为进一步拓展生态位宽度会考虑以联合发展来应对市场风险与经营风险。合作社选择联合,通常会考虑数个地理位置临近、经营品种类似、处于同一生态位的合作社进行“横向”结合,尽管联合后组织的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但由于新组织经营品种、销售途径与原组织雷同,联合后生产加工能力、市场资源以及联合后的管理才能并未有效突破资源禀赋的桎梏,供应链中、后端能力提升不足造成联合社生态位宽度没有完成实质性的拓展,其资源调配能力与产业发展的要求脱嵌。 组织同质性越强,生态位重叠强度越高,组织之间合作可能性将会下降。(44)Mizik, N.,Assessing the Total Financial Performance Impact of Brand Equity with Limited Time-Series Data,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14,51(6),pp.691-706.专一型组织面临资源约束时,组织将更倾向于结成“异构型”联合体,(45)Hantan,M.T.and Freeman,J.,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82(5),pp.929-964.“异构型”联合体的主导者促成联合的目的在于帮助其获得供应链多个环节的位态优势,实现供应链上下游环节之间的资源、能力互补,即形成占据不同生产环节优势合作社之间共享资源、弥补能力短板(如共享市场资源,提升加工生产能力,选择更有经营能力的管理者来领导联合社的发展),围绕供应链的流程形成“链融合”,将有效促进联合社生态位宽度的拓展,并且在参与群体增加的同时促进社会网络密度增加,强化信任规范内化行为实现结构洞占据者联合,有助于产品利基型或者流程利基型合作社提升经营效率。(46)Granovetter,M.,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19(1),pp.33-50.因此,“链融合”有助于“异构型”联合体拓展生态位宽度并实现农产品供应链上多个网络结构洞的有效占据,更适合产业融合中期全产业链的发展需求,较之传统的横向融合更具优势。假设2成立。 图2 联合社的“链融合”示意图(47)图2中农户与每个合作社均有双向信息交流,联合社形成“异构型”产业联合体内部合作社之间存在双向信息交流,联合社占据生产-加工-销售整个农产品供应链各优势位态。 随着联合社的发展与进化,联合社的产业化进程已经不再仅考虑单一农产品供应链“产前-产中-产后”的优化问题,而关注多维度供应链的协同问题,因此建立联合社的“产业联盟”将有助于妥善解决上述问题。产业联盟不仅包括产品生产单元,也包括农资供应单元与融资服务单元以及生产性服务供应单元,并且与其他供应链形成交互影响,所有的参与者均能在各自的产业链中占据关键位态,使得产业联盟的生态位宽度不再局限于单一平面,而是构成多维、立体式的生态位宽度。如浙江农业“三位一体”改革中出现的由农民联合社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简称“农合联”)演进的过程就是这一构想的现实写照。 农合联模式依照“区域聚合、功能互补、产业互联”来完善组织体系,并遵循“功能模块化、服务实体化、资源集约化、运转市场化”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功能,在农合联内部设立服务中心,为各个辖内联合社提供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与信用服务,弥补各联合社自身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通过综合服务功能来促进各个联合社的发展与壮大,形成多条供应链的协同和进化。 图3 “环-链-层”组织进化示意图 由单一功能、专一型种群向多功能、多样性种群演化,其核心要义来自于由平面、单维组织生态位宽度向多维、立体组织生态位宽度演化,并且宽度进一步拓展,实现组织融合后创新型组织对资源禀赋调配能力提升。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三点: 1.依靠组织能力提升后能挖掘更多禀赋资源。组织通过融合与创新在农产品供应链各个环节以及关联产业中寻找到更多潜在资源,如原本无法利用的市场信息资源、电商平台资源与技术资源,组织的进化使得组织有能力掌握这些资源并能顺利使用。 2.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了组织进化的韧性。一方面,创新型组织通过承接政府社会化服务项目与技术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了组织自身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能力。另一方面,组织内部形成面向内部成员的社会化服务供应体系,通过服务将各个独立的个体有效串联,通过生资供应信息、技术、流程管理、市场、培训实现组织内部、组织间的社会化服务无缝覆盖,有助于供应链关键环节、供应链、多条供应链之间形成高质量发展。 3.有效配置与使用资源禀赋。组织的融合发展,更多有能力、有专业技术的高素质农民投身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设中,提高了合作社、联合社与农合联内部的人力资本与企业家能力,有助于创新型组织依托高素质农民的领导才能带动组织实现跨越式发展。假设3亦成立。 本文选取的5个案例分别来自山东省烟台招远市蚕庄镇灵山蒋家村灵山果蔬专业合作社(后文简称:灵山合作社)、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欣跃三莓果业专业合作社(后文简称:三莓合作社)、山东省沂源县鲁村镇福吉山村新民养兔专业合作社(后文简称:新民合作社)、浙江省台州市台联九生猪产销合作社联合社(后文简称:台联九联合社)、浙江省台州市小芝镇下里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后文简称:小芝农合联)。上述案例素材均由作者于2016—2021年分别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获得,素材按照三角互证原则,(48)Yin R.K.,Case Study Research:Design and Methods,Sage,2009.分别对合作社理事长1人、核心成员2人、普通社员2人进行半结构访谈,同时对所属地区农经站负责人进行无结构访谈,最后为验证结论作者还利用python爬取相关案例的新闻素材、网络报道作为第三方佐证材料。 案例1选取的灵山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11月,现有社员463人,是一家具有鲜明特点的党支部领办的果品种植类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中村集体占股95%、社员占股5%,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540亩,扩大建设现代苹果矮砧栽培示范基地,引进以色列先进技术,建成肥水一体化滴灌设施。2020年灵山合作社的生产规模占全灵山镇的1/5以上,占据招远苹果供应链生产环节的优势地位。 案例2选取的三莓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9月,由宾县职教中心5位教师发起成立的黑加仑、红树莓、蓝靛果种植合作社,发展鼎盛时期共有社员146户,种植面积达750亩,年销售三莓鲜果300吨。但由于合作社专用性资产投资过大使得合作社无力强化生产流程管理,造成合作社产品与普通农户生产产品同质性过强,合作社在当地并未形成三莓鲜果生产端的定价权和规模优势,对于普通种植户入社吸引力逐渐减弱,2014年后合作社经营陷入困境,有73家社员退出合作社经营,合作社也被迫转让冷藏设备和果品流水线,原本的合作社内部“三产融合”模式出现了退步。 案例3选取的新民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4月,注册资本51万元,是集科学养兔、种兔繁育和兔肉初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合作社,入户社员由初创期的5户发展到现在的160户,资产850万元,2020年销售额1500万元。2020年底新民合作社牵头与当地梅花鹿养殖合作社以及果品种植合作社共同出资300万元,成立了沂源禾牧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形成兔业养殖、梅花鹿养殖、果品种植多元发展格局,养殖合作社提供的兔粪、鹿粪的药物残留少,能为种植合作社提供有机肥;合作社共享销售渠道与生产流程服务。养殖合作社的季节性经营特征也能为种植合作社在农忙时提供套袋等田间管理的季节性劳动力,解决用工问题,新民合作社参加联合社能有效解决粪肥使用、销售渠道拓展、社员就业途径拓展等问题,在强化自身农产品供应链建设的前提下促进了关联合作社的成长。 案例4选取的台联九联合社成立于2012年,由台州市九个县市区的规范化合作社和养殖企业联合建立,注资600万元。目前有276家会员,核心会员57家,省标准化养猪企业7家,美丽牧场5家,还拥有5万吨级的饲料加工厂与年产有机肥3万吨的有机肥厂,成立规模5000万元的资金互助会。联合社与大北农等农产品生资、疫苗生产头部企业合作,生产专供联合社内养殖合作社使用的优质饲料与兽药,联合社的多元发展使得生猪供应链产前、产中与产后各个环节的经营能力得到增强。 表1 案例特点简介 案例5选取的小芝农合联成立于2016年3月,现有51家会员单位、5名个人会员,其中专业合作社代表42家,家庭农场4家,购销大户1家,其他涉农企业4家,农业服务中心、信用社各1家,该农合联除了拥有多条完整农产品供应链以外,还提供农民培训、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项目,农合联的农产品供应链包括小芝永泰粮食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主导的优质稻米供应链,谷牧盛景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主导的“小芝”米粉生产-加工-销售供应链体系、“念芝味”中药(灵芝)与土特产(姜片、番薯)种植产业链、鸵鸟养殖等多条完整供应链。 案例1中的灵山合作社通过五个维度建设形成合作社的凝聚力,拓展合作社的生态位宽度,确立了合作社在优质果品生产环节的主导地位。一为组织建设: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高效的组织内部治理(如设立党员考核制度,合作社领导监督机制),夯实了合作社发展的组织基础和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合作社骨干力量;二为科学生产:合作社采用统一采购优质种苗、免费分给社员种植,生产过程中采用“四统一”模式进行苹果生产(统一种植技术、统一生产管理、统一技术培训、统一收购销售),使得果品种植的质量和价格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且农户掌握经营主动权,农户参与热情较高;三为专用性资产投资:合作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如建立现代苹果矮砧栽培示范基地,以色列肥水一体化滴灌设施,硬化村道1000余米,为苹果适度规模化生产、科学化运营打好基础;四为完善社会化服务:合作社按照机械化生产的技术要求,成立果业技术服务队为社员提高全程社会化服务,社员经营规模由原来的3—5亩提高到30—50亩;五为提升销售能力:合作社一方面加大营销团队建设,另一方面建成高标准果品贮藏冷库、气调库,为果品错峰销售夯实了基础。 案例2中的三莓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并不顺利,尽管发展初期,职校教师领办的合作社具备较强的技术优势,创业初期发展势头良好,但合作社在经营过程中对于组织建设与社会化服务建设的投入不足,没有形成要素契约与商品交易契约的治理环境(表现为没有按交易额/量对农户的二次返利机制),也缺乏对社员的生产流程的系统化管理,而是将建设重点用于重资产投入硬件设施上(自办冷冻加工厂,投产果品生产流水线)。过度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加剧了合作社经营被供应商与社员“套牢”的风险。大量的农户跟风种植三莓果品,宾县的三莓果品出现供过于求,加之合作社的产品与普通种植户的产品同质性高,收购企业通过向中小农户收购来打压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缺乏质量与定价优势造成其产品的市场销路受阻;同时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专用性资产投资过大使得合作社经营在生产服务环节的投入不足,合作社的社会网络嵌入能力不强。多种因素的交织造成合作社丧失了生产端的规模优势,使得自身在三莓产业中的组织生态位宽度不但没有拓展,反而被其他经营者挤压。最后,合作社内部互信与规范行动机制丧失,使得合作社无法有效约束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合作社对于普通小农户吸引力也逐步降低,合作社经营绩效下降严重。 案例3中的新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已较好地占据了肉兔供应链中生产环节的核心位置,具备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可观的生产规模。(49)2017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合作社营业收入1619万元,存栏种兔8万多只,存栏商品兔5万只,年可出栏优质肉兔40万只,成为四川、重庆等肉免消费地区最重要的肉兔供应商。但合作社经营依然存在三方面的隐患:一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兔粪)无法有效处理;二是养殖户坚持发展的信心不足;(50)肉免养殖是季节性工作,每年肉兔出栏后养殖户有长达三个多月(分为夏、冬两季)的空闲时间,外出长期务工会耽误下一个生产季的安排,很多养殖户为追求更稳定的收益被迫放弃养殖。三是销售渠道单一。新民合作社原本的肉兔主要集中供应重庆、四川等地,在其他地区的肉兔销售渠道缺乏。新民合作社于2020年9月牵头,联合同一地区的其他两个合作社(梅花鹿养殖合作社、果品种植合作社)成立联合社,养兔、养鹿产生的粪肥经过堆肥后能为水果种植提供优质有机肥,解决了养殖合作社困扰已久的粪肥处理问题,果品的质量和收益也因有机种植而获得提升(黄桃销售价格普遍提升4元/斤)。果品合作社能够为部分人员提供专职负责兔粪与鹿粪清运的工作岗位,降低了养殖类合作社的人工投入。 梅花鹿养殖合作社有很强的市场拓展与销售能力,成立联合社后新民合作社的肉兔销售得以拓展到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市场,销售能力得以显著提升;梅花鹿养殖合作社借助新民合作社肉类加工设备,开发了鹿肉干等新产品,果品合作社具有本地生资供应渠道,为两家养殖类合作社提供优质、廉价的生资产品。三家合作社通过共用商标,共享生资资源,实现了资源互补;最后养殖合作社加入联合社后有效解决了社员劳动力闲置问题,农闲时节养殖类合作社社员可以去果业种植合作社从事套袋、疏果等工作,提高了社员的收入。通过联合,三家合作社各自实现了在供应链上、下游的补强。联合行动的主导者——新民合作社并未选择经营品种相同、地域先进的同类合作社形成合作,而是通过差异化联合来补齐发展短板,形成生资供应、销售、就业、附加产品销售等多渠道能力的提升,起到“1+1>2”的效果。实际上地域内农产品市场存在高度重叠,市场销售渠道不通畅条件下,群体的增加但社会网络密度并未提高,同类合并无法有效增加种群存活率。新民合作社组建的联合社证实了联合不是追求单纯的规模效应,更多考虑的是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的互通与产业协调。但该联合社发展尚停留在供应链补强阶段,并未真正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案例4中的台联九联合社,不仅吸纳了普通社员219户、核心社员57家,还吸纳多家养猪企业与美丽牧场,更与大北农合资成立高标准饲料加工厂,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异构联合体,通过全产业链发展拓展了自身的生态位宽度。首先,联合社通过强化规范提升经营效能,联合社内部按照“统一生产技术、统一防疫采购、统一饲养标准、统一营销、统一信息共享、统一排污物处理”的原则进行规范生产,在生猪生产端形成了产业优势;其次,通过全程社会化服务打通全产业链发展的阻点。一是解决生资供应问题,筹资1200万元与大北农集团合作办饲料加工厂,统一了联合社内部的饲料来源,保障了生猪的质量,按内部优惠价格供社员使用放心饲料,社员年均可降低成本150万元;按此经验联合社还通过大客户团购的方式向国内著名兽药加工厂家采购放心兽药。二是解决环保问题。联合社投资413万元建成1万立方米的沼气池进行发电(装机容量120kW)。生猪养殖粪肥的利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联合社建立有机肥厂,年吸纳消化畜禽粪污9万吨,不仅提供联合社社员单位使用,还通过外销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三是解决资金供应问题,成立资金互助会(资金委托农商银行统一投放、统一回收),为社员经营提供了资金保障。四是联合社实现社会网络的高效嵌入。表现为参股大北农、台州路桥的生态农场项目建设,经营范围进一步拓展;与东北、宁夏生猪供应商合作发展,在整个生猪供应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凸显。 图4 小芝农合联社会化服务类型 联合社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形成主导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更要向其他产业链拓展,实现单一维度的生态位向多维度、立体的生态位进化。案例5中的小芝农合联具备拓展多维度发展的实力。农合联既包含了生产优质稻米的永泰粮食种植合作社联合社(7家专业合作社组成),(51)联合社粮食作物生产规模6000亩,年产量超过2400吨,是台州市首屈一指的粮食经营主体。也拥有薯粉、鸵鸟肉、猕猴桃完整产业链,拥有较强的生产与加工能力以及成熟的商贸交易平台。小芝农合联同时也具备完善的社会化服务能力。农合联通过多元社会化服务为联合社的生产提供保障(提供生产指导、庄稼医院、产销服务、合作金融服务、农信担保服务等),促进联合社健康发展。 农合联内部各条供应链之间实现平衡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积极承接政府项目、自主提供服务两种方式形成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供应体系使得农合联这一多维“异构联盟”在抗御外部风险,有效解决资源使用方面的能力(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企业家能力)全面提升,形成供应链环境中多维生态位宽度的提升(小芝农合联提供社会化服务类型详见图4)。 1.“吸附式”融合与社会化服务支撑 灵山合作社通过集结合作社所能掌控的资源,利用党支部领办模式来增强社员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合作社通过“吸附式”融合成为当地果品生产的龙头合作社,合作社的资源环境、生存空间得以改善,其组织生态位因为融合实现了拓展。三莓合作社经营起点很高,在三莓种植与销售环节曾经是当地的“先行者”,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注重社会化服务的提供,关乎合作社生存的生产流程管理、技术改良、统一生产等社会化服务投入低下,造成合作社在生产端的规模与技术优势丧失,合作社并未占据由社员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洞,直接导致合作社对社员的“吸附”能力下降,合作社的组织生态位宽度没有得到有效拓展。 因此,两个发展效果截然相反的案例说明,社员加入合作社的目的在于提升自身的组织生存率,实现收益与能力的提升。而提高组织生存率的关键在于组织嵌入度增强,合作社为小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合作社社员依托合作社能在获得社会化服务的同时,提升自我经营能力和合作社参与度,合作社的壮大也带动了社员的发展。而在自身经营能力未有效调配资源的前提下,合作社经营范围盲目扩张且不注重内部社会化服务的提供,社员满意度的下降导致组织凝聚力不足与组织对网络的嵌入度下降,将影响合作社的发展效能,合作组织生态位宽度也受影响。因此,假设1可证。 2.“链融合”与社会化服务能力提升 新民合作社尽管在肉兔养殖生产端占据了优势地位,但合作社在生资供应、销售能力、社员经营的稳定性以及养殖废污的处理等方面均存在短板,合作社自身的资源调配能力无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合作社拓展自身组织生态位宽度存在障碍。新民合作社主动与梅花鹿养殖合作社、果品种植合作社联合成立联合社,其目的就是提升合作社在社会网络的嵌入度,使得原本存在缺位的供应链建设通过联合得以补强,联合社通过资源互通,以社会化服务形式来为参与者提供急需的粪肥利用、市场拓展、生资服务。新民合作社发起组建的联合社属于融合初期向融合中期的过渡阶段,通过“链融合”与其他两家合作社进行合作,新民合作社进一步拓展了组织生态位宽度,完成了肉兔供应链全产业链发展。 台联九联合社的进路属于典型的“链融合”,台联九联合社自身已在生猪生产环节形成产业绝对优势,联合社通过“外引内联”方式,与生资供应商、生产大户等实现联合,补强了种苗、饲料、养殖、屠宰、有机肥全产业链的多个薄弱环节,台联九联合社因此能占据生猪供应网络中结构洞,有效拓展了组织生态位宽度。 无论是新民合作社案例还是台联九联合社案例均体现出联合促进“互利共生型”发展态势,联合社围绕农产品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建设为突破口,构建产业“链融合”,扩展其生态位宽度,随着产业融合的深入,主导融合的合作社更愿意围绕自身供应链构建形成上下游经营主体融合,合作社纵向联合后的组织生态位宽度明显优于横向联合的效果。因此,假设2可证。 3.“层融合”与多维供应链集合发展 小芝农合联由51家会员单位、5名个人会员组成,既专注于粮食、农副产品完整供应链的构建,又为农合联内部成员提供生产、供销、信用等服务,保障了多维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同步。农合联通过联合实现内部经营主体的取长补短,提升了组织资源调配能力,社会化服务供给能力提升也促进了内部组织的“黏合”,使得农合联成为真正功能互补的异构产业联盟,因此由“合作社→联合社→产业联盟”发展遵循产业进化循序渐进规律,资源的配置能力提升与内部社会化服务的完备性是产业联盟实现组织生态位立体式拓展的保障。因此,假设3可证。 本文借助组织生态学的分析框架,研究分析了农户融入合作社发展、合作社联合形成联合社、联合社构建产业联盟的发展脉络,并通过多案例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1.农业产业融合的初期,小农户加入合作社实现“吸附式”融合,获得社会化服务的提升与能力的改善。合作社围绕供应链重要节点吸引农户加入,合作社通过提升社会网络嵌入度来构建“环融合”,实现组织生态位宽度的拓展。促进合作社“吸附式”融合的关键在于社会化服务的完备性与组织的凝聚力。 2.合作社通过联合实现“互利共生型”发展,围绕供应链上下游展开合作,有助于其拓展生态位宽度并增强市场中组织生存率。因此,构建产业“链融合”发展异构型联合体的组织生存率更高,形成“链融合”的基础是构建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3.联合社为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将谋求多维供应链整合发展。构建功能互补、多链协同的异构型产业联盟性质“层融合”,提升社会化服务的完备性是产业“层融合”成败的关键。 根据研究结论,作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合作社应加强社会化服务供应能力建设。将合作社定位为社会化服务的承载中枢,既承接政府的社会化服务项目,又为社员提供针对性的全程社会化服务。通过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发展带动合作社经营体系高效运转,促进合作社在供应链重要节点做大做强,提升合作社的凝聚力。 2.鼓励骨干合作社通过供应链体系纵向融合来发展联合社。围绕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重要环节,针对性地找差距,寻找互补的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进行联合,弥补供应链短板。实现以核心成员引领的农产品供应链全产业链发展,创造“链融合”发展环境;对单纯横向融合扩大规模、功能单一的联合社发展持谨慎态度。 3.鼓励异构性产业联盟性质的“层融合”。以联合社为核心,打造多条完整供应链协同发展模式,形成多维供应链在禀赋资源、技术能力、管理方法上的互通,将成为联合社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参照浙江“三位一体”发展经验来建设产业联盟,为“层融合”提供体系化的生产、供销、信用多元服务,提升产业联盟的核心竞争力。
(二)“链融合”与“多样化”种群演化

(三)多维生态位宽度的构建与产业联盟的形成

(四)形成种群演化的关键因素
三、案例比较与分析
(一)案例简介

(二)产业融合前期的合作社的生态位
(三)联合社生态位宽度与供应链的有序构建

(四)产业联盟发展与多维供应链的形成
(五)进一步讨论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