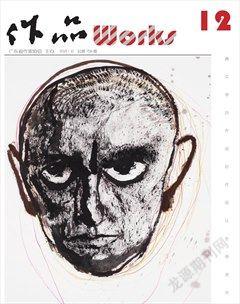黑匣子(短篇小说)
张沪佳
推荐语:龙扬志(暨南大学)
《黑匣子》展示出一代人寻找自我的深意。王福来遭遇考试作弊的污蔑,在被剥夺辩护权力的刺激下,培育出超强的画面再现能力,一段挫折因此阴差阳错地造就一位摄影师,可谓现实之补偿原则。然而,借助相机讲述内心的故事,何尝不是信息化时代大众处境的隐喻?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貌似你我生活在一个万头攒动的广场空间,其实屏幕前尽是静默无言的众生,上网就是在他者制造的符号串里代入自己一些零碎感受,不过看起来人们很享受这种被操控的自由。
小说不长,采用表现主义的手法耐心推进,用一个稍显时髦的概念表述,是融入了“二次元”的创作理念。从卡夫卡的《变形记》开始,变形成为彰显现代性症候的一种手段被不断借鉴使用,在《黑匣子》这部新秀作品里,物化于文本形式的探索尝试同样回应了新的时代情境,就像王福来利用相机说出不敢面对、讳莫如深的隐痛一样,作品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那些被时代所制造又暂时无解的问题,这很重要,找回自己可能历经千辛万苦,但不可回避。
讀完《黑匣子》的刹那,我下意识联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倒不是因为王福来跟拉斯柯尼科夫一样中途辍学,而是面向灵魂的追问与探询,展示出再现意识之流的细腻、冷峻与娴熟。日内瓦学派批评家乔治·布莱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意识行为。《黑匣子》的自我意识也参与了现代小说对自我认知的介入,像一道急流流过峭壁,浸湿读者内心却并不与其混为一体,作品对网生代心理情感结构的思考与探索值得重视。
这间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馆在午夜的时候会发生奇妙的魔法,而王福来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一到夜里十二点,在咖啡馆里坐着的王福来就会变成一个苹果。随着时间流逝,他的皮一点一点脱落,他的汁水一点一点被吸食,最后干瘪的果肉自动变成薄片,挨个地排队离开他,进入真空的食品包装里。他只剩下了核,得以用最平滑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他发现只有在这个时候,世界才是圆的。
凌晨两点左右,他又会重新变回来。变回来后,他就会迅速离开咖啡馆。当他与咖啡馆背道而驰的时候,他察觉身后有一道炙热的目光。于是他转过身去确认那道视线,透过咖啡馆的窗户,他看到自己之前坐过的桌子上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它们一边被火烧着一边带着强烈的意志朝桌子边缘移动,并在被烧完前到达了桌子边缘。他看到了从那儿垂下的一小截苹果皮。
苹果皮在火焰中化成灰烬的同时,王福来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去,从黑黝黝的车行隧道中穿过。顺着这条隧道可以一直走到他住的小区。在他即将走出隧道的时候,水泥地里混杂着不知名透明物质,就已经在折射月光了。当隧道覆盖在他头上的阴影全部消失的瞬间,月光凝聚成了一束明亮的光,在他身后的世界形成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
小区的环境十分糟糕,所有的设施不是蒙上了灰尘,就是已经被腐蚀得破烂不堪。还好小区的人工河堤岸旁种了一排柳树。这是一群在夜晚充满活力的柳树,厚厚覆盖在柳叶上的尘土在月光的掩护下悄然消失。
王福来慢慢地在柳树丛间走过,顺势垂下的枝条时不时地从他的头顶上掠过,穿过头发,轻轻地在头皮上挠一下,这若有似无的触摸感,让他放松下来。在快要走到柳树群的尽头时,他发现其中两棵柳树中间坐了一个女人,她的长发就如同柳树枝条般柔软地与她依偎在一起。他打量着她的背影,柳树枝条正如抚摸着王福来那般轻抚着她。王福来刚要从她身边经过时,她转过头来。
在看到她熟悉的面孔时,他停下了脚步,刚好停在柳树枝条触碰不到的缝隙里。她的皮肤仍旧像之前那般白净,只不过眼下的黑眼圈在这般通透的皮肤上出现,让人不得不注意到它。他的视线从黑眼圈处向上移动,看到了她的瞳孔,她也同样看着王福来。他们俩谁都不说话,就这样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她只敢看他瞳孔漆黑幽深的部分,以掩饰自己的心虚与慌乱,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于是对视久久无法结束。最终,她移开了视线,对王福来说道:“要一起坐会儿 吗?”王福来的鞋底与水泥地产生的摩擦,发出了这静谧氛围内最大的噪音。他带着颇有怒气的余音,从她的身后渐渐走远了。
自那以后,王福来就再也不去那家咖啡店,也不从车行隧道抄近路回家了。他再也没有变成过苹果了。可不知为何,他总是会想起那一小截燃烧着的苹果皮。而一想起那苹果皮,他就会想起小区里的那两棵柳树和坐在柳树间的那个女老师——那个污蔑他考试作弊而导致他从大学退学的女老师。
当时的情形说是污蔑也有些言过其实。那是大三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王福来被同学举报作弊,那个冤枉他的同学还向老师提供了“证据”。她若是好好调查考证一下那些“证据”,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可她在工作与家庭间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分心在这件事上,二话不说就取消了王福来的考试成绩,并打算上报到教务处。
下午在办公室里,只有王福来和女老师两个人。刚开始,王福来有条有理地向老师解释考试那天发生的事情,恳请她调查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再做决定。他轻声细语地,生怕惹得她不耐烦。
可她却兀自陷入自己的情绪中,连看都没有看王福来一眼。
王福来一下子感到了夏日的闷热,办公室里产生了让他喘不过气的窒息感。皮肤表面在发热、发烫,汗液从中渗出,可身子却变得愈发冰凉,在热气中隐隐颤抖。他为了能让父母骄傲所做出的努力、他耗尽时间与精力钻研的成果、他从小到大的人生中唯一可以自己掌控的东西,如今在他眼前一点一点地消失了。起先只是微小的,但在办公室里酷热与冰冷的僵持中,微小的绝望密密麻麻地布满在王福来的身体。
他跌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当看到在地上放声大哭的王福来时,女老师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跟着他一起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向王福来抱怨她的老公、她的婆婆、她两岁的儿子、学校的领导、她的同事、班里的学生……说个没完没了。
当王福来缓和过来时,泪水已在脸颊上变得干涸,办公室单调地回荡着老师撕心裂肺的哭声。女老师刚来学校没多久,她面容清秀,脾气又好,在同学之间很受欢迎。王福来曾经也对她有着几分没由来的好感,不过现在都已消失殆尽了。他从地上站起来,不顾此刻已经哭得没有形象的老师,跟她说了声再见,就从办公室出去了。结果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王福来被取消了期末考试成绩,上报到教务处后,他又被记了大过。
但在女老师办公室的那个下午,王福来觉得自己的心好像变得更明晰了,离某样东西更近了些。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温暖的冬天悄悄生长。他担心这只是一时的错觉,于是耐心地等待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心中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主动从学校里退了学。
六年之后,王福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可当他坐在工位上,女老师、苹果皮、火焰、灰尘、柳树轮流在他脑海里出现时,那年午后的闷热感又扑面而来。随之而来的是灼热散去后的清凉,他感知到当时正在生长的某样东西经过时间的孵化就快要成形,再过不了多久就可以被用来填补他心中的那个空缺。
那时出现在他心中的那个模糊轮廓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女老师、苹果皮、隧道、火焰、柳树、灰尘、月光……变成了一幅幅鲜明的画面。每个主体各为一张画面,各自占据着在画面中她们想要的位置,当她们排列在一起,一齐出现时,她们互相交织着讲述相同的故事——一个只有王福来能一目了然的故事。
周六一早,王福来就去了家附近的数码城,他在那儿买了一台相机。周六周日都是大晴天,所以从视觉上来说,除了在晚上拍摄的照片,其他的时候,王福来并没有捕捉到任何氛围昏暗、阴郁的照片。从周六到周日,从清晨到深夜,王福来徘徊在那几个特定的地点,尝试在不同的光线下,变换拍摄的角度和姿势。他并不想要一比一地完美再现,他只是想要寻找一个角度,能与他内心的画面产生共振,让在他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就能确信:这是曾经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画面。
周一凌晨,王福来坐在柳树间的台阶上,缓缓地躺下,以仰视的视角拍下了摆动的柳树枝条,作为他想讲述的故事中的最后一张照片。他把相机放在一边,躺在地上睡着了。当刺眼的太阳光把王福来从睡梦中晃醒时,刚好是早上十点。他向公司请了假,回家继续睡觉。睡醒了后,他就起床开始挑选照片。
拍完照片后,可以在相机里查看回放,但是他没有看。一是因为他担心若是自己看了回放后没有勇气继续拍下去;二是因为只有当所有照片都拍完了之后,故事才是完整的。他忐忑地期待着查看最终成果的时刻。
照片呈现出来的效果出乎他的意料。
他的眼前仿佛被电子显示屏氤氲了一场梦境,曾经与他密不可分的悲伤、痛苦、迷茫、释怀、逃避、面对,都游移在这场梦境中,不再完全属于他了。他是这组照片的亲历者,也是照片背后故事的亲历者,可当它们真的以这种形式呈现在他眼前时,王福来又与它们产生了全新的、内在的关联。它们给他带来了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
他一张一张地划过这些照片,内心激动不已。拍摄这些照片本来是出于说不清的本能,可王福来却觉得自己误打误撞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他甚至觉得,六年前到现在的所有事件,都是为了唤醒他身体中潜在的艺术天赋。
他从拍摄的642张照片中选择了16张,并把这16张照片作为一个系列,投给了一个还在时效期内的全国摄影比赛。在投稿截止之后,还要耗时四个月进行评选。不过仅仅在两周后,王福来的生活就又复归于平淡。之前出现的艺术激情一下子没了影踪,但也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变成了一簇小火苗,在他心中忽明忽暗地闪烁着。五个月后,他的作品被评为大赛一等奖,他心中的小火苗才重新燃起熊熊烈火。
一等奖除了有奖金之外,得奖者的作品還可以在本地的美术馆里展出。当王福来和主办方还有策展人见面时,他们都称他为“王老师”,把他的照片叫作“作品”。当他们从专业的角度解读王福来的“作品”时,王福来恍惚觉得自己在看一出无声的独角戏。
那天晚上回到家时,他生出了一份责任感。这份责任感不是奖项所带来的荣誉赋予他的,而是他赋予他自己的,为了即将要看到他照片的那些人。他想弄明白摄影到底是什么,或者对他来说摄影将会是什么。
审美是主观且难以统一的,所以他果断放弃从这个角度切入进行思考。他坐在电子显示屏前,重新翻看自己拍摄的照片,除了它们在现实世界中重现了王福来抽象又不着边际的所想之外,王福来自己也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否还有其他含义。相机与现实之间有着秘密的暗号,电子显示屏与图像之间也被加密的信息间隔开,而王福来被横亘于这层层幻象所构筑的现实之外。他本能地闭上了眼睛,黑暗、色块、光斑、颗粒,在他闭上眼的这个无垠空间里自由地流动着。在它们的流动中,王福来眼中关于摄影的真相被牵动出来:他利用相机说出了他原本永远不敢主动面对、用于讳莫如深、远超于他想象之外的内心故事。他被赋予了一种积极的冲动,他被引领着去直视。
尽管没有任何布展经验,但王福来还是坚决拒绝了策展方提出的陈列建议。他选择将照片打印成同一大小,装裱在黑色的相框中,在洁白的墙面上一字排开,他认为最简单的就是最有力的,这样一来,没有其他形式或排列方式的结构、顺序可以将人们对这组照片的解读从照片本身和它们作为整体的本身移开。
当他观察陌生人观看他照片时的反应时,他觉得很神奇,特别是以下的神情:痴迷、严肃、迷惑、恍然大悟、震撼和沉默。他们从我的照片中看到了什么呢?通过我的照片,他们又联想到了什么呢?王福来着迷于这些没有答案的提问,也着迷于这种通过照片与陌生人相互联结的方式。在作品展出的两个星期中,王福来每天都会在自己的照片周围徘徊,悄悄地观察人们的反 应。在展览结束后,他盯着空荡荡的墙面,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是想从我的故事中找到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找寻一种共鸣。
更多的人通过这次展览认识了王福来。他的照片受到了一致好评,他也收到邀约帮一些小有名气的主持人、作家、企业家等拍摄肖像。他们评价王福来拍摄的人像:“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具有故事性。”
王福来辞去了公司的工作,当起了全职摄影师。比之前的工作累了些,收入比之前可观多了。他的日子就在忙碌的拍摄日程中度过,可生活越充实,他的内心就越空虚。他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分裂感:这一切都来得太快,毫无兆头且过于顺遂,与他一开始只凭内心驱使而拿起相机的冲动截然不同。
他拍过的人越来越多,他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仔细观察这些人,以一种接纳、具有包容性的目光去理解他们。他以为这样就能更加接近他们的内心,拍出更有深度的照片,却无奈发现他与他们之间永远隔着一层不厚不薄的玻璃屏障。
那天拍摄结束后,即使他脖子僵直、腰酸背痛、腿脚绵软无力,但他的心灵却仍旧比他的身体要疲惫好几倍。他一时失神将相机摔落在地上,相机又狠狠地撞上了街边的路灯。晦暗、昏黄的路灯下,相机与镜头的连接处被摔出了一处裂缝。
而我正是趁着这个时候,偷偷地从那个细缝中潜入王福来的相机中。
我很痛苦,却又很激动。
我陷入了一个不健康、不正当的恶性循环中,这是我十分痛苦,身体上及心理上。可同时只有在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下,我才能得以窥探我内心无数零星想法的苗头。而这些一直被忽视的,随时会被遗忘的想法可能比我在清醒状态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实。
我试图找到一种极限:可以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这种状态,并且我的社交生活也能正常延续,而我的家人、朋友也不必为我担忧的一种平衡的极限。
我试图想象这种平衡的极限,随之想起了我在呼啸而来的寒风中行走的感觉。当时的温度已是零下,我穿了一件单薄的长袖套头衫、一件同样单薄的秋装外套和一条轻便透风的运动裤。风从我身上衣物的每一个缝隙中灌入,我感觉手指被冻僵,失去了知觉。腿上的运动裤像我的另一层皮肤一样即将被剥离开来。我也马上就要在风的驱使下走到路边肮脏的水坑了。
于是我索性闭上眼睛,也不管下一秒,身体的某个部分会被风交付到哪里。我决定先完全信任它,等到时真的磕碰到哪里的时候,再大声地对它吼骂两句。
可它把我带到了天空。它散发出了神奇的气流,使地底肿胀的重力变得稀疏。我变得和空气一样来去无形,漫无目的。我不再吸入尘土和空气,而是承载着它们,和风一起将它们从这儿转移到那儿。而一些极其幸运的颗粒得以加入我们。我们可以瞬间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我们在浪花溅起的水地上得到净化,然后我们净化跟随着我们一同前来的少数尘土。当这个过程完成后,它们将完全成为我们,拥有我们的模样和净化能力。
瞬间之后,我回过神来,再次回到了地面上,面前是路灯,脚下不远处是水坑。那空中“腾空”的时间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时间。而我那“不正常”的状态,则最接近于我“腾空”的状态。
我再次感觉到寒冷,并生出自主且强烈的意愿:我想要陷入幻觉循环。我渴望无节制的精神自由发展。
我感到来自生物本能的劣根性正在掏空我,它不允许我拥有任何的思想。要想远离它,首先一定要认识到它的可恶与可憎,它对我外部躯体的摧残以及对我内部精神进化的阻碍。我到底想放弃些什么,又想从中获得些什么,一下子变得十分清晰:我需要一具全新的躯体作为开始。王福来的相机此时恰巧掉落在我眼前,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决定寄身于这台相机中。
进入相机之后,我的日子不再以“早晨”“中午”“下午”“晚上”“黄昏”“清晨”这种暧昧的时刻来区分,而是处于一种“非黑即白”的鲜明差异中。但这并不代表除了这两者之外的东西就不存在了。
透过眼前的小孔,我亲眼看到外面的世界,被这种自然之美所震撼。没过多久,那个小孔就惊恐地合上,裹挟着外部纯洁的白色,进入到我置身的这片黑暗之中。一片混沌的黑色由此而生。外面活生生的事物,被这团灰色结构成单薄的概念,它们的灵魂已经不知所终,无念无想地飘浮在相机内部。
它们没有游荡多久,就受到内部空间的召唤。根据感光元件的记忆,它们被有序地排列、拼凑成与之前一样的視觉秩序,不过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严谨的、数字化的形式。摄影师面前的屏幕亮了起来,而我所处的地方变回漆黑一片。按下快门只是眨眼间的事情,可在这眨眼间一切都被改变了。大海的蓝色与照片的蓝色也许无限接近,但永远不是同一样东西。但我并不觉得相机比王福来强大,相机只是更善于无声无息地捕捉、潜入别人的思绪,并进行操纵。
我想做些什么,却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相机中的寄居者,我的声音无法被相机听到也无法被王福来听到。
王福来回到了当初的柳树下。我感受到了他的迷茫与思索,我将这看作是他觉醒的前兆,并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我的开心还没持续一会儿,我就又从王福来的脑海中感受到了令人恐慌的空白。王福来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平静地坐在柳树下了。他对心中悬而未决的这个问题感到不耐烦,于是干脆不想了。以后再想吧,拍着拍着就会明白的,他这样告诉自己。
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以为是根据自己意愿所拍摄的照片,不过是相机这个不透明精密机器内部操纵他去拍的照片罢了。他的选择是一种被支配的选择,他的自由是一种可操纵的自由。人们都想以影像的方式留下自己记忆的证明,而王福来只是在顺从地生产相机的记忆。
王福来躺在床上,在社交软件上查看自己发布的照片以及网友的评论。当他感受到他的眼睛随着手指的上下滑动而产生的干涩时,头晕、乏力等都会接踵而至,放下手机瘫倒在床上,整个人像被束缚在潮湿、黑暗的密闭感里。蓬松、柔软、草地、户外、阳光、空气都被机械化地揉碎放进那块由他的意志支配光亮的屏幕。他本可以像最初那样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眼睛,现在却受制于自己。眼睛本该是包罗万象、最自由自在、最清澈也最轻盈的,如今却因为看多了过剩的东西而变得过剩。
第二天早上,王福来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走在街上,昨晚的发现又再次困扰着他,这种重压都已经蔓延到了他的脚底。他心情低落,觉得自己是一只孤零零地暴露在破洞袜子外的脚趾。他悲伤的原因虽然难以理解,但是让人不得不心生同情。
清洁工枯黄瘦小的身体完全消失在垃圾车后,远远看去,在没有一片落叶的街道上,垃圾车正在悠闲地散步。王福来与垃圾车擦身而过,就连这短暂的一瞬间,他都在皱眉苦恼着:最近的一切都太顺利了,连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都成了真。这一切是真实的吗?是不是马上就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是不是应该放慢节奏,精进自己的技艺,而不是急于求成?
他越想越觉得不安,不过最后这种不安变成了一种不满,他又从这种不满中滋生出了对自己的肯定情绪。他想:我为什么要质疑自己的成功呢?这难道不是对我之前所经历的磨砺的奖励吗?
随即,他仰起了头,眉头也舒展开了。尽管马上就要三十岁了,但他走起路来还是和小时候一样一摇一摆的。他身子一开始晃动,被他斜挎在背上的相机也跟着一起晃动,沾染上他喜气洋洋的神色,准备好再次和他一起开始忙碌的一天。
我在晃荡的机身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或许他应该和我一起住到这个黑匣子里来。
责编:周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