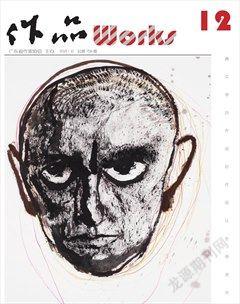紧箍咒(短篇小说)
丰一畛
见了面,一时却无话说了。蔡小希抿着杯子里的果汁,对这必然要到来的沉默报以微笑。我却没那么安之若素,看她的目光有点飘,总想着没话找话。微信聊天里,可不是这样。起话头的通常是她,还总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说说话。我有些恍惚,想掏出手机确认下,但这样一点也不礼貌。我试着凝神静气,越过她,往尽量偏尽量远的地方瞟。角落里有个女孩,背对着,我把眼光聚过去,想看看她的马尾辫是不是在轻轻摇晃。这有点难。我也是三十岁的人了,这是怎么了,心还跳得厉害了。我按捺着呼吸,故意看一眼蔡小希。
上次,我认错人了。我还是说话了,仿佛某种束手就擒。
蔡小希收紧微笑,望着我。
那天,那边藤椅上坐着个姑娘,我昂昂头,示意蔡小希大体位置。她也侧身往马尾辫姑娘那儿瞟。进了咖啡店,只那个姑娘是落单的。她正小声嘟囔着什么。我凑近点,问她是不是你。她将头发往耳后撩撩,背对着我,回答不是,接着又嘟囔起来。我退后两步,眼盯着她戴上了耳机。我当时有种冲动,想绕过桌子瞧瞧她的模样,然后反问她,默记不更好吗?
抱歉,那天放你鸽子了。蔡小希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到了,就这么一说。
那天想送你件礼物,一本诗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突然就不好了。我跟你说过了。
真不是这个意思,那天我也迟到了。不,我是想说,你也应该像那个默记的姑娘,别去读诗,多背点实用的书。我想开个玩笑,但自己都觉得,好像有点冷。
蔡小希却笑了,扑哧一下,专门配合似的。你怎么知道,她说,那个姑娘读的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正想说那可够洋气的,她欸了声,那你到底冲动了没?
嗯……我拉长了音。她是不是长得可洋气了?蔡小希用了我的口头禅。我逮着了机会似的,肆无忌惮瞪着她,假装哭笑不得。微信聊天里,她跟我分享阅读经验,里尔克、阿米亥、波拉尼奥、安妮·普鲁,我一个也没读过,就说太洋气了。她说有种面包叫布雷欧,我没听说过,也说好洋气。她听出了口头禅里没有恶意的那种淡淡的嘲讽,回击我,你好淳朴,以后就叫你老土了。
我确实土。但她也确实误会了。
上海交大组织了个短诗大赛,针对大学生的,声势浩大。我刷微博,被那句宣传语——人生总要写首像样的诗触动,又看到参赛须知里说,在读博士也能参加,就翻出了以前为哄女朋友高兴乱编的短句子,稍作整理,临时以微博名字为笔名,再挂上学校的名字,发了过去。没承想,入围了,进了复赛,还得了个优秀奖。某一天,学校官微@我,推送了诗作。我并没回应,不久便收到了条私信,是你吗?我是小编,加个微信?
就认识了蔡小希。她微博和微信同一个名字,都叫——在苹果里面。她说她是官微的小编。以前的,现在已经不是了。她补充说。
萍水相逢,以为只会寒暄几句,结果却聊起来了。这段时间,我过得挺糟糕。其实,自从来G城读博,我一直过得挺糟糕。蔡小希误会了,因为一首诗,在我身上附着了另外的想象。我没想到,可能她也没想到。我承认,后来我意识到了,也在用一句口头禅一再暗示与调侃,但心里是欢喜的。我说了我过得不好,乐得跟一个陌生人聊天,就当调剂了。这心思挺坏。或许,想象是聊天的过程中附着的。这样说,好像我有什么魅力似的。不是那个意思。我以前也算个半吊子的文艺青年吧,外国作家没读几个,国内作家的作品倒是翻了不少,我是说,得亏有点储备,要不然,蔡小希的话,还真不好接。
蔡小希有双深邃的大眼睛,我只好又往不相干的地方摆弄目光。咖啡店里人不多,音乐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钢琴曲类似变幻的云朵,托举着人们同样流动不居的心思。角落里的马尾辫姑娘好像不见了,我突然想,她会不会也喜欢默记呢?她会不会就是那天那个姑娘?那天下午,确定蔡小希还没到,我要了杯东西,独自坐了会儿。那个戴上了耳机的姑娘始终对着墙,没转过脸来。喝光了咖啡,望着窗外,我意识到蔡小希不会来了。窗外有个拉二胡的,还有个磕头乞讨的。我出来吃饭,经常遇见他们。他们脚前躺着的纸盒子里都有几张纸币,不知是提前放的,还是真有路人愿意行善积德。我从没往里面丢过钱,但那天,从咖啡店出来,我把服务员找的零钱分开,放进去了一份,走几步,又放进去一份。我想,他们起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蔡小希在看我。我的余光能感受得到。她总时不时地这么看我。我有个同门,小眼睛,一个人在寝室,多晦涩的书,都要读出声。我说。我说得有点含混,甚至因专注而显得心不在焉。她眨了眼。
我不好看吗?蔡小希没接我的话茬,怎么总是左顾右盼,不看我?她像是回到了微信里,变客为主了。
这让我怎么回答?……那是首情詩。我答非所问。
算了。她说,你喝干姜水了吗?
这会儿,我敢看她了。她的脸、脖颈、脖颈上蓝莹莹的吊坠,我没办法形容,有一瞬间,我很想哭。喝了吗?她又问。这是微信里的话题。在那个关于“我是不是有点不对劲”的冗长的词不达意的话题之后,她说,干姜水。我说,干姜水咋了?她说,没咋,干姜水挺好喝的,如果你去餐厅尽量点干姜水。她接着发了好多条,有些进口的特别好喝,然后加两片柠檬,比起一般气泡水什么的好喝多了,那个汽水其实不是生姜的味道,总觉得喝起来是一种甜滋滋的清爽的味儿,一回忆起来很令人开心的那种。
我们现在去买,好吗?我说。
好。蔡小希说。
我从塑料袋里取出一瓶干姜水,启开盖,喂给蔡小希一口,我喝一口。看见了吗,她说,前台那儿有个孩子也喜欢嘟囔着读书?她该是给我们办理入住手续的女服务员的孩子吧?我说没注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要跟一个迷人的姑娘开房了,哪还有那心思。
我迷人吗?蔡小希撒娇。迷死人。我说,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姑娘。我是怎样的姑娘?她噘着嘴,要再喝一口干姜水。丰富,深刻,敏感,专注,美。我一面说,一面伸过头去,要吻她。等等好吗?她说,我们把汽水喝完。好。我说。我安静地坐着,内心里充满了欲望,仿佛那欲望是干净的一样,我居然特别踏实。顺着她的话,我想起了曾经那个断了的话头。我说,我同门,眼睛成天眯着,是个学霸,也喜欢哼唧哼唧地看书。是吗?蔡小希附和。他长得有特色,两颗大门牙间缝隙宽阔,下嘴唇外翻得厉害,平常不笑的时候,很像瘪着嘴在哭。蔡小希摸出了手机。我往她那儿凑凑,牵住了她的另一只手。我读博才来这里,不认识人,差不多只跟他有点来往,他本硕博都在这儿读,信息多些。
是他吗,杨明峰?蔡小希举着手机。是的,我诧异,你认识?那你的导师姓卞?蔡小希追问。我点点头,好奇地盯着她。她身体不自觉一抖,愣怔了片刻,说,你知道,我以前是学校新媒体中心的记者,采访过他们。你的导师还给我们开过选修课,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你的这个同门在上。她拿过我手里攥着的干姜水瓶,几乎是夺,咕咚了一大口。我也喝了一大口,瓶子还在她手里,我捏住瓶底,直接灌的。
她扔了瓶子,我们拥抱了。我吻她的额头、鼻尖、嘴唇,头蹭着她的脸,亲她的耳垂。她一下子推开了我,抱歉,她说,我去趟卫生间。
我有点发痴,喘着粗气,咽唾沫。一会儿,她出来了,脸泛红,也喘着粗气。没事了。她说。我试探着抱她。她回应了,甚是决绝。我擎着她的脸颊,唇对上了她的唇。我吻她的下巴,接着一路向下,低着头,噙住了那颗神秘的吊坠。
她又推开了我,特别用力,我还没来得及恼怒,她跑进卫生间,反锁上了门。水龙头也打开了。我感觉到了冷,一绺一绺的,还有怕,也是一绺一绺的。我转着脑袋,东张西望,被陌生的环境钳住了呼吸。这不是个梦吧?我鬼鬼祟祟走到卫生间的门前,敲了两下。抱歉,我说,你知道的,那是首情诗。里面没动静,我不敢敲了,干巴巴站着。都是我不好。我说,我不该这样。
别说了,蔡小希的声音温暾着,把我的包递过来吧。她关掉了水龙头,门也打开了。接包的时候,囔囔地自语,我把那首诗背下来了。她没再关门,对着镜子补了妆,走出卫生间,看着木呆的我问,好看吗?我机械地点头。她开始脱衣服,T恤,牛仔裤,胸罩,小裤,袜子也脱掉了,她的胴体矗立在我面前,犹如一尊神。我们一块背你写的那首诗吧?她莞尔一笑,嘴唇翕动起来:
在骨头的深处,我刻录过
这样的雨夜,现在,疤已经好了
当然,疤本身就意味着好起来了
我没有抽烟,不是因为
你说烟味难闻,是烟没了
我内心平静,或许这要归功于白天的自慰
我说了,我想邀你,重回子宫
或并排躺进棺材
你可以咬我
我可以叫
钉子可以楔进骨头
雨夜可以覆盖雨夜
疤上可以裂开口子
灵魂上可以长出新疤
她的泪在眼眶里打转。纸巾。她朝床头伸手。我赶紧抽了张给她。她揩去泪痕。妆花了就不好看了。她说,你这首诗太深情了,要是写给我的就好了。
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没事,都是我不好,是我的错。她主动抱了我,手在我身上摩挲。我挣脱。她抓住我的胳膊,恶狠狠咬下去。我忍着,没有叫。她松了口,拽着我胳膊蹲下来,她好像比我还疼。
他摸我,摸我耳朵。她的话异常清晰。
还摸我屁股。
谁?
还想摸我的吊坠。
谁?
你的那个导师,姓卞的。
她哽咽了。
我搂住她。冷吗?我呢喃着问。她不回答,缩起身子。我抱住她,起身将她抱到了床上。我也脱光了,钻进被子里,搂紧了她。她就像个静物,沉到伤痛深处,躺进棺材,或重回子宫。
老土。她叫我了。小洋。我回道。她蹬开被子,换了个人似的,跳起来,又蹦下了床。我给你讲讲吧。我真傻,真的,我被性骚扰了。我都不知道这就是性骚扰。不止一次。我不记得几次。我没反抗,我一次也没反抗。我千百次地問自己,为什么没反抗?
蔡小希赤裸着身体,走来走去。窗外雾气弥漫,我拉上了窗帘,揿住床头灯的按钮。光晕闪了下,又灭了。她说,你坐着,好好坐着。房间里雾蒙蒙的,仿佛雾蒙蒙的。就像担心光晕永远都不会弹出来,我颓丧得没再开灯,挪到床边,坐好了。
杨明峰开的门。之前也是他找的我。他让我进来坐,先等等。门虚掩着。办公室里有个隔间,他回身进去了。我犹豫,是在门内还是门外等。我在这种犹豫里站着。脚下的地板裂了条纹儿,特别像我右手上的一条掌纹。我打量了很久。门外光线不好,是个下午吧?不对,是傍晚。操,我竟然记不清了。那些事件的片段和背景总在自行组接。
你在听吗?她胳膊勒紧胸,环抱着自己,突然问。
在听。我说。
我把手机放包里,腿都站麻了。我走进去,坐在了门边的沙发上。还是觉得在门外站着更合适,可站在门外读书就太傻了。幸亏带了本书。我没多想。他既是行政领导,又是学术大咖,临时有更重要的事处理,情有可原。隔间里传出说话声,时高时低。我坐得特别靠近门边,像是随时要走。为了避免成为一个窃听者,我在心里幻化了个隔离罩,书读得全神贯注。
我想送你本诗集,找不到了。她的思路切换得迅速,我完全蒙了。
书是不是落在那儿了?她俨然舞台上的演员,兜着圈子自问,要不,怎么会找不见呢?她目光如炬,像被某种真相点燃了。
就跟丢了什么似的。
她念叨着这句,眨下眼,终于不再说话了。
上了91路公交车,五个站下来,是学校的另一个校区。蔡小希换了身打扮,不仔细看不出来,还是T恤配牛仔裤。杨明峰那儿有逸夫楼501室的备用钥匙。我直接去借了,说要找本书。我当然没说谎。他舌头舔舔下嘴唇,从一串里取下一把,递给我时,满脸狐疑。还好,卞老师那间旧办公室里,的确摆着个书架,书架上也的确躺着几本书。
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我们走得蹑手蹑脚。钥匙进了锁孔,逆时针旋转,咔嚓,再咔嚓,门开了。这次不用再想那个高难度的问题了,蔡小希义无反顾迈过门槛,飞蛾扑火一般。我跟进去,反锁了门。
是这里吗?蔡小希也狐疑起来。格局好像变了。她的记忆里,隔间在办公桌的后面。这间办公室,隔间在办公桌一侧。她推开门,又站到门口。是这里。她摊平右手手掌,眼光移向地面,像打了个卦。
反锁了门,我们对视了好一会儿,灵魂出窍,不认识了似的。我先瞥向沙发。她也瞥沙发了。房间里雾蒙蒙的,仿佛雾蒙蒙的。找吧。我说。她直接行动了。沙发,办公桌,办公桌的每一个抽屉,都找遍了。我们进到隔间,沙发,藤椅,茶几,书柜,书柜里的每一本书,我们都翻遍了。没有那本诗集。
我们坐回门口的那张沙发,面面相觑。真丢了?我问。是。她的目光决绝地挪到我眼里,回得果断。真丢这了?我再问。我记得清楚,她说。我就这样坐着,诗集搁在膝盖上。她表演起来。不会错的。她说,我太投入了,杨明峰什么时候走的,他什么时候过来的,我都没察觉。他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靠着我。他捏起我的手,斜着身,嘴唇蹭着我耳根。我听见了粗重的呼吸声。蔡小希一哆嗦,癫痫了似的双手在空中乱比画。我不记得了,她说,我不记得我怎么跳开了,怎么瞠目结舌。我恨死自己了。
他说了话。他说,抱歉,我有个女儿,和你差不多年纪,在美国留学,你们长得有点像,我想她了。他把我带到了隔间。我们也去隔间吧?她没等我反应,拉起我的手,往右走。隔间里陈列着几张单人沙发,我们坐下。我承认,蔡小希说,他学识渊博,工作的时候专注,甚至,散发着某种迷人的气质。他找出了我的课程作业,讲解循循善诱,点评鞭辟入里。我是采写组成员,他还谈了对采访稿的看法,挺独到。我想起了《论语》里的话: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后来,我脑子空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好像都是对的。他要抱我,还要抱起来掂一掂。他说一年没见女儿了,我俩的身材挺像,他要感受一下女儿是不是变胖了。蔡小希站起来示范。我被他托着,往空中一甩,吊坠脱离了皮肤,飞起来,操,他衔住了。
我一阵恶心,止不住的恶心。那本书呢?我打断了蔡小希,听不下去了。是啊,那本书呢?蔡小希也跟着问,连着眨了两下眼。她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匪夷所思了。是不是另外一次,那次是在他的车上,我也带着一本书的?我有随身带一本诗集的习惯。是不是落在他的车上了?一定是落在他的车上了。我再跟你讲讲吧。车上空间窄……我们该走了。我咬着牙,再次打断她,这里是他的办公室,我们还是走吧。蔡小希过来抱了抱我,说,老土,你最好了,我爱上你了,你听我讲讲好不好?求求你了,先听我讲讲好不好?
蔡小希又滔滔不绝讲起来,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奇怪了,她越说,我浑身越疼,像唐僧对着孙猴子念起了紧箍咒。她还犯了考据癖,有些场景反复讲,颠三倒四地讲。我感觉在她喋喋不休的讲述中,我身上长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疤,疤上裂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口子,类似荼蘼的花,一朵朵,一瓣瓣,粘粘滞滞,生生不息。我想逃,我想炸开,我想杀了我自己,可我动不了。我的意志和行动割裂了,反目成仇。她太投入了,投入得一点都不真实。我眼睁睁看着她,她不再像一尊神,越看越像一个鬼。
有没有水?她一个人出了隔间,又回来。饮水机里空了,她说,我说到哪儿了?
你别讲了好不好?我说,求求你,你嗓子都哑了,让我也讲讲。我没得到她的允许,也不准备得到她的允许。我抓住了这次见缝插针的机会。
我进了办公室,不是这间,研究所的那间。那是第一次见面。我当时报考的不是他,是个女的。来了才知道是陪考的。那女的根本没打算招我。但就这么阴差阳错,我被补录了,还跟了更牛的他。当时觉得天上掉了个馅饼。办公桌边角上摞着几张纸,他没寒暄,示意我过去。有个事,你做了。他说,要求都在上面。我拿起纸,人僵着,不知道该认真看下去还是直接塞背包里,仿佛时间琥珀里一只被定格的虫子。我张着嘴,说不出话。我甚至忘了自己是不是想说话。没事可以走了。他又说了,头都没抬。这是第一个活儿,四万字,期限两个月。
这个隔间里,他半躺在藤椅里,脱了鞋,小腿搭在茶几上。你现在就是他,我给你演演吧。我给你揉揉肩、捶捶背、捏捏腿。我蹲到蔡小希旁邊。我没办法。我们都没办法。学术研究圈子化太重,论文只有给他才能发出来。他不仅能决定发谁的烂稿,还能左右你绕过他投的好稿能否刊用。我说了,我以为捡到了个馅饼。原罪就在这里。他每每念我发给他的短信:您拍板要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学生,这生命拐点上的提携再怎么言谢都不足为过。他把道德这种东西制作成了精致的笼头。我说不出话,从始至终说不出话。我按着蔡小希的脚,头趴过去,哧哼着鼻子嗅。她狠狠踹了我一脚。你疯了吗?别再讲了,你他妈的别再讲了。她吼我。
求求你了。我说。
求求你了。她说。
求求你,再让我讲吧。我说。
求求你,再让我讲吧。她说。
我们又对视了一会儿,好像同时意识到了那种曼妙的疼痛的无所不在。我们好像在往风暴的中心走,家就要到了。
蔡小希扇了我一耳光。
我摸摸火辣辣的脸,反手也给了她一耳光。
我们能说出来吗?蔡小希问。我们不是一直在说吗?我说。我是说,除了这样相互说,我们还能说给别人听吗?我们要说给别人听吗?我反问。操,蔡小希说,你是个男人吗?我避开这句挑衅的话,踱步到外间,饮水机的确空了。
你他妈的该做点什么,不能这样。等我回来,蔡小希歇斯底里地咆哮,我们该做点什么。我要告诉姓卞的,我的诗集丢了。那是本阿米亥的诗集。真的,我太傻了,我当时怎么没录音呢?她的声音低沉下来。我抱住了她。我们总归要做点什么吧,不说明天、以后,就现在、此刻、马上。我抱紧了她。老土,我们做爱吧。她的声音又高了。
她开始脱衣服,T恤,牛仔裤,胸罩,小裤,袜子也脱掉了。她蹬掉我的鞋,开始帮我脱衣服,T恤,牛仔裤,小裤,袜子也脱掉了。
我们看着彼此。蔡小希问,你有女朋友,我是不是贱?不是。我说。我是不是贱,他才骚扰我?不是。我说。我脏了吗?身上有一股味儿吗?我没说话。你骂我!快点骂我!蔡小希被附体了似的陡然甩起我的手臂,他那样对我,我恨里居然还藏了别的东西,是欣赏吗?是渴求吗?是爱吗?操,那不会是快感吧?
那不会是快感吧?我也惊恐地发现了我的什么。
蔡小希的眼睛汪汪如水、笑意盈盈,我们张开了嘴,像在读一首美妙的诗。
詈骂声回荡之中,敲门声降临之前,我们做爱了,在那张藤椅上。不是性骚扰,我被诱奸了。蔡小希自顾自说着话,话里没了连贯性。我没听,沉浸在某种感觉里,那感觉太好了。等我回过神,吱嘎吱嘎的摇晃中,蔡小希已泪如泉涌。她背起了诗,那本丢了的诗集里她最喜欢的一首诗,就仿佛背诗,而不是做爱,才能带来快感:
你来看苹果里面的我。
我们一起听见刀子
在我们外面一圈圈地削皮,小心翼翼,
以免皮被削断。
你跟我说话。我信任你的声音
因为里面有一块块坚硬的痛苦
就像从蜂巢中取出的
醇正蜂蜜里,也有着一块块蜂蜡。
我用手指碰了碰你的唇:
这是一个先知的手势。
你的唇是红的,就像一片被烧过的田野
是黑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
你来看苹果里面的我
你跟我一起待在苹果里
直到刀子把苹果皮削完。
电话响了,我看了眼,没接,索性静了音。谁呀?杨明峰问。女朋友。那你接吧,都响三次了?没事,我说。确定?我没回答,他明明不想让我接。
他不追问了,眺着窗外的夜。
我也不想再说了,我们是不是朋友,在什么层面上是朋友,都只是种说法而已。窗外下着雨,很细很细的那种,也许已经停了。
你听说了吗,良久,他吧唧了下嘴,瓮声瓮气地说,学校里有个女孩跳楼了?就是前两天下午,消息封锁得死,我也才听说。
他没收回视线,眼神直直的,我还认识她。
是吗?我有些魂不守舍。
那天,有人说,她在校门口的咖啡店里坐了一上午,就是从我窗前隐约能窥到的那家,还跟另一个女孩吵了一架。
因为这个?我问。
不会吧,怎么可能仅仅因为这个。停了一会,他又改口说,不过,也无非那么点事,情感呀,学业呀。
我晃了晃啤酒罐。他才意识到了似的,举起啤酒罐子,嘴上说着感谢,跟我碰了下。他叫我来的,叫我过来坐会儿。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有点怕,怕自己会出什么事。他摘下眼镜,揉揉眼,又戴上。他的眼眶已经内陷了,眼球突出。我总想走到窗前,自觉不自觉往下看,关了窗想开,开了窗想关。走火入魔一般。他说,你也许说得对,我们不算朋友,只是身处同一片阴影,抱团取暖而已。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你也别想太多了。他喝了口啤酒,嘴角残留着气泡,舌尖舔了舔。我以前总劝你,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忍忍,熬一熬就过去了。我现在不这样想了。你真要去考那个文学编辑的岗儿?
票订了。我说。我本来内心里是确定无疑的,他这么硬戳戳一问,我又有点心虚了。如果你退学了,说不定我也退,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相近的专业再考,实话说,我已经在联系导师了。他起身抱起桌子上厚厚一摞书走到窗前,摇摇头,又抱回来了。别这样。我说,你比我好混,卞老师离不开你。杨明峰不说话,看着桌子上的书,又看书柜。你也读诗?我问。那摞书里好像有本诗集。图书馆借的,还没来得及翻。他揪揪嘴唇,冷冰冰笑了声。知道吗,你来之前,卞老师来这间寝室了,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我身体一激灵,抬起屁股,又缓缓坐下。杨明峰走到床边,我就这样坐着,他说,我们面对面,谁也没看谁。他竟然流泪了,像个娘们一样哭哭啼啼。无非还是课题的事,八十万字没那么好凑。我知道是出苦肉计,专门演给我看的。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本是他惯用的伎俩。可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当场就答应了。那么多年,他把我完全摸透了,像猫在戏弄老鼠。我盯着杨明峰门牙间若隐若现的肿胀,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卞老师怎么会哭呢?
白天,有时候看书看不进去,我站在窗前,往咖啡店那儿俯瞰,忍不住想,我连那个拉二胡的都不如,我就是那个断了条腿穿得脏兮兮跪人行道边上不停磕头的……你在听吗?杨明峰开了罐啤酒给我。我眨了下眼,对,我感觉我眨了下眼,端起酒罐子,一饮而尽。你怎么了?杨明峰问。没事,我说,你继续。
如果你退学,去写诗写小说,我也退。说不定还能送你个礼物,到那时,我们就是朋友了。记得衣俊卿事件出来的时候,你找不到常艳写的那本所谓小说的资源,我下载传给了你。《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讲的是一个官学一身的大牛怎么被一个神经质女博士拉下马的故事。可那些官学一身的大牛又是怎么上马的,是不是也能写本文学书?
是。我头一磕,迷迷糊糊应道。我感觉我好像醉了。他知道我不能喝酒。我说了不喝的。他非说买都买了。到时候,我把素材当礼物送你。好。我囫囵着,扶着铁架子床挪动步子。你没事吧,脸煞白,几罐啤酒不至于吧?我手脚冰凉,浑身冒着虚汗,顾不上说话了。
终于蹒跚地进了卫生间,插上门梢,一屁股跌坐地上。那种想吐的感觉太汹涌了,全世界只剩下一个马桶的洞。谁在外面敲门?這是哪里的门?谁在小声读书,默记不更好吗?手机亮了下。一个电话进来。一直有电话进来,操,已经三十七个未接来电了。
可我像被箍住了,闭上眼,一个女孩正坐我对面,她微笑着,抿着杯子里的果汁。我这是怎么了,不至于这么无所适从的。
偏偏这会儿,咖啡店里,似乎没人说一句话。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