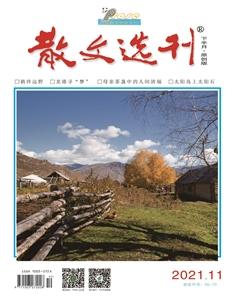那个秋天
王宁子
那个秋天,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家家户户在苞谷地里套种了各种豆类。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每一寸都是希望。眼瞅着到了收秋的季节,雨却好像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抽噎起来没完没了。
雨渐渐小了,男人坐不住了,挽起裤腿就出了门。隔着窗户,女人看着男人的背影,赶紧溜下炕,抓起草帽走了几步,又转过身一把拽过挂在门闩上的化肥袋,边喊边追了出去。男人站在泥水中一脸不耐烦,又没下雨!女人站在门楼下嗔怪,马上掰苞谷了,千万不能淋雨!对门正在疏通水道的四嫂听了哈哈大笑,不会骚情胡情,不会睡觉胡蹬!女人被说得羞红了脸,瞥见她家男人也出了门,好像逮住把柄一样反击道,我四哥也准备下地了,你赶紧给我哥也骚情去!
早等不及的男人们扛着锄头拎着耙子一溜带串出了村,看到成片的苞谷浸泡在没踝深的雨水中,个个脸上凝重悲怆。
额滴爷呀!这还让人活不活!连日见不到太阳,苞谷叶已经发霉,各种豆蔓缠绕在苞谷秆上,因不堪重负,苞谷秆弯下了腰,天花处的几个豆荚,被蹦出绿芽的豆子顶得咧开了嘴。再不收,就烂到地里了!大人们愁眉苦脸,唉,这天啥时候能晴啊?
午饭时,椿树下的老碗会,因为雨天被转移到二爷家的门楼下。吃罢饭,抽一锅烟,胡吹浪谝,是老碗会的主题。庄稼人的话题离不开土地。二爷蹴在门墩边,看着一张张闷头吃饭的脸,吸了一口烟笑骂道,一个个心坏得很,以前农业社的时候,你们巴不得一年四季都下雨!这地一分,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二爷话音还没落地,男人们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干农业社,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温饱都成问题,反过来还欠生产队的,二爷,您老说句公道话,那日子过得恓惶不?
唉,要是这政策能早点来就好了!二爷长叹了一声。身为队长,那时候,除了一冬三个月,二爷每天的任务就是睁开眼去巷口的大椿树下,拽下挽在树杈上的麻绳,一边敲着铃铛一边大声喊着:“上工咧!上工咧!”铃响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出来。蹲在碾盘上抽烟锅的二爷急了,气急败坏地从巷口喊到巷尾,一个个是不是掉到茅子坑了!上工不積极,分粮的时候,个个像饿狼一样!
提起分粮食,门楼下又热闹开了。张三说,那年分苞谷,分了一夜,他拉着架子车都在打盹。王二说,那年李四婆娘为了多分二斤麦子,在地上滚得像个泥母猪。
唉,一句话,还不是穷嘛!要是家家粮满囤满,谁还争那啊!二爷说罢站起来,将烟锅别在腰带上走到门楼下,仰头望着雨天。
这雨要是继续下,咱就看着苞谷烂在地里?二爷忽然大声问。一语点醒梦中人,×他先人呢,这跟雨怄气磨自己洋工?
男人们一个个拍拍屁股,起身拿了碗筷,就都走了出去。各院开始吼起了男人的声音,娃他妈,赶紧收拾东西,咱掰苞谷去!
早都收拾好了!就等着你发话呢。女人的大嗓门立刻从窗户飞了出来。
椿树巷里呼声一片。男人们戴着草帽拉着架子车,躬身于半腿深的稀泥中,女人们披着塑料布跟在后面,支腿推着车子,娃娃们顾不得摔掉手中的“大炮”,也加入到队伍中。二婆扭着小脚急匆匆追出来,对着雨中喊着,他大,把这块油饼捎上!
哈哈哈,二伯,看额二妈多疼你!有人大笑道。
庄稼人的希望是土地,一旦涌出豪情来,摸爬滚打也在所不惜。
各家的地头,大人娃娃纷纷挽起裤腿,光着脚蹚入冰冷的雨水,掰的掰,扛的扛,水深的地方,木盆木梒派上了用场,娃娃们推着盛满苞谷的木盆木梒像一只只小船,在泥水中穿梭,一不小心,一个趔趄,就溅得一身泥。关中汉子粗犷豪迈,恨不得一次就把所有的苞谷都扛上,肩上的袋子必须装满装实在了,才对得起吃饭用的大老碗!女人们也不甘示弱,鼓足力气挎着苞谷袋,深一脚浅一脚跟在男人身后,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也只有土地,让女人们忘了自己是女人,跌倒,爬起。肩上的苞谷袋里的泥水顺着后背直到脚后跟,人人都成了泥人。
袋子满了,架子车满了,男人拉着湿漉沉重的架子车,躬身将肩上的袢绳绷得拧出水来,女人和娃娃跟在车后,埋头使劲地推着,从地头到路边,几步之遥,就像隔着一座大山。
二爷的袢绳断了,负重的架子车像一头深陷在沼泽中的老牛,纹丝不动。
他叔,别急,缓缓气,我们来了!
二爷的袢绳断了,负重的架子车像一头深陷在沼泽中的老牛,纹丝不动。他叔,别急,缓缓气,我们来了!
不知何时,西边的地平线裂开了一道口子,太阳穿过昏暗的云层,将一抹晚霞挂在天边。
哈哈,火烧云啊,老天爷终于睁眼了!
二爷开怀大笑着,余晖映红了他那古铜色的脸,像一幅兵马俑的剪影。
不知是谁吼起了秦腔,粗犷的声腔从青纱帐里冲出,穿过田间地头,震颤着天边那抹迟来的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