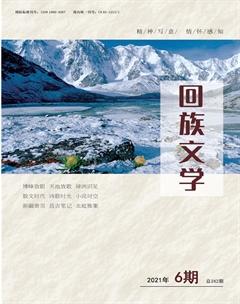刀耕火耨
刘梅花
豌 豆
山里的豌豆根本不需要搭架子,只需要种得稠一点就行。如果哪一年春种时撒种子失误,苗稀稀拉拉,那就没有办法,豌豆秧子只能匍匐在地。豌豆绝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它自己本来就是五斗豆。
高原上深山小村庄,气候寒凉,种庄稼也就几样,青稞、豌豆、土豆等。青豌豆秧子低,白豌豆秧子高,收成倒也差不多。论价钱,白豌豆贵一丢丢。这些年,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庄稼地荒废掉许多。后来陆续又有人家搬走,村庄越来越干瘪,只剩下三五户人家。
留守在家的老人苦不动,只能种半亩地,大部分旱地都扔掉。撂荒的庄稼地野草汹涌,半人高,疯疯癫癫胡长,迷了路那样乱长。弃耕还草,草还得过于丰盛。野草太多,野兔子、鹌鹑、蓝马鸡都来筑个豪华窝,快快活活过日子。然后狼也跟来,时不时吃个烧烤。有人去地里薅草,猛乍乍碰见狼,人吃了一惊,狼也吃了一惊——怎么是你?对峙几分钟,各自后退走开。生活不易,谁也别伤害谁。
老人们种庄稼,都交给天。套牛耕地,撒一把种子,耙一遍,得啦。薅草什么的,确实很难。青稞吃得少,那就种豌豆种土豆。村庄周围都是豆田,豌豆苗有一搭无一搭生长,反正也没有人管。它们柔软的秧子彼此搀扶,风一吹,推来搡去,挨挨挤挤。绊倒的秧子极力爬起来,开花的秧子越过杂草梢子。
懒汉庄稼都是草盛豆苗稀,就那样。有的田里杂草太多,只有在豌豆开花的时候,才发现有豆苗。老人们挤进杂草里,寻个豆角,豆秧子缠绕在大蓟草上,缠绕在青燕麦上,一眼看上去,豆角挂在野草枝叶上,好奇怪。其实杂草善于伪装,为了不被人薅掉,硬是把豌豆秧扯过来缠绕在自己身上。这样的杂草当然不能铲除,豆秧子保护着它,彼此相安无事。
尽管只有三五户人家,但是过年的时候外出的人都要回家,千里万里都得回来。这一年,他们拖着箱子背着包回到家,热热闹闹过完年,发现竟然出不去,路封了,因为疫情的原因。
开春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很遥远,小山村也要约束好自己。出不去,庄稼人闲不住,田野里走走,土地开始酥软,草芽都钻出地皮,草色若有若无。人们不能预估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总得想办法过日子。
无论怎么样,山里种点庄稼,就算靠天吃饭,日子能过得去。于是,几家人挑个日光很暖,一点风也没有的正午,点燃一把荒草,把撂荒梯田地里的杂草烧光。
倒伏在地的干草腾起火苗,冒着烟,一路呼啸而去。荒山秃岭,没有树木,引不起山火。火焰所過之处,田地焦黑,草木灰铺了一层,这是上好的肥料。东山坡烧过,西山坡烧过,差不多了,这些地都是曾经的好地,旱涝保收。
年轻人赶着牛,把土地深耕一遍。多年不种,土地板结得很呢。老人们撒种子,种豌豆,撒稠一些。老牛拉着耙,细细耙过去,庄稼就算潦草地种好了。蛰伏两三个月是什么感受呢?倒也没啥,有吃有喝,顺手把庄稼给种上。
过些天,路通了,村庄里的年轻人丢下老人小孩,背着行囊出门,不出去就不行似的。打工这件事对于庄稼人,是要永远做下去的。世界足够大,钱足够多,你不能窝在家里,必须去挣一点回来,除非生病。
大野里,豌豆苗扑簌扑簌抖着自己,迎风生长。接了几场雨,豆苗稠密。嫩豌豆苗薅回家,拿开水一烫,凉拌特别美味。大野里有无尽的豌豆苗,谁能吃得完呢。麻雀吃,兔子吃,旱獭吃,反正多,随便吃算了。老人们腿脚不好,撵不走。
雨水广,杂草也越来越多,挤在豆苗里,乱哄哄的。马刺盖最霸道,把豆苗挤得柔弱纤细,几乎站不住脚。马刺盖顶着一头乱刺,咋咋呼呼,绿色里带着灰,长得肥大明艳。豆苗很想一脚踹走马刺盖,但是豆苗的脚太细,又拔不出来。
这种野草为啥叫马刺盖呢?因为它的高度刚刚够着马的膝盖。茎叶带刺,刺异常尖利,能够刺破马的厚皮,让马疼得受惊。就这么豪横的杂草霸王。
野燕麦是猖獗的植物,它生长速度极快,根系深,需要大量的养分。青燕麦一路狂奔,只用了不长时间,就攻陷豌豆地,变成自己的领地,迎风招摇。
野燕麦不能让结籽,一旦结籽,落在地里,它的繁殖能力超乎想象,发了疯一般生长,所有的庄稼都会被挤死。如果指望收燕麦籽,产量又低得吓人,毕竟野生的嘛。野燕麦可不会把所有的心思花在结籽上,它使出浑身的劲儿,就是繁殖,扩张地盘,不给庄稼留空隙,撵走庄稼。这是一种有野心的植物,恨不能把地球变成燕麦地球。
留守老人们拖着关节炎腿,佝偻着腰,喘着气,一镰刀一镰刀,把青燕麦连同豆秧子全部收割。没办法,薅草是薅不掉的,阻断青燕麦蔓延只能这样。收割的青燕麦和豆秧子撂在地埂上,晒干,拉回家给牛羊当饲料。马刺盖自然无法自保,也一起砍下来,然后剔除。这个刺扎扎谁敢吃。
这个世界嘴太多,马刺盖为了保护自己浑身是刺。砍倒的马刺盖也无所谓,反正根还留着,明年再大干一场,踢走庄稼。这个想法虽然糟糕,甚至有些差劲,但对于野草来说,也没啥。庄稼有人照顾,野草不行,得自己想办法生存。所有的野草都比庄稼顽固强悍。
黄牛,山羊,驴子,家里仅有的牲畜都赶过来,拴在地埂上,让它们吃青燕麦,吃豆秧子。牛吃不完,羊吃不完,驴子也吃不完,它们都很发愁——这么多的青草,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儿呀。一发愁,牲畜们开始干架,拿脑袋砸,拿角戳,尥蹶子踢仗,不然一身好力气没地儿使。吃青草长膘实在快。
白茅草啦,灰条草啦,苦苦菜啦,往日里很吃香的青草,现在可没有谁在意。牛、羊、驴子都不吃,它们抖着嘴唇,在燕麦草里寻找豆秧子吃。豆秧子嫩,好吃。别看牛笨拙,它挑豆秧子那可很灵巧,缀满花苞的豆秧子是牛永远的爱,清甜,水嫩,怎么吃都吃不厌。
可是,有那么一面山坡,二阴地,真是老天的眷顾,杂草少到看不见。土地歇了几年,积攒出深厚的养分,庄稼长得比谁都好。豆秧子深绿深绿,摇摇晃晃扑起来,半人高,紫色的、白色的花朵开得繁密。细密的触手彼此缠绕,花朵一层一层喷薄而出。最多的豆秧子有七层花,结七层豆角。
下雨天山上的草木灰渗透地皮,豆秧子简直肥得要喘气。蔓生苒苒草,空心茎蒲公英,不歇气开花的紫花地丁,这些杂草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豌豆秧猛烈生长,吸走全部养分。杂草们面黄肌瘦,发出微弱抗议。
如果雨水足够,这些肥嫩的豌豆秧也许会长到半山腰去,攻陷所有杂草,打败沿途的马刺盖,让藤蔓植物给它做苦工,给它搭架子,让它攀爬冲锋。豌豆秧放肆而热烈地生长,把杂草都踩到脚底下——虽然它没有脚。
春风得意的豌豆秧纵情生长,不管蜜蜂、甲壳虫抽风,也不管蛾子癫痫。被吓坏的虫儿踉踉跄跄逃走,逃到有野草的地里去讨生活。豌豆秧任性地扯开自己的秧子,连朴实的花朵都摩拳擦掌怒放。风一吹,十万紫花朵、白花朵齐齐摇曳,简直美得地老天荒。
这一年虽然有疫情,但是烧荒后种下的豌豆竟然大丰收,是老人们说的那种成一年吃三年的丰收。打工的人们不得不丢下工地上的活儿,回到村庄里来收庄稼。
打麦场上豌豆垛一个紧挨一个,干燥的豆荚被太阳晒得裂开,豌豆啪啪往外弹。没有人想到豌豆竟然丰收到泛滥成灾的样子,一车一车往家里拉。
村庄里家家烙豆面饼,吃豆面凉粉,喝豆浆。豌豆的本质就是烟火人间,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只要豌豆丰收,庄户人的心咚哧一下落到实处。豌豆就是丰衣足食的象征,叫人心里踏实。
干燕麦呆呆躺在墙头,做梦都想不到村庄成了豌豆的村庄。豌豆秧明明看上去那么柔弱,一点攻击力都没有。大地上的事总是变幻莫测,往往柔弱的胜出,因为老天眷顾弱者。
小茴香
腾格里沙漠边缘,有无数小村庄。沙土地,适合甜瓜和小茴香生长。这些小村庄里,盛产这两样农作物。
小茴香属于伞形科植物,样子实在漂亮,简直是从《诗经》里跑出来的。事实上,小茴香是古老的本土植物,确实有古风。我们古老的蔬菜里,秋葵算一种,小茴香算一种,汉朝人吃,唐宋人吃,总也吃不够,皆因实在太好吃。
种小茴香也要稠一些才好,嫩苗蹿出沙土,细嫩,叶子很像芫荽,又细又密,一蓬青绿,苗冠如伞盖,相当好看。结籽如燕麦,小,有棱,青黄色。茎粗,肥茎丝叶,毛刷刷的,散发出清幽香气。
《救荒本草》说:“(小茴香)今处处有之,人家园圃多种,苗高三四尺,茎粗如笔管,旁有淡黄袴叶,抪茎而生。袴叶上发生青色细叶,似细蓬叶而长,极疏细如丝发状。袴叶间分生叉枝,梢头开花,花头如伞盖,结子如莳萝子,微大而长,亦有线瓣。采苗叶炸热,换水淘净,油盐调食。”
古人的文字,真叫人佩服。只几行,多余一个字都没有,你就知道小茴香的一生,妥帖又凝练。
茴香菜熟食或泡酒饮服,可行气、散寒、止痛。茴香苗叶生捣取汁饮或外敷,可治恶毒痈肿。
小时候,爹给我们烙饼。小茴香籽挑拣出来,文火炒,炒到焦香味散发出来,然后碾成粉末。发好的面使劲儿揉,揉得有了韧性,擀开,淋一层胡麻油,撒上小茴香粉,卷起来,再擀饼,搁锅里烙饼。茴香饼出锅,满屋子都是香味,猫儿都馋得伸着脖子咽口水。
至于小茴香饺子和小茴香油饼,是拿小茴香嫩苗来做。青绿嫩苗掐回来,开水烫一下,切碎,撒点花椒面儿就行。别的调料都不放,小茴香本身就是干调料出身。搅拌好的小茴香馅儿,一半包饺子,另一半揉面,下锅炸油饼子,好吃到目瞪口呆。
小茴香播种要精耕细作,粗疏了不行。草木灰、羊粪都是好肥料,出苗快。刚出土的嫩苗纖细柔弱,只需要浇一遍透水,拔节生长。硕壮的沙老鼠来了,这家伙盗窃小茴香苗,无比贪婪。它躲在沙地里,劈脖子咬断嫩苗,只吃根茎那一段,别的扔掉不要。沙老鼠的小爪子摁住嫩苗,咬断,吮吸汁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立刻抱头鼠窜,小爪子一路疾跑,谁都撵不上。
沙老鼠也掘向日葵苗,咬梭梭苗,但都不如祸害小茴香苗那么残暴。大概,小茴香那种若有若无的香味撩拨沙老鼠的心,叫它忍不住疯狂,躁动不安,不祸害简直不行似的。有时候一群沙老鼠在小茴香地里遇见,大打出手,打得吱吱乱叫头破血流。明明那么多小茴香,不知道它们争夺什么。老鼠的世界也是世界,人类不懂。
沙老鼠的洞穴不深,四通八达。村庄里的人们把骆驼撵到沙地里对付沙老鼠。骆驼根本不想闲着,跑来跑去找草吃。无论哪种动物,吃最要紧。骆驼凭借它的体重,硕大蹄子,只要遇见沙老鼠洞穴,无一例外要踩塌。沙老鼠洞穴塌方,那么它们出来祸害庄稼频率就会减少。不然,一大群沙老鼠一夜之间就会毁掉一块庄稼地。
但是,骆驼只能缓解沙老鼠带来的危机,不能完全阻止。沙老鼠子孙繁茂,一些老沙老鼠消失不见,另一群新沙老鼠蹿出来,接管地盘,继续祸害。村庄里的人们不得不和老鼠争夺庄稼,有什么办法呢?你不能投诉沙老鼠,它们没有主管;也不能养很多的猫,猫这东西,相当势利眼,如果它觉得打不过沙老鼠,一定会怠工,反而需要大量猫粮来养活它们,真是得不偿失。
沙老鼠以自己强悍的体魄和飞快的逃跑速度,并不怎么怕猫。而且有些成精的老耗子还会挑衅猫,吱吱乱叫,小爪子东扑西挠,令猫很没面子,好丢人。有时候沙老鼠在沙子里滚蛋蛋,看见猫,抖去身上的沙子,一溜烟跑了。如果猫非要撵上去,它掉头就和猫打架。毕竟它也比猫小不了多少。
沙老鼠也很忙,天一黑就按点儿出门,偷偷摸摸跑啊跑,咬啊咬,盗啊盗,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强大的人类,能主宰世界的人类,不得不俯身,同一个小东西斗智斗勇,够恓惶的。
到四五月间,小茴香苗已经相当茂盛,能上市了。这时候沙老鼠就会偃旗息鼓,转战别的农作物,它们只喜欢很嫩的苗。沙老鼠一生缚于土地之上,也缚于土地之下。总之它们根本离不开土地,死缠烂打。庄稼人种什么它们随机祸害什么,不会空手而回。沙漠里动物稀少,沙老鼠对庄稼的祸害远大于任何一种动物。实际上鸟儿能啄几根呢,沙兔子喜欢野生的植物。
割小茴香,庄稼人叫起菜。一把一把捆扎好,装进筐子,被车拉走。超市里卖得贵,不用搭配别的蔬菜,小茴香总是独立完成一道好菜。
大田里那么多小茴香,无边无际,空气里弥漫着清幽香味。大部分小茴香要收籽。小茴香葳蕤生长,浇过二遍水就开花,繁密得不像样子;三遍水结籽,一粒一粒茴香籽挂满茎秆,村庄里的人说,茴香结籽索罗罗。
收割,碾打完毕,一部分小茴香籽去了药材市场,一部分进了调料铺子。小茴香为啥叫茴香呢?说是能去除肉类的腥味,让肉回到原本的香味,所以叫茴香。还有一种大茴香,也是香料,要区别开,就叫小茴香。
大概我是沙漠里长大的缘故,特别喜欢小茴香。籽碾碎烙饼,嫩苗包饺子。那种味道独特,有点异域之味,有点思乡之意,有点倦怠,渗透人间烟火气息。
雨天,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让人心里顿然觉得岁月深幽,光阴清净。这样的时分,慢火炖一锅骨头汤,小茴香嫩苗开水烫过,凉拌一碟。然后再切一点,揉面,炸一些小茴香油饼。
热腾腾的食物端上桌,也不会想很多事,粗茶淡饭,就安安静静吃喝,把自己的心交给小茴香的清香。鲜衣怒马都卸下,素面朝天度雨天。轻柔的音乐,一地碎碎的雨点声,院子里聊天的老人,一只披着雨丢丢丢小跑的花白狗儿。厨房里炖着的汤,盘子里一摞茴香饼,只觉得,时光美不可言。
地 耳
大地上,总有这么一些家伙,长得拖拖拉拉,根本就不打算长成具体的形状。褶皱状,水波状,反正就是随心所欲的样子。它是极简主义,没有根,省略掉茎,叶子花朵都不要。绝不站起来,大大咧咧躺着,不修边幅。颜色嘛,尽量低调,黑褐色,或者稍微带一点深绿。名字也无所谓,叫啥不是个叫,地耳、地达菜、地见皮都行。
不下雨的日子,地耳去哪儿了?躲在草根底下,乱石头缝隙,羊粪蛋里,不好找。它干枯,薄如纸,蜷缩成一点点,又脆弱,指甲抠出来,一捏就碎成粉齑给你看。地耳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隐身于大地,混杂在草屑尘土里,皱缩休眠,以碎末末的分身术,最好别让人看见。
没有谁可以依赖地耳生存,绝不能,连蚂蚁也没办法。地耳太接地气,不能轻易获取。不下雨时,地耳干缩,烂渣渣,紧贴干土,一动不动,以隐居的方式和世界相处。只有和土地混为一体,地耳才觉得自己安全无虞。
然而,地耳这种东西,没有必要如此谨慎吧?又不是多么好吃,可有可无嘛。如果大地没收掉青草和苜蓿,牛羊一定会饿死;如果老天没收掉粮食,人类就要遭殃;如果大风刮翻树木,鸟儿就得流浪;如果旷野删除地耳,多大点事,人类和动物毫不在意。地耳是谁?它是干什么的?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人类还没有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地耳已经悄无声息登陆了。恐龙绝不会吃它,剑齿象看都看不见地耳,虫子、蚂蚁也不见得靠地见皮过活,可它为何要把自己进化成这个鬼样子?谁知道呢。反正地球就是它栖身的宿主,它就要贼头贼脑潜伏。
起风了,空气里有雨水的味道。铁线莲顶着一头白发,一根一根派遣它的绒毛种子,让风刮走,越远越好。种子掉到脚下,就会和它争夺养分。蒲公英也不闲着,竖起一支支白色绒球,吹一口气,打发它远走高飞。蘑菇暗暗抽出菌丝,一圈一圈布下蘑菇圈八卦阵。地耳按兵不动,紧紧吸住草根,别让风吹跑。
大雨小雨,从天空一路旅行而来,大地上湿漉漉的。雨水不断降落,填满草窠的间隙,填满小河沟壑。大地上的植物心满意足,天旱了很久,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蘑菇已经沉不住气,摁不住狂跳的心,在土壤里躁动起来。菌丝钻出地面,细细的,戴着小圆帽。雨下雨的,蘑菇长蘑菇的。只用了半天时间,小蘑菇长成大蘑菇,山野里,树林里,一个一个的蘑菇圈白生生地摆好阵法,发射信号给老天。
地耳沉住气,颜色深了一些,依然不起眼。你下你的雨,我藏我的身,何必要招摇呢。它稳重,土眉沙眼窝,不想给人类献殷勤。
雨停了,太阳还没出来。枯萎的地耳倏然之间活过来,迅速膨胀,干枯皱缩的碎渣渣吸足水分,扩展成片状,皱皱巴巴的一片,铜钱大,状如胶质皮膜,软软晃晃,舒展在草丛里、河滩里、山坡上,心花怒放的样子。
地耳知道人類很懒,视力也不如鹰,所以不想长得很大,颜色伪装成草滩色,紧紧贴着地面。这样,地耳就好好待着,柔软的褐色褶边触动草根,探寻周围的事物。毕竟,它也是活的,也有自己的小光阴。
生长的地耳真的没啥样子,扁也不扁,圆也不圆,也不三角,也不四方,稀里糊涂的一张薄片,一脸褶皱,像从树叶上随便撕下一块揉揉扔到地上。没形状就是大形状,没用处就是大用处。反正地耳就那么歪歪扭扭躺着,匍匐在地,过自己自由自在的日子。
继续下雨,地耳就接着快活。如果雨过天晴,太阳热辣辣晒,地耳赶紧又蜷缩起来,变薄,变小,继续皱缩休眠,等下一场雨。草木的一生是从春到秋,地耳是从一场雨到另一场雨。它的一生很漫长,不死,除非被人吃掉。
没有谁会盯着地耳去捡。放羊的老汉闲着无聊,碰到眼皮底下,顺手捡一些。雨天小孩没地方去野,扭住打架,被大人呵斥一顿,撵到山野里去捡地耳,好歹有一顿包子馅。尽管地耳一定不想当包子馅,不想和豆腐、韭菜搭配。
大多数的地耳,暗自膨胀,暗自收缩,大野地里远远近近散开。它们可能想当大地的耳朵,能听见雨天淅淅沥沥的声音,能听见苍茫大地万物对老天倾诉的喃喃细语。地耳洞悉万物,洞悉天地之间的秘密,却秘而不语,它没有嘴。它是枯萎又生发的耳朵,独自行走江湖。
地耳想成为独居的物种,河滩里的地耳不想撞见山坡上的地耳。地耳擅长伪装,混在草木杂色里,宁愿在薄雾中发呆打盹,也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很小的时候,某一回在河滩里瞎逛,突然遇见一大片黑黝黝的地耳,肥嫩,柔软,躺在石头滩青草丛里,软软瘫着。小孩子心浅,看到一大片地耳就觉得特别奢侈,跟发现一窖金子没啥两样,于是颠儿颠儿跑回家报信儿。那时候我跑起来小腿内撇,营养不大好。
我的姑姑们拎着篮子风一样刮来,打算狠狠拾一篮子地耳蒸包子。路过树林子,野菜呈上新鲜的枝叶,蘑菇闪着白光。可是我们蹚过野菜,看都不看一眼蘑菇,一路狂奔河滩。走得太急,脚踩到河滩的石头上,碎石头不稳当,脚底下嘎巴嘎巴响。
然而诡异的是,我们跑了一大圈,并没有找到那片地耳。姑姑们骂我是个白话匠,类似于扯谎精。可是,我的确是遇见过的。那么喧哗的一大片地耳,说消失就消失了。它蛊惑了我,让一个小孩白白跑那么远的路,还是个内八字小短腿。
世界之大,地耳有理由逃匿不见。对于它的背叛,我们悻悻而去。好在人类不是只对一种东西有饥饿感,我们吃得很宽泛,蘑菇,野菜,酸刺枝嫩尖,豌豆秧子,很快忘记了那些只够塞牙缝的地耳。
越简单的,越复杂。对于地耳,大概是这样。虽然它把自己简约成一张薄片片,皱皱巴巴,粗陋难看,但是它的内心可能谁也不能触及。地耳就那样简单潦草,雨天活了,旱天又消失。我们常常问自己,我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对于地耳来说,那才简单呢,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有什么要紧。天地之间,有它蹚出的一条路,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