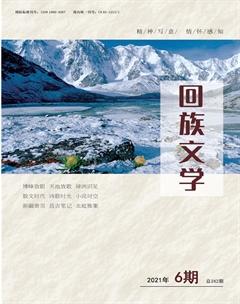在生活中绽放的什物:信(组篇)
外祖父和信
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外祖父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说:“小罗海,你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放假了就到上海来玩。”
那时我六岁,在安陲小学上一年级。外祖父在遥远的上海,而我才离开他不到半年。
母亲把信读给我听的时候,我觉得无比幸福。我已经离开上海了,可是外祖父还记挂我,要我放假了去上海玩。
我收到的第二封信还是外祖父写给我的,他给我寄了好多小人书来,并在信中叮嘱我要热爱读书,将来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母亲让我给外祖父回信。“敬爱的爹爹:……”母亲教我这么写。在上海,外祖父叫“爹爹”。我刚开始叫的时候觉得非常拗口,叫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敬爱的爹爹:”母亲让我给外祖父表决心,“我一定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长大了做一名合格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假期的时候,母亲真的让我回到了上海。在假期里,我看到外祖父几乎每天都会读信写信。外祖父有十个儿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子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先后离开上海去祖国各地,支援各地建设。大舅舅在陕西,我们在广西,三姨娘在新疆,小姨娘在青海,等等。
外祖父收到信了,不像多数人那样把信口随手一撕。他有一个小刀片,他会小心翼翼地把刀片插进信封口的缝隙里,慢慢一点一点把信封口完整地撬开来。
刚开始,我看到外祖父这么做的时候十分不明白,不明白外祖父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这么颇费心思。
后来很快就明白了。
外祖父这么小心翼翼把信封口撬开来后,将信抽出来阅读,并把空信封放在一只抽屉里存起来,等集得了七八个的时候,他就会把它们拿出来,用刀片把信封纸一个一个拆开,展平,然后翻过来,折叠成一个新的信封,用糨糊粘起来,以备写信时使用。
他不仅自己这么做,还手把手教我。他让我坐在桌子前,他在身后围抱着我,我手里拿着刀片,他抓着我的手,教我如何轻轻地将刀片插进信封,如何恰到好处地用巧劲儿一点一点慢慢把信封撬开来。
后来我长大了,很长时间,一直都没有改变小时候外祖父培养起的这种重复使用信封的习惯。同学何政一见到我如此对待信封,非常不解,犯得着如此劳心费神地节约吗?我听了,笑而不言。
给潘小琴的情信
潘小琴分配到我们医院做护士的时候,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性格如火,热情,开朗。
我极其喜欢她,仰慕她,但并没有暗恋她。
我和张望那时在县中学读高一,暗恋她的人是张望。有一天张望对我说:你看潘小琴美不美?
我仰头想象了一下潘小琴:她那红扑扑的脸蛋,那双扑闪着长睫毛的会说话的大眼睛,那张红润小巧一笑便露出一排洁白牙齿的嘴,简直美极了。
我说:潘小琴挺美,真美极了。
张望听我这么说完,就得意地笑了,好像潘小琴是他正捧在手里给我欣赏的一个宝贝,我赞赏潘小琴就是赞赏他。
张望盯着我,郑重其事地说:我爱上潘小琴了。
我听了不以为然,撇撇嘴。
爱上潘小琴也是新闻吗?需要郑重其事宣布?!
张望好像有点急,我爱上她了,你就不能再爱了。
原来是这样。
切,为了表达清白,我毫不犹豫地声明,我根本就不会爱上潘小琴!
其实张望这么说后我发觉我果然是有点喜欢潘小琴的。说完声明后,我心里略微有点惆怅,有些后悔,我为什么不先于张望把爱上潘小琴的话说出来呢?现在后悔药是吃不着了,我不能再爱潘小琴了。
张望见我这么斩钉截铁地声明了,就放下了一颗吊着的心。
张望忽然脸上露出点羞涩说:我给潘小琴写了一封情信,你帮我送去给潘小琴吧。但是,你不能偷看。
我不肯,我说:又不是我爱上潘小琴,要送你自己送。
张望没有想到我会拒绝,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举起手来抓着他脑袋上像野草一样乱蓬蓬的一堆头发,不知怎么办。然后,他望着我笑了。哦,我知道了,他说,你是吃醋了。
我愣了一下,否认说不是,然后认真地想了想,可能我真的是在吃醋呢,心里不是有点酸溜溜的吗?
好吧,为了表明我没有吃醋,我改了主意答应道:只送这一次。
就送这一次!
我伸出手来接过张望递过来的信。
张望眼睛亮闪闪望着我,好像我就是潘小琴。
傍晚的时候,我上到潘小琴住的宿舍楼。她住在二楼的集体宿舍,两人一间。进屋的时候我看到,除了潘小琴,她的舍友吴小丽也在。我说:潘小琴,这里有你一封信。
潘小琴刚抬起头来望向我,吴小丽已经起身笑眯眯地把信抢在手里了。她说:我看看又是哪个痴情的小伙子给我们大美人写来情信了。
潘小琴说:拿来吧,别闹了。她一下把信抢在了手中。
我还站在屋里,没走。吴小丽发现了,咦,你还不走干吗?给我下驱逐令。
我很不高兴,望向潘小琴说:潘小琴还没让我给送回信呢。
吴小丽听了大笑,如果是你写的现在就有回信,不是你写的就没有回信。
潘小琴也抬头望着我,盈盈地微笑着,好像并不急于看信。
我只好转身走了。
张望早已等着急了,见我到来,用急切而渴望的眼神望着我。
我不说话。
张望见我不说话,伸出手来说:回信呢?给我吧。
我说:没有。
张望感到很迷惑,怎么会没有?他不相信没有回信。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你肯定没有送到。張望说。
送到了。我说。
那怎么没有回信。
我又不是潘小琴,我怎么知道。
我气愤地转身走了。不欢而散。
我没料到帮张望做了好事,没得到张望感谢,还弄得一肚子气。
许多天后张望来找我了,他小声地说:还没得到回信。
我不答。
又过了几天,张望又找我了,他耸耸肩,还是没有回信。
要不,张望,你自己去问问潘小琴,为什么没回信。
张望抬起头望望天,扯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声音小得好像只有他自己能听见:我不敢。
这成了一封永远没得着回信的信。
世上许多的情信就是这个结果吧。
张望的爱情表白浅尝辄止,到此结束了。
在部队写信和收信
我在部队当着我的小兵。新兵那一年,以及后来的许多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写信。
我给父母写信报告我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我给我的外祖父写信报告我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我给我所有的亲人写信报告我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
我给我的同学写信报告我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我给我们医院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们写信报告我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我还给任何我想得起来想得到的人写信报告我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
部队寄信不花钱,把信写好后,拿到连部让文书盖个菱形的戳,就可以请邮递员送走了。感谢国家有这个好政策,感谢部队有这个好政策,不然我写信就要写穷了,写得身无分文了,也不够支付邮费。感谢国家有这个好政策,感谢部队有这个好政策,它让我同所有的亲戚,同所有看着我长大的前辈,同所有的好友,同所有的同学可以畅达地沟通,传递信息,鸿雁分飞了,还像仍在一起,彼此温暖。使我的思念能够倾诉,使我的思念得到倾听,使我也能够听到别人的倾诉,使我们能够开心地互诉衷肠。
我在部队当着我的小兵。新兵那一年,以及后来的许多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收到回信。
收到来自父亲母亲的回信,收到来自外祖父的回信,收到众多亲人的回信,也收到同学的回信,收到医院里叔叔阿姨们的回信,收到所有想得起我记得起我的人们的回信。
在好长的时间里,在好多的日子里,每到早上十点该是邮递员送信来的时间了,我就设法悄悄地跑出营房,站在路口,引颈翘望。
我要第一时间看到邮递员,我要第一时间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亲人们的来信。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敲着铃铛,叮叮当当地来了,一跨腿下了车,笑盈盈地向我点头,把连里所有的来信递给我,然后又叮叮当当地敲着铃铛,跨上车,笑眯眯地走了。
我急忙低下头翻看这众多的来信。
我找到了预期到来的亲人们的来信,我找到了预期到来的同学们的来信,我找到了预期到来的那些医院里叔叔阿姨们的来信,我还看到了一封不知是谁写给我的来信。这封不知是谁写给我的来信,更让我激动万分,我抢着最先打开阅读。
有时我也没有接到预期到来的来信,我怅然若失,望着直通远方长长的道路,不知这封信是还在长远的漫漫路途中旅行,还是给不小心弄丢了。我心神难定,失魂落魄,四顾茫然。我觉得肯定是在路途中丢失了,心里生出无限惋惜,无比失意。
有时我没能在邮递员送信来的时间里找到借口走出营房。我心里失落得要命,心悬着放不下来,我感觉我的耳朵对耳边的一切什么也听不见,我感觉我的眼睛对眼前的一切什么也看不见,常常要人喊我一声,才能回过神来。
我就无比羡慕文书,我就无比羡慕文书有每天去路口向邮递员领信的任务。
我常常想,如果我也能当上这个文书就好啦,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每天到路口等邮递员了。
其实我们的文书从来也不到路口等邮递员,只有我才到路口抢先去领邮件。他总是待在文书室里等邮递员送信上门。
我见他安安稳稳地坐在文书室里等邮递员送信上门,我总是不能理解,我总是感到不可思议,我总是感到无比奇怪,我总是不能接受。他怎么能够耐得下性子,如此若无其事、慢条斯理地等待?!换成我来,我恨不能两脚生风,早就站到路口翘首以待了啊!
我非常地想当文书。在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我知道我还不够格当文书。可是在我已经是老兵的时候,已经够格当文书了,可还是当不上文书。我当上了班长,我当上了代理排长,我还当上了值班长,就是偏偏当不上文书。当上文书的人是骆宏。我非常地不理解,我多少还算有点文才啊,骆宏没有任何文才,可是他却当上了文书,而我却当不上文书。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连一点小小的愿望也没能满足,也不能实现。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它总会和你的愿望闹别扭,它总是喜欢与你的愿望背道而驰。
我写出的信越来越多,我收到的信也越来越多。当我收到的信在我的抽屉里开始像一支军队一样整齐雄壮地排成一列一列,我满心欢喜,但是我发誓要让我的信在抽屉里排出更多的队列,一个抽屉排不下,就排到下一个抽屉。
每当我打开抽屉看着这些一列一列排列着的信时,我就无比自豪,我就想起潘小琴。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次我去潘小琴的宿舍找她玩,她正在开着抽屉翻信。我一眼看见,惊呆了,我看到她的抽屉里也像我现在一样,排列着很多信,而且有满满一整抽屉的信。我立即羡慕得要死,我立即嫉妒得要命。我暗想,有一天我的抽屉里也能有这样满满一抽屉的信就好啦,我会幸福得要死。
从《黄金时代》来去的信
《黄金时代》是广东的一家青年杂志,当时在广东青年里影响火爆,特别是在广州,几乎人手一册;我在广州当兵,我们单位的兵也几乎人手一册。
每一期杂志到来了,战士们都纷纷抢着翻阅。
我们多么喜欢上面刊登的文章啊,它写满了我们的信仰和追求。
现在,这样的杂志没有了,或者说,那时的那种信仰和追求没有了。而现在的信仰和追求,一份杂志是难以表达和涵盖的。
那时候《黄金时代》向我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一扇门,更向我们打开了通往无数未知心灵的道路。它办了一个交友栏目,每位想交友的青年都可以免费在上面登出自己的信息。我和我们许多的战友都在上面发出了自己的信息。当我们拿到杂志看到我们的信息變成铅字堂而皇之地登在杂志上时,我们都无比激动,我们都激动得全身发抖,我们都叽叽喳喳喜气洋洋地向对方说着:你看,这是我的。可是谁也没心思注意到别人的信息,谁都只沉浸在自己的喜悦里。
然后我们就等待,充满希望地期待,期待着不期然的鸿雁飞来。并且我们也仔细地翻阅着别处的信息,悄悄选择着要给远方的谁谁去信。
那时我一口气寄出了几十封信,写得我臂膀酸了,握笔的手指麻木了,我还乐此不疲,不肯停下,不舍得放下。
一个礼拜后我收到了别人给我写来的信,再一个礼拜后我开始收到了我写给别人然后别人写给我的回信。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纯真、喜悦和希望,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特别是对未知心灵的探究和交流。在信里面我们一见如故,在信里面我们陌生又熟悉,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询问和了解对方,也像面对老朋友一样把自己介绍和表达给对方。我们彼此坦诚,真诚,毫无心机。我们像白纸一样主动地在陌生的朋友面前把自己铺展开来,让陌生的朋友在我们洁白纯净的心灵绘画出一朵一朵鲜艳的友谊的花朵。
这些美好的来信,这个美好的时代,真是令人无比怀念啊。
我们生逢其时,我们生逢这样一个最后的纸质时代,我每回憶起来就心怀感激。
香港的来信
我的三姨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支边去了新疆,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戈壁滩,戈壁滩上生长着红柳和骆驼刺。我无数次想象着新疆,想象着新疆生长着的红柳和骆驼刺,想象着红柳和骆驼刺的样子和习性。我觉得我的三姨娘应该就像这些红柳和骆驼刺,就是这些红柳和骆驼刺,顽强地生长,生根,开枝散叶,绽花结果。
我在上海见到来自新疆的小表妹时,小表妹总是向我活泼地唱着新疆的歌谣,跳起新疆的舞蹈。她的一个保留节目最让我喜欢,百看不厌。在跳起这个舞蹈的时候,身子一动不动,颈部却像长着可以拿过来拿过去的关节,头在颈上一下移向左,一下移向右,一下移向前,一下移向后,好像不是生长在身体上,而是连接在身体上似的,让我觉得无比地神奇。我也总是学她这样舞蹈,可是当我试图像她那样移动我的脑袋时,无论如何我的身子总是定不住,总是跟着一动一动,总是不成功。表妹看到了,呵呵地笑,笑得弯了腰,笑得趴在了床边起不来。
三姨父和三姨娘都在新疆的一所建在戈壁滩上的学校当老师,而三姨父的兄弟姐妹全在海外,只有他一个人在国内。到了1978年,他带着三姨娘和我的小表妹也去了海外,最后定居香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来到广州当兵,与他们几乎是一水之邻。多年没见了,三姨父和三姨娘都渴望见到我,他们辗转通过我父亲同我约定了相见的日子。
在这一天我无比激动地来到东方宾馆,在东方宾馆的大堂里见到了他们。
三姨父西装革履,梳着一个大背头,气质儒雅;三姨娘穿着旗袍,手上挽着一只坤包。
三姨父见到我非常高兴,他有点拘谨地走过来,像平辈一样同我握手。这让我很不习惯,对这种待遇,也有点不敢接受。
那时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世界各地的交流日渐增多。
那几年国内变化实在太快了,我们追着世界的足迹跑,努力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我们的发展日新月异,跟几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三姨父和三姨娘非常震惊,他们出去没几年,内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他们还没来得及感受,没来得及融入。
这次见面只是短短的半天,三姨父和三姨娘要回香港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通信地址写给了他们。
三姨父和三姨娘回到香港后给我写来了信。我拿着信封,薄薄的,感觉里面好像并没有信纸,暗暗吃了一惊,又有点迷惑,不知是怎么回事。
我把信打开来,香港的信封不太一样,它的封口以一种三角的形式粘贴在信封背面的正中,粘着一点蜡。我用我常用的开信的小刀片把信封轻轻地撬开来,它立即就全部展开来了。我惊讶地发现,信是写在信封纸里面的,不用信纸。而且,这么用信封来写信并不是三姨父和三姨娘有意为之,而是工厂印刷信封时本来就这么设计的。
我想到了外祖父,如果说外祖父重复利用信封只是他的个人行为,那么三姨父三姨娘用信封背面给我写信,就是一个政府倡导的行为了。如果说外祖父重复使用信封只是着眼于节约,那么香港让民众这么使用信封,不仅是一种节约,更融入了一种对地球资源珍惜珍重的理念,就像我们现在提倡无纸化办公一样。
父亲的信
我在军队的四年多,父亲给我写来了许多信。
每收到父亲的信,读完了,我都铺展开来,把它们的折皱捋平了,小心地按收到信的时间顺序安放在一个文件袋里。四年多来,已经收到了父亲的厚厚一摞来信,一封也没有丢失,一封也没有损坏,全都完好得就像刚刚收到的一样。
退伍的时候,我把这些信带在身边。我先是回到了父母家,把它们放在我的书柜里;后来我分配在工厂工作,我把它们带到工厂,放在我宿舍的床头柜里;再后来我下海经商了,四处奔波,我仍把它们带着,它们跟随我走南闯北。
奇怪的是,虽然我始终带着父亲多年来写给我的这些信,但离开部队后我几乎再也没有打开来重读过。
我就只是这样让它们始终跟随着我,不离不弃。
后来我突然觉得,我不再看不再读它们也许是我没必要看,没必要读了,它们其实已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
父亲有时挺得意地对我说,我能在部队混得那么好,能那么顺利,一年入党,当年又直接提班长,接下来又当了代理排长,又当了值班长等等,有他一份大大的功劳。起先我以为父亲指的是他写给我的信,他在不同时期写给我的指导我人生的信。我有点不服气,有点不以为然,又有点承认。
有一次,父亲跟我透露,我在部队四年多来,他不但给我写了许多信,另外,为了我也不止一次给部队上写了信,给我的上级、我的首长写了信。他在这些信里努力地让部队和首长了解我们的家,我们家每个家庭成员,介绍我在家里的各种情况,我的个性、爱好,我的各种优点和缺点,请求部队教育、指导、帮助我,等等。
我吃惊了,没想到父亲会这么做,真是用心良苦。
难道我在部队所取得的进步,都是因为父亲的操心吗?都是因为父亲在暗中助我的一臂之力吗?我又有点不愿意把父亲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我还是愿意相信这是我自己在部队里的表现和努力的结果。
父亲在讲述的时候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这种心思,他最后总结道:当然,你能够在部队有进步,主要得益于你自己的不断努力,得益于你对自己不断地要求。
父亲真是面面俱到,把我的心放平了。
父亲母亲原来一直住在单位的宿舍里,后来我们在开发区买了一块地皮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安了家。这个家,我觉得不仅从此就是我父母的安身之所,更是我灵魂永远的归属地,我就把跟着我东奔西走几十年的父亲写给我的信放在了这个家里。
我以为我安放得妥妥的。
每次我漂泊归家,一定要去看看它们。
它们装在一个旅行袋里。这个旅行袋自从我下海经商,生活奔波飘荡、居无定所后,就一直这么安置着它们。
我见它们每次都好好地搁在书架顶上,安然,安详,从来也没有人去翻动,从来也没有人去打扰,我就很放心。
可是,最近父亲要把这栋房子卖了。我进到屋子里,希望把那些信重新带在身边,突然发现,我珍藏了几十年的信,居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不翼而飞了。那个曾跟随我走南闯北东奔西跑的旅行包还在,可是里面的信却不在了,统统没有了,莫名地失踪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我不敢动问父亲,不敢向任何人打听。
这些信,只是我个人的秘密,属于我一个人拥有,我不想向任何人提起。
就这样,从此我有了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这个心结从此悄悄地跟随我,如影随形,我去哪里它也到哪里。
解不开,我也不打算解开。
只是它常常在心灵深处隐隐地疼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