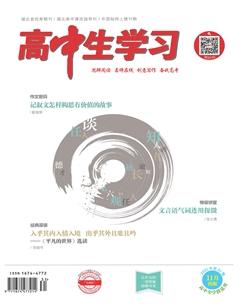等
我曾读过一段话——一位盲人,若是先天的,那他的生活便如在幽暗深淵中沿着峭壁向上爬,终有一天到了顶,虽看不到光,却能感受光的温度,他的心从那一刻开始便不再寒冷;若是后天的,那他犹如先坠到谷底,在滚烫的岩浆中受着刺骨的痛,在朽毁中呻吟,在磨砺之中迎来涅槃重生,然后奋力飞上去,让大片大片的光照在身上,所有的苦痛都得到升华。
他是后者。我明白,我需要等待,等待他的涅槃重生。
他原本很健朗,背着手,站在那里,背挺得很直,那染着星点白霜的头发,在风的吹拂下,微微晃动。母亲说当初他在地质队工作的时候,曾跑遍全国各地去勘探、测绘,祖国大好河山全靠一双脚去丈量——他,是我的外公。
我上初中后,父亲留在北京工作,我和母亲随他去新的城市“开荒”,垦出了新家,遇上了新同学、老师,开启了新生活。对我来说,在熟悉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后,又面临迁至他乡,心里充满惶惑和不安。这种情况对外公而言,即使仅仅隔着一道山沟沟,或是夹着一个山头,他也想天天去瞅着、盯着。于是,每周六我从寄宿学校回来后,他都会和我有这样的对话:
“回家了?”
“嗯。”
“早上吃的什么?”
“豆浆,油条。”
“那好哦!”
“嗯。”
“作业多吗?”
“多。”
“那你去写作业吧。”
“好。”
对话很短,每次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我们之间大多是少言或无言。因为许久未见更是多了些生分,心里有些烦躁。一般都是,他等着我回家,我等着他问完。
慢慢地,慢慢地,我意识到我和他正渐行渐远,我发现:他不出门,不打麻将,大多时候只是在阳台上看看窗外风景,或是看看电视打发时间,那落寞的眼瞳深处,仿佛一直在等,等着我们主动说出“一切安好,您放心”。
渐渐地,我想多跟他说点话,让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开开心心地随着我的话语蹦到他的耳朵里去。
我说:“老家降温了,您衣服要多穿点。”
他说:“晓得。”
“晚餐吃的啥?”
“稀粥就剩菜”
“多弄点新鲜菜吃嘛!外公,我跟您讲,晚饭和午饭就隔着五六个小时,剩菜里的亚硝酸盐含量处在最高峰,吃了不好!”
“哦……哦,你莫操心。好好学习……”
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跟我说:“你外公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
大家都沉默了。大人们总是善于藏住自己的情绪,不让其在脸上爆发,可是,语言和声音是不会隐瞒的。变长的停顿,增加的音节,嗓子里微弱的颤抖,悲伤、难过充斥其中。
现在,轮到我等他了。每周六给他打电话时,“嘟……嘟……”,电话拨通我就等,等电波穿越大气层进入他的手机中,等着他摸索着去拿手机,一个一个摸索着按键,接通后开心地说:“哦!殷越!”。我的耐心前所未有地足,盼望着等到春节的时候回去见一见他。
可,因为疫情蔓延,惊恐和紧张席卷而来,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推翻了我回乡的安排。但,却挤不走我心中的思念。
时隔两岁春秋,又平添半载,我终于回到老家。
一进门,我刚喊一声:“外公!”随即瞪大眼睛看着他:人瘦了,几年前他还像是棵衰老却暗藏韧劲的树,经历了两年苦痛的折磨,现今瘦了一大圈,有了颓然的沧桑;白发苍苍,眼皮紧闭,看来着实令人伤心。我挨着他坐下,他摸索着抓住我的手——他的指尖微凉,手掌粗糙,微微沁出一层汗来,恰似是他激动的心。他终于把我盼了回来,他一直喃喃着:“回来好啊,回来高兴啊……”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说我平常遇到的好玩的事,我说我的同学、老师、朋友的事,我说东京奥运会的奇葩开幕式。我想把我这两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说给他听——他已被困在黑暗中,而他等我等得太久了。
人老了,变“犟”了。
他什么事情都“不要你们管”。他自己刷碗,自己去厕所,自己摸着到餐桌来吃饭。他想让我们明白“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我明白,他需要一次涅槃。我会站在他旁边,默默看着他,陪着他去探寻。若他要摔倒了,我就稳稳扶住他,其余的,让他自己来。
即使他用近乎吼的语气说着“不要你管”,我也想像母亲那样去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好。”我还想告诉他点新鲜事,讲点我学的新知识,也让他“暮而点灯,学而不辍”。
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等我,现在轮到我缓一缓脚步,等一等他了。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看到他走出家门,咧开嘴欢笑。那时,阳光洒下,一切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