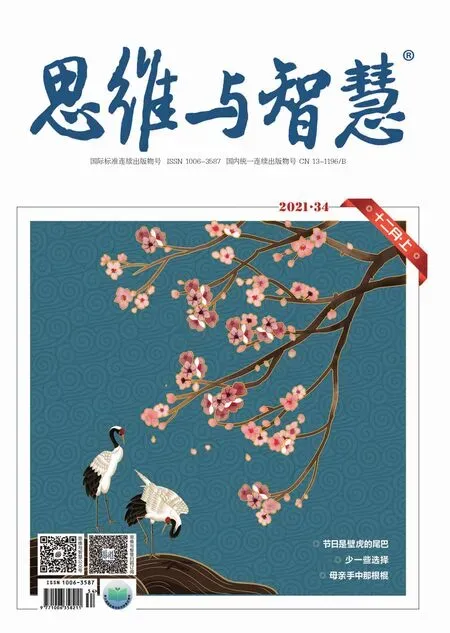做好饭菜等母亲
●董改正

每次回家,我都不提前告诉母亲,怕她把我当客人。这次也一样。回家时,母亲果然不在,我放下背包便进了灶屋,洗锅,查看油盐酱醋,便准备做午餐。
去菜园砍了毛豆,摘了辣椒,掐了一大把山芋藻子,收拾妥当已经十点多了,但我不慌不忙,因为母亲肯定还有三个多小时才能回来。在我家,中餐是早餐的余事,热热菜,热热饭,扒拉一碗饭,中餐就算解决了。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那时候田多,从播种到插秧到收割再到归仓,没有哪一样不纯靠人工的。母亲常常是天不亮就起来了,煮一大锅稀饭,歘歘歘炒几个菜——腌白菜是一年到头的标配。早上还好,中午放学回家,粥早已凝固,我懒得热菜,更别说热粥了。很多年的夏天,我一直是“划粥而食”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十二岁学会做饭才结束。
别人回家一般是去商场超市,而我一般是去菜场——给他们买的牛奶、衣帽鞋子等,常常要么是过了保质期,变成了石灰一般的怪物,要么是素蟫灰丝时蒙物什,已经不堪入目了,而这时,他们却不愿意扔,反倒要吃、要用了。于是我只给他们买必须现吃的,鸡猪鱼鸭肉,回家做好了,等他们疲倦而回。
依然烧柴锅。引火我技艺纯熟。架好松木,我煮鱼烹鸭,任其毕毕剥剥着,我坐在灶屋的门口,吹着过堂风,剥豆子,撕山芋藻子皮。左邻右舍或戴帽而回,或裹巾而过,或点头而笑,或问声“回来啦”。鸡们一改开始时的拘谨,或于豆荚内擒青虫而寻偶嘚瑟,或在芋叶中啄丝皮而嘀咕惊异。间有麻雀无声射下,于晒场那浩瀚的玉米海中恍惚忘我,伸颈撅尾,忽又尖叫一声,劲投而去。在时刻变化的背景里,记忆越过时间的篱笆,飞回遥远的少年时光。
对于肉类,我一向认为有嚼劲为好,但我让小火和我一起发了好一会儿呆,直到锅里的鸭肉酥软烂化——母亲老了,装了七八成假牙。对于鱼,我向来是要多放辣椒的,一是去腥,二是起味,但我却一点没放——母亲怕辣。菜一个一个地盛起,日影一点点地移向晒场,村道上响起了各种回家的声音。其间父亲踢趿着拖鞋回来了,见到满桌子的菜,孩子一样笑了;接着弟弟骑电瓶车回来了;然后是不知藏身何处的几十只鸡,一起涌到阶下,叽叽待喂。
我站在门口等母亲,就像一个小小的孩子。时针指向一点时,母亲回来了。母亲看到了炊烟,看到了系着围裙的我,快活地笑了,满身的疲惫似乎都在那一刻消散了。我看见她,心中一直悬着的念想落下了。母亲轻松地坐下来,脱鞋,喝水,坐到桌前,喝了一碗温汤,再一个个菜试吃。不管好不好,她都笑着说:“今天享你的福了。”
三十多年前,每当我做好饭菜,就特别盼望母亲回来,盼望得到她夸张地褒奖。她总是扬眉瞬目,瞪大眼睛,惊异地说:“我儿子做得真好吃!我是享你的福了!”我就快乐得心怦怦跳,就像今天一样——而事实上,那时候,她穿过烈日炎炎的田野,带着满身的疲惫而回;今天依然如此。她享过我多少福呢?我给予过她多少呢?多少年我是受之无愧视若等闲,而她每受我一点孝心,总是如蒙大恩,定要显摆四方。
这样想着时,母亲已盛好一碗饭,夹好菜,端着串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