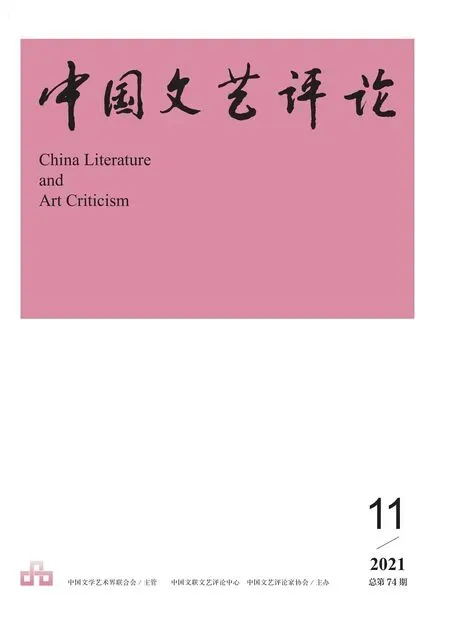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批评话语和价值构建
范志忠 潘国辉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的生态。由于电影生产的集体性制作和电影影院观影的封闭性,其社交距离的短板在疫情的冲击下暴露得尤为明显,电影生产和消费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悬崖式的断裂和下滑,流媒体的乘势而上更是进一步加剧了电影的危机。很显然,电影的这种危机势必进一步动摇乃至瓦解电影批评的生存空间。
当下,中国电影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格局中。由于国家疫情防控得力,中国成为在疫情危机中全球最早复苏的电影市场,2020年,根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中国电影以204.17亿元总票房第一次领跑全球电影票房榜,其中国产电影的票房为170.93亿元,占比高达83.72%。2021年,根据“灯塔专业版”统计,截至10月10日,中国电影年度累计票房业已突破400亿元,领跑全球单一电影市场,其中年度票房排名前十的电影中有八部是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市场的强劲复苏以及对全球电影市场的引领客观上呼吁着中国电影批评应该大有可为。
一、电影批评的现状与舆论场域
1.“新主流”“疫情”“流媒体”“电影强国”成为批评关键词
电影作为通俗易懂的大众艺术,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湄公河行动》《战狼Ⅱ》《红海行动》《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等作品强势崛起,从不同的视角演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艰辛历程和辉煌业绩。这类被命名为“新主流”的电影,以新的题材开拓、新的审美表达和新的工业化制作方式,突破了长期以来“主旋律往往不商业、不艺术;商业片往往不主旋律、不艺术;艺术片往往不商业、不主旋律”的固有面貌,改变了一段时间以来主旋律影视叫好不叫座的格局,在赢得口碑的同时赢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引起了电影理论界和批评界的高度关注。1999年理论界首次提出“新主流”这一电影概念,《当代电影》在2007年第6期设立专栏,探讨中国电影形成主流态势的生存环境及发展策略;2008年第1期又推出“本期焦点:新世纪主流电影的新形态与新格局”专题,分别刊登学者对主流电影的阐释和访谈。此外,诸如《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电影专业期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中国电影报》等,也纷纷刊登众多文章,研讨和评论“新主流电影”的内涵与价值。如《文艺报》在2018年1月10日刊文《信心》,文章认为“中国的‘新主流大片’正在形成,这包括了制作规模、内容主题、审美情趣、情感认同等各个方面。从世界范围看,除好莱坞之外,目前只有中国才具备出现这种主流大片的可能,这意味着建立一个有别于好莱坞的也有别于西方电影文化的新电影文化和电影产业系统是完全可能的。”新华社2021年9月30日刊文《新主流电影次第开花》,文章认为《我和我的祖国》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为轴、《我和我的家乡》以不同区域为序,《我和我的父辈》则以代际为章,更加聚焦个体与家庭的关系,并从家庭伦理出发勾画时代精神谱系,“‘我和我的’系列反映了新主流电影的一个创作趋势,就是从‘由宏观看微观’转向‘由微观看宏观’——国家性和民族性虽然是主题,但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回归到了人,以及人与时代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重构了世界电影的格局与生态,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和批评的另一热点问题。饶曙光、兰健华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的高峰之路与世界电影新格局》一文中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将全球的电影行业推向了至暗时刻。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社交距离的限制以及消费者的消费模式转变,电影产业将被迫进行深度结构性的改革,这对电影的生产格局和创作理念都将带来深刻影响。文章认为:“如将疫情影响作为对电影产业进行深度改革和调整的契机,或可对中国电影高峰之路的路径进行当下性的优化和调校,从而助推中国电影在后疫情时期顺利向电影强国目标迈进,并重塑世界电影格局。”陈旭光、张明浩在《中国电影报》2020年6月3日刊文《“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宣发营销与创作问题的若干思考》,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在给电影行业带来严重危机的同时,也将促使业内加大力度在电影的宣发营销和创作上另辟蹊径,并积极探寻借力互联网新媒介,实施“影游融合”、全媒介、跨媒介发展的电影工业美学道路。与此同时,2020年春节档中的《囧妈》因疫情暴发、影院关停转而与流媒体深度合作,大年初一开始在流媒体平台免费放映,引发了巨大争议,流媒体崛起对电影行业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王伟、檀秋文在《流媒体与线上放映:“电影的终结”与新生》一文中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流媒体的线上放映不仅对身处寒冬的电影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且意味着电影行业将被迫面对“存在还是毁灭”这一“电影之死”的问题。马瑞青在《美国流媒体平台与非院线电影的兴起和冲击》中,则以美国奈飞(Net fl ix)这一流媒体平台为例分析在线视频流媒体技术的诞生,在拓展电影的“非院线”发行渠道的同时,又由于其同时介入影片的生产而衍生出新的“非院线电影”内容,并由此对传统院线电影产生巨大挑战。孙承健在《被数字视觉化了的世界:虚拟制作时代电影的身份危机》一文中指出,“当下正在发生的数字视觉技术革命,对传统电影本体观念所具有的颠覆性则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进入虚拟制作时代之后,一系列涉及创作实践的变革正在发生。一方面,光学成像技术的主导地位正在被数字视觉技术所取代;另一方面,虚拟技术与数字资产的开发,已开始将当代电影从传统的、以再现现实为主导的发展路径,引领到以创造和构建新的数字化视觉愿景与视觉神话的创构性(creativity)为主导的发展路径之中。”
虽然当前中国电影取得了“看上去很美”的成绩,但其工业化、国际化程度和好莱坞相比,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学界因此加强了对“电影强国”问题的探讨,提出了新的引导路径。厉震林在《新时代、新现象与中国电影新路径》一文中指出,“需要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电影美学的‘用力过猛’现象。”尹鸿、陶盎然在《从走向世界到影响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一文中认为,“中国电影则在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过程中进入了一个试图创造世界‘新体系’的阶段。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中国从走向世界到影响世界甚至试图改变世界的过程,既证明了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甘于既存的世界体系而试图发挥更大的全球作用。”司若、姚磊在《如何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一文中认为,“虽然我们在疫情之下特殊的全球电影产业格局中凭借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人口红利以及政策优势拿到了‘看上去很美’的答卷,但与好莱坞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相比,中国的电影工业化之路仍然道阻且长,只有认清差距,夯实基础,才能以‘不变之态’迎‘万变之局’。”饶曙光、王曼在《电影强国建设视野下的国际传播》中对电影强国的建设提出期待,“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早日打造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用中国智慧、中国精神推动中国电影由大到强,让中国成为包括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强国”。
2.互联网生态下资本绑架电影创作与批评,舆论场乱象堪忧
很显然,针对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新主流创作以及流媒体冲击下电影产业发展的新特点,我国电影理论和批评界体现了理性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洞察力,在学术期刊和各大媒体努力发声,对推动中国电影的创作和产业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影这种专业的研究与批评,往往体现为学术界自身的探讨,或者有关方面组织的学术界和业界的对话,其影响力更多局限于学术界和业界,对于公众的影响力显得严重不足。或者说,在当前中国电影的批评话语中,显然存在着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两个舆论场域。如果说在学术界这一舆论场,中国电影的研究与批评针对现象与热点问题能够努力发声、积极引导,那么在社会大众舆论场中则是频繁“失声”,呈现出创作和批评断层的怪象,电影的批评话语因此让位于网络媒体或自媒体,其舆论场也因此被资本所绑架和引导。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媒体或自媒体的兴起促使了电影批评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但是在这个开放场域,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利益陷阱,那便是资本进驻舆论,逐步渗透引导进而控制舆论。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大,电影数量增加,各电影之间的营销竞争异常激烈。评分高低、口碑好坏一定程度上影响电影的票房走势,因此很多电影公司特别注重电影打分。为了争取排片,某些公司雇佣“网络水军”在各大网站评论打分,无原则地哄抬或贬低某部作品,严重破坏了电影批评的舆论生态。
编剧宋方金谈及影视行业的现状时提到:“影视行业已经被居心不良的资本绑架,我们有一大堆产品,没有作品;有票房,没有‘心房’;有大数据,没有审美依据;有收视率,没有回头率。”随着时代发展,“饭圈”现象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饭圈”群体在网络上谩骂互怼、应援打榜、举报无边、人肉搜索、混淆是非、网络恐吓……严重扭曲了价值观,影响了舆论生态。应该说,国内“饭圈文化”的形成,跟韩国、日本等的“选秀”热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究其根本,“饭圈文化”是商品经济时代发展的产物,是技术、产业和资本共同合力的结果,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操控下的流量作祟。曾经“轰动一时”的“锁场”与“反锁场”之间的斗争便与“饭圈”密不可分。2017年由杨洋和刘亦菲主演的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上映,这部电影有着“流量明星”、IP等热门要素,称得上是粉丝经济时代的“典型代表作”。但电影在上映几日后票房急转直下,主角的粉丝为了维护偶像的声誉和利益,于是展开了一场规模大、组织性强的“锁场”大战,造成了电影火热的假象。当时影院也联合反击,实施“反锁场”。客观地讲,这部电影从故事内容到画面特技都表现一般,但这种失去理性的“锁场”行为,既不利于电影市场的稳定,严重影响了电影市场生态的平衡,也不利于明星演员自身的发展。
在这种“饭圈文化”的影响推动下,很多电影围绕着“饭圈”拥护的“流量明星”进行创作、生产、销售,这些流量明星片酬暴涨,导致薪酬体系不合理,使得电影创作生态失衡。媒体关于“流量明星”的负面报道有很多,比如天价片酬、滥用替身、不背台词等。从电影创作生态角度讲,一部电影的创作经费是有限的,演员拿走了天价片酬,那么分配到编剧、导演、摄影、后期等核心创作层的资金便不足,创作者缺乏创作动力,必然导致整个影片的质量水准大打折扣。究其根本,天价片酬现象的出现与盲目资本逐利、媒体夸大事实博人眼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依然是粉丝经济下的畸形产物,贻害无穷。因此,无论是“饭圈”“流量明星”,还是“天价片酬”等现象,反映的都是当下电影创作、批评被资本绑架之后所形成的一种触目惊心的畸形现象。
二、传统影评与微媒体、自媒体影评
1.微媒体、自媒体成为当下电影批评的重要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兴起,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拥抱互联网”的时代。当下,网络影评已经成为电影批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现了“微媒体”批评和“自媒体”批评等新的影评生态。微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发布的主要是影片评论,包括“网络吐槽”“豆瓣打分”“弹幕文化”等。从根本上说,这种网络批评不仅仅是一种审美鉴赏活动,更是一种娱乐式的互动参与,批评也由此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与传统的纸质媒体相比,网络影评拥有更广泛的参与者,覆盖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海量评论内容,因此其作者与受众的参与度以及影响力,显然都是传统影评所无法比拟的。
网络这一虚拟空间有着时效性强、互动性强和多媒体性等优势,扩大了批评的场域,使得批评不再受制于载体,不再有传统批评的门槛与限制,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公共开放的场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人人都可以成为影评人。但网络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使得电影批评变得多元化;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把关,出现了很多非理性的批评,导致批评陷入巨大的利益陷阱。2016年年底《长城》《摆渡人》等电影曾不同程度地被恶意刷低分,与之相伴的还有言语谩骂和人身攻击。这种非理性的虚张声势、恶意打分,严重误导了观众的审美判断,破坏了电影批评的伦理规范和舆论生态。
从传统电影批评到微媒体、自媒体批评,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变化,更是批评主体和批评话语的巨大变化。从职业到非职业、从实名到匿名、从建构到解构、从统一到零散等等,这些都是新媒体影评产生的新特征。微媒体、自媒体平台的出现与兴起,在对传统的专业电影批评造成一定冲击的同时,也为大众影迷开辟了影评写作渠道,活跃了电影批评。自媒体使得电影批评由原来的“点对面”的单向传播变为“面对面”的多边传播,并呈现出时效性强、短而灵活、简单直接、视觉图解、互动性强、自由度高等新的特征。可以说,豆瓣、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批评在电影创作和电影观众之间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评分网站越来越影响着观众的选择。
“我们和工具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是双向的。就在技术成为我们自身的外延时,我们也成了技术的外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利益诱惑和资本的操控下,影评被商品化了,自媒体平台沦为资本操控的场域,很多评论家、影评人沦为媒体的附庸。当今,各个电影之间的营销竞争尤为激烈,制片方极为关注电影的评分,其中一些制片方花钱雇佣水军在自媒体平台上对自己的影片哄抬宣传、虚假造势,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实施恶意差评、诽谤诋毁,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人情批评和红包批评等。种种乱象使得电影批评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和主体性,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陷入价值失衡、伦理失范的泥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今天观众已经不再是电视时代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喧闹无序的大多数”。
2.传统影评发声不够,影响甚微,面临重大挑战
当网络上的电影批评暴露出平面化、碎片化、情绪化等诸多严重问题时,专业的深度影评依然要回归到专业的学术期刊。巴赞在电影批评方面曾主张:写作平台必须是专业期刊,而不是以明星八卦为主的通俗刊物。作为众多高校师生科研成果重要考核指标的CSSCI来源期刊,目前在电影领域只有《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三本专业期刊,这给电影批评的学术空间造成了很大限制,而且就这三本期刊来看,在电影批评方面也没有给出太多的篇幅空间。我们对近三年(2018年至2020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的电影批评发文量进行了统计,发现这三本专业学术期刊电影批评的发文量占各自总发文量的4%、13%和1%(见表1)。

表1
另外,传统电影期刊的时效性经常受到出版印刷时间、影评人创作时间、期刊编辑部审稿周期的限制,出现了作品超前、影评滞后的现象。很多电影上映后,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比较客观深入的电影批评。就当月上映的电影来说,评论文章往往不能及时刊发。我们将截至2021年10月的中国电影总票房排名前几位的电影的评论刊发日期与电影上映日期做了对比统计,可以发现,没有一篇评论是在该电影上映当月刊发出来的(见表2)。因此,传统影评对受众引导存在滞后性,很难在一定时间内和电影创作者、观众形成有效对话。

表2
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传播特点,《当代电影》《电影艺术》《中国电影报》等学术期刊、报纸近几年一直在努力搭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将滞后有时差的学术评论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努力解决学术期刊专业影评的时效性问题,力争在电影上映初期受众便能在微信公众号里看到有深度的评论。电影《长津湖》于2021年9月30日上映,10月1日当天《电影艺术》杂志便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了专业的学术批评,有效解决了时间差的问题,体现出专业影评的权威性和引导力。
在电影工业发达的美国,影评人行业具有产业化的特点,其层次多样、体系庞大、分工明确,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受众黏性也比较高,因此批评的声音能一直引导着受众。这种良性引导与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大型报纸都开设电影板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等。建立电影与观众的连接是影评的起点,影评的核心任务是完成电影文本有深度有内涵的信息传达。近年来,中国很多主流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也在开辟影视评论专栏,针对当前影视乱象发声,积极引导受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是又一次思想文化转型,中国社会及其批评进入一个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话语,以各种‘新潮’理论为边缘话语的众生喧哗的‘杂语’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批评舆论场和社会大众舆论场之间的失衡现象,在影评领域暴露得更为充分。针对当下的互联网影评乱象,电影专业批评不是没有发声,发声也不是没有力量,而是这种声音很难进入到观众的视野,更多时候成为了电影批评家之间的“自说自话”。从内容来看,当前很多电影批评呈现出越来越理论化、学术化的倾向,使电影批评由生动感性变得晦涩难懂、高深莫测。甚至有时一些批评家为了彰显批评的“深度”,使用晦涩难懂的新概念,使“专业性的电影批评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内循环的知识生产活动”,其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当前新媒体处于一个语态变革时期,“卖萌”和“接地气”成为两种主要的语言表达形态。同样,电影批评也需要语态变革,要想让深度的、专业的电影批评走进大众视野,并起到引导作用,最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是批评的理论化和学术化。一个好的办法便是让电影批评在了解观众心理以及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讲人话”“接地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电影批评“发声”,并进入大众视野,从而引导大众。
面对当下传统纸质媒介和传统影评人受到的冲击,主流媒体的自媒体化、专业学术化的批评和业余批评形成合力双向互动,或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影评人要“从‘知道分子’向知识分子蜕变……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肩负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和情怀使命”。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批评家和学者要学会自身的转型,积极适应并运用新媒体技术。传统影评那种长文本的写作已经很难激发大众的阅读兴趣,而那种短小精悍的批评更适应移动媒体的阅读,因而更具有生命力。电影批评要打破传统批评字数限制的桎梏,更注重内容的深度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只有这样,电影批评才能与时俱进,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三、电影批评的反思与价值重构
1.重构电影批评与创作的对话关系
电影批评要重振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必须澄清、辨析长期以来笼罩在电影批评领域里的种种错误认知和做法。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电影批评作为一种理性主导的思维方式,能否与以悟性和直觉为主导的创作构成对话关系?
对艺术作品而言,它是完整、独特、不可解析与复制的。换句话说,优秀的文艺作品虽然可以通过批评拆解出结构、语调、意象、隐喻、神话等元素,但却无法按照批评所分解出的这些元素重新组合成一部新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电影批评对创作而言是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是不可能有什么积极作用的。
但是,作为理性判断的电影批评,完全有可能以其理性的光辉照亮感性的创作所难以达到甚至无法企及的广度与深度,从而提供一份充满理性力量的电影作品诊断书;同样,作为感性的电影创作,也只有以电影批评为诤友,才有可能最终抵达仅凭感性力量而无法抵达的艺术高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赞曾发自肺腑地说,“如果说评论是电影的良知,那么,电影正是借助评论而对自身有了自觉意识。”电影导演陈凯歌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国电影需要更多冷峻影评家》,也认为,“以电影为艺术的时代已经逐渐消亡,但电影不会消亡……中国电影在今天自创新格,除了创作者,还需要评论者”。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曾有过两次电影批评的黄金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电影批评与当时的电影创作构成了对话关系,创作为批评提供了新的问题和话题,从而引发了批评界的强烈关注;而批评则为当时的电影创作大声疾呼,鸣锣开道,推动了电影创作走向繁荣。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剧了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人成立了影评小组,在当时的上海《申报》“电影特刊”、《时事新报》“电影时报”和《晨报》“每日电影”等开设专栏,开展电影批评,关注电影的社会价值,呼吁电影创作直面现实人生。作为中国电影批评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左翼电影批评,直接影响了郑正秋、蔡楚生等人的电影创作,涌现出《姊妹花》《马路天使》《桃李劫》《渔光曲》《十字街头》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其中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在上海创造了首轮连映84天的纪录,并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电影大师费穆曾经这样评价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到现在能担当起文化任务,从《火烧》、《大侠》之中能有今日正确的进展,电影批评者有着极大的功效。现在电影在中国,已经是相当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现象之一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奇迹”。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巨大转型的新时期,中国电影批评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诸如“电影的戏剧性”“电影的文学性”“电影美学”“电影本体”等话题,都曾引发广泛讨论。白景晟的《丢掉戏剧的拐杖》、张暖忻与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一系列解放思想、带有革命意义的文章,引发了强烈的争鸣与热议,并对当时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学者指出,当时导演“带一部新片上北京,第一站是电影局,取得放映证;第二站是电影发行公司,为了要钱;第三站就是影协,听取批评家的意见,为影片的艺术质量定位”。在批评为创作鸣锣开道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创作迎来了井喷式爆发,涌现出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骆驼祥子》《城南旧事》《乡音》《老井》《黄土地》《红高粱》等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的优秀作品。
因此,电影批评是否具有价值,关键在于批评本身是否具有价值。参照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种形态,我们可以把对电影的批评研究同样区分为关于电影的社会、历史和时代关系的外部研究,以及关于电影的文本叙事、隐喻象征的内部研究。我们认为,新时代要构建中国电影批评的价值体系,至少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从电影的内部研究而言,电影批评应该具有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能够准确地诠释电影文本叙事、结构、隐喻和象征,能够敏锐地发现电影文本自身的独特价值和艺术创新,同时也能够尖锐地指出电影文本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只有这样,电影批评才有可能激发或唤醒主创和受众的共鸣或共情,才有可能令他们感同身受,进而影响他们对电影的创作与解读,使他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判与反思。其二,从电影的外部研究而言,唯有从世界电影发展的角度出发,立足于人类科技和文明的高度,才有可能发现电影创作与生产中存在的痼疾与问题,才有可能鼓励呼唤电影创作的创新思维,才有可能推动电影工作者创作出真正弘扬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2.电影价值构建的理论资源与保障机制
当下电影批评和创作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远,创作面对批评“敬而远之”,批评被束之高阁,二者很难实现有效的沟通和对话,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电影理论界和评论界没有建立起符合当下中国国情的理论话语和批评体系,致使电影批评失去了价值构建的力量。要想重振电影批评的价值观、建构中国特色的电影批评体系、发挥批评和创作的对话功能,必然需要借鉴当下中国电影的理论资源和生产实践。
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共同体美学”和“电影工业美学”成为中国电影的三大前沿理论。胡智锋从“战略观、文化观、美学观、创作观和教育观”五个方面梳理出“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的理念和主张;饶曙光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阐释“共同体美学”,“在宏观层面,它倡导建立整体利益观、共同利益观、长远利益观、平衡利益观……在微观层面,‘共同体美学’聚焦影片中真实的人物、人性、人心、人情,强调与观众产生共情、共鸣和共振”;张经武则从文化与美学的角度,将“电影共同体美学”的核心要义概括为“‘尚同’‘存异’‘崇和’‘共美’”;陈旭光在“电影工业美学”的阐释中侧重于“理性”“标准”“规范”“平衡”“折中”“平均”等关键词。由此可见,这三大理论的共性便是当代电影学者以一种敏锐的洞察感知能力,站在时代前沿,从创作生产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当下中国电影生存发展的需要,为使中国电影走出发展困境从而走向电影强国提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智慧。这些务实的理论体系,有着一致的文化价值追求与美学意蕴期盼,并且在历史事实和文化渊源上都存在着合理性。近年来,尽管电影的观众群体和消费需求发生重大变化,但我们依然看到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韩延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曾国祥的《少年的你》等影片不仅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还在情感上与观众实现共情。这与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美学观”中的“内容讲求伦理美”、电影共同体美学中的“强调与观众产生共情、共鸣和共振”、电影工业美学中的“诗性内核”实现了不谋而合。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当下中国电影丰富的实践。”当下,中国电影票房猛增,但是电影工业基础依然薄弱,视觉技术特效与好莱坞相差甚远,制约着中国电影的长远发展,因此学界对电影“工业化”的呼声一直不断。前文提及,电影的外部研究要立足于人类科技和文明的高度。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科技助力视觉奇观成为吸引观众、获取票房的重要因素,而电影是否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与当下社会产生互动,则决定了电影是否能够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电影与市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电影与观众的关系,而电影与观众的关系问题是电影美学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不能只注重工业层面的画面奇观,更应该注重其美学精神意蕴和中国故事的表达。“中国电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学建构,有了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审美需求。”近几年,国内很多电影除了在工业制作上下了大功夫,还在美学价值观的表达上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例如,电影《红海行动》中“尊重个体、不负使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战狼Ⅱ》中“服从命令、顾全大局”的“战狼”精神、《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去流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都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平等、博爱、家国情怀和共同体意识。
值得强调的是,电影批评的价值构建还要从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中汲取营养。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不仅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理论命题,也是对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具有实践指导性的命题。无论是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美学观念,还是电影共同体美学“对中国传统美学、文化、思想的继承和转化”的理论学理性,或者是中国特色电影工业美学体系建构中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都在启示着我们传统文化资源是“无价之宝”,电影创作与批评应该从传统美学、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诚然,要推动电影批评真正实现繁荣,我们还要着力优化电影批评赖以生存的土壤和保障机制。毋庸置疑,高校师生和研究机构无疑是电影批评的主力军,但在现行的各种考核评估机制中,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评论者撰写电影批评的积极性。近期,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相关部门要做好支持保障,健全激励措施,可通过优稿优酬、特稿特酬等方式为文艺评论工作提供激励,改进学术评价导向,推动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重要文艺评论成果纳入相关科研评价体系和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制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相关评估和激励机制的改革到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跻身于电影批评的行列。
“面对电影界众多的‘新事物’‘新经验’,首先最需要改变的是电影批评本身,是电影批评家自身。”电影批评需要我们重审语境和重新出发,重新回归到对“电影是什么”的思考,思考电影作为商品、作为艺术、作为媒介的演变历史以及和当下产生的互动、碰撞,重新思考新时代电影批评对于创作者、对于观众、对于批评本身的重要意义。我们相信,在疫情冲击下的互联网时代,只要人类还拥有梦想,电影就永远不会消亡、就一定会浴火重生。而中国的电影批评,也将迎来第三次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