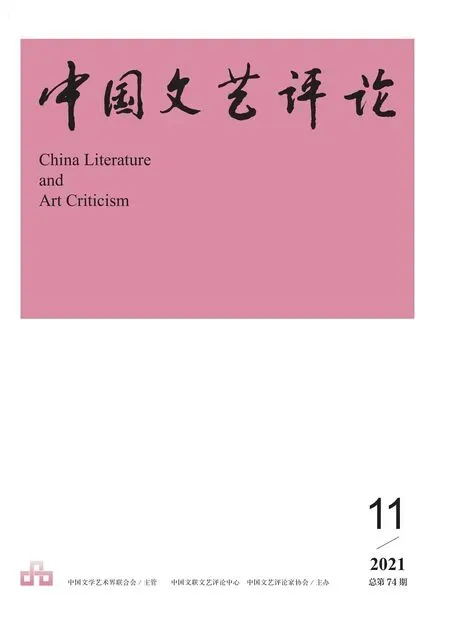融情铸艺 以情带声
——访粤曲艺术家黄少梅
采访人:罗 丽 黄静珊

黄少梅简介: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931年生,祖籍广东番禺石碁,著名粤曲平喉“星腔”表演艺术家,小明星(邓曼薇)“星腔”第三代传人,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政协委员。1944年,黄少梅拜“星腔”第二代传人李少芳为师,并向梁以忠、王者师、梁巨洵等名师学艺。1946年,黄少梅在广州首次正式登台,后曾到香港、澳门演出。1956年黄少梅以《子建会洛神》获得广州市第一届专业曲艺会演一等奖。1958年进入广东音乐曲艺团工作,同年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受到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接见。1963年,黄少梅以《花木兰巡营》获广州首届羊城音乐花会一等奖。1985年,黄少梅举办从艺40周年独唱会,是首位举办个人演唱会的粤曲表演艺术家。1987年,她代表广东曲艺界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多年来,黄少梅为国内外数十家唱片公司灌录音像制品,作品在海内外广泛传播,获得第九届中国金唱片大奖。
2021年8月的某个午后,笔者沿着广州荔湾的狭窄长巷寻路而往,前去这个被誉为“粤曲之乡”的老城区“西关”,拜访德高望重的黄少梅老师。尽管笔者生于斯长于斯,但若没有带路人,还真不太容易找到她这隐藏于深巷之间的寓所。拾级而上,叩响门板,自报家门,高寿九旬的黄老师应声而出,热情招呼,把笔者引进了她朴素而温馨的家中。墙上的几幅人像旧照,一整墙的工笔寒梅,一副对联、几座奖杯,无需过多修饰,已充分展示了这处居所主人的职业与志趣。
一、艺海无涯 转益多师
罗丽、黄静珊(以下简称“罗、珊”):
黄老师,您好!一直很喜欢粤曲“星腔”,十多年前曾有幸在舞台下聆听您的现场演唱,真的是久久不能忘怀。这些年您深居简出,已经甚少登台,这次能采访您,十分荣幸。作为第三代“星腔”传人,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星腔”艺术家,能否请您谈谈个人的学艺经历以及师父李少芳对您的教导?黄少梅(以下简称“黄”):
我12岁开始学艺,1944年从艺至今,已有77年。自小,我爸爸就喜欢带我去看戏,为此我喜欢上了粤剧、粤曲。当然,我爱好广泛,也喜欢听时代曲,是白光的歌迷。不但如此,就连做法事的“喃呒先生”唱的“喃呒”,虽然不知道唱的具体内容,可我也觉得很好听、很喜欢。可以说,从小喜欢音乐,是我最终走上文艺道路的重要原因。我家中无人涉足艺术,是机缘巧合让我有机会拜于师父门下学艺。早年,我爸爸喜欢听广播,我也跟着听。有一次,小小的我听到小明星的粤曲《夜半歌声》后非常喜欢,于是就在家里模仿着瞎唱起来。没想到,这一唱却“惊动”了住在隔壁的简伯。他在得知我喜欢“星腔”后,就表示可以带我去找“星腔”传人李少芳学艺。
不久后,李少芳(按照歌坛习惯,人称“芳姐”)到西门口的祥珍茶楼唱曲。休息的时候,简伯就带我去见她。我当时还小,见到生人都很害羞,只敢躲在简伯身后轻声叫了声“李姑娘”。见面后,芳姐首先要试试我的声音。那时候的我不知天高地厚,唱了《夜半歌声》《一代艺人》。一直唱到芳姐说可以了,我还回答说:“我还会别的,还可以唱下去。”
回家后,我就跟父亲提出要拜师学艺。当时拜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师父交学费;另一种是将来登台演唱,有“茶价”(收入)时师徒对分,这叫“帮师”。可是,我当时家里穷,连一件像样的衫裤都没有,就连去见芳姐时,我也只穿了一套妈妈的“阴丹士林”才敢出门。因此,我最终选择了以“帮师”拜师学艺。拜师当天,我捧着一块烧肉,拿着元宝蜡烛,拜了天地,又向师父鞠躬行礼。芳姐说:“我排第三,你叫我‘三家’(意为三姐)就行了。”就这样,我拜李少芳为师,开启了艺海学徒之路。

图1 黄少梅童年照
罗、珊:
“星腔”是广东曲艺粤曲“平喉”唱腔中的一大流派,其曲式、曲调、节奏、旋律自成一格,别具韵味。“星腔”由小明星所创,李少芳老师承继后,又传给您。拜师之后,师父芳姐是怎样教您唱曲的呢?
当时,师父教我的第一支曲是《恨海葬痴心》。最初,我听留声机播这首曲的时候,觉得很容易,但是到了自己学唱时,才发现很难。尤其是那句【二黄】“缘偏短,恨偏长”,拉“尺”字和“上”字腔。这句【二黄】空口唱还好,一打板就唱不了,唱到了又打不到板。由于师父只是比我大了十岁,当时才二十二三岁,正是当红时,平日非常忙碌。因此,她担心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教导我,为了不耽误我,她便希望推荐我到其他地方学习。可我已痴迷于“星腔”,无论如何都死心塌地地跟着她,下决心苦练把曲子学会。
罗、珊:
当时您除了跟师父芳姐学唱曲,您还跟谁学过音乐呢?黄:
1945年,音乐家梁以忠回到广州,芳姐带我去见他。尽管那时候我已经学习唱曲一段日子了,但平时师父教学都是口传心授,我并没有试过配合乐器伴奏演唱。因此,当梁以忠用小提琴伴奏,让我跟着演唱时,我只能傻傻地听着小提琴的旋律,却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口唱。由此,他们才知道,我还不会跟着音乐伴奏演唱,必须要让我补上这一课。当时,梁以忠就住在荔湾宝华路,他家地方虽然小,但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找他学曲,其中包括师父、梁瑛、冼剑丽、何飞霞等已经成名的唱家。每次芳姐去他家上课时都会带上我,我旁听着也渐渐学到了很多东西。
随着梁以忠忙于主理华南茶座后没时间继续教学,芳姐就送我去她的“私伙头架”(私人音乐演奏员)王者师那里去学习音乐。半年后,王者师也去开茶座了,芳姐又送我去梁巨洵那里学唱曲。稍后,梁巨洵在西门口的祥珍茶楼做主理,就把我带去“出台”(演出),有他在一旁配合,我演唱时就不那么紧张了。
罗、珊:
那是您第一次正式演出吗?可以说,由那之后您就开始了在茶座歌坛的演唱生活,当时的情境是怎样的呢?黄:
其实,最开始我爸爸是不同意我“出台”演唱的。在老一辈的观念里,女孩子抛头露面唱曲,多少会令家族脸上无光。但在我的哀求之下,他最终还是拗不过我,同意了。我还记得自己当时非常害羞,演唱时一直拿“曲纸”挡着脸,不敢看台下一眼。那时候的演出不会提前排练,我和音乐师傅之间的合作都是靠“出手影”(打手势)。我爸爸还是很不放心我“出台”,于是白天做生意,晚上就跟着我去茶座。一直到我三十多岁时,他还是会陪着我。一来他不放心,怕我学坏;二来他也喜欢听粤曲,一举两得。1947年,我和芳姐一起到香港高升、先施、莲香三间茶楼唱曲,边唱边学,在实践中磨练演唱技巧。在香港的茶座演唱是计时间的,而在广州的茶座演唱则按曲目计算。当时,我很不习惯香港的生活,哪怕张月儿的老师徐桂福一再挽留我,半个月后我就回了广州。1950年,我也到澳门生活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在音乐家陈卓莹的大哥陈鉴波开设的淘声音乐社里学习。1954年,从澳门回穗后,芳姐组织广州曲艺界在戏院做专场演出,我便跟着她边演边学,以勤补拙。
罗、珊:
芳姐是唱家,梁以忠吹、弹、打、唱、撰兼擅,而王者师、梁巨洵则是音乐家,他们的教学各有什么特别之处,对您都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呢?黄:
我的师父有很多,有“一音之师”,也有“一字之师”。李少芳是我的开山师父,但还有很多人教过我。只要有人肯教,我就愿意学。说起来,我是解放后由党培养起来的。我从澳门回广州之后,参加过中南汇演,登台也没那么紧张了。芳姐的先生仇洪涛是音乐师傅,平时我们练曲时,他来伴奏,因此在短时间里我进步得比以前快。
图2 黄少梅与李少芳合影
师父叮嘱我,“清歌”(清唱)一定要“搭线”(音准)。因为清歌没有音乐伴奏,只要稍微发力过猛就会“飙高”,发力不足又容易唱“低”了。这就要求演唱者“耳轨”(听音)要准。芳姐是出了名的音准好、“叮板”(节拍)稳。她叮嘱我,一定要控制好发声的力度,不管是否听得到伴奏音乐,只要感觉自己力度到了,就不再发力,听音要准,声音发出来也要准。
多年后,曲艺作为文艺轻骑兵常常在场地空旷的田埂地头演出。在这样的地方演出,条件简陋,音乐经常听得不是很清楚,很多人就一个劲儿地发力唱,结果就容易“线面”(跑调)。只有我一直发音准确,气息稳定,也不走音跑调。这些都多亏早年间打下的扎实基本功,这既是师父教的,也是我自己练出来的。

图3 黄少梅1956年演出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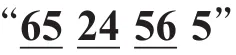
后来,王者师拉小提琴给我伴奏,梁巨洵教我如何听音乐伴奏演唱。半年时间,我慢慢学会了线口(调门)和节奏,也学会了在音乐的伴奏下演唱。待我完整掌握了几支粤曲后,登台自然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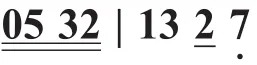
罗、珊:
除了专攻“星腔”,您还学习过其他名家唱腔吗?您最大的学习体会是什么?黄:
芳姐的优点是她经常让我多向其他人学习,又劝我多学点传统曲目,还带我去向苏朗天、熊飞影、叶孔昭几位师父学习了《宝玉怨婚》《月下追贤》等唱官话的古老曲。苏朗天和叶孔昭是玩音乐的,熊飞影是唱“大喉”的,我们叫她“五家”(五姐),通常一支曲由几个老师教,他们教一段,我学一段。虽然现在的粤曲不唱官话,但是这些古腔是很好用的,譬如《宝玉怨婚》的【十字中板】,后来就被我运用到《梁祝仙缘》里了,这就叫“古为今用”。20世纪50年代,许多外省的兄弟曲种剧种也来广州演出,师父就让我去增长见识,融会贯通。1956年,师父还让我去跟失明艺人梁洪学唱南音《祭潇湘》,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我的艺术积累。
过去,很多唱曲的都不懂音乐,甚至演奏的人也有很多是不懂乐理的。但是他们在演唱和演奏时又很灵活,遇到各种变数时很懂得“执生”(应对)。我记得,1980年前后我在中唱(中国唱片总公司)录《秋坟》,当时是骆津做“头架”(领奏)。我们根本不用排练,也不用看谱,一次就过,因为大家都很熟悉音乐,彼此之间也有默契。其实,这些既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也是在多年表演中积累的临场应变能力。
二、为舞台而生 为观众而唱
罗、珊:
20世纪30年代,歌坛蓬勃发展,粤曲迅速崛起,占领歌厅、茶座,粤曲“平喉”“子喉”“大喉”三大唱腔鼎足而立,在曲坛各领风骚。开始登台的时候,您都是在茶楼、赌场、歌厅中演出的。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专业的演出团队,您又是怎样加入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呢?黄:
1956年,广州市文化局组织了曲艺队,共分了三四个组,一组有四五个人,可以自由组合到市内各茶楼茶居唱曲。当时,芳姐被分在一组,我在二组,都没有固定工资,是按分数发钱。后经过工商业改造,发展到最高可以有1800元的收入。1958年,广州市文化局的华嘉局长多次动员我入团,开始我有点犹豫,不愿意受聘,担心会没有演出的机会。不久后,身边人纷纷加入,大势所趋,我便也参加了曲艺团,每个月50元工资,后来工资调到108元。罗、珊:
您进入曲艺团后,和在茶座时唱曲应该还是很不一样的,您能说一说其中的变化以及您个人的感受吗?黄:
1958年,我受聘进入曲艺团,团内有一团、二团两个分团。一团以音乐演奏为主,主要有方汉、刘天一等人,二团就是以演唱为主,演员主要有熊飞影、白燕仔和我等人。1949年后,我们主要都是排练现代题材的粤曲。那段时间的文艺政策受“左”的思潮影响,“星腔”长期受到冷落,就只剩下我和芳姐两个唱“星腔”的人了。但芳姐加入曲艺团后,同年被调到电台工作,再没什么机会和观众见面了。由于舞台上就只剩我一个唱“星腔”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自己能够登台的机会。
图4 1985年“黄少梅独唱会”照片
曲艺团成立后,团址设在中山纪念堂旁边,刚开始的时候演出比较少。到了1959年、1960年间,我们的演唱机会逐渐增多,经常上山下乡为工农兵服务,登台逐渐越来越多。由于观众反应热烈,团长便加场又加场,最高一年演出达到400场,几乎场场满座,每每唱到声嘶力竭。其实现在回头想,这样密集的演出安排对演员来说负担太重了。可那时候的我们觉得,演员的身份地位提高了,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加上演出确实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所以自己拼了命也要坚持在舞台上演唱。
我还记得,那时候经常唱到喉咙充血,又经常感冒,煲中药很不方便,只能去药店买感冒茶喝,真的是非常辛苦。曾经有一次我因为打盘尼西林过敏而晕厥,在医院短暂抢救后,又回到舞台继续唱,因为我不想让观众失望。有一次,我发烧高达41度,站都站不住了,但一想到舞台下观众一直在等我出场,我便硬撑着又站在了舞台上演唱。

图5 黄少梅1985年在平安戏院演唱《乡恋》
罗、珊:
“星腔”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观众们的喜爱,但也命运坎坷,您的演艺生涯也随之浮沉,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持续到什么时候呢?黄:
1949年后,“星腔”虽一直受到冷落,但并没有被公开禁止演唱。直到1963年,掀起了一场“‘星腔’能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论战,有一派认为“星腔”是靡靡之音,唱的都是才子佳人,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另有一派就反驳,提出小明星也唱过《人民公敌》,怎么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陈卓莹、李少芳、梁巨洵都登报表态,谈“星腔”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当然也认为“星腔”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英雄人物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嘛。这场论战虽然没有定论,但“星腔”在舞台上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少,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星腔”被认为不够硬朗,除了参加劳动之外,我再也没有机会上台,被迫离开舞台和观众。当时就有很多观众来信,问为什么没见黄少梅?其实,当时团里安排了我演唱现代题材的粤曲,半年排一首,一年半内我排了三首新曲。其中一首就是《农讲所里木棉红》,但彩排时却被认为我一开口就是“星腔”的风格,整体感觉太“软”了,不适合登台演出。
后来,团里的一位前辈方汉替我着急,他帮我想了个办法——排练时,我按上级要求的风格来演唱,等批准登台后,我再唱回“星腔”。多亏这招“狸猫换太子”,在1973年至1974年期间,我终于得以重返心里一直挂念的舞台,为观众们演唱了《红线金针》。当然,我还是不敢完全用“星腔”演绎,只是唱得婉转一些,带点“星腔”的味道。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方汉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不是他提出这个办法,让我有机会登台,“星腔”就可能要绝种。当时我复出舞台,还有人骂我是“牛鬼蛇神占领舞台”,但当我演唱《蔗香儿女》《念亲人》时,观众听到里面有两句“星腔”味道浓郁的【反线二黄】,都欢喜得不得了,可见大家还是喜欢“星腔”的。而我也在复出登台后,在观众身上找到了坚持的力量,也看到了“星腔”的群众基础。

图6 黄少梅在拍摄唱片封面的现场
“文革”结束后,整个社会氛围都在改变,舞台上也慢慢开始可以唱“星腔”了。1979年,我的《子建会洛神》在太平洋唱片公司录了唱片,但表现爱国主义的《花木兰巡营》唱得最多。1981年,广东省歌舞团赴香港演出,我们曲艺团有几个人获批“搭班”一起去。那时候,我已经几十年没去香港演唱了,香港观众非常激动,纷纷来到后台探班。不过,我为了保护嗓子,保证好的演唱情绪、状态,拒绝了会面应酬,一个人躲在更衣室候场。这次演出,曲艺团是“搭班”去的,能赴港演出的名额很少,领队加上演员和演奏员一行12人,连完整的乐队都凑不齐。为此,香港的冯华就无条件带了三位音乐师傅来帮我们的演出“拍和”(伴奏)。
因“左”的思潮,过去数十年“星腔”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这次赴港演出,虽条件有限,但我抱着“‘星腔’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信念,更重要的是怀着重返舞台与香港观众见面的激动心情,将《子建会洛神》这首曲完美发挥。观众太久没有听到“星腔”了,当我一曲唱罢,台下掌声雷动,他们很激动,掌声久久不息,我谢了三次幕。那天,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绕梁三日”,心潮澎湃。后来,2013年我拿到金唱片奖时的心情,都比不上当日观众的热情回馈让我激动。
三、融情铸艺 以情带声
罗、珊:
您第一次尝试做唱腔设计是《王十朋祭江》,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呢?您可以给我们详细讲一讲吗?黄:
那是大概1955年至1956年的前后。过去我们唱粤曲的,大都是把粤剧的主题曲改成独立的单曲来演唱。有一天,我和曲艺组在广州海珠路的擎天茶座演唱,珠江剧团的编剧莫志勤来探班。大家见到莫志勤就都追着他喊“五哥”,都想请他为自己写一首曲。那次,莫志勤给了曲艺队三首曲,一首是大喉演唱的粤曲《黄飞虎反五关》,一首是偏硬朗的平喉粤曲《林冲雪夜上梁山》,还有给了我的那首《荆钗记》的选段《王十朋祭江》。这个片段到我手上时还不完整,莫志勤就临时加了一段【恋坛】“恨煞那奸细,好盟约毁碎,遗恨绵绵,永久无尽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创作,我非常重视,于是正式邀请了珠江剧团的音乐名家黄壮谋帮我谱两段小曲,一段是河南梆子,曲词不改,音乐做调整,取名为【仿南调】,另一段是粤讴。粤讴过去我学过一点,本来想找师父帮忙“度腔”(唱腔设计),但是她刚好没空,我就自己来。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我就借鉴梁以忠教的【解心腔】,自己一个人反复琢磨,“度”(设计)了十几节,总之反复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莫志勤听过之后觉得很不错,恰好那时候北京电台来广州为一些“大老倌”(名家)录音,他就推荐我一起去录音了。我也为此完成了自己生平的第一次独立唱腔设计。
罗、珊:
这首《王十朋祭江》在谱新的曲的时候,您对唱词作过调整吗?为什么粤曲进行唱腔设计时常常需要调整词句?后面您还自己进行了《子建会洛神》的唱腔设计,具体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图7 黄少梅1987年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获奖照片
黄:
唱词基本没有改,但是在唱腔不顺的时候,有些字句也是要调整的,比如“江滨”的“滨”字拉不了腔,要拉“合”音,就改为“江头”;【反线二黄】中“伤脾”的“脾”字拉不了“尺”音,就请教莫志勤改成了“伤悲”,一共就改了两个字。当时,来自北京的录音师听了之后也很喜欢这首曲,便请莫志勤多写一首曲供我演唱。刚好梅兰芳的戏曲电影《洛神》很火,我们就决定写《洛神》。不过,《洛神》唱词的平仄与粤语不合,莫志勤就提出只写梦会的场次,名为《梦会洛神》。后来,我又提出改为《子建会洛神》,就这样把曲名定了下来。
《子建会洛神》写出来之后,我觉得里面的一段【合尺滚花】情绪出不来,就尝试“拉”(运腔)京腔。细想又怕有人觉得不合规矩,因此就改名叫【凤尾曲】,寓意龙头凤尾。新创的运腔处理,给我很大的创作自由度,怎么唱都可以。因此,曲目最后是以【双星恨】结束:“今生爱她愿已空”。到了试唱时,我发现“空”字怎么发力都是鼻音,没法“拉腔”(运腔),情绪也出不来。于是,我就加了“水向东”三字,转【昭君怨】结束。这样,整首曲所蕴含的情绪就出来了。
可以说,《王十朋祭江》《子建会洛神》这两首曲让我开始尝试自己进行唱腔设计,逐步摸索到“以情带声”的创作心得,进一步总结运用了“星腔”的演唱技巧。同时,两首曲也深受观众喜爱,让我扬名粤港澳。
罗、珊:
确实感觉到,黄老师尊重传统,又不会固守传统,而是站在艺术创作完整性的高度上,“以情带声”,不断调整唱腔,从而更好地塑造人物、抒发情感。那么在此之后,您开始了自己度曲创腔的历程,也多次获奖,1963年《花木兰巡营》在第一届羊城音乐花会获一等奖,1986年的时候,您又以《瀛台恨》获得广州市专业唱腔改革优秀奖。您可以谈谈这两首曲的特点吗,还有《瀛台恨》这首曲的改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黄:
《花木兰巡营》是曾浦生为我创作的。原来他根据粤剧创作的是“夜沉沉,人寂寂”一段。然而我不太满意,我认为,粤曲和粤剧不同,是以唱为主的。如果一开始就是士兵都入睡了,周围静悄悄的,就没法吸引观众。于是,我就要求改为开场点将,然后接花木兰深夜思乡,发现有鸟儿受惊飞过,原来是敌人袭营,最后准备迎战。我借鉴了常香玉的《花木兰巡营》里面的一段曲子让曾浦生参考,并起了个名字叫【宿鸟惊飞】,运用【流水板】重新编译。修改后,曲的第一句就是“身肩重任,自知责非轻,夜检哨点兵,巡营,传令为戒备宵禁应守职责,你等要领命”,使得花木兰的形象一下子就立起来了。可以说,唱了《王十朋祭江》和《子建会洛神》之后,我的创作观念有了积累,也产生了转变,所以才诞生出《花木兰巡营》。但是最难唱的还是《瀛台恨》。
《瀛台恨》由刘汉鼐撰曲(实际按格律填词),我自己“度腔”。后来,这首曲子获得了广州市专业唱腔改革优秀奖。但是,我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前后创作了十个版本。我还记得当初“度”这首曲时,我经常失眠,真的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状态,睡觉时也在想,想到了就马上写下来。演唱时,我不喜欢由音乐伴奏来“带”(定调),而是更喜欢由我来“给线口”(定调),让音乐伴奏来跟。其实,这是学小明星的,她的《孔雀东南飞》就是“秃头”带落(不用前奏)。不过,这要求演唱者音准要很稳,基本功要过硬,可见其难度。
罗、珊:
《瀛台恨》这首曲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图8 黄少梅演唱《瀛台恨》
黄:
特别之处在于,这首曲里变了好几个调。从【乙反清歌】的“我只好乔装改扮慰玉人”,接转【旧苑望帝魂】重复唱“慰玉人”时,要降调,随后【旧苑望帝魂】“见你愁思冷漠对孤灯,杨花雪后色尽褪”一句,“思”字又回到原调。短短几句,就跨了好几个八度,这样的处理,实际上就是按照“以情带声”进行的。罗、珊:
从您刚才哼的这几句,确实能让人仅仅通过旋律就能感受到情绪的起伏变化。黄:
我在演唱中,始终把“以情带声”作为首要原则。我凡是唱一首新曲,都一定会找相关的书籍作为参考,了解这首曲目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典故。为了唱好《子建会洛神》,我好不容易才在厚厚的史书中找到了关于曹子建的简短文字介绍;唱《啼笑姻缘》时,我就去买了张恨水的原著来看;后来创作《瀛台恨》,我又专门买了《瀛台泣血记》一书。只要有条件,我都尽量通过阅读文字资料去了解曲目的时代背景,这样在演唱时的情绪表达才能更准确。举个例子,同样是悲伤,《光绪皇夜探珍妃》和《瀛台恨》的情绪就很不一样。前者是生离,后者是死别,因此情感尺度的把握都大有不同。四、艺无止境 永不停息
罗、珊:
曾经有人评价您的唱腔既“洋”也“新”,您怎么看?黄:
很多年前,我在干校劳动时,就有人对我说:“梅姐,虽然我不太喜欢粤曲,但是你唱的粤曲我就能接受,你的粤曲很‘洋’。”当时我想,我从来也没去过洋学校,哪里来的“洋”呢?后来我想,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除了喜欢小明星,也喜欢听流行歌手吴莺音、白光的歌。还有当时很流行的西方电影《出水芙蓉》《魂断蓝桥》的主题曲,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另外,十六七岁的我很喜欢跳舞,经常瞒着我父亲和小姐妹去舞场跳舞。尤其是1947年我和芳姐去香港茶座演唱时,一有空就到那里的高级舞场跳舞,什么恰恰、伦巴啊,什么都跳,尤其喜欢跳伦巴,因此我对西洋音乐都很熟悉。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到澳门,有位音乐伴奏在弹钢琴时问我:“黄老师,要几个‘巴’啊?”我愣了一下,一般没有人用“巴”这个说法的,但我很快反应过来,说要两个“巴”。其实,“巴”是西乐的说法。如果我没去过舞场,不懂西乐,肯定答不出来。
图9 黄少梅20世纪80年代在澳门康伶曲艺会演唱
我的唱法被认为很“洋”,我觉得跟年轻时经常去舞场有关。那这种“洋”体现在哪里呢,举个例子,当时有首很流行的时代曲《街头月》。有些粤曲行家处理其中那句“我哋阿妈,真正仁慈”时,会把字咬得很“死”,但我会借鉴西洋唱法,唱起来“活”一些,显得轻松跳跃。再比如,创作《梦会牡丹亭》时,我请蔡衍棻创作时要融入流行曲《梦中人》的一段旋律,使得作品在旋律上更为丰富。其实,这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至于说“新”,主要我比较喜欢在创作中借鉴新曲调。1949年后,我的粤曲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新创的曲调。这些都得益于当时有很多外来剧种到广州来演出,包括河南梆子、陕西的碗碗腔等戏曲,给了我很多学习借鉴的机会。还有大量民族音乐,我都很喜欢听。我尤其喜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面的《江河水》,闵惠芬来广州演出的时候,我就站在台口,看她的弓法,看她是怎样将这首曲拉得这么有感情的。可以说,1949年后各剧种来穗汇演都开阔了我的眼界,对我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我在设计唱腔时都会不自觉地把新的音乐元素运用进去。
罗、珊:
可以举例谈谈您对粤曲、对“星腔”艺术的理解与实践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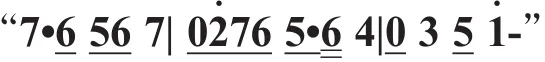
以前,艺人讲究“声、色、艺”。然而,小明星一来无“声”(声音条件先天不足),二来没“色”(长相一般),她就是靠“艺”取胜,尤其是依靠超凡的演唱技巧。“星腔”好听,但确实演唱技巧很难掌握。我自己唱的时候不觉得“星腔”难,到了教授徒弟时才知道。如“如此情魔如此劫,喜你入棺犹是,犹是碧玉无瑕”一句,需要在“情、魔、喜、棺、犹、犹、玉、无”八个字之间作气息处理。但我的徒弟们总是不容易唱好,原因是还没有掌握好“抢位”“偷气”的技巧。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星腔”的技巧是很不容易掌握的,这也是“星腔”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所在。“星腔”中隐藏了很多好的演唱技巧,需要不断有人来总结和传承。
罗、珊:
确实如此,这些年来,您也一直积极传授“星腔”,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收徒弟的?您觉得授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黄:
我是1987年才开始收徒的,第一个徒弟是叶幼琪,收徒的过程比较有趣。有一次,我到广州的文化公园中心台,刚好叶幼琪在台上唱曲。一曲唱完,台下观众都鼓掌说,“这是黄少梅徒弟”。我当时就觉得,连观众都这样认为,那我不收这个徒弟都不行了。事实上,她通过反复揣摩我的录音带,不断练习,“发音”(嗓音)、“发口”(运腔方式)确实和我的声音很接近。其实,我收徒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得唱“星腔”。她们的“发口”必须接近“星腔”,同时又得有改进空间,这样的人,我才肯收为徒弟。因此,这些徒弟大都是“录音带徒弟”,都是她们听熟了我的音像制品后,然后我集中点拨一下。我认为徒弟要似我,如果不像我,我收徒何用?你如果是唱别的腔,那我能教你什么?“星腔”婉转入味、细腻多情,很多人都喜欢学唱,但易学难精。现在“星腔”发展得不错,梁玉嵘是我徒弟,何萍是我师妹,两个人都已经在带下一辈了,“星腔”也算是后继有人,能告慰前人了。

图10 黄少梅2013年荣获中国金唱片奖
罗、珊:
在您看来,现在的粤曲演员最需要的是什么?黄:
首先,现在的人没有我们过去那么刻苦。以前,我们都是天没亮就起来练声了,然后什么都学,西洋也学,传统也学,盲公的曲目也学。现在,虽然我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但是我很注重听,新旧的歌曲都听。唱曲,是要多听、多学、多想、多练。我最喜欢听阮兆辉,他的南音很有味道。我对艺术是很痴迷的,也一直都很勤奋,什么都愿意学。我总结我自己的艺术经验,就是十六个字:“艺无止境,集思广益,专注艺术,永不停息。”我还很重视“艺德”,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我跟音乐伴奏师傅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互相尊重。其实,演员和音乐演奏员是唇齿相依的,有好的音乐伴奏从旁协助,演员就能在舞台上发挥得更稳定更好。所以我常说,我能拿到金唱片奖,有一半功劳是音乐伴奏师傅的。现在,有些“老倌”动不动就发脾气,这是不对的。演员要懂得自省,我演唱的时候发现有不对头,都要先自我检讨,为什么唱得不顺,是什么原因,而不会埋怨他人。
这一点,我是跟前辈张月儿学的。当年,她是红透半边天的“大老倌”,可她每次上台,都一定会对音乐师傅说:“唔该师傅兜住(请师傅您多担待)。”下台时就说:“辛苦,师傅。”这就是艺德,是需要每一位同行所重视修行的。艺德的高低,也决定了一个人在艺术道路上能否走得远、登得高。
访后跋语:
8月,正是羊城广州一年之中的酷暑时节,午后暴雨不但没有带来一丝清凉,相反让地气升腾,犹如蒸笼,让人大汗淋漓。然而,让笔者在这个酷暑时节,两次兴致勃勃前往拜访的动力,正是能与黄少梅老师畅谈粤曲唱腔艺术、感受艺海情真的宝贵体验。黄老师尽管已年届90,但头脑思路清晰,描述起当年往事时绘声绘色,讲解星腔演唱技巧时依旧声音清朗、行腔稳健。两次均长达数小时的访谈中,黄老师并没有年迈的疲态,相反始终洋溢着对音乐的热爱、对艺术的执着、对曲艺事业的真挚。这种融洽而富有精神滋养的交谈氛围,恰恰印证了她在采访中所提到的——好的艺术经历,过程都不会让人感到丝毫辛苦,那点点滴滴,都是一种享受。星腔、粤曲、音乐于黄少梅老师如是,访问她的这段经历于笔者亦如是。
采访人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