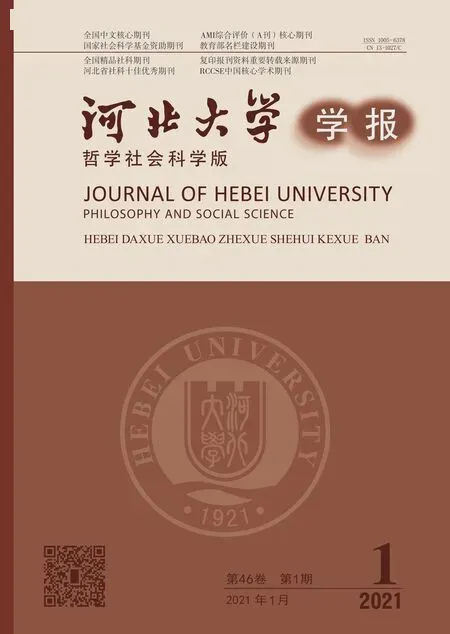赵弘殷显德三年行迹考辨
顾宏义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赵弘殷为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之父,后周时与赵匡胤同朝为官,任侍卫司将领,卒于后周显德三年(956),宋初谥曰宣祖昭武皇帝。虽然赵弘殷病死于宋朝建立前数年,但宋代史籍中却甚少其生平事迹的记载,如《宋史》《东都事略》之《太祖纪》等皆附录有赵弘殷的事迹,然颇为简略,且时有错乱之处。本文拟据相关史料,对史籍记载颇见错乱的赵弘殷显德三年之行迹加以订补辨析。
一
《宋史·太祖纪一》载:
周广顺末,(赵弘殷)改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从征淮南,前军却,吴人来乘,宣祖邀击,败之。显德三年,督军平扬州,与世宗会寿春。寿春卖饼家饼薄小,世宗怒,执十余辈将诛之,宣祖固谏得释。累官检校司徒、天水县男,与太祖分典禁兵,一时荣之。卒,赠武清军节度使、太尉。……(赵匡胤下滁州后),宣祖率兵夜半至城下,传呼开门,太祖曰:“父子固亲,启闭,王事也。”诘旦,乃得入。韩令坤平扬州,南唐来援,令坤议退,世宗命太祖率兵二千趋六合。太祖下令曰:“扬州兵敢有过六合者,断其足。”令坤始固守。太祖寻败齐王景达于六合东,斩首万余级。还,拜殿前都指挥使。[1]卷一《太祖纪一》,第1-3页
《宋史·太宗纪一》亦载:
(赵光义)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饬厉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1]卷四《太宗纪一》,第53页
《东都事略》卷一《太祖本纪》载:
世宗征淮东,宣祖为前军副都指挥使,领兵先入维扬,禁止侵暴,民情大悦,世宗嘉之。未几,以疾归,与太祖会于寿春。归及中途而崩,赠武清军节度使。……(赵匡胤)遂下滁州。后数日,宣祖率兵夜半至城下,传呼开门,太祖曰:“父子虽至亲,城门王事也,须明乃敢奉命。”至明乃入。又破江南兵于六合,斩首五千级。时韩令坤为招讨使平扬州,唐主遣陆孟俊据蜀冈以逼其城,令坤潜议退师,太祖下令曰:“扬州兵敢有过六合者,吾当折其足。”令坤惧,始有固守之志。太祖率兵击之,孟俊遁,为追兵所杀。又破其齐王景达兵于六合,斩首万级是役也。……宣祖崩,起复,拜定国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2]卷一《太祖本纪》
《东都事略》卷三《太宗本纪》又载:
(赵光义)幼颖悟,好读书。宣祖为将征淮上,克州县,诸将皆争子女玉帛,宣祖为访其书籍,归以遗太宗,谓之曰:“文武立身之本,汝其勉之。”[2]卷三《太宗本纪》
至南宋后期类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七《皇朝源流》,所载赵弘殷事迹,较《宋史》《东都事略》为详,其有关显德三年行迹者,云:
世宗征淮甸,以宣祖为前军副都指挥使,领所部兵先入淮阳,安民禁暴,吴人悦之。时诸将皆争子女玉帛,而宣祖但使人购书籍,得三千余卷。先是,我太宗年甫志学,耽翫经史。宣祖尝谓曰:“惟文与武,立身之本也。尔其勉之!”尽以所获书付焉。时宣祖扬州驻军数月,厉兵捍寇,声振敌境,世宗嘉之。未几,以疾归,欲与太宗(今案:当作“太祖”)会于寿春。后至京师,薨,赠太尉焉。太祖皇帝,乃宣祖第二子也。[3]续集卷七《类姓门·皇朝源流》
赵弘殷于后周广顺末年(953)升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4)三月擢任龙捷右厢都指挥使、遥授团练使,后转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领岳州防御使①按:(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一《祖宗世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页)称赵弘殷“仕晋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乃是将其在后周时的官衔误植至后晋时。。二年十一月初,周世宗命宰相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将以伐唐”[4]卷二九二,第9532页。赵弘殷为十二将之一,《东都事略·太祖本纪》《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皇朝源流》皆称其时为前军副都指挥使,《资治通鉴》称其任马军副都指挥使[4]卷二九二,第9538页,当是淮南道前军行营马军副都指挥使,故所谓前军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应皆属省称。
《宋史·太祖纪》云赵弘殷“从征淮南,前军却,吴人来乘,宣祖邀击,败之”。据史载,显德二年十二月,后周军于正阳(今安徽寿县西北正阳关)渡过淮河,进围南唐淮南重镇寿州(今安徽寿县)城,遭到后唐守将清淮军节度使刘仁赡的顽强抵抗,攻击月余不克。三年正月六日,周世宗下诏亲征淮南,并命侍卫司都指挥使李重进率兵先赴正阳增援,河阳节度使白重赞领兵三千进屯颍上(今属安徽)。殿前都虞候赵匡胤扈从出征。南唐主闻知后周军渡淮,急命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率兵二万增援寿州,并命奉化节度使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姚凤率兵三万进屯定远(今安徽定远东南)以为策应。后周帅李谷见南唐刘彦贞率援军逼近,“以战舰数百艘趋正阳,为攻浮梁之势。李谷畏之”,特“焚刍粮,退保正阳”。南唐军急进追击,为李重进率部击败[4]卷二九二,第9533-9536页。据《宋史·李重进传》记载,当时“周师未朝食,吴师奄至,周师望其阵皆笑之。宣祖领前军,与重进、韩令坤合势击之,一鼓而败”[1]卷四八四《周三臣传》,第13976页。而《韩令坤传》所载略同:“(李)谷退保正阳,为吴人所乘,令坤与宣祖、李重进合兵击之,大败吴人。”[1]卷二五一《韩令坤传》,第8832页据《资治通鉴》所载,此次战事发生在显德三年正月十三日,时周世宗至陈州(今河南淮阳),获知李谷已自寿州城下引兵退保正阳,急令李重进赶赴淮上增援,遂大破南唐兵。《宋史·太祖纪》置于显德二年末,不确;又称“前军却,吴人来乘,宣祖邀击,败之”,也属夸饰之词。
此后,赵弘殷的行军作战事迹,与其子赵匡胤多有交集,但诸史籍之记载却颇见混乱。
显德三年正月二十日,周世宗至正阳,以李重进替代李谷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主持淮南战事。二十二日,周世宗进抵寿州城下。二十六日,周世宗“耀兵于城下”[5]卷一一六《周书七·世宗纪三》,第1541页,亲督诸将攻城。赵匡胤作为天子禁卫将,也亲乘战船杀入寿州城外护城河:“及攻寿春,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车弩遽发,矢大如椽”,帐下牙将张琼“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琼股,死而复苏”①《宋史》卷二五九《张琼传》,第9009页。按:《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将赵匡胤“乘皮船入城濠”事置于三月甲午朔周世宗“行视水寨至淝桥”时,似不确,此时赵匡胤当仍在滁州。。但南唐寿州守军坚守不退,周世宗见寿州城池高深,易守难攻,遂在留重兵长围久困寿州城的同时,遣将分路出击攻取南唐长江以北诸州,以孤立寿州城。
二月戊辰(五日),殿前都虞侯赵匡胤奉命“倍道袭清流关”[4]卷二九二,第9538页;壬申(九日),赵匡胤上奏大破南唐军“万五千人于清流关,乘胜攻下滁州”[5]卷一一六《周世宗纪三》,第1541页。己卯(十六日),周世宗侦知扬州(今属江苏)唐军无备,遂命韩令坤等“将兵袭之”,赵弘殷同行督军。乙酉(二十二日),韩令坤军至扬州城下,攻克之②《资治通鉴》卷二九三,第9539、9541页。按:《宋史》卷二五一《韩令坤传》(第8832页)载:“世宗亲征,闻扬州无备,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赵晁等袭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骑数百迟明驰入,城中不之觉。令坤继至抚之,民皆按堵。”。辛卯(二十八日),赵匡胤奏南唐天长军制置使耿谦“以本军降,获粮草二十余万”[4]卷二九三后周显德三年二月,第9541页。
四月初,南唐军反攻扬州,后周军将韩令坤等弃城走,周世宗调兵马援之,并命赵匡胤率本部二千人进趋六合(今属江苏)以为声援。赵匡胤“令曰:‘扬州兵有过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是月,赵匡胤破南唐军于六合,“杀获近五千人”[4]卷二九三,第9552-9553页。
五月,周世宗见天气渐炎热,不利于攻坚作战,遂于戊戌“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围寿州”,自己率周军主力北回京师,“乙卯至大梁”[4]卷二九三,第9555页。
六月中,寿州南唐守军乘围城的周军“无备,出兵击之,杀士卒数百人,焚其攻具”[4]卷二九三,第9555页。当时“城坚未下,师老于外,加之暑毒,粮运不继。李继勋丧失之后,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正逢赵匡胤“自六合领兵归阙,过其城下,因为驻留旬日,王师复振”[5]卷一一六《周世宗纪三》,第1548页。
七月初,南唐乘周军主力北归,连续攻取江淮诸州,迫使后周“淮南节度使向训奏请以广陵之兵并力攻寿春,俟 克 城,更 图 进 取,诏 许 之 ”[5]卷一一六《世宗纪三》,第1549页。 于 是 滁 州 守 将 “亦 弃 城 去,皆 引 兵 趣寿春”[4]卷二九三,第9558页。
在此期间,赵弘殷行迹,据《宋史·太祖纪一》,称赵弘殷“督军平扬州,与世宗会寿春。寿春卖饼家饼薄小,世宗怒,执十余辈将诛之,宣祖固谏得释。累官检校司徒、天水县男,与太祖分典禁兵,一时荣之”。又于赵匡胤攻占滁州之后记载云:赵弘殷“率兵夜半至城下,传呼开门,太祖曰:‘父子固亲,启闭,王事也。’诘旦,乃得入”。《资治通鉴》卷二九二明确记载赵匡胤“克滁州”之“后数日”,赵弘殷“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据《东都事略·太祖本纪》,赵弘殷随军进入扬州,“禁止侵暴,民情大悦,世宗嘉之。未几,以疾归,与太祖会于寿春,归及中途而崩”。因赵匡胤于二月上旬攻占滁州,韩令坤等统兵于是月二十二日攻克扬州;此后赵匡胤于四月初率军进屯六合,六月间赵匡胤“自六合领兵归阙”途中留寿春城下“旬日”。因此,赵弘殷至滁州的时间大抵在三月中。赵弘殷离扬州而抵达滁州的原因,史书无载。《东都事略·赵普传》云“时宣祖将兵抵滁上,得疾,普躬视药饵,朝夕无倦”。《宋史·赵普传》亦称“宣祖卧疾滁州”。因赵弘殷作为前线重要将领,不能无故离扬州而去,故可推知其当因患重疾,而自扬州至滁州,欲就其子以养病耳③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称“时宣祖扬州驻军数月”之“数月”,当为“数日”之讹。又《东都事略·赵普传》称赵弘殷“抵滁上,得疾”,所云当有颠倒。。因赵匡胤攻占滁州后,周世宗即“遣翰林学士窦仪籍滁州孥藏”;诏左金吾卫将军马崇祚知滁州;宰相范质荐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赵匡胤“与语,悦之”④《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39页;《旧五代史》卷一一六《周世宗纪三》,第1541页。。因赵弘殷“卧疾滁州”时,赵匡胤恰受命率军去六合,故视为“同宗”的赵普遂“躬视药饵”。此后大概因“滁州守将亦弃城去,皆引兵趣寿春”,赵弘殷也随之北归,而与自六合北归的赵匡胤相见于寿州城下,时在七月中。由此,可证《宋史·太祖纪》赵弘殷“督军平扬州,与世宗会寿春”云云不实,即赵弘殷再至寿州城下时,周世宗早已北还京师,故赵弘殷“固谏”周世宗释寿春卖饼家之罪,当在年初周世宗初抵寿州、赵弘殷往扬州之前。
赵弘殷死于显德三年七月二十六日①徐松等《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中华书局版。《宋朝事实》卷一《祖宗世次》(第3页)记载同。,享年不详。赵弘殷死于何处,《东都事略·太祖本纪》称其“以疾归,与太祖会于寿春,归及中途而崩”,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称其“后至京师,薨”,此外诸书皆未记载。综合相关史料分析,赵弘殷当因病情恶化,死于自寿州北还途中。周世宗追赠赵弘殷为武清军节度使、太尉。赵匡胤随即“起复”[4]卷一《太祖本纪》视事。
二
元末修撰《宋史》,其所据史料来源主要为宋修《国史》,而宋《国史》又主要依据“实录”修撰。记载宋初史事的史籍主要有太宗初年编撰的《太祖实录》、真宗初编撰的《太祖新录》与太祖、太宗《两朝国史》等。按理说,赵弘殷之死下距赵匡胤开国仅有数年,下距宋太宗初年修纂《太祖实录》的时间也并不很久远②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六《太祖实录五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页):“太平兴国三年(978),诏李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董淳、赵邻几同修,伦总其事。更历二载,书成。”,但有关赵弘殷事迹的记载却是如此简略、零乱,且时见错讹、矛盾,其原因当与宋初并不寻常的帝位授受如陈桥兵变、斧声烛影等事大有关系。继太祖登基的太宗,因其继位不正,在贬责赵廷美事件以后,为尽量消弭因兄终弟继带来的如德昭自刭、廷美贬死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一方面要通过所谓上膺天命、下符人心之说来为宋太祖篡夺后周帝位作辩护,以证明赵宋立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要极力拔高赵弘殷的政治地位,着意强调赵弘殷在赵宋王朝创立中的关键作用,以证明自己虽是兄终弟继,但其实也是子承父业,即赵宋王朝是由赵弘殷所奠基的,由此,在宋代相关文献中留下了不少自相矛盾的记载。
如前述赵匡胤拒绝赵弘殷夜入滁州城一事,虽然称誉“史言太祖勇于战,谨于守”[4]卷二九二,第9538页,但忠于王事的赵匡胤,却坚拒病父及时入城,显于孝道有亏。这或许亦是宋人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圣宋仙源积庆符瑞》未采录此事的原因。可能出于同样原因,虽然赵弘殷病死一事,对赵匡胤兄弟来说甚为重要,但宋代文献记载却甚为简略,仅《宋会要辑稿·帝系》《宋朝事实》卷一云是“显德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崩”,其他诸书皆未记载,甚至《宋史·太祖纪一》仅记一“卒”字而已。这或许是因为赵弘殷死时,赵匡胤兄弟均不在其身边奉侍“药饵”,从而使高调倡导孝道的太祖、太宗二人颇见难堪的缘故。当也因为此,《东都事略·太祖本纪》虽已称赵弘殷“以疾……归及中途而崩”,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皇朝源流》却要改为“后至京师,薨”了。
同时,虽然有关赵弘殷的记载甚为简略,但其中夸饰文字却有不少。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所载赵弘殷“少骁勇,善骑射,为乡里所推,而雅好儒素”之“雅好儒素”一语,显然是与此后所记赵弘殷从周世宗征战淮南,“领所部兵先入淮阳,安民禁暴,吴人悦之。时诸将皆争子女玉帛,而宣祖但使人购书籍,得三千余卷。先是,我太宗年甫志学,耽玩经史。宣祖尝谓曰:‘惟文与武,立身之本也,尔其勉之!’尽以所获书付焉”之事相照应。而史载赵弘殷从征淮南仅此一次,且卒于北归途中,而当时赵光义并未随军,故可知赵弘殷将自己于淮南所搜集之书付与赵光义,并督促其读书之事乃出自虚构,而非事实[6]327-328。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记载,南征淮南时搜罗大批书籍运回东京的不是赵弘殷,而是赵匡胤:“上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7]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条,第171页两相对照,可见赵弘殷于出征淮南时搜集图书以“归遗”赵光义的记载,当是抄袭赵匡胤之事而已,以强调赵光义能“工文业,多艺能”,乃是赵弘殷“恒饬厉之”的结果。
为强调赵弘殷在赵宋王朝创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即所谓“宋之兴,虽由先世积累,然至宣祖功业始大”[1]卷二四二《后妃传上》,第8606页,宋人竭力宣称赵弘殷在后周显德年间“与太祖分典禁军,一时荣之”。因赵弘殷至后周时才任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此时赵匡胤官拜殿前都虞候,父子两人虽分居侍卫、殿前两司,但似不能担起“分典禁兵”之名。按,“典”有主持、掌管之意。《广雅·释诂三》曰:“典,主也。”唐孔颖达疏《书·舜典》“有能典朕三礼”曰:“掌天神、人鬼、地祗之礼。”周世宗初年军制,侍卫司长官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都虞候,下分马军、步军,分设都指挥使,龙捷乃马军所属之军号,分左、右两厢;殿前司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都虞候,后又于殿前都指挥使之上加设殿前都点检一职。虽然此时殿前都虞候地位约同于龙捷、虎捷都指挥使①如《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世宗本纪一》载:后周世宗即位初,“以散员都指挥使李继勋为殿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韩令坤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以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赵弘殷为龙捷右厢都指挥使,以散员都指挥使慕容延钊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以控鹤第一军都指挥使赵鼎为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并遥授团练使”。,但殿前都虞候似还可称为“典”殿前司,然仅任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却被称作“典”侍卫司,显属夸饰了。
夸饰赵弘殷的“功业”之举,在太宗祭祀“配享”一事上亦有较为充分的反映。如乾德元年(963)十一月,太祖“始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于圜丘”,因“宣祖皇帝,积累勋伐,肇基王业”,故“奉以配享”[1]卷九九《礼志二·南郊》,第2438页。至太宗继位之初,改以太祖“配享”,随后又加更改。
如《宋史·扈蒙传》载:
初,太祖受周禅,追尊四庙,亲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礼官以为舜郊喾,商郊冥,周郊后稷,王业所因兴也。若汉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顿君,虽有帝父之尊,而无预配天之祭。故自太平兴国三年、六年再郊,并以太祖配,于礼为允。太宗将东封,(扈)蒙定议曰:“严父莫大于配天,请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罢封禅为郊祀,遂行其礼,识者非之。[1]卷二六九《扈蒙传》,第9240页
《宋史》卷九九《礼志二·南郊》亦云:
自国初以来,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祗、神州凡七祭,并以四祖迭配。太祖亲郊者四,并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岁亲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雍熙元年冬至亲郊,从礼仪使扈蒙之议,复以宣祖配。四年正月,礼仪使苏易简言:“亲祀圜丘,以宣祖配,此则符圣人大孝之道,成严父配天之仪。太祖皇帝光启丕图,恭临大宝,以圣授圣,传于无穷。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将来亲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谷、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
因太祖为开国之君,故只能以追尊为皇帝的宣祖赵弘殷“配天”,以“符圣人大孝之道,成严父配天之仪”。所谓“积累勋伐,肇基王业”,只是为顺利举行以赵弘殷“配天”仪式的门面语。待太宗继位,按礼制规定,自然得以先帝太祖“配天”,况且太祖又“光启丕图,恭临大宝,以圣授圣,传于无穷”。然自“德昭自刭”“廷美贬死”一系列事件之后,太宗乃欲通过提高赵弘殷的地位以消减太祖的政治影响,故扈蒙“严父莫大于配天,请以宣祖配天”的建议,大惬圣意,虽“识者非之”,却依然“遂行其礼”。但依礼制,宣祖赵弘殷“虽有帝父之尊,而无预配天之祭”,于是太宗不得不依据臣下建议,再改为“亲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谷、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但是此举依然不合礼制,故此后争议并未消止,如仁宗即位后,太常博士谢绛“用郑氏经、唐故事议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惟太祖始造基业,躬受符命,配侑感帝,据理甚明”。虽然后因翰林学士承旨李维“以为不可”而未果[1]卷二九五《谢绛传》,第9843页,但仍可见宋代士大夫对此举所持之异议。
三
综上,赵弘殷于后周显德三年的行迹,其记载显得过于简略、零碎,且颇有虚夸不实文字,甚至时见错讹之处,并非是因为历时久远而失记,而是密切相关于宋初特殊的政治局面,即记载赵宋开国前后历史的宋初《国史》《实录》,一方面为回避可能给太祖、太宗兄弟带来负面影响之记事,另一方面又要着意拔高赵弘殷在创立赵宋王朝上的关键作用,由此形成有关赵弘殷在显德三年行迹的记载,出现或略或溢,或岁月前后颠倒,甚至虚构事实等情况。
此外,需再加指出的是,虽然南宋类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七《皇朝源流》所载赵弘殷事迹,要较《宋史·太祖纪》《东都事略·太祖本纪》为详,但仔细比勘其与《宋史·太祖纪》《东都事略·太祖本纪》等所载的相关文字,仍可推知其当也源自宋朝官修史籍,而又据其他史料予以增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