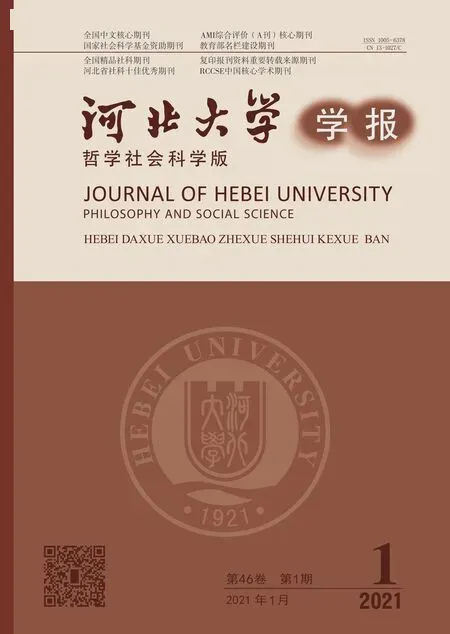德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规范体系、发展趋势和借鉴价值
任 超
(北京建筑大学 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2616)
一、引 言
德国在处理文化遗产①较之于其他概念,“文化遗产”在内涵方面侧重于遗产属性和代际公平,在外延方面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因而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指称。此外,文化遗产不仅涉及物质形态的文物、设施等内容,同时还包含非物质形态的精神元素,以上两者在现实中互为支撑、互相依存,无法割裂,但是鉴于文章篇幅的限制和研究重点的选择,本文拟将论述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领域。保护方面有着较为成熟的做法,并且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完善法律体系所提供的制度支撑和规则保障。纵观中国,德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数量较少。从法学视角对德国文化遗产展开论述的文献屈指可数,整体研究的丰富性严重欠缺。二是内容粗糙。大部分著述在讨论德国文物返还制度的过程中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进行附带性介绍,缺乏涉及规范体系的全面性、概括性和系统性的探究和思考。为了填补理论研究的漏洞,实现相关知识体系“质”的积累,本文拟将德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作为研究视域,并重点选取规范体系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证。此外,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在2020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所提出的“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需要在吸收域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性完善。因此,本文研究的另外一个目的正是在于“洋为中用”,为中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制度性完善提供理论素材和参考借鉴。
二、德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规范体系
(一)内部构成要素
1.联邦州立法。德国联邦州在文化主权[1]和社会思潮双重因素的共振作用下先后制定了各自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按照德国的宪政体制,各个联邦州享有文化主权(Kulturhoheit)[2]。因此,德国联邦只能针对“防止本国文化财产流入国外”的内容进行立法规范,其他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事项则属于各个联邦州的权限范围。除了以上制度性铺垫,社会大众对于古典历史建筑、文化以及艺术态度的转变,对于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强烈反思则是推动联邦州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刺激性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保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思潮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发展,并且逐渐开始向法律领域进行渗透和传导。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80年代,保护文化遗产的立法潮流在当时席卷了联邦德国的全部11个州。两德统一后的90年代中期,所有新加入的联邦州也对此纷纷进行效仿,分别制定了相关的专门性法律①在联邦州层面,德国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半期,第一部专门性的规范性文件为1780年由黑森-卡塞尔邦国冯德里希二世伯爵公布的《维护邦国内现有文物和古文物》规定,具体的保护对象为公共财产。1902年,黑森-达姆施塔特颁布了德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关于文物保护法》。二战以后,巴登州在1949年最早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性立法。。总结来说,在立法模式方面,各个联邦州基本上采用了相同的做法,即对文物、周遭环境以及历史街区等不同层次的要素进行统一性规制。以上所指称的文化遗产(Denkmäler)不仅涉及各种可以移动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及其组成部分,同时还延伸到整体性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同时,在立法规范的形式结构方面,大部分联邦州在设立总则的基础之上,粗略的将分则划分为“主管机关”“保护措施”“行政程序”以及“其他事项”等四个部分。其中,在“保护措施”的部分,立法者采用类型化的逻辑思路,或者遵循一般和特殊的逻辑主线。
2.联邦立法。德国联邦在立法分权的框架下通过专项性立法和周边性立法的形式对文化遗产予以规范保护。德国联邦针对“防止本国文化财产流入国外”的事项而享有排他性的立法权力②需要说明的是,联邦国家针对“防止德国文化财产流入国外”事项的排他性立法权限并非自始固有。根据二战以后德国基本法的相关规范内容,以上事项属于竞争性立法的内容。换言之,该种立法权限并非由联邦国家单独享有。一直到1994年,其又被作为“框架性立法权”的内容。2006年德国联邦体制改革之后,该种事项才最终被纳入排他性立法的范畴。。据此,原联邦德国议会在1955年制定了《防止德国文化财产流失法》(Gesetz zum Schutz deutschen Kulturgutes gegen Abwanderung),随后又在1967年制定了《针对1954年5月14日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的法律》(Gesetz zu der Konvention vom 14.Mai 1954 zum Schutz von Kulturgut bei bewaffneten Konflikten)。两德统一后,联邦议会于1998年制定了《文化财产返还法》(Kulturgüterrückgabegesetz),此后对其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正。以此为基础,联邦议会又于2016年制定出统一的《文化财产保护法》(Gesetz zum Schutz von Kulturgut)。该部法案吸收了欧盟现行规范的相关内容,并且最终承认了世界遗产委员会1970年公约的法律框架和法律标准。除了以上专项性立法,德国联邦所出台的各种周边性立法也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多样化的制度工具和有力手段,并且具体体现在建筑、环境以及税收三个方面。举例来说,在建筑法领域,1960年《联邦建筑法典》(Baugesetzbuch)第1条第6款,2008年《空间规划法典》(Raumordnungsgesetz)第2条第2款第5项以及第8条第1款等条文都规定了“文化遗产本身的利益必须被充分考虑”的内容;此外,在环境法领域,1990 年《环境影响评估法》(Gesetzüber die Umweltverträglichkeitsprüfung)第2条以及2006年《环境法律救济法》(Umwelt-Rechtsbehelfsgesetz)第2条、第3条分别从实体和程序的角度将文化遗产纳入保护对象的范围。
3.欧盟条例和指令。欧盟层面的条例和指令通过直接适用以及间接转化的方式进入德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体系之中。受制于自身的政治体制和组织架构,欧盟的职责范围并非一种抽象权力的集合,相反更多地体现为个别化的任务内容[3]。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欧盟制定了诸多在效力层级上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①较之于各成员国的国内法,欧盟法的优先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员国国内法不能在内容方面通过任何形式变更或者撤销欧盟法;二是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欧盟法处于更高的效力位阶。Vgl.Klaus-Dieter Borchardt,ABC des EU-Rechts,Luxemburg:Amt für Veröffentlichung der Europäiche Union,Dezember 2016,S.48.的次级性欧盟法(sekundäres Unionsrecht)②次级性欧盟法(sekundäres Unionsrecht)是和原生性欧盟法(primäres Unionsrecht)相对应的概念,后者主要是指创设欧盟的诸多 协定,以及后续的补充协议等,而前者则是指欧盟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制定的各项规范。,并主要表现为条例(Verordnung)和指令(Richtlinie)等③为了实现在创立欧盟协定中所设定的各项目标,通常需要各种形式的法律意义上的行为(Rechtsakte),并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条例(Verordnung),在所有欧盟成员国范围内发生直接的效力;二是指令(Richtlinie),需要各个成员国选择不同的形式和手段来进行转化,因而具有间接性的效力;三是决议(Beschuluss),需要面向特定的对象做出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四是建议(Empfehlung),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五是立场(Stellungnahme),同样不具备法律效力。参见《欧盟工作方式的协定》(Vertragüber die Arbeitswe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第288条的内容。。欧盟条例具有直接适用性,成员国的公权机构和私权主体可以直接依照条例的内容享有权利(力),承担义务或者职责[3]。例如由欧盟理事会制定的《关于文化财产出口的116/2009号条例》(Verordnung(EG)Nr.116/2009 des Rates vom 18.Dezember 2008über die Ausfuhr von Kulturgütern)以及由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制定的《关于文化财产过境和进口的条例》(Verordnung(EU)2019/880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17.April 2019über das Verbringen und die Einfuhr von Kulturgütern)。比较而言,欧盟指令需要通过成员国的转化行为才能产生相应的约束力。例如由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共同制定的《关于返还从成员国境内非法转移的文物以及修改1024/2012号条例的指令》(Richtlinie 2014/60/EU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15.Mai 2014über die Rückgabe von unrechtmäßig aus dem Hoheitsgebiet eines Mitgliedstaats verbrachten Kulturgütern und zurÄnderung der Verordnung(EU)Nr.1024/2012)。总结来说,以上条例和指令构成了欧盟层面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主体内容。在规范对象方面,欧盟立法的侧重点在于可移动形态的文化财产;在规范内容方面,以上立法主要围绕文化财产的进出口事项进行规制;在规范目的方面,欧盟立法的初衷更多地体现了补充性和协调性,以此来磨合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制度性差异。
4.国际公约。德国对于国际组织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始终持有开放欢迎的态度,通过批准加入国际公约的方式来扩张自身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渊源。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代表的专门机构在推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并且重点在世界遗产、战争地区文物保护、打击文物走私、水下文物保存等领域制定了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公约、细则和协定等法律文件。以上这些规范不仅是人类在保护文化遗产过程中所形成的智慧结晶,更是为各国全面实现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制化提供了统一的资源要素。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发国家,德国加入了以下国际公约: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4年制定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以及随后制定的1954年《第一议定书》(First Protocol)和1999年的《第二议定书》(Second Protocol);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制定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移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除此之外,基于某些客观理由,德国对于其他特定公约的态度仍然犹豫不决④就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德国尚未批准通过的公约有两个: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制定的《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二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2001年制定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但是总体情况已经显现出积极良好的发展态势。
5.司法判例。司法判例也是德国文化遗产保护规范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同于一般的裁判,司法判例是指那些有可能与当前待决案件有关联的先前判决,这一概念预设了某种约束[4]。因此,基于法官裁判所形成的判例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规范性效力[5],但是德国现行立法只是赋予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正式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以上所指称的规范性效力更多地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提供指导性和支持性,增强说理说服力,进一步支持的事实上的拘束力”[6]。尽管如此,司法判例仍然应当被视为一种补充性的法律渊源。具体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早的司法判例可以被追溯到“一战”之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联邦财政法院、各州的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以及其他各级法院系统都在各自的管辖范围之内制作并公布了诸多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裁判文书。在对其进行整理、筛选、梳理以及归纳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以下四类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案例群:一是拆除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申请被主管机关拒绝的情况下,所有人或者权利人以此来寻求救济所形成的判决;二是针对被批准的建设计划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所有人或者权利人以所有权的防御功能为基础来寻求救济所形成的判决;三是基于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采取措施的需要,主管机关以此来提出诉讼所形成的判决;四是针对保存和维护文化遗产所形成的不利负担在经济层面的合理性问题,利害关系人以此来寻求救济所形成的判决。
(二)实际运行效果
1.喜忧参半的成文立法。德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文立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拭待解决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德国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法治化,同时,联邦州层面的立法则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模仿来实现自我完善。具体来说,在规范供给的基础上,围绕文化遗产保护衍化形成了各类制度性内容。在主体方面,德国联邦以及各个联邦州都配置了履行保护职责的公权机构,公众参与条款的存在也直接激发了样态各异的民间性保护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起来。在客体方面,受保护的对象呈现出一种“层层扩散、由近及远”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群状化和扩大化的发展趋势。在公法性义务方面,文化遗产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被负载了诸如维护、使用、协作以及容忍等诸多公共性负担。此外,各个联邦州的立法过程并非闭门造车,相反更多地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吸收和借鉴[7]。换言之,立法者往往都会引用其他联邦州的成熟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转化性创新,最终制定出富有实效性以及逻辑性的规范条文。通过实践效果的检验,某个特定联邦州所制定的规范开始具备了优势地位,并逐渐成为参照比较的标准,其他联邦州则通过修法的方式取消和淘汰同现实严重脱节的劣势规范[8]。借助此种机制,联邦州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实现了动态化的自我革新。不容否认的是,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文规范具有易于僵化的通病,在对现实案例进行法律规制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9],相应的,学说理论对此也多有持续性的批评和质疑。无论在数量层面,还是在调整对象的重要性方面,联邦州的成文立法在整个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中都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同时,各个联邦州基本上都采用了大体相同的综合性立法模式。因而,选择某一特定联邦州的相关规范作为讨论对象,并以此来窥探文化遗产保护成文立法体系所存在漏洞和不足的论证路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德国拜仁州在20世纪70年代年就已经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性法律,以此为发端,在其后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德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开始步入高速化发展轨道,其他各个联邦州纷纷效仿,成文化立法“遍地开花”。总结而言,拜仁州的文化遗产保护规范具有先导性和示范性,适于作为例证来进行阐释和说明。
拜仁州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出台具有转折性意义,其在对当时广泛存在的拆除和建设行为进行法律管控的同时显著地提升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和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部法律中的部分条款被司法裁判重复性的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其仍然表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迹象,尽管立法者对其进行了多达17次的修补矫正,但是仍未实现预期的效果。因此,拜仁州的某些政客针对文化遗产保护法所进行的自我标榜是绝对错误的,其并不能掩饰公权主体怠于对其进行革新的事实[10]。进一步而言,拜仁州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结构性瑕疵和内容性缺失尤为突出,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概念界定所导致的现实困境。立法者偏向于抽象思维,并且放弃使用上位概念以及“文化遗产资格”(Denkmalfähigkeit)和“文化遗产价值”(Denkmalwürdigkeit)两种构成要件来描述文化遗产本身,从而致使相应的法律涵摄出现障碍[11]。此外,立法者将地下埋藏遗产局限于史前或者历史早期的做法完全基于其主观臆断,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中的大部分来源于中世纪或者近代的客观情况,因而无法为现实中地下埋藏物所受到的建设性破坏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二是保护系统混乱所导致的适用困境。根据该法第2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拜仁州的文化遗产经过通知程序而被纳入保护名录。事实上,根据该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数量众多的动产和考古挖掘物只有在经过登记之后才能被纳入保护体系,而此种意义上的登记就具有了构成性效力(konstitutive Wirkung)。总结来说,由以上不协调的规范所形成的混合保护体系在内容层面存在冲突,在具体运行方面效率低下。三是体系结构的陈旧所导致的区别对待。该法根据文化遗产的类型而将保护性条款和程序性条款加以区分的做法已经过时。在此基础上,立法者对于可移动文化遗产刻意保持沉默,而仅仅针对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设置了维护等公法义务,此种厚此薄彼的规范性设计对现实中的保护不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是审批权力转移所导致的监管弱化。该部法律不断修改的目的之一在于将原属于建筑主管机关的职责权限转移至相对来说较为“薄弱”的基层文化遗产保护机关,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行政审批的标准变得越来越宽松,拆除文化遗产的情形变得越来越多。五是不法行为条款所导致的适用不足和体系冲突。受制于基层法院的司法审查,公权主体基本上很少使用不法行为条款中的“修复、恢复原状以及罚款”等处罚手段;此外,该法针对不法行为所规定的独立规范构成要件同刑法中涉及“公共遗产破坏行为”的内容存在不一致之处,因而容易造成法律适用的无所适从。六是“宝藏库(Schatzregal)”规则阙如所导致的保护不力。不同于其他联邦州的做法,由于反对派的抵制,拜仁州议会一直并未能够在该法中配置“宝藏库”规制,从而致使无主的或者长期埋藏而无法确认所有者的、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文化遗产不能由国家强制取得所有权,并进一步加剧了现实中保护不力的弊端。
2.蓬勃发展的司法判例。经过多年的发展,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所形成的数量众多的司法判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成为影响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的关键性因素。从结果导向的角度出发,基于法律适用而形成具体的裁判在大多数情况下服务于相关规范条文的解释和补充,成为明确其内涵、外延以及合体系性等事项的参考因素。由于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上诉审查必须以联邦州的相关立法作为依据,具体的裁判内容不能与其存在冲突,这就导致大量裁判的管辖主要集中于各个联邦州的高等行政法院,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的案例群。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联邦法院对于所涉文化遗产的案件毫无管辖权,其针对某些特定的案件仍然有权受理,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有关违宪审查的个案裁判也不断涌现,并且在数量方面呈现不断增多的态势。在此种意义上,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关系私法财产权,同时还涉及宪法中的基本财产权。举例来说,围绕如何认定特定联邦州文化遗产保护专项法律的合宪性等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个案裁判的方式对以上事项进行了细致化的阐释。在有关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所有权的一则案例中,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以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4条第1款有关“所有权受到法律保护”以及14条第2款有关“所有权负有义务”“权利行使应当维护公共利益”等规范内容为基础形成如下决议:“所有权受保护并不意味着应当维护文化遗产所有人营利性的使用”,“所有权负有义务意味着文化遗产所有人可能会承担忍受营利性使用被禁止的不利后果或者并不意味着对于文化遗产的持有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基于公共利益而对文化遗产所有人进行的限制是否过于苛刻,还需要考虑权利人对于该种负担是否知情或者应当知情”[12]。此外,在其他案件的决议中,第一审判庭认为:“如果联邦州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在‘没有排除针对权利人不合理的负担,并且没有包含避免此种所有权限制的预防性内容’的情况下才存在违反宪法的可能性。”[13]
除了以上框架体系内的解释补充,部分司法判例还针对既有规范进行了续造性和创新性的发展。举例来说,根据理论通说,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维护,因而文化遗产的所有人对此并不具备某种主观性权利,因而也不能针对某项对其文化遗产的价值产生不利影响的建设计划,通过提出诉讼的方式进行防御和阻止。不可否认的是,行政主管机关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倾向和利益偏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所做出的行政判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价值偏差,进而忽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此背景下,作为权利维护的最后屏障,司法权力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通过放宽“诉讼管道”的方式允许私权主体对相关行政措施提出异议,进行纠偏,从而间接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应的,部分司法裁判开始做出改变,寻求新的尝试。在联邦行政法院的一则判决中,案件的主审法官认为:“受到保护的文化遗产的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被赋予请求撤销在周围批准建造的行政决定,如果该建造计划对于遗产保护可能产生显著性的重大影响。”①Vgl.BVerwG,Urteil vom 21.April 2009-4 C 3/08,BVerw GE 133,347(1.Leitsatz).可以说,针对“联邦各州成文立法规范无法对文化遗产所有权提供有效保护”这一法律漏洞,裁判者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此予以创造性的填补,并承认了文化遗产所有权积极的防御属性。从形式上看,虽然以上裁判体现了个案化的正义,但是却能够对其后相关的判决产生积极的促进、引导和示范效应,为其提供论证和说理的材料和依据。此外,在科布伦茨(Koblenz)一例有关“城堡所有人请求拆除在保护区域内被批准建设的农业设施”的案件中,作为上诉审的联邦行政法院认为,“依照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所有人在其文化遗产的价值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14]。虽然原告最终败诉,但是该案上诉法院的相关论述却对今后其他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借鉴的正当依据,并进而产生了某种事实上的约束力。随后在明斯特(Münster)地区的一例案件中,高等行政法院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文化遗产所有人的利益能够被某项行政措施所影响,从而成为具备诉权的利害关系人”[15]。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制度性工具方面,由于并不存在明确的立法规范,因而只能在利益比较的基础上,通过类推适用环境保护法律中的相关条款,从而推导出“文化遗产的私权主体享有相同的诉权,并进而提起公益诉讼”的结论。总结来说,司法判例通过法律续造的方式为私法主体通过诉讼来实现和维护文化遗产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三、德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发展趋势
德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发展轨迹并非毫无规律可循,相反却始终围绕着“如何优化权利义务的配置”这一特定的逻辑主线而向前运动。鉴于国内立法在整个规范体系中发挥着显著重要的作用,笔者拟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详细论述。
(一)国际化
德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法越来越多地吸收、借鉴和转化国际条约的相关规范,并且在制度内容方面产生某种一致性和趋同性。具体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虽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其发挥效力作用的前提在于主权国家的批准和加入。同时,即便国际条约具有域内效力,但是根据其规范内容,国际组织或者国际援助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仅仅发挥着次要辅助性的作用。比较来说,主权国家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主导性作用,尤其是在健全和完善规范保护体系方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德国大部分联邦州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未在立法层面对世界文化遗产“另眼相看”,并设置专门性的保护条款。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将其视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就此来说,德国联邦州在对国际条约的相关内容向国内法转化方面较为滞后。因而,如何在法律层面履行国际条约所确立的保护义务仍然是各个联邦州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此种情况,以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为代表的部分联邦州开始寻求一定的转变,其在该州2015年修订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引入了“保护区”(Schutzzone)这一上位概念,并将“世界文化遗产及其缓冲区”视为其重要组成部分[7]。凭借此种立法转变,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再仅仅停留于国际条约层面,而是进一步被“嫁接”到国内法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一种新的规范体系“图像”。虽然做出以上类似规定的联邦州在整体数量层面处于弱势,但是它却集中反映了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主流发展趋势。在未来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会有更多的联邦州对此进行效仿。
(二)欧洲化
德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法越来越多地直接适用、转化或者借鉴欧盟所公布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等。具体来说,作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成员最多的政治联合体,欧盟已经成为超越主权国家的新型政治实体,并且通过发布条例、指令、决定、命令等方式来协调内部共同事务。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欧盟和各个成员国遵循着一定的分权原则。以建筑物为代表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形态各异,具备相当的地域性特色,且无法进入流通领域,因此由其所在地的各个成员国政府进行独立的个性化管控和规制。比较而言,可移动文化遗产能够在欧盟范围内从某一成员国被运送至其他成员国,或者被运送至欧盟范围之外第三国家。在此种意义上,可移动文化遗产具备流通属性,涉及不特定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国的共同事务或者其他非成员国家的利益,需要在欧盟层面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制定具有共通性的适用规范。为此,欧盟制定了《关于文化财产出口的116/2009号条例》《关于返还从成员国境内非法转移的文化财产以及修改1024/2012号条例的指令》以及《关于文化财产过境和进口的条例》等规范文件。正是在欧盟统一立法的背景之下,基于对相关指令进行转化的需要,德国联邦议会制定了统一的以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为规制对象的《文化财产保护法》。随着欧盟范围的扩张以及欧洲大陆统一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有关立法在质量层次方面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数量种类方面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对成员国的立法进程产生直接重大的影响。换言之,除了对相关条例的内容进行直接适用,德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制定和修改进程中会更多地通过吸收和转化的方式将欧盟规范中的制度性内容“嫁接”融入到本国法律体系之中。
(三)去国家化
德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法越来越多的为私权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提供相应的规则空间和制度便利。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扩大化,公共事务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相对模糊,更多的原本属于私人所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被赋予了文化遗产的属性[16]。同时,保护对象的扩张化也为公权主体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其只能诉诸于各类社会资本的帮助和支持[17]。因而,“去国家化”所形成的文化遗产保护真空只能由其他非公权主体加以弥补和填充,文化遗产保护开始越来越多的被视为一种私人事务。在此背景下,“去国家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保护职能的分散和公法义务的强化。文化遗产保护的职能并非完全集中于公权主体,几乎所有的联邦州都在各自的立法中对于由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咨询和建议机构(Rat oder Beirat)等类公权主体的性质、地位和功能等事项予以规范,例如巴符州(Baden-Württemberg)和石荷州(Schleswig-Holstein)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相关条文规定,所有重要行政决定的做出必须要听取此类咨议机构的意见①Siehe Denkmalschutzgesetz vom Bundesland Baden-Württemberg,Artikel 4 und Denkmalschutzgesetz vom Bundesland Schleswig-Holstein,Artikel 6.。此外,联邦州在各自的立法中都不断强化和完善针对文化遗产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而配置的公法性义务以及具体违反后果[18]。二是间接性物质利益的给予。在直接性的补助资金存在巨大缺口的情况下,所有联邦州的立法都为文化遗产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提供了开具所得税优惠证明的可能性,以此来减轻其从事保有、维护等行为所带来的经济负担[19]。三是对于社会保护力量的有力扶持。大部分联邦州的立法为民间保护团体或者个人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充足有效的程序保证和实体保障,拜仁州文化遗产保护法第13条甚至还规定特定公权主体在适当情况下对于地方机构和私人行动提供全面服务的职责。
四、德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中国立法的借鉴价值
德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立法成果,并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性的动态更新,这就为后发国家的立法继受提供了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模板。中国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以文物保护立法为主干,以其他专项保护立法为辅助映衬,以国家性立法为主导,以地方性立法为附庸,横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的规制模式。其中,作为龙头和核心的《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工作正在按照法定程序加紧进行。如何以此次修法为契机来构建和完善文物保护的制度内容和规范体系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立法者、实务部门以及理论界所需要共同面对和思考的中心议题。总体来说,《文物保护法》的修订虽然应当坚持本土化的发展方向,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外来经验的绝对排斥。相反,为了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和体系化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有必要对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予以吸收和转化。
(一)立法理念的转换
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文物保护法》的立法理念进行革新。归纳来说,德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在发展变化方面呈现出两种面向:一是对于外部经验成果的引入和转化;二是对于内部非公权保护的鼓励和支持。比较而言,中国《文物保护法》的历次修订更加倾向于渐进式的“小修小补”,其对于国际保护经验的立法吸收较为迟缓,对于社会现实发展的立法回应则较为僵化。进一步来说,立法者在修法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国有馆藏文物、行政监管方式和审批制度的改革等内容,相应地,涉及保护对象的扩张、公众参与保护、国有文物使用人以及非国有文物所有人的公法性义务等内容则未被给予充分的重视。例如工业遗产、文化线路和文化景观等在存续时间或者外在形态方面具有特殊性,而且早已被各类国际性文件认可的文物类型一直游离于《文物保护法》第2条的保护对象范围之外;社会公众或者民间团体参与文物保护的条件、形式、途径和效力等问题也一直未在《文物保护法》中得到恰当的规范。为此,笔者建议未来《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应当坚持以下立法理念:一是民主化导向。通过法律修订来为文化遗产的社会保护提供更多的规则供给。二是国际化导向。通过汲取国际先进经验来构建完善的规范保护体系。
(二)立法模式的升级
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立法模式进行重构。针对文化遗产的本体及组成部分、群体、周边环境、历史街区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等内容,德国各个联邦州几乎都采用统一的立法对其进行规制。比较而言,中国《文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仅限于一般的可移动或者不可移动文物,涉及其他文化遗产的特殊类型则分别由《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管理办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以及《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加以规范调整。以上模式虽然立足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国情,能够有效兼顾立法的稳定性和发展性,但是在保护对象范围不断膨胀和延伸的背景之下,其已经无法对文化遗产的全要素保护提供有效的法律供给。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在“文化遗产”的概念框架之下,统合所有相关的规范条文,并进一步将《文物保护法》扩充升级为《文化遗产保护法》,以此来提供全面性的保护规范,并且强化其统领性和龙头性的作用和地位。此外,针对确有单独规制必要的特定种类的文化遗产,则可以继续保留既有特殊规范的独立性。
(三)形式结构的重塑
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文物保护法》分则的形式结构进行改造。大部分德国联邦州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在分则部分的内容构建方面都遵循了一定的逻辑线索。比较而言,中国《文物保护法》分则将保护对象划分为“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文物”“馆藏文物”“民间收藏文物”以及“进出口文物”等不同类型,并以此为基础分别进行规制,这其中还夹杂着些许程序性条款。此种章节安排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程序性条款依附于实体性条款;二是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履行的共通性义务并没有在规范条文结构中得到独立体现;三是将“不可移动或者可移动文物”的抽象称谓同“馆藏文物或者民间收藏文物”的具体概念相互等同,欠缺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为此,笔者建议未来中国《文物保护法》分则部分的修订可以采用以下形式结构:一是将程序性条款集中独立成章;二是在保护措施的逻辑框架之下,将不同文物类型中涉及“公权行使”以及“义务履行”两方面的实体性条款进行总结,归纳出其中具有共通性内容要素,并形成独立的章节。此外,针对“考古挖掘文物”“进出口文物”等具有显著特殊性的文物类型,将其单独罗列成为独立的章节。
(四)制度内容的优化
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文物保护法》的制度内容进行充实。以德国拜仁州文化遗产保护法为代表的成文规范在具体运行过程中遭遇各类问题的原因最终可以归结为制度本身的漏洞和瑕疵。在反思德国“前车之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物领域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文物保护法》的制度内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增加文物概念的抽象化描述。现有《文物保护法》第2条针对文物本身采用列举性的界定方式,未能对文物类型的扩张和发展留有充足的规范空间,因而需要引入文物资格以及文物价值等规范构成要件来进行概括性表达。二是实现文物登录的常态化。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例,文物登录可以克服中国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的局限性,从而适应文物保护扩大化的内在需求。《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对此只是进行了笼统性的规定,因而中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应当对登录的条件、程序以及效力等事项予以进一步明确。三是合理界分出土文物的所有权。中国《文物保护法》第5条将出土文物划归为国家的做法欠缺周延性,漠视了现实中私人利益的存在。因此,《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应当将出土文物国家所有权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出土的无主文物以及所有人不明的文物。相应的,诸如有主墓葬中的陪葬文物应当归属于私法上的继承人,但是古墓葬中陪葬品除外。
五、结 论
德国联邦州在文化主权的框架下,基于社会思潮的推动纷纷制定了各自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德国联邦议会则针对“防止德国文化财产流入国外”的事项制定了专门的《文化财产保护法》。德国通过直接适用欧盟条例或者间接转化欧盟指令的方式来“调适”本国的保护政策和措施,并且还通过批准或者加入国际条约或者公约的途径来融入国际保护的大潮之中。此外,司法裁判案例群也逐渐成为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规范体系中的成文立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但是也存在诸多拭待解决的问题,并主要体现为制度层面的结构性瑕疵和内容性缺失。比较而言,数量众多的司法判例在现实中也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不仅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体系内的解释补充,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了规范续造和内容创新的功能。德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始终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主线而向前运动,并且呈现出国际化、欧洲化和去国家化的发展趋势。德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所形成的成果经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实样本和理论参考,为此,中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应当对立法理念进行转换,对立法模式进行升级,对形式结构进行重塑,对制度内容进行优化。
——写在《文物保护法》修订征集公众意见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