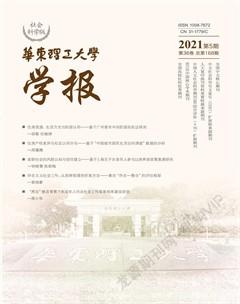流散族群、侨务政策与本国发展:中印比较的研究
[摘要] 印度和中国都具有悠久的移民流出史,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都具有规模庞大的海外流散族群社区。两国如何理解海外流散族群社区和本国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解如何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这又如何影响了两国的侨务政策,并进一步影响了本国发展?两国在这方面的经历有何相似和相异之处?本文以“迁移—发展关系”范式为主要框架,从海外汇款、海外流散族群带来的直接投资和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的流动三个方面,比较中国和印度两国与各自海外流散族群的关系、两国政府所采取的相应侨民政策,以及这些给本国发展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迁移—发展关系”這一范式。
[关键词] 流散族群 侨务政策 “迁移—发展”范式 中印比较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来华印度商人的跨国网络和融入适应研究”(16BSH017)、华东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团队建设基金项目“我国居民对接纳来华跨国移民的态度及其生产机制研究”(JKE022123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玉琴,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性别与发展、流动与迁移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1)05-0114-11
一、 导言
中国和印度具有悠久的移民流出史。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20》指出,2019年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居住于中国以外的移民人数为1070万,排在印度、墨西哥之后。而印度作为世界第一大国际移民来源国,目前居住于国外的印度移民人数为1750万。规模如此庞大的海外流散族群(diaspora)如何影响母国发展?
总体上来看,海外流散族群如何影响本国发展,是处于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大多要面临的议题,也是国际发展学和跨国迁移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个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被学界和发展组织及机构广泛关注,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形成两次讨论高潮,形成了“迁移—发展关系”(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范式。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近年跨国移民和难民规模的大幅增加,学界再次对该范式产生了兴趣。虽然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但该范式所观察到的迁移对本国发展影响的着力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海外移民(尤其是短期劳工移民或者近期移民)汇往母国的“海外汇款”(remittance);二是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的流出;三是海外流散族群(尤其是较早移民中的定居者)向母国的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这三点也成为学界和发展机构考察“迁移”对“发展”影响的主要领域。
作为世界第一、第三的国际移民来源国的印度和中国,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和海外流散族群社区建立联系。那么,两国如何理解海外流散族群社区和本国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解如何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这又如何影响了两国的侨务政策,并进一步影响了本国发展?两国的案例对“迁移—发展关系”范式有何启发?本文以“迁移—发展关系”范式为主要框架,从海外汇款、海外流散族群带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的流动三个方面,比较中国和印度与海外流散族群的关系、两国政府所采取的相应侨民政策,以及这些给本国发展带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迁移—发展关系”这一范式。
二、 “迁移—发展关系”范式
如上所述,作为国际发展和国际迁移重要议题的“迁移—发展关系”范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虽然其核心问题都是关注“迁移”如何影响“发展”,但这三次历程中的侧重点是不同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对“迁移—发展”关系的关注点主要放在“汇款”(remittance)上面,即移民向北方国家的迁移一方面可以填补后者劳动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汇款以及回归之后的技术和知识转移来助力全球南方发展中母国的发展。这个阶段的“迁移—发展关系”范式带有一种发展主义现代化的乐观看法。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发展”本身被“依附”(dependency)所取代,认为“迁移—发展”的关系反映的是一种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中心—边缘”的关系,因此迁移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发展”,而是“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迁移—发展关系”范式开始关注“欠发达”和“迁移”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欠发达”导致发展中国家高学历高技术人才从全球边缘迁移至中心的全球北方国家,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这会进一步加重其欠发达的状况,从而加剧了全球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不平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之前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乐观看法有所回潮。这一时期对该范式的新兴趣基本上抛弃了“迁移—发展”关系中的负面观点如移民的汇款是否会造成来源地更大的经济依赖,而主要聚焦在迁移对发展的正面效果。大部分学者将移民看作推动发展的能动者,迁移将给移入国/地和移出国/地都带来有益的发展。
“迁移—发展关系”范式的第三个阶段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的主张。首先,迁移所带来的汇款极大地提升了移民来源国的减贫、商业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近些年,从早期主要关注经济汇款即外汇给本国经济带来发展外,学者也提出了“社会汇款”(social remittance)的概念,指的是在移民过程中,在移入地和移出地之间,除了金钱,观念、实践、社会资本和认同等文化性因素也在循环。其次,虽然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的外移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人才流失”(brain drain),但是近些年来一些研究也表明,这些人才可能会通过“人才循环和联动”(brain circulation and linkage)的方式显著加速信息和技术向母国的流动,从而促进母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论他们是否回归。最后,不仅仅近期移民能带来汇款,那些在东道国定居的流散族群社区成员也仍然可以通过或短或长时间的暂时回归服务母国。他们和母国之间的联系得到重视,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侨务政策。本文正是在第三阶段的“迁移—发展关”系范式的框架下讨论中国和印度的流散族群在海外汇款、直接投资和人才方面与两国的联系状况,两国与之相关的侨务政策,以及这又如何影响了两国的发展。
三、 流散族群与母国:关系的发展及侨务政策的调整
流散族群社区并不是天然和母国就有紧密联系的。海外流散社区在母国眼中的形象如何,母国是否与其建立密切的往来,各国的情况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在同一母国之内,这种联系也可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首先以印度为例,在前独立时期,民族主义领导人强调印度民族与其海外流散族群团结关系的重要性。但在1947年独立后的时代,政府逐渐采取与海外流散族群社区“积极分离”的政策切断了这种关系。尼赫鲁政府在不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旗帜下,鼓励海外印度人融入东道国社会。直到20世纪70年代,流散的海外印度人社区才被印度政府视为会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一支关键力量,从而重新恢复了双方的关系,并力求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中国也经历了相似的变迁。在19世纪中期以前,居于海外的华人通常被历届政权视为叛徒或者罪犯而被忽视。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对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追求,时任当权者开始意识到这个群体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可以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正是在那个时代,“华侨”一词被创造出来,指称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这一策略是有效的,海外华人华侨在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后来抵御日本侵略的抗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种联系在1949年至1978年之间被切断。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海外流散华人社群的联系得以重新建立,并随着新时期走出国门的国人数量的增加而不断加强。而这一时期,在官方话语中,“海外关系”不仅不再被视为危险的、有罪的,反而经历了一种“升级”(upgrading),成为一种“爱国的”、有潜力的资源。
由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再次认定海外流散族群将成为助力本国现代化和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从而调整本国侨务政策,建立与海外流散族群社区的新关系。两国都在本国海外迁移史和当前流散族群社区构成的基础上对海外移民进行了区分,不过两国的工作机制有所不同。
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到1991年之间针对海外流散族群社区的态度还不十分明确,而1991年之后逐步建立起一个分化的侨民政策框架。它主要表现为将海外印度人划分为三个不同的范畴,针对不同的范畴实施不同的侨民政策。非居住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s,NRIs),是指拥有印度护照和印度籍但居住在海外的印度人。印度海外居民(Overseas Citizens of India,OCI)多是指1947年以后移居海外并取得东道主国家国籍的印度人。自2006年开始,三代及以内移居海外的印度海外居民可以向印度政府注册申请并获得OCI卡来确认OCI的身份。印度裔外国人(People of Indian Origin,PIO)则是一种更广泛的文化身份,指殖民时期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的后裔。2002年以后,四代及以内移居海外的印度裔外国人可以向印度政府申请PIO卡。这三种身份在印度所享有的权益是不同的。NRIs虽然不居住在印度,但享有印度公民所能享受的權益。2010年,印度政府规定,只要NRIs能在选举日回印度指定的投票点,他们也有投票权。而OCI除了不具有投票权和被选举权外,可以享有多种权益,比如给予持卡人15年的访印免签证旅行权,并且如果持卡人停留时间不超过180天,不必向警方登记。持卡人在经济、金融和教育领域内可以享有和NRIs可比拟的设施使用权等。PIO卡持有者享有的权益要少于OCI卡持有者。他们通常被认为在感情上是和母国最疏远的一群人,他们的印度认同“稀薄”,和母国纽带脆弱。
中国在1978年后重新与国(境)外流散族群建立了联系。与印度相比,中国制定了更广泛的国(境)外流散族群社区参与的政策和制度机制。为了便于工作,中国政府也从概念上对国(境)外流散族群社区成员进行了区分,比如“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官方话语中,出现了“新移民”这一范畴,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虽然有操作上的区分,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的侨民政策更侧重于包容,即和所有华人建立情感联系,无论其国籍或移民时期。这种政策重点在于鼓励他们重新加入建设祖国的运动中,不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知识技术上。
四、 海外汇款、外国直接投资及本国发展
流散族群对母国经济发展在资金上的支持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海外汇款(remittance)和外国直接投资。作为海外资金的两种来源形式,海外汇款比外国直接投资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力,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多是投向了发达国家,而海外汇款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另外,和直接投资相比,学界对海外汇款对移民来源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看法,是有争议的。有观点认为,海外汇款主要是用于购买家庭生活必需品或者其他消费而不是投资,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有限。
而中国和印度的流散族群在海外汇款和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形成有趣的对照:印度接收的来自流散族群的海外汇款多于中国,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21世纪早期,中国接收的来自国(境)外华人华侨的直接投资要远多于印度接收的来自其海外流散族群的直接投资。具体来说,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20》,2018年全球侨汇流总量为6890亿美元,其中汇入印度的金额是786亿美元,汇入中国的金额为674亿美元,分别占据全球第一、第二大侨汇汇入国。在国(境)外直接投资方面,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国接收的国(境)外直接投资比印度多出16倍。并且在中国接收的国(境)外直接投资中,来自国(境)外华人华侨投资[本族裔直接投资(ethnic FDI)]的比例远高于印度。例如,1991—2000年,中国接收的本族裔直接投资在总国(境)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都超过一半,在最高峰的1991年、1992年,甚至超过了80%。而同期,海外印度侨民对印度的投资占印度接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的年平均值只有13.8%。以上差异也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表现的异同提供了一种解释,即两国同样具有亮眼的表现,是因为两国都从流散族群社区获得了巨大的资金支持;而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速更快,是因为中国获得了更多的本族裔投资,而印度从流散族群社区中获得了更多的海外汇款,而海外汇款多用于消费而不是促进生产。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流散族群社区海外汇款和直接投资背后的动机分别是什么?政府如何理解海外汇款和直接投资,又分别采取了怎样的政策?
(一) 海外汇款:印度高于中国的原因分析
印度和中国成为全球两大侨汇汇入国,也经过了一段发展历程。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侨汇汇入国的印度,在1975年接收的海外汇款还不足5亿美元。但自此开始迅速发展,到2005年增至221亿美元,2015年更是增长到689亿美元,直至2018年的786亿美元。在中国,1982 年流入的移民汇款也仅有6.16亿美元,到 2015 年增至 639 亿美元,到2018年进一步增至674亿美元。相较于中国,印度的国际移民汇款保持了更大幅度且持续的增长。多种原因造成了这种国别差异,比如流散族群的规模、移民类型和母国侨务政策等等。
首先,两国流散族群社区的形成史和移民类型不同。印度在南亚地区之外最大的离散族群社区主要分为两个类型:20世纪70年代前往海湾国家的合同劳工(contractual labor)、20世纪50年代开始迁移到英国以及1990年以后迁移到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professional)。而这两类人员与母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表现在巨额的海外汇款,而不是直接投资。20世纪70年代以后迁往海湾国家从事短期合同工作的印度移民数量剧增,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专业技术人员迁往欧美发达国家,提升了移民的层次,同时也带来了收入的提升。这些都给母国带来了海外汇款的巨大增长。而中国在东亚、东南亚以及欧美的流散族群社区整体上比印度的流散族群社区更有资源、具有更多的商业经历。在中国开放后,他们带来更多的是资本、制造技术以及和全球市场的广泛关系,而不是汇款。
其次,母国侨务政策形塑了中印两国海外汇款的格局及差异。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来自流散族群社区的海外汇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吸引印度侨民将资金存入印度的银行,印度政府就开始实施各种针对印度侨民的特殊存款计划,允许印度侨民办理各种银行账户,比如非居民(境外)卢比账户、非居民外币账户、非居民普通账户等。同时,政府放宽汇率和资本管制,增加海外汇款的渠道,并减低正规渠道汇款的成本。而从海外向中国汇款的成本远高于印度。世界银行2020年有关海外汇款价格的数据显示,印度2020年前三季度平均的汇款成本是5.34%,而中国同一时期平均汇款成本是8.25%,高额的手续费、货币兑换费用等对中国的海外汇款流入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二) 外国直接投资:中国高于印度的原因分析
在来自流散族群社区的直接投资(本族裔投资)方面,中国远多于印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这与母国的侨民政策、营商环境、母国与流散族群社区之间因地缘等因素形成的经济网络等因素相关。首先,中国和印度的经商环境有差异,中国的营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高于印度。世界银行《营商报告2020》(Doing Business 2020)显示,在“营商便利度排行榜”上,中国在190个国家中排第31位,印度排第63位。
其次,两国在吸引族裔直接投资方面的政策力度不同。自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個“升级”的过程。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办)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侨联)等机构先后建立,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海外华人华侨投资的优惠政策,比如:1988年推出《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1990年通过《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保障归侨和侨眷的财产权、继承权和接收汇款的权利;2001年推出《国务院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以此来鼓励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房地产和高科技产业。但相比较而言,印度政府在吸引海外印人印侨投资方面就不这么具有策略性、措施也不够精准。海外印人印侨和其他国家的外国投资者一样,面临着一些障碍,主要包括在某些部门的投资受限、官僚体制复杂、工作拖延效率低以及腐败。
最后,两国在地缘、文化亲缘性和地区性经济网络方面有所不同。中国的流散族群社区相对集中在亚洲,地理上相近,并在当地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社区(比如东南亚)。另外,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南部地区形成了某种区域性经济整合,制造业形成了地区性生产链条。而印度的流散族群比较分散,无法形成这种地区性生产链条。此外,海外印人印侨中的高收入者更愿意从事教育、健康服务和工程等非商业的职业而不是做生意,因此海外印度社群的成员更多的是向母国汇款而不是直接投资。
五、 从“人才流失”到“人才循环和链接”:状况及政策
在过去20多年里,随着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全球对高等教育日益重视。但伴随着这股潮流的,是对欠发达地区高学历高技术人才向发达地区迁移所导致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担忧。但近几年,研究者也注意到外流的高技术人才也会通过“人才循环和联动”(brain circulation and linkage)的方式促进母国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显著的例子。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国际学生最大的两个来源国。这一方面造成了两国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也因为两国人才短期或长期的回归以及两国政府的侨民政策,促进了中印两国科技的发展,虽然两国展现出的背后作用机制有类似的地方同时也有所差异。
两国政策相同的地方在于,都强调离散族群社区中的高技术人才和本国之间的族群纽带,都着力培养这些人才和母国之间的情感联系,由此网罗一批向母国进行知识和技术转移从而推动母国经济发展的“情感公民”,即虽然可能拥有他国国籍,但仍然对母国充满感情的移民。
但两国海外高科技人才的情况以及各自的政策也有不同之处。在中国,根据教育部的数据,1978—2018年,共580多万名学生学者出国留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回国人员人数则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1978—2018年,共360多万学生学者归国,占同期出国人数的84.46%。2008年之后,学生学者归国速度显著增快。除了这些学成归国定居的人才,中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推行各种政策来鼓励离散族群社区中的高技术人才通过短期或长期的回国访问计划为国效力。通过这些计划,他们在中国的各种高科技园区和欧美如硅谷等高科技地区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些人才在中国创造了显著的“溢出效应”,推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和升级。中国政府的各类政策主旨是通过上文提到的情感联系将这些人才重新纳入“建设祖国”的队伍中。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人才,中国政府政策的侧重点不同。比如,针对“华人”群体,中国政府鼓励他们从远处在经济上贡献祖国、建设祖国。而对“华侨”和“新移民”,中国政府更强调吸引他们长期或短期的回归,通过各种政策鼓励这些人才长期“回国服务”或者短期回归“为国服务”。因此,中国政府针对高科技人才的侨务政策主要建立在一个“短距离”参与的基础上,鼓励回归和定居。同时,给予海外人才进入中国工作市场的特权。
美国高科技人才中印裔占据较高比例。截至20世纪末,硅谷约三分之一的软件和工程人才都是印裔。印度政府也积极建立软件科技园并推进规章制度的自由化来提高“人才循环”,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为印度服务。印度海归人员为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中国的情况相比,印度的海外高科技人才不仅参与“人才循环”(brain circulation),而且还积极建立正式的网络来促进“人才链接”(brain linkage)。他们和留在印度国内的同胞交换有关东道国工作和生意机会的信息,担任国内公司的顾问,或者建立印裔专业人士的全球网络来促进知识转移。印度政府在吸引这些流动的人才时,采用了分化的、阶层化的侨民政策。针对为印度汇回大量汇款的(海湾地区)NRIs,印度政府给予一些特别的福利政策,比如为他们的子女设立大学奖学金、只有他们的子女才能享有的打折学费等等。而OCI群体中有较大比例的高技术人才,他们多在发达国家定居,获得了东道国国籍。对于这些海外人才,印度政府和他们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系,积极地把他们发展成印度在全球北方商业上有声望的积極代理人和政治上的游说者。对于和印度制度化联系最弱的PIO群体,目前印度政府试图通过“认识印度”等项目培养他们的后代和印度的情感联系。和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公共部门是不向非印度公民开放的。同时,印度不允许双重国籍,这就意味着那些获得东道国国籍的印裔人才只有永久回归,才能加入公共部门。而那些选择外国国籍的印裔高学历高技术人才只能创业或者成为印度和全球北方高科技之间的人才链接者。从这点上看,印度的侨务政策主要建立在一个“长距离”参与的基础上,更鼓励印裔高科技人才从海外回国短期访问进行知识转移,而不是在印度就业和定居。
六、 结论和讨论
庞大的流散族群社区如何影响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的国际移民来源国,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如何受到其国民海外迁移的影响?中国和印度与各自的流散族群社区关系的发展,印证了第三阶段“迁移—发展关系”范式的主要观点,即迁移所带来的海外汇款、族裔直接投资和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的流动都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虽然两国侧重点以及作用机制可能有所不同。
但重要的是,通过梳理中印当权者对流散族群的态度和政策及其演变史,我们会发现第三阶段“迁移—发展关系”范式可能忽视的一点是:“迁移”和“发展”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即“迁移”会对“发展”造成影响;而应该是一种双向的关系,即“迁移”能对“发展”造成影响以及能造成何种影响,是以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移民向母国汇款、进行(经济、社会)投资和知识转移是有先决条件的,这些先决条件包括良好的政治和制度条件的发育。中国和印度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在母国政府将流散族群社区认定为会促进本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并推出良好的侨民政策,投资能获得可预期的收益的情况下,海外流散族群(包括已在移民国定居和近期的移民)才会积极向母国汇款、投资、传递新的知识和技术。
“迁移—发展”关系是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结构性持续变迁的一部分。对于两者的关系,一方面需要置身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另一方面需要对结构性变迁和能动性层面都做细致的分析。而自2020年以来,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情况,再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如何影响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主要国际移民来源国与其海外流散族群社区的关系?海外汇款和族裔直接投资将如何受目前的经济局势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情感公民”的策略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是否仍然可行?海外流散族群社区的成员是否会被要求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选边站、表忠心?这些是新格局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责任编辑: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