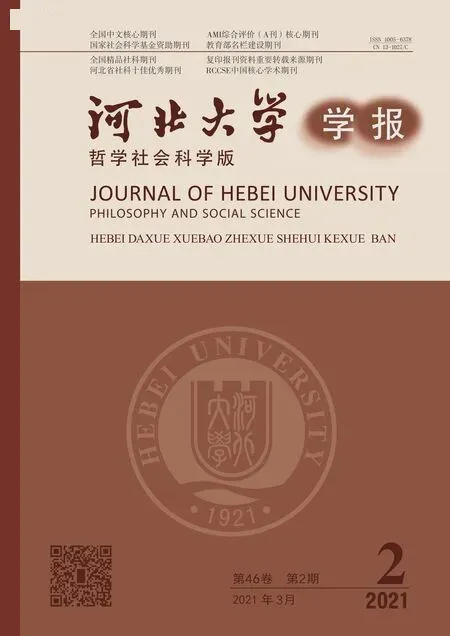《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
张乃芳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3)
“天人合一”被视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但它被儒者明确提出最早已经到了汉代,“在明清时代已经有了信仰、信念和套话(共同赞颂语) 的特征”[1]。《论语》①文中所有《论语》原文均以《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本为准。中显然没有“天人合一”的明确提法,甚至孔子本人也没有建构“天人合一”的意向。但是,《论语》微言大义,其文本的内涵非常丰富而又极具张力,深入其间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天人合一”思想的义理脉络,这在一定程度上铺陈出儒家“天人合一”的着力方向。后来,通过孔子的弟子和后世儒家思想家的不断传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天人合一”理论。
一、《论语》中孔子对“天”的“敬而远”与“敬而行”
《论语》中是否隐含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意蕴?隐含了怎样的意蕴?阐释清楚这两个问题,首先要考辨孔子对其中的“天”有怎样的态度与立场。孔子对“天”的“敬”在《论语》中是有迹可循的,所有谈及“天”“天命”②《论语》中直接谈到“天”“天命”的共计十六则,在下文的三个层次中分别是九则、四则和三则;《论语》中谈“命”的次数多达二十四次,但多指命令、寿命,意指“天意”“天命”的有两则,在下文的“天意人承”“天命人成”中有详解。的内容里都没有任何言语态度上的疑,或者行为上的逆;相反,充分表现出“敬”,具体体现出听从、承受,甚至是配合、成就的不同层次①“听从、承受”主要指后文的“天意人承”层面,“配合”指“天启人合”层面,“成就”指“天命人成”层面。。进一步分析孔子所“敬”之“天”的特质,还可以区分出其神秘性与神圣性的不同侧重,孔子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是“远”前者而“近”后者的。孔子从不深究为什么应该敬“天”,“天”的绝对权威从何而来,具体又是如何作用于人的。他与这类神秘性的问题始终保持着距离,不去讨论。所以子贡评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论语·公冶长》)孔子对“天”的听从、承受、配合、成就等都着力于在言语行动上、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并由此而成就天的神圣性。
这一“敬而远”与“敬而行”并行的理路,在孔子面对鬼神问题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明晰。他在言语和行为上都表现出“敬而远”的一面。例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是孔子通过言语上的存而不论与鬼神的神秘性保持距离,他无意讨论神秘性本身的为什么、是什么与怎么样。再如,涉及“人”(或“民”)与“鬼(神)”之间的问题时,孔子向来近人远鬼。如:“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
但是,“敬鬼神而远之”并不是孔子鬼神观的全部,还应看到孔子在祭祀鬼神时的言语和行动都不容丝毫质疑与差错,是“敬而行之”。他赞颂大禹敬鬼神的表现时说:“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在祭祀的过程中,孔子严格遵守各种仪轨,“虽蔬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他强调参加祭祀要身心俱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祷”是人与鬼神沟通的重要方式,孔子十分强调其纯粹性,“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这两则都特别强调不以人的功利性需求而逾矩,其意也在维护鬼神的神圣性。其中,引发注家学者争议较多的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他们的争论看似讨论孔子是否相信鬼神,但其实质的焦点在于祭祀时鬼神的“在”究竟应凸显其宗教性、神秘性的“实在”,还是强调其道德性、神圣性的“应在”②诠释“祭神如神在”时,学者们大多将鬼神的“在”解读为“如在”,这就隐含了鬼神可能并不“实在”的意味,不过,明确指出鬼神“不在”的学者并不多见,有墨家的墨翟、近现代哲学家的劳思光、日本儒者的中井履轩和山片蟠桃等;孔子本人也未曾明确否认过鬼神,因此可以说孔子是否相信鬼神真实存在并不是学者们争论的真正重心。大多数学者如孔子一样并不执着于探讨鬼神的“在”或“不在”,而是把重心放在鬼神“应在”对祭祀者诚敬的重要影响上,也就是弱化其宗教性、注重其道德性;有学者特别强调鬼神的“实在”,典型代表有朱熹,他认为人与鬼之不过是气的聚散之别,祭祀者足够诚信,便能“感格”鬼神,这是强调其宗教性,还要看到朱熹强调宗教性目的恰恰是筑牢道德性的根基。可见,宗教性与道德性是相通的,因此还有一些有学者如梁漱溟等着力论证二者间的联通。本文以“实在”描述鬼神“在”的宗教性,以“应在”描述其道德性。。前者相信祭祀时鬼神是“实在”的,祭祀者足够“诚”“敬”就能够与鬼神达成感通;后者则不执着于深究鬼神是否“实在”,而更注重通过鬼神的“应在”彰显祭祀者内心“诚”“敬”的重要性。儒者在鬼神问题上宗教性与道德性的区别体现在他们的态度言行上就是“敬而远”与“敬而行”的区别。
《论语》中孔子面对“天”“天命”和“鬼神”时的内在思维理路并无二致,逻辑上区分出神秘性与神圣性的不同侧重,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孔子在“敬”的前提下,会有时远时近的不同行为抉择,即对其神秘性“敬而远之”,对其神圣性则“敬而行之”。具体到“天(命)”与“人”关系上,《论语》中有十六则直接谈及“天”或“天命”的文本,他们与其他相关文本相互诠释印证,可以从其内在意涵的侧重上区分为“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面。
二、《论语》中“天意人承”的层面
《论语》中有九则内容①这一层面直接谈到“天”的文本有九则,按照它们在这一部分的出现顺序依次是:11.9,3.24,7.23,9.5,6.28,3.13,9.12,12.5,20.1。谈到“天”时,都指的是超越的、神秘的、神圣的“上天”,根据其内涵的差异,可以细化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平之事、抒发不平之气时所喊的“老天爷呀”一类的感叹。如: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颜渊不幸早逝,孔子痛失最心爱的弟子,他痛彻心扉,因而发出了呼天喊地式的悲叹。这是他感性情绪的日常化、世俗式表达,这里的“天”超越、神秘、不可把握,是作为情感倾诉的象征性对象。
第二类“天”是具有神秘威力的“上天”,有“天赋”“天定”意味②此类的天常常被释为“天命”,如《论语注疏》中,多把此类之天视为“天命”。本文对“天”与“天命”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从《论语》中“天人合一”角度看它们在不同层面内涵与侧重。这一类的“天”与后文所说“天命”的内涵有所差异,主要侧重体现天赋的力量。,是圣人君子的德性之必然、行为之必然的有力保证。如:“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这里,仪封人为了强调“夫子为木铎”的毋庸置疑、不可更改的必然性、神圣性,用神秘的“上天”来做保证。再如:“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两则中,孔子认为,圣德之所生、斯文之所丧,均由超越、神秘的“天”来定夺。再如:“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这一则中,原典的含义究竟何指,学界仍有诸多争议,但“厌之”的主语多指“上天”,并且神秘的“上天”可以起到确保孔子言论的正确性。总之,这四则内容中的“天”都蕴含了神秘的“天意”“天定”等意味。有学者认为应该理解为“天命”,但是,不同于后文所说的“天命”,这里的“天”并不参与到人具体、实质的活动过程之中,即不影响夫子如何为木铎、圣德如何得以生、斯文如何得以丧等具体的圣贤行为,他们都是独立于、超越于人的具体活动的“神秘”之天。
第三类的“天”也指“上天”,同时还含有“天理”之意,其重心在于借“天”理无可置疑的应然说明人的行为须合“礼”的当然。如,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其中,王孙贾所说的“奥”与“灶”,代表的都是俗世之势,他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环境中实现依势得利。孔子也关心现实政务,但从不止步于成功处理政事这样短期的、具体的目标上,而是指向更为根本的问题,这里他提到“天”,就是要凸显人的行为合天之“礼”的重要性和根本性,从而向王孙贾提出警示,说明凡是违礼之行即使暂时得势、得利,也终将导致失败。“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这里,孔子批评子路的重点仍然是子路不应当做违礼之事。这两则中神秘之“天”是引子式的存在,目的是借“天”的神圣性引出孔子所提倡的“行为必须合礼”这一观点。
第四类“天”明确凸显了孔子“行仁由己”的观点③这里的天,有天定命运的含义,但是人无法参与的天定命运,与后文的第三重意涵有所区别。。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尽管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无奈在前,子夏要表达的重心却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的坚定性与重要性,换句话说,天意是可以搁置的,人事却必当尽力。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这里,尧向舜禅位时指出,舜应当听从天意、顺天即位,但是,紧接着却用更长的篇幅要求舜做到勇于担当、严己宽人等。可见,在尧看来,舜被定为天子是顺天意,但成长为好的天子更需要尽己之力。可以看出,这两则“天”的出现,试图引发的并不是对“天”神秘性的关注与讨论,也不是人们应该怎样听“天”意、顺“天”命的问题,而是如何尽“人”事行仁道的问题。
上述文本中的“天”具有神秘性质,含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孔子没有明确否定他们的存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对外在神秘之天的肯定与敬畏。但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把这一类的“天”真正纳入他们的生命活动之内,而是在情感上采取了“敬之”“远之”的态度,在行动上单向承受天意,无需对天意予以回应。在处理天人关系问题上,他们并未具体指导儒家圣人君子如何言、如何行,也就是说,孔子接纳“天”的神秘性与神圣性,但更突出的是其神圣性。
在这一逻辑层面,天人之间的关联不是双向的天人互通,而更多体现为“人”对“天”敬畏的情感与态度。后世儒者也沿袭了这一情感价值取向,对天保持了足够的敬畏之情,同时又拉开了与神秘“天”“鬼”等的距离。
三、《论语》中“天启人合”的层面①这一层面直接谈到“天”的文本有四则,按照本文出现的顺序依次是:2.1,8.19,17.19,19.25。
《论语》中,孔子在如何为政、如何为君,以及如何成就君子人格等问题上,展现了“天启人合”,即“由天启人,以人合天”的思路,这是他“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容。
孔子沿着“由天启人”的思路,指出为政的核心在德。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里,孔子论证为政应当以德,用的就是北辰“无为而成”的自然之理,如范祖禹所释:“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2]77其中的思路正是由自然品质出发,启发式地推出人应当具有相同的行为准则。具体来说,就是效仿北辰的“居其当居之所”的行为。所以,为政最为重要的原则就应当是“为其当为之德”。
谈到为君、为圣的关键,孔子更强调“以人合天”。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这里,“唯天为大”之后紧接着说的是“唯尧则之”。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圣功可颂的原因正在于圣德可敬,而圣德可敬的根由恰在于圣者对天德的模仿。所以,圣人高于俗子,君子高于小人,共同的原因就是圣人君子懂得崇敬天德,并善于对其模仿、学习,能够做到德行方面的“以人合天”。
在论说君子人格的时候,孔子同时运用了“由天启人”与“以人合天”。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里,孔子凸显了天“不言而行”的美好品质和因此产生的强大力量。在他看来,正因为天有“不言而行”的大德才拥有了能“行四时”“生百物”的大成就。所以,他要求自己具有同样的德行,以“予欲无言”(《论语·阳货》)约束自己。同时,他也要求君子应当“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要做到“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等。这里,孔子正是由“不言而行”的“天德”推出同样的“人德”,通过圣人君子对“天”的模仿实现天人之间的合德。
孔子的弟子思考问题的时候,也曾将天与人并立。如子贡所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子贡以自然之天的高远难及,喻孔子境界的高远,我们同样无法望其项背。这仅仅是一个比喻,上升不到“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高度,但这显然是将自然与人并立而言。同时代流传的、被孔子重视的《诗》,即后来的《诗经》中,大量运用了“比”“兴”的手法。“比”是由人到物,“兴”则是由物到人,无论人与物谁先谁后,都是将自然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艺术表现手法,它由物而起,落实到人,表现的正是“由天启人”,体现了天人之间的自然同构,运用了典型的“天人合一”的思路。如《诗经》开篇的《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自然之境、自然之情入手,继而引发君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心声,在自然天地之间,由动物之情引起君子之爱,用的正是由天到人、以人仿天(合天)的思维方式。孔子熟读《诗》、重视《诗》,在《论语》中不止一次提到《诗》的重要性,如“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季氏》),《诗》可以兴、观、群、怨,乃至事父与事君(《论语·阳货》)等。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孔子及其弟子将天人并立而谈,乃至对“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运用,也就合情合境、自然而成了。
由此可见,孔子面对自然之天的时候,坚持“天”与“人”相合,运用的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遵循了“本天道以立人道,立人德以合天德”[3]的理路。同时,“天”依然是外在的,因为“天”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人”向“天”模仿、学习的关系,尤其是圣贤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对“天”的效仿。这里并不关注“天”的品质的神秘性,强调的是“人”对“天”神圣性的模仿。
后世的儒者也大力传承了孔子“天启人合”的思路。如《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后世儒者多通过“天启人合”的思路解读孔子这一对川流不息的感叹,如程子阐释说:“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2]153朱熹则认为孔子的指向是“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2]153。可见,程、朱等这些后世的大儒从孔子的川流所叹之中,都把握到了其中蕴含的深层脉络,即孔子的所思所言超出了对自然状态的简单描述,是沿着“天人合一”的思路,指出君之为政、人之为学等都需要通过模仿天德才能有所成就。
四、《论语》中“天命人成”的层面①这一层面直接谈到“天”或“天命”的文本有三则,按照本文出现的顺序依次是:2.4,16.8,14.35。
《论语》中的“天命”虽然神秘,但不是某种具象性的存在,不是人格神的意志;“知天命”“畏天命”也不是人趋向于天或者天降落到人的某一单向过程,而是“天命”在儒君子的生命中逐渐“生成”,并由儒君子从多重维度不断“证成”的天人双向互动过程。
天命“生成”的关键在“知”天命和“畏”天命。知天命是孔子人生过程中非常重要又十分难解的阶段。他回溯自己阶段性变化的成长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是圣哲晚年时对学生回顾、评判自己的一生。他向来追求“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所以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会随意堆砌文字,而应秉持同一标准对自己人生不同时期予以精准的定位,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他所求的一贯之道正是仁道。以此为据,孔子大约在十五岁左右有了求学仁道的志向,三十岁学仁道而有所立,四十岁能笃仁道而不惑,五十岁时仁道与天命有了沟通,六七十岁学仁道、习仁道时身心已然能渐入化境。同时,孔子的仁道还是从心出发的,曾子用“忠恕”二字概括孔子的仁道,忠和恕的字形都从心。朱熹则认为,忠和恕是尽己与推己两个层面,如他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2]102。牟宗三也说:“仁的表示,端赖生命的不麻木,而能不断地向外感通……是从内心发出的。”[4]因而还可以据此阐释孔子的成长变化,即他的人生自从十五志于仁道,就开始了从心出发的历程:心志所向,心有所立,心之不惑,心知天命,心身相通,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结合上述“仁”与“心”两个维度看,在“知天命”之前,孔子是由心出发追求仁道,经过了立志、有成、不惑三个阶段,到四十无所惑的时候,显然已经是仁心清朗的至高境界。但是孔子又有后面五十、六十、七十三个阶段的新进境,可见正是在“五十而知天命”时孔子追求境界的层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知天命”是个承前启后的关节点、转折点,如徐复观所言:“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一生学问历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五十以前的工夫所达到的结果,是五十以后的进境所出自的源泉”[5]。在“知天命”前,孔子的仁道追求境界着重于人的经验性体验,在达到经验领域内的不惑至境后,天命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在他的生命中“生成”。可以说,孔子自“知天命”起,打开了人、天之隔,开始追求人与天命相合的、超验境界的“天人合一”。
“畏”天命与“知”天命相连,包含“认知”与“证知”两重含义、两个过程。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君子“畏天命”体现的正是对天命庄严审慎的认知与证知。首先,如朱熹所诠释,天命是“天所赋之正理也”[2]235,是“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2]79,可知君子对天命之“畏”,并不是因恐惧而产生的怯懦与退缩,而是认知到天命的神圣高远之后,由衷而生的敬仰之情,继而开始自觉自愿、慎而又慎地证知天命。这就是神圣的天命在君子生命中逐渐“生成”的过程,既是君子对自己心灵本然的忠实守护,也是他们对神圣天命的追求,因而是人与天命双向互动的过程。相比之下,小人追逐的是眼前小利,常常心随物迁,显然不能守住本心、不能知晓超越性的天命是什么,所以小人不畏天命不是勇敢,而是无知,因无知而不懂得敬畏、不能与天命沟通,可见对天命之“畏”造成了小人自我之知和天命之知的双重丧失。其次,证知神圣的天命时,儒君子的“畏”重在审慎,儒君子的证知过程是慎而又慎的,他们庄严审慎地诠释、践履了对天命的敬畏。这是一个因敬生畏、由畏护敬的过程。
天命进入到君子的生命中,就开启了君子“证成”天命的过程。以孔子为例,他自五十起,一直持续对天命的证知,经年累月,孜孜以求,才达到了后来“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实现对天命的“证成”。儒君子对天命的证成是历尽艰辛、庄严审慎的,是成己且成物的过程。
儒者认知、证知天命的过程就是他们追求仁道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自我成就的“成己”过程。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这里“命”与“君子”之间,并不是君子被动、单向地接受宿命的安排,而是“成为君子”与“知命”之间的相互实现,这与孔子思想中天命人成的双向过程是意涵一致的,可见这里的“命”是指“天命”。钱穆诠释说:“惟知命,乃知己之所当然。”[6]儒者认知、证知天命必然成为君子。他们追求修养君子“盛德”,自觉自愿地心向仁道,向上向善。儒者既追求君子“盛德”,也追求君子“大业”,尧帝兼备二者,既有合于天的盛德,也有闻于世的大业。孔子赞叹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可见,《论语》中的“知天命”是通过君子自觉自愿地承担、履行道德使命和社会使命来实现的。
《论语》中还有用“天”表述“天命”内涵的。如“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知我者其天乎”强调的是“天”知“我”;不怨天尤人、不归因于外,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下学继而实现向上通达于天,这是“我”知“天”。这种天人间的相通相知,正合孔子“天命人成”式双向成就的思路。“下学而上达”还指证知天命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儒者证知超验天命的过程是根植于现实生活、不离日用常行的,但又能不陷于此,体悟到超越经验日常的超越境界,如二程所说:“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2]215
五、影响了中华民族担当境界的精神样貌
《论语》中隐含并在后来真正成熟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不同的层面存在逻辑意义上的差别,相对来说,第一个层面更多是对“天”的神秘性的“敬而远”,后两个层次是对“天”“天命”的神圣性的“敬而行”,是对其模仿、成就的过程。当然,在《论语》文本中,天意、天启、天命之间的意涵是动态交融、难以辨析的,在态度上都是至诚至敬。不过,在行为层面三者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即天意外在于人的行为具体,天启单向指导人的具体德行,天命则与人生成了双向的交互印证。了解这些差别既有利于把握儒家思维方式的逻辑层次性与独特性,也有助于分层次实现其现代转化,推动其在新的时代生发出新的意涵。
今天中国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和乐于担当的精神境界都与《论语》文本中包含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内在精神上相契相合。
第一,形成了理性积极的担当之勇。西方传统文化中,天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天人二分”。在《圣经》中,全能的神对人的生死祸福、使命担当等都有绝对控制权,其中的“天赋”有“天定”“天赐”的含义。如《圣经·创世纪》中,世间万物包括人,都是通过“神说”而产生的,神赐予人生命、形象、食物,乃至福祉等一切。人需要做的就是全然遵从神的安排。西方传统文化如基督教中,人的一切使命源于全能的神,因而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一切行为都必须合神意,凸显“天意”的绝对价值。在西方文化中,天赋与天命没有根本区别。
《论语》中的“天赋”和“天命”不同于西方宗教中重“天”的、神秘的、被动的宿命论。《论语》中的“天赋”则有两重含义:在“天意人承”的意蕴层面,重在借“天”的神秘性说明人之言行的正当性,尤其是儒者仁道担当的正当性;在“天启人合”的意蕴层面,则是从天道是什么出发,引出人道的应当状态,论证儒者担当的应然性。重心都在“人”而不在“天”。
《论语》中的“天命”是主动、积极而又理性的。孔子了解天命的神秘性,却更注重它的神圣性。同时,他也不认为天命是某一具象性的存在或者目标等,儒君子并不被天命所困,反而在明知人能力有限的同时,更加注重天命赋予我应当做什么、能够做什么的一面,激发出为我当为、承担使命的勇气与魄力,追求积极有为、成己成人的担当人生,兼顾内圣与外王。“天”的神秘性、掌控性的让渡,使得儒者的勇敢担当不依赖于天,而是更取决于自我的理性抉择。在《论语》中有“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之说。忧道与忧贫不是简单的两种抉择,而是会因此区分出君子与非君子,从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生状态。所以说,君子忧道,是理性抉择下充满勇气的生命担当,是在自身生命中将天赋使命与理性自觉进行的对接。孔子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呈现的正是这样融天赋、天命与理性于一体的生命担当。可见,不知所起的神秘“天命”促成了圣人君子对仁道担当的敬畏与践履。
孔子的“吾从周”也能印证这一点。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7]他认为,殷商因为笃信“祖先神”,依赖他们天上庇护的神秘力量而有恃无恐。周文王却在西岐“阴修道德”,突出德性的重要性。孔子所“从”的正是周之德。
第二,形成了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儒者证成天命任重而道远,却能在艰辛中挺立,不过孔子并没有其与悲观、无为相连,反而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等,表现出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与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展现了从容和悦的圣人气象。儒君子在证知天命的时候,也以圣哲为榜样,在压力中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弘道求仁的动力,把自己和榜样联系到一起。
同时,儒者也沟通了自我与天下。他们对大德的追求不是孤立、静态的、仅限于自我道德成就的,而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系中动态实现的,是由爱亲,到爱君,再到泛爱众这一不断外推的过程拓展出去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都秉持了同样的理路,沟通了自我“盛德”与天下“大业”,消弭了自我成仁与天下归仁之间的距离。
第三,形成了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儒家的担当还是自觉的。先秦儒家和道家都是从自然之“天”出发寻获生命实践的根由,都主张“以人合天”,即修人德以合天德。但是,老子盛赞的是天道的“自然”,因而主张人们顺应自然,无为而成;孔子则看重自然的生生不息之道,所以力倡圣贤君子自觉自愿、刚健有为的生命担当之勇。可见,儒者有为担当的人生并不是天然生成,而是后天自觉抉择的结果。孔子的生命担当就有高度的自觉性。他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这凸显了人的行为的自觉性、主动性。他坚定地将行仁的自觉性贯穿于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勇于在各种情形下担当。如生时的仁道担当要不畏艰险,须臾不离,孔子将其描述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即使面对死亡威胁也不会动摇,直至“死而后已”(《论语·泰伯》),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可见,孔子主张在生命行进过程中,为行仁道要不计得失、不避生死,甘之如饴地担当起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孔子担当的勇气、远大的追求、乐观的态度等都极大影响了后来的儒者。如孟子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2]478(《孟子·尽心上》)他强调尽道才能知命、成命,他“天降大任”式的人生使命的担当中,充满了不畏艰辛、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义无反顾的豪气。儒家经典《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2]5其中的“止于至善”“知止”所说的“止”不是停止,不是了解了自己能力的有限性之后而被动、无奈地接受,而是指“必至于是而不迁”[2]5,是志之所向的高处。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进一步高扬了儒者的人生使命所在。今天,我们要观往知来、温故而知新,开创出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