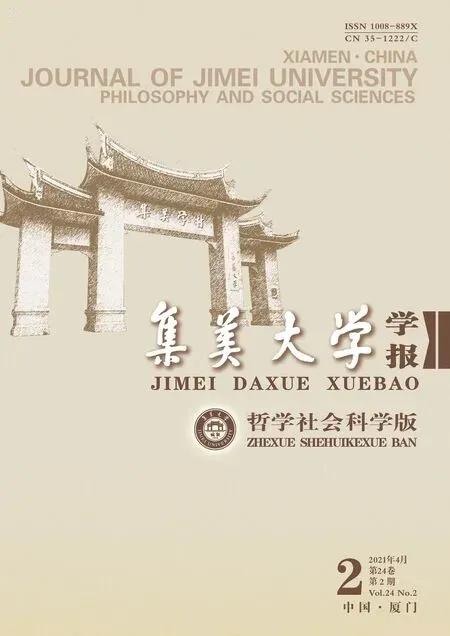小学与经学:段、顾之争与校勘学的取径
钱 寅
(河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律学院,天津300222)
段、顾之争是清代乾嘉时期学术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则公案,向来聚讼纷纭。由于段玉裁在当时学林的辈分较高,声望较重,因此检讨此则公案的时候学人或直接是段而非顾,或尽力做弥缝的论述,阐发两方各自具有的合理性。然而,由于段、顾二人所争论的内容是围绕《礼记》所展开的,而《礼记》是经学传承中重要的文献,所以笔者认为裁判两家争论的关键在于经学本身。有鉴于此,妄揣拙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既有成果的检讨
自段、顾相争以来,很多学者都纷纷表明态度。由于段玉裁在学界内的地位和声望,支持者良多。阮元的《礼记正义校勘记》以及晚期朱彬的《礼记训纂》都采用了段氏的主张。近年随着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围绕段、顾之争的讨论硕果累累,若每条必举则恐行文啰嗦,今择其要者陈述如下:
李庆在《顾千里对校勘学的贡献》一文中,简要概述了段、顾之争的焦点,同时对一些学者评价顾氏为“死校”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其“以不校校之”的校勘准则是不可易之论[1]。王欣夫在《顾千里集》的整理前言中虽然也提到了段、顾之争,却只是做了对历史事实的简单陈述,对段顾之争并没有持明显的态度。
漆永祥认为这次论争本身反映了乾嘉学术界内吴、皖两派的矛盾冲突[2];在探讨段玉裁的“理校”时,提到其自信太甚,以至于不求版本和佐证,往往武断而误;反之,顾千里的校勘原则更加稳妥[3]。罗军凤提出了段玉裁“义理校勘”的校勘方法,即推求义理,义理先行,“合于己意者用之,不合己意者改之”,无形中具有了宋学的特征。罗氏还指出段氏的这种方法不仅与顾千里不合,而且与其他乾嘉学者龃龉,段氏的这种义理校勘不仅存在于《礼记》中,也存在于《左传》中。最终罗氏认为段氏这种义理校勘往往是主观武断的[4]。刘跃进认为段、顾之争,有性格、学术等多方面的因素,并且认为两人在争论中的言语都有失当之处。而在学术层面的讨论上,刘氏认为两人的争论还是围绕段玉裁的“理校”与顾千里的“不校”展开的[5]。
武秀成《段玉裁“二名不徧讳说”辨证》一文,围绕段、顾之争中“二名不偏讳”和“二名不徧讳”孰是孰非的问题进行全面详细的考证,最终认定段玉裁的“二名不徧讳”是缺乏根据的[6]。在这个问题上,之前的学者往往服膺段氏的意见,因此武氏所进行的这番检讨确有振聋发聩之用。乔秀岩《学 〈抚本考异〉记》一文,虽然没有以段、顾之争为主题,但是结合顾千里《抚本礼记考异》来清理清代校勘学和文献学上的问题,对比了段顾不同的风格,认为顾千里的校读方法更具有文献学特色,而段玉裁以及其他清代考据学者的考据方法过于主观。[7]
通过对上述诸家论著的评介,不难发现学术界在关注段、顾之争的问题时,主要还是围绕着校勘原则和校勘方法来讨论,认为二人的争论来自校勘方面的不同。这应该是接受了晚近叶德辉提出的“死校”“活校”概念,以及陈垣所总结的四种校勘方法。于是,才有了段玉裁为“理校”、顾千里为“死校”的说法。然而在段、顾之争的时代,两家并不能预设下“理校”“死校”等概念。同样,将段、顾之争归结为吴派、皖派的矛盾,也是受到晚近对清代学术史描述中进行分派的影响,故而将段玉裁归入皖派,将顾千里归入吴派。至于吴派求古、皖派求是的刻板印象,可能会使学者误以为段氏的校勘更胜一筹。但是,从史实来看,吴、皖之间似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皖派领军人物戴震也离不开吴派代表人物惠栋的指点提携。而且在上述所及论文中,学者们也发现皖派的段玉裁在“求是”之路上有不少武断之处。更何况两派治学的终极目的都是“求是”,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从校勘和学派的角度来考察段、顾之争,容易陷入一个循环的怪圈,即将后人总结的概念简单地回用到前人的问题上,而无法在问题本身的认识上有所突破。
武秀成的文章从文献本身出发,循着段、顾二人争论的理路进行考证,考察两家持论的依据,并进行评析,从而得出段非顾是的结论,与前辈学者的观点虽有不合之处,但有理有据使人信服。武氏的论文也给我们重新检讨段、顾之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即从两家争论的观点、佐证等内容着手,考察其持论的根源,进而从学术的内部获得真知。乔秀岩的文章提出了顾千里能够尊重文献流传中的历史面貌,这一点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乔秀岩论说此为经学与文献学的不同,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经学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别,不同的版本源流自然是其一方面,但两汉经学尊重家法,不同家法间传承的文本自有不同,也是造成经学文献于流传中产生不同的重要原因。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经学与文献学也有契合之处,即倘若要传承一家的经学,就要守住其家法文本的本来面目。
基于这种思路,笔者认为既然二者所争的是《礼记》的内容,那么就应该以《礼记》为中心来考察。众所周知,传统经学在传承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遵家法,否则经学的特质就会消失,《礼记》也会随之成为普通的历史文献。《礼记》是一部记录历史的历史文献,这种观点虽然和我们今天的认识相契合,但并不符合古代儒生的观点。所以,要检讨段、顾二人的观点对立,则先应承认《礼记》是经,其传承自有家法。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有一定的判断标准。
二、段、顾的学术分歧
段、顾之争主要围绕《礼记》展开,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如:《礼器》“先王之治礼也,有本有文”,该不该有“有文”二字?《曲礼》“二名不偏讳”,该作“偏” 还是“徧”?《祭义》的“四郊”与《王制》的“西郊”,该何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郊”“西郊”之争,段、顾两家各自持论,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中间又涉及了“饗”“乡”等多个经学问题的辨析,内容复杂且艰深,若不进行相关的考证分析,则很难把握问题的真貌。
(一)关于《毛诗·椒聊》经传
段、顾之间的异见虽然围绕《礼记》展开,但最早出现的分歧并不在于《礼记》,而在于《毛诗》。因此,探其源才能更好的检讨两家的差异。段玉裁尝勘定《毛传》,嘱托顾千里为其补充修订。从顾千里的《与段茂堂大令论椒聊经传书》中可以得知,顾氏“鹿鹿未得从事”[8]100,并未能完成段玉裁交代的任务。但是,顾千里在书信中对段玉裁《椒聊》一诗的校勘提出了异见。《毛诗·唐风·椒聊》凡两章,每章结尾均是“远条且”三字,段玉裁拟将首章改成“远修且”,次章仍作“远条且”。
顾千里首先指出了段氏的校勘没有版本依据,其云:“此诗两章末句,自唐石经以下诸本,无不皆作‘远条且’,考《释文》《正义》本亦如此,日本国古本则皆作‘远修且’。”[8]100接着顾氏利用经、传、笺的内容来考据日本国古本作“远修且”渊源。顾氏云:“传于首章下云‘条长也’,笺云‘椒之气日益远长’,经云远条,传云条长,故笺云远长,毛以长训条者,谓条修同字,其义兼包条鬯在内矣,两章为字既同,训自无异,古本之作修,正依此为之耳。”[8]100顾氏通过毛传和郑笺之间关系的推导,颇具逻辑地论证了日本国古本作“远修且”的根据。然后,顾氏借助毛传的内容和毛氏传诗的体例来探讨“远条且”句与毛传的对应关系,其云:“至于末章之传云‘言声之远闻也’,乃毛总传全诗,非别为次章‘远条且’一句更发传也,例见《采苹》《木瓜》 传末矣。”[8]100顾氏还指出:“尊定于此经首章作修,次章作条,既非诸本,亦非古本,合中外两书偏据者各一,此不能无疑者也。”[8]100除了考定段玉裁校勘改书的依据之外,顾氏还指出段氏为了迎合自己所改动的经文任意增减传笺内容的行为。其云:“于首章下之传,增为‘修条长也’,而云‘此言树’云云,审尔,则郑笺此不得云‘椒之气’矣,笺既云‘椒之气’,必所据之传不作‘修条长也’,而郑意不以传为谓树枝长,尤所显然。《正义》引‘厥木为条’,解此条长,以笺订之,决知其误,而尊定反有与之合者,此又不能无疑者也。于章末之传云‘声当作馨’云云,审尔,则岂非即郑首章笺所云‘椒之气’者乎?于已改之传,则诚两章有别,于未改之笺,适见其无分,此又不能无疑者也。大抵唯以章末之传为次章‘远条且’别发,而经、传遂俱不可通,不得已,辗转改易以迁就之,然仍未见其可通也。”[8]101顾千里发现段玉裁在校勘时并没有确凿的版本依据,便轻易改动经文;改动经文之后,发现传、笺无法说通,便以己意增减传、笺。然而,段氏虽然着力于弥缝,可是经、传、笺三者之间的抵牾仍然存在。据顾千里所言,“阮中丞撰《考证》时所以不载尊定而别作云云者”,原因就在于段氏的解读和校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通过这一条意见的疏理,可以发现顾千里在校勘经书的时候,首先要找到可靠的版本依据。这并不是只要其他版本有异文就要依之校改,而是要先仔细分析异文产生的原因和依据;其次要将目光放在整部经书的体例之内,不可拘泥于一字一句而就事论事;最后,所校的经书本身包含注释和解说,所以校订文本的内容一定要能与注释解说相对应匹配,不然经自经、传自传、笺自笺,当然也就失去了经书中经传笺体系的意义和本来面貌。
顾千里重视探讨传、笺在《毛诗》传承中的作用,与之相反,段玉裁则认为“周末汉初,传与经必各自为书也”[9]5,并在其校理的《毛诗诂训传》定本中“釐次传文,还其旧,而每篇必具载经文于前者,亦省学者两读也”。[9]5段氏认为经书成书最早,其次是毛传,再次才是郑笺,所以应该按照这样的次序来编排。同时,段氏发现毛、郑相异处,也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和说明。如他在《诗执热解》中用毛传来解读“执热”的意思“濯所以救热也,礼亦所以救乱也”[9]16,认为郑笺所云濯其手“转使义晦,由泥于‘执’字耳”,接着便用杜甫的诗歌作为引证来支持毛传。这种解读是放在《左传》引诗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看似有理,但完全忽视了《毛诗》和《左传》皆为古文传承,其大义自然应当是相近或相似的,而郑氏的解读自有其他家法传承,不宜妄断是非。相似的例子还出现在《奚斯所作解》中,段氏认为“以‘奚斯所作’上属者,乃郑笺之说,非古说也。郑笺之异于毛者多矣,不当混而同之也。……此语滥觞于《颜氏家训》,以附会康成,而非诗序及毛、韩古义”[9]16-18。可见段玉裁对毛传、郑笺的认识仅限于此,并没有意识到《诗经》传承的家法异同。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段玉裁才敢于不顾传笺的内容而改动经文。
相比段玉裁对传、笺的认识,顾千里从经学家法入手似乎认识得更为深刻。顾千里在《答张子絜问读毛诗注疏书》中说道:“他经注疏皆一家之学,《毛诗注疏》则传、笺实两家之学。……夫传也者,全是古文家法,笺也者,或用今文诗破传,或用今文他经说以破传,或又用古文他经说以破传,此自是郑氏家法,不专主古文,亦不专主今文。明乎此而后二家之体例憭然,经与《正义》亦憭然也已。是故《正义》解毛,不拘有传无传者,转转所受习古文家之说也。《正义》解郑,决知其破毛之意者,转转所受郑氏学之说也。近人鲜明此者,于是往往泥传害笺,及泥笺害传,甚至误执郑诗为毛诗,辄驳《正义》,余波及乎《释文》、唐石本,岂非读此书之大病耶?”[8]101-102据此可见,顾千里深明经学传承中的家法问题,准确地指出毛、郑之间差异的根源在于家法的不同。这明显是比段玉裁的议论更符合经学本身的要求。
因此,顾千里从经学本身着手校书,就必须顾及严守家法的文本传承,这样才能保持经学的特色。而段玉裁未能领会家法之奥,故而往往臆改经文,虽然有时也显得有理有据,但已经丧失了经学本身的特色。掌握这一点,就容易探讨段、顾二人相争的内容了。
(二)关于“西郊”“四郊”之争
“西郊”“四郊”之争主要集中在《礼记》的《王制》和《祭义》篇上。《正义》本的《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郊,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郑注云:“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东序、东膠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于西郊。”[10]观此则知经注明文“西郊”。但是,段玉裁认为这里的“西郊”当作“四郊”,是孔颖达作《正义》时把经注弄错了。段氏所凭据的直接理由是《祭义》篇中“天子设四学”,注“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段氏认为《祭义》用了《王制》的话,其中作“四学”“四郊”,故而能够证明《王制》中的“西郊”当正为“四郊”。在段玉裁之前,孙志祖《读书脞录》中引《北史·刘芳传》来证明“西郊”当为“四郊”的误写。这个观点和例证为段氏所欣赏,进而辗转引述。《北史·刘芳传》中说道:“《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又说:“‘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大子齿。’ 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11]1544这样看来,段氏所言当作“四郊”确实有一定的根据,而且段氏又引皇侃本、崔灵恩说,以及杜佑《通典》中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校勘观点。详细论述见段氏所著《礼记四郊小学疏证》等。[9]275-280
顾千里对此所持有的观点正与段玉裁相反。顾氏认为,“四郊”之“四”当作“西”。顾氏引《正义》云:“天子设四学者,谓设四代之学:周学也,殷学也,夏学也,虞学也。”又云:“天子设四学,以有虞庠为小学,设置于西郊,是天子设四学,据周言之。”顾氏说:“正义所释,据郑此注,最得其解。郑注四学为四代之学,与四郊迥不相涉。其云‘谓周西郊之虞庠也’者,周即《正义》所谓‘据周言之’者也,上至虞四代,周立虞庠在西郊,是设四代之学含夏、殷也。注文周字在上,虞庠在下,故《正义》自周学也逆数至虞学也,不用虞、夏、殷、周顺数,用意下语,极是精当。而下云‘以有虞庠为小学’至‘据周言之’云云,即复申其义也。”[8]74在这里,顾氏先把《正义》 和郑注之间的关系疏理清楚,并且从《正义》的体例出发探究注疏的真实意思。虽然段玉裁广征博引各种文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这一点非常基础的工作是其所没能做到的。既而顾氏说:“《正义》本此注是‘西’非‘四’字,决然无疑,后来本误改作‘四’,并《正义》中设置于西郊亦改之,非是。”[8]74这是顾氏提出的校勘意见,至此顾氏的校勘仍然没有在注疏之外参考另外的他校资料。而对于致误的原因,以及对段氏所征引的证据,顾氏都有着自己独到的意见,他说:“其所以致误者,因《正义》释此注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为四郊皆有虞庠,故遂改之耳,不知此《正义》但广异说,即《文王世子》‘凡语于郊者’《正义》所谓‘或遍在四郊者’耳,皆不取为义。彼说从西郊不从四郊,已详,此可互见,不假更说矣,改者未识厥旨也。皇侃之义,以《北史·刘芳传》证之,实出于王肃,或肃义作四郊,《正义》序已言皇氏时乖郑义,无足怪者,崔灵恩亦以肃义解郑,与皇同见,《通典》乃或又据《芳传》所引,并欲改《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亦作‘四’,致为巨谬。”[8]74顾氏指出了《正义》 在疏通经注时的常用体例,认为《正义》罗列皇侃的说法并不是要以此来解释经注,而是存备异说。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因为“疏不破注”是唐代义疏中最重要的原则。如果引用皇侃之言而使郑注与经文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种疏应该算是失败的,何况顾氏也举了《文王世子》篇存备异说的例子,可见其说并不是空言。
顾氏指出皇侃、崔灵恩、刘芳可能是传承了王肃的家法,考《北史·刘芳传》中刘芳不仅征引了“周四郊为虞庠”的注文,还引了王肃的“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11]1544的观点。进一步考察《刘芳传》的上下文,可知刘芳这样做的本意是为了进言议定北魏太和二十年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这一制度是否合乎礼制,并不是严谨的经学研究表述,其中或许存在着为了认定四门置学符合礼制而有意剪裁材料的可能性。这样看来,以刘芳之言为证就显得似乎不太适合。何况,不同家法间所传的经典文本和解读自然是不同的,因此也就无法勉强定论哪一家的本子是对的,哪一家的本子是错的。因此,顾氏说:“礼是郑学,贾、孔具有家法,难以他文强生同异。”[8]75汉代经学传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家法,正如古文经和今文经在文本上会有差别一样,不同家法之间也会有或多或少的文字和解说的差异。顾氏的观点明显是出于守家法的立场,如果用王肃所传的经来校郑玄所传的经,那无异于要毁掉郑氏家法,而依附于郑玄注经的《正义》,也将随之瓦解。对于经、注、疏的校勘,顾氏的意见是从全局上把握经义,而不是局限于一篇或一段,这即是所谓的通经之学。顾氏云:“《王制》此文与《内则》文同,既不容有误,况彼郑注曰‘或上西’,又曰‘或贵在郊’,又其下凡三言西郊,苟如所改,无一可通,而彼《正义》以及贾《仪礼乡射疏》等所言亦无一可通矣。”[8]75段氏在校勘时,虽然也关注了《礼记》的其他篇,但他只看到了《王制》和《祭义》的差异,没看到顾氏所列举的这些经典中相同之处。
“西郊”还是“四郊”,这是段、顾之争的导火索,也是焦点。关于两家争论的文献还有顾千里的《礼记祭义郑注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考异》《学制备忘之记》《周立学古义考》《祭义四学为四代之学解》《与段茂堂大令论周代学制》等等,段玉裁的《礼记四郊小学疏证》《与顾千里书》《答顾千里书》《与顾千里论学制备忘之记》等等,此处仅举其各自的主要观点来论述。从讨论中可以看出,段氏的校勘也是有理有据的,但问题在于他对其他篇章和材料的信任度甚至要高于本经本注,没有意识到经学文献的特殊性,没有把汉代经生的家法摆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种校勘方法应该算是史料的校勘,而不能算是对经学典籍的校勘。放在今天整理文献的情况下看,或许段氏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放到经学学术背景下就会显得失去经学味道了。因此可以说是否具有经学特色,才是段、顾之争的根本。
(三)“饗”“乡”考辨
段、顾之争虽然围绕着“西郊”“四郊”就《礼记》中学制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在当中还涉及了“饗”“乡”这对文字及背后礼制的考释。简单来说,段玉裁广泛地占有历史语言材料,利用其研读《说文解字》所得到的文字学知识,结合经文充分进行考辨;顾千里更偏重于经文本身,利用经文自有的体例来诠释文字在经学体系内的含义。这样看,段氏的考释或许真的可以接触到文字的古义,但未必适用于经文;顾氏虽然在文字学上的成就不及段氏,但在说经上或许还是更契合经学本身的要求。
在这场争论中,段玉裁曾有七篇《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从顾千里《与段茂堂大令论周代学制第三书》中的信息可以得知,段氏连作四书后,顾氏才予以回复:“茂堂大令阁下:旬日中作书四通,数千余言,得无劳乎?侧闻阁下以仆不答为罪,夫去冬答阁下之两书,阁下既以为罪矣,今又云然,然则进退罪也,为阁下之朋友亦难哉。”[8]105段氏以为顾氏拖延不回复,是因其学力不济,故在《答黄绍武书》表达了这种讥讽:“虽然愚为《四郊小学疏证》以正于千里,千里经两月之久,为《学制备忘之记》驳之,其立说大凡曰:乡、遂学与小学、大学为二类,绝不相通;乡饮、乡射可行于乡、遂,断不可行于小学、大学。《王制》注中‘郊学’非《文王世子》注之‘虞庠’,郊学乃乡学耳,乡学在王城中及远郊境上,中间百里之宽,绝无乡学;以愚与彼五札考之,乡饮、乡射行于小学、大学者,经有明文,国中绝无乡学。千里自谓潜心三礼,自必所据博精畜而未发,故不惮四五请正而一字未复……苟其确凿指示,令愚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愚方愧之不暇,谢之不暇,北面执经为弟子之不暇……”[9]332其中段氏奚落之态,跃然纸上。因此顾氏在自己的回复中讽刺道:“阁下责仆以答者,果急欲闻仆解阁下所不解者乎?”[8]105顾氏针对段氏的发难,详细解答了段氏的三个“不解”:其一是“乡饮、乡射可跻于大学,而何不可行于小学”[8]106;其二是“国中何以有乡学、 州序、 党序”[8]111; 其三是“郑注《文王世子》、《王制》两言郊学,何以必不同实”。[8]111这三点本是顾氏《学制备忘之记》中提出来回应段氏《礼记四郊小学疏证》的,而段氏对顾氏持论的不理解也表现在《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数篇之中。
针对段氏第一个不解,顾氏说:“异哉斯言也,乡饮、乡射又可跻于大学乎哉?”[8]106令顾氏诧异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表达过二乡礼能跻于大学、小学的观点,不知段氏的疑惑从何而来。考《学制备忘之记》中顾氏的表述是:“乡射在州序,乡饮酒之正齿位在党序,而二者亦可就乡学行之而已,从未尝有乡射、乡饮酒行之于虞庠小学者也。……今段乃将此射、乡二事本来只得行之于乡学以下者,忽跻而习之于虞庠小学,解经如此,不亦异乎?”[8]76可见顾氏持论乡射、 乡饮酒礼不独不能行于小学,亦不能行于大学,段氏在争论中转述顾氏之言时作了不小的改动。段氏在第一篇《与顾千里论学制备忘之篇》中提出:“《说文》水部‘泮’下曰:‘诸侯乡射之宫。’夫泮宫,诸侯之大学也。而曰‘乡射之宫’,则诸侯于是行乡射之礼,必先行乡饮酒之礼矣。《说文》‘雍’下曰:‘天子饗饮辟雍。’依食部‘饗’下曰:‘乡人饮酒也。’与《毛传》合,然则此饗饮即乡饮也。辟雍,天子之大学也,而曰‘天子行饗饮处’,则天子行乡饮酒礼于是矣。”[9]306段氏认为以《说文》 来训释字义,则“饗”即乡饮酒,可以行于大学。这里主要的逻辑是用“饗”的“乡人饮酒”意来解读“雍”下的“饗饮”,从而得出辟雍是乡饮酒之处。需要注意的是,段氏展现的是一种非常精妙的训诂技巧。但是,也能够看出,段氏对顾氏之说的曲解,来源于自己的成见。
顾氏对此则云:“夫天子国君大学但有饗,又有大饮酒之饗,小学亦有饗,又谓之饮酒,有何乡饮酒?不过其礼之篇已亡,而乡饮酒亦可名饗,故阁下因思以乡饮酒冒之耳。”[8]106顾氏认为段氏之所以会将乡饮酒跻于大学,是因为其将“饗”的含义与乡饮酒等同起来。继而举出《月令·孟冬》“是月也大饮烝”,郑注“十月农功毕,天子诸侯与其群臣饮酒於大学,以正齿位,谓之大饮,别之于燕,其礼亡,今天子以燕礼,郡国以乡饮酒礼代之”为证,说明大饮之“饗”与乡饮酒礼并无关系。接着顾氏仍举《毛诗》及郑笺、《周礼》及郑注等资料以论证“饗”有大饮酒和酒人自酿之酒的含义,目的就是要考定“饗”不能简单地被视作乡饮酒。同时,顾氏还考辨了段氏所援《说文》的条目,首先校勘大徐本“诸侯乡射之宫”中的“乡”字讹,当为“饗”,与“雍”条下的“饗”合观,则一为天子大学之饗,一为诸侯大学之饗。顾氏又指出,《说文》“饗”字因为从乡,所以许慎“取乡人饮酒之名乡者”[8]107,与“雍”“泮” 下的两个“饗”字不同,不能直接缀合为说。顾氏认为“字之为用,并非一义”[8]107,复以《说文》 的通例来证明其说,至于这一点顾氏以为段氏“以《说文》 之学名其家者”[8]107理当心知肚明。对于段氏援《豳诗》毛传为佐证,论述乡饮酒能行于大学的做法,顾氏指出:“毛以为此乡饮酒之在乡学者,则阁下所当知也,至郑改之以为此大饮酒之在大学者,则又阁下所当知,而阁下能割截毛之半、郑之半,凑合成一事,使乡饮酒在大学乎?”[8]108顾氏的语气中的确有讥嘲之意,但毛传、郑注理应为段氏这个等级的学者所熟悉。有鉴于此,段氏将毛、郑各取一半凑合成一事,很有可能是因为不明家法。前面已经谈到,顾氏认为毛传和郑笺多不同处是因为毛传为古文学,郑玄则不偏主今古,自是一种家法,所以郑玄往往用其他家说来解读《诗经》。依不同家法所传承的经说,当然不能勉强凑在一起了。这或许是段氏对家法不甚明白的最好证据吧。
然而,反观段氏在其他文章中通过文字的引申、假借等意来证明“饗”本意即乡饮酒,除此之外亦有同音假借为“享”义者。段氏著《享饗二字释例》云:“祭祀曰享,其本义也。故经典祭享用此字。……而燕饗用此字者,则同音假借也。……乡饮酒之礼曰饗,引申之,凡饮宾客亦曰饗,凡鬼神来食亦曰饗,而祭享用此字者,则同音假借也。”[9]285又云:“献于神曰享,故凡下献上曰享也。……‘饗’之字起于乡饮酒,故从乡、食,会意。……其礼主乎养老。……隆于宾客之礼,皆谓之饗者,谓敬之如养老也,敬之如尊贤也。是其名因乡饮酒而立也。最重曰饗,次曰食,次曰燕。”[9]286段氏最基本的根据自然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继而用《周易》《诗经》《尚书》《周礼》《论语》等经典中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解释,其说可详见《享饗二字释例》一文。总之,段氏从文字学上立论,认为“饗”“享”二字各有引申之用,至于在经典中有混同之处,①如《礼器》“大饗其王事”等,本为下献上之意,依段氏当用享而经用饗者。盖为汉儒同音假借者。段氏对自己能够掌握文字本义和引申假借义颇为自负,其云:“近有莽人,于‘饗’字绝不知其本义以及引申假借之义,故略为言之,可以知叔重之精诣也。”[9]287所谓“莽人” 恐即指顾千里而言。②除了《享饗二字释例》外,段氏对于这个问题还有《说文饗字解》《乡饮酒礼与养老之礼名实异同考》,皆为论证饗即乡饮酒礼,这是与顾氏重要的分歧处。
通过“饗”字的论争,很难评论段氏和顾氏谁更高一筹。但是要结合校勘《礼记正义》经学文本的实际情况来看,顾千里之学全出郑注和经文本身,并不夹杂其他学说,而段玉裁则旁征博引,走着一条从小学到经学义理的学术道路。《礼记正义》乃唐代孔颖达为《礼记》郑玄注所作的疏,由于“疏不破注”的基本原则,所以从根本上来讲《礼记正义》也可算是一部传承郑学的著作。这样来看《礼记正义》的源头还是郑氏家法,那么顾氏本着郑注来理解经义,进而校勘文本,自然是符合家法,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段氏的校勘则一展其小学功底,从《说文》的体例到文字的引申、假借等用法,段氏无一不精,且征引文献不徒一家一经之言。这种广泛地从历史语言材料中取证,并且运用文字学的原理和规律,来进行缜密考证的做法,当然是非常高深精妙的,也能够弄清文字意义的渊源和流变。然而段氏的问题在于他所得到的观点可能并不符合当前经学文献文本所呈现的面貌,因此便会以己意改书。这就造成了有些校改虽然很有道理,但无法找到足够佐证的文本依据,即被称为“义理校勘”。这种校勘没有意识到经学家法的特点,将不同家法传承的内容杂糅并勉强统一为定本,无疑是泯灭了经学家法。由此可见,段、顾之争的根本在于对待经学文本时是用小学的方法,还是用经学的方法。
段氏第二则不解是“国中何以有乡学、州序、州党”,因为段氏在《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的第二、第三篇中着重论述了“城中无乡”的说法。为了回应段氏,顾千里认为“国中四郊通为六乡”[8]109,并引据三礼的经文和郑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使段氏“城中无乡”的论点置于《周礼》经义之中无法说通。顾氏还标榜自己的立场是“就经言经”[8]109,这样一来就和段氏以小学和其他文献来说经的立场有了明显的界线。其实,顾氏的立场也不仅是严格地遵循经文,更主要的还在于谨守郑注。除了郑注之外,对于疏解郑注的孔颖达,顾氏也是抱着尊信的态度,这一点与段氏恰恰相反。段氏不信孔颖达,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搬出其师戴震来为己证明。段氏云:“闻之东原师曰:郑注有八九分,正义只四五分。故正义必分别观之,去其非,以求其是,淘其沙而金益见。愚守其说,不敢忘也。”[9]312关于戴震是否说过这些话,现在无法考证,在段、顾之时亦很少有人清楚。这样来看,戴震此番言论尚不适宜成为支持学者观点的论据。顾氏也讥讽段氏的这段引证是来源于“临终枕膝独受”[8]110,并且回应段氏不应盲从于近人的言论,要从经注正义的文本出发,仔细研读,细心体会。顾氏云:“但今举以奉告,皆经之正文,注之明说,不在五分四分之内,阁下倘必欲相贬,必谓之‘名不正’,必谓之‘正名百物谓何’?请阁下其问诸经,其问诸注,幸少宽孔仲远而已。”[8]110可见,顾氏通过一系列的举例,阐明了其在治学上的要求,即从经注本身着手,而不是从其他人的论述来草率判断。只有从经注本身进行的解读,才能最终回置于经注本身,不然就会像段氏一样盲目地批判注疏有错误。这也显示了顾氏治学的经学品格,与段氏由小学考据到解说经义的学路十分不同。此外,顾氏还揪出了段氏自相矛盾之处,段氏先说大学有乡饮酒、乡射之礼,后又说城中无乡,然而天子大学即在城中,这就无法说通了。
段玉裁在第一篇《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中提出《王制》和《文王世子》两篇中郑注两言“郊学”,应该是相同的。段氏认为《王制》“移之郊,如初礼”郑注“为之习礼于郊学” 可以为“虞庠在国之四郊” 之证[9]305,且与《文王世子》“凡语于郊者”郑注“语谓论说于郊学”名实相同[9]307。这即是顾千里所谓段氏的第三个“不解”:“郑注《文王世子》《王制》 两言郊学,何以必不同实?”[9]112顾氏对此的回应是:“夫郑注之为郑注,将上下贯通为义耶?抑画断上下而单以字面为义耶?”[9]112显然,顾氏认为理解郑注及经义要放到经文上下中去整体考察,不能单就一字一词而仓促立论,他觉得段氏的做法属于后者。顾氏驳段氏云:“《王制》注上文有‘郊、乡界之外者也’,一气贯下,而《文王世子》注不然,何能附会纽合之使同实乎?然则《文王世子》注‘天子饮酒于虞庠’,阁下能将通部《礼记》注内有饮酒字面者一一附会纽合使之同乎?”[9]112复按《礼记·王制》“移之郊,如初礼”郑注:“郊,乡界之外者也,稍出远之,后中年又为之习礼于郊学。”[10]确如顾氏所言段氏只截取了最后数字来作为自己解经的证据,当然是不严谨的。由于《王制》注中的郊学有严格的限定条件,自然也就不能简单地认定与《文王世子》注中的郊学是相同的。顾氏云:“字面同而不同实,注之通例,亦经之通例也。”[8]112结合前面所提到的顾氏驳斥段氏以饗为乡饮酒的观点,可见顾氏尤其重视同字异义的问题,而不是考定字的本义再以本义统一解释所有同字。这种根据不同的上下语境,对文字进行灵活且适应文意的解释,也算是契合郑氏家法的。而顾氏研究的基本路径就是整体把握经书和经义,这或许即所谓的通经之学吧。
(四)小学与经学之争
通过前面对段、顾之争的梳理,可以看出段玉裁对经文的解释和校勘是基于小学和考据的方法,顾千里对经文的解释和校勘是基于对经学家法的认识和经文经义的整体把握。当然小学和考据在传统学术中也是经学的附庸,但具体到实际校勘中则应该慎重采用。段玉裁用彼处同字的解释移置于此处同字下作注解,即是一种常见的训诂技巧,如前文所提到的乡饮酒在辟雍,以及《王制》和《文王世子》中郑注两处郊学被段氏用来互训,这些议论都略显仓促盲目。从检讨中可以看出段玉裁通过广泛征引材料以及进行颇具逻辑的考据来解释和校勘经典,往往会因为不识家法而引发问题,如用王肃一脉的观点来解读郑注就产生了抵牾,又如郑玄、许慎本不同家法,而盲目用《说文》来参验郑注也会造成很多抵牾。面对抵牾,段氏又利用其学识进行所谓的“义理校勘”,而没有充分考察经文文本的传承源流,这就造成了师心自用的不良学风。顾千里在寄给陈鲈的信中严厉批判段玉裁的学问,说:“大令素于小学类外多不寓目,只缘抵巇捭阖之心甚锐,偶闻何许人叹此云云,遂居为奇货。”[8]123虽然措辞略显刻薄,但确实道出了段玉裁的学问根底全在小学上的实情。
阮元在《浙儒许君积卿传》中引述朱筠之言“经学则有张惠言,小学则有王引之,词章则有吴鼒”[12],足见当时学者目中,经学和小学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而王引之之学和段玉裁之学往往被归入一派,这也证明了说段氏的经学并不纯粹是有根据的。当然,段玉裁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不可取,他想要探讨的是礼制的最初面貌。由于周代礼制很难考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利用文字学的手段努力去还原经书的本义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这其实是将《礼记》等经书当成史料来对待,视为考证周和周以前历史的重要资料,并没有体现其经学价值。顾千里所做的,则是努力去认识郑玄所传授的周代礼制的面貌。二者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另外,段、顾二人读书的方法和态度也有差别。顾千里在《重刻宋本仪礼疏后序》中说道:“经之不易晓,晓之必由注,经注之意不易晓,晓之必由疏,此读疏所以为治经之先务。”[8]131顾氏重视经、注、疏三者的关系,认为研习经义必须要通读注疏。同时,顾氏又指出段玉裁轻视注疏的问题,说:“若膺大令待其晚年别读《诗序》‘先王之所以教’郑注,而后始见其或不言文王、或言文王有不合,仍未述及贾公彦具有明文,转谓从前不能知此。”[8]130这一点通过前面的检讨也能体会到,段氏往往就经文中的字句、片段来征引他书进行考证,然后一旦发现与注疏不合,便师心自用认为有误。顾千里则是争取在郑注的系统内,结合经、注、疏三者,充分对校不同版本再形成校勘意见。而除了在校经、读经中细读注疏、谨守家法外,顾氏在校勘其他典籍时也会博引他书材料以作所谓的“他校”,亦可见其对待经学文献有着特殊的意见。
以往的研究者将清代学术分为吴派和皖派,顾千里属吴派,段玉裁属皖派,并认为吴派求古,皖派求是。从段、顾二人的学术旨趣来看,段玉裁通过考据力求得到最合理的经文文本,而顾千里在家法范围内去追求文本的正确性,的确体现了求是与求古的趋向。然而,放置在经学体系内则又能发现顾千里追求家法传承的准确性,而段玉裁则要超越家法以追求古礼,这样来看则成了段氏求古,顾氏求是。而钱穆在《经学大要》里讲皖派的学术实际出自宋学,大意是说:江永是皖派最早的人物,而其礼书纲目是讲朱子学的,又拿朱子自己的话来注解《近思录》,那么江永固然讲经学,至少也是个宋学家,戴震年轻时追随江永,其学问大部分是来自江永的[13]。段玉裁师从戴震,其学自然也是有宋学渊源的。而顾千里谨守汉儒家法,遵从汉人经说,与吴派惠栋相似,或可目为纯粹的汉学家。那么段、顾之争又可放在清代朴学内部汉学倾向与宋学倾向的视角下来考察。
乔秀岩在《学 〈抚本考异〉序》中提到顾千里是遵循文献学家的方法来校勘经典,有着保存古籍不同版本原貌的重要贡献,而段玉裁等则要结合不同文本校订出统一的定本。同样的观点,还出现在乔秀岩的《论郑王礼说异同》中,其云:“清代前期以前,各种经说往往比较接近王肃的观点,像《五礼通考》即经常采用王肃之说。而乾隆中年以后学者开始一味地推崇郑玄……但学者永远不会满足于纯粹的文献学,于是有王念孙、段玉裁等注重内容合理性的研究。尽管他们采用相对客观的音韵、训诂学手段,毕竟为了内容的合理性,不惜牺牲文献文字的复杂多样性,故文献学家顾千里与段玉裁水火不容。”[14]这很有启发意义。但顾千里之时并不能知晓今天所言的文献学是何物,所以窃以为遵循郑氏家法治三礼才是顾氏持论的根本,而保持不同家法下所传经文的差异性是其目的和追求。从两汉经学家法的角度来说,郑玄是杂糅今古且不守家法的。但正由于郑玄不守家法,遍注群经,从而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也造成了两汉其他家法的衰亡。没有了其他家法,郑氏所传就成了郑氏家法,为清代很多学者所推崇。乔秀岩在另外一篇涉及《礼记正义》的文章中论断孔颖达“必遵郑氏一家之法”[15],“疏不破注” 也是唐代经疏的基本原则。因此《礼记正义》本身也可以算是沿袭郑学的著作,所以在郑氏家法内进行研究和探讨才有经学的意义。
三、结 语
通过本文的检讨,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段玉裁的学问根底在于小学,重视广泛占有资料,利用逻辑思维进行考据以求得到统一确定的解释;顾千里的学问更保守汉代经学的家法,探讨问题重视分辨不同家法的差异和特殊性。治学根底的不同是二人相争的根本原因,两位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经典的整理和诠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已经不再是争与不争的问题了,而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作为后人,我们无法评论在当时的争论中孰优孰劣,只能说这两个走在不同道路上的人通过争论为我们呈上了一道精彩的学术大餐。仔细钻研和检讨这场学术争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东西:(1)能够对清代学术的细节问题拥有更多的认识,像小学和经学的差异,经学家法的问题,考据学者的不同治学风格等等,这些都是之前论述学术史时往往大而化之的。(2)能够对全面认识清代学者的性格和面貌。(3)可以向清代学者学习读书的方法,段顾两人都是饱读群书且会读书的,段氏善于小学训诂,逻辑推理方面颇见所长;顾氏善于全面把握大义,能够分辨不同家法的特色。若将段氏的方法拿来治上古历史和语言,一定能有很多收获;若循着顾氏的道路去研究传统经学,也自然能获益良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