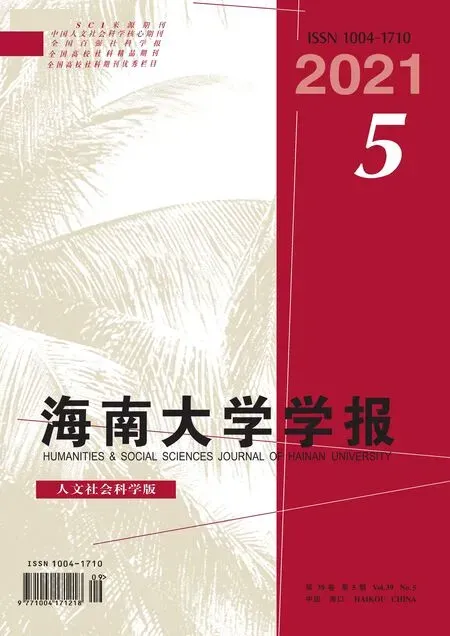整体与个体的悖谬
程志敏
大道至简,可用“一”名之。“一”为“道”所生,本质不同,却直接相通,故《庄子·齐物论》曰“道通为一”。有所分别,既为“成”,也成“毁”,惟“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荀子·儒效》)。然“一”必生“二”,而“二”虽为障碍,却不得不然,故“不二”终成难题。整体是一,个体也是一,形有大小,要之皆一。对于个体来说,“得一察焉以自好”乃是(为了)存在本身,看似并无不妥,结果却使得“一曲之士”破裂大道,天下大乱,“一察”也难以为继。这就是“道”的存在论悖论。
道理看上去颇为简单,整体与个体、全局与局部、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普遍与特殊、世界与民族、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相互对立却有不可或离的“对偶”本质上无非是“大与小”或“一与多”的构成和涵盖关系。这种“对偶”揭示了万物最终的“偶在性”①张志扬先生多年前提出了“偶在论”,他更多地从“偶然”(accidens/Akzidens/contingency)这个角度来指明有无之境(《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349 页;《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15,229 页),超越虚无主义和绝对主义这两个摇摆而互通的极端。我们再次借用这个极具启发性和思想张力的概念,主要表示“对偶”甚至“悖谬”的存在论情态。而“偶在”与“悖论”之间的关系,或偶在的悖论性,张志扬先生也早在其著作中深刻地阐明过了,参见《偶在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版,第13,21,37 页;《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第301,393 页;《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第4,28,41,108,180,196,204,230,246,284,293,373 页。,却没法把它下贯到现实之中:即便把天下大道说清楚了,也似乎没什么“用”。“一”的实践意义自不待言,故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道德经》39 章)但何以为“得”,又如何“得”,仍然恍兮惚兮。个体虚冲恬淡而近于“无”,则是大“用”,而“是以各由其一而不自以为德也”②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黄曙辉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72 页。当然是很好的道理,但如何实现却让人踌躇。“一”如何统摄与涵盖“多”,个体凭借什么而能主动“耦合”成为整体?在极简而又极高的领域,问题可能都太简单化了。
个体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挣扎,如何悲苦,如何形影相吊,一体化的进程似乎都不可阻挡,丝毫不会考虑每一个同样有着神圣存在理由的个体。每一个可怜的“小东西”被迫裹挟到整体之中,甚至有时为了自身的存在而主动融入整体,因为在存在的网络中,没有哪一个个体能够独立在外、逍遥自足。这种情况在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机体中更为显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个体的存在也就越来越破碎。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指出: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4 卷),第469-470 页。
文学如此,经济、政治和哲学也是如此。古代强调家庭、村坊、部族和城邦等“集体”,近代高扬个人性的“主体”,而现代似乎又不得不回到“集体”意识之上。人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只不过现代观念并不是回到古代的“原点”,没有以整体主义成功地消融个体主义,而是让这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和纠结。诚然,“今天开始成为现实的世界和人类的全球一体化,开启了地球上真正的普遍史,即世界史”②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85 页。。然则,如何理解其中的“全球一体化”或“星球化”(planetarischen)以及“世界”和“人类”的含义?
即便“人属于一个整体,人存在着一致性”,甚至人的同一性必然演化为一种趋同的意志,但我们就能轻易地说“国家的自决权、平等权、主权等概念保留了其相对意义,而丧失了其绝对意义”吗③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第52,228 页。?对于那些国家主权都还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美好的前景是不是太早了一点?他们不得不怀疑发达国家这番高妙的说辞是不是别有用心。节食减肥固然能够让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但能这样要求本来就营养不良的人吗?
雅思贝尔斯所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让渡权力,也就是把权力集中起来使用,形成一种充分管控的力量,生活共同体才能得以维系,毕竟每一个人都无法仅凭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更谈不上“美好生活”(well-being)。这就是一种悖论:个体有充分的生存权利,但为了生存及其质量,就必须限制自己这种权利——这是现代契约论的意义所在,也是它根本无法突破的界限。扩而言之,“大政治”(grosse Politik)需要消灭“各民族相互间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克服民族、等级、种族、职业、教育、教养等种种荒谬的偶然性,以便“创造一种权力,强大得足以把人类培育为整体和更高级者”,最终“要把人类培育为整体”④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1429-1430 页。。
但这种伟大的理想一开始就蕴含着矛盾,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家主权与跨国合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一个各民族国家想要兑现其保证安全的诺言,就必须结成跨国的(军事和安全)同盟的世界上,兑现主权诺言是同放弃主权诺言联系在一起的”⑤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见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 页。。这听上去同样符合逻辑,因为这种情况与个人所碰到的完全一样:每个民族国家如果放弃(哪怕不重视)自己的主权,就完全无法存在;而绝对性的主权诉求必然导致世界性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受害的还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是弱国),甚至导致自身的灭亡。
跨国合作,甚至直接结成某种形式的区域同盟,虽不是“太一”,也绝对不像“小一”那样不成气候,容易在弱肉强食的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中遭霸凌甚至“国除”。由于目前世界政治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而他们的思想基础乃是“强权即真理”,即罔顾道德信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全球政治气候日渐变得极端化,这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所以,绝大多数民族国家被迫“抱团取暖”。再从整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来说,区域联合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庇护每一个成员,而个体的健康、生机与稳定,对于全局的和谐与发展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甚至根本性的结构意义。
不过,仅仅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超越民族国家就一定是可行的,并且一定是好的吗?也许今后是,但目前还很难说,因为人类至今依然太过幼稚,完全不知道如何相处。最起码来说,个体之间的融合如果没有遵循正道,没有采取恰当的方式,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理论界的例子就是自康德在现代重提“世界主义”以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弗兰克(1978a)的‘世界经济/体系’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与过去的以‘民族’和‘社会’为单位的历史和理论相比,涵盖了整体中的更大部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走得不够远,本身又变成了前进的障碍”①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版,第450 页。这本书原名Re 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实际的例子就是“欧盟”,正如哈贝马斯在这个区域经济组织刚诞生不久就预言的那样,“欧洲统一过程极有可能证明,对这些放弃货币主权而坚持大多数其他主权的国家来说,缺乏统一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就业政策的货币联盟所带来的问题将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②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见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第79 页。。实际上,对于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联合的机体来说,现实政策只是很微不足道的方面,内部组织涣散,成员离心离德,自私贪婪,等等,才可能是致命的因素,如贝克所说:“如果缺乏一种政治上强大的世界公民的自我意识,以及相应的全球市民社会和世界舆论机构,那么,(即使有种种制度方面的空想)世界主义民主将只能是一种(必要的)理念”③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见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第33 页。。
就算人们在危机的逼迫下,出于善意和共识建立起了某种大型组织,这根“救命稻草”在现有的文明水平之下也很难不走向衰亡,因为“世界公民意识”或“世界舆论机构”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这种脆弱的同盟能够侥幸存活下来,也极有可能演化为新的暴力机构,蜕变为对内自我殖民的区域帝国主义。所以,很多国家对于结盟都持怀疑甚至拒斥的态度,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甚至亲身经历了包括“经合组织”之类的国际共同体的局限性,而国际金融、军事和科技领域等方面的合作机构也“使人们看到那种听上去冠冕堂皇的宣言是如何转变为歧视性的实践的”④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见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第45 页。。
结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化最终导致了世界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很多人现在看得越来越明白,这种“逆全球化”恰恰就是“全球化”的产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每一个民族自我解放的必要基础,但同时也很可能是帝国主义惯用的“分而治之”的伎俩和阴谋⑤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64-165 页。。“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表面上具有金色的神圣光环,但实际上却是削弱第三世界的“特洛伊木马”,它会导致这些民族国家各自为战,最后分崩离析。而民族国家为了对抗帝国主义的分化瓦解,又必须坚定地走本民族的道路,也就越来越封闭、狭隘和羸弱,这看上去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如果不坚持自身的特色,大概连“饮鸩”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全面殖民了——这着实让人左右为难,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最终都可能是西方列强投放的精神病菌,与枪炮和钢铁一样,都是致命的武器。
难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相对较弱的个体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只能如此,那么,我们还是不妨先看看“整体主义”的危害(尽管它并非没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因为迄今的“全球化”或“世界主义”本质上乃是西方人发明的东西。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尔对西方的双重道德标准感到气愤,他们以人权总教习自居,却固守在西方的堡垒中,粗暴推行他们的单极主义的价值观,并以此建立世界主义——这不是悖谬,而是荒唐。因此,恩岑斯贝格尔清楚地看到,普遍主义其实是一个道德陷阱,无非展示了西方的伪善⑥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见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第47-48 页。。萨特在批判西方的“假普遍主义”时尖锐地讽刺道:“欧洲人只有通过制造奴隶和怪物,才能使自己成为人⑦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见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第49 页。。”西方理论家贝克坦承:“人们声称‘世界主义’,最终暴露出的却是自高自大的西方小市民道德。”⑧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见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柴方国等译,第46 页。
张志扬先生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现代意识形态或种族中心主义,更是明目张胆地借技术来购买自我的普遍主义或世界化”①张志扬:《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第290 页。,因为“一切普世价值或普世命题都是意识形态”②张志扬:《归根复命——古典学的民族文化种姓》,《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第1 页。,都是装饰,更是套在赤裸裸利益诉求外面的遮羞布。
全人类当前的生存焦虑空前高涨,理论上的乌烟瘴气和不知所云当然是很重要的诱因。不是说理论家们无法取得一致,而是说他们讲得越清楚,我们就越糊涂,就越不知所措——我们的确在理论上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天下大同”。这个时候过多讨论“天下”理论,虽然会产生一点点微弱的理论意义,却无疑会在实践上造成更大的误区,甚至可以说是有害的,至少对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误事。
但我们又不得不在整体上去思考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能源危机、生态灾难、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这就需要大智慧,需要我们全面深入地重新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以指导我们全新的生活。所以,我们有保留地认同这样一段话: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问题,并不是西方是否会继续主宰世界,而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在灾难使我们一蹶不振之前,突破创新,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③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钱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第XXXVI 页。
这个现实问题太过急迫,甚至让“整体与个体”的形上思辨在当下这个“大时代”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