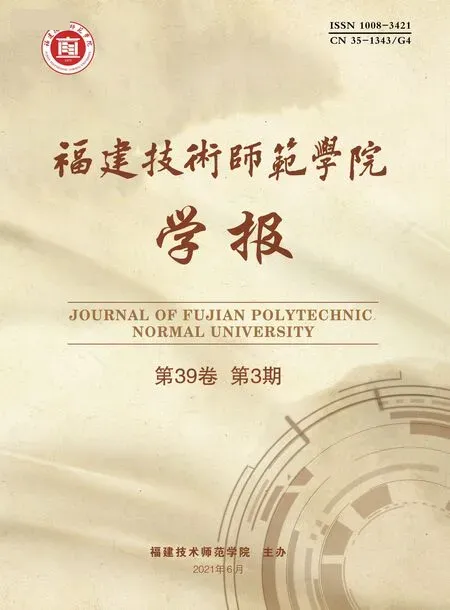论刑事证明标准中的客观性标准
——以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为起点
赵飞龙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证明标准既是现代刑事证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塑刑事证明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随着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推进,证据制度也面临再次转型的需要与机遇。就证明标准而言,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引起的初次转型中,法律真实论与客观真实论成为分庭抗礼的两种刑事证明观。然而,两种刑事证明观的论战多是从结果意义上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改革进行宏观讨论,鲜有学者从方法意义上阐述刑事证明标准的内部结构。从证明的角度来讲,证明标准既是对证明结果的要求,也内含了对证明方法的要求。一般而言,证明方法包括技术化的逻辑论证和思辨性的经验判断两种,亦即对《刑事诉讼法》中要求遵循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的具体化。逻辑论证是经验判断的主观外化,为后者供必要的理性基础和外在约束。学界对技术化方法的忽视反映在实践中,即为司法人员更为关注法律层面的分析,缺乏对证据分析的深层次表达。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证明方法层次化构建中的客观性标准及其证明方法的选择进行初步探讨。
一、刑事证明标准中客观性标准的转向
1230年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法令之后,在大多数受普通法影响的国家,证明有罪的权力回归人类法官之手。随着审判失去上帝视角提供的保证,人类法官同样承担起了说明定罪正当性的责任。为此,罗马教会法设定了两条证据规则:第一,定罪需要获得被告人供述或两份证人证言的证明;第二,间接证据不得独自证明被告人有罪。此二者在实质意义上消除了法官定罪的主观性,恢复了神律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客观性标准,即证据的充分性标准。这一标准在欧洲沿用了数个世纪,在此期间囿于同时获得两份证人证言较为困难,导致刑事司法系统热衷于获得被告人供述,并由此发展出了合法的刑讯制度。随着对刑讯制度的废弃,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复杂疑难案件中,要满足上述两条证据规则的要求十分困难,所以除死刑案件外,其他案件的定罪标准放宽至一份证人证言或间接证据的证明。
自18世纪开始,定罪证明不再要求法官适用普通法中的客观标准,转而诉诸于法官自身的理性与公正,追求庭审证据对事实认定者主观上的说服。自此,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便开始由证据充分性向证明充分性的转变,证明方式也随之更加灵活。以苏格兰大法官的释明为例,最早定罪仅要求有两份证人证言即可,之后则将上述形式规则解释为两点,即无论单个证人证言多么可信都不得据以定罪,但并不对每一个案件事实都做如此要求。最后则将间接证据或中间事实吸收进补强证据的范畴之中,二者的增加只需满足必要的确定性要求即可,且在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案件中,并不要求每一个中间事实都得到两个证人的证明。同时单个证人对不同中间事实的证明若相互交错,且中间事实的指向存在一致性则足以认定被告人有罪。此时,法官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一条充分性规则能够解决所有证据充分性的问题,单纯的客观性标准已不足以支撑刑事定罪。因此,无论是否需要两份证人证言来证明某一事实,证明都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可以看出,刑事证明标准已不再是纯粹的客观性标准,而是逐渐吸收主观性标准,形成了主客观相互配合的证明标准体系,以保证定罪证明在形式与实质上的双重充分性。其中,保留形式充分性的原因在于,虽然在证据质量评价时要避免任何数量要求,但仅是出于对证明力法定的否定。其先验依据为“事实不应仅仅由证人的数量决定”,在评估相互矛盾的证据时,并不存在简单的证明公式或工具供以量度事实。除极少数例外情况,法官可以自由评估证据的可信性,其最终标准是证据质量而非数量。但对证据质量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证据数量要求的摒弃,为解决证据证明乏力和证明需要之间的冲突,在单纯增加辅助证据无力解决证据可信性问题时,仍需增加补强证据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因此,虽然随着刑事司法理论的发展,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不再独占刑事证明标准的宝座,但却因其为定罪证明提供了形式理性成为刑事证明标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中客观性标准的应然回归
我国关于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的讨论始于2001年,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确实、充分”的解释性条款引入其中。围绕这一规定共出现了四种观点:其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是隐性层次与显性层次并存的二元体系,隐性层次指的是虽然针对不同的证据调查阶段在形式上都适用了“确实、充分”的标准,但其在实质层面是存在差异的。显性层次指的是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在实体法上的性质归属不同,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1]。其二,应当以审前程序到审判阶段的递进性为基础,构建“证据确实充分→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进阶式证明标准[2]。其三,应当在区分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构建“一纵多横”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一纵”指的是在递进式的刑事诉讼结构中,从审前阶段到审判阶段会出现由证据标准向证明标准的转变。在审前阶段,从侦查阶段到提起公诉,证据标准应当呈现出递进性。而在审判阶段,从普通审判程序到死刑复核程序,证明标准应当呈现出递进性。“多横”指的是应当根据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的不同,适用递进式的证明标准[3]。其四,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刑事证明标准界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排除一切怀疑,适用于死刑案件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第二,排除合理怀疑,适用于其他案件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第三,盖然性优势,适用于被告方出罪事由的证明及反驳[4]。
上述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需要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刑事证明标准。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中,阶段论者认为证明机制的转变在于终局性的证明活动由侦查阶段向审判阶段让渡,审前阶段的证明活动仅为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准备活动,其证明标准囿于庭审证据检验的实质化无需也难以达到实质上的“确实、充分”[5]。在此基础上,阶段论者言称审前的诉讼活动是一种围绕证据收集进行的查明活动,适用的是证据标准。而审判阶段才是围绕证据审查进行的事实证明活动,适用证明标准[6]。亦即在坚持广义刑事证明观的前提下,又否定了审前诉讼活动的证明性质。这实质上是在明修栈道的同时,悄然向狭义的刑事证明观靠拢。这种观念上的暗自革转在证明标准上体现为由原先对客观性标准的强调转向对主观性标准的强调,虽然也出现了尝试将二者相结合的观点,但在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化构建中更多的是学习西方国家,对“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解释性条款的主观分级,甚至将之擢升为与“确实、充分”并行的证明标准,反而忽视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中的客观性要求。
根据2018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的立法解释,“确实、充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证据充分性、证据合法性以及证明充分性的审查。其中,证据合法性审查侧重的是“确实”,证据充分性和证明充分性侧重的是“充分”,此二者分别代表了刑事证明标准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其中,证据充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认定单个案件事实的证据充分性要求;第二,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充分性要求。《刑事诉讼法》虽然对此二者没有像荷兰一样作出明确规定,但却通过司法解释间接提出了要求。首先,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言,要求犯罪确实存在等十类案件事实都需得到“确实、充分”的证明;其次,就单个案件事实的认定而言,要求作证能力存在缺陷等三类证人证言应当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方能采用。这也就意味着,在理想状态下若要认定被告人有罪,至少需要十份证据。若存在证人作证能力存在缺陷的情况,则需新增其他证据。
立法在证据充分性的基础上吸收排除合理怀疑作为主观标准,本意是通过概念重述来明确证明充分性的内涵,若将之擢升为与“确实、充分”并行的刑事证明标准无异于叠床架屋。另一方面,排除合理怀疑的认定本属于法官的主观范畴,它的提出目的是让事实认定者因案下判,避免裁判的僵化与教条。当前对证据主观审查标准层次化构建的聚焦,一方面是出于对“确实、充分”在实践中被客观化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为避免抽象的条文在实践中失去应有的导向意义。若将之具象化为概率意义上的数字,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标准的内涵,但难免会引起向古典证据制度的退归。这种量度外化的尝试在理论探讨中有一定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只会出现两种结果:或将刑事证明标准再次退归为一种纯粹的客观标准,为法官套上数字标准的枷锁;或因法官的主体差异性从内部将之消解,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7]。当然,主观证明标准外化的不能并不意味着证明充分性无需制约,否则会陷入消极法定主义的“悲剧”。消极法定主义的原罪在于缺乏对法官主观审查的制约,即在外没有英美法系国家复杂的证据规则对法官加以约束,在内又无心证过程外化公开的制度要求。此二者正是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中,学者在呼吁主观证明标准回归时所希望解决的两个问题。
我国立法中的刑事证明标准本就暗含了主客观相结合的二元标准,在程序主义和狭义刑事证明观的影响下,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化构建应当回归到这种二层次构建中。当前学界的构建或集中于主观性审查标准的层次化构建,或将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以阶段为标准机械二分。前者在学理上是有意义的,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达成预期目的,不仅难以摆脱后果主义的影响,也会因主观标准的外化不能失去其应有的指导意义。而后者则在反思证明标准印证化的同时,对主客观审查进行了阶段性隔离,在可能导致侦诉人员权力扩张的同时,将我国的刑事证明推向消极法定主义。在实质上,无论是主观审查标准外化还是主客观二分,都是对主客观二元标准中部分内容的极化。为保障证明结果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应当回归对主客观二元标准同等关注。其中,形式合理性包括前提合理和证明方法合理,前提合理指的是存在一定的证据为证明提供必要的信息输入,使得证明内容“有物可言、有据可依”,为后续证明内容的合理性、可接受性审查提供基础。证明方法合理指的是诉讼参与者进行证明活动时选取的符合实践需要的可行路径,为证据信息的加工处理搭建骨架。其普适意义在形式上为刑事证明的必然性提供一定担保,同时也为证据信息存疑的证据留有可供补救的后路。形式合理性为实质合理性指明了前进路径,限制了活动场域,而实质合理性则在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上,诉诸诉讼参与者的内心。实质合理性的认定标准虽然无法外化和具体,但却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必要条件。虽然个体差异性会导致认定结果存在差异,但配合相关制度的外部制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差异限缩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三、客观性标准回归视域下证明方法的选择
一般而言,事实认定共有三种模式,即逻辑推理、假设检验以及叙事嵌入。其中,逻辑推理模式指的是根据从证据中得来的信息出发,自下而上地逐步推论某一事实是否成立。假设检验模式指的是首先预设某一案件事实存在,继而根据证据要素或事实要素的法定要求自上而下地探寻能够支持其事实预设的证据或事实。而叙事嵌入模式指的是将事实认定置于案情的整体构述之中,首先对案情整体构述的似真性、逻辑自洽性进行检验。在没有发现叙事元素缺失或元素矛盾时,继而探寻案情整体构述中的独立事实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证据支持。有学者指出逻辑推理模式无力于解决证据冲突及其带来的无限倒退问题,假设检验模式虽然理论探讨中多有提及,但在具体案例中却鲜有适用。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叙事嵌入式模型应当成为事实认定的一般模型[8]。
然而,该观点在批评逻辑推理和假设验证两种事实认定模式时,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逻辑推理只是一种事实认定工具,仅在形式上担保事实认定结果的必然性,即在承认锚定规则的前提下,输入证据信息必然得出认定结论。证据冲突以及无限倒退均属于证据信息的输入问题,应由事实认定主体选择并解决。第二,假设验证并不必然要求事实认定者存在一个数学建模的过程。对于案件事实成立的校验一般通过扩大证据信息的输入来完成,这一过程只能通过证据的增加来表现,事实认定者的主观心证过程无法也不可能完全外化为数字的机械标准。相较而言,叙述嵌入式模型只是较为宏观的一种初步认定。若接受案情的整体构述,即表明接受了整体构述中独立事实的成立,进一步的认定仍是借助逻辑推理以假设验证模式展开。因此,可以说叙述嵌入是一种优于逻辑推理和假设验证的事实认定模式,但绝对无法抛弃后两者而独立存在。
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同阶段,由于主体职能和目标的不同,事实认定模式的选择顺序会存在一定的不同。各阶段均以犯罪发生为预设,侦查阶段以收集证据为主,最终以此为依据重构案件事实,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则是对侦查阶段事实认定活动以及结果的全面审查,检察官与法官首先接触到的是起诉意见书、起诉书以及相关的案卷材料,亦即其中构述的案件事实。此时起诉意见书、起诉书中叙事的似真性要优先于事实,在初步接受二者所叙之事的似真性之后,方才对支撑叙事的证据进行审查,亦即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已接受似真的案件事实进行解构验证。在解构验证中,证据充分性是必要条件,而证明充分性是充分条件。就单个待证事实而言,在单个证据证明乏力时,尽管可以通过叙事嵌入的方式解决其似真性的问题,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证据充分性和证明充分性的双重要求,这两个问题仍需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以客观标准的刑事来解决。一方面,就证据的充分性而言,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价值主要在于引导和督促控方全面收集证据。与叙事嵌入标准对控方整体证据收集活动的引导不同,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仅针对某一待证事实起到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就证明的充分性而言,对单个证据证明乏力的待证事实,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在赋予单个待证事实证明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上,为其证明结果的实质合理性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