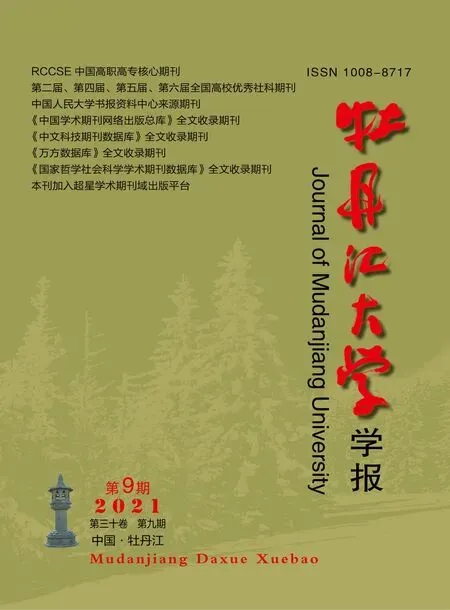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露易丝·格丽克诗歌自然意象与生态意蕴
——以诗集《野鸢尾》为例
孙 岚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美国当代诗人露易丝·格丽克(1943-)获得了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在格丽克的颁奖词中写道:“她那无可辩驳的诗意般的声音,用朴素的美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①此后,格丽克的诗歌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格丽克的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先后创作并出版诗集12部,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诗歌奖等奖项以及“桂冠诗人”的称号,成为了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格丽克众多的诗集中,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野鸢尾》别具风格,诗集以野鸢尾这种植物的名字命名,共收录诗歌五十四首,诗集中的诗歌大部分都以自然景物来直接命名,诗中也包含着对具体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体现格丽克对存在、死亡、生命等永恒而深刻话题的思考。
21世纪初,中国学界开始译介格丽克诗歌。学者们或结合格丽克的生平经历,选择单一角度对其诗歌进行总述,如柳向阳《露易丝·格丽克的疼痛之诗》[1]、沈玉慧《创伤理论下露易丝·格丽克诗歌解读》[2]等;或对格丽克具体诗歌作品进行评论、分析,如方婷《孤独、重生和死亡:评露易丝·格丽克<幻想>》[3]、 黄冰莹《露易丝·格丽克<阿弗尔诺>中的爱、灵魂与死亡》[4]等;或关注格丽克诗歌所传递出的关于生命的哲学意识,如吉曼青《露易丝·格吕克诗歌中的孤独意识》[5]、刘文《露易丝·格丽克:生命的短暂与永恒》[6]、胡铁生的《格丽克诗学的生命哲学美学价值论》[7]等。总体来看,国内研究格丽克诗歌的论文数量不多且角度有所局限,亟待突破。
生态女性主义处于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第三阶段。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奥博纳提出,在这一阶段,该理论将妇女运动与生态环境运动相结合,从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双重视角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主张妇女和自然的解放,促进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稳定的发展。[8]1生态女性主义与诗集《野鸢尾》有着诸多契合之处。从《野鸢尾》中具体的自然景物描写,以及格丽克作为一名女性诗人而在诗歌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能够察觉到《野鸢尾》蕴含着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诗集《野鸢尾》既有对自然意象的描写,又有从哲学、伦理、文化、审美的维度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男性与女性性别身份的差异作出的具有生态意蕴的思考,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文本实践。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诗集《野鸢尾》中的自然意象和生态意蕴进行分析。
一、《野鸢尾》中的自然意象
自然意象是诗歌意象中最普遍的类型,每一自然意象都是诗人主观情思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将自然意象与女性主体相联系,其理论的形成借助于符号和意象的使用。[8]56《野鸢尾》中的自然意象是诗人女性身份的表征,其中渗透了诗人的主观情感以及社会文化内涵。《野鸢尾》的自然意象有多种类型,人与自然意象构成了“女性-自然-文化”的关系,这对于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有着积极的文本与实践意义。
(一)自然意象的类型
《野鸢尾》中的自然意象类型较为丰富,可简单概括为三种类型,即“花、树”系列,“天空、月亮、太阳、大地”系列以及“鸟和其他动物意象”系列。
第一类是关于树和花的描写。《野鸢尾》中描写了各类自然植物意象,其中以花和树居多。如娇弱的玫瑰、顽强的雏菊、雨中摇荡的百合花、枝桠晃动的松树、燃烧的枫树等。花和树在形态和寓意上都和女性相联系,诗人对这一系列自然植物的生存状态的特殊限定(如玫瑰是“娇弱”的、雏菊是“顽强”的)是诗人对自然、女性生存体验的主观感受与描绘。
第二类是关于天空、月亮、太阳、大地意象的描写。天空、大地、太阳、月亮也是诗集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意象,如月亮“升起在潮湿的大地之间”[9]34(《冬天结束》),“天堂的空虚/映在大地上/田野再度空虚/死气沉沉”[9]90(《夏天结束》),以及像天空一样的花朵,火红的不升不落的太阳等。天空、大地、太阳、月亮在开阔的视野中被置于人类/自然/文化的场域,自然意象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人类建构出的社会文化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第三类是有关鸟以及其他一些动物意象的描写。动物意象也是《野鸢尾》中的自然意象组成部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鸟”这一意象。“深色的鸟表演宵禁的音乐”[9]59(《晨祷》)以及反复出现的鸟鸣,给诗中寂静的自然环境增添了生机。其他自然生灵如萤火虫、羔羊、蚜虫等,在格丽克的《野鸢尾》中,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是和谐共生的,不存在等级上的高低贵贱或压迫。现实话语中,人类中心主义导致自然万物为人所控制与奴役,父权制的中心主导又导致女性群体被压迫,不能表达与发出自己的声音,属于自然、属于女性的声音和经验被遮蔽,这与诗歌中描写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了鲜明反差。
(二)女性主体与自然意象的情感联结
格丽克在诗集《野鸢尾》自然意象的选择方面,多以个人主观感受为主要依据,这种主观感受之中蕴含着女性群体普遍存在的心灵疼痛感以及女性的生存体验。这种微妙的女性生存体验在与外在自然物叠合时,形成了“女性-自然-文化”的结构特征,即女性主体与自然意象形成一个情感的联结。如《天堂与大地》中“生活将再不会结束/我怎能留下我丈夫/站在花园里”[9]73,格丽克童年时期敏感孤独,成年后又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因而她诗歌中的自然意象一贯呈现出伤感、悲凉的特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自然和女性都充当着孕育培养的角色,自然与女性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由于人类文化观念的偏差,大自然受到人类剥削,女性也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致使女性与自然有着相同的情感价值属性,女性的形象与自然的形象相联结,背后遵循着自然与社会文化的逻辑:自然和女性同属于被压迫的一方,“女性-自然-文化”结构背后正是对男权、父权社会压迫的反抗。格丽克结合个体自身的经验,将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融入《野鸢尾》中,使得原本物质性的自然意象具有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属性。
(三)非个性化的自然表达
诗集《野鸢尾》除自然意象种类多元、诗人与自然意象构成情感联结符号等的特点以外,在自然意象的情感表达方式方面也呈现出“非个性化”的表达特性。象征派理论家艾略特提出诗歌的“非个性化”理论:“诗歌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10],认为诗歌不应该直接宣泄情感,而是要找到“客观对应物”,间接表现情感。格丽克借鉴了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在诗集《野鸢尾》中不对自我情感进行大肆渲染,而是将自我情感投射在自然意象中,并对自我情感加以控制和收敛,从而使原本极端的自我情感(如悲伤、压抑、绝望)透过自然意象的缓冲变得轻描淡写,从而实现自我情感的隐晦呈现。如《白玫瑰》中的“你是谁?在亮灯的窗子里/此刻掩映在那棵绵毛荚蒾树/枝叶摇曳的阴影里/你能存活吗?在我活不过第一个夏天的地方”[9]100,格丽克以白玫瑰的口吻发出疑问,诗人予以自然物以思想,让它们成为主体而对于生死进行思考和发问,虽然格丽克对个人情感并未直观表露,但通过诗歌中白玫瑰的疑问和情感的间接表露,能体会到作者对死亡持一种绝望与悲观的态度。又如在《牵牛花》中,“我在另一生里有什么罪/就像我此生的罪是悲伤/不允许我向上攀登/永永远远/无论什么意义上/都不允许重复我的生命/在山楂树中受到伤害/所有的世间的美我的惩罚/正如它是你的——我的磨难的源头”[9]102,以牵牛花的口吻,叙说生命存本相中的压抑与磨难。以拟人化的形式,表现牵牛花对生命的悲伤感叹,实则是表达诗人对生命的悲观感受和痛苦之感,自然意象的运用使诗人沉痛的情感得以节制和收束,自然意象成为与诗人情感相印证的“客观对应物”,更能启发人们去思考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增强了诗歌的深意。“格丽克的诗歌虽然描写外部世界但意在精神内在,人们可以感觉到内在与外在之间的联系,但诗歌表现的目标是精神、神话与宗教的层次,而不再是日常生活本身”[6]38,正是这种“非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方式而使得格丽克《野鸢尾》的内在精神和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得到彰显,构成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情感表达方法。
二、《野鸢尾》中自然意象的生态意蕴
生态意蕴是文学作品中的生态环境描写所传达的深层思想,生态女性主义者善于从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生态意识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诗集《野鸢尾》的生态意蕴集中体现于哲学、伦理、审美、文化四个维度。
(一)自然哲思
诗集《野鸢尾》的生态意蕴在哲学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对自然生命的哲思、从上帝视角来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这两个方面。
生态女性主义将生存和死亡描述成线性生命周期上的自然阶段,[8]256格丽克在《野鸢尾》中反复表达了对生死的思考,生死的意象构成其诗歌的一个基本母题。例如这首《野鸢尾》“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为死亡的/我还记得。头顶上/喧闹/松树的枝杈晃动不定/然后空无。微弱的阳光/在干燥的地面上摇曳”[9]21,世间万物都将经历从美好的盛放,到苦难的摧残,就像柔弱的松树枝杈,在风里摇曳,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最终必然经历衰败,走向凋零。《野鸢尾》对生与死的哲思,将人类与自然紧密相连,它们有着同样的生命结构与规律,在自然生命的哲学意义上,宣扬了人与自然生命的相似性。
生态思想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认为,人类对待自然采取竭泽而渔的手段,背后原因在于支配人类意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凸显,美国兴起环境保护运动,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病所在,要拯救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就应该摒弃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家们也顺应了环境运动的潮流,因此,格丽克的诗集《野鸢尾》的创作背景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环境运动的影响,其中不少诗篇体现出格丽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并以上帝的口吻对人类不加约束掠夺自然的行为予以委婉警示:“当你寻找着田野之上明亮的天空/你们仓促的灵魂/像望远镜集中在/你们某种放大的自我上”[9]78(《仲夏》),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大自然加以掠夺,上帝发出控诉,批判人类盲目自大。“是我先在这里/在你到这里之前/在你建起一个花园之前/我还将在这里/当只剩下太阳和月亮/和大海/和辽阔的旷野/我将掌握这旷野”[9]56(《女巫草》),客观自然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终将归属自然本身。格丽克在诗集《野鸢尾》中描摹的“神蘋之声”,借造物主之口,感慨人类的轻浮以及他们对永生的徒然渴望,[11]提醒人们摒弃自以为是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平等的实现,实质上也意示着男女平等的实现,生态女性主义者一直以此为目标而斗争着,《野鸢尾》是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一次伟大实践,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二)生态伦理
生态伦理思想是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思考,它将整个自然都纳入人类的伦理关系当中,提倡人与自然平等共生。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种“土地伦理观”:“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从以土地征服者自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12]环境伦理是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重点,格丽克的诗歌创作是对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的一次探索与实践,将人类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土地”是《野鸢尾》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其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在关系:“我种下一棵无花果树/在这儿,维蒙特/没有夏天的国度/这是一个试验:如果这棵树活下来/那就表示你存在”[9]45(《花园》),以恶劣生存环境下的播种来验证大地与生命的关系,格丽克以自然物的存在来确证人类自身的存在,将自然与人相连接、沟通,体现了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的生态伦理思想。“如果另外的某个世界上存在正义/那些像我这样的人/因大自然强迫而过节制生活的人/就应该得到/所有事物中最好的份额/所有渴望、贪婪的目标/作为对你的颂扬”[9]80(《晚祷》)。格丽克体会到大地、自然万物与人的深刻关联,受限于自然条件,人类应当节制生活。这种生态正义观正是生态
女性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之流露。
(三)间性美学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审美价值也相当关注,格丽克的诗集《野鸢尾》的诗歌语言是优美且雅致的,并且体现出人与自然交融以及主体间性的美学特点,这是格丽克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原则的发展。格丽克对自然景观有着敏锐、细腻的感受,能够捕捉到独特的自然画面,并运用恰切的感情对自然画面进行表达,这源于格丽克对大自然的细致敏锐的观察以及整个身心融入自然时的真切感受。“我的愤怒结束/当冬天结束/我的柔弱对你应该是显而易见/在夏日的微风里/在成为你自己的应答的词语里”[9]115(《日落》),诗中的“我”和“你”,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主体的自然之间的对话,诗人有意将两者模糊,让人分辨不清是以自然的口吻还是诗人的口吻在叙说,呈现出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状态。格丽克的诗集《野鸢尾》“将自然还给自然,全神贯注地感知自然的一切,接收自然的能量和智慧”[13],体现出人与自然交融的特征。
生态审美的主体间性是指在生态审美的过程中,除了将欣赏者视为主体以外,视自然景物为另一主体,并在两个主体之间进行交互主体性的联通,在平等的沟通中寻找、体验自然景物的美。“我已经把自己和那些花相比/它们的感受范围要小那么多/而且没有反应/和白色的绵羊/实际上是灰色的/相比:我是独一无二地适合称颂你”[9]84(《晚祷》),诗人创设出自我主体与自然意象平等的情景,将“我”与花朵、绵羊等同,实际上传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友好、平等的思想,人与自然都是主体,两主体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沟通。格丽克企图通过诗歌创作实践,让自然由“他者”回归主体,就如同让女性从“他者”回到和男性拥有平等身份的主体一样。诗歌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与共生的美好愿望,体现出生态审美主体间性的积极意义。格丽克诗歌中运用的交融性和主体间性原则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文本示范,为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美学实践经验。
(四)文化批判
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学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通过重读和发掘文本,帮助读者理解文本的潜在意义,从而树立“生态观念”[14]。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比较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属于一种“框架观念的压迫”的逻辑,这种逻辑根源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等级思维、价值二元论和统治逻辑”[15],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对此,生态女性主义者从性别、种族等文化维度对其进行批判。格丽克在诗集《野鸢尾》的某些诗篇中体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和男女关系中感受到的个性压抑、性别歧视及心理冲突,以及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家庭,责任、义务、女性本能等错综复杂的关系”[16],流露出女性从自身出发,对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如诗歌《花园》借自然环境的“浅山淡绿,花团锦簇”[9]45映衬诗中男性和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想停下来/他想继续做这件事/直到结束”[9]46(《花园》),女性的话语力量被男性话语所遮蔽,格丽克深感男女地位不平等,从而对男权社会制度进行控诉。在《月光下的爱》中,“有时一个男人或女人把自己的绝望/强加给另一个/这被称作裸露心/或称作,裸露灵魂——意思是此刻他们获得了灵魂……外面,夏夜/一个完整的世界被抛在月亮上……”[9]49,男女双方情感的交互,并置于自然画面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本男女间对立、冲突的关系得以缓和,勾勒出男女平等、相处和睦的幻象,格丽克幻想自然环境的和谐景象以及男女关系的平等地位,对自然和谐、男女平等进行了构想,反衬出现实世界存在着的人与自然、男性和女性不平等的真相。文化意义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自然、性别、宗教等文化互相交织,女性身份的建构以及自然环境以及宗教典故都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花葱》一诗内置了《圣经·创世纪》中“雅各的梯子”的故事和宗教的主题,“但正如男人女人似乎欲望彼此/我也欲望天堂的知识——而如今你的悲伤/一根赤裸的茎/正伸到门廊的窗口/而最终,什么/一朵蓝色的小花/像一颗星”[9]57(《花葱》),在《圣经》中,雅各梦里的梯子连接大地与天堂,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在宗教世界里,人们相信上帝与人类同在,将永远保佑人类。格丽克化用这一典故,借助蓝色小花、星星等宁静的自然意象点缀与反衬,表达对现实世界中男女关系的不平衡与失和状态的不满和控诉,对人间悲伤的同情以及对幸福降临的追寻,将诗歌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和宗教文化相联系,显示出神圣的宗教文化意味。格丽克从性别和宗教维度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生态文化意蕴作出了反思与实践,推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实践的进步。
三、结语
格丽克在诗集《野鸢尾》中表现出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对男权中心与人类中心进行“对抗”。从格丽克诗歌创作的谱系上看,除诗集《野鸢尾》之外,格丽克的其他诗集如《草场》《新生》《七个时期》当中,也有一些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诗篇,如诗集《草场》中的《无月之夜》《下雨的早晨》《蝴蝶》等,诗集《新生》中的《废墟》《鸟巢》等,诗集《七个时期》中的《月光》《星》《纱窗门廊》等,这些诗篇与诗集《野鸢尾》共同构成了格丽克生态女性主义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格丽克诗歌创作中占极大的比例,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显著特点。美国其他的生态女性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如洛里·安德森的诗集《培育失度》、诺拉·霍兰德-莫尔斯的诗集《泥姑:黏土中的诗篇》、达琳·霍根的《美洲狮》《命名动物》《皮肤幻想》《伟大的度量》、奥克塔维娅·巴特勒《野生种子》等,与格丽克的生态女性主义诗歌在思想内核上一脉相承,都表现出对自然和女性的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一切生命平等的呼吁。这一群诗人的作品共同构成了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诗歌创作的谱系和网络,很能代表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诗歌创作的显著成就。
格丽克的生态女性主义诗歌写作,拓宽了自然意象的类型,形成了其独特的“女性-自然-文化”意象结构关系,其独特的以女性个体的经历与体验来写诗,既体现出文化意义上的自然与女性群体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联结,又对社会意义上男性和女性身份的不平等现象作出反映与思考,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也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提供了生态意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思考,以及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多个角度的经验。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契机,使西方传统中偏狭的男权、父权制在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视野中被人们再度关注,同时促使人们对生态女性主义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生态女性主义并不局限于关注生态、性别、种族等,较之于西方人类中心论和男权中心论,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关注视野是更加开阔与包容的,其思想核心在于打破种种等级框架,为一切被压迫者发声。通过研究格丽克等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能更好地为全球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转变提供新的视野、经验与方法。
注释:
①参考自Nobel prize.org,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20:Louise Glück https://www.Nobel 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0/summ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