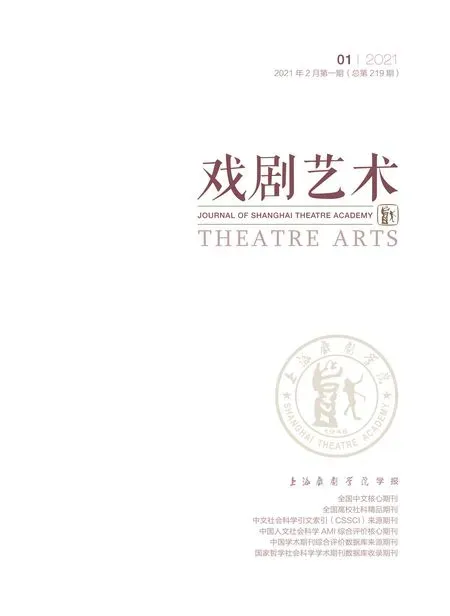论曹禺戏剧序跋的“对话性”及其演变
袁联波
序跋是作家与批评界间建立有效对话机制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作为关于作家创作的写作,序跋往往是围绕“为什么写”“如何写”及“写了什么”等展开的。作家进行序跋写作时,是作为一个叙述者来追述创作过程中的种种情形以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等;同时由于单行本或选集的出版同剧本的发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作者在序跋写作中往往会展开某种自我反思,可能对这期间的批评进行某种回应。换言之,作家在序跋写作中具有三重自我,即叙述自我、创作自我与批评自我。“批评自我”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思想与理性意识,“创作自我”需重建交织着许多感性与非理性元素的创作情境,“叙述自我”则是对前两者的真实而准确的叙述,以及叙述与创作相关的其他事情。序跋写作中,“批评自我”既需建立在“创作自我”的基础上,以便结合作品进行批评;又需超越“创作自我”,以能进行理性的自我反思。“批评自我”以理性姿态,超越于“创作自我”(及作品)与既有评论之上展开批评。正是由于“批评自我”能凌驾于“创作自我”(及作品)与既有评论之上,在自我批评的同时,或明或暗地回应既有批评,序跋的“对话性”才得以形成。序跋“对话性”的形成,是建立在作者强大的主体意识与理性意识基础上的,既不能因既有批评而丧失自身的立场,也不能因作为创作者而毫无理性地排斥批评。在序跋写作中,作者的三重“自我”之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关系。正是由于融入了“创作自我”,融入了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和原初感受,序跋中的自我批评具有了独特的价值意义,在戏剧研究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篇好的序跋当是思想与精神交流的载体,而非简单的自我陈述或事件性记录。曹禺戏剧序跋等自述文字中的“对话性”,从横向关系来看,显示了曹禺同批评界之间的思想张力;就纵向发展而言,则显示出曹禺同主流戏剧批评之间的消长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某种思想困惑。本文拟以曹禺戏剧序跋为基础,结合其他自述文字,探讨曹禺戏剧序跋中的“对话性”及其演变问题。
一
曹禺为自己的剧作单行本写作的序跋并不多。除《〈雷雨〉序》与《〈日出〉跋》之外,似只有1936年初为日译本、1956年为英译本写的序,以及1958年写的《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等文字。曹禺为自己剧作集所作序跋也只有《〈曹禺选集〉序言》(开明书店1951年版)、《〈曹禺剧本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及《〈曹禺选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等几篇。为《蜕变》,曹禺尚写了分析剧作题目的简短文字,而没有再为《原野》《北京人》《王昭君》等剧作过序跋。根据“对话性”的强弱与有无,似可将曹禺的序跋等自述文字分为四个阶段,《〈雷雨〉序》与《〈日出〉跋》为第一阶段,此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为第三阶段,“新时期”为第四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第四阶段,即晚年曹禺的自述性文字,尤其是田本相对他的访谈,包含着对其创作的回顾与反思,以及对他与批评界之间各种对话的回应和总结。总体而言,第四阶段中,相对于青年曹禺而言,经历过数十年人生风雨的晚年曹禺,对于自己创作的自述性文字,除了政治性意味略有增强之外,对于其“创作自我”的叙述以及自己创作的总结性批评,实现了自我回归。由于本阶段曹禺没有再创作新的戏剧作品,本文不拟进行专门论述,而是在戏剧创作的相应时期分别加以讨论,尤其是在自述文字很少的第二阶段。同时由于曹禺与其他批评者往往都是逐一对作品进行多角度的集中讨论,为方便资料运用与论述,这里亦循此例。
在曹禺戏剧序跋等自述文字中,最具“对话性”特征,同时也最具研究参考价值的即是《〈雷雨〉序》与《〈日出〉跋》。《〈雷雨〉序》的写作,几乎都是围绕对批评界的回应和对演出的期待而展开的。在《〈雷雨〉序》中,曹禺说道,“这一年来批评《雷雨》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令我深切的感触自己的低能”。(1)曹禺:《〈雷雨〉序》,《雷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3页。一些批评者提出的“模仿国外”观点,或许是最“刺痛”曹禺的地方;“批评自我”的刻意自谦包含着作者的某种不满情绪。他曾说,“这个剧有些人说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剧的影响”。(2)曹禺:《〈雷雨〉的写作》,《质文》,1935年第2号。他承认《雷雨》受到古希腊戏剧的影响,却否认所谓的“模仿”说。晚年他在接受田本相访谈时还说道,“学外国人的好的东西,是不知不觉的,是经过消化的。不是照搬模仿,而是融入,结合。在这种融入结合之中,化出中国自己的风格,化出作家自己的风格”。(3)曹禺:《曹禺谈〈北京人〉》,《曹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第589页。这也可看作是他对于此类观点的一次总回应。事实上,在曹禺戏剧批评中所涉及的“模仿”及批评取向等问题,已经超出了曹禺戏剧本身,深刻地折射出了中国话剧如何学习西方戏剧,创作中接受影响与简单模仿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界定等重大问题;他们之间的批评与回应实际上就是与此相关的两种不同观念的对话。
在写于1935年的《〈雷雨〉的写作》中,曹禺曾说,《雷雨》“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4)曹禺:《〈雷雨〉的写作》。而在稍后的《〈雷雨〉序》中,对于批评界提出的《雷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的观点,曹禺则表示自己可以追认。这显然是对批评界某种妥协的结果。尽管如此,他却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自己创作时的感受与认识,即“创作自我”。他说,“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而非有意识地“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5)曹禺:《〈雷雨〉序》,《雷雨》,第4页。事实上,这也是他从“创作自我”角度对所追认的“暴露”主题说的一种委婉否认。他认为,《雷雨》是他的“蛮性的遗留”,是“天地间的‘残忍’”。他说,《雷雨》中的人物是生活在“狭的笼”“残酷的井”之中,人物不断地在里面“挣扎”。然而他们就像“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坑里”。(6)曹禺:《〈雷雨〉序》,《雷雨》,第4-7页。这里作者结合创作时的原初感受,将“创作自我”融入“批评自我”之中对《雷雨》的分析批评,同所谓的“暴露”说与单纯的社会批判式解读划清了界线,两者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话性”。此时的曹禺是充满思想锐气的,其主体意识是鲜明而坚定的。“创作自我”对作品的富于生命质感的直接而深刻的剖析,为《雷雨》研究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1941年出版的《英译中国三大名剧》中,在介绍《雷雨》时,尽管引用了曹禺的观点,如《雷雨》写作是源于“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以及“枯井”“挣扎”的主题表达等,但“介绍”仍坚持认为《雷雨》的主题是“暴露了中国社会和大家庭的罪恶”。(7)伯文编选:《英译中国三大名剧》,上海:中英出版社,1941年,第5页。事实上,即使在曹禺通过《〈雷雨〉序》陈述了自己观点之后,对于《雷雨》的主题,当时批评界中持“暴露”说者仍占有相当比例。或许出于革命和政治启蒙的需要,这些批评者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现实性和社会性较强的叙述,而对那些神秘虚幻的内容则往往采取排斥的态度,对于最具民众色彩的戏剧创作似乎更是如此。曹禺在《〈雷雨〉序》中“创作自我”和“批评自我”的阐述,没有得到这些批评者的重视,而他们对于剧作者观点的某种忽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两者之间对话机制的有效性。然而尽管如此,曹禺的观点并不孤独,得到了那些艺术视界更为开阔的批评者的呼应。譬如吕荧在《曹禺之路》的长文中,结合《〈雷雨〉序》,深刻地分析了《雷雨》等作品的主题和艺术。他认为,《雷雨》中的“人的故事只是这篇悲剧的形体,宇宙的主宰才是这幕悲剧的灵魂”。(8)吕荧:《曹禺的道路》(上),《抗战文艺》,第9卷第3-4号,1944年9月。吕荧对《雷雨》的分析是深刻的,并同《〈雷雨〉序》形成了某种互动。
谢迪克曾说,“《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但他同时认为,第三幕“仅是一个插曲,一个穿插,如果删掉,与全剧的一贯毫无损失裂痕”。(9)H.E.谢迪克:《一个异邦人的意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曹禺专集》(下),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1979年编印,第415、417页。独特的片段式的结构,使《日出》在情节上显得不够紧凑,如仅从人物与情节上看,第三幕更似有些“脱节”。曹禺则认为,《日出》的“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日出》的心脏”。他希望“切实地注意到这一幕戏的氛围,造成这地狱空气的复杂的效果,以及动作道白相关联的调和与快慢”。(10)曹禺:《〈日出〉跋》,《日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21、24-25页。这里既有作者“创作自我”的原初感受,也有富于理性意识的“批评自我”。在他看来,有了第三幕,《日出》才算完整;只有展示了翠喜等人生存的悲苦,并在同潘月亭、顾八奶奶之流的骄奢淫逸的强烈对比中,才能充分表达戏剧“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主题。为此,曹禺对欧阳予倩初排《日出》时去掉第三幕的做法感到不满。尽管当时一些批评者对《日出》第三幕提出质疑,但是刘念渠却认为,《日出》的“第三幕决不是强拼在一起的累赘”。他同时指出,“《日出》实在不是一个容易搬到舞台上的剧本”,“演出者必须牢牢的把握住它的主题而充分发挥”。(11)刘念渠:《关于〈日出〉》,刘念渠:《抗战剧本批评集》,汉口:华中图书公司,1940年,第23页。刘念渠从艺术角度的评论既呼应了曹禺的观点,也回应了非议第三幕的批评者,并客观地指出了曹禺戏剧演出的困难性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关于《日出》第三幕的批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超出了曹禺戏剧本身,涉及话剧的文体意识,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关系等话剧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曹禺在《〈日出〉跋》中对批评界的回应,事实上也体现了两种不同话剧艺术观之间的对话。
曹禺在第二阶段对于自己的创作谈论得很少了。为《蜕变》,他仅仅写了分析戏剧题目的简短文字,同时没有再为《原野》《北京人》写作序跋。这一阶段,曹禺对于自己的创作陷入了某种沉默状态。关于他对本时期创作的看法,这里主要依据晚年曹禺的相关论述。在曹禺创作的剧本中,他谈得最少的当是《原野》。当时一些批评者认为,曹禺不熟悉农民生活(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同时由于思想倾向模糊不清,《雷雨》中即已存在的神秘色彩,在《原野》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李南桌曾说,《原野》的“思想那可以说是不大清晰的,——而且有点杂乱,原因是作者从技巧出发,模仿的作品太多,外来的成分占了上风,影响到思想表现的不一致”。(12)李南桌:《评曹禺的〈原野〉》,《李南桌文艺论文集》,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第32页。李南桌在该文中的某些观点和措辞相当犀利与偏激,甚至超越了正常学术批评的范围。至1978年,曹禺认为,“《原野》不算成功,原想写农民,写恶霸欺负人”。(13)赵浩生:《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曹禺专集》(上),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1979年编印,第128页。这是“批评自我”对于作品及“创作自我”的某种否定,而作者的“批评自我”显然或多或少受到批评界此类观点的影响。吕荧则认为,“人与命运的抗争”才是《原野》的主题。他认为“《原野》里反抗命运的人——仇虎,不是作为一个农民(社会的人)描写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原野的人(观念的人)描写出来的”。(14)吕荧:《曹禺的道路》(上)。应当说吕荧对《原野》的把握是深刻的,甚至这种认识与理解是作者本人所没有意识到的。
继《雷雨》之后,《原野》也被一些批评者指认为有模仿的痕迹(对《日出》也曾有过类似说法)。《原野》与奥尼尔《琼斯皇》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批评界关注的重点。1983年,在接受田本相访谈时,曹禺曾说,《原野》“不是模仿奥尼尔的《琼斯王》”;认为“《原野》决不是失败之作”,并准备在死前,“一定要写些散文,对我的剧,无论褒的贬的,我都要谈谈”。(15)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曹禺话剧与西方戏剧的关系,一直是曹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如前所述,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曹禺戏剧本身,而是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戏剧界对于中国话剧如何学习西方戏剧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事实上,正如曹禺晚年所说,“话剧本来是外国的东西,向外国戏剧学习是必然的”,“怕的是自己根底不深,消化力不好”。(16)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175页。作为“舶来品”的中国话剧,本即是在数代戏剧人学习西方戏剧的过程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是在阅读西方戏剧和不断的舞台实践基础上开始话剧创作的,曹禺更是阅读了数以百计的西方戏剧。对于西方经典戏剧作品,曹禺喜欢反复地细细品味,认真研读并将其化为自己的“知识”,乃至形成自己的某种戏剧经验,而这些经验在其创作过程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显现出来。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非简单的模仿。而从《雷雨》诞生直至曹禺晚年,这一问题似乎始终纠缠着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他的心结(17)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147页。据田本相1983年9月14日对曹禺的访谈记录,可以发现,当谈及刘绍铭的曹禺研究时,谈到其创作中的“模仿”问题时,曹禺情绪比较激动。。这或许也是曹禺同批评界之间逐步丧失掉对话有效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北京人》是一部深受批评界和演出者喜爱的剧作,但也有一些批评者认为,该剧宣扬了某种原始主义。1982年曹禺曾说,“当时常常看到周围的人,看他们苦着,扭曲着”,“绝不是宣传什么原始主义”。(18)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剧本》,1982 年第10期。这里,作者结合创作时的原初感受(即“创作自我”)来支撑“批评自我”,是曹禺对于批评者的迟到的回应与对话。谈到《北京人》时,茅盾认为,剧中人物“刻写得非常细腻,非常鲜明。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物”,认为“这是作者极大的成功”;同时他也认为,剧中“北京人”与袁任敢父女的暗示和象征,对于观众或将像一个“哑谜颇费猜详”。(19)茅盾:《读〈北京人〉》,《解放日报》,1942年8月12日。吕荧认为,到《北京人》,“作者所向往的已经不单是原始人的野性,力。而是养成原始的纯真的生活形态”。(20)吕荧:《曹禺的道路》(上),1944年9月。应当说茅盾与吕荧对《北京人》的分析是深刻的。同时吕荧也指出,曹禺戏剧创作“观念,趣味,与真实的不相统一,在结构的重心和剧的结尾上,明显地留下了塑造的刀痕”。(21)吕荧:《曹禺的道路》(下),《抗战文艺》,第9卷第5-6号,1944年12月。茅盾也曾指出,《蜕变》的“处理题材的手法,形象思索的过程,特别是提问题的方式”(22)茅盾:《读〈北京人〉》。是值得商榷的,他敏锐地发现了《蜕变》的概念化倾向,并对此后曹禺又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创作出《北京人》而感到欣喜。然而遗憾的是,从曹禺以后的创作实践可以发现,这些中肯的批评声音,似乎并未对他产生实际影响,他们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批评与接受机制。
二
与批评界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对于作家创作而言无疑是重要的。作家应善于吸收其中有益的养分,而摒弃那些于创作无益的成分。对于两者间的关系,曹禺曾说,批评时“话说狠了,会刺痛一个年青人的情感,又怕过份纵容,会忽略应给与作者的指示”。(23)曹禺:《〈日出〉跋》,《日出》,第30页。显然曹禺期待的是一种客观公正的、具有某种指导意义的批评。自1934年《雷雨》发表后,曹禺成为了中国剧坛备受关注的剧作家。他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会引起剧坛轰动,成为演出团体竞相表演的剧目,并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焦点。或许是对曹禺寄寓了太高的期望,当时批评界对曹禺及其剧作的认识与评价大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第一阶段的序跋等自述文字,既体现了曹禺与批评界之间的对话和思想张力,也蕴含着某种深刻的自我反思,并企图以此建立起两者间健全的对话机制。但在革命与救亡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许多戏剧批评亦具有比较浓厚的政治实用主义色彩。这些批评的角度往往比较单一,对于曹禺戏剧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如作品中的人性的复杂性、某种命运色彩等,往往采取或无视或批判的态度。由于批评角度的单一和视野的狭隘等原因,批评时言辞犀利,甚至带有某种强烈的情绪色彩。另一方面,对于曹禺戏剧,自始至终也有较为客观公正的评论,并且提出了关于创作方法和艺术上的一些诚恳而深刻的建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曹禺与批评界之间的思想交流发生了某种错位,他似乎更为在意的是前一种批评倾向,而非后者;而他在序跋中的“批评自我”和“创作自我”的分析和阐述似乎也未得到预期的回应。由于两者关注焦点的错位,曹禺与批评界之间的对话机制逐渐失去了有效性。
在《〈雷雨〉序》与《〈日出〉跋》中,曹禺有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且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对自己不认同的,尤其是某些不客观的看法展开了讨论式分析。《〈日出〉跋》中,曹禺花了大量的篇幅对朱孟实等人的某些观点进行了逐一讨论。在这两篇序跋中,曹禺的主体意识是鲜明而坚定的。“批评自我”与“叙述自我”能够遵循“创作自我”的真实状态展开批评与叙述,三重自我之间是一致的。在这两篇序跋中,应当说作者的“批评自我”做到了超越于“创作自我”(及作品)之上而进行理性分析,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对于某些不客观批评的不满,以及对于公正批评的热切期盼。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曹禺对于自己的创作几乎陷入了某种沉默状态。写作《〈雷雨〉序》与《〈日出〉跋》的充满锐气的曹禺渐已远去。在某种程度上,本阶段自述文字的减少及其“对话性”特征的弱化,可看作是曹禺进入了对自身创作的某种调整期,似乎也意味着他创作中出现了某种思想困惑。
到第三阶段,曹禺戏剧序跋等自述性文字向革命文艺思想靠拢。在《〈曹禺选集〉序言》(1951年)、《〈曹禺选集〉后记》(1978年)等文中充满了“统治者”“剥削”“荒淫残暴”“无产阶级”等政治话语,在叙述逻辑上亦具有简单明了的政治化色彩。曹禺说创作中他“凭一些激动的情绪去写,我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追根问底,把造成这些罪恶的基本根源说清楚。譬如《日出》这本戏,应该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社会的控诉,可是当时却将帝国主义这个罪大恶极的元凶放过”。(24)曹禺:《〈曹禺选集〉序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曹禺专集》(上),第60-61页。在《〈雷雨〉序》与《〈日出〉跋》中所呈现出来的灵动和生命质感消失了。在接受田本相访谈时,曹禺曾说,“我真的是服毛泽东思想的,我也很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又说,“建国初期,周扬的话,我佩服得不得了”,并且他就是按照周扬的观点修改《雷雨》《日出》的。(25)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37页。然而如他所说,没有“化为自己的血肉”的思想,毕竟不是自己的,也并没有帮助他走出思想困境。
在第三阶段的一些序跋等自述文字中,曹禺在几乎否定自己作品的同时,还对其作品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在《〈曹禺选集〉后记》中,曹禺说道,“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但严格地说,那时我仍还根本不懂得革命”。(26)曹禺:《〈曹禺选集〉后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曹禺专集》(上),第64页。在接受田本相访谈时,他又说“在这个戏里,瑞贞觉悟了,愫方也觉醒了,我清楚地懂得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没有点明”。并说,“写《北京人》是党影响着我”。(27)曹禺:《曹禺谈〈北京人〉》,《曹禺选集》,第588、589页。可见,曹禺在序跋等自述文字中,“批评自我”因主体立场的丧失而趋于消失了。同时由于主体立场的丧失,“批评自我”非但没有建立在“创作自我”的真实体验基础上,还反过来改写了对其“创作自我”的叙述。事实上,除了一些事件性记述之外,“叙述自我”主要呈现出来的则是一些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消化的政治性术语。
曹禺曾多次说自己是一个胆小而敏感脆弱的人。正如周恩来所说,“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28)徐开垒:《访曹禺(节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曹禺专集》(上),第141页。在为《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版)作后记时,曹禺曾说,剧集的出版“却总还为我带来一些不安”。(29)曹禺:《〈曹禺选集〉后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曹禺专集》(上),第64页。剧集再版带来的“不安”,或许是害怕某种不公正的和偏激的评论;也正是这种长久的“不安”,使其创作的主体意识逐渐消失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主流叙述之中。《明朗的天》与《王昭君》的创作,明显是这种情形下的产物。对于《王昭君》,曹禺说他是受周总理的嘱托而创作的。戏剧“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她有志气,有胆识,愿意为民族和睦和当时汉胡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的一生”,因此“人们再也不为她流伤心的泪,而是为她唱昂扬的歌”。(30)曹禺:《昭君自有千秋在——我为什么写〈王昭君〉》,《中国民族》,1979 年第 2 期。事实上,正是过于明确的创作主题,使王昭君等人性格刻画单一,缺乏动人的艺术力量,明显地留下了如吕荧所说的“塑造的刀痕”。晚年的曹禺曾说,“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叫人看了那么直来直去,一览无余,不应该是那么窄狭,那么简单,一看就知道是反封建、反这、反那”。(31)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同田本相的谈话》,《戏剧论丛》,1981 年第 2 期。但是并不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对于政治的贫乏了解,使他没有能力处理好艺术与政治间的关系。早期创作中即已流露出的“塑造的刀痕”问题,不但没有被克服,反而在《明朗的天》与《王昭君》等剧的创作中得到比较集中的暴露。
序跋的“对话性”折射了曹禺与批评界之间的某种思想张力。在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等主流思想的影响下,曹禺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随着曹禺创作思想不断地向主流戏剧批评靠拢,他在序跋等自述文字中的“对话性”特征也逐步减弱,直至进入第四阶段。青年曹禺曾说《雷雨》并非有意识地“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晚年曹禺也曾说,“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叫人看了那么直来直去,一览无余”。晚年曹禺在对戏剧的认识上实现了自我回归。然而在创作期间,序跋等自述文字“对话性”弱化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曹禺创作主体思想渐趋贫困化的过程;而对过去创作的重新认识与解读,显示出曹禺对于自我的怀疑与否定。全面向主流戏剧批评的靠拢,使他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创作方式,而选择了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化戏剧创作。这一转变并未使曹禺迎来创作上的新生命,反而使其陷入更大的思想困惑之中。同时如前所述,曹禺戏剧序跋等自述文字的对话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曹禺戏剧本身,深刻地反映了在戏剧现代化过程中,戏剧界对于中国话剧如何学习西方戏剧,以及话剧的文体意识、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透过曹禺戏剧序跋等自述文字,可以清晰地触摸到话剧现代化过程中,不同戏剧艺术观念间碰撞和对话的历史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