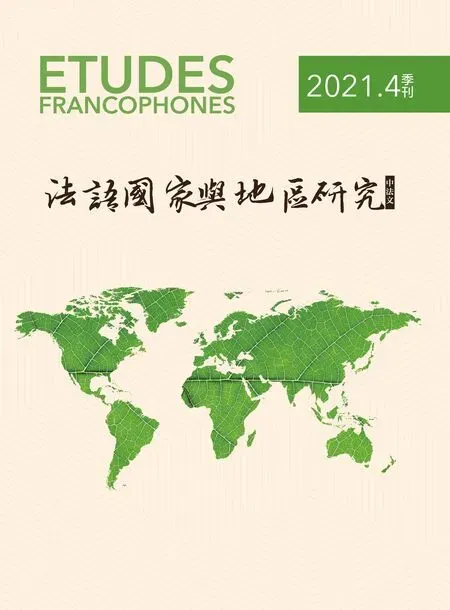从文学到电影:奥斯曼·桑宾笔下自主与开放的非洲
段维珊
内容提要 早在20世纪60年代,奥斯曼·桑宾便力图在其文学及电影作品中呈现出非洲的本来面貌,而非外界加诸其上的刻板印象。他的小说《神的儿女》叙述了一个历史事件:1947-1948年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工人大罢工;电影《黑女仆》讲述了一个达喀尔姑娘在法国南方做女佣的经历。在创作时,桑宾擅长将文学的写作手法与电影技巧相结合。本文将从空间与叙事手法两个方面,研究上述两部作品间的相似之处。在奥斯曼·桑宾看来,无论外部枷锁如何沉重,非洲人的自我意识都未曾泯灭,他们始终秉持开放心态,渴望得见非洲蓬勃发展并融入世界。
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起,奥斯曼·桑宾(Ousmane Sembène)始终致力于从非洲人的角度向世界展示非洲,这一坚持在其小说与电影作品中均有体现。他既是作家又是电影导演,这一双重身份让其创作手法更加丰富,他在小说中恰当地运用电影技巧,增强故事的可视性,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他还在电影中适时插入小说的叙事手法,为观众解读荧屏上的每个画面。桑宾作品中的主人公性格鲜明且极具典型性;他笔下的非洲形象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他深刻剖析非洲人内心的复杂性,以反驳外界认为非洲“原始”“野蛮”“迷信”的刻板印象,他坚信非洲人拥有理性。艺术家并不执着于歌颂非洲自然的美好,他更关心非洲社会的变化和人民的生活。笔者在其众多作品中选出了两部:小说作品《神的儿女》(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和电影作品《黑女仆》(La Noire de…)。这两部作品在空间建构与叙事手法方面有着共通之处,而基于对上述共同点的分析,本文将探讨奥斯曼·桑宾眼中的非洲形象,以及这种形象如何传达出黑人性的内涵。基于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文章的第一部分将首先探讨桑宾两部作品中空间的逻辑性,即人物与特定地点之间的互动,空间如何反映出人物的精神状态。随后将研究空间的转换和地点的变换如何拓宽人物的精神世界。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基于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笔者将首先研究两部作品中非线性的叙事时间,小说与电影中的时间线索均不明朗,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不受局限,随后将研究两部作品中的叙事视角,分析桑宾如何以内外聚焦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出他眼中开放的非洲形象。
一、空间:自我的依托
在一个故事中,空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元素。每一部小说都需要一个空间体系来进行自我建构。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空间往往是一面背景墙。它总是受书中的人物、地点或事件所限,为情节服务,仿佛人物与空间有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桑宾的这部小说也是如此:空间与人物之间往往有暗合之处,某个特定地点会成为某一特定人物的象征。同时,空间在桑宾的作品中也起着主导作用,它拓宽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成为非洲民族精神的载体。在分析两部作品中的空间建构之时,笔者会用到两种方法:第一,研究空间的逻辑性,第二,研究空间的转换,借此分析桑宾如何描绘出他眼中独特的非洲画卷,又借助画笔诠释出“黑人性”(négritude)中立足于自我的精神内涵。
1.空间是人精神状态的外部映象
2000年,在巴黎瑟利其国际会议中心地理学研讨会(Logiques de l’espace,esprit des lieux.Géographies à Cerisy)上,法国地理学家雅克·列维(Jacques Lévy)与米歇尔·卢索(Michel Lussault)首次聚焦于空间的逻辑性这一概念,研究空间对于人以及社会的影响、空间与人的互动。而依据空间社会学的理论,空间的逻辑性是指为人物与空间建立一个对话体系,从而更好地找出人物与特定地点之间的逻辑关系①Jacques Levy,Michel Lussault.Logiques de l’espace,esprit des lieux.Géographies à Cerisy. Paris:Belin,2000.。奥利弗·弗赖(Oliver Frey)也在其文章《城市社会学或空间社会学?城市的概念》②Olivier Frey.«Sociologie urbaine ou sociologie de l’espace ? Le concept de milieu urbain».[En ligne]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sociologies/4168.Page consultée le 27 février 2021.中具体分析了城市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基于这一研究,探索桑宾两部作品中的空间如何与人的精神世界相融。
小说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城市,它们划分出三个不同的故事框架:巴马科(Bamako)篇、捷斯篇(Thiès)和达喀尔篇(Dakar)。在阅读整部作品的过程中,读者会感受到这三座城市次第呈于其面前,每座城市有不同的色调。虽然整部小说的主旋律均为反抗,但这三座城市代表不同的抗争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巴马科代表非洲传统城市,体现了殖民统治初期非洲的情状:黑人和白人之间冲突不断、难以调和,前者始终处于下风;保守的老一辈和大胆的新青年之间难以沟通、拒绝妥协,前者不愿接受改变。这座城市的特点表现在两个中心人物的对立之上:老妇人尼亚克罗(Niakoro-la-vieille)憎恨白人,忠于非洲传统,拒绝追随时代的脚步;新青年蒂耶莫科(Tiémoko)时常心血来潮,头脑发热,有高涨的斗争热情,却全无有效的斗争方式。这一切都表明,在当前阶段,面对殖民侵袭,非洲人虽有心抵抗却束手无策。在这一时期,非洲人的自主精神同样初步萌生,渴求独立之焰灼烧着他们的内心,也焚化了他们的理智。巴马科展现了一个略显脆弱无力的非洲。
捷斯城将读者带进了抗争的第二阶段。罢工开始前,在捷斯生活的人们已然贫困交加、饥寒交迫,这场罢工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苦难。小说里,作者刻画了一幅清晰的捷斯城图景,“捷斯:在一片腐烂中,只有几棵不起眼的灌木,妇人们还在收割灌木上的果实,以维持生计”。(38)③Ousmane Sembène.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Paris:Presses Pocket,1971.本文引用凡出自此书者将只夹注页码。这一切无不展示出,罢工之下,非洲人民生活艰难、度日如年。然而生活愈艰辛,愈会激发非洲人民抗争、力求改变之心。表面看来依然脆弱、任人欺凌的非洲人已然不满足于坐以待毙,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并理智地采取行动。彭达(Penda)是一个穷困潦倒、无人尊敬的妓女,但她在必要之时,却为维护黑人群体的利益而献出了生命。在他人看来一向懦弱无能的豆豆(Doudou)也表现出他的勇敢和忠诚:为了支持黑人获得应有的权益,他拒绝了300 万非洲法郎和一个酋长头衔,只为将罢工进行到底,这便是“黑人性”内涵中精神胜于物质的最佳印证。捷斯城中满是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类平民英雄映射出了作者眼中的非洲。在小说结尾,作者再次将读者带回了这座小城,这表明无论抗争发展得如何激烈,桑宾都坚持要回到原点,要将重心放在人民和他们的生活上,关注大众的需求。对于非洲人生活环境的描绘,作者不加任何修饰,他希望启发非洲人认清事实:在最黑暗的时刻,非洲的崛起不能依靠外力,人民需要自主改变命运。
达喀尔是一座代表着希望、重生与独立的城市,它大踏步迈向未来,体现出非洲人的无限潜力。这座城市的出现也将读者带往抗争的第三阶段:冲突已然白热化,黑人的力量不断增强以至于白人开始使用武器镇压:“统治当局大大加强了秩序管控:警察、水兵、宪兵、小兵,似是不知疲倦般在街上巡逻。”(317)此情此景下,黑人不甘示弱,他们的罢工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座城中的妇女形象也有很大变化,她们坚强而勇敢,如成熟女性的代表拉马图拉耶(Ramatoulaye)、马梅·索菲(Mame Sophie),以及新一代青年女性,恩德耶·图蒂(N’Deye Touti)和达乌达(Daouda)。达喀尔能够孕育出一切变化:“达喀尔的赛马场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盛况。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渔民以及所有大公司的员工”(328)。这一事态进展也表明,非洲远非一成不变,时代的大潮中有一条不容忽视的黑色支流,非洲人也并非懒散堕落,这些画面均颠覆了西方强加于非洲的刻板印象。
《黑女仆》这部电影中有两个不同的城市情境:达喀尔(Dakar)和安提布(Antibes)。这两座城市展现了女主人公迪乌瓦娜(Diouana)生命中两个不同的阶段。虽是黑白影片,但这两座城市的色调却对比鲜明:一座缤纷绚丽、活泼生动,另一座灰暗单调、无精打采。因为在迪乌瓦娜的心中,她的家乡达喀尔清晰、明亮而触手可及,在现实生活中,她所在的安提布却模糊、昏暗而遥不可及。由此可见,这两座城市的不同色彩与女主角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到达法国后,迪乌瓦娜的独立之梦随即幻灭,这进一步体现了欧洲并不是解放非洲的灵丹妙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非洲苦难的始作俑者,但解放者的角色需要非洲人立足于自我,独自担任。
电影中达喀尔城所扮演的角色,与小说中的巴马科城遥相呼应,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非洲人最初的心态,前者偏重于无力,后者更多是懵懂天真。在达喀尔的生活始终萦绕在女主人公的脑海深处。她的家、达喀尔的广场,对身处法国的迪乌瓦娜来说,都不再是当下的真实,观众也有理由对其记忆与叙事话语产生怀疑。但迪乌瓦娜却让人不愿起疑心,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少女的真诚和坦率。镜头下,达喀尔城中既有富人区,也有贫民窟。为了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迪乌瓦娜逃离难以窥见未来的 “窟洞”,闯入沐浴在阳光下的现代生活。作为新一代非洲青年女性,她独立勇敢,有所追求,也相信自我的力量能为她带来光辉前景。
象征女主人公未来的城市——安提布与小说中达喀尔城所扮演的角色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展现了人物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故事发生之时,迪乌瓦娜正身处其中,所以观众有理由期待这位青春的非洲少女与这座美丽的欧洲都市间有积极的互动。然而到头来,他们的期待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电影中百分之九十的场景都摄于室内,即迪乌瓦娜雇主的家。这也间接表明女主人公的未来无望,她永远无法在法国过上梦想中的生活。这个国家对她来说,“就是厨房、客厅、卫生间”④Ousmane Sembène.La Noire de… [drame] Sénégal,Filmi Domidev,1966.本文引用凡出自此电影者将只夹注时间。(25min24s),是一个 “黑洞”(25min44s),在这里她 “不认识任何人”(37min37s)。她独自一人被敌人包围,无亲友相伴,与外界相隔。这个绝望的女孩只能以自杀来寻回失去的自由。故事中的讽刺意味在于女主人公在离开家人和故土后,想象着自己即将过上自由与独立的生活,但事实上她却从自由之身转而成为囚徒。她的身体虽然受到禁锢,但心灵却依然自由。她完全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能认清自己的境遇。在这一点上,她与小说中的罢工者命运相似:即使受到外界环境的束缚,但非洲人的心灵是自由、自主的。
桑宾将生活搬上艺术舞台,揭示出非洲人的复杂处境。他们已经开始寻求解决方案,力图自救,摆脱困境。然而,外部世界的枷锁,如物质的匮乏、他人的歧视与非难,使他们无法重获新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略感沮丧,即使非洲人渴望展示真正的非洲形象,即他们有可靠的工作能力、独立的思考能力,但西方人不愿相信,仅因这一形象与其刻板印象大相径庭并会损害其既得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确是非洲人自我解放的客观约束。
2.空间拓宽人的精神世界
根据《电影技巧基本理论》一文,镜头切换指“在跟踪拍摄时,摄像机在空间中水平移动。而这种动态技术也相当于一个演员在戏剧舞台上移动”⑤Frédéric Gimello.Les Techniques cinématographiques de base.[En ligne] http://fgimello.free.fr/documents/technique_de_base_cinema.pdf.Page consultée le 18 février 2021.。桑宾不仅将这一创作手法运用在其电影中,在其小说创作中也有迹可循,他在书中融入大量地理空间转换,让故事拥有史诗般的色彩。
《神的儿女》并不是一部歌颂英雄丰功伟绩的史诗,而是在讴歌平凡人的伟大。作品中空间转换的手法展示出非洲人的视野在不断扩大,自我空间在不断蔓延。故事中的人物在相距甚远的地点间往回穿梭,他们拒绝被困在角落中等待:为了养家糊口,拉马图拉耶一次又一次来到朱玛广场,在多家商店间辗转徘徊,只求购得5 公斤大米。虽屡次遭拒,但她从未失去信念。而在故事情节的高潮,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从捷斯到达喀尔的游行让这部作品的史诗色彩愈发鲜明。
电影《黑女仆》也是一部史诗,一部歌颂平凡少女为了自由而牺牲自我的史诗,她的平凡也因其举动而变得神圣。在影片的最开始,一艘大船占据了观众的视野。女主人公跨越山河,终于到达梦想中的国度——法国。镜头拍下她从走下轮渡到踏上法国国土的全过程。随后,迪乌瓦娜坐着男雇主的小轿车进行了一次极短的“旅游观光”。这也是她唯一一次有机会欣赏到这个美丽的国家,虽说依旧隔着窗户。这层车窗也象征着黑人在争取自由之路上难以攻克的关卡。从她到达雇主家中的那一刻起,她旅行的目的地就只剩下三室一厅。记忆无数次将她带回家乡达喀尔,那时她还是自由之身。镜头跟随女主人公在家乡的脚步,展现出这个非洲少女想要打破社会中的条条框框而四处奔波的场景。她并非似小说《神的儿女》中的拉玛图拉耶那般,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四处流浪,迪乌瓦娜找工作的欲望来自一颗渴求自由、自主的心,而非外界压力。她日复一日地走遍整个城市,尽管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但她始终表现得无比坚定,在这一点上,两位女性如出一辙。在法国,她被困于封闭空间中,但较之以往,她的内心世界却愈发宽广。离开人世前,她不再天真,已然认清现实、触摸到了挡在她身前的钢盔,也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将其摧毁。身体难以获得自由,心却不然,迪乌瓦娜用行动证明了自由并不完全由物质条件决定,也可以由精神世界给予。
两部作品中,空间的逻辑与转换均侧面体现出人物心态的变化,非洲人的自主意识在不断加强。在桑宾看来,国界与地域的限制不能成为非洲人自锁于象牙塔、拒绝为自己负责的借口,要想获得身体上的自由,首先要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他同样认为,随着视野不断扩大,更多的非洲人会认清自己的处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完全有能力独自掌控命运,
二、枷锁中的开放性心态
在奥斯曼·桑宾看来,非洲人的思想是开放、多元的,因此他的叙述手法不受客观的线性时间或特定的叙事角度限制,而是采用错时与内外聚焦相结合的手法,不仅展现出非洲人眼中的自己,也传达出欧洲人眼中的非洲。
1.不受局限的心灵状态
奥斯曼·桑宾的电影作品正如濮波先生所述,“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对象,而逐渐变成了一种观众了解社会、参与社会的社会性实践”。⑥濮波.《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非洲本土电影叙事、产业、媒介对社会的介入观察》.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13(05):1.在影片《黑女仆》中,镜头接过了导演的叙事任务。“每部叙事作品中都有双重时间性:故事发生的时间和讲故事的时间。”⑦Gérard Genette.Discours du récit.Paris:Éditions du seuil,2007.想讲好一个故事,作家或导演无须严格遵循某种线性、规律的时间进程。事实上,错时更能代表人类心灵的状态:我们的思想永远在流动,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为了阐明这一论述,笔者将在本文探讨的两部作品中寻求例证。
首先是追叙手法。在小说和电影里,塞姆班笔下的人物始终希望回到从前。《神的儿女》中,大多女性角色在痛苦时,脑海里便不断回放往日的平静岁月:因这场罢工而失去丈夫的胡迪娅·姆·巴耶(Houdia M’Baye)如此,看到丈夫日渐憔悴的乌拉耶(Oulaye)亦是如此。
“胡迪娅·姆·巴耶还在沉思。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她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过去的画面,那些快乐的时光。在8年的共同生活中,丈夫巴迪安(Badiane)只让她失望过一次,8年中只有一次……她又想起了刚结婚时……”(92)作品中人物对于往昔幸福时光的追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下部分非洲人的精神状态,现实过于痛苦,让他们难以接受,枷锁过于沉重,他们难以用开放的心态迎接改变。
电影《黑女仆》从故事的中间展开叙述,女主角已抵达法国。她的身份不明,旅行的目的与动机不清,观众只看到一个漂亮而又优雅的非洲少女。不久后,一个欧洲人的出现让他们略受冲击:这个穿着打扮都无比精致的女孩只是一位女佣。这种形象与身份间的反差,加强了观众对该人物的性格以及故事情节的好奇。导演却一直等影片进行到11 分钟才给出答案:故事真正的开端在达喀尔。“就在那个清晨,故事拉开序幕”(11min42s)。闪回的手法一瞬将观众带到女主人公的故乡,进一步揭开非洲大陆的面纱。迪乌瓦娜是一个有决心、有野心的女孩,她想在白人那里找到一份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她成为一个欧洲家庭的女佣。这些本该让她感到幸福、满足的回忆,现在却让她分外痛苦,她的努力最终换来的是在安提布囚徒般的悲惨生活:她就是一个杂工,一个奴仆。对于迪乌瓦娜、胡迪亚·姆巴耶或乌拉耶来说,回忆困扰着当下,她们太想回到过去,以至于不愿面对现实,也逐渐对未来失去希冀。像她们一样的非洲人并非少数,这些人躲在保守主义中,步步谨小慎微,始终扛着捍卫非洲传统的大旗,害怕接受任何外来事物,时刻警惕西方文化的侵袭,实是受尽生活之苦,只想求得自我保护。
其次是预叙手法。小说中象征着“变革”的人物——蒂埃莫科的一番话,已经让人看到这场罢工后,非洲的未来会在何处:“你知道吗?这次罢工后我们应该多上点课。”(148)他没有被当前的形势蒙蔽,而是已经放眼未来,想象着黑人所应有的无限可能。这体现出:一方面,在此次与白人的斗争中,黑人自认能够大获全胜;另一方面,部分非洲人已经在寻找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来保障人民的福祉,那便是教育。
在影片中,预叙手法向观众透露了迪乌瓦娜决心离开家乡的原因:看一看法国。她希望女雇主会对她的工作能力感到满意,既而予以她相应回报:“也许夫人会带我在城市里转转,我们能一起去看看戛纳、尼斯……四处走走,逛逛漂亮的商店……我会把这些照片都寄回达喀尔……”(11min)。但这种合情的愿景终究只是幻影。
非洲人希望得到西方世界的理解,但他们也意识到,只有足够了解西方世界,才能够与其交流,进而得到对方的理解。但正是因为想要接触广阔的外部世界,他们才进一步被绑住手脚,他们努力呈现的美好一面也被部分人恶意扭曲。尽管如此,预叙的手法使我们看到,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发展,融入世界是黑人性的本质,黑人性是一种联结世界、联结他人的方式,是向世界的敞开,是与他人的接触与碰撞。
2.开放的多元视角
根据热内特的理论,文学作品有以下三种叙事视角:零聚焦也即全知叙述,内聚焦和外聚焦。在桑宾的两部作品中,内聚焦和外聚焦担负起传达作品主题、诠释非洲民族精神的重任。
在小说作品《神的儿女》中,作家以大量的笔触描绘非洲城市景象,情节大多以对话推进,第三人称叙述占据了大面积篇幅。桑宾以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了这场罢工的点滴,例如,工人间的争吵与彼此鼓励:“‘干活的人是我们,工作和那些白人也一样,凭什么他们挣得比我们多?……要想活得体面些,就得罢工!’‘对!罢工!罢工!’”(24)以及罢工的环境:“从屋子里到小院,从小院再到邻近的街区,只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回响:‘罢工!’”(27)除此之外,作者不仅关注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发生的环境,同时也关注参与事件的每一个人。他清晰地刻画出其笔下人物的形象,让读者有看电影般真切的体验。“这个人好奇心极重。看见他没有人不乐的,他穿着一件老旧的土黄色外套,衬衫耷拉到裤子上,裤子又太长,裤脚都是褶子,一直垂到凉鞋上。”(37)在作者看来,对非洲环境以及人物外貌、性格的朴实描写能够让读者摆脱刻板印象的条框,看清真正的非洲。
但在写作过程中,桑宾也不满足于始终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他还要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让读者与人物有更多的共情,让他们看到在罢工过程中,不同人物眼中的世界都覆上了同一层焦虑不安的色彩。
“她边走边在脑海里回放上午发生的事,口中喃喃自语……我怎么能告诉哈德梅(Hadramé)我还会回来呢? 即使我回来了,我又能做什么呢……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场罢工,还是,难不成我是个坏人?不,我不是坏人……这次罢工太苦了,我们有太多该思考的事……”(84)
拉马图拉耶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象征着理智而叛逆的非洲女性。她没有将自身问题归咎于他人,而是不断自我发问、自我探索,思考着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她的思想也体现出黑人性的又一内涵:即使内心脆弱,被苦难折磨,但依旧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寻求解决方案。
“遭受了这么多折磨,现在倒好,我又回到了苦难之始。难道我就命该受罚?上帝啊,您为我做过什么?……饶恕我,帮帮我吧,上帝,我好饿,我真的好饿。”(206)
往日的保安队长苏恩卡雷(Sounkaré)此刻也暗自认输,意志力不断地被生理饥渴消耗殆尽。桑宾将非洲人对自我、对世界的认知毫无保留地展现给读者,企图激发读者的移情能力。非洲人同样有着一切正常的生存需求,却因为外界的折磨与否定,逐渐开始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将自己困于没有出口的封闭空间,不再接受改变的可能性、不再相信世界的开放性。由此可见,非洲人并非不具有开放的心态,而是在难以满足生存需求的前提下,他们寸步难行。
在电影中,对于叙事视角的探讨不同于小说,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摄像机的位置。由此,镜头的视角就是故事的叙述视角。影片中,镜头像一双眼睛,时而从女主人公的角度观察其周边环境,时而从白人雇主的角度观察女主人公,时而只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客观地呈现黑人与白人间的冲突,而不做任何分析。
当镜头落在了女主人公迪乌瓦娜的身上,影片便覆上了一层“心理小说”的色彩,因为她不断地向观众吐露心声,而在其雇主面前却始终不言不语,只说“好的,老爷”或“好的,夫人”。这种内心独白从影片的开端持续到结尾。在迪乌瓦娜眼中,“夫人并不高尚”(37min06s),白人夫妇温馨、舒适的家只是一个牢笼。影片中,她不断地描述自己单调、乏味的生活环境:“法国对于我来说,就是厨房、客厅和卫生间。”(25min24s) 同时,她也开始困惑于自己的身份,“我在这里到底算什么?厨娘?清洁女工?洗衣女工?”(25min52s)和拉马图拉耶一样,她也在不断反思,而通过这种反思,迪乌瓦娜终于意识到,在白人雇主眼中,她仅仅是个奴仆。导演在此间接表达出部分欧洲人始终怀有种族主义情结,理所当然地崇尚尊卑有别。
电影镜头有时会与主人公拉开距离,以外聚焦的视角客观描述剧情。故事最开始,白人雇主邀请朋友来家中做客,镜头便以旁观者的角度捕捉了每个人对迪乌瓦娜的不同态度,有新奇、有鄙夷、有冷漠。当一位白人女性径直调侃迪乌瓦娜“像个动物似的”(21min24s),无人反驳,但镜头却在此刻移到一位白人男性的面部表情上,他欲言又止,眼神犀利,却最终还是输给强大的社会成见,一言不发。
当镜头聚焦在白人夫妇身上时,迪乌瓦娜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都变得神秘莫测、难以捉摸。这也是由于从始至终,除了吩咐任务,他们从未与这个黑人女佣有过任何交流,也不认为有与其交流的必要。对他们来说,这个黑人女孩只是“有用”。影片中,迪乌瓦娜的女雇主不断强调,“迪乌瓦娜,别忘了你就是个女佣!”(33min45s)。常年在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她已形成了麻木的认知:这个非洲女孩除了女佣的身份外别无所求。当男雇主提出让迪乌瓦娜休两天假时,她更是不假思索地回绝:“为什么要让她休假?她休假又能干什么?”(31min16s)她不愿给予迪乌瓦娜最基本的尊重,这也是黑人被物化的有力证据。当迪乌瓦娜开始反抗之时,这位白人女性更是以难以置信的口吻一再重复:“她疯了,完全疯了!”(37min29s)这对白人夫妇从不了解迪乌瓦娜,是因为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了解,也不愿做出任何妥协,而最初迪乌瓦娜还天真地以为她与夫人之间存在友谊。这一切都在不断加深黑人与白人世界间的隔阂,宣扬开放多元心态的白人,却连一丝理解都不愿给予黑人,反而是后者在不断做出努力与让步,却也难以改变前者的态度。
通过上述叙事手法,桑宾传达出非洲人身处枷锁中的开放性心态。非洲渴望发展并融入新世界。非洲人愿意从其他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恰是部分欧洲人仍被地缘政治思维蒙蔽了双眼,不愿看清时代背景早已发生转变。
结语
通过分析桑宾文学与电影作品之间的呼应,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奥斯曼·桑宾眼中的非洲。这位艺术家不仅在讲述集体记忆中的非洲,更在借助过去的事件更好地传达非洲的现状。小说与电影中类似的空间建构与叙事手法都与桑宾的创作目的相吻合:多角度、全方位展现非洲的变化,从而不仅让非洲人更好地理解自己,也让世界更好地理解非洲。这一创作目的也包含了桑宾对于黑人性内涵的诠释,完整的自我建立在自我理解、自我接纳、自我担当之上;完整的世界建立在理解他人、包容他人、接纳他人之上。
桑宾认为非洲大陆会有何种未来,完全取决于非洲人自身。正如塞内加尔女作家法图·迪奥姆(Fatou Diome)所说:“我知道我的同胞们在努力,努力工作与生活,但他们更需要意识到,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会来自他处。‘未来由他人给予’是一个弥天大谎。”⑧Alison Rice.“An Interview with Fatou Diome”.sur Francophone Metronomes,juillet 2005,1h37min40s.Vidéo disponible su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6RHx8ifO38.不仅是非洲人需要打破不实之镜,其他人也需摘掉有色眼镜,去认识真正的非洲,而非刻板印象中的非洲。我们看到,非洲发展的障碍很大一部分就出自这些陈词滥调。事实上,一个人、一个国家,以至于一个大陆想要获得身份认同,既需要清晰的自我认知,同时也必须得到他人的理解与肯定。只有愿意不存偏颇地理解自我、理解他人,才能够看清自我,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