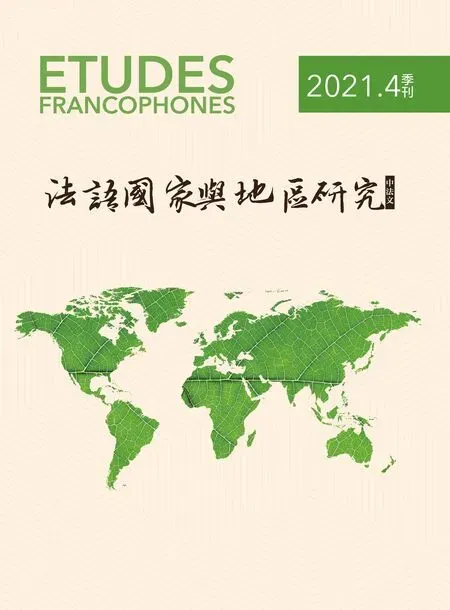波德莱尔美学思想中“恶”的探索
——纪念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
钟晋芸
内容提要 波德莱尔是现代文学的开创者,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恶”是贯穿波德莱尔整个诗学的精神旨要。他的诗集《恶之花》以“恶”为主线,为整个诗歌甚至文学界开辟了全新的视域。波德莱尔之“恶”含义广泛:在美学范畴内,“恶”即是丑;放眼社会,“恶”是一种苦难;在宗教领域,“恶”可被诠释为原罪;在身体方面,“恶”可以被解读为痛苦、衰老甚至死亡;而在反叛的精神层面,“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抗、一种越界。本文将从美学角度探索波德莱尔之“恶”背后潜藏着的令人震惊的灵性诉求、高贵意义以及感动人心之美。
引言
“恶”在字典里被解释为恶劣、坏。艺术中的“恶”是一种大胆的精神,是对伪善与墨守成规的颠覆,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与趣味。波德莱尔虽然并非是艺术中“恶”之开创者,但他的诗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在承前的基础之上将“恶”与美并谈,为“恶”开启了一片全新的领地。追求美是波德莱尔毕生的事业,也是困扰他一生的大问题。他认为:“严格来讲,诗的原则仅仅只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①Charles Baudelaire.Œuvres complètes II.Paris:Gallimard,1976:334.此处系作者所译。波德莱尔对美的定义有着一种令人新鲜的古怪,美在他的眼中或是忧郁、或是痛苦、或是厌恶、或是苦恼、或是遗憾又或是丑恶,总之,是与传统中以和谐、优雅、完整、鲜明、愉悦为美的理念背道而驰的。他在为《恶之花》写的一首《跋诗》(Épilogue)中将自己神圣的美学使命阐述如下:
我从每件事物中提取精粹,
你给了我污泥,我把它变成黄金。②Charles Baudelaire.Œuvres complètes I.Paris:Gallimard,1975:192.此处系作者所译。
这里的“每一事物”可指这世间大大小小被世人视之为轻贱、可怖、可憎或是微不足道的消极元素:丑陋、丑恶、情欲、痛苦、死亡、尸体等等,但这些因素必定满足一个条件:诗人能够从中提取出“精粹”,将其变为“黄金”。无论是“精粹”还是“黄金”,一定是蕴含于“恶”中的圣洁,是隐藏在这些消极事物背后的积极的精神启示。在波德莱尔看来,世人眼中值得称赞的美丽事物也许并没有高贵的意义可寻,而丑的事物虽然外表令人作呕或是惧怕,但它们当中蕴藏着深邃的奥秘。他曾在《论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 [I])一文中称赞戈蒂耶通过表达丑恶与怪诞而通向美的才能:
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表达看到一件美丽的艺术品时想像力所获得的幸福,哪怕是一件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冷漠、最可怕的艺术品。丑恶经过艺术的表现化而为美,带有韵律和节奏使精神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这是艺术的奇妙的特权之一。③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7—78.
“丑恶经过艺术的表现化而为美”,这便是波德莱尔所抱定的化丑为美的决心。作为一个神经敏感而又饱受痛苦折磨的现代诗人,波德莱尔擅于在苦难中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对“恶”的耕耘来传递美,而这种美并不是表面的精美雅致,而是一种从恶性之中绽放出的神圣之光。本文将选取其“恶”的一方面,从不同角度的丑来探寻波德莱尔之“恶”的美学意义。
一、残缺身体的奇特之美
波德莱尔之“恶”的意义丰富,而丑在美学范畴内作为“恶”的一个分支,它首先有着因残缺或是畸形而导致的丑陋之意。波德莱尔作为巴黎这座大城市中的“闲逛者”(le flâneur)④Walter Benjamin.Paris,capitale du XIXe siècle.Paris:Édition du Cerf,1997:42.,他深入人群里,从世界之最阴暗、最畸形的丑陋中搜集零零散散将其拼凑成最有积极力量的诗歌。
《小老太婆》(Les Petites Vieilles)是波德莱尔题献给雨果的诗歌,道尽了小老太婆这种畸形的人间残渣凄惨的命运,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残忍的美。诗句中不乏死亡意象的词语:“丑恶”“魔鬼”“棺木”等。诗歌开篇通过今昔对比,衬托出小老太婆们如今悲惨的丑模样:
这些丑八怪,也曾经是女人啊,
埃波宁,拉伊斯,她们弯腰,驼背,
曲身,爱她们吧!她们还是人啊!
穿着冰凉的布衣裙,破洞累累。⑤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70.下文中出自该书的引文均只夹注页码。
身为女人的她们,或许曾妖娆多姿、亭亭玉立、秀丽端庄,但在岁月和时代的腐蚀之下,她们的体态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她们变成了弯腰驼背的丑八怪;在生活的压榨之下,只能穿着用冰凉布料制成的破洞裙子。弯着腰、驼着背已是一幅凄楚的画面,而冰凉的、破了洞的裙子更显残酷,这些悲惨的丑态和小老太婆们孤苦的内心相衬,也与冷冰冰的现实世界相应!
——你们注意到许多老妇的棺木,
几乎和孩子的一样又小又轻?(171)
波德莱尔对丑陋的耕耘层层递进:小老太婆们不仅已是弓腰驼背,并且许多老妇的棺材如同孩童之棺般窄小,小老太婆们身材的微不足道更进一步影射了这恶毒社会的残忍与凉薄。孩童象征着新生,而棺木象征着死亡,这样的生死纠结无不衬托出一个历尽种种困苦,饱尝种种折磨的小老太婆的悲哀与可怜。然而在这样被社会百般磨折下:
她还能挺直了腰,骄傲而端庄,
贪婪地欣赏这雄赳赳的乐队,
她的眼有时睁开像老鹰一样,
大理石般的额头似等着月桂!(173)
无论裙子如何冷冰冰且破了洞,还是身材被碾压得如儿童般瘦弱,小老太婆们还能坚强地把腰挺直,无畏地穿梭在这浑浑噩噩的世界里,她们的心中充溢着反叛的力量,眼中宣泄出愤怒,她们要与这恶魔般的世界对抗下去。她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诗人在这些被边缘化的老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他与她们融为一体,礼赞在这个无情世界里艰难前行的英雄:
我看见你们的初恋绽出花朵,
我经历你们已逝的悲喜人生;
我宽广的心享受你们的罪孽!
我的灵魂闪耀着你们的德行!(174)
诗人没有直接鞭笞这个腐朽的社会,但他通过小老太婆残缺的丑陋体态、破旧的衣着等悲惨形象给世人以最恶毒的警醒,让世人知晓在这个煤气灯代替了蜡烛、钢笔尖替换了鹅毛笔的所谓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精神文明却是一滩死水。所谓的上流社会穷奢极侈、肆意挥霍,而步履蹒跚地行走在社会边缘的苦难者却连安宁的生活也不可得。
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中收录的部分诗歌是与《恶之花》一一对应的。其中《老妇人的绝望》(Le Désespoir de la vieille)就与《小老太婆》相呼应,同样以丑作为起始点,通过那位瘦小干瘪老妇人的可悲形象让众人领悟到人世间的可哀可叹:
有一位干瘪的小老太婆看见这个漂亮的小孩,感到满心欢喜,所有的人都善待他,都想讨他喜欢:这漂亮人儿,像她一样脆弱,小老太婆,也像他一样,没有牙齿,没有头发。
她走近他,想对他微笑一下,做出一副讨他喜欢的样子。
可是孩子却吓坏了,在善良衰弱的女人的抚爱下挣扎,尖叫声充满了整个屋子。
于是,善良的老太婆又退回到永久的孤独中去,在一个角落里哭,自语道:“啊!不幸的衰老的女性啊,讨人喜欢的年龄,哪怕是对于天真的人,已经过去啦;我们想要喜欢那些孩子,可我们却让他们害怕!⑥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郭宏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
诗歌的开篇,老妇人见到这位漂亮的孩子,心中充满喜悦,希望自己能向他表达爱意、与之亲近,然而字里行间的明快晓畅却加深了之后的遗憾与残缺,诗人通过孩童与老妇人的对衬让老太婆的丑陋跃然纸上:小孩的脆弱会让人心生呵护之情,他没有牙齿没有头发,但却依旧可爱,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可是老妇人的脆弱却是历经世间沧桑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掉光的牙齿与脱落的头发尽显其可怕的丑态。同样的脆弱、同样的没有牙齿和头发,孩子是美的象征,老妇人却是丑的代表,如此,美丑之间的天壤之别让这位人间残花的丑陋更加明显。因此,孩童被吓坏,“尖叫声充满了整个屋子”。这样的行为对于这位善良的妇人来讲是多么绝望与寒心!老妇人真挚的喜爱与小孩儿强烈的抗拒之间的鲜明比照无不渗透出老人的凄惨之境。她那慈母般善良的爱抚却因其丑陋的模样惹来一位尚未经历世事的孩童的厌弃,连这样单纯无邪的孩子都会被吓坏,更何况是那些灵魂被恶魔侵蚀的人呢!最终,可怜的妇人只有重回孤苦伶仃,独自一人感叹这世界的可怕与残忍。诗人对老妇人的怜悯之中既透露着对这个世界的冷嘲与唾弃,也再一次为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衰落敲响警钟,让世人在替老妇人感伤的同时,也深刻地领悟到这阴暗社会的冷漠与残忍。
与小老太婆命运相似的还有《七个老头子》(Les Sept Vieillards)中的老人:
突然,一个老人,黄黄的破衣裳
竟是模仿这多雨天空的颜色,
若不是他眼中闪烁着凶光,
真会引来雨点般落下的施舍,
在我眼前出现,仿佛他的眸子
在胆汁里浸过;目光冷若寒霜,
硬得像剑一般的一把长胡子,
支棱棱射向四方,犹太人一样。
他的背不驼,腰却弯了,脊椎骨
和腿形成一个直角分毫不差,
他的木棍也把他的外表补足,
竟使他的举止和笨拙的步伐
像残疾的走兽或三足犹太人。……(167—168)
“黄黄的破衣裳”、脊椎骨与腿已经形成一个90 度的完美直角、因为杵着木棍,“像残疾的走兽或三足犹太人”。这位老人破旧的衣着和凄惨的体态与小老太婆一样,他们损毁的身体都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腐朽与暴力中的畸形产物,是物质世界的牺牲品,也是波德莱尔眼中可以绽放光芒的丑陋艺术品。老人的眼睛似浸在“胆汁”中,胆汁本是由肝细胞分泌出的液体,味苦,呈黄绿色。此处的“胆汁”可转意为这世界的恶毒、老人所经历的痛苦与辛酸、心中所抱有的怨恨与愤怒。波德莱尔把在混混沌沌中颠簸的老人比作“犹太人”,犹太民族在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处于外族人的奴役之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流散、迁徙与漂泊中流浪着,他们曾经屡屡遭受其他民族的歧视与迫害,甚至被屠杀。波德莱尔眼前的这位老人正像犹太人一般在迫害与苦难中挣扎跋涉,漂泊不定。老人虽然腰不能挺直,但眼中的“凶光”与硬得像剑一般的长胡子却强烈而坚定地展现出这位孤苦的灵魂在焦虑、绝望与沮丧中对这个世界的敌意和一种不甘心沦落于此的反抗与攻击。
无论是小老太婆的支离破碎、老妇人的可怖模样、还是老头子的拙劣丑陋,都是他们以一己之身支撑起这败坏尘世所带来的痛苦而留下的伤痕,他们的畸形丑态之下都隐藏着一种刻毒的美,这种美与他们的丑成一种可怕的正比。模样越是可怜、越是狼狈、越是可怖,越是可以从中发掘出令人震惊的美。这种美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警觉与清醒、是从心底呐喊出的与世界之恶进行反抗的勇气与力量、是一种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佝身前行的英雄主义。这世界带给老妇人与老头子的残酷与狠毒,让世人们从中认清什么是真正的恶、什么是真正的善。这何尝不是一种以丑收获美、以恶来获取善的方式呢?这便是波德莱尔通过他那炼金术士的神奇力量在邪恶中开出的花朵。《小老太婆》 与《七个老头子》 都是波德莱尔赠予雨果的诗歌,虽然在字词层面多有模仿雨果之处,然而诗人的内在精神早有从传统迈向新颖之意。雨果在回信中对波德莱尔化丑为美的艺术才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你把《七个老头》和《小老太婆》赠我,我对此表示感谢。当你写这些惊人的诗句时,你在做什么呢?你在做什么呢?你在迈动脚步。你在向前行进。你赋予艺术的天空一种莫名的令人恐怖的光芒。你在创造一种新的战栗!……先生,你拥有高贵的性灵和慷慨的心地。你写出的东西是深刻的而且往往是庄严的。你热爱美。让我们紧紧握手。⑦转引自刘波.《波德莱尔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48.
雨果在这封信中接连用了“惊人的”“令人恐怖的”“新的战栗”这样从灵魂深处拨动人心弦的词语,发出对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独特与创新的最高赞美。波德莱尔令人惊叹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以平静的情绪去拾起散落在街道边缘的苦难者,以冷静的态度和冷酷的用词与感伤拉远距离:老太婆的棺木与小孩子的一样“又小又轻”;老妇人像小孩一样,“没有牙齿,没有头发”;老头子的脊椎骨和腿成一个直角,他在表达上故意为之的冷峻与淡然实际上正是他所称之为的“艺术的奇妙特权”,诗人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对此做出这样的评价:“在表现最强烈激情和最惨烈痛苦时,也保持着高度冷静的心绪,这种冷静常常接近冷酷,有时候像冰一样寒冷刺骨。”⑧Paul Verlaine.Œuvres en prose complètes.Paris:Gallimard,1972:608.此处系作者所译。并且,他也为波德莱尔这种不为至深苦楚而动情的冷静处理发出如此赞叹:“相当戏谑,相当咄咄逼人,相当残酷——相当超卓。”⑨Ibid.的确,波德莱尔正是通过这种异乎寻常的冷漠方式来强化他对苦难儿的深切恻隐,以淡漠的关照凸显出人世间的极端不公,最终在这极度悲情的世界中领悟最为彻底的清醒。
二、丑恶中的精神之花
波德莱尔笔下的丑亦包含着令人惊怕的丑恶之态,《恶之花》中最能表现波德莱尔经艺术将丑恶转化为美的即《腐尸》(Une charogne)一诗。这首诗是写给情人让娜·杜瓦尔(Jeanne Duval)的,诗中的“腐尸”一般被认为是一具狗的尸体。波德莱尔的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用美好的事物直抒爱意,他将一具丑恶的、并且无论在视觉还是嗅觉方面都令世人惊骇且作呕的狗尸视作奇珍异宝,对它的丑发出最深刻的礼赞,最终挖掘出一种永恒的美。这具隐秘在小路拐角处腐烂的狗尸正是诗人心意中那件最冷漠、最可怕的艺术品:
……
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
在碎石的床上横卧,
仿佛淫荡的女人,把两腿高抬,
热乎乎地冒着毒气,
她懒洋洋地,恬不知耻地敞开
那臭气熏天的肚子。
……
天空凝视着,这尸体真是绝妙,
像花朵一样地开放。
臭气那样强烈,你觉得就要
昏厥晕倒在草地上。
腐败的肚子上苍蝇嗡嗡聚集,
黑压压一大群蛆虫
爬出来,好像一股黏稠的液体,
顺着活的皮囊流动。
……
——而将来您也会像这垃圾一样,
像这恶臭可怖可惊,
我眼睛的星辰,我天性的太阳,
您,我的天使和激情!
是的,您将如此,哦优美之女王,
领过临终圣礼之后,
当您步入草底和花下的辰光,
在累累白骨间腐朽。
那时,我的美人啊,告诉那些蛆,
接吻似地把您啃噬:
我的爱虽已解体,但我却记住,
其形式和神圣本质!(55—57)
诗歌的开篇就表明这具腐尸的丑陋,这是诗人视觉所感受而得之。随之,视觉之感传递至人的内心深处,让人从心理上对这具腐尸生出厌恶之情,因此,这具横躺在街角的尸体具有十足的丑恶之性。除此之外,“臭气熏天”“臭气那样强烈”通过嗅觉的体验进一步印证了这尸体之丑、之可怖。不仅如此,这具尸体的肚子上还聚满苍蝇,肚中爬出“黑压压一大群蛆虫”,可以想象出这是一幅多么令人作呕的画面,仿佛带来真真实实的两眼发黑且胃不舒适之感。这样的镜头是视觉、嗅觉与心灵之间关于丑恶的“应和”(correspondances)⑩Charles Baudelaire.Œuvres complètes I,op.cit.,p.11.:所见的丑恶之物唤起内心的厌恶之感,尸体的丑态通向内心的憎恶;所嗅的腐臭激起内心的波澜,腐尸的恶臭同样通往心中的惊恶。这种感觉的互通就是心理学上所称的“联觉”现象,也就是批评家们通常所说的“通感”(synesthésie)⑪Victor Segalen. Les Synesthésies et l’école symboliste.Paris:Mercure de France,1902:7.。从心理学和精神学的角度来讲,视觉与嗅觉这种特殊经验所引起的人的精神状态之变化并非是一种内心之感的错乱,而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波德莱尔曾在《理查·瓦格纳和〈汤豪舍〉在巴黎》(Richard Wagner et Tannhäuser à Paris)中表达了其万物皆可合一的意思:
不经过分析和比较地进行先验的推论,在这里不会是可笑的,因为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声音不能暗示色彩,色彩不能使人唤起旋律,声音和色彩不适合传达观念;自从上帝说世界是一个复杂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之日起,万物就一直通过相互间的类似在彼此表达着。⑫转引自刘波,前揭书,第26 页。
波德莱尔在评法国女诗人玛斯丽娜·代博尔德-瓦尔莫(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1786—1859)时写道:“我总是喜欢在外部的可见的自然中寻找例子和比喻来说明精神上的享受和印象。”⑬波德莱尔,前揭书,第103 页。他认为唯有横向应和与纵向应和相结合才能达成完美的艺术效果。此处提及的“声音”和“色彩”即是听觉与视觉在感官层面的相互作用,构成横向应和,并且最终上升至一种“观念”(即所感)的转达,形成纵向应和。同样,在《腐尸》这首诗中,视觉、嗅觉与观念这三重经验的横向与纵向应和让诗人得以歌唱精神与感官交错的狂热,也令世人对这件可怕艺术品之“恶”刻骨铭心。然而在波德莱尔的妙笔之下,腐朽可转为神奇。在诗歌的最后三节突然笔锋一转,诗人将自己的情人比作这具可怖可惊的尸体,虽然“您也会像这垃圾一样”,但终究“您”是“眼睛的星辰”“天性的太阳”“我的天使和激情”“优美之女王”“美人”。这腐烂的、让人惧怕且作呕的尸体竟然变作“我”的星辰与太阳,“我”的天使与女王。星辰或指辉煌的灯光,宛若照亮夜空的星星,象征着黑暗中的力量与希望;而太阳有着火热、明亮的特质,象征着永恒、光明、温暖与希望。星辰和太阳都是明亮与希望的代名词,能为“我”指引方向。天使代表着神性与智慧,通常被视作灵魂的指引者,它既不会衰老也不会死去,因此象征着永恒与不朽。“女王”带着霸气、力量与指引之意,充满着征服感,可以见出情人让娜在诗人生活中扮演着灯塔的角色。而最终的“美人”一词,此处的美绝不是面容的美丽,而是能够在腐朽与败坏中给予诗人积极力量、希望与永恒的精神之光。爱人的身体终究会变作这恶臭的腐尸一般,阴森恐怖、令人作呕。但这具腐臭的尸体又有何妨,只不过是生命形态的一种转化,而深深烙在诗人心底的是一切具有精神意义或是能够将其精神注入其中的事物,是指引未来的星辰,是带给人希望与光明的太阳,是灵魂的永存。此外,腐烂的尸体表明死亡到来已久。死亡在医学上意指心跳停止、呼吸停止以及脑死亡;宗教认为死亡或是新的轮回的起点或是对永生的期盼;从哲学上讲,死亡是维持生命存活系统属性的丧失与永久性终止。然而,心跳的停止、属性的丧失并不代表精神的终止,人的精神拥有超越生命、永不消亡的力量,恰如这具腐尸之意,哪怕爱人原本丰盈的肉体最终变成阴森森白骨也无妨,因为肉体的死亡开启了精神的永生,爱人会化作“星辰”与“太阳”照亮未知之途,如天使般永久守候。波德莱尔爱之深切的并非是情人的肉体,而是她那不朽的灵魂。诗人将自己的精神之力灌注在这丑恶的腐尸上,让爱的光芒成为永恒,而这恒久之爱便是波德莱尔心中的“黄金”。
诗歌《被杀的女人》(Une martyre)中的那具无头尸体与《腐尸》中这具腐烂的狗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具无头的尸体,鲜血流成河,
流淌在干渴的枕上,
枕布狂饮着鲜红的流动的血,
仿佛那干旱的草场。
就仿佛从黑暗中产生的幻象,
让我们目不能斜视,
她的头,一大团浓发又黑又长,
还戴着珍贵的首饰,
……
有罪的爱情,各种奇特的狂欢,
充满了恶毒的亲吻,
一群魔鬼也高高兴兴地消遣,
在窗帘折褶里浮动;
……
你丈夫跑遍全世界,你不朽的形
守护着熟睡了的他,
而他也将会像你一样地忠诚
直到死也不会变化。(215—217)
这具无头女尸同样以其惨不忍睹的丑模样令世人畏惧、作呕想吐,像那具狗尸被苍蝇、蛆虫垂涎一样被魔鬼觊觎,而最终腐烂的肉体在艺术的作用之下化作永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传递出女子与丈夫之间恒久不朽的忠诚之爱。
波德莱尔善于发掘隐藏在庸常生活与事物中的诗意因素,在抽空其现实价值的同时将自身的精神价值灌注其中,从而把物的价值置换为精神的价值。从更深层次来讲,有形的肉体可以是物质世界的象征,诗人在诉说肉体与精神之爱的同时也暗示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参差:物质世界必然是人类生存之本,但那些渴望以物质的进步去弥补精神之丧失的举动必然是得不偿失的。在波德莱尔生活的时代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物欲横流,而人心的冷漠无情、世人的灾难重重正是精神文明沦丧的恶果,只有精神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世间的苦难才可被救赎。诗人将自身积极的灵性诉求付诸丑恶的腐尸上,通过无形的灵与有形的肉之鲜明对比,发出对精神之光的强烈呼唤与渴盼,因为在他看来,物质世界终有一天会如人的肉体一般毁于一旦,但精神的产物却不会因物质的毁灭而消失殆尽,它如诗人的无形之爱一般永不解体,它将抚慰人间疾苦,永远照亮前行之路。最终丑非丑,死亡非死亡,丑恶中开出了精神之花。
结语
从美学的角度来诠释,街角腐烂恶臭的腐尸或是血流成河的尸体以丑陋、令人作呕、恐惧彰显其恶,但波德莱尔式的丑恶并不与美相排斥,腐朽化为神奇。他提倡用“恶”来对抗发达资本主义时期所谓的进步与虚幻文明,让艳丽的花朵在罪恶或丑恶中自豪地盛开。波德莱尔笔下的丑恶自有其高贵与惊艳之处,他拥有让暗淡无光的丑恶变得熠熠生辉的能力。波德莱尔从肉体的腐烂中所提取出的精神之爱长存,是他化丑为美,由消极向积极过渡,也是他从转瞬即逝中夺取永恒的见证。作为大城市的“闲逛者”,波德莱尔痛恨一切天然存在的事物,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Le Peintre de la vie moderne)中谈道:“看一看、分析一下所有自然的东西以及纯粹的自然人的所有行动和欲望吧,你们除了可怕的东西之外什么也发现不了。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理性和算计的产物。”⑭波德莱尔.《美学珍玩》.郭宏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431.这里提到的“理性”即是波德莱尔通过其独到的思维活动对时代和人性所抱有的深刻见解,而“算计”则是指波德莱尔那新颖震撼的艺术改良。的确,他从“恶”之消极因素中提取出了令人震撼的积极要素:踉踉跄跄穿行在城市中的小老太婆和老头子的畸形之丑在波德莱尔的艺术点睛之后转化为了一种在悲丧境地之中最为清醒的觉悟,以及最为乐观、最为动人的精神抗争;街道拐角处散发着恶臭的腐烂尸体在波德莱尔精神之光的照耀下上升为神圣本质的永存。这些通过精神作用且又最终在精神上所捕获的平静与永恒就是波德莱尔美学思想中之“恶”所散发出的积极之美。